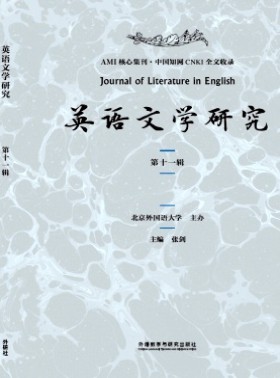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研究的涵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