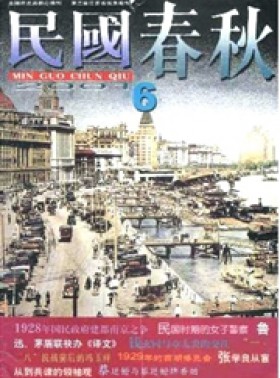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谈葛亮《北鸢》的民国情怀和文化寄寓,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葛亮的长篇小说《北鸢》突破了一般对传统民国历史战争的书写,以男女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以卢、冯两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于家庭人伦中见浓浓孝亲质性、在想象中展脉脉民间温情,并运用传统美学精神——寄寓事象手法来表达对民国情怀、传统文化的追忆怀想,让我们徜徉在蕴藏着民国风情和传统文化想象的画卷中。
关键词:民国情怀;家风伦理;文化寄寓
葛亮的长篇小说《北鸢》以温润典雅的工笔被誉为“新古典主义小说的定音之作”,作者将历史情怀与民间想象寄托于家庭与日常叙事中,将人性深处的善良和诗意永存的民间放置于传奇色彩的民国中,熔铸于生命肌理之中,实现了民国景象从传奇向生活化的转变,缝合了当代中国民间文化认同与儒家传统价值承续之间的断裂之处,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文学想象时空场域,并化为“温润风骨”流淌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构筑出新时期小说的生命伦理诗学。
1以家为基:家本位立场的伦理张力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可以说是以“伦理本位”的,而伦理又始于家庭,家庭便是伦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家庭本位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精神实质,对此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1]32孟子在直接继承孔子的伦理思想上,提出更为具体的人际伦理观,“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33这五种人伦关系中,家庭伦理占了重要地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家国同构”入世精神的基础。个人的修养得益于家庭内部氛围,所有波浪涟漪都围绕家庭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而去,最终又返回来养育这个本源。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来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2]。《北鸢》以家庭为圆点向四周所散发的伦理规范,进而影响下一代乃至整体社会风范,延续传统文化中道义责任、平等互爱等精神内核,因而这种孝亲为本的家风伦理极大程度彰显出其历史叙述旨趣:“因为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生活的常态之中,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反高潮的运作。”[3]足见出其家庭伦理本位的基调。葛亮长篇小说《北鸢》完稿之际,作者自陈“笔喻七载,尘埃落定”。《北鸢》突破了一般对传统民国历史战争的书写,它以男女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以卢、冯两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于家庭人伦中见浓浓孝亲质性、在想象中展脉脉民间温情,并运用传统美学精神——寄寓事象手法来表达对民国情怀、传统文化的追忆怀想。亚圣孟家后代昭如用小说的语言说,是“先天的颟顸,使得她少了许多女子的计算与琐碎”,她天性宽厚,善待家里的每一个人;丈夫卢家睦虽为商人,但坚持重诚守义,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人相敬如宾、夫义妻贤,这为儿子卢文笙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文笙延续着父母的仁爱诚信,“以静制动”,以不变之心性与智慧应万变之世间沉浮,他温雅智慧的人格气质正是作者心中理想的中国人象。葛亮将家庭和谐文化的熏陶作为涵养卢文笙成长的精神来源,满怀温情地描述了他在时代浪潮下对家风伦理的践行过程,赋予了这个家庭一个时代的精神。平等、诚信、仁义等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因子落在普通家庭,映射家庭观念,支撑着家庭的发展,在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那不变的伦理情怀,呈现的是古典精神的涵养。作者从家庭本位出发,找寻君子外在价值呈现的第一层要义,并在新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将建构民族国家的叙事目的转换为对当下家庭伦理的情感认同长篇小说《北鸢》中,在感受到父母给他深沉的爱后,卢文笙也同样反馈给父母以最尽心的孝。全书儒风弥漫,以小家之面映射社会群像,让家镶嵌在国家的链条中,实现“庙堂”与“民间”的对接;又从社会群像管窥小家之风,使孝亲伦理得以延续和发展,使君子有一个更为宁静温煦的成长环境,这样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远阔的精神世界。
2史蕴诗心:想象与记忆
《北鸢》没有如绮似锦的华丽,没有寒花秋叶的冷峻,它以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真挚感情贴近记忆中的历史,用文学想象来表现历史记忆。葛亮努力赋予民间以诗意的栖居之所,传递给读者对美好社会伦理的守望。葛亮在两大家族中精心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带有诗性与梦幻色彩。这种采用时间性较为隐蔽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某些恒久不变的价值的写作方式,被王德威视为“想象中国的重要方法”。他认为国家的建立、改革和成长,离不开献血兵戎这种政治律动,而国史的编撰、国格的塑造、国魂的唤醒和国体的凝聚,这都离不开文学虚构与想象的必要,这正是我们叙述‘中国’、想象‘中国’的开端[4]。《北鸢》的民国想象除了体现在民国场域的构建,还包括民国历史背景、习俗场景等氛围的营造。以儒家“仁爱”“诚信”等传统文化来抵达对民国的想象,可以称之为民国风骨,表达了作者对民国文化的想象和传统精神的追求。孟昭如开篇即收养了一位因家境贫寒被母亲卖掉的孩子,在自己落难时也慷慨救助下人小荷;丈夫卢家睦虽为商人但重义轻利,曾说到:“自古以为,商贾不为重视,为何?因别人觉得咱们做事不正路、为人不正义。但是我们自个的心术要格外端正,不然就是我们看不起自己了。”[5]在民国十一年豫鲁大旱之时,他尊承“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设棚赈灾,发放主食“炉面”,不仅让灾民免受饥饿,更消解了他们的思乡之苦;儿子卢文笙在时风已变的商业浪潮中依然践行自己的生意准则,甚至倾囊相助濒临破产的姚永安。他们在民国历史浪潮的裹夹下依然谦薄地坚守属于自己的天地,在旧传统社会向新社会过渡时始终坚守仁爱精神,承续着孔孟儒家向仁向善的传统,正是一个时代风骨的象征。作者将他们放置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民国,在营造古典场景的同时开启了现代性时间,这里新旧碰撞交缠,时间让他们生命消逝但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我们看到了那无法被遮蔽的精神价值,使“民国”脱离了符号意义,而是带有可触摸的人格风骨和被浸染的生命温度,从而到达中国文化之根柢。带有理想状态的民国风骨在传统文化呈式微状的情况下孕育而出,正因其“脱节”于时代,带有儒家文化的风流余韵,所以人们才想要去触碰理想的尾巴,留下关于民国文化的回忆。作者对民国风骨爱的深沉,所以他并没有把传统文化精神仅仅落实到孔孟后裔人的身上,而是把这种精神弥散到小说每一个角落。冯仁桢的曾祖父冯大列发迹后,时刻提醒自己莫忘微时,光绪二十四年,襄淮一带遭遇水灾之时,他出资万金,买米、豆饼和杂粮等物救济灾民,并修筑黄河大坝,重修鼓楼,为村民提供了巨大便利;风筝手艺人龙师傅因与卢家睦约定每年生日送儿子一个虎头风筝,没想到一坚守承诺便是几十年。儒家的行善好义精神在葛亮笔下绵延不绝,他们的身上都寄寓着作者所推崇的民国想象,更是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投射。作者有意避免政治意识形态,淡化民国时期的丑陋,去丑存美诱发读者对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将美好的想象寄托在连着大地、不会失去主心骨的风筝中,高高扬起,带有鲜明的文化指向性和生存指向性。《北鸢》写出了儒家文化的时代新变,这里亲情、友情和爱情中的暖意抵消了原有观念中民国的冰冷无情,而处处展现想象民间的诗意栖所,而这种维系家国命运和人心向度的儒家精神,落实在每一位小人物身上,使民国不再只是留在纸上的镜像,不再是易消逝的无根浮萍,而是带有鲜活的生命温情,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民间真精神”,深刻体现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作者让儒家平等、孝道等家风伦理留在纸上,留在对民国的回忆中,投射出对民国文化的想象与记忆,演绎了绚丽多姿又充满温情的现代新儒风。
3寄寓事象:传统美学精神审视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重视在艺术创造过程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相互融合和作用,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深刻阐释了构思和创作中情与物、思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关系,不仅肯定了审美主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能动性,也道出了审美心理的客观来源。另外还有“寓理于情说”“思与境偕说”“以形传神说”等等,都充分表现了主体对艺术审美规律中寄情与物、寄寓事象的理解和运用。而所谓之“事象”,乃是创作主体通过内心与外在世界在头脑中完成互动交会、经去芜存菁、去粗取精后在意识中留下印记,并透过文字将所想所感所悟落实于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情意与客观物象。而研究“事象”的寄寓过程便是通过破解在小说文本中具有符号、象征性质的“着事之象”,进而探求主体附加在“物象”之上的深层次的、多重意蕴的过程,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内在旨韵。具有新古韵特点的长篇小说《北鸢》,化用传统符号——风筝来链接故事情节,达到含蓄蕴藉、传情达意、传递个体意旨的深层效果。首先小说中的风筝具有抒情串针的功能。与卢文笙交流画的时候,毛克俞引用徐渭在《墨荷图》中所写诗句:“拂拂红香满镜湖,采莲人静月明孤。”这不仅营造出一种画意美感的意境氛围,也借孤高傲洁的一轮明月暗含着对保持高尚道德情操的毛克俞的赞誉。看似在赏画,但这幅寄寓作者理想化身、赋予情感体验的画饱含了对品质高洁的君子人格的赞扬,作者以物象的瞬间感触来制造情境和情感的永恒,使得审美观照落在了客观事象身上,与审美理想融合为一。风筝还隐喻着人生哲理。主人公卢文笙在抓周时被旁人赞誉“无欲则刚,目无俗物”,而其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为“一叶知秋”;在老师毛克俞图绘风筝的课堂上,卢文笙将图题名为“命悬一线”,学生们建议取“扶摇直上”,而毛老师最终定名为“一线生机”,受文笙放风筝学问的启发,雅各的人生哲学是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他长大后更是端庄文弱,谦谦有礼,但当国军伤员面临被敌人抓捕之时,他借助风筝为叶师娘通风报信,帮助伤员安全转移;在天津求学漫漫时,他深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影响,心向延安,毅然弃文从军,帮助工人阶级队伍实现突围。卢文笙从衣食无忧的商家独子、到战争爆发后发出“入寇未灭,何以家为”的深思、最后到命悬一线之际领悟“生与死,原来是战场上最小的事。谁也不在意,也无法在意”。文笙的一生恰如一只随风飞扬的空中纸鸢,虽命悬一线,也葆有一线生机,暗示着故事中人物如风筝一般的多舛命运。葛亮从风筝特点入手,它适风飞行、立高望远、随风沉浮,他便将这样一种哲学处事隐喻地寄托在风筝中,让我们感受到风筝与生命的某种内在联系。作者用冷静、理智的叙事语调,表面上他追求的是文学中的“理趣”,背后他是在小说中不断申诉他的理想——传承寄寓事象的传统写作手法,用含蓄、隐喻的功能给读者以生存之思。他活用传统文化符号,赋予风筝以抒发主体情感、寄寓生命之思等丰富内涵,将借物喻理、含蓄蕴藉的传统写作手法藏匿在深层的历史文化中、不忘修洁的生命价值中。正如陈思和在《北鸢》序言中所论述的,它重新审视着维系我们民族文化永不熄灭的“民心”,它的写作手法和情感意蕴都真正做到了“回到中国文化立场”。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概念范畴、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重视审美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强调在审美过程中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的渗透与融合,强调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情与理、神与形、思与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与传统文化和审美经验的特点相联通。这些客观物象本没有思维所属,但在被作者所感知后,能以其所要禀赋、传达的文化意蕴而赋予其多重涵义,借用风筝来寄托作者所欲传达之“理”与寄托之“情”,皆成为传统美学精神审视的栖身所,而这与作者想昭明的传统文化美学精神和坚守道德良知、顺势而为的文化品质相契合。寄寓事象、含蓄慰藉的写作手法,揭示了艺术形象和审美意象所构成的美学法则,使其与文化人格存在契合点,扩大了原属于本物的存在意义,赋予其超越本身的多重意义将审美经验和审美观照融合为一,转化为超越性的人生境界且意义深远。《北鸢》以中华文化质素为本,以工笔画般的细腻淡描之笔写浓浓深情,用文学想象编织文化回忆,勾勒出一个充满“人情人味”的理想世界。作者从历史浩荡、生存之悲出发,借家庭伦理本位、文化想象追忆和传统美学精神缓缓展开历史叙述,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为书写对象,以时间的“变”烘托文化价值的“不变”,将民国情怀与文化情愫放于历史场域中,体现了作者在经过文化祛魅之旅后重返民间、维系精神信仰的文学创造,构成《北鸢》历史叙述的温情民间底色,打通文学与历史的壁垒,以诗心与文心表现历史,为我们呈现出温情化、生活化又具美学化的民国场域。
作者:郗琪 单位:长治学院物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