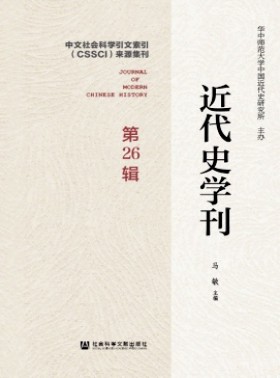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近代汉语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
一 汉语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但各个时期文献资料的数量和性质并不是相同的,反映在程度副词上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文献中程度副词的使用状况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中古汉语时期。此期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两类。这两种文献是不同质的,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不少显著性的成果,如朱庆之[1][2][3]、胡敕瑞[4]、陈秀兰[5][6][7]等。在研究汉语特别是中古汉语的时候,一方面应该把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全面准确;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二者的比较研究,因为通过比较,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历时的变化,还可以辨清两种语料语言上的差异。程度副词与人类的认知行为关系密切,能够敏锐地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中古汉语时期的若干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作穷尽式统计分析①,以程度副词为切入点,考察这两类文献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并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 比较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程度副词,可以得到六种不同的类别:1.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2.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3.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4.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5.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6.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以下分别叙述。 (一)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 中古汉语继承了为数不少的上古汉语程度副词,其中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都使用的程度副词很多,如“最、至、极、最为、绝;太;甚、大、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益、弥、更、愈、滋、加;小、少”等②,它们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又不尽相同。其中,“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词是上古汉语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中古以后继续广泛使用。如:(1)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论衡•言毒》)(2)时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极甜,若压取汁,还灌甘蔗树,甘美必甚,得胜于彼。”(《百喻经》,4∕545b)(3)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汉书•成帝纪》)(4)太子睹妻哀恸尤甚。(《六度集经》,3∕10a)除“更;小”外,上古时期使用不多的程度副词,如“最为、绝;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更、加”等,在中古汉语仍保持较低的使用频率。如:(5)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世说新语•德行》)(6)汝等恭肃净施饭食,具设众味当令绝美。(《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15∕452a)(7)诚岁余以来,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然,必置沟壑。(《汉书•元后传》)(8)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众人中犹如日月,倍好于常。王意悚然加敬问曰:“有何道德?炳然有异。”(《法句譬喻经》,4/585b) (二)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 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主要有“穷;已;孔、偏、丕、殊大、重;愈益、尤益、兹益;差2、颇2、略”等③。此类程度副词在上古时期的使用频率不高,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古汉语之中。其中,程度副词“穷;偏、殊大、重;愈益、尤益、兹益;差2、颇2、略”等使用不多,虽沿用到近代汉语之中,但仍不常见。如:(11)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洛阳伽蓝记•城西•大觉寺》)(12)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汉书•苏建传》)(13)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汉书•项籍传》)(14)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已;孔、丕”等词主要见于上古汉语,中古以后使用频率下降,近代汉语以后则基本消亡。如:(15)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三国志•魏书•荀攸传》)(16)神监孔昭,嘉是柔牷。(《宋书•乐志二》)(17)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南齐书•乐志》) (三)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 这类程度副词仅“益大”一词,它的使用频率不高,近代汉语只用于变文。如:(18)七日既满,益大欢喜。(《撰集百缘经》,4∕208a)(19)魔见三女还,皆成老母,益大忿怒。(《修行本起经》,3∕471a) (四)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较多,主要有“极为;过;颇1、特、何、甚为、深自、深为、痛;转、更倍、益更、益加、转更、倍加;微、稍稍”等。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不均,其中,以“极为;过;颇1、特、何、甚为;转;微”等词的使用为常,且沿用至近代汉语之中。如:(20)家业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南齐书•褚炫传》)(21)复闻一臣道,外沙门被杀者多,所有者少,极为懊恼,闷绝躄地。(《阿育王传》,50∕107c)(22)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金匮要略方论》第六)(23)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尝微悔。吾以许焉,尔无违矣。”(《六度集经》,3∕9c)“深自、深为;益更、益加、转更、倍加;稍稍”等词在两种文献中得使用频率均不高,近代以后仍继续使用。如:(24)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恸,绝而复续。(《宋书•张邵传》)(25)今者威颜,益更鲜泽。(《撰集百缘经》,4∕217a)(26)吾甚怜爱,倍加开奖。(《颜氏家训•勉学》)(27)王闻语已生欢喜之心,倍加恭敬,作礼而去。(《阿育王传》,50∕128c)“痛;更倍”等词在两种文献中使用均不多,近代以后消失。如:(28)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书•食货志》)(29)已身中更苦痛剧。(《漏分布经》,1∕853b)(30)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痼,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更倍发热……热在里,结在膀胱也。(《金匮要略方论》第二十一)(31)虽有生死,所更倍好。(《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14/12a)#p#分页标题#e# (五)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颇多,主要有“第一、最差、至为;伤、太伤;雅、笃、正、差1、精、酷、不胜、奇、独、全、尤为、横、盛自、尤绝、殊自、痛自、雅自;倍、稍益、弥复、稍更、愈自、更加、更愈、尤加、益复、益自、愈加、愈甚;稍、粗、多少2、略小、稍少、稍小、少小、小小”。以上词语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不一,其中“至为;差1、精、酷、不胜、奇、全、尤为;倍、愈自、更加、尤加、愈加;稍、粗、多少2、略小”等词,延续到近代汉语之中。如:(32)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世说新语•简傲》)(33)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宋书•本纪•武帝上》)(34)至兄弟尤为叨窃,临海频烦二郡,谦亦越进清阶,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阖棺矣。(《宋书•王微传》)(35)家无储积,无绢为衾,上闻之,愈加惋惜。(《南齐书•萧赤斧传》)“第一、最差;伤、太伤;雅、笃、正、独、横、盛自、尤绝、殊自、痛自、雅自;稍益、弥复、稍更、更愈、益复、益自、愈甚;稍少、稍小、少小、小小”等词,仅在中古时期使用,近代以后消失,它们反映了中土文献在程度副词使用上的一些特征。如:(36)收待霜降。伤早黄烂,伤晚黑涩。(《齐民要术•种葵》)(37)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汉书•杨敞传》)(38)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南齐书•文惠太子传》)(39)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六)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有“极大、极甚、最大、最极、最是;大甚;转倍、倍复、倍更、倍益、更复、更益、甚倍”等。这些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均不高,且仅见于佛经文献,是具有佛经语言特色的程度副词,如:(40)悉见世间勤苦者,尔时极大愍伤。(《道行般若经》,8∕462c)(41)而彼夫人,生一太子,极甚端正。(《佛本行集经》,3∕770b)(42)若有菩萨闻是三昧信乐者,其福转倍多。(《般舟三昧经》,13∕907b)(43)若令学若为读,其福倍益多,何以故?(又,8∕437a)以上词语除“最是、极甚”外,其它成员均在近代以后消失。 三 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是不同质的,它们的语言面貌不尽相同,反映在程度副词的使用上就会有同有异。二者相同的部分呈现了中古程度副词系统的基本特征,体现出中古程度副词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不同之处则反映了两种语料性质的不同,从而折射出二者在历时演变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两种语料口语性程度的强弱。总体来看,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主要受到使用频率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使用频率 频率的高低是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使用情况的决定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使用频率是词语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其使用范围自然就广;相反地,其使用范围就小。程度副词在中古汉语的使用情况也是这样。 1.使用频率高的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均有使用。中古时期使用频率高的程度副词,既有上古汉语已经广泛使用的成员,如“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也有上古时期出现而在中古发展壮大的成员,如“更;小”等。它们在两种文献中均有不俗的表现,是中古时期程度副词系统的主要成员和中坚力量,代表了中古汉语程度副词的基本特征。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在这些词语的使用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在两种文献中基本一致。 2.使用频率低的程度副词常常用于一种文献之中。使用频率低的程度副词或仅见于中土文献之中;或仅见于汉译佛经之中。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自身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程度副词自身的特点所致。一些继承上古汉语而来的程度副词,其生命力不强,它们或者使用频率较低,或者是处于衰落过程之中,因此它们往往只出现某一种文献之中;一批中古新兴程度副词,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不高,近代汉语以后逐渐消失。因此,它们是具有中古特色的一批词。 (二)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是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使用情况的又一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的被较多地使用,处于衰落过程中得程度副词往往被较少使用。由于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自身口语性的差异,因此处于不同阶段的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差别比较明显。 1.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被较多地使用。汉译佛经的口语性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多用于汉译佛经之中,如“更”。程度副词“更”在先秦时期已有使用,但数量不多,中古以后发展迅速。其特征是时代越晚,“更”的使用越频繁,如《史记》3次,《汉书》4次,《三国志》15次,《世说新语》6次,《南齐书》8次。以上是中土文献,“更”在汉译佛经之中使用更多,如在《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佛本行集经》中分别使用5次、14次、14次。可见,在两种文献之中,“更”都获得了较大地发展。 2.处于衰落过程的程度副词多用于中土文献。处于衰落过程的程度副词多用于中土文献,而少见于佛经文献,如“愈、弥、益、滋”等。它们的衰落与“更”的大量使用形成鲜明对照。“愈、弥、益、滋”等词在先秦已经广泛使用,在中土文献中仍较多,使用频率依然不少于“更”,特别是“益”和“愈”。不过,“更”在翻译佛经中的使用频率却远远高于“愈、弥、益、滋”等词,如“更”在《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佛本行集经》中都有使用,而“愈、弥、益、滋”在此三部文献均无用例。#p#分页标题#e# 3.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中单音词、复音词的分布不同。复音化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程度副词也是这样。上古时期复音程度副词已经出现,但为数不多,在词汇系统中所占比重不高,沿用到中古汉语之中的复音词很少,它们在两种文献均有使用,差异不明显。中古新兴程度副词的有单音词和复音词之分,复音词的数量较上古有大幅增加,在词汇中比例显著增高,而且单音词、复音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分布不同。其中,不少单音词仅见于中土文献;而复音词较常用于汉译佛经,特别是仅见于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均为复音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在语言使用的差异。 (三)原因解释 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的使用存在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文献并不是同质的,对语言真实面貌的反映不尽相同。一般认为,汉代以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开始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古语料的语言成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正如汪维辉先生所指出的:“综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典籍,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反映口语的程度不太高;二是口语成分常常和文言成分交织在一起。因此语料的语言成分较为复杂。”[8](P17)正统的诗文、史书、某些文人著述等大都很少或者几乎不反映口语,口语性较差。而翻译佛经、小说、民歌等语料又较多地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性成分,相应地它们反映口语的程度就较高。 对于程度副词而言,一方面是汉译佛经主要以口头宣讲的形式传播,它的口语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它必然首先选择那些口头常用的、人们熟悉的程度副词,而那些日常少见、渐趋消亡甚至带有仿古色彩的程度副词则少用或不用;另一方面,中土文献自身的情况也很复杂,既有《世说新语》这样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也有史书等口语性稍弱的语料,因此中土文献中既有使用频率很高的程度副词,也有一些沿用上古而来或中古新兴、使用频率不高或渐趋衰微的程度副词。 新兴程度副词的结构形式及发展趋势在两种文献中有不同的表现。不少中古新兴的单音程度副词只见于中土文献,不见于佛经。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可能与佛经翻译者的汉语水平有关。现有材料表明,除严佛调、康孟详外④,对于其它佛经翻译者来说,汉语都不是他们的母语,汉语是他们的成年之后习得的,他们的汉语水平肯定不如汉本土士大夫那么纯正和地道,因此他们多沿用那些上古使用频率很高的程度副词,而较少采用那些新兴的程度副词。复音化是汉语发展的总体趋势,在这种大环境下,程度副词的复音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佛经还是中土文献都出现了不少复音程度副词。 在复音化过程中,音节节奏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为了适应音节节奏而将两个或几个单音程度副词组合起来,这种现象中土文献中有,而汉译佛经中更加普遍。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变体,佛经的文体形式很特别,“一方面讲求句子的节拍字数,另一方面却不像传统韵文那样讲求押韵,通常为四字一大顿,两字一小顿”[2],这种特殊文体的需要,决定了佛经对复音词的需求是很大的,它比中土文献更易于使用或出现一些复音形式。为了满足数量较大、篇幅较长的译经需要,翻译家们会尽力搜求汉语已有的复音词,如果在译者个人言语的词汇系统里没有足够的双音形式可供选择时,就不得不创造一些双音甚至多音的表义形式。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佛经中的复音程度副词一部分可能来自当时口语,如“极为”、“甚为”、“深为”、“深自”、“转更”、“稍稍”等;另一部分则是译者的创造,仅见于佛经的新兴程度副词全部为复音形式。这些新兴的复音词基本上是程度副词的同义连文形式,诚如董志翘先生所指出的“一个四字的‘顿’中,在表达相同语义的前提下,为了形式的整齐,往往用同义复迭的办法来凑足音节(当然有时也有用省略应有虚词的办法来满足四字格的)。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单音词,所以同义单音词的复迭成了首选的手段”[9]。不过,它们的使用频率一般都不高,很多在佛经中也只有一两例,而且除极个别词语沿用至近代汉语外,绝大部分在近代汉语时期已基本消失。
文化与语言的交流特性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间不断与外来文化接触和交流,其形成发展必然会受到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文化和语言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是始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①文化现象的形成、发展、吸收要通过语言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也要以语言接触为先导和手段。游汝杰就曾经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②文化间的交流往往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因此以语言演变作为研究视角,考察外来语与汉语的接触过程,分析汉语中受到外来语影响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呈析外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透视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轨迹。 一 从东汉开始,佛教从印度及中亚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大量以梵文为主的佛教典籍被翻译为汉语,形成了首次大规模系统性的汉语与外来语间的接触和交流。据朱庆之①统计,在东汉至隋期间的汉译佛经文献就有814部、3187卷、约2552万字,语言接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空前的。因此,从汉译佛经中厘清由语言接触所产生的语言现象,对于探寻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佛教对汉语的影响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尤其在词汇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已有的研究例如王力《汉语词汇史》②、向熹《简明汉语史》③、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④和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⑤等考察了佛教传入中土的大量外来新词,诸如禅、慈悲、佛、和尚、罗汉、僧、刹那、世界、塔、比丘、钵、忏悔、地狱、法宝、法门、袈裟、劫、烦恼、方便、伽蓝、魔、涅槃、平等、菩萨、庄严、比丘尼、玻璃、导师、未来、现在等。史有为在探讨外来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时指出,“外来词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反映了某种社会的或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交流形式。可以说,外来词的产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社会进步和文化融合的一个标记。”⑥外来词固然是外来文化和语言反映在词汇方面的典型标记,然而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对词汇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外来词,其影响更为深刻和广泛。佛教在中国漫长的流布过程中,汉译佛经中某些构词语素的使用也产生了相应的演变,本文将以此作为研究对象,从词汇角度考察中国历史上佛教流布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二 “语素”这一术语源自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指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词语正是由一个或多个语素构成。语素之间的搭配构词能力不尽相同,有些语素构词能力较弱,只能和少量的其它语素构成词语,而有些语素则可以大量地与其它语素进行搭配。语素的搭配构词是语言中重要的词汇现象之一。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某些语素的搭配构词能力在汉译佛经文献中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它们具有很强的与其它语素结合构成汉语复合词的能力,而且这种新用法逐步扩散到中土文献中。本节将以“净”和“妙”这两个佛经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构词语素为例,描写它们在上古时期(先秦到西汉)、中古时期(东汉到隋)和近代时期(唐代以后)的构词特点,呈现这些构词语素的演变过程。 在上古时期,“净”用作形容词性语素,义为“清洁”、“干净”。“净”通常是单用或是与其它表示洁净、干净等义的形容词连用,构成同义连文的并列复合词,一般不用于名词性语素前面充当修饰语构成偏正复合词。例如:(1)观辜是何圭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先秦《墨子•明鬼下》)(2)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先秦《吕氏春秋•任数》)(3)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西汉《春秋繁露•山川颂第七十三》) 在中古时期的中土文献中,“净”的这种用法仍然沿袭下来,例如:(1)如天能原鼠,则亦能原人,人误以不洁净饮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岂故举腐臭以予之哉?(东汉王充《论衡•雷虚》)(2)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为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3)食瓜时,美者收取,即以细糠拌之,日曝向燥,挼而簸之,净而且速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 中古时期的佛经文献中,“净”的基本意义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可以用于大量名词性语素如“水”、“目”、“法”等之前,构成偏正复合词“净水”、“净目”、“净法”等,其搭配构词能力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1)每至斋日,吾要入佛正真之庙,听沙门众散说净法,以为德本,防绝凶祸,而子婬荒,讹云有务。(三国吴康僧會译《六度集经》卷6)(2)譬如长者,若尊者子,净水洗沐,着新好衣,所有具足,无所少乏。(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2)(3)净目修且广,上下瞬长睫,瞪瞩绀青色,明焕半月形,此相云何非,平等殊胜目?(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1)(4)其于初时虽无净心,然彼其施遇善知识便获胜报,不净之施犹尚如此,况复善心欢喜布施?(南齐求那毘地译《百喻经》卷3)(5)又如净衣置之香箧,出衣衣香;若置臭处,衣亦随臭。(元魏慧觉译《贤愚经》卷5) 到了近代时期,“净”与名词性语素搭配构成新词的用法不再局限于佛经文献,在中土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用例,例如:(1)幽光落水堑,净色在霜枝。(唐张籍《西楼望月》诗)(2)净濑烟霞古,寒原草木凋。(唐张乔《青鸟泉》诗)(3)尖两耳,攒四蹄,往往于人家高堂净屋曾见之。(宋欧阳修《戏答圣俞》诗)(4)百媚算应天乞与,净饰艳妆俱美。(宋张先《百媚娘》词)(5)易器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泻清汁于净器中。(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2)(6)见坐着一个人,头戴顶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子,下面皂靴净袜。(明施耐庵《水浒传》第8回)#p#分页标题#e# “妙”是汉译佛经中另一个常见的构词语素。上古时期,“妙”用作形容词性语素,义为“精妙”或“美妙”。“妙”可以放在名词性语素前面充当修饰性成分,但是这种情况很少,主要是与其它形容词性语素构成同义连文的并列复合词,例如:(1)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先秦《庄子•齐物论》)(2)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先秦《商君书•定分》)(3)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先秦《吕氏春秋•勿躬》) 中古时期的佛经文献中,“妙”的构词能力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放在很多名词性语素前面充当修饰性成分,构成偏正式复合词,如“妙乐”、“妙花”、“妙体”、“妙音”、“妙果”等,使用频率非常高:(1)心念若干品,不慕其诤讼;少欲如妙花,大男子所好。(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2)云何贤者,世尊大圣,已以圣通身最正觉,讲世妙法,难及难了。(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1)(3)以一妙音,演畅斯义,常为大乘,而作因缘。(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卷3)(4)我等何缘,得离苦恼,受是妙乐?(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卷3)(5)超世圣王子,乞食不存荣,妙体应涂香,何故服袈裟?(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3)(6)昨夜二天,来觐世尊,威相昞著,净光赫奕。昔种何德,获斯妙果?(元魏慧觉译《贤愚经》卷1) “妙”的这种用法逐步扩散到同时期乃至后代的中土文献中,酌举如下:(1)命班尔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晋蔡洪《围棋赋》)(2)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唐李白《草创大环赠柳官迪》诗)(3)妙舌寒山一居士,净名金粟几如来。(宋黄庭坚《再答并简康国兄弟》诗之二)(4)今日要擒拏庞涓,雪俺六国之恨,皆赖军师妙计。(元无名氏《马陵道》第4折)(5)尔其孤禀矜竞,妙英隽发,肌理冰凝,干肤铁屈。(明徐渭《梅赋》)(6)“八千里外常扶杖,五十年来不上朝”,将杖朝二字拆开一用,便成妙谛。(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6) 三 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逐渐传播开来。汉译佛经是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的最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汉语首次系统欧化的直接产物。这种以汉语为材料而进行的言语再创造,不可避免会有羼入其中的外来成分,从而造成了汉译佛经语言的特殊面貌。许理和认为:“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佛教的‘经典系统’已经形成,它的语言既不同于中国的世俗文学,也不同于佛经的印度原典,它已逐渐变成了脱离于活语言的一种定型的佛经语言。佛经语言在术语和风格上的定型是几种力量产生作用的结果:印度原文的长期影响、古典汉语的影响和译经者在创造或借用新形式新方法时的个人的创造性。”①朱庆之也指出:“汉文佛典的语言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②在汉译佛经的语言中,有些语言现象是汉语固有的,也有些语言现象是受到原典语言(主要是梵文)的影响而新产生的。通过将梵文原典与相应的汉译进行对照考察,汉译佛经文献中“净”和“妙”这类构词语素迥异于中土文献的用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梵汉语言接触的产物。从梵文与汉译的对照分析来看,“净”和“妙”来自于相对应的梵文,它们所修饰的名词性语素也对应着梵文原典中的名词性成分。可见,汉译佛经文献中“净”和“妙”大量放在名词性语素之前搭配构成复合词的现象并非汉语固有的,而是译者翻译原文造成的,属于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新的语言现象。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东汉时期的佛教最初只在皇室贵族中流行,并未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影响力比较有限。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大规模的佛经译场开始出现,译经事业更加进步,佛教逐渐进入普通民众之中才真正发展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隋唐之后,佛教进一步与本土文化融合,日益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和流布,以梵文为主的外来语对汉语的影响也在逐步深入。最初阶段,“净”、“妙”等语素放在名词性语素之前充当修饰性成分,主要是出于对应原文的需要,而且这种用法仅局限在汉译佛经文献中,具有了一种宗教色彩。但随着佛教文化的深入传播,这类用法逐步扩散开来,在中土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佛教义理无关的用例。到了这个阶段,语言接触对词汇的影响已经不再限于佛经文献,而是融入到汉语的全民语中,成为汉语自身的一类词汇现象。 四 本文考察了“净”和“妙”两个构词语素在上古、中古和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这类语素在中古汉译佛经中呈现出新的用法,它们可以跟大量名词性语素搭配使用构成偏正式的复合词,这种用法迥异于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的中土文献。“净”和“妙”的新用法最初仅限于具有宗教色彩的佛经文献中,随后逐步渗透到同期和后期的中土文献中,日益脱离了宗教色彩而成为汉语全民语的一部分。通过与梵文原典的对照,“净”和“妙”新用法的形成并非属于汉语的固有现象,而是梵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接触的产物。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语言接触在构词语素层面的这类影响扩散到汉语的全民语中,成为汉语自身的语言现象之一。佛教在中国经历了初期的传入、逐步流布和最终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漫长过程。文化间的交流与上述语言现象的变迁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语言演变作为视角,不仅可以呈现外来语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也透视着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轨迹。与单纯的外来词相比,外来文化和外来语言在汉语构词语素层面的影响更为隐蔽和长久,而这类深藏于汉语自身中的印记则更为深刻地呈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伦理学核心术语生成途径探索
作者:杨玉荣 单位:海军工程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全力灌输中,在欧风日雨的浸润中,一些新名词层出不穷。它们宛如一股潜流悄然改变着中国固有的思想,使其一点一滴地向近代新学质变。在众多新名词中,“伦理学”、“道德”、“善”、“义务”、“平等”、“自由”、“博爱”、“幸福”等词脱颖而出,构成中国近代伦理核心术语群。这一术语群究竟如何生成,有着怎样的特点,一直以来扑朔迷离。但是,探究它们的生成规律对于研究中西日文化互动中传统伦理的近代转型却至关重要。
一、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路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是一门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运行的学问。它以血缘关系为起点,以家族伦理为本位,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融政治、哲学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如忠、孝、仁、义等。而西方伦理学是一门在西方文化传统哺育下的伦理专学,它所形成的概念术语反映的是西方价值观念、宗教情结、行为准则或社会风尚等,具有明显的西式风格,如功利、平等、快乐等。因此,中西伦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其概念范畴大不相同。中国近代伦理学是在西方伦理学指导下的中西融合,它的许多核心术语都是西方伦理学术语在中国的移植和重生,具有崭新内涵。只有少数术语属于中西伦理学共有,能够直接对接。这样,就形成了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生成的三条途径:一是重新创制,二是直接对译,三是侨词来归。
(一)重新创制
由于中西伦理学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两种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伦理术语,中国传统伦理中是无法找到相应的对译词的。对于这些术语译名,只有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工作,一般应由最初翻译者完成。但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时代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术语译名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伦理术语最早的创译者是明末清初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来华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后,在传播西学常识和宗教伦理的过程中确实创造了一部分新词。利玛窦在传播西方Philanthro-py思想时为其厘定学名“博爱”,在对译Happi-ness时为其拟订学名“真福”,艾儒略将Ethics引以为“厄第加”等等,但随着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夭折,这些译名烟消云散,并未流传下来。19世纪早期,随着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帷幕的拉开,来华传教士再次面对西语中译问题。但这批传教士的西学素养与汉语水平同明末清初传教士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在翻译中不太注意区分中西术语内涵的差异,而是按照大体相似的原则对译,因此在他们手中很难发现有利玛窦那样精确考译的新词,而是一切依据中国旧语。碰到一些实在无法用汉语表达的西语,他们就采取用英语解释的手段。因此,Duty被译做了“分”、“本分”、“己任”、“责任”;Philanthropy被译为“仁者”、“仁”、“仁德”、“仁爱”;Happiness被译做“福”、“祺”、“福气”、“福祉”、“兴头”等等。由于他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在考察中西术语差异的基础上创译新语,只得忽略二者差异,简单对译。他们的这种“粗心大意”,使其翻译也常常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既然兼通中西语言的来华传教士都无法创制新词,那么,这一重任国人自己是否可以承担?遗憾的是,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国门,但晚清思想界仍以固步自封、陈腐不堪的“中学”为主流,要想寻觅兼通中西的人才,难上加难。因此要想依靠依旧陶醉于科举梦想、苦读四书五经的国人传递西学新知似乎比登天还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创制新语的重任竟由日本人肩负起来。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很大一部分核心术语是从日本“贩卖”来的。日本何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媒介?这是因为日本自明治初年开始接触西方伦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消化吸收,终于在19世纪末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近代伦理学。日本在学习西方伦理学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西学术语无法在日语中直接对译。对于这些概念,他们首先采用音译法,但后来为了概念精准,他们又用表意准确的双字汉语词来表示。这样,日本学者通过创造新词、旧义翻新等手法,创制了一大批汉字新名词来对译西方伦理学术语。这些新名词被称为“和制新术语”。甲午战后,西方列强纷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被瓜分豆剖之时,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开启民智、培养具有新道德的新国民,于是引进西方先进伦理思想迫在眉睫。但中西语言不通,精通英文的洋才又寥寥无几,要想掌握西方伦理的精粹谈何容易。正当中国人举步维艰之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发现了日本西学的精进。他们发现日本几乎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华,西方文化的经典之作几乎都可找到相应的日译本。康有为就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1]日文西书的精要,使中国人如获至宝,于是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伦理学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在引进日本伦理学时自然引入了日译伦理新语,“伦理学”、“义务”、“人生观”等名词都以这种途径进入中国。这些名词都是日本学者在对译西洋概念时创制,在中国学人对日文汉字的转换中,直接成为了汉字“新名词”。晚清瞿铢菴在《木屯庐所闻录•新名词》中记载了这些名词的由来:当时新政皆自日本稗贩,而译者未谙西文原义,又不通古训,一概直袭,若文襄者,固未可厚非也。由于中国译者中西学问有限,因此对于日文汉字不加辨识,一概直袭,导致了日本新学语的大举入华。虽然,日本新名词入华遭到了一部分人士的抵制,但由于日本新名词表意的精准和通俗易懂,却广受清末社会的欢迎。即使严复这种痛恶日本新语的抵抗派,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如严复曾为Ethics拟定了“人道之学”、“德行之学”和“义理之学”三个译名,而他自己最终还是接受了“和制新术语”———“伦理学”的学名。对于Obli-gation,他也拟定了“民义”译名,他最后也抛弃了“民义”而选择了“义务”。严复后来回顾这段心路历程时说:“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y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2]由于以Obligation对译“义务”,以Duty对译“责任”已为社会普遍接受,严复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最后只得无奈接受。因此,日本新名词在清末名噪一时,以致众多严译新语也在其强力辐射下湮没无闻。#p#分页标题#e#
(二)直接对译
国内地名汉译还原的有效手段
翻译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人名地名等的还原问题。“‘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这八个字是历来翻译人名地名的准则。其中尤以‘名从主人’为主。”[1]。已故台湾翻译家思果先生曾不止一次撰文论述翻译还原问题的重要性和难度[2-3]。有研究表明近代英语文献中中国地名的拼写主要是跟旧邮电式拼写走的,部分跟威妥玛式拼写走,少数为这些拼写法出现前有人用拉丁字母拼写而约定俗成[4],还有一些为意译或音译意译并用。旧邮电式、威妥玛拼写法跟汉语拼音有较大区别,对这些拼写法缺乏了解或存在误解会使汉译还原此类中国地名出错。意译的中国地名如果不借助相关文献也容易出错。该文将简述上述拼写法与近现代英语文献中的中国地名拼写的关系,及其与汉语拼音的对应关系,以笔者翻译两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资料①时遇到的部分地名翻译还原为例,谈谈如何在汉译近现代英语文献中出现的中国地名时实现“名从主人”。 1旧邮电式、威妥玛拼音与中国地名拼写的关系 已故地理学家曾世英先生1981年曾指出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近代史上英文里拼写我国的地名主要是采用“威妥玛式”,对“威妥玛式”与“旧邮电式”的区别缺乏认识[4]。权威者如耕田编《英语中的威妥玛式汉语拼音》认为“威妥玛拼法1867年创自英人ThomasWade,是长期在国内外流行的中国人名地名的一种拼音法式。”[5],“‘邮电式(笔者注:曾著中称“旧邮电式”,为行文方便,该文统一使用“旧邮电式”)’拼法即过去邮政方面用的地名拼写法,大部分与威妥玛式相同。”[5]。这种误解至今仍然存在,如孙伟杰认为“威妥玛”拼音出现后即成为中国人名、地名和物品名的译音标准,葛校琴谈到汉语地名英译的三种方法时也只提及威妥玛拼音而没提到旧邮电式拼音[7]。曾世英先生比较了1958年英国出版、在西方国家里影响较大的《泰晤士地图集》里中国地图上的重要地名跟我国旧邮电局名,发现旧邮电式与威妥码式相同的中国地名不到400个,通过统计旧邮电式与威妥码式不同的部分,发现使用两者拼写的中国地名分别为1270个和72个,即两者相比是18:1。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地名拼写法是跟旧邮电式拼写法走的”[4]。当时还有另一种拼写法“翟理斯式”,曾先生指出其第一版已经不可考,通过对比发现其第二版与威妥玛式的区别是,翟理斯式只在u上标发音符号为ü,不在e上标发音符号[4]。鉴于此,该文不再单列这种拼写法。 2旧邮电式、威妥玛式拼音的区别及其与汉语拼音的关系 两种拼写法互有差异,与汉语拼音也有较大不同,要避免翻译还原文献中的地名时张冠李戴,既要了解两种拼写法的差异,也要清楚它们与汉语拼音的对应关系。曾世英先生摘自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的汉语拼音-旧邮电-威妥玛式对照表可揭示旧邮电式区别于威妥玛式的最突出特点。限于篇幅,下面转录部分汉语拼音、旧邮电拼音和威妥玛拼音例子对它们的区别加以说明。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旧邮电式拼写把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混同起来,也没有发音符号,威妥玛式区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且有发音符号;同一个汉语拼音声母或韵母对应的旧邮电式和威妥玛式拼音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字母符号。如果误以为中国地名在英语里的拼写都是威妥玛式,就会在转换到汉语拼音时出现错漏,造成译名错误或翻译困难。 3例外的拼写法式及英语中一般地理名称的表述结构 英语中有一些中国地名既不是旧邮电式也不是威妥玛式,而是这两种拼写方式出现之前已经有人用拉丁字母拼写的,邮电局名沿袭照用,类似的例子有Peking(北京),Foochow(福州),Chunkiang(镇江)等[4]。此外,旧邮电式拼写的地名中还有采用方言拼写(如Kongmoon江门)、少数民族语拼写(如Jirin吉林)、拼写错误等情况,都是翻译还原地名时需要注意的。曾世英先生把英文中一般地理名称的表述结构大致归纳为四种:(1)只有专名,不加通名,如theAlps;(2)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如theBiscayBay;(3)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如LakeGeneva;(4)通名在前,中间加of,再加专名,如theSeaofMarmara[4]。国外拼写中国地名,除了使用旧邮电式、威妥玛式等拼音法,还会用这四种表述结构意译或音译意译并用等手段。 4地名的翻译还原 笔者在翻译两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英语文献时,遇到要还原的中国地名近百个。这些地名可分为两类:(1)市级以上包括少数县级地名,这类地名是翻译中遇到的多数。这些地名有的今天仍然使用,如HongKong;有的虽然已经不用,但查阅一般英汉词典或者如“有道”这样的在线词典,甚至用百度引擎搜索就可以还原,如Chefoo(烟台),Amoy(厦门)等。(2)县级及以下地名,包括街、路、道、巷等。这些地名绝大多数一般英汉词典查不到,在线词典查不到,甚至在收纳了众多中国地名的?光域《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之类的词典中都无法查到。第一类地名只要译者本着严肃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勤查字典,多数就能准确还原。不过也有些地名字典里能查到,由于作者的笔误或者理解错误,英文里写错了,则需根据地理常识和上下文进行甄别。如Taiku,ShensiProvince和FenyangAssociationinShensi中的Shensi,字典上查到是“陕西”,但Taiku(taigu“太谷”)和Fenyang(fenyang“汾阳”)均在山西,可知Shensi为Shansi(山西)的笔误。总体而言,只要译者认真负责,这类地名的还原相对容易,在此不再赘述。第二类地名则要视具体情况综合不同方法进行翻译还原。首先要看看它是采用旧邮电式或威妥玛式拼写音译还是意译或部分意译,音译的首先要结合两种旧的拼写法式与汉语拼音的对应关系转换成汉语拼音,意译的则要根据相关文献确定中文。不论是音译还是意译的地名,还要视具体情况结合地理名称的常用表达法、地图及相关文献等,进行还原,对于音译的地名还要考虑方言的影响。下面结合笔者翻译的资料中部分地名加以论述。#p#分页标题#e# 1)逐字对应音译,不受方言影响的地名,要结合旧邮电式和威妥玛式拼音与汉语拼音的关系及有关文献翻译还原。如长沙青年会旧址资料中的“TaSsuFangTang”对应汉语拼音tasifangtang和dasifangtang。结合中文的基督教青年会文献[7]还原为“大四方塘”。杭州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YingTzuLu”对应的汉语拼音有yingzilu,yingcilu,yingzulu,yingculu,yingzili,yingcili,yingzuli和yingculi,共8个。结合杭州市志翻译还原为“迎紫路”(www.hangzhou.gov.cn/main/zjhz/hzsz/citymark/423/T83297.shtml?catalogid=5446)。广州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WuHsienMenGate,WuHsienMen对应的汉语拼音为wuxianmen。WuHsienMenGate为专名在前、通名在后的表达法,gate为通名“门”,结合中文的广州青年会文献还原为“五仙门”。福州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ChingLuehMiao,TsangHsiaChou,旧邮电式和威妥玛式拼音中ch对应的汉语拼音包括j,q,zh,ch,查询对应汉语拼音的方法与查“YingTzuLu”相同,为节省篇幅,对应的汉语拼音太多时只列举最终确定的,下文也一样。最后确定ChingLuehMiao,TsangHsiaChou分别对应汉语拼音jingluemiao和changxiazhou,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文献关于福州青年会会址的信息[7]提及苍霞洲,查询与jingluemiao音同的“经略庙”搜到网络文章“七省经略庙?边糊”(mag.fznews.com.cn/html/fzwb/20110906/fzwb285426.html),确定经略庙与苍霞洲的地理位置关系,把ChingLuehMiao,TsangHsiaChou还原为经略庙(全称“七省经略庙”)和苍霞洲。 2)逐字对应音译,受方言影响的地名,要结合旧邮电式和威妥玛式拼音与汉语拼音的关系并考虑方言影响,还可利用地图辅助翻译还原。从曾世英先生借助《泰晤士地图集》考证中国地名在英文里的不同拼写法使用频率的做法可以看出,根据地图还原地名是个有效的方法,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通过goole或百度地图方便快捷地查询全球地名,特别是google卫星地图为地名的查询带来很大便利。如翻译还原武汉?口青年会资料中的地名“Chiakow”。从文献看,只知道Chiakow协会是武汉的一个分会,没有别的信息,查询到的中文版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馆信息的文献均指出武汉的青年会主要在武昌、汉口两个地区,可知Chiakow在武昌和汉口两镇辖区内。按照两种旧式拼音与汉语拼音的对应关系,Chiakow对应的汉语拼音为qiakou或jiakou,goole武汉市区,找带有“口”字的地名,位于汉口的“?口”进入视野,进一步查阅?口的历史沿革,对照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宗旨和开展的事功,确定“?口”即武汉的Chiakow,“?”在武汉方言中念qia。再如成都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KoChiaHang”,hang为四川方言,对应普通话中的xiang(巷),最终确定KoChiaHang对应的汉语拼音为kejiaxiang,google查成都街道名还原为“科甲巷”,与有关文献[8]相符。类似的还有福州青年会会所地址资料中的Ingtai(烟台山)和南昌青年会会所地址中的HsiaoChiTai(小金台)等。 3)音译字数和读音与中文文献有出入的地名,可通过地图和其它文献甄别还原。如汉口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cornerofHouchengMaluandHuangPiLu,landpurchasedin1914”。HouchengMalu对应的汉语拼音包括houzhengmalu和houchengmalu。有关文献[7]指汉口青年会会址在后城马路和黎黄陂路。武汉有许多为纪念名人而命名或改名的路,查询相关文献可知,“黎黄陂路”原名“黄陂路”,据传为湖北黄陂旅人修建而得名,1946年此路为纪念黎元洪而改名,因为黎元洪也为黄陂人,人称“黎黄陂”。会址材料描写的是1914年的情况,因此该路英译名为“HuangPiLu”。又如南昌青年会会所地址“cornerofHsiaoChiTaiandNiehHouCiang”。有关文献[8]指南昌青年会会所在法院后街与小金台街。可是NiehHouCiang对应的汉语拼音是niehouqiang和niehoujiang,跟“法院后街”相去甚远,google南昌市地图,发现与小金台路相交成夹角的是后墙路,百度查询“小金台”和“后墙路”,搜到一位南昌基督教青年会员后人写的文章“我们的爷爷(www.ttniao.com/blog/blog_3_log_one.php?log_id=2253)”,文章说青年会的旧址在小金台和后墙路交界处。南昌市志显示,后墙路几经易名。“清代时,后墙路东段靠近按察院,得名臬台后墙,民国时期将按察院改为省地方法院,路亦更名法院后街。西段靠近巡抚部院的后墙……1966年两端合并改名图强路……1984年复名后墙路。”[9]NiehHouCiang是音译“臬后墙”。 4)意译的地名。这样的地名是用普通名词来表达的,翻译还原需结合上下文,查询相关文献,而不能简单查字典了事或照字面翻译。如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theBund”,字典和网络搜索引擎查询结果均注为“(上海)外滩”,依据上下文“PearlRiver,outsideWuHsienMenGate”及广州青年会资料,theBund应是广州的“长堤”。福州青年会会址资料中的thebridgeofTenThousandAges,根据福州青年会会所文献“1922年,青年会迁入南台苍霞洲临江朝向万寿桥的新会所”[8],因此thebridgeofTenThousandAges应翻译还原为“万寿桥”。再如吉林青年会会址“thenewnorthgate”,很容易误译成“新北门”,但根据青年会有关文献[7]和吉林市志[10],thenewnorthgate为“新开门”。 综上,翻译还原近现代英语文献中的中国地名时,查字典、查文献特别是方志、查网络地图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准确把威妥玛式和旧邮电式拼写的地名转换成汉语拼音是翻译音译地名的重要一步,翻译时还需要考虑方言的因素。地理变迁的因素也要加以考虑。
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文化的互为关照
摘要: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包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态特征,包括思维模式,意识习惯以及审美情趣等。在现在已知的语言体系中,汉语具有独特的,且与其他民族语言所难以理解的面貌,这同汉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本论文以汉语语法为视角,浅析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文化间血肉交融的关系。
关键词:汉语语法;民族文化
一种民族的思想意识在确立的过程中,必然的会决定并伴随形成独特的感受把握客观现实的认知方式,它是长期积累,多方面实践培植起来的民族心智方法论。作为汉民族文化中流砥柱的儒家思想,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关照下,传统的中国人更加注重对自身的一种探索,这是一种内敛的思维方式,孔老夫子就曾说他要多次反省自身。这同西方文化中追求外向,追求从众多具象中剥离抽象真理是不同的。如果说西方人是注重理性分析,严密逻辑的话,那么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明显就更感性了。而这两者的截然不同势必决定了两种文化之下的语言也是大相径庭的。
一、重意轻言与非形态
与西方民族语言相比较,汉语是非常典型的非形态语言。汉语音节一般组成为声韵两分,形成表意语素,这与西方语言以多音节词为基本单位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所以汉语词的音节特征决定了汉语言不能像西方语言那样进行自由的形态变化。这是从语言本身来看,汉语的基本特征,如果结合民族文化来看,就更能理解汉语中的重意轻言。由于汉语没有词类的显性标志,在思想认识方法上没有建立借助语形深入分析的意识观念,故我们汉民族没有在早期便建立起科学系统的语法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汉民族注重悟性思维而不注重对思维对象进行抽象的分析推理。为了表达的言简意赅,往往用事物性状和征喻来表达自己的意念和体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一贯贬低语言作用的同时,他们的语言作品却呈现出严谨的组织规则与惊人的表现力。所以,不难看出,传统中国人更多的注意的是意蕴意象,内心的感受,而不热衷于对物质世界进行精密科学的描述。他们在利用语言,但在思想上却不愿为其所囿,于是总是在做着超形质重精神的努力。因此汉语不必象西方语言那洋有严格的性、数、格的形态变化,而注重意合法,力求简约,所以汉语多省略句,多跳跃式结构,多不完整句,词类则不太稳定,多活用兼类。正是因为汉语言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进行汉语教学的时候,或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结合汉语的重内在意蕴与意象的特点。例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如果按照正常的语法顺序的话,这句诗歌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但是诗人的诗意却是回忆长安美好的景物(香稻和碧梧树等),诗人首先想到的是香稻和碧梧,所以才把它们放在句首。如果改成正常语序,就会失去原诗的美好境界和韵味。
二、重简轻繁与非逻辑化
汉语句法组织结构有着鲜明的简易性的特色,很自然,这种特色也是与汉民族文化中重实用的传统思维模式有关。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如今的现代汉语,随着单音节词向着双音节词的转变,行文上看似有所增繁,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词汇系统上,其内在的句法简约特征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即在繁复的语意信息中选取最核心的有限词语在表述中予以凸显,这就是吕叔湘所说的“占据一点,控制一片。”该段文字多为动词性词语的组合,于汉语记叙性语句是有着典型意义的。词语短小,文字极简,意义间跨度大。这都是在汉语中才会出现的现象。汉民族文化中的务实性,简易性的特征给汉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汉语少了一些赘疣性的条件规定附加,词语凭意会便可以随意组合,于整体语意表达更加富有弹性与张力。另一方面呢,由于句法过于灵活,词语组合太过粗疏,相应的会使语意不够严谨。综合起来看,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重整体综合,轻细节分析。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习惯定型了的思路框架。它在思维与语言这种统一体中呈现表里状态或明显或隐晦地存在反应着,并以强大的力量制衡着我们民族认识、反映事物的方式。汉语作为一种有着厚重文化积累的民族思维形态,不断表现出它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语言时,既要有一定的创新和规范,也要兼顾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体现着我们语言本身有着强大适应性与应变力。
早期法律的翻译史
英语世界对中文法律的系统英译盖滥觞于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于1810年翻译出版的英文版《大清律例》(TaTsingLeuLee;BeingtheFundamentalLaws,andaSelectionfromtheSupplementaryStatutes,ofthePenalCodeofChina)。1815-1823年间,比小斯当东仅年幼一岁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完成鸿篇巨制三部六卷本《华英字典》,其中的《五车韵府》(1819)对中文法律词语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屈文生,2010:79-97)。本文拟考察的重点不在于早期中文法律词语的英译情形,而在于早期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状况。对于英文法律词语传播至华的主体,文章的主要考察对象亦不在于诸如马戛尔尼(GeorgeLordMacartney,1737-1806)、老斯当东(SirGeorgeLeonardStaunton,1737-1801)、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等早期外交使节及商人,而主要在于19世纪中叶前后的来华传教士。如果说19世纪中叶前后的传教士在“中法西传”中发挥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那么他们在“西法东渐”中则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传播者甚至是布道者角色。早期西方法律词语的中国化及其“跨语际实践”过程实现,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华所编、所译、所著的各类书籍介质。1839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9)和四川人袁德辉节译出《滑达尔各国律例》,是文盖为的英文法律著作汉译之嚆矢,并在日后被收录于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三(王维俭,1985:58-62)。及至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译出《万国公法》,西方法律词语的一部分明显进入了汉语语言之中,并成为当时乃至今日中文法律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近代中文法律词语或话语体系至此还远未形成。自西徂东的法律词语除大量见于《滑达尔各国律例》和《万国公法》等主要由传教士完成①的译作外,还散见于传教士亲纂的双语字典、创办的报刊及撰写的文字作品之中。 一、传教士字典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在19世纪中叶传教士编著的众多字典中,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的《英汉字典》(1847)和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最值得关注。单就英文法律词语汉译(而非中文法律词语英译)的课题而言,其他传教士字典的研究意义则要稍逊一筹。比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大体上属于汉英词典(特别是其中的前两部,即《字典》和《五车韵府》),因而最好作为汉译英研究的史料,而非英译汉研究的脚本。马礼逊于1828年出版的《广东省土话字彚》(AVocabularyoftheCantonDialect)也属于汉英性质的辞书,它们不同于前述麦都思、罗存德等人编纂的由西向东式英汉词典。马氏辞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是中西初遇时中译英水平的忠实记录者,成为早期词汇交流中由中向西的重要载体。是故,在做英译汉研究时,马礼逊汉译英式的《华英字典》和《广东省土话字彚》均似无需过分着墨。 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1841年编纂的《广东省土话文选》(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于1842年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LessonsinChinese;orProgressiveExercisestoFacilitatetheStudyofThatLanguage;EspeciallyAdaptedtotheCantonDialect,Macao)和1844年出版的另一本辞书《英华韵府历阶》(An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均意在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以《英华韵府历阶》为例,它最初意在用拉丁字母为一批日用词汇标记官音,使外国人能掌握官话,方便他们到新开放的口岸与当地人交流,因为广东话在这些地方是不通行的(程美宝,2010:90-91)。它们的编纂目的因而主要在于解释或标记中文,而不在于将承载英语国家观念、制度、文化的词语翻译成中文,因而亦可不作重点研究。为使读者能对麦都思《英汉字典》和罗存德《英华字典》中的法律英文的汉译情况有一个大致的、直观的了解,笔者从上述二书中摘取数例,见表1。 相较而言,罗存德的字典因出版在后,所以它较麦都思的《英汉字典》收录的法律字词更多,解释也更为精细和准确。收词方面,以bankrupt为例,前者收录了与bankrupt直接相关的诸如bankruptcy(theactofbecomingabankrupt/倒行、倒灶、败盆)以及bankrupt-law(折本律例)等词条,而后者则未收录这些相关词语。再以law为例,罗存德的字典中新增了与该字有关的若干词语,如divinelaw(上帝之法)、humanlaws(人法)、municipallaw(民法/民例)、lawsofnature(性之法)、criminallaw(刑例/刑法)、ecclesiasticallaw(圣会律例)、commonlaw(通行之例)、statutelaw(律例/所书之例)、mercantilelaw(通商章程/通商法律)、lawofnations(公法/万国通行之法)、theMosaiclaw(摩西之律例)、ceremoniallaw(礼/礼仪)、doctoroflaw(律法博士)、topervertthelaw(枉法)、law-maker(设法者)等。而诸如Tort这类常见法律术语,麦氏的字典根本未加收录,但在罗氏的词典则可查到此字。解释方面,以bigamy为例,罗氏的字典已明确将其译成达意的某种犯罪——“双室之罪”,离今日通用的“重婚罪”已是一步之遥。 还要注意的是,从表1来看,麦都思早在1847年的《英汉字典》中就已将law译成“法律”(虽然二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尚未确立),更早的,在马礼逊《五车韵府》中,即可看到law与“法律”的对译(Morrison,1819:146)。可见“法律”并不是一则“外来词”(高名凯、刘正埮,1958:131),准确地说,中日“书同文”的“法律”二字只是借清末大规模的日本法律译介和法律新词的输入,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使用,进而与英文词语law正式确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此外,上述两部词典中也有部分英文法律词语找到了汉语中的对应词,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得到了后世学者、字典及书籍的认同,并一直传承到了今日。如witness(证人)、bribe(贿赂)、plaintiff(原告)、defendant(被告)、testimony(证言)等。当然这些词语的对应早在马礼逊的《五车韵府》(1819)中即已确立。(屈文生,2010:95)#p#分页标题#e# 二、传教士报刊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也是早期英文法律词语汉译的重要载体,其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andWesternMonthlyMagazine)尤其值得一提。前者被认为是已知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主要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于1815年8月5日(嘉庆乙亥年七月初一)在马六甲创办;后者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ützlaff,1803-1851)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1837年后出版地迁至新加坡),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内地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政法类文章较少,米怜曾自称该刊“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宁树藩,1982:65)。但该杂志曾连载前述麦都思撰写的《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Catechism)文章,对英美两国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些许介绍,故涉及不少法律词语;该文于1819年单独出版,共21页,用作小学生简明教科书(熊月之,1994:115-116)。现择其要者,对文内法律词语的中译名列表分析如下,材料主要来自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从上表可知,《地理便童略传》保存了早期中文法律译词的形态,但它们大多尚未定型;传教士在翻译上述词语时,多采用“归化”译法,以贴近当时的中文习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世代公侯”“乡绅世家”“乱拿”等译词即为例证。“总理”二字看似熟悉,但笔者认为它并非是今日PrimeMinister或Premier的译词②,而是President一字的翻译;关于这一判断可从如下引文判断得出:“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熊月之,1994:116)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涉及政治与法律的文章较多。王健教授认为,《东西洋考》是最早将世界各国的国情、政治和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重要文献;它为考察与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法律的概念、术语、思想和制度传入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路径(王健,2001a:40)。刊物中刊登的不少词语与《地理便童略传》中的相似,但又不尽相同,译词体现出演进与变化的特点。除表3中的文章涉及法律词语,1838年戊戌四月号的《论刑罚书》、五月号的《侄答叔论监内不应过于酷刑》、七月号的《侄答叔书》、八月号《侄奉叔》、九月号《侄复叔》等文章,多触及清朝刑罚残酷的弊端,因此也值得细查。 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发现,在若干早期英文法律术语汉译中,不少英文法律词语在最早翻译成中文时,曾有多个不同的汉语译名。比如President有“总理”“首领主”“统领”等译法。实际上,在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等文献中还被译为“伯理师天德”⑤,在下述《万国公法》中又被译为“伯里玺天德”(何勤华,2003:50),此外还有诸如“民主”(取万民之主的意思)“国主”“酋”“长”“酋长”“大酋”“头目”“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花旗合部)大宪”“头人”“邦长”“总领”“大统领”“皇帝”“国君”“国皇”“伯理玺天德”(熊月之,1999:58-61)及“伯理玺”等译法。再以juror一词为例,它有诸如“有名声的百姓”“副审良民”“批判士”等不同译法。这还不是全部,它实际上还有如“乡绅”“衿耆”“有声望者”“绅董”等译法。(胡兆云,2009:46-50) 三、《滑达尔各国律例》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出于“制夷”的需要,“天朝大吏”林则徐于1839年奉差赴粤查办烟案,期间在广州组织节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deVatell,1714-1767,今译“瓦泰尔”)的国际法著作——《滑达尔各国律例》(TheLawsofNations,orPrinciplesoftheLawofNature,AppliedtotheConductandAffairsofNationsandSovereigns,1758年出版),它是最早翻译到中国来的国际法,比《万国公法》早25年,林则徐因此成为晚清最早的一位翻译赞助人(王宏志,2011:49,51-52)。节译部分的译者是伯驾和袁德辉,总字数不到2000字⑥,有学者认为林则徐请伯驾翻译依据的是滑氏著作的法文版,而袁德辉重译和增译依据的是该书英译本,理由是滑达尔国际法著作原为法文,袁德辉“不谙法文”而伯驾“精通法文”,但王维俭先生认为,“可以确凿无疑地断定不论伯驾还是袁德辉均依据英译本。而且是奇蒂(JosephChitty)的英译本”(王维俭,1985:63)。还需指出的是,美、中两位译者翻译的实际是同一国际法文本中的同一个片段,尽管他们在对源语及目的语的处理和取舍上确有差异,袁德辉增译了一小节。笔者按图索骥,分别查阅了《滑达尔各国律例》(光绪二季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的中译本和奇蒂的英译本(Vattel,1833:38,171-172,291-292)。现将典型的法律词语包括短语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发现,作为已知最早的法律翻译作品,《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使用的译词不少传至了今日,成为今天通用的译法;上述某些英文词语基本上与中文法律词语建立了“词词对应”关系,这其中典型的有“law/法律”“confiscation/充公”“smuggling/走私”“export/出口”及“makelaw/立法”等。这恰如挪威汉学家鲁纳所言,伯驾严格依据当时的汉语以及瓦泰尔著作的原意和语言,创造了一种勉强能为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的“混合式”(hybrid)语言。而袁德辉发现伯驾的语言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在伯驾文本的基础上,将他的译文改造为更接近中文习惯的文本。袁创造了一些表达核心概念的语义上的新词,并使整个观点都简化和中国化了(鲁纳,2000:309)。若以信息为取向的翻译视角来看,或许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本均已接近达到了林则徐组织翻译该法的目的。#p#分页标题#e# 虽然我们尚不能直接证明汉译法律词语在这一时期的传承情况,但种种间接证据指明,上述二位译者在翻译《各国律例》时极有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先生的文章指出,袁德辉曾从北京出发,专程赴广州购买过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1985:67);而据裨治文发表于《中国丛报》的《鸦片贸易危机(续)》(CrisisintheOpiumTraffic)一文,林则徐在虎门接见美国商人经氏(C.W.King)和他时,曾直接提出索要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马礼逊编字典(Morrison’sDictionary)(Bridgman,1839:76)。林索要字典全本之时正值其委托伯驾翻译滑达尔著作之际,由此可判断他们完全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字典。(王健,2001b:110)仔细翻阅马礼逊《华英字典》之《五车韵府》,我们发现“夹带”“漏税”“走私”对应的均是tosmuggle(Morrison,1819:388,768,795),再对照《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两位译者对于smuggling的翻译,发现它们是一致的;一个严肃的译者常会认真查考以前的译本以吸取其中的优势,基于这一朴素的判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译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沿用或传承。另,上述麦都思的字典(第1186页)中将tosmuggle也翻译为了“夹带、漏税、走私、逃抽”,足见部分译词的传承至此并未断裂。就《滑达尔各国律例》所译片断而言,它们“给读者留下的仅仅是有限而艰深的印象”(鲁纳,2009:80);它们对于下述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正如鲁纳所言,伯驾和袁德辉的译文之所以意义不菲不是因为他们对后来的中文国际法语言和逻辑产生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原创性以及他们在国际法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鲁纳,2000:309) 四、《万国公法》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与麦都思、罗存德、伯驾和袁德辉等人简单的、片段式的译介相比,丁韪良主译的惠顿(HenryWheaton)著《万国公法》(1864年)则有系统地创造了一套与国际法上主要英文法律术语相对应的汉语译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译事”。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万国公法》有张剑先生点校本(惠顿,2002)和何勤华先生点校本(惠顿,2003)两种,围绕该书的论文和专著已有不少,比如《<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何勤华,2001)、《<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张用心,2005)、《1864年清廷翻译<万国公法>所据版本问题考异》(王开玺,2005)、《关于丁韪良译介<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吴宝晓,2009)和《“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赖骏楠,2011)等,还有马西尼(1997)、王健(2001)、刘禾(2009)、林学忠(2009)、崔军民(2011)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或文章多从宏观、中观层面分析了《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引进之于近代中国政治、法律、外交及战争等问题的影响。而从微观上,列举全书中典型法律词语汉译的作品,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万国公法》的点校本共计262页,但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截取部分加以考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分析上表,我们发现丁韪良创造了不少法律术语。马西尼的研究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有诸如半主、动物、公法之私条、公使会、过问、离婚、民间大会、民主、判断、权、全权、人之权利、上房、首领、特权、下房、信凭、义务、债欠、掌物之权、植物、自护、总会等(马西尼,1997:188-274)。何勤华教授考证后则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概有下列24个,如万国公法、性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何勤华,2001:142-143)。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统计还有待挖掘,将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分门别类地分析可使研究变得更加深入和有说服力,比如“沿用至今的”与“已被淘汰的”;“归化的”与“异化的”“;逼真的”与“失真的”等等。对此,笔者将另撰文予以论述。丁韪良的翻译显然受到了中国文化不小影响,以致其部分译文出现了“变异”或“失真”。比如他将“alegislativepower/ajudicialpower”(立法权力机关/司法权力机关)一概译为“君”。而这一简单化处理,无疑使当时的读者误以为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有正当化的理由,进而具备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将law和positivelaw一概译为“律法”,则可能会使法的科学分类不易被人们察觉。将citizen译为“庶民”、obligations译为“名分”也属这一范畴。还有一对有趣的例子,丁氏在翻译realproperty与personalproperty这组词语时,将前者译为“植物”后者译为“动物”。后来,可能它与表示animal的“动物”相同,在和制法律新名词的影响下,property不用“物”而用“产”来翻译。所以这种对应关系出现不久就被两个日语汉字词汇“动产”“不动产”所取代(张璐、赵晓耕,2009:81)。词语由于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意义(俞江,2008:6),但由于能指与所指、所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致使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无法固定下来“,植物”与“动物”因而终究未在法律语言中被确立。 有学者认为,同治年间中西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构成了启动《万国公法》翻译工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向中国介绍国际法,能够引导中国自觉地遵守刚签订的条约,从而使条约上的权益现实化,这要比使用武力的强制手段远为高明(赖骏楠,2011:4)。但实际上,这可能并非是丁氏翻译《万国公法》的真正动力。西方在当时也不乏有人将丁韪良看成是制造麻烦的人,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Michel-AlexandreKleczkowski)曾抱怨:“有人想让支那人窥探我们欧洲国际法的秘密,这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会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一译“威廉士”)则担心,把国际法引入中国,会刺激中国人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譬如“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法律依据(刘禾,2009:165)。可见不少外国人对译介国际法到中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担心的。#p#分页标题#e# 不过,令卫三畏等人“稍感安心”的是,中国历史上系统翻译与引进之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的《万国公法》,似乎并没有让中国立刻找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天朝并未将国际法利用为保护国家权益的法律武器;甚至连国际法用语在中国的传播也未产生即刻的影响。倒是我们或许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万国公法》的翻译帮助我们创设了一批近代中文法律词语,它之于现代中文法律词语的形成与传播意义在于,它使得部分重要法律新词不但从英语世界进入到了汉语世界之中(特别是“主权”“权利”等极为重要的法律新词皆通过《万国公法》进入汉语),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还最终成为今日通用的法律词语,而这有助于缓解法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们的现代性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此外,《万国公法》中的这些新词和衍指符号还第一次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知识系统,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虚拟对等关系,并构成起码的可译性。(刘禾,2009:147) 五、结语 《万国公法》的出版只是揭开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的大幕,这一时期之后诸如法国人毕利干、中国人汪凤藻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李提摩太等人的作品以及谢清高著《海录》(1820)及比这一时期更早的《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著,1745-1751年间成书),均在近代法律词语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较大的影响。它们发挥的介质作用理应被深入挖掘,但限于文章旨趣在于考察19世纪中叶时期传教士汉译法律词语的形态,故不展开。 从19世纪上半叶前始至20世纪初期止,近代法律词语汉译的主力一直是以传教士居多的外国人,而国人仅扮演着“配角”的角色。该时期的法律翻译策略与路径亦明显有别于自1902年晚清“变法修律”以降的翻译策略与路径。1902年以降,和制法律新名词大规模传入中国,但在这以前,传教士与部分本土译者始终未放弃自创译名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似乎未成正比,但却无疑已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情景化教学的古代文学论文
1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障碍分析
首先从学生授课基础看,蒙汉双语班学生古汉语、古汉文基础普遍较低,古文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蒙汉双语专业生源主要集中在内蒙东部地区的纯农牧区,调查赤峰学院近三年(2010年—2013年)的蒙汉双语专业生招生情况来看,来自通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纯农牧地区的学生占主导.对赤峰学院在校的蒙汉双语专业103学生进行的调查问卷分析中发现86人来自纯牧区,93人家庭中纯蒙语交流,103人没有古汉语,古汉文基础.这些学生所成长的环境是纯母语环境,对汉语的学习只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课堂应试教学,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用蒙语授课,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汉语的特殊语言培训,也未曾接触过古汉文,所以在汉语读写听说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古汉语,古汉文基础相当薄弱.汉语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所谓不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横向比较中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学生汉语水平较高,理解阅读能力较好,而纯农牧区的学生汉语水平较低.其次是纵向比较中同一学生蒙语理解,阅读能力高,汉语理解阅读能力较弱,如何提高这些学生的汉语和古汉语基础水平,继而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有效教学是一项难题.采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和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深化内容的教学方法显然不适于蒙汉双语学生的学习现状,图文并茂,视觉和听觉结合,表演为辅助手段的情景化教学更适用于古文初学者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
其次从学生学习心态和心理上看,面对古文课程有畏难心理,学习兴趣不浓.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性质来看,属于难度较高的课程.本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作者、作品、流派、文学思潮、社会背景等等一系列的繁杂内容;从时代来看从先秦开始至近代,年代跨度较大,故作品的语言文字及其所反映的生活与当代距离较远,对古文基础薄弱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造成了畏难情绪,进而造成了教学障碍.从赤峰学院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问卷(2014年4月14日)得知,三个不同年级的103名学生中98名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难度较大,在尚未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2013级蒙汉双语专业23名学生中只有4名同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表示感兴趣,可见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对这门课程存在很严重的畏难心理.情景化教学是通过情景模拟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能更直观,形象地把教学内容和授课体验输送给学生,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据调查报告分析得知赤峰学院2010级、2011级、2012级三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共103人中,乐于接受《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情景化教学的学生84人,乐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19人,由此可见古汉文基础水平普遍较低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更愿意接纳情景化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手段有很多种,如采用图像,音频,视频,文字,自主表演等形式再现教学内容.如:在讲授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窦娥冤》时,可以选取片段让同学们分组表演,在练习台词时不仅提高了对古文的解读能力,更是加深了教学内容印象.基于授课学生的特殊性,课程本身的特殊性,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选择情景化教学更加有利于营造浓厚的古文学习氛围和提高学生积极性,从而能够提高其教学效果.
2情景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方法
2.1与知识构建相结合
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为提高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古汉文理解,分析能力,提高汉文修养,为培养蒙汉兼通的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这里强调的是蒙汉兼通的综合性、应用人才的培养.单纯的,单一的认知性情景化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在所涉及内容外围形成更多的相关知识体系,无法完成知识的构建,更是无从提起综合能力的提高.情景化教学应该和知识结构的构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系统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古文阅读,解析能力.例如:在讲授李白生平的时候,可以选取李白与酒的图片,以点带面讲李白与酒的关系,然后让同学去找李白写酒的诗歌,让同学们解读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使同学们很直观、形象地感受李白与酒的关系的同时,又留有空间让同学们自主去解读和思考,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整体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情景化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知识构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能使知识独立化,单一化.使用情景化教学方法讲授阶段性内容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发展演变的趋势的整体把握.如:在讲授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时可选用人物图片,视频片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课外还可让同学们自主去表演小说中人物,开展讨论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作品品评等,同时必须还要用文字的形式让同学们把握明代小说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可采用多媒体简明的方法,屏幕上演示如下文字:秦汉时期(史传文学)———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元时期(话本小说)———明清时期(可谓空前繁荣)———近代(把古代的和现代的结合,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是同学们对小说发展史有整体的把握,有利于学生古代文学小说史知识的构建.
2.2双主体原则
文章学译学范式建构
1.引言 佛典汉译始于东汉,终于宋朝,历时一千多年,期间佛教高僧研习佛典,讲经布道,翻译佛典近六千卷,阐述的翻译思想如同天空的星星熠熠生辉。这些是中华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脉相承的明清实学翻译和近代西学翻译具有直接的影响,是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诞生的土壤,是我国翻译学的根基和传统。所谓“典籍”,“主要指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被人们所公认的、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作。”(魏晓红、李清源2010:109)佛典就是指佛教的根本典籍,涵盖经、律、论“三藏”。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伊始,我们一方面要吸纳西方译学精华,做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更要继承我国传统译论“勘称典范的学术成就”,做到古为今用。只有古今打通,中外融通之后,我国翻译学才能健康发展,我国才能从翻译大国质变为翻译强国。本论文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学术范式视角研究佛典汉译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 2.范式 范式(paradigm),有时译作“规范”和“典范”,是1962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ThomasKuhn1962)。1989年科尔勒把学术范式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缩小了范式的内涵和外延,用来指语言学史上堪称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传统语言观念的理论体系(KoernerKonrad1989)。1984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余英时1984:19-21,77-91)。自此,学术范式在我国学术界逐渐得到推广。1999年傅勇林先生把学术范式引入到翻译研究中,采用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定义,认为“在范式的上述四个要素中,精神信念关乎译学思想与学术品位,研究传统关乎译学知识的探索过程及其‘层累叠加’,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则直接涉及译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四者藕合,才可构成译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并借以形成译学研究的学术面貌,因此绝对不可偏废。”(傅勇林、朱志瑜1999:30)本论文沿袭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定义,拟构建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 3.文章学 “文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颇具考究的词汇,锦绣文章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文人墨客才华的精髓,《千家诗》首章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之说。“文章”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其本义是色彩之间的错杂搭配。后来在《论语•公治长》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开始表现为文字作品之义,两汉时期这一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如:“汉之得人,以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义招选茂才。而肖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班固1962:58)“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才能若奇,其称不由人。”(王充1954:275)我国古代文章的范围很广,清人章学诚感叹“六经皆史”,后人对曰“四库皆文”,因为《四库》经、史、子、集无一不是文章。“中国的文章,历三千年之久,存在于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举凡哲学、政治、历史、宗教、艺术、民事、风俗,以及个人抒怀述志,无不借文章以传布和存留。”(毛庆耆2002:113)这句话说明文章在我国走过的岁月之长,涵盖的范围之广。文章学是指研究文章的学问,通俗地说,文章学就是文章研究。佛典汉译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受我国古代文章学、史学、佛学和中华文化的浸染熏陶,我国古代把翻译纳入文章学范畴,衡量译文与评价文章都采用文质标准。严复说:“(信、达、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1981:11)这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经典话语,文章正轨就是译事楷模,“信、达、雅”三者既是文章要求,也是翻译标准,佛典汉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章学译学范式。究其根源,合作翻译传统使然。 4.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构建 4.1合作翻译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成因 佛典汉译历时千年,一直采取合作翻译方式进行,无论是初期的私人合作,还是后来的译场合作,合作翻译是根本,佛典汉译形成了合作翻译传统。一是因为佛典汉译初期没有原本,外国僧人根据记忆口诵佛典,即使在印度本国,当时也无佛典写本。《分别功德论》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梁启超分析其原因:“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困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宗教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梁启超1984:53-54)竹帛携带不便和宗教禁写是造成印度佛典没有写本,佛典汉译没有原本的原因。印度佛典何时才有写本?这个问题学界尚未解决,据梁氏研究,“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梁启超1984:54)说明至少在5世纪初法显西游之时,印度等国尚无佛典写本。二是因为佛典汉译初期译者多为单语者,梵汉两种语言不能兼通,外国僧人负责口诵佛典,本土汉人负责润饰加工,形成译文,佛典汉译由外国僧人和本土僧人合作翻译完成。释赞宁对佛典汉译做过概述:“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內竖对文王之问,扬雄的绝代之文,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释赞宁1987:52-53)是说佛典汉译初期梵僧未谙汉语,汉僧不通梵文,加上没有原本,只能进行合作翻译。先由梵僧口诵佛经,进行传言,初步译成汉语;再由华僧笔受润饰,加工成文,这是简单的私人合作形式。佛典汉译中后期,梵僧习得汉语,汉人学习梵文,玄奘、不空更是梵汉皆通,“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释道宣1984:48)但是即使个人翻译水平达到很高境界,很多佛典原本也从印度带回,佛典汉译还是沿袭了合作翻译传统,依然采取梵文理解和汉语表达分步进行,梵僧和汉僧合作完成的方式,只不过由初期的私人合作发展为颇具规模的译场合作。以唐朝玄奘组织的译场为例,翻译程序就有十一道,包括:“一、译主:执笔人,胸怀全局,贯彻始终;二、证文:朗诵原文佛经,斟酌原文是否有错;三、笔受:根据梵音录本译出毛稿;四、度语:音译暂无对等信息的事物,据母本正音;五、缀文:按汉语字法、句法进行整理;六、证义:译出初稿与原文对照,看本旨是否偏移歪曲或有遗漏;七、参详:再回证原文是否有纰漏、错误;八、利洗:去芜冗、重复,梳整译文;九、润文:修辞、润饰;十、梵呗:由于佛经是要供人诵读的,所以再据母语(梵文)的诵经方式诵读汉译经文,看是否有不适合诵读之句;十一、监阅:最后有钦命大臣监阅(终审)。”(李全安1993:806-807)整套程序非常严谨,第二、六、七条强调原文理解,第五、八、九、十条重视译文表达,译场翻译的重心仍是加工译文,形成文章。事实上,无论是初期的私人合作,还是中后期的译场合作,合作翻译一直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梵僧负责原文理解,汉人负责译文表达,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分步进行使佛典汉译选择了合作翻译方式,而合作翻译传统的形成又进一步细化了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分工。对于汉人来说,如何根据佛典原文意思用汉语表达成文才是关注的重心和焦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p#分页标题#e# 4.2“文以载道”是佛典汉译的信念,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 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文章,视其为治国、传世之大业,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郭绍虞2001:159)我国文章学的核心思想是“文以载道”,道是文章的精神所在,是衡量文章的内在准则,因道设器、道因器显,道决定了文章的体式,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质,造成了文章学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文与道的关系和“文以载道”的实施都以人为纽带,通过作者实现,文与道的关系隐含了人与道、人与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道———人———文’是三个紧密相连的三环,其中,人是核心与根本,以人立极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重文意识的根本是重人意识,因此中国文章的功能实施,是靠对人影响完成的,以文观人是中国文章品鉴论的核心,并由此推衍出鉴文知人、文如其人等相关命题。”(杨广敏2001:39)关系到人,就会牵涉到人品因素,孔子曰“修辞立其城”,是说写文章要讲心里话,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这是我国古代对作者人品提出的要求。同样,佛典汉译对译者人品也有要求,释彦琮在《辩证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玄,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释彦琮1991:118)“八备”是彦琮对译者提出的八项条件,其中“四备”针对译者人品。具体是:一备要求译者诚心爱护佛法,志愿救世帮人,即使历时长久,也绝不懈怠;二备要求译者牢守佛教戒条,具备良好的操行;五备要求译者宽容平和,谦虚待人,不可固执己见;六备要求译者钻研佛学,淡泊名利,不事炫耀。这四项对译者人品的要求与另外四项对译者学业上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八备”,彦琮认为译者的人品与学业同等重要,一个译者必须同时具备这八项条件,才有可能是个翻译人才,所谓“八者备矣,方是得人”。释彦琮首次把译者人品与翻译好坏联系起来,这是我国,也是世界翻译史上最早谈论译者人品的文章。“文以载道”既是文章学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国传统译学的精神信念,是佛典汉译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 4.3“文质之争”涉及佛典汉译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表征 我国古代把翻译纳入文章学范畴,文、质原是我国古代评判文章好坏的一对概念,移用到佛典汉译中,指译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任继愈1981:174)“文质之争”是贯穿我国佛典汉译思想的一条主线(赵巍、马艳姿2010:93),始于公元224年支谦的《法句经序》,终于7世纪玄奘的“新译”,历时四百多年。“文质之争”之前,我国最早的佛典汉译家安世高和支谶属于“质”派人物,其译本给人总体印象是“辞质多胡音”,音译较多,译文朴拙,不加润饰,不合汉语习惯。质派有所不足的局面为文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支谦和康僧会是三国时期的文派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汉语,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所译佛典简略文丽。支谦《法句经序》拉开了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帷幕,文质自此成为译者争论的焦点。文派译风在三国和西晋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文派过于追求译文的文采美巧,有时不免脱离佛典原意,造成“理滞于文”,遭至后人诟病。之后佛典汉译又偏向质派,竺法护、赵政等都是质派代表。竺法护译经力求详尽,存真偏质,“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释慧皎1994:24)对比竺法护的译本和安世高、支谶的译本,很容易发现:虽然同属质派,但是安、支二人的“质”胡音较多,不合汉语语法习惯,只能算是“朴拙”;而竺法护的译文质量明显提高,“质”的内涵有所提升,译文流畅,符合汉语习惯,质派翻译由朴拙走向质朴,克服了译文结构僵硬、义理晦涩等不足之处。赵政也认为:“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释道安1995:382)赵政批评译者嫌弃梵文语言质朴,趋于时尚追求译文文丽的思想,主张译文应像原文一样保持质朴的语言,因为质朴是经文本身的特点,何必改之?佛学大师释道安则主张文质兼备,提倡“合本”,融合文、质两派的优点进行翻译。道安认为梵文佛典语言质朴,而当时的读者喜好文丽,佛典汉译“文质之争”变成是照顾原文,保持质朴;还是照顾读者,使之文丽的争论。质派认为“经之巧质,有自来矣”,认为译文应该保持质朴的语言风格。但文派鸠摩罗什却认为:“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僧祐1995:534)原来梵文也非常重视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丽和质朴之分,那些繁琐的偈颂是梵文体裁的一种形式。鸠摩罗什认为“改梵为秦”不应“失其藻蔚”,主张译文应向原文一样注重文饰,翻译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而且要再现原文的文采和风韵。此时的文派与三国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强调译文流畅、具有文采的基础上,文派开始重视准确传达原文意思。鸠摩罗什的译文不仅语言精美,而且内容准确,其翻译的《法华经》被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但是如同支谦一样,罗什译本依然存在“删削原文”的缺点,后人对其也有“理滞于文”的评价。关于译文是否需要文饰,语言风格是文丽还是质朴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文、质两派在争论中前行,在磨合中发展,文质矛盾得到调和,翻译质量有所提高。那么如何融合文、质两派的优势,克服不足之处?“文质之争”的出路在哪?东晋高僧慧远主张文质“厥中”,提倡文质兼备的思想,认为“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释慧远1995:391)是说文丽和质朴属于不同文体,质朴的原文若用文丽去译,怀疑的人就很多;文丽的原文若用质朴去译,感兴趣的人则很少,因此译者应该遵循原文文体,做到以文应文,以质应质,文质厥中。释僧祐也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释僧祐1995:14-15)认为文过和质甚都是翻译的弊端,同样有损经文文体,主张译文“质文允正”。这一说法其实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在翻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此时,人们开始从翻译思想上解决文质矛盾,寻求“文质之争”的出路。不过,具体到翻译实践,直到玄奘“新译”才从根本上解决文质问题。“这是因为玄奘译文融合了文质两派的优点,真正做到了‘案本而传’,‘以质应质,以文应文’,不但传达了原文意义,而且能够再现原文风格,译文语言流畅,适合诵读,远远超出前人所译,其翻译被世人尊称为‘新译’”。(汪东萍、傅勇林2010:99)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圆满结果,从此“文质彬彬”、“文质相半”成为衡量佛典汉译译文好坏的重要标准。#p#分页标题#e# 5.结语 佛典汉译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受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浸染熏陶,合作翻译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成因;“文以载道”是佛典汉译的信念,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文质之争”涉及佛典汉译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表征。几方面藕合,共同构建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这一饱含中华智慧的译学范式必将为世界翻译学提供新类型,补充新动力,我国翻译研究者应该抓住契机,深入研究我国翻译传统,吸取养分精华,借中国翻译之“道”走世界翻译之“路”,为世界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这一文化古国和翻译大国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