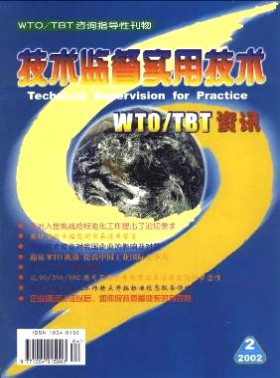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技术哲学的人类学未来,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斯蒂格勒大概是当代最与众不同的哲学家了。作为一个以形而上学为己任的人,他竟然同人类学家安德烈·勒华-古尔汉(AuditLeroi-Gourhan)①的团队开展紧密合,以期“完完全全地重新建立一套关于技术的论述”。[1]这一切实在太不正常。
哲学家并非没有关注人类学的先例,拉图尔(BrunoLatour)就算上一个。但和拉图尔亲力亲为地走到实验室里去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不同,斯蒂格勒却始终坐在摇椅上,借助古尔汉团队实践的所谓实验性科技——在实验室里重新复原(古人)磨燧石的动作,并通过这些动作复原尼安德特人的生活来思考技术问题。古尔汉是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MarcelMauss)①的学生。延续了莫斯乃至整个涂尔干学派整体主义的传统,古尔汉认为工具、技术是构成了作为生物的人与人类社会的关键中介。同样是得益于莫斯(当然也包括法国的殖民主义实践),古尔汉特别强调了今天已被认为是人类学标配的“田野”工作来小心求证。古尔汉发现:从东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不仅发生了大脑皮层的差异化过程,而且也发生了石器的差异化。[2]但由尼安德特人开始,大脑皮层系统几乎不再进化了。相反,技术却以极快的速度进化着。([1],p.74)这一切被斯蒂格勒看在眼里。斯蒂格勒甚至由此历史性地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本质上就是一个生命技术外置化的过程。([1],p.73)从而,人就变成了技术而并非仅仅是文化的产物。甚至没有了字面、模拟或是数码书写等第三持存(tertiaryretention)的支持,人类就不可能拥有动物所不具备的第三记忆。由一代传到另一代的经验,或者说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也不可能实现。([1],p.87)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是文化的条件。如果拉图尔也能多一点耐心或是斯蒂格勒本人能小心地收起他的冗长,他们肯定会相互同意。毕竟在上世纪70年代在索尔克(Salk)实验室的田野中拉图尔早已发现,有了铭写装置(inscriptiondevices)这样的的技术,科学家才可以成为共同体,科学知识也才有几乎无限增衍的可能。[4]
那么话说回来,将人类定义为技术存在,其他人是否会同意呢?斯蒂格勒回到了古希腊。无法被纳入先验论范畴的人类学不是古希腊的传统。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人的问题不感兴趣,([2],p.112)技术作为一种无目的、无逻辑的工具也被哲学所鄙弃:古希腊的厨师——同时也是屠夫和祭司甚至会厌恶使用刀具,一旦把禽兽杀死就弃之一旁。([2],pp.216-217)但斯蒂格勒还是必须回去原因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字母是在古希腊时期出现的……而严格来说是字母化促成了城邦”,即运用逻辑(logos)掌控的人类社会,构成其可能性条件。([1],p.54;90)然而回到古希腊,就不得不面对柏拉图,面对哲学的诞生。然而问题在于,既然“只要时间改变,我们对自己所说的就有不同的理解”,理解的多样性也被视为感受文本的巨大的历时性的表现。([1],pp.91-116)甚至连柏拉图都无法重现柏拉图,那斯蒂格勒又凭什么能够保证,他自己对于柏拉图对于哲学诞生的理解是“正确”的?斯蒂格勒并没有直接作答,却还是端坐在摇椅里反诘:为何不放弃人文科学乏味的实证论所赖以存续自身的,为形而上学和诡辩论共有的人类中心论?([2],p.114)斯蒂格勒断言,只要把以书写的形式将生活规则外置化以及客体化的人工记忆的因素加入进来,柏拉图所致力于谴责的诡辩术就绝不可能构成挑战秩序的无限。这太不人类学了!斯蒂格勒显然了解人类学:在作品里,他大量地援引、批判了卢梭、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类学家的著作;他和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也是建立在一个人类学发现——“古代社会技术和巫术合二为一”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在对话柏拉图时,斯蒂格勒却并没有事无巨细地描摹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细节,用以说明自己传达的真的是柏拉图“主位”的观点。相比之下,他只是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柏拉图“陌生化”了。就这样,一边标榜将人类学请进哲学的殿堂,一边又转手将她送了出去。
不过斯蒂格勒有一个判断倒是对的:当今的哲学家对技术问题不甚敏感乃至视而不见:“这或许是一种可怜的无力感的表现,不然就是极大的傲慢,它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歇斯底里,让人难以忍受。”([1],p.41)何止是哲学家,人类学家也对技术问题避之不及,尤其是在中国。斯蒂格勒坦言,他如此关注技术的首要原因是:他是工程师的儿子,敬仰父亲激发了他对技术的巨大热忱。([1],pp.35-36)诚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并以此作为打开或是拒绝打开技术黑箱的理由。但别忘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被技术所包围的时代。如斯蒂格勒所言,“我们一不留意就被链锁上了。”([1],p.113)拉图尔也早就提醒我们,回避科学和技术,我们就只能“原封不动地阐述难以对付的对象”。[5]人类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地了解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陌生的实践和世界的有力工具。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从舒服的摇椅中走出来——是的,在这一点上必须超越斯蒂格勒——再到充满了异质性技术的田野里去,“把裤子坐脏”。如拉图尔所说,“参加2至3年亲自的观察还有什么世界令人们不熟悉呢?”([5],p.17)真正的困难恐怕就在于这2至3年。或许可以归咎为这个急功近利的大环境,或许构成了这个大环境的本就是急功近利的我们:愿意去花时间去深入科学、技术田野的中国学者凤毛麟角。即便有,也更多关注了田野中非科学、技术的“相关”部分,以便于能够快速套用现成的西方术语讲一个似曾相识的中国故事。更多地,只是将科学、技术“黑箱化”,人云亦云地讨论诸如人工智能(AI)等“时髦”话题——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现行阶段、算法特点和应用场景全然不知,却依旧空谈所谓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谈负责任的创新。人类学家项飙提醒我们,“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边界越来越模糊”。[6]我们不得不警醒:当所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家,乃至于更多活跃在自媒体上的非知识分子都可以以这种“简便”的方式谈论科学、技术时,技术哲学和技术人类学又会给自己留下什么?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C.Scott)曾用瞎子背瘸子来比喻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7]“技术”即人的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哲学能够提供深度和术语,人类学则奉以经验和证据。正如斯蒂格勒所言:技术的问题的人类学思考,将引向一种纯粹哲学性的认识。([2],p.94)是的,经验和证据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那个为拉图尔所不齿的仅关注了实验室中非科学、技术部分的特拉维克(SharonTraweek),在荣获国际4S学会(SocietyforSocialStudiesofScience)的贝尔纳奖时还不忘记骄傲地提及,她在《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的田野工作至今还有人引用、提及。从某种意义上讲,斯蒂格勒之所以能够从古尔汉的发现探讨到哲学起源,也是因为柏拉图“写下了他的思考”,([1],p.94)成为他与之对话的绝佳素材。所以,去田野吧!难不成,想将技术哲学和技术人类学的未来拱手让人吗?
作者:王程韡 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