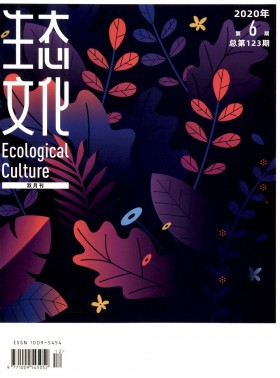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1
一、在田野之中:求实的人类学意识
方李莉所著《中国陶瓷史》不同于过往的陶瓷史书写方式,是一部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渗透完全的艺术人类学意识的舂容大雅之作。这部《中国陶瓷史》以史的线性序列作为著述的结构,以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主导,用人类学的方法进入研究,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成就了这部不同凡响的中国瓷的著述。其《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亦采取人类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察,展示了从陶瓷技艺的变迁到窑业的变迁,从窑业的生产到窑工的日常生活。人类学是一门具有整体性眼光的学科,往往采取跨学科方式来观察与研究对象。方李莉研究中采取了人类学研究方法来研究陶瓷这门具有“历史性与地方性手工艺人们的社会群体活动” [6],并且采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方式研究陶瓷“传统在现代化中的复活和重构。 ”[7]此外,因人类学是一门注重田野调查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她无论是对田野资料还是历史资料,均采取了历史比较、文化渊源考证以及文化对位方法论,进行整体研究。她提出,在研究一个器物过程中,不能拿标准来衡量某一个地方性知识。而是要在 “具体生活方式的充分描述上,旨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 ”[8]
中国人类学家提出“从实求知”及“走向田野”的思想。方李莉承袭了师门的研究作风,进入田野实实在在地调查与分析。她对于知识与田野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她主张人类知识不能止步于书本,而更重要的是关注其“真实的生活空间中” [9]。过去岁月历史中留下的理论以及今日当下社会的理论,均需要从实践中来进行重新认识,唯有如此才会有更接近事实的深切体会。另外,她认为新理论往往取之于生活的直接一手资料,而书本理论的间接资料是需要通过今日社会生活来考证。她主张中国学者要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则需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完整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而具有价值的理论需要从从实践中来,从田野中来。她深刻认识到理论“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10]。方李莉对于现实总是具有敏锐的
触角,她对学术具有一种现实责任感,她认识到人类世界目前正处于社会的激烈转型期,人类发展需要多样性的世界智
慧和经验,“而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11]因此,她用一个个的扎扎实实的中国个案研究,面对现实,提出问题,找寻问题的答案,提出闪亮的思想。
二、在器物之外:细腻的物质文化研究
器物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结构并携带着丰富的文化观念,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说处于文化之中的人,“行为均决定于他手中的传统材料。 ”[12]历史研究方法在近生了革命性变迁,学者们渐渐地从圣者的言论与象牙塔中走出来,而是把人文的研究情怀转向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人群。因此,社会底层的人文也如同圣者的理论一样,进入研究文本,于是普通人的信仰、思维与文化结构进入文字中。人类的事象纷纷落入学者们的目光中,从时令、技术、人群到曾经琐碎的日常生活。学者们纷纷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展开了对于形形物质的细枝末节的研究。这种历史意识也渗透到方李莉的陶瓷研究之中,她把目光从器物拓宽到匠和艺。越过孤立的器物之外,结合时令、技术、人群方方面面的因素,分析器物技艺特点,并延伸到技术背后的非物质的因素。譬如瓷工的生活、窑业生产方式等。同时,她将研究对象从物衍生到人,通过对陶工的制瓷活动来揭示陶瓷史的另一种丰富的侧面。
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了近代历史研究。近年来,柯律格、彼得 ・伯克(Peter Burke)、林・亨特( Lynn Hurt)、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 Nataliz Zemon Davis)、罗伯特 ・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许多学者的著述渗透了人类学意识,以历史为田野,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研究。方李莉的著述也深刻地携带着人类学学科的意识与方法,深入到器物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譬如在研究陶瓷纹样时,她重视分析文化内涵发生的内在文化动因。在《中国陶瓷史》中,她分析了唐代城市的新布局与手工艺的发展、科举制度与文人生活、茶文化的兴起、外来人口与文化交融对于器物的影响。中国文化学者往往容易滑入中国文化“道”与“器”分离研究,方李莉的艺术学与人类学严格的专业训练背景,使得她对人类的“造物”行为及其文化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方李莉指出器物日常器用其实就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物” [13]。因此,她将器用研究置于器用的文化之中,不但研究器,还研究器用其道。通过将器用置于整体性研究之中,找寻器物背后存在的“整套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14]。因此,她的文本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细腻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
三、在历史的深处:浓厚的历史意识
器物不仅是人类的人工产品,也表达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时还携带着人类审美意识。器物能映射出中国的社会变迁轨迹,方李莉在其研究中渗透着浓厚的历史意识感。譬如她细腻地分析了中国历史各朝的器物美学,采用历史的线性因素分析中国瓷器的美学品位的变化。她分析了中国在唐代瓷器的日用化进程,体味到“动物纹装饰题材逐渐被植物纹所取代。 ”[15]她用器物的纹饰来印证中国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向,观察到从器物的型器变化来看,元代走向世俗化。从元代的陶瓷纹饰中,辨认出了中国陶瓷“由雅向俗转化的一个重要开端之一。 ”[16]她比较了明清时期瓷器的美学品位,总结出明代青花瓷 “色彩明丽” [17]而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则显现了“完全不同的世俗美。 ”[18]在此,她的浓厚的历史意识渗透到对器物的美学价值观,准确地体味了中国陶瓷器物审美世俗化的走向脉动。她将器物文化置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器物的器型及纹样的历史流变,显露出中国文化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追索。在此,展现了中国器物的审美走向。早期器物,主要作为一种礼器。东汉时期之后实用器日渐增多,日用器之中的六朝青瓷的装饰依然具有宗教意味。而隋唐五代世俗转型,宋元得以发展,明清器物世俗化更趋明显。她的著述不仅是关于陶瓷艺术的历史描述,同时是关于中国文化艺术历程的理解,映射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认识” [19]。因此,方李莉的陶瓷文化研究,同样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变迁轨迹。这是她深厚的历史意识对于著述的渗透,使得文字注入了浓厚的历史意识。
同时,她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末民初景德镇窑业的社团组织及行帮进行了访谈,鲜活地再现了“血缘”“地缘”与“业缘”的传统在新的窑业中的灵活重构。她叙述的那条名为“樊家井”古老街巷,还有那鲜活生动的陶工故事,阐释与叙述了这一类型的群体与器物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她的著述注重窑业传统的历史,在历史中分析窑业的行帮、窑户、坯户、红店。战国时期,中国丝绸销往罗马,在汉代销往欧洲。唐代,中国的海上陶瓷之路,将陶瓷扩展到亚洲各地区,同时到达北非与东非地区。明清之后销往欧洲和美洲直至全球地区。此外,中国的茶叶、家具、漆器也陆续输出。同时,文化也随着器物而渗透到不同的国家,异民族与异文化在中国整体文化演进中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历史过程就是民族迁移、融合、相互影响、人种特征的改进、文化变迁和发展的过程。 ”[20]她考察细致入微,即具有平实的叙述语言,更具有批判性思维。因此,在她的研究中植入了一种深刻历史意识。
四、在世界之上:思想与文化的交流
方李莉的恩师先生非常推崇实证研究,先生提出光辉的 “从实求知”思想。他指出 “从实求知,就是不断地、全面地深入田野工作求取人类学的知识。 ”[21]方李莉一直真诚地传承了师门的学术精神,注重面对现实人民生活的关怀。先生曾在《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论她,“你的研究不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而是到生活实践中去,亲眼看人做的事情,亲身体验社会的发展,这是很好的” [22]。
方李莉的著述十分关注中国对内及对外的交往。在对内文化交往方面,她将官窑与民窑、南方窑口与北方窑口、中原窑口与边缘地区窑口的技艺交往纳入研究。譬如少数民族辽、金、元统治时期陶瓷对于中原陶瓷文化的交往。在对外文化交往中,编入了丰富的外销瓷篇章。此外,对于外销瓷的研究,不仅对于外销瓷的贸易路线与港口做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对于外销瓷器形、纹饰做出了丰富的图像研究。采用图像证史方法论,详尽论述了外销国家的文化影响以及瓷业影响。在行文中,多关注因瓷器的流动,因瓷器的载体而生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技艺与文化的流动与交往。难能可贵的是,花费大量人力与物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采撷图像,同时,在国内外的考古文献中发掘新的考古图像。这些书法体现了其深刻的历史书写意识。譬如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方李莉在美国的皮博蒂 ・艾塞克斯博物馆发现了清朝外销瓷的《广州全景图》与《广州黄埔码头图》,同时,还发现了《19世纪的澳门》以及《中国瓷器作坊》等接近 20幅稀罕的图像资料。她采用这些图像资料,充分论证清代外销瓷的繁荣的外销事实。在具体外销瓷研究中,不仅考察其外销路线和港口,分析其类别、器型、纹饰,更对对外传播的陶瓷技术以及当地陶瓷业的交流互动进行了深入剖析。
因此,方李莉的研究正是携带着这样一种历史感,去体味人民的生活,去描摹市井的气息,用闪亮的中国思想来照耀社会的尘埃。
注释:
[1]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城旧事[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
[2]方李莉.景德镇民窑[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3][22]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代序9.
[4]方李莉.中国陶瓷史[M].济南:齐鲁书社,2013.
[5]方李莉.方李莉陶瓷艺术[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6][7][8]方李莉.传统在现代化中的重构:景德镇田野札记[J].装饰.2008(1).[9][10][11]王永健.方李莉.立足本土立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6):6;6;7.
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2
>> 电影《成吉思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文化人类学的身体动作研究及其对体育人类学的启示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语境问题 文化人类学的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赏析《故乡》中的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情怀 图像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探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 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及其在华语世界中的表达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计量分析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票据研究 “双轨水利”:农村水利运行机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广西南丹那地村“地牯牛”运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以文化人类学视野论旅游文化 佛教仪式音乐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对心理影响的价值挖掘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边远地区教师继续教育的主客位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构建 花鼓起源:文化人类学视角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 朴一根. “拔河也被韩国抢占”――拔河登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不高兴了[EB/DL]. (2015-12-03) [2015-12-07]. http://.
[5] 任章赫. 传统体育拔河的历史[J]. 韩国体育学会会刊,2009,14(1):105-115.
[6] 朴开洪. 韩国民俗学概论[M]. 首尔:萤雪出版社,1997.
[7] 金光彦. 东亚细亚的游戏[M]. 首尔:民俗院,2004.
[8] 新罗时代的遗物,民众的东莱索战[N]. 韩亚日报,1938-01-05(01).
[9]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38[M]. 首尔:民俗文化促进会,2006.
[10] 洪锡谟. 东国岁时记[M]. 首尔:民俗院,1989.
[11] 今村昌平. 民俗人类学体系[M]. 首尔:民俗院,2009.
[12] 国史编撰委员会. 韩国史料丛书・续阴晴史(下册)[M]. 首尔:国史编撰委员会,1980.
[13] 崔永年. 海东竹枝[M]. 首尔:奎章阁,1925.
[14] 郑观海. 观澜斋日记[M]. 首尔:国史编撰委员会,2001.
[15] 封演. 封氏闻见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 韩国史料丛书・舆地图书・补遗篇[M]. 首尔:国史编撰委员会,1980.
[17] 村山智顺. 朝鲜的乡土娱乐[M]. 首尔:集文堂,1992.
[18] 许龙镐. 民俗游戏的全国性分布和农业性基盘――以拔河、摔跤为中心[J]. 民俗文化研究,2004,41(2):41-60.
[19] 六千名的大蟹戏[N]. 东亚日报,1921-03-21(03).
[20] 徐永锡. 重要无形文化财保存20年[J].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1984(17):364-386.
[21] 宋英柱. 我们国家拔河的体育考察[D]. 清原郡:韩国教员大学,1993.
[22] 表仁柱. 荣山江流域拔河文化的构造分析和特征[J]. 韩国民俗学,2008,48(11):299-332.
[23] 徐钟源. 拔河性格的持续和变化――以近代橹行[J]. 实践民俗学研究,2011,17(2):157-190.
[24] 李昌植. 拔河的传承和正月元宵节[J]. 韩国文化和艺术,2015,15(3):207-252.
[25] 张筹根. 关于拔河的研究[J]. 韩国文化人类学,1968(1):56-62.
[26] 苏赫肃. 稻作文化性拔河的传承研究[J]. 南道民俗研究,2011,22(6):135-167.
[27] 林在海. 岁时风俗[J]. 韩国民俗学,1990,23(9):285-308.
[28]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9] 何星亮. 中国图腾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0]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1] 尹光凤. 岁时游戏的性象征体系[J]. 韩国民俗学,1995,27(12):257-281.
[32] 何根海. 绳化母题的文化解析和衍译[J]. 中国文化研究,1998,19(2):74-81.
[33] 苏赫肃. 韩国拔河的稻作文化性格[J]. 农业史研究,2010,9(2):1-16.
[34] 任兆胜,李云峰. 稻作与祭仪:第二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5] 魏征.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M]. 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36]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1]WotgeLepenics: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inthesociologyofscience,in"SciencesandCultures",EditedbyE.MendelsonandE.Elkana,D.ReidelPublishingCompang,1981,p.245,p253.
[2]KarinKnorr-Cewua:"TheEthnographieStudyofScienelifieWork:TowardsaConstractivislInterpretationofScience,in"ScienceObserved",EditedbyR.Knorr-CentinaandM.Mulkay,SagePublicalionLtd,1983.p.115,pp.117—118.
[3]YehudaElkana:AProgrammaticAuemttatanAnthronologgofKnowtedgein"SciencesandCultures",P.6.
[4]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5]BarryBarnes:ScientigieKnowtedgeandSociologicdTheory.RoultedgeKeganPaulLtd.1974.p.63.
[6]DavidBloor:ScienceandSocidlImage,RonteedgeKeganPaul&fd.1976,pp.4—5.
[7]DavidBloor:Wettgenstein-ASocialTheorgofKnontedge,MacmillanEducationLtd.1987.p.83.
[8]MichaelMulkay:ScienceandtheSociofogrofKnonfedge,GeorgeAllenandUnwinLtd.1979,pp.68—95.
[9]Ethnography,BritanicaVoi.4,pp.583—584.
[10]R.S.Anderson:TheNecessaryofFieldMethodinFliedgmmethodofScientificRecearch,in"ScieneesandCutlures,p.218,p.216.
[11]BrunoLalour:LaboralorgLifePrinceton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KarinD.Knorr-Cetina:TheMonut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13]"Precoce",in"KnontedgeandSociety: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Vol.9,1992,"JALPressInc.p.x.
[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法〕乔治•梅塔耶、贝尔纳尔•胡塞尔著,李国强译民族生物学(上)[J]世界民族,2002(3)
[2] Justin M Nolan Ethnoecology[A] 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2)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3] Victor M Toledo What is ethnoecology?: origins,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discipline[J] Etnoecologica, 1992(1)
[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苏〕BN科兹洛夫关于民族学的界限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苏〕Ю•В•布朗利从逻辑系统分析看民族学的对象[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苏〕科兹洛夫著,黄德兴译民族生态学的任务[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3)
[9]〔苏〕B科兹洛夫著,王友玉译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J]国外社会科学,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苏〕尤里•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瑞译民族与民族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J]民族研究,1995(3)
[16]〔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民族论丛,1984(3)
[17]任国英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24]Sergey Sokolovski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Russia: Draft Case Report [Z] Paper presented at “Anthropology in Spain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Madrid, September 2-7, 2008
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5
专题、专项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从第1期开始推出“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的讨论。这个讨论专栏分别对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多为知名学者进行专访。所涉及到的论题主要为:如何看待音乐人类学?目前所关注的学术热点?
在专访中,韩锺恩提出“音乐文化人类学”,力求考证文化状态是否对人的自然状态有影响?包括文化人类学对体质人类学的作用。“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提出希望从音乐和文化的关系平台上去理解音乐人类学的审美经验。音乐人类学与音乐美学两个领域不仅可以互动,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整合。
薛艺兵目前关注的学术热点为音乐民俗学的研究,并于2007年底完成了书稿《音乐的民俗模式――中国民间音乐的民俗学研究》。该论著从音乐人类学视角进行音乐民俗学研究,应用了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阐释出中国民众音乐生活中如何构建起音乐的民俗模式,又怎样受制于这种模式的一系列音乐的和文化的规律。杨民康谈到了仪式音乐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现在学界提出的精神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的三分法较为合理,从这个角度看仪式音乐中的仪式化因素更多涉及了音乐行为,应该定位于社会文化层面。李海伦提到了近些年的热点“离散和全球化论题”,大量移民社群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对象。汤亚汀对音乐人类学的概念解读是:在当地和世界两种空间的互动中,一种音乐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如何反映特定的文化和社会方面,哪些方面被全球化了,哪些维持了自己的独特性,虽然会有许多变化,在变化中又生成了哪些新的意义。
杨燕迪认为音乐人类学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和研究各个不同的族群和人群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中应用“音声”材料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蕴,以及产生这些“音声”材料的内在机理和风格条件。并且认为音乐人类学与历史音乐学在渐渐靠近。目前,完成了著作《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西方音乐文化批评》主要是通过音乐人类学的文化视角来看待西方艺术音乐。他认为,目前高校学科目录中“音乐学”被当作整个音乐学科的总名称,这种现象使得音乐学和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生活和知识生活中的功能与定位模糊,出现了所谓“大音乐学”(指整个音乐的学科,包括作曲、表演和理论研究)和“小音乐学”(指音乐的理论学科)之分。萧梅认为田野作业自身的经验制度史,是学者撰写“民间音乐文化书”(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而言)的历史叙事。她强调田野作业与历史叙事的密切相互关照,以及田野调查过程不是单方向、单维度的授予与被授予,而是寻求“对话”,寻求多元的视野和心态。
由上专访讨论,可以看出近些年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课题组成果显著。除此之外,还有于会泳先生及其专著《腔词关系研究》的专项研究。
戴嘉枋在《论于会泳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音乐艺术》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于会泳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进行的研究,包括民歌、说唱、戏曲以及他的综合音乐理论研究。他在“综合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了,“腔词关系研究”、“句式研究”、“结构规律研究”、“宫调研究”、“唱腔与伴奏研究”和后来提出的“润腔研究”。此外,在京剧音乐研究领域于会泳进行京剧现代戏音乐的研究和“样板戏”音乐创作,有许多创新意义的成功经验。
沈洽在《〈腔词关系研究〉读解――第四章 腔词节奏关系:腔词节奏轻重关系》(《音乐艺术》第1期)一文中,对于《腔词关系研究》著作进行解读,提出“腔词节奏关系”研究基点:一是腔词节奏的“轻重关系”;一是腔词节奏的“段落关系”。中国传统声乐中的“板眼”和西方古典音乐中的“节拍”只是形似,而非同质。“板眼”只是一种伴随音乐过程中参考性的量度,而非音符运动前绝对化的制约。腔词节奏轻重关系,确切的指唱腔节奏的强弱变化与唱词音节的响度变化的关系。“创腔”对于“演唱”而言,主要是音节元音时值的长短、元音调值的高低、声调调域的宽窄、声调调型的完整程度和音强的大小。唱词节奏的轻重类型分为“习惯轻重音”、“特意轻重音”和“节拍轻重音”。该书中提到的:唱腔“不受(唱词)节拍重音的制约,并无害处,反而有益;而接受(唱词)节拍重音的制约,并无益处,甚至可能有害”在今天看来也是对中国传统声乐创作经验很精辟的总结。
文化中探究音乐
2008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从文化的角度探究音乐,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究民族音乐的相关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姜姝在《后传统社会里的民间音乐守护者――英国北部城市酒馆民间音乐集会个案调查》一文中,以英国北部城市谢菲尔德市酒馆民间音乐集会为个案?熏对其生息空间、参与者、活动特征及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查和事象分析之后得出:处在文化边缘的英国民间音乐集会充满着强大的生命力?熏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现代日常文化生活中?熏传承着英国民间文化的传统?熏成为英国酒馆不可缺少的文化事象。社交性生活酒馆空间不仅给予了民间音乐集会一个固定的生息场所?熏而且轻松、自由的氛围激发了集会参与者的热情?熏增进了人与人的亲和力,并为传承民间文化创造了契机。集会参与者成为后传统社会里传统的真正守护者?熏以音乐实践活动延续着这种鲜活的民间音乐传统。
杨民康在《中国音乐》第4期发表《论布朗族人生仪礼与个体音乐活动过程》一文。该文提出在布朗族传统的社会民俗中,诞生、成年、婚、葬四大人生仪礼习俗,标志着每一个社会成员成长过程的四个重要阶段。一般认为,人生仪礼同“过关仪礼”有密切关系。在过关仪式的分离(脱离)阶段和聚合(进入)阶段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阈限)时期。通过对人生仪礼及其阈限阶段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种民间音乐类型,其实完全可以纳入这个人类学――民俗学的人生发展周期及结构框架内来做整体性描述和分析。通过对人生仪礼与阈限阶段“一维两阈”环链中存在的模糊性、混融性以及阶段性、渐进性等结构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布朗族传统音乐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音乐的诸多艺术与文化个性特征。
蔡际洲、许璐在《鄂州牌子锣的变迁》(《中国音乐学》第4期)一文中,以2006-2008年作现状调查时获取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并将其1980年代的调查资料相比较,从乐人与班社、乐队构成、演奏曲目、音乐形态、演奏程序等五个方面,对鄂州牌子锣20年间的变迁状况作了比较研究。黄妙秋在“广西北海D民咸水歌研究”一文中,认为在地理环境和历史社会境遇的影响下,北海D民咸水歌音乐形成自身独特的音乐特征、歌唱风格和审美思维,它处于复合的双重边缘文化状态,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化内涵。
解B然在其论文《阿细跳月与萨尼大三弦舞――两个彝族支系音乐、舞蹈及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中提出,“阿细跳月”、“撒尼大三弦舞”是云南彝族阿细支、撒尼支的传统舞蹈。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阿细跳月”、“撒尼大三弦舞”已由原来的婚恋乐舞活动变为各阶层群众共同参与的娱乐性活动。由于“阿细跳月”、“撒尼大三弦舞”在音乐、舞蹈和文化功能上都有极为相似的特征,因此该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同时,借助于其他的音乐分析手段如“申克分析法”和“简化还原”的思路,归纳出“阿细跳月”、“撒尼大三弦舞”的音乐、舞蹈共性和深层结构特征。
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正如薛艺兵在《音乐研究》第六期中所说:生活环境的文化模式建构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而生活在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又凭借这些模式不断建构着他所处的环境。
仪式音乐研究
仪式音乐研究也是2008年度学者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研究领域。各位学者主要针对具体的田野调查成果,或进行学理分析、理论提炼;或进行音乐文化分析;或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田野调查的数据进行解读。
蓝雪霏在《畲族仪式音乐与盘瑶仪式音乐文化之比较》(《中国音乐学》第1期)一文中,认为畲族与盘瑶有着共同的祖先崇拜和共同的神灵信仰,有相似的原始巫术与道教相结合的道统和学法经历,有相似的仪式类型,但其法事音乐暂时尚难找到共同点。
陈燕婷的《安海雅颂南音社迎请郎君神像开光与安位仪式研究》(《中国音乐学》第2期)是作者亲自到福建安海雅颂南音社进行田野调查,对迎请郎君神像开光与安位仪式进行研究,并对郎君神像开光、安位仪式的缘起、过程、音乐、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齐琨的《灵验的音声――浙江省富阳市龙门镇元宵节灯会仪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第3期)认为,“灵验的音声”可以视为信仰具有灵验性的音响表现。在龙门镇元宵节灯会中,信仰的灵验又具体表现为祖先崇拜和龙神信仰的持续有效。该文对“音声如何具有灵验”和“音声为何具有灵验”的问题进行回答,并阐释了仪式音声得以有效存在与持续存在的动力因素。
孟凡玉的两篇论文《两腔三调:荡里姚傩仪式音乐唱腔的原生分类概念及其文化内涵解析》(《中国音乐学》第1期)和《贵池傩仪式音乐研究三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都是对安徽贵池荡里姚以及周边村落参加傩仪式乐舞表演者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当地傩仪式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唱腔类型:傩腔、高腔、歌调、吟诗调和诵经调。这些分类概念中透露出唱腔的历史与“出身”信息。从安徽贵池荡里姚两支高腔曲牌来看?熏仪式音乐在传承中具有稳定性的一面?熏但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从歌调在傩戏、目连戏和民歌中并存的情况来看,仪式音乐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地其他音乐种类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的;从“局内人”的“吟诗调”概念来看?熏“吟诵调”不仅和音乐形态有关?熏更和曲调的使用场合密不可分。
杨殿斛在《濡化・互惠:乡邻参与丧葬仪式音乐活动的价值取向――黔中营盘民间丧葬“救苦”仪式音乐活动的人类学解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中,认为民间音乐的盛衰消长是乡民社会生命追求对文化变迁境遇自觉调适的结果,而乡民参与乡邻丧葬活动的核心仪式――“救苦”仪式音乐活动,是传统乡民社会孝道濡化的现实需要,是乡民概化互惠生存伦理的典型体现,音乐?穴音声?雪既是仪式形式也是仪式内容,在营造神圣语境的同时起到了重要的神圣叙事作用。
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
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在2008年也是学术界讨论热点之一,学者们集中于对历史进行反思、总结,并对未来的传承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邱怀生在《富裕的贫困――浅析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国音乐学》第1期)一文中,认为当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地使民间音乐处在了文化生态的边缘地带。2005-2006年的田野调查分析显示,各个乐种的弱化成为摆在学者面前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问题。政策方针、学者视角、地方需求及其表演民间音乐的人的个性选择是音乐生态系统中直接对民间音乐文化产生影响的四个重要因素。
周吉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中国音乐学》第3期)一文中倡导:保护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对于不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和方法。注重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风格”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保护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传承人,是做好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张振涛在《民间文艺汇演的历史反思――保护民间音乐的一项措施》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舞台上一种特殊的汇演形式,大规模地调动地方民间文化资源,无意中塑造了,也形成了由汇演连带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为刚刚打算铺开自己视野的中国音乐学界,发现了大多数民间艺术品种。参与演出的民间艺人,则因为政府行为的权威性?熏彻底改变了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在20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晋京演出?熏参加调演?熏就是政府对一个民间艺术品种从内容到形式的政治肯定。从此,“下里巴人”变成“阳春白雪”,吹鼓手变成艺术家。一系列舞台上下的艺术活动,充分体现和反映出“国家在场”的巨大势能,成为我们咀嚼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向艺术化、现代化、城市化迅速转化的一条重要渠道。
除了以上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音乐》第1期中,还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于林青《曲牌音乐学习笔记(续篇、终结篇)》一文,对曲牌音乐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了一些探讨。
姚艺君《数字化时代的传统音乐分类问题思考》一文提出“声腔”的“族群”中大致包含两种类型:一类是“单亲族群”,如梆子腔、二黄腔;另一类是“多亲族群”,如高腔、昆腔、曲剧腔等众多曲牌(曲调)组合使用的戏曲品种。戏曲声腔以三种方式存在,即:全国传播性的声腔、地区传播性的声腔、非传播性的声腔。冯光钰在《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下)》一文中,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源溯流的探寻,从曲牌音乐传播历史及途径;同宗曲牌音乐与异宗曲牌音乐等五个方面,对曲牌的传播及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
冯洁轩先生在《纪念黄翔鹏发现一钟双音30周年》(《中国音乐学》第2期)一文,在黄翔鹏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纪念黄翔鹏先生发现一钟双音30周年,并对其发现及理论确证的过程进行了回顾。
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6
英文名称: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245
国内刊号:65-1039/G4
邮发代号:58-8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