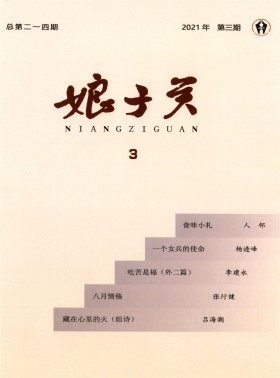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1
记者:为什么书名叫“土地的黄昏”,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背后蕴涵的是什么?
张柠:书名中或许包含着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一种对农耕文明、乡土文明消失的隐秘焦虑。离开故乡多年,回看乡土世界,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用“黄昏”来比喻。我在绪论里一开始就来描写“黄昏”的感受,它不是一种绝对的黑夜,也不是绝对的消失,它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在运动和生长。它仍然在那里改变着,以一种潜藏在暗夜中的形态。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晚上它是以一种元素和分子的形式在运动”。“动”与“静”是一组辩证关系,因此我用“黄昏”这个比喻,一方面象征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黄昏”本身不是一个绝对死寂的状态,它还是有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可能性。
记者:这本书的内容很多是基于您个人的乡土经验,按社会学常识来说,较为丰富的个人体验往往带着比较强的主观性,但读后感觉您写得很克制,作者的主体性在隐退,您在写作时是无意识地还是有这个自觉呢?
张柠:我觉得,这是搞文学的人的一个长处,擅长在叙述过程中选择和使用更合适的词语。我在写作和选择词语的时候,态度力求冷静,叙述力求客观,比如对形容词的使用就很谨慎。因为形容词主要是对一种个人感受的表达。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之中也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形容词很不可靠,使用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在学术著作中更是如此。但在文学创作里,为了加强文学性,达到个人对世界认知的强烈效果,会经常使用形容词,特别是古典浪漫主义的写作,它用大量的形容词来渲染情感力量。我不反对民俗志写作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但我自己比较谨慎,在写作的时候,我极力过滤个人色彩,尽量多地用名词和动词去描述,让观察和叙事视角往后退,保持视角的相对客观。当我脑海中的某个事物通过回忆的方式摆在我面前时,我会描述它是某一个空间结构里的一个要素,呈现它跟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形容它,尽管我有大量的个人经验,仍然尽量滤去个人化的感受。
记者:既然书中所写的内容并不单纯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层面。那您是如何实现从个人层面的乡村经验向集体层面的跨越的?比如您是江西人,但我作为福建人读后也有同感,可能贵州、云南等地的读者看后也有共鸣,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柠:面对农耕文化,我会发现一件事情表象背后更根本的一个构成方式,或说,这个事物、动作表象背后稳定的规律,我要捕捉的就是那个不变的东西。如果我只描述事物的表象,它就成了一个太个性化的对象。比如说刈草,蒙古人的割草方式与江西人肯定不同。而当我不关心割草的表象,而关心割草动作和工具背后的一些原则,情况就大不同了。比如农民用短柄镰刀割麦子,用长柄锄头锄草,不是随意设计的,它要符合农具使用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在场原则”和“节约原则”。在场原则就是你必须把农具抓在手上,如果你用电门来控制它,那是使用机器,不是农具,也不再属于农耕文明范畴,而是属于工业文明。第二个原则是节约原则,如农具的柄要安多长,必须是根据农民弯腰和直起腰来所使用的、消耗的能量来计算的。锄草时要用长柄,因为草除掉之后,不需要再回收,直接让它在田里晒干或者腐烂,还可以做肥料。因其不需要回收,农民就可以省去弯腰捡拾的动作,所以锄头用长柄,劳动时拿在手里保持站立即可。割麦子就不同了,它需要弯下腰割下麦子再捆绑起来,这时用镰刀,省去了一个再直起身的动作,这就是是节约原则,节约动作、时间和体力。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在对农民使用工具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了其背后存在的稳定结构,在场和节约,无论你是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内蒙的,如果不符合这两个原则,那就不是农民了,农具也不是农具了。所以通过对一个客观事物的呈现,力求发现它背后不变的恒量、程式。我不直观地去描述表象,所以我的方法还不能完全说是民俗志的写作方法,描写是一个起因,结果是指向背后的规律的分析,或者叫文化哲学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民俗志的方法就是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哲学的分析方法却是我看到许许多多的表象,但我要对它进行归纳、抽象成一个模型。这样不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方的人看后也会产生认同。
记者:您的书里描述了最日常的乡土生活,对有过乡村经验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但您以一种重新发现的眼光对它们进行了陌生化的加工,这会不会反倒拉开了读者们的心理距离呢?
张柠: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学的文科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喜欢读的人里又有两类,一类是情感式的阅读,这类读者熟悉乡村经验但自己不知如何表达,他一方面觉得你说的很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勾起了他对乡村的回忆,所以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伴随着乡土文明的情感的。另一部分读者实际上对乡村不熟悉,对农村没有太多情感,但他会发现这本书所运用的方法本身的智性触动了他。我的描述跟一般的理论书不同,是把事物从杂乱无章的符号世界带回到原点,再从原点出发,重新描述和编码。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一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展示,这对于乡土经验不丰富的学生来说,是有挑战性和新奇感的,看到把众多无章可循的东西拼成这么严谨清晰的图案,他们更感兴趣。
记者:还有个问题我比较感兴趣,您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事实上您已经离你的家乡很远很久,那现在您觉得和家乡的联系,包括情感上和身体上的,或者说故乡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张柠:童年回忆镌刻在你的记忆之中,往往是比较深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它的存在不因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爱它还是不爱它而有所改变,是一种镌刻得非常深的印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国度里的人,天生有着对土地和祖先记忆的基因。我们没有更高的、具有超越性的仲裁者,我们只有一个出生地的概念,有人称之为“我的血地”,有人称之为“我的第一哭处”,我更愿意称之为“出生地”。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但为什么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叫做“张家村”的故乡的记忆呢?其实不仅是作为出生地的“故乡”,凡是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记忆,比如我曾经生活过的上海和广州,我都会回忆它。比如,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很多记忆,这些记忆是和一些场景、感官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某一条街道、街道拐角的一棵树、某种食物的味道,某处的气息等等。这些记忆的呈现,往往是作家的重要写作动力。我的书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童年回忆。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它镌刻在我记忆里的一些痕迹,重新描述出来。我说的是“痕迹”,痕迹不是情感、不是颜色和气味,可能是一个几何图案,以及这种图案的文化背景。此外,的确还包含着一种寻根的冲动,我们来自哪里?将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根是在土地和血缘,我们没有全人类意义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只有血缘意义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问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怎么喜欢“同乡会”那种东西,我不认为只有家乡的人、姓张的人才是兄弟姐妹,我认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姐妹的观念。这种价值观打破了地域和血缘的限制,是“世界城市”的新要求。所谓的“世界城市”的观念,就是不同的人群,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契约”关系上重新结合在一起。
中国乡土“熟人世界”是不需要契约的,靠传统道德规范就行了,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人”和“君子”,要求太高,所以经常出现“伪君子”。伪君子就不如“先小人后君子”,意思就是先订契约来限制你。乡土社会里的人对“契约”很不习惯。到了城市里面来,和陌生人打交道,契约也没用,中国人是不讲契约的。除非变成兄弟,喝酒喝成了兄弟,他可能会很关心你,或者是老乡说一样的口音,这是农耕文明里的人还能团结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从这个文化里面出来的人的非常大的局限性,他只跟熟悉的人、共同血缘的人打交道,不熟悉的人一概视为潜在的陌生人,潜在的敌人,是需要提防的、反对的、消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必须先变成亲属关系,比如说兄弟、姐、婶,换成家里面的称呼,他才可以跟你交往。对这样一种价值观念我内心是不认同的,我纯粹是把我所知道的乡土文明的东西,变成一个解剖学的对象,将它的元素呈现出来。
记者:那本身这种乡土经验对您的价值观,对您的心理有多大影响,或者您现在回头看,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柠:潜在的影响还是有的。比如说,我对城市生活中那些变化的、新奇的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好奇、喜欢刨根问底。但是我也有很保守的地方,你比如说自己的生活中不喜欢变化,迷恋重复性的东西。饮食中我就喜欢那几样东西,老吃,吃家乡菜的口味,抽烟我不抽洋烟(生烟草或者混合型烟草),洋酒我也不喝,只喝中国的烧酒。我儿子一代喜欢吃的西餐,我都吃不惯。所以我的肠胃还是一个“乡土肠胃”,这个“肠胃”习惯隐藏得很深。表面上我会说“吃什么都行”,其实我喜欢的还是家乡饭菜的口味,喜欢长江流域的口味,或者说南方的口味。北方菜我也不习惯的。我也不大喜欢山水、风景那种东西,小时候就在农村长大的。整天看风景,有什么好看的?我着装也不喜欢变,比如说一双皮鞋我很喜欢,穿破了,我还买一双一样的。就是这种很细微的,跟身体层面相关的,跟肠胃相关的,还是很有农民性的。我称之为有着一副“农耕文明的肠胃”。
乡土社会:“熟悉”与“陌生”
记者:关于宏观权力说法较多,如“皇权不下县”以及1949年之后我们对农村的改造,您在书中却回避了对宏观权力与政治的直接解析,而以微观权力切入乡土社会的肌体和灵魂,为什么您会产生这样一种视角,并用它去分析乡土文明或说乡村意识形态?
张柠:“微观权力”实际上是被词语判定的一个静态事件内部细微的动静。宏观权力可能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微观权力却是在一个看似静止的动态内部的细微的冲突和矛盾,它可能会表现在乡土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细微的变化上。
乡土文化、农耕文明之所以逐步地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工业革命所取代,被城市文化所代替,我不认为完全是宏观权力的原因,当然宏观权力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包括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城市文明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变成城市文化的一种大的格局。我觉得这种格局的出现,这种巨变的背后,还是会有很多细微的动因。动因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农耕文化里感到不舒服,想离开。这群想远离乡土的人里大部分可能是智力很发达,体力不是很好,敢于求异、求变、求新的人。而能够忍受乡土社会静态状况并且恪守那一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可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愿意过一种用身体和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生活的人,就留在了乡村。留下来的人一来是身体素质比较好,二来可能是思维中固化的比重压倒了变化的,不愿折腾。我认为之所以导致一批人在乡土社会里感觉不舒服而要离开的现象,就是其中的微观权力在起作用。农耕文明排斥那些体力不好但智力很高的人,排斥那种不能忍受重复生活而求新求变的人,排斥那些脑子很活泛、想法很多的人。我想这是我从农村走出来,将城市生活与之相比较而发现的一个冲突。乡土社会作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可能很有诗意,但当你真正身处其中却感到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根源,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微观权力。
记者:先生对中国乡土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他曾说,从根本来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土的中国,您在书里也突出了现代性和传统农民文化心理层面的对比和冲突,但其实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也是有着相互渗透和博弈的,对此您怎么看?
张柠:先生的“乡土中国”研究不仅是中国理论家的原创,在世界的社会学研究里也有特殊的地位。是他首次把一个无法用现代逻辑与语言言说的对象,通过几本专著阐释出来。其中有些命名十分精辟,比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等,都用很简短的术语,就把我们不曾知道或知道而无法名状的一种“存在”一语道破。前辈对于乡土文明、乡土社会的研究也是我的研究的基本起点,还包括杨懋春、许烺光、林耀华,这一批老一辈的学者的著作我都读过。在阅读过程中,我一方面惊叹于他们高度抽象总结和命名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们的有些命名在我熟悉的乡土经验中也并不完全能解释通。他们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田野考察,有它特殊的敏感性。但是,像我们沉浸在乡间十,对乡下的农民的一举一动,眨巴眼睛,叹一口气有什么隐秘含义,都非常熟悉,而这种东西是田野考察考察不出来的。
我在这本书里面十分关注的不只是“熟人社会”,还有它的镜像:“陌生人社会”,它属于“熟人社会”共生在一起的,同时又是对立面。既然“熟人社会”是描述乡土社会是怎么团结到一起的,那么“陌生人社会”则是描述这个共同体是怎样分崩离析的。熟人社会内部也是有很多陌生性的,它要维系这个熟人社会的高度的统一性、整一性和团结性,必须在不断的生产实践和道德规范里面排除掉陌生性。而这种熟悉性和陌生性,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内部共同存在的两个要素。农耕文明排斥陌生性,也是压抑和制约人性中的要素之一,所以有些人会感到不舒服。
农耕文明的熟悉性,建立在高度统一的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上,所以它的家族繁衍和两性关系的道德准则的建立,是首先维护熟悉性而否定陌生性的。比如,血缘的熟悉性对学院的陌生性的排斥,体现在对所谓的“家种、野种、杂种、私生子”这四类人的不同态度上。因为它搅乱了血缘关系的纯粹性和熟悉性。另外,还有价值观念上的陌生性。比如说,农耕文明认为劳动或生产(谷子和儿子)才是唯一的最高价值标准。而有一种陌生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但被压抑下去了,那就是“惰性”——不愿意用自己身体或汗水与土地进行能量交换的这种人,在乡土社会是受排斥的。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是用脑力代替体力的人,商人和科技发明的人就是属于这一类。这样一种使得世界上的资源得到高效的运用的智力行为,在农耕社会却被排斥。所有乡土文明社会内部微观权力的争斗,都是以熟悉性去排斥陌生性为底色的。所以我的书的重心是用陌生性来描述乡土社会的离心力,而用熟人社会来描述的是乡土社会的向心力。因而我这本书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而且它崩溃的原因并不只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文化,也来自于乡土社会内部的离心力,人性的复杂,我描述的就是乡土文明价值观是如何排斥陌生性的。
记者:我阅读完这本书可以看出来在书的理论建构上综合了各种学科,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的尝试,那您是如何做到在书中融合这么多学科,以及这种尝试给您带来的困难多一些还是便利多一些,比如说,它可能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张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因为我在构思、设计这几大版块的时候,并未有意识地想到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新史学的方法,但这些领域的著作是读过很多,也许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我的思路与那些学科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我们的学科设置往往不是寻根究源的,而是从事物发展的半途开始的。而我觉得学术思路应该是,让任何一个问题都回到它的原点上去。特别是人文学科,多是关于抽象的“人”的问题的讨论。回到原点就是回到“自然人”(生物学、动物学),然后才有“种的人”(人类学)、“群的人”(社会学)、“精神人”(美学和心理学)。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随之你会考虑自身如何在自然中凸显出来,求得生存,如何学会一系列的技巧,这实际上是人类学的问题。之后你生存在这个世界就要与别人打交道,怎样压制个人欲望,摆脱丛林法则,与人相处,相处的规则是什么,这些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最后才是精神科学,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思维应该是这样的。因此我的思路就是把我所有的经验部分,我所想到乡土世界里的所有要素全部还原到最初的源头去。
正是基于此,我在整个社会构架的前面,加上了比较抽象的关于乡村时间和空间描述,也是我要客观呈现的乡土社会的事实。这个事实首先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在此基础上,生活在这个时空内部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个身处其中的时空坐标,这两方面共同呈现出乡土社会的基本时空结构、生产实践方式、对时间的理解等内容。在明确这些之后,我开始写乡村器物。这些器物包括家具、工具、农具、玩具,它们是跟人的身体最相关的、直接发生接触的东西。在一个村落集团里面,这些工具和器物被如何使用,它们又是怎样作用于人的身体,这其中的规则和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比如,有时通过工具使用的不同方式去实现群体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透过器物可以看出乡村内部社会化的过程。接下来就是纯粹社会层面的分析,如对人际关系、等级制、族长制、权力、职业等的描述,再后来才是文化层面的解读,如声音、歌声、传说、故事等。循着这样一种正常人的发散性思维的路径去写,它可能会歪打正着地把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等全串联在一起。但我当时在写的过程中,是严格地遵循了一种逻辑学和分类学的方法,有学者把它描述为从代数学、几何学到微积分,或者逻辑学、分类学、发生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一直强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方法——从里向外,从物质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
那么现在各个学科的人都从中看到自己研究领域的影子,但实际上这个著作,如果单独从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标准的任何一个角度切入,它都不像。就像有一位民俗学的学者说我的这本书看似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但因为描写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替换的对象,所以在这个维度上,它超越了一般民俗志的写法,它变成一个可替换主体、对象和内部零件的模型,这也许是很多人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可以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根据人与物的接触、人和自我、人和他人的接触而重新梳理出来。
乡土文明:现状与未来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在说“沦陷”,但回过头去挽救这种“沦陷”的人却很少,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乡土。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这样的“沦陷”是不是不可逆的,或者说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离去,会使这一“沦陷”加剧?
张柠:这里的“沦陷”本身是个社会管理范畴的概念,这一过程是个社会学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剥夺农耕文明的资源来养肥城市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沦陷”是资源配置这个意义上的“沦陷”,而不是说农村已经消失了,全是城市了。解决这个问题已有两个思路,一是既然城市各种强势,就让农村彻底消失,也变为城市;二是提倡城市反哺农村。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这就是十二五规划所谈的“城镇化”。我个人觉得“城镇化”最关键的问题是让农村“升级”,就像一个杀毒软件,升级后还是这个软件不是别的杀毒软件。同理,农村升级后还是农村而不是城市。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这几件事情:搞卫生,建厕所,打水井。我觉得十二五规划中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对十一五规划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伸和补充,举措不再仅停留在打水井、建厕所、搞卫生的层面,而是让自来水、抽水马桶进家,让村民室内过着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通邮、通水、通电、通路。这在西方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叫“居室革命”。这是“农村升级”的硬件方面。软件方面主要是教育网,不仅要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学,还要推进到孩子毕业后,能够有能力反哺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京漂”“沪漂”“广漂”,还要到家里去要钱。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资源配置的平衡是个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扎根,因需要花费的成本太大,但是其他地方的资源与这些地方相差又太大,所以人们不得不重返北上广。如果各地的资源分布是较均衡的,人们就不会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而是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我的家。
记者:现在还有个现象就是,一边是所谓的农村文明的萧条,一边是很多城市人对“农家乐”“乡村游”的热衷,这能代表一种乡土生活的“回归”吗?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柠:农耕文化变成消费品进入了城市人的视野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文艺青年的好奇心,比如说把农村的农具、手推磨、犁买回来,挂在酒吧的墙上或摆在地上。农耕文明对城市里的青年来说是正在逝去的历史,他们把农耕文明的遗物作为收藏,并把它作为招徕顾客的道具,这一消费农村的文艺行为,实际上是历史消费的一部分,真正作为商品的是历史。
第二种形式,是农耕文明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就是到农村去吃“农家乐”,实际上只是消费行为,而并不是打算返回乡村。
第三种是把乡村变成旅游景点。有些地方会把民国时期或晚晴时期乡村的完整的面貌保存下来,包括住宅里的厨房、客厅、门口的陈设或设施等。有的地方还会安排当地民风民俗的展示,比如浣纱、捣衣、车水等。农民都变成景点上的演员了。
最后一种情况是,部分城市人厌倦了城市。其实城市的优势在于教育、文化、权力各方面的资源和资本,但论空气质量、生活悠闲等都不如农村。所以有一类人进入城市掌握城市的很多资本后,一边骂一边还生活在城市。也有一类人掌握了很多资本,但是他厌恶了这种生活,就到终南山、峨眉山去隐居,有看破红尘的意思。还有一类人在城市里面资本掌握得不多,也没有享受到山水、新鲜空气,他们也返回到乡村去居住了。
不论是哪一种返回乡村,成本都很高。比如一个人卖了北京的一套房子,到广西阳朔、贵州的长寿村去居住,但一般住不长,久居会改变思维方式不适应城市生活,但他们的资源、资本还是来自城市,所以还要以城市生活为主。
由此可见,返回乡村的代价不菲,而乡下人想扎根城市成本也很高。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土地流转,让乡下人可以通过流转获得收益到城市里去买房子,变成市民。这样就方便实现城乡间的交换与流通,解决了进城难和出城难的问题。
记者:在日本考察时发现他们乡村基本完成了升级,他们现在有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叫“半农半X”。“半农”是指从事部分农业生产,“半X”指你仍可兼做其他职业。现在日本已有很多精英返回乡村,而且很有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当地的传统文化。日本几乎每一个农村都有自己的文化节,几百人的一个村庄都会有自己的画册供给游客做宣传。而在中国,乡土文化好像一直在萎缩,目前还看不到保护的自觉性。那您觉得,以后中国的乡土文明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日本这样复兴起来,还是渐渐湮没在城镇里?
张柠:像你说的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已经有保护乡土文化的自觉,是需要条件的。首先是要有剩余时间,这点我们农村是有的。其次,要有剩余资金,这点我们还不足。第三,想让农民自己完成文化宣传册的制作和传播,能力上也不够。随着以后整个一代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我觉得高中生就完全有能力去做一些文化事业,如果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也许这种乡土文化自觉的形成就指日可待了。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乡村也不会消亡,而是会升级。实际上,国家已经开始做了,现在已经开始免税,而且农民种地国家还会给补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黄昏之后黎明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