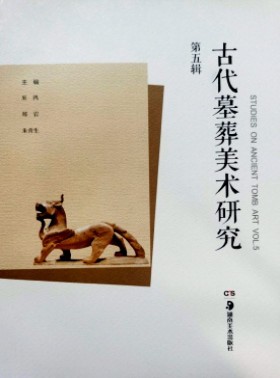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古代天文学简史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古代天文学简史范文1
一、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和网络化
(一)云南地方文献数字化资源。
在云南社会历史发展中,由于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语言文字、,形成了不同风格类型的民族文献,可概括为民族文字古籍、石刻、影片图片、汉文民族文献几大类。
民族文字古籍。云南有自己古籍传世的民族有:纳西、彝、傣、藏、白、壮、布依、瑶、傈僳等民族,其中以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彝文、傣文、藏文文献和白族文献最为珍贵、悠久。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还在使用的极少数象形文字之一,共1400余字,并以此创作出东巴经书1000余卷。东巴经记载了古代纳西族社会的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学的方方面面,是研究纳西族社会的百科全书;东巴彝谱,是迄今世界上唯一的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舞谱,东巴文是研究人类文字起源的第一手活资料,堪称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彝文古籍不仅有写本,还有刻本。如用彝文翻译的《太上感应篇》,原系云南武定茂莲乡土署旧藏,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部明版彝文刻本。如20世纪20年代杨成志赴滇民族调查时所获的《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是明代有年代可考的彝文抄本经书中最早的一部。其它如彝文《彝族天文学史》,《彝族医药志》,彝文文献《吴三桂》,《夷榷濮》、《尼苏夺节》、《洪水泛滥》、《裴妥梅妮》等均是彝文古籍中经典之作。傣文古籍中,贝叶经所占比例最大,号称84000卷的傣文贝叶经,是小乘佛教典籍中的精品:《芒策法典》是最早的傣文法规,在西双版纳长期保持法律效应;《囊丝本勐》记述了1180-1950年间西双版纳的史实;《论傣族诗歌》,虽成书于公元1614元,但对诗歌的起源发展、与佛教的关系论述已十分精辟。天文学是傣族崇尚的学问,《苏定》、《苏力牙》、《历法星十要略》等,都是重要的傣族天文学文献。云南的藏文古籍,以《格萨尔王传》为最着名。白族典籍较为特殊。白族创造了南诏文化,有语言但无文字,历史上曾用汉字记录白语之音,以《古通纪》、《玄峰年运志》为代表,而典籍以汉文撰写的居多。
石刻文献。云南民族地区的石刻,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史料。现存云南少数民族石刻文献,文种包括蒙文、藏文、满文、回文、彝文、纳西东巴文、傣文等,以丽江东巴文《麦宗摩崖》为最早,系宋宁宗、理宗时期的石刻;刻于1533年的彝文汉文合壁的《镌字崖》,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彝文石刻之一,石刻反映了彝族先民开发滇池地区的情况。此外,《德化碑》、《石城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等一些汉文少数民族的石刻文献,亦是研究云南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古代天文学简史范文2
(一)
公元五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罗马时代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有的成为设防据点,有的成为封建诸侯或主教的驻地,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统治西欧各地区的各个蛮族王国由于刚刚才脱离原始部落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这时,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其中,以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所组织的教育活动影响最大。僧院学校的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准备充当僧侣的儿童,称为Oblati,意味自愿献身者;另一种是学成后不准备充当僧侣者,称为Externi,意味外来者。前者又称为内学,后者又称为外学。除僧院学校外,还有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大主教学校设在主教的所在地,学校的性质与水平同僧院学校相当,学校设备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教区学校设在神职人员所在的村落,学校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教授一般的读、写、算和基督教的初步知识,它虽然是由教会举办的,但也向一般世俗群众开放。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这样,就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文艺学科教育)的学习课程。在当时的学校都设有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后者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两者和在一块即所谓的“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但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初期,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也停留在基本知识的传授上。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开始重新出现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欧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开始多了起来,人们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也开阔了,此时,教会学校已无法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于是,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大学。城市大学的诞生标志着西欧文化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它的出现又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分不开的。
和东西文化交通为大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发表煽动基督徒的长篇演说,为“征讨异教徒”进行总动员,以此为标志,开始了长达200年的。通过,欧洲人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在阿拉伯人占领的比利牛斯半岛和诺曼人占领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学者将古典文献和阿拉伯文献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由此,中世纪的欧洲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等。另外,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杰出成就,如阿维森纳的医学和哲学著作,阿维罗伊的哲学著作,以及各种代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方面的知识也都传人欧洲。这对于当时西欧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是一场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文艺学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外,新的三个高等学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也开始确立,从而为大学各学科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是市民社会的直接产物,它的组织形式来自城市和行会的组织形式,当时西欧城市各种行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在城市的发展中,兴起了各种手工业的同业行会、商会,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成为控制城市的力量。在行会的发展和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与规章制度,这成为了大学组织的榜样,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与教师行会。大学(university)一词由拉丁语universitas而来,而universitas本意为“共同体”,它是由介词Versus(往,向,朝向)与名词Unum(唯一,单独)构成,意思是“成为一体”。因此,大学在它诞生之初无非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学校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师联合成特殊的组织即专业行会,称为系或教授会(faculty),它是由拉丁语facultas而来,本意为才能,即教授某种科目的能力,后来开始把系这个名词理解为教授某部门知识的大学分部;学生则组成同乡行会,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简单来说,大学作为一种行会体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师傅(magister)与学徒(discipulus)的关系。
最早兴起的大学是12世纪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随后巴黎、牛津大学相继产生,到15世纪,整个西欧建立了近80所大学。据统计,意大利有20所,法国有18所,英国有2所,苏格兰有3所,西班牙有13所,葡萄牙有1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16所,匈牙利有3所,波兰、丹麦和瑞典各1所。由于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每个地方的大学都向各地学生开放,而不限于周边地区,这就使得那时的大学都有着很强的国际性,各地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自由到自己所喜爱的大学求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完成了以传统的“七艺”为内容的基本人文学科课程后,才可能进入法学、医学和神学等其他专科的学习。
(二)
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对所在地的条件及环境感到不满意,便会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继续办学。大学的自治性还表现在它享有其他一些特权,如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其成立之初都同当时的市政当局和教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中世纪大学按领导体制可分为两种类型。以最早兴起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称为“学生大学”,由学生主持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等,均由学生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法国(巴黎大学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称为“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瑞典、丹麦、德国等地的大学,则多属此种类型。
中世纪大学统一用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就使得欧洲各地的学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学习。不同的学科虽然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教学方法上却大致相同。如在当时的神学院,除了圣经外,最重要的教科书是彼特朗巴特(Peter Lombard,1100~1164)的《箴言四书》(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但其主要的教学方法仍是通行的讲授和论辩。讲授(lectio)来自拉丁语动词阅读(lego),即阅读指定的教材,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解,学生逐字逐句地笔记,授课的内容则被记录、整理为“注释集”(Commentarius)。论辩(quaestio)最初只是一种口头训练,后来演变为一种正式的教学方法。在神学院,论辩又分为两种,即问题论辩(quaestio disputata)和自由论辩(quaestio quodlibetalis)。问题论辩在课堂上进行,由教师提出一个论点,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由教师主持,裁定胜负。有时,由一名学生就某一问题的两面自己提出论据,自己辩驳,称为独辩。自由论辩则是在公开场所进行,一般是在降临节(Advent)后的第二周和四旬斋(Lent)后的第四、五周举行。自由论辩的规模很大,不局限于学术问题,任何问题都可提交讨论,参加的人包括学生、老师以及其他著名的访问学者。论辩的题目最后整理、汇集为“论辩集”(Quaestiones),各种题目的论辩集则进一步总汇为“大全”(Summa)。它的写作方式是围绕一个题目提出一系列问题,每一问题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作者先列举维护这些意见的理由,然后陈述自己的观点,最后逐一反驳其中一种意见的各种理由,并论证另一种意见的各种理由。
按当时大学的规定,文学院的课程需要4年半到6年,有的学校甚至要求7年。文学院毕业后,学生首先获得的是学士学位(baccalaureus),然后才可能继续申请硕士(magister)和博士(doctor)两种学位。当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无程度上的差别,它们的区别是,硕士考试不公开,合格者发给证书,取得教学资格;博士考试则公开举行,有隆重仪式。通过考试者,到主教所辖的地区,由副主教赐给学位。凡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统称为教授(professor)。事实上,学位制最初只是教师行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它起着决定职业标准和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的作用。学士最初根本就不是一种学位,它乃是教师行会所新招学徒的一种身份,这些年青人希望有一天也成为行会的正式成员。那些获得许可证,被接纳到教师行会的人,最初一律叫硕士,magister其本意就是师傅,表明已出师了,可以开始授课带徒,而博士或教授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
巴黎大学是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典范,是欧洲各国学生云集的中心,13世纪的巴黎有欧洲雅典之称。巴黎大学的前身是诺丹(Notre Dame)主教学校。12世纪初,学者香浦的威廉(Guillaume de Champeaux,1072~1121)在此主持校务,著名经院哲学家彼特阿贝拉尔(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1108年至1139年间也曾多次在这里讲学。起初,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按乡土组成德意志、诺曼底、罗马和英格兰四个同乡会,教师则按学科的不同组成艺学、神学、医学和教会法学(罗马民法在巴黎被禁止讲授)四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有权颁发本学科的教学许可证书,决定本学科的教学规则和学生纪律,大学的重大事务都由这几个教授会共同会商。巴黎大学鼎盛时期师生达5万多人,号称与教皇和皇帝一起并为欧洲三足鼎立的势力,因此,在当时就有“罗马有教皇,德国有皇帝,法国有知识”这种说法。到了13世纪,随着经院哲学的繁荣,它更是成了欧洲学者云集的中心,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在这里求学与讲学,不同学派与思想的论战也大都在此发生,因此,它更是享有“哲学家的天城”(Civitas Philosophorum)的美誉。
(三)
中世纪的大学产生以后,迅速成为欧洲文化复兴和传播的中心,也是随后进行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此外,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种种较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如希腊雅典的学院、阿拉伯的“智慧馆”和中国的书院等,但是,西欧中世纪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却是近现代世界高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
中世纪的大学是欧洲重新获得和了解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当欧洲还处于文化的黑暗时期时,却正是阿拉伯世界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彪炳于世的时候。公元7、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古代东西方诸多民族、宗教融合、碰撞的结果,它在产生之初即表现出勤于学习、尊重知识的特点,据说,穆罕默德曾对穆斯林发出“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号召。经过阿拉伯人200年左右的努力,欧洲古代的主要经典几乎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当这些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而为中世纪的学者所了解后,重新点燃了欧洲人的智慧,而这主要是在当时的大学展开的。
中世纪的大学直接促进了经院哲学的发展与繁荣。随着大学的发展,教会的势力也慢慢渗透进大学,经院哲学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内容。当时兴起的两个托钵修会,即多米尼克修会与法兰西斯修会更是积极向各个大学渗透,他们在大学的活动,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属于法兰西斯修会的著名学者有“不可辩驳的博士”(Doctor irrefragibilis)哈列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Halensis,1185~1245)、“六翼天使博士”(Doctor seraphicus)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悲惨博士”(Doctor mirabilis)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约翰邓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1265~1308)以及威廉奥康姆(Guillelmus de Ockham,约1285~1349)等;属于多米尼克修会的著名学者有“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以及约翰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等。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成为了中世纪神哲学的中坚力量,他们让他们的时代成为了欧洲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之一,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也成为了近现代哲学的重要源泉。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中世纪的大学体制为学者们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成为当时各方面学者活动的舞台。例如13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当时欧洲的科学中心,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在那里开始萌芽。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和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将柏拉图对数学的强调和亚里士多德对实验观察的强调结合起来,奠定了现代科学兴起的基础,他们自己也成为现代科学的先驱。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学的土壤上产生的。
中世纪的大学让“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讲,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作为实现某种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它是自由的人进行的自由思考,它有着其内在的价值,因此,科学活动更类似于游戏,而不是获取某种实用价值的工作。然而,这种理想唯有通过某种见证获得现实力量后才能表达出来,中世纪大学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就是一种见证,它让那种理想成为了现实的可能。在大学兴起以前,古代学院中的学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既是真理的追求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更是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帝王师。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成为四处游荡的乞儿,另一方面更是让他们活动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中世纪的大学通过知识活动的行业化,使得知识分子以“分子”的方式显现出来,让他们不再停留于“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说知识是由于对自己的否定,最终才被某种力量见证出它的价值的话,那知识分子也必须通过对自己的限定才可能为某种力量所见证。
以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传统式的书院教育就终结了,现代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然而,无论是从大学教育的理念,还是从大学的法律地位来看,我们的大学与西方大学又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构架、学科的分类等都使得回到传统书院几乎不可能,因此,重新审视和理解西方大学教育的精神,或许会让我们思考到更多的东西。 主要参考文献
(1).C. 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2).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3).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宏译,1999年.
(4).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
古代天文学简史范文3
关键词:建筑场;共生;康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3-0047-02
收稿日期:2006-11-28
作者简介:林煌斌(1981-),男(汉族),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
1 引言
人与环境处于共生状态,人创造了环境,生态、和谐的环境又会促进人的发展。在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里,既包括纯粹客观的物,又承载着人类思想和文化的物。波普把纯粹客观的物组成的世界称为世界一,把凝结人的思想和文化的物组成的世界称为世界三,人类的主观心理活动构成了世界二。在波普看来,世界三对于人的影响更大,它更为直接地作用着人的主观世界(世界二)。[1]本文认为,虽然波普的学说有片面之嫌,但他无疑指出了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的世界对于人类自身有着不可忽视的涵育功能。波普意义上的世界三包括可以弹奏音乐的乐器、凝结人类思想的书籍、体现人类设想的建筑等等。然而,本文并不满足于单纯谈论世界三对于世界二的影响,而是试图把建筑作为研究的核心,探讨通过建筑连缀起三个世界的整体对于个人的影响和作用。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建筑场的概念。它既不是纯粹的物理场,也不是完全的心理场,更不是二者之间的简单结合。建筑场包涵人本身及人相互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与建筑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融为一体。建筑场中人和建筑是相互塑造、相互共生的。本文提出的基于建筑场的共生哲学分析是源于笔者在阅读伊曼纽・康德哲学作品时的联想,如果要真正理解伟人的创作和思想时,是否应该到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参观,到他所曾经历的生活环境去体会,是否应该到与他创作思想共生成长的建筑场去体验?是否应该到康德故居到弗里德希炮台间的被后人喻为“哲学大道”的街道去体验?答案是肯定的。
2 建筑场概念阐述
建筑生态环境学是指人类建筑环境与自然生物共生关系的生态学。[2]建筑场就是人类建筑环境与自然界共生所形成的和谐整体,它包括建筑物、气候、山水、土地和植被等。在参与塑造生活在该建筑场中每一个内界(精神)的方面,建筑场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莫扎特是在18世纪非西方的建筑场中成长的,他的音乐语言将是什么模样?他还会攀登上西方古典音乐的顶峰?他还会有千载独步的成就?孟子主张:“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不仅指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也包括惊叹宏伟秀丽的建筑。宋朝苏辙则直接强调“……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而后知天下之巨丽”,也可见古人对建筑场的理解。
孔子故居面对阙里街,夹于孔庙、孔府之间,是孔庙中最古老的地方,门内为孔子故居,内有御赞碑亭、礼器库及诗礼堂等古迹,如果换成是古希腊建筑,那能和《论语》中的意象和语境对得上号吗?孔子一生除了住在鲁国外,其他时间都在周游列国。游览这些建筑场对我们了解孔子生平和学说是会有帮助的,至少提供给我们想象力的空间。
莫扎特经年累月接触、感知到的建筑,包括教堂、剧院、音乐厅和普通民居。所有这些环境结合一起营构了一个建筑场,这样的建筑场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在宗教、音乐方面,正如流水孤村、寒鸦古木的建筑场塑造中国古代诗人一样,这样宗教建筑场造就了莫扎特的宗教音乐,建筑场同音乐是共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语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圣・彼得堡18和19世纪的建筑(含教堂、修道院、火车站和普通人的住宅)是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因为在这两百年里,俄罗斯出了不少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从收集的建筑文献出发,笔者试图从这些建筑场中听出、见出文化巨人的文化创作同这环境建筑场内在、微妙和隐蔽的关系。如果这些建筑都换成欧洲建筑,那还有柴可夫斯基和他的音乐?还会有俄罗斯味十足的旋律吗?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俄罗斯的建筑场参与了“甜美忧郁”的创造。
建筑场同音乐、诗歌、绘画和哲学思维等都有微妙的内在关联,这微妙关联正是共生的哲学。建筑一舞台、人生一出戏,建筑场构造了大舞台,其他文明活动在该舞台上展开。
3 析康德哲学思维形成的建筑场
在阅读康德著作,在研究他的哲学继承关系时,常局限于哪些思潮对其哲学体系形成的影响较大,可以列出如牛顿力学、18世纪的天文学等等,几乎所有研究康德的传记著作都忽略分析康德所生活过的建筑场的分析。柏拉图说过:几何学把灵魂引向真理,产生哲学精神。建筑场是由无数个几何形体构成,康德的哲学精神不可避免地在建筑场中酝酿与共生。
3.1城市历史与“物自体”和“现象”的二分
“物自体”和“现象”的二分是康德哲学的基石。在康德看来,我们无法真正认知物本身,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主体对物自体给予人刺激的整理。对于康德的这个思想,我们不仅要从哲学史进行分析,更应该从康德所生活的城市历史与其理论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历史上,普鲁士曾经分为东、西普鲁士两个行政省,东普鲁士的首府叫哥尼斯堡。1724年康德就诞生于此,1804年这位哲学家逝世并长眠于此。作为首府的历史赋予哥尼斯堡一些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徜徉在这些建筑之间不免让人浮想联翩,追忆那些辉煌的岁月。然而康德在世时哥尼斯堡已经沦落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曾经的浮华与眼前的寥落形成了极强的对比。面对此情此景,熟悉历史的康德很可能会产生世界如梦、历史变幻的想法,这是否是他把“物自体”与“现象”对立起来的原因呢?据说康德除了曾到几十英里外的但泽旅游过外,几乎没有走出哥尼斯堡一步,真正做到了“不出户、知天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虽然说地理意义的旅游很重要,但是伟大思想的升华却是孤独思索的结晶。康德习惯了哥尼斯堡,当然也习惯了这个城市的建筑,也许康德只有在这样的建筑场里才能做出令后世叹为观止的思考和写作。苏联学者古留加曾写过:“按照惯例,我们叙述康德的一生要从叙述他生活的那个城市开始,哲学家的那些严密学说仿佛是用这个城市的花岗岩石砌筑而成的”[3]。很可能,康德的思想不仅受惠于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家,更受惠于城市的花岗岩和城市的历史。
3.2崇高感是康德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
事实上,康德的哲学体系本身就宛如由花岗石砌筑而成的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给读者以崇高的美感。在哥尼斯堡及其周边的地区并没有高山峻岭,就外部环境而言,教堂建筑和星空是康德有关崇高概
念的两个刺激源。同时还有抽象意义上的崇高――数学和力学上的崇高。如果把康德哲学体系比做哥特式大教堂,那么其尖顶便如他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头顶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罗伯尼切教堂是康德住宅对面的标志性建筑,偏爱眺望的康德,同罗伯尼切教堂默默对话,随后堕入沉思默想,悲壮沉郁。
3.3道德星空思考是康德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
哥尼斯堡的建筑场净化、营养和拔高了康德,助他登高临远,洞察一切。星空之所以被注意到,与哥尼斯堡挺拔的教堂建筑的指引是分不开。建筑引发人的思考,也激起康德对道德星空的探索,使其越来越体会到人性之伟大、人性之美,引发“人是什么”的思考。康德的星空与古希腊的宇宙(cosmos)概念一脉相承,在康德的宇宙中一切都井然有序,并充满着人的意志自由。或许正是这种以教堂为背景的星空,成就了康德“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考[4]。
3.4城市建筑与“为自然立法”思想
康德习惯于每天出去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他会想起哥尼斯堡这个名字还与一个数学难题联系在一起。在哥尼斯堡的莱茵河上有七座桥,将河中的两个小岛和河岸连接。生于斯、长于斯的哥尼斯堡人产生了一个疑问:能否寻找一条路线,经过每一座桥只一次而能回到出发点。整个城市没有人能解答,欧洲的著名数学家也一筹莫展。后来数学家欧拉于1736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为拓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初等的例子。如果哥尼斯堡人没有提出问题,哥尼斯堡七桥问题也不会成为数学上的著名问题。这说明哥尼斯堡人非常喜欢理性的思辨。康德应该经常在七座桥梁上漫步,桥梁以及七桥问题对他那善于思考的气质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加上他的前提是“物自体”与“现象”的二分,所以他认为自然本身并无规律,所谓自然的规律只能是人先天能力赋予的。这就是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后来被视为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分水岭。对于专业哲学家来说,哥尼斯堡七桥与康德哲学是个“弱”相关关系,但又有谁能否认它们之间微妙的联系呢?
4 结语
在阅读康德的哲学著作和浏览哥尼斯堡城的建筑时,我们深深感动于康德哲学思想的深邃及与其哲学思想共生的建筑场的壮丽。建筑场可以使人产生崇敬感、敬畏感、使人兴奋、激昂、深沉、伤感、惆怅……建筑场可以容纳人类所有的情感中。建筑场可以影响人们的深层意识,对人们在形成科学、人文、历史、物质、生命、环境、技术等观念的形成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在建筑场理论分析基础上可以融合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设计等方面,使设计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最佳答案。建筑场与意识共生发展,它不仅是对和谐发展观的补充,也将进一步推进建筑设计思想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2]孙鸣春.生态环境设计中的诸多因素[J].环境设计,No.01,2002:21-24.
[3]贾泽林译.康德传.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
[4]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古代天文学简史范文4
人类的一切抽象思想或许都要起源于神话意识,而从古希腊神话分离出哲学而使其具有它自身的内容和方法,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先哲所开创的学术研究,。亚理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它把主要依赖比喻、经验推理的辩论的哲学思维推进为可以用概念和命题表达的逻辑方法,亚理士多德的学术研究方法明显地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的古希腊哲学家的地方,首先表现在他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到对名词、概念与事物属性、本质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而不是仅仅依靠辩论和比喻的方法直接对事物、属性、本质等进行研究,就是说他意识到了用概念、命题进行表达和思维,而不是主要地依靠形象来表达,用比喻、经验来推理,苏格拉底的辩论和柏拉的对话都是对话人之间的直接解释和辩驳,基本上是对事物的直接思维方式,而基于空间意义的形式正是柏拉图的理念的立足点。亚理士多德把基于事物的思想形象的表达为概念关系,把对事物的原因研究推进到逻辑关系的表达,把主要依靠经验比喻的推理方法推进为逻辑推理,把辩论转变为完全理论性的学术方法,简言之,把广泛的思维变成了精确的思想,这种进步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对于哲学领域的,而是整个文化意义的。
亚理士多德所建立的三段论的思维形式是迄今为止我们仍学习和训练思维的基础方法,我们或许不应当把人类智力进步台阶上的这一大步归功于某一个人,但亚理士多德对此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无疑代表了这一伟大的进步。
亚理士多德在哲学和自然哲学上所做的重要贡献就是他的形而上学,如果说柏拉图代表的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那么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代表的就是自然哲学的雄伟建筑和近、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即基于客观性的科学本质,尽管它看起来存在着内部的混杂不清甚至是错误,人们可以夸张而不失其真实性地说,它托起了整个西方知识型文化的摩天大厦,即是后人对它的反对,也是站在它所提供的基石上,比如伽利略用落石试验证明了亚理士的一个错误论点而成为了近代科学的一个象征,但上人们不能忘了伽利略的比萨之塔是屹立在亚理士多德所提供基础上。如果我们可以说,对儒家学说的领悟感受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那么也可以说对亚理士多德的理解就是对整个西方知识型文化的鸟瞰能力的把握。
一、形而上学
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实体,形而上学主要地就是以实体概念研究事物的终极原因、所以形而上学讨论的重心不在事物的属性和它们的关系的而是实体概念和事物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区分上,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是的纯粹哲学思辩,而是真正的自然哲学,这正是他的“形而上学”一词的真正意义所在,或许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将它看作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哲学的在起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 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已为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证实。在他的建筑物之上,科学已远是今非昔比,而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却仍然坚固、旧貌斑驳,但却更加分离孤独,史蒂芬霍金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的末尾对现代哲学与科学的分离现象评论说:“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理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他的批评或许一方深刻地反映了潜藏在现代科学家意识中的亚理士多德的哲学传统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表明了哲学、科学、科学哲学之间二千多年来复杂的互生消长关系在今天所见的一个更加变易从面难以把握的剧烈现实。
亚理士多德广泛地考察各种哲学和自然哲学,他把所有当时流行的学说总述为追求事物的终极原因,他看出了事物的终极原因即不能把所有的事物归结为某一个事物,比如泰勒斯主张“水”为万物之因,也不能归结于事物之外的超验存在,如柏拉图的理念,而是在于事物的自身原因,事物的自身原因存在于事物的自身但又不等于事物自身,因此事物的自身原因即不是别人又不是自己,这种困惑几乎成了所有的哲学家无法逾越的障碍,亚理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本因 (原因)、物因 (物质)、动因 (动力)、极因 (目的),以实钵概念和实体与事物的逻辑关系表达了这个困难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了它,关于事物自身的学术研究是物理学和数学,而关于事物自身原因与事物的属性的关系的学说就他所说的形而上学。当然他的形而上学仍在一般哲学意义的框架内,因此更精确的说法应当是亚理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自然哲学精神并以逻辑方式表达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和的统一,亚理士多德的形同上学自身正是哲学与科学之间即mate-physics意义的实体。因经这就是亚理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本义上对智慧的追求。
二、实体
亚理士多德的实体不是实际事物本身而是事物自身的原因,也不是某种超验的存在,亚理士多德认为不存在一般意义的实际事物,这正是他与柏拉图的分歧,因此亚理士多德的实体即不等同于科学活动中的具体对象。又不相同于柏拉图的超验的理念,实体取决于质料和形式,但又不是这二者,而是这两者之间的潜在关系,亚理士多德就是努力地去说明这种多重层次的关系,但是亚理士多德并没有给予我们一个一致性的实体概念,实际上他只是通过对实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量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他的实体概念的思想过程,但正是在这些精微的方向区分上,他把对知识的追求导向了作为思想对象的客观性。
首先亚理士多德的论述的实体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 因此实体的意义与质料紧密系在一起,而且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质料”在很多情况下是指物理性质上的“原料” (material), 而不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物质” (matter), 因此虽然他说:原料被制成物品后, “质料”仍保留着, (形而上学5) 但在这里, "质料"等同于物品的本质即“原料”,而不是指更进一层的原料的本质, 即没有把质料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物质概念来使用。因此他虽然区分了两种“原始物质”的含义,即构成具体事物的原始物质,和一般意义的原始物质,如青铜是青铜器的原始物质即原料,但水是青铜的原始物质,后者才是早期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物质概念之一:凡是可熔性物质〈包括青铜〉都是水。恰恰在于亚理士多德不是在这种纯粹的哲学观念上坚持他的实体演说,避免了柏拉图的超验,但另一方面,实体与质料又不是象实际事物一样具有与原料直接的构成关系,质料依靠潜在的形式以目的性的变化过程而成为具体的事物,这样形式又不是物理意义的形状而是对它的抽象,这才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事物自身的原因,正是在这样一种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意义上,它成为亚理士多德的实体和形式的关系,所以亚理士多德的实体正是自然哲学与纯粹哲学观念之间的桥梁,这与人们所熟悉的关于事物与属性的关系都不相同,从而使许多人都很难跟随亚理士多德的思想。
实体实际上是亚理士多德提出的事物的终级原因的四因说与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统一的概念方法,四因一方面可以融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可以归属于哲学领域的因果理论,因此从四因说出发而完成实体概念是亚理士多德建筑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整套结构蓝图,他在哲学、自然哲学,和科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过渡性的统一,虽然存在混乱和错误,但绝不是拼凑,他的“实体”正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形而上学实体。
为了了建立实体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的一致,他提出了潜在或潜能的概念 ,潜能一方面可以解释实际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动力,即科学意义上物因和动因之间的关系,这很自然;另一方面潜能使质料走向事物自身的目的形式,这是物理学意义的物因和哲学意义的极因之间的一种超越关系,同样在哲学意义的本因与物理学意义的动因之间也有这种超越关系,他使用了另一个一个概念实现,潜能使质料走向事物自身的纯粹目的超越关系被等同为事物的概念在实际事物中的实现这样一种间接的说明,这是一种莫比乌斯-克莱因式的转换,而且亚理士多德也不是在他的所有论述中始终一致地使用这些概念,但在一种可以理解的意义上它们是一致的。这样他也就在具有哲学意义的极因和本因与科学意义的物因和动因之间建立了转换性过渡,在实体的哲学意义和物理学的客观对象之间建立起了通道。
另一方面,亚理士多德从几乎是不可质疑的数理观念“一”的基点出发,用潜能解释潜在的形式,一是一切事物的自性而非属性,这是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古老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作为具体的计数意义的数字,亚理士多德总结它的意义有四个方面:延续性(时间)、整体、个别和普遍性,亚理士多德认为人们通常所讨论的事物的统一性往往都是这四义中的一方面,比如柏拉图的形式就是普遍性的共相,而亚理士多德的形式却是“这一个”的一,即整体与个体对立与分别在科学计量意义上的对象,他是这样说的:
自然哲学家于运动亦以简单而短促的移转为运动之计量;这些运动单位就是占时间最短的运动。在天文学上这样的“一”也是研究与计量之起点,在音乐上则以四分之一音程为单位,在言语上则为字母。所有这些计量单位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一。
这才是亚理士多德心目中作为事物的统一性形式的真正能够与柏拉图的形式理念相抗衡的意义,它既不同于具体计数的数字,也不同于柏拉图想得到而未得到的象数,它是实体在数理意义上的意义而又可以归属于哲学观念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二千多年后才充分展开的数理逻辑原理的一个哲学基础。这样亚理士多德的实体与实体的形式就存在一种基于客观性的真实联系,实体就在事物的自身原因与事物的属性之间建立了形而上学的过渡。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亚理士多德的形式不仅是他实体理论的一大支柱,它还是一般事物的概念与事物及事物和事物属性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它就是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实体学说整个论述中的的灵魂逻辑学意义上的形式,在这个最重要的轴心上,逻辑学实现了自己。
三、逻辑学
亚理士多德对形式的论述与柏拉图的理念形式不同不仅仅是哲学和自然哲学意义上的,亚理士多德对此已进行了许多分析和比较,但是这些细致的论述混杂而层次不清,原因在于,柏拉图的理念抽象而简洁,层次分明,而亚理士多德的实体概念虽具体但意义纠缠,层次超越,实体的概念在本质、物质或物料、形式这些诸概念之间缠绕,游移难决,亚理士多德自己所提倡的用种差作定义方法在这里根本用不上,这些概念之间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因果关联,它们似乎不取决于这些概念自身而取决于对它们的定义途径,把实体解释为质料与形式或它们的关系对他并不困难,他的论述的所有困难并不在于如何用质料或形式去解释实体,他已经从多方面已作过多种说明,他的困难在于去表达和说明这种复杂而纠缠的关系的方法自身,他的所有论述与他的前人不同之处正在于他不是用事物的属性和属性之间的关系去论证,而是企图依靠概念和事物、属性、本质,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去进行论证,他把对物理学、数学、自然哲学的经验性讨论提升为可以用纯粹学术方法表达和论证的学问,他的伟大事业正是表现在这种独创上亚理士多德把抽象的思想过程表达为专门的学问逻辑学, 略摘其言如下:
因为专研实是之为实是的学术是能够独立的一门学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门学术与物理学相同抑相异。物学所讨论的是自身具有动变原理的事物;数学是理论学术,讨论静止事物,但数学对象不能离事物而独立存在。那么异乎这两门学术,必是专研那些独立存在而不动变事物的学术,这样性质的一类本体,我们以后将试为证明其实存于世间。世上若真有这样一类的实是,这里就该是神之所在而成为第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于是显然,理论学术有三物学,数学,神学(哲学)。
于是明显地,这一门学术的任务是在考察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和作为实是所应有的诸质性,而这同一门学术除了应考察本体与其属性外,也将所察上列各项以及下述诸观念,如“先于”,“后于”,“科属”,“品种”,“全体部分”以及其它类此各项。
我们必须提出这一问题,研究本体和研究数学中所称公理〈通则〉是否属于一门学术。因此,明显地,研究一切本体的哲学家也得研究综合论法〈三段论法〉。
现在,让我们进而说明什么是这样一个最确实原理。这原理是:“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 (同一律) 。可是关于这个论点〈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为是亦可以为非是”,〉只要对方提出一些条理,我们当用反证法来为之说明这不可能成立。(矛盾律) 同一事物既是而又不是,除了同义异词而外,必不可能。
逻辑学就是这样逐步地在他的表述中艰难地实现的,三段论是思维的基本逻辑形式,逻辑三律是形式逻辑的公理,当然亚理士多德并不是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逻辑学,他主要地只是在各方面用逻辑方法论述了他的学说时表现了形式逻辑方法,提出了最基本的观点,而且这也并不是始终一致和清晰的,其中也避免不了混乱和错误,但他的逻辑学方法是坚实的,虽然亚理士多德并没有把它表达为逻辑系统,但他已撑握和运用了它,而且亚理士多德仍用使潜能解释他的哲学意义的形式,但这已经是在逻辑学意义上解释形式,潜能不过是他对逻辑的运用的解释的替代物,因此与用潜能解释质料的潜能在形式不同,它不是指实体作为质料内在的变因,而是指实体作为概念的逻辑意义的变因,它是通过实体对自身的逻辑否定而实现的,他勉强称之为“潜在的事物”。有别于实体的潜能通过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而实现目的,潜在的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不是”(即逻辑否定)所有论述过的运动和变化这是一级难于察见而可以实现的逻辑过程。他论述这个思想过程是艰难的,我们甚至无法从始终如一地追随他的思想,他并没有直接指出他思想中的这种意义的形式是什么,他主要地只是以概念与事物的区别和与它们的关系,特别是从概念实现为现实事物的过程间接地表达了他的形式思想,比如他说::
铜,潜在地是一雕像;可是雕像的完全实现并不是“铜‘作为’铜”而进行之动变。因为“铜‘作为’铜”与“作为”某一潜在事物并不相同。
能够导致健康与能够致病不相同倘“能致”为相同,则正是健在与正在病中也将相同,真正相同的只是健康与疾病的底层,那底层或是血液或是体液则确乎为同一的血液或体液。
有如颜色(概念 )与可见物之不同那样,事物与潜在事物并不相同。
例如可建筑物之作为可建筑物者,可能有时实现与有时不实现,可建筑物作为可建筑物而进行实现,则为建筑活动。实现就或是这个建筑工程,或是房屋。然而当房屋存在时,这可建筑物就不再是可建筑物;这恰已成了被建筑物。所以,实现过程必须是建筑活动,这就是一个运动变化。
如果仅仅从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上去读这些文字就几乎令人无法捉摸,这不是对事物或事物属性的抽象,也不是对概念的逻辑关系的整理,而是企图从逻辑思想活动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形式的过程,这种艰难正是人类智力进步的伟大足迹的一点点遗迹,弥足珍贵,所以亚理士多德对他的形式的论述比他的实钵概念更难于被人理解。二千多年后,维特根什坦以更纯粹抽象的方式表现这一过程,比如逻辑哲学论中所说的“型式概念”就正是亚理士多德艰难而未说出来的一种“潜在的事物”。虽然今天逻辑学已进步为能与数理方法结合的产生了强有力的数理逻辑方法,但人们在亚理士多德的最初起点上并没进步多少,他所未解决或他已接触而未意识到的问题比如有关逻辑的形成和逻辑的本质问题,逻辑公理的意义如排中律的适用性问题等等,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远非完全解决了的课题,甚至纯粹的形式系统自身也因哥德尔定律的出现而面临难以自保的最深刻的危机。
四、形式、范畴与现实的思想
逻辑学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这完全反映在亚理士多德的学说中形式这一概念即是他的实体理论的构成部份,又是其论证的逻辑工具方法上,这正与亚理士多德的实体概念处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地位相类似,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学一方面是他的实体学说的论证工具方法,它的自身又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方式和过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成为认识论即纯粹的哲学。所以亚理士多德的形式也在两个方面与柏拉图的形式理念的不同。作为实体的形式,亚刊士多德充分论述了他的形式不同于柏拉图的形式的区别,这主要在于他的形式主要地是基于数理的和逻辑的意义上的,因此不同于柏拉图的几何意义上的绝对抽象的空间形式。他从多方面论述了柏拉图的理念形式不可能成为事物的原因,柏拉图的理念的超验性与数字(即今天所说的算法意义)所包具有客观性格格不入,因此柏拉图企图将数字纳入到理念的框架内就没有成功。另一方面,亚理士多德从逻辑方向出发,把他的形式从他的实体理论中导向了逻辑意义的范畴系统,成为了他的形而上学的一个支柱,并给后世哲学研究带来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