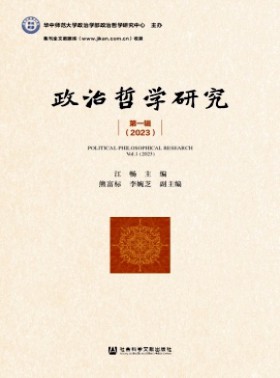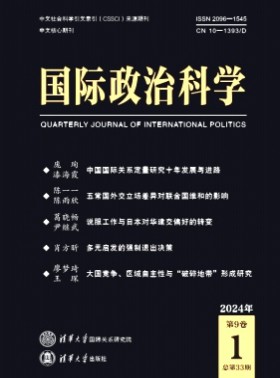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政治学习意义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政治学习意义范文1
政治知识是以课本知识为基础的,所有事例的分析都是依据课本来的,而且高中政治与初中政治不同,高中政治的知识点都是灵活的,而且分析的事例都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更新不断变化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注重基础的把握,最好是对必修课本的基础知识都能做到倒背如流,而且能够列举出知识体系。这样的能力才可能在做新的案例分析时尽可能多的得分,更透彻的分析问题。
1.每个模块的知识都要进行整合归纳
高中政治要求学生必修的有四个模块,经济、政治、文化与哲学,这四个模块是高中三年学生需要透彻掌握的知识,而且每一个模块,尤其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模块,都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考查的。高考之前,教师都会根据往年的高考内容,对试题内容进行预估,但是,这三个模块能够预估到的概率特别小,因为,这三个模块都是根据材料进行分析的,而材料大都是社会热点或者是社会时事,每一年的高考出的题目都不一定是哪一年的材料。所以,教师无法精准的为学生预估高考题目。
另外,高考中政治是和历史、地理综合在一份卷子上,时间是两个半小时,这相对于以前的政治学科单独考试,时间缩减了很多,学生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做政治题目。所以,在考试过程中,如果学生对课本的基础知识没有全面的掌握,不能熟练应用基础知识,那文综考试就会更加棘手。
由此,我认为,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要注意基础知识的整合,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去整理,高考考查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各个模块都是分开的,但是,材料呈现的不一定是限制于一个单元,有可能是运用整本书里的重点知识。拿文化模块来讲,每一单元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材料可以用任何一个单元的符合题目要求的理论去解释,文化模块第一单元讲的是文化的传播,之后根据这一基础,有引进西方文化的意义途径,文化创新、文化交流、中华文化、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有很多都是相似的,如果学生不能够理清每一单元对应的知识,在给出材料让学生分析的时候,就很难答到点上。为提高政治解题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最多的分数,学生在学习完所有的基础知识后,就要开始整合作业,不能放松。整合工作的进行可以在课间、课堂或者是周末自习,这些工作学生可根据时间的长短去进行。
比如,课间休息时间比较短,学生可以拿出五分钟时间进行一课内容的整理,或者是列举一个单元的知识大纲。说起知识大纲,有些学生不明白该如何有效的去整理,这里我想说的是,政治课本每一单元每一课都是非常有逻辑性的,每一单元的大标题,每一课的小标题,这些标题学生可能都忽略了,但在考试中,这些简练的标题内容都有可能是一个得分点。有些学生只要答出标题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得分点,而有的学生写了一堆,却没有得分点。所以,利用课间休息时间,按照课本给出的顺序,进行整理,有了主干,再进行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记忆,而且在考试时可以帮助自己不重复的去考虑知识点,可以节约考试时间。
2.哲学模块初学阶段与复习阶段应有的不同
哲学是高中政治学习的最后一个模块,在新授课阶段,哲学应该是学生公认的最难的一个模块,但是在学完之后,进入复习阶段,学生慢慢了解了哲学的理论,就会知道哲学是最容易得分的。在初学阶段,很多学生会搞混知识的分类,整体来讲,新授课阶段,大部分学生以一种迷茫的态度去学习,哲学的单元顺序是唯物论、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顺序。尤其是学完唯物辩证法后,很多学生混淆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因为哲学题目考查都会明确要求运用唯物论还是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所以总体学完之后学生很容易得分。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初学阶段,学生不懂唯物论、违心论,形而上学法这些概念,这时候,学生只要根据教师的节奏,听从教师的安排,把基础知识背熟练。我认为政治的学习讲究的是"死去活来",只有先把知识背死才能灵活运用,这并不是说每个阶段都这是这种方法,只是尤其在哲学模块的学习上,一定要先把知识记牢。在学完全部基础知识之后,学生的哲学能力相对于初始阶段会有很大的提高,因为在这一积累过程中,学生会接触很多生活现象,慢慢理解现象之后的本质。而且学完全部之后,学生的学习方法就要发生改变,这时候学生的主要方向是跟随老师的节奏,但是细节内容要自己进行安排,唯一不能出错的就是不能把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搞混,这是基本的哲学素养。
3.政治知识要与社会相联系
教育对于政治学习的意义就在于,教育能够通过传播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促进政治社会化,高中阶段的学生大都具备一定的学习判断性,抛开政治是一门学科,学生还需要了解很多政治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学习政治时,学生要改变自己的意识,不能把政治学科纯粹的当作是高考内容,它更是学生了解国家以及社会形态的一本参考书。
大部分的高中学校都是一个封闭化管理的教育场所,由于高考压力,学生不能随意带电子产品到学校,尤其是手机,所以很多学生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可能对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动态不了解。针对这种情况,政治教师就要时常的向学生传达政治要闻,或者可以根据课本知识,筛选社会热点,将素材拿到课堂,让学生运用所学进行分析。
政治学科所学的知识在应用时是需要灵活转换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事关国家的,还是文化的,只要能够与政治学科所学的知识联系上,都有可能成为考查的范围。所以,在日常学习中,对课本中给出的事例要认真对待,比如反腐问题、文化交流问题,有可能描述起来不一样,但是学生要将课本中给出的事例,对应的理论位置,都要搞清楚,在哪一知识点后出现的,因为这些大致相同的事例在考试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只要熟悉在课本中的知识方向,考试时就可以迅速的联想到对应的知识。
总而言之,在高中的日常学习中就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科的社会性意识,同时每一模块的学习都要注意整合归纳。
政治学习意义范文2
关键词:学习兴趣;投其所好;故事;照片;亲身经历;歌曲
中图分类号:G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085-02
在传统的政治课堂教学中,课堂教学模式十分陈旧,“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课堂缺乏学生的声音和活动,更谈不上学生的参与和主动性学习。这种单调、枯燥的政治课堂学习模式,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习效率低下。要提高学习效率,必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抓住学生的心理“投其所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道出了兴趣对于工作学习的重要性。初中学生尤其是初一学生年龄小,喜动不喜静,喜欢争辩,不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安心思考。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个特点来安排课堂学习。在学习《性格的培养与塑造》时,笔者引导学生就俗语“江上易改,本性难移”开展辩论赛,将班级分为正反两方,各自围绕自己的观点搜集材料。然后,各派出两个学生做代表进行辩论,当派出的辩手有困难时,其他学生可以随时提供帮助。这样,既使课堂充满趣味,也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中去,极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通过故事的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故事的趣味性既可以吸引学生积极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来,又可以让抽象的道理浅显易懂。教师要善于融道理于故事之中,让学生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受到教育。在学习《陶冶高雅生活情趣的意义》时,发动学生讲自己的见闻或读到的故事,来阐述高雅生活情趣对人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学生讲了自己读到的一个故事:一群中国的游客到欧洲旅游观光,到一家饭店用餐。欧洲的饭店都是大厅形式的。饭前,几个中国人开始一边拍手一边唱歌,外国人投来异样的目光,觉得在餐厅大声唱歌不可思议,但还是没表示什么。开始用餐了,几个中国人开始猜拳喝酒。一边大呼小叫一边伸缩拳头。跑堂的以为是要打架,想上来劝解,可是又觉得不像发生争执,站在一旁好一会儿,才知道是一种娱乐,很厌恶地摇着头走了。周围其他用餐的人也不满地起身离开。在中国人看来,在餐馆喝酒猜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外国人看来就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因为他妨碍了别人的用餐环境。另一个学生讲了一个中国人到了加拿大,坐在汽车里吃香蕉,吃完后随手将香蕉皮扔到车窗外。随行的加拿大人赶忙停车,跑回去将香蕉皮捡回来,放进车里准备的塑料袋中。一扔一捡却表现了高雅情操和生活情趣的重要性。故事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使得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三、利用竞赛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竞赛的竞技性和激烈性更能激发学生的快速思维和积极投入。在学习一些描述性知识时,因为这些知识的不可生成性,比如,名誉权、肖像权、基本路线、基本国情、发展战略等概念,学生的思维能力在这里得到限制。为快速掌握这些识记性质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竞赛的形式,让学生分组竞赛。学生既是参与者也是评价者,既当选手,又有机会担任评委,可以极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四、运用图画、照片等直观教具,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画、照片因其具有直观性和形象的特点,备受学生喜爱。教师可以选取和学习内容有关的图画或照片,来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关爱他人的生命健康》时,教师可以从网络上下载宝马司机打死奔驰司机的照片,通过图片所表现的内容对学生产生一种震撼的效果,让学生懂得生命的脆弱和珍贵,从而唤起学生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爱。还可以给学生展示药家鑫受审时的照片,从其悔恨的表情以及他的法庭陈述,来理解伤害他人也是对自己的伤害的道理。通过照片和生动的事例来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五、以学生的亲身经历为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政治学习内容和学生生活紧密相连,很多学生都遇到过课本中提到过的情形,有着切身的感受。这种经验比任何名人故事更有说服力。教师要善于善于挖掘这种宝贵的课程资源,让学生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来感染其它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做情绪的主人》时,让一个爱冲动的学生讲他和同学因为口角引发争执,他端起一杯开水泼在同学的背上,同学被烫伤,他受到老师的批评,家长因在医院护理同学而耽误了工作,受到单位的处分,而且他们家支付了同学的医药费三千多元。通过这件事,他明白了:冲动是魔鬼,要善于控制情绪,做情绪的主人。学生也从中受到教育,更加认识到学会控制情绪的重要性。自觉去探讨控制情绪的方法,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六、以歌曲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政治学习意义范文3
一、“空白”的意义
(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空白”艺术的主旨在于留给学生相当的时间,由学生自己对学习内容进行解析、消化,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这将激发每个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热情,使之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二)逐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素质
“空白”艺术要求教师放弃“满堂灌”“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方法,彻底克服教者“包办代替”、学者“生吞活剥”的现象。教师将由演员变成导演,学生则由台下的观众变成领衔主演。在“空白”中,学生在教师的指点下,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解析概念、归纳原理,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确定掌握内容的具体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应用能力和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三)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空白”艺术的特点是:教师指导,学生操作。在“空白”中,学生既要动脑又要动手,或“悟”,或“做”,或“记”,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必将诱发学生的学习灵感,不同思维特点的学生皆可找到用武之处,从而增强教学过程的趣味和学生学习的信心。
(四)大幅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运用“空白”艺术,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一方面,教师必须于课前对课堂教学作精心的研究和策划,科学地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每道题、每句话都应充分准备。另一方面,学生必须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空白”中,教与学得到有机统一,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认知和掌握程度必然会有较大的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空白”的操作
(一)在“空白”中“悟”
“悟”是领会,是理解,是温故知新,是由感知到思辨的升华。思想政治课的内容理论性强,一些概念、原理十分抽象,单凭教师分析讲解显然不够,至于希望通过“讲得多、讲得细、讲得深”达到学生的透彻把握更是缘木求鱼。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这个“思”,就是“悟”。
在新授概念时,教师应在点化之后让学生自己去“悟”。譬如物质概念中的“客观实在”,教师应该告诉学生,所谓“客观实在”,就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所谓“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就是“无论你看得见看不见,摸得着摸不着,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然后就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
(二)在“空白”中“做”
“悟”的结果是懂,但懂的仅仅是理论。理论还要与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学生去实践,去“做”。
讲授新知识前,教师应该指导学生预习,让学生初步了解新内容,特别是要让学生发现自己理解的“难点”。这样,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有备而来,目的和重点自然明确。
课堂内容的总结和原理的归纳,也应让学生自己进行。教师的责任只在引导学生得出全面而准确的结论,不应把现成的结论强加给学生让他去死记硬背。
练习是检查理解广度和深度的工具,是比较重要的“做”。只“悟”不“练”,对知识的掌握难以全面、深化和巩固。教师应该精心设计一定量的选择题、思考题,让学生于练习中发现知识点的误区,通过比较、辨别,加深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
有时还需要把课堂上的“空白”延伸到课后,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到农村、到工厂去调查研究,把理论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做”是学习的根本,是学习的捷径,只有“做”得出色才算是真正领会,才能把书本内容变为自己的知识。
(三)在“空白”中“记”
“悟”了、“做”了好“记”,“记”了更好“悟”,也更好“做”。“记”是对旧知的回忆和对新知的记忆,既是巩固又是提高。理解了并不一定能够记住,记住了才能进一步加深理解。与学生交谈常常会有这样的对话:这个原理你懂了吗?懂了。这个原理的内容是什么?记不得了。诚然,死记硬背是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大忌,但切不可因噎废食。
重复是记忆的重要形式,然而教师的重复绝对不是学生的记忆。每新授完一个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应要求学生即时强化记忆。给定较短的时间,明确具体的内容,当场抽查。有理解作基础,加上时间的限制、气氛的压力,往往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其记忆能力。
复习旧课时,教师更应坚持“提问――记忆――回答”的原则,或回忆概念,或归纳原理,或比较关系,都要让学生先作准备、先“记”。在这个过程中,“记”是目的,其他是手段。
课堂教学要尽可能地利用“空白”让学生记忆那些该记的内容,不要把“记”留到课后,这不仅仅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更重要的是遵循教学规律,趁热打铁。
三、“空白”的原则
(一)求实原则
具体概念或具体原理的新授与复习,留不留“空白”,留下的“空白”是“悟”,是“做”,还是“记”,没有固定的模式,应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生搬硬套的形式主义。譬如,哲学要多“悟”,政治学要多“记”,而这两门课都要多“做”。
(二)适度原则
提倡“空白”,讲究“空白”艺术,“空白”艺术依赖于教师的指导,没有导演的高屋建瓴,就不可能有演员的精彩表演。如果一味“空白”,面对新知旧知,教师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说,甚至将整节课都交给学生“自由”支配,则是放任自流,违背教与学的基本规律。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白”,更谈不上什么“空白艺术”。
(三)科学性原则
政治学习意义范文4
关键词:高中政治 课程教学 问题意识
由于高中阶段的学生还未接触社会,其政治视野狭窄,不敢大胆表达。而政治作为高中教学科目中的副科,又不能占用学生太多时间,加上政治知识较枯燥乏味,学生往往失去对政治学习的兴趣。长此以往,学生政治学习效率较低。因此,创新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问题意识,使学生带着富有趣味的问题去学习,这样不仅提高了课堂效率,调动他们的思维积极性,还能帮助学生从原先枯燥无味学习中演化为学习动机和热情。学生问题意识的激发是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断进行革新的产物,是从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学模式,同时也是有效、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对高中政治教学质量的有效提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着重从创设问题情境、合理提出问题、解决生活问题几方面分析了学生问题意识的激发方法,旨在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使原本枯燥乏味的课堂变得生机勃勃。
一、创设问题情境
质疑源于问题,问题源于情境,情境就是实际的课堂教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老师的启发、引导作用很重要。要想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能够积极主动地质疑、提问题,老师就应该根据政治课程的特征,恰当的设计情境,适当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问题。教师在教学实践的活动中问题的最初设计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在参考本节所讲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生活的实际情况设计和提出相关的问题。这样做实际上是在为同学创造一个问题讨论的情景,通过这一情景的设置,从而将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提出的问题上来,从而在激起学生对于问题的兴趣,为后学的深入探究做好准备。如:学习“价值决定价格”这一课时,在讲到“货币”这一内容时,将是可以钱作为引子,通过在课堂上展示不同面值的货币吸引学生的注意,然后通过设置问题:钱是一个好东西,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大家都离不开钱,而且都爱钱,那么请同学们想一想,钱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了钱,那么买东西又要通过什么?这样通过一个关于钱的通论就可把学生的思路引导入货币的起源问题上,然后再从货币还没有产生的时代说起,一步步引导学生理解货币的产生,最后又回归到货币的作用上面。
二、合理提出问题
提高高中政治教学有效性,当教师提出问题之后,为了顺利的实现学生的学习目标和教师的教学任务,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讨论探究,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学生个人探究和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在这个小组谈论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小组讨论的观察和指导,以保证探究方向的正确性,并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不同同学出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指点,而且还要避免出现一人独大现象的出现,让每个人都主动地参与讨论。如学习“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内容时,教师选择展示一些比较详细的自学笔记,通过大家的分析和讨论,让学生掌握了社会保障制度含义。而且通过优秀的自学笔记还可以帮助拓宽其他学生的学习思路,明确教学重点。进而,向学生介绍的美国的外交政策,让学生展开讨论,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的对比来例假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因及带来的效益。又如,政府职能管理和服务章节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针对政府是管理角色还是服务角色的问题展开讨论式的合作学习。在进行讨论式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根据结合要进行讨论的观点和内容进行小组分工,然后进行资料收集、问题分析,一直到最终解决问题的环节。学生在问题解决后还要对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探索和总结,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问题分析和归纳总结能力。
三、解决生活问题
在高中政治课堂应用探究式提问教学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对于材料和问题的设置要主要和学生的现实生活经验向贴近,这也是新课标对于各学科对于提高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设置情景,给出材料进行提问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和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一则这样会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师提出的问题和材料,从而结合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二则学生往往会对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事物感兴趣,这样教学方法的应用和设置也能够提高学生政治课堂学习的兴趣,从而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在这种与实际问题的结合过程中也培养和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能使他们将自己在政治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接受检验,符合了新课标中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要求。如学习环境问题时,如果仅仅靠教师的讲解和课本知识的读背,学生很难感同身受,学习兴趣不高,自然不会有思考探究,提出问题的欲望。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可利用多媒体课件,结合“雾霾”现状及其热点问题展开教学,先播放视频、图片、新闻等,为学生展示我国存在的严重的雾霾问题,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感受,说一说当前环境中雾霾产生的原因,使学生认识到雾霾的危害,进而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如何防治雾霾。在自主思考并探讨生活问题的同时也能促使学生在反思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感悟,达到思想品德课程的教育目的。
四、结束语
随着新课改理念的不断深入,对高中政治教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高中政治教学中,不仅教会学生文化知识,而且还应培养学生各项能力,而问题意识则是各项能力的前提条件,相比以往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模式,激发学生问题意识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创新能力。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激发学生问题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政治学习意义范文5
一、新课程高三政治复习课问题出在哪里
1.对新课程复习课的特点认识不足
新课改后政治课除了四个必修模块,还有相应的选修课,面广量大,知识点多。新的《 课程标准 》对思想政治课是怎样定位的?什么是思想政治学科能力?针对不同能力层级我们有什么有效的具体训练方法?《 考试说明 》中的“考核目标与要求”如何有效落实?近年来新课程背景下高考走向发生了什么明显变化?如何指导学生在新课程淡化学科体系背景下建构知识体系?如何整合模块之间的相关内容?如果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的复习课就处于一个盲从状态。同时,复习课不同于新授课,其主要任务是:对学生已学的知识进行巩固、加深、拓宽、查漏补缺,使学生更加系统地掌握知识,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由于有的教师对此认识不足,缺少有针对性的规划,什么已经解决好,什么还没解决好,什么要重点解决,心中缺少一本“账”,以致存在着盲目性教学行为。
2.对新课程的高考方向把握不准
新课程下的高考指导思想是“总体保持稳定,深化能力立意,积极改革创新”。从近几年的新课改省份的政治试题可以看出,高考评价要求和评价方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明显以新课程改革理念为导向,有的教师研究《 考试说明 》、研究教材、研究高考试题不够深入、细致,高考的方向把握不准,走一步看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随意性教学行为。
3.对学生现有学习情况缺少调查
复习课只有在切实了解学生实际掌握知识程度的基础上,才能对症下药,明确复习教学目标。有的教师仅凭以往的经验判断,讲解过度,指导过度,包办代替,课堂交往和有效互动建立不起来;有的教师认为复习就是“教教材”,过分强调“以本为本”,教师、教材依然处于中心位置。
4.思想政治课复习缺少科学模式
有的教师复习课与新授课变化不大,简单重复,毫无新意,基本不适应新课程下高考的需要,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教学行为。
5.基础知识的巩固并不令人放心
有的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理解不准确,过分地讲究课堂形式;有的教师也懂得构建知识体系,但体系的构建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反而使学生如坠云雾之中;有的教师过度依赖多媒体,形式冲淡内容,从而使理论观点阐述不到位,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够牢固,导致学科能力失去有效的支撑。
6.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招数不多
现实教学存在着能力培养和能力训练依然停留在浅层次的现象,实践中缺少具体有效的训练方法。有的教师复习备考依然主要依靠大习题量训练,搞题海战术;有的教师认为“政治课的复习就是背书和做题”,但怎样把书背好、把题做好,教师缺乏切实可行的办法予以指导;有的教师大量搬用现成的市面或网络上的资料,对复习资料不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工作,滥讲、滥做;有的教师缺乏问题意识,不深挖,不探究,缺少敏锐捕捉典型问题的眼睛,以致学生思维贫乏,能力难以提升。
7.与时事政治粘合较差
做好实际联系理论工作,是政治课复习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大特色。有的教师讲时政,没有科学的分析,没有适时适当地与课本链接;有的教师即使注意两者的链接,也仅仅是将书店里买来现成的时政本子照本宣科,缺少自己的思维构建。
8.教师个体思维存在局限性
一般说,一个教师的教学实践很难超越于其教学认识。有的教师认为教书都教老了,应对高考已是轻车熟路,听不进不同意见,也不愿与别人合作,缺少进取心,固步自封;有的年轻教师尽管锐气十足,但邯郸学步,明显经验缺乏。
二、高三政治复习课推行研讨课活动,是克难攻坚的有效方式
开展研讨课活动,我们倡导个体的学习创造,同时发挥名师的示范引路,学科组成员整体联动,相互交流,实现集体合作、诊断,创新新课程高三复习课的新思路新模式。
高三复习研讨课不应有过多的条条框框,既然是研讨课就要鼓励教师个人敢想敢试,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开展高三复习研讨课活动大体上可以遵循这样一个过程:第一步,确定研究目标――这节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二步,定授课人――通常是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课程建设的引路人,研究目标中心执行人;第三步,确立课题,授课人准备初始教案;第四步,集体研讨,先由授课教师简要说课(说这节复习课的总体构想,说教材的处理、教法的选择和学法的指导,说关键性教学细节的设计和生成性教学细节的捕捉及处理,说研究的价值等),然后集体研讨,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形成授课的正式教案;第五步,上研讨课,学科组集体听课;第六步,评课、授课人进一步反思;第七步,修改,完善,推出研讨课成果。从实际情况看,通过这几个环节,一节经过精雕细刻、反复推敲的精品课就被打造出来了。
发挥名师的引领作用是开展研讨活动重要的一环,这一定意义上影响着一个学科乃至一所学校的整体水平。而参与集体备课的成员有学校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领导和政治组的全体教师,可以说是群策群力,因而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科组整体水平。
三、以研讨课探索高三政治复习课的科学模式
建构高三政治复习课的科学模式,有其重要功能,一是预设功能,能为教学实践预先提供一种达成教学目标的程序和活动方式;二是预见功能,能为教学实践预见预期的教学效果,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三是改进功能,在一定模式内来思考各种相关教学因素,利于不断改进,追求最佳效果。
经过研讨,我们认为建构政治复习课科学模式,可采取如下基本步骤:
(1)给学生发放复习课教学案,使复习课有文字材料引路,避免出现上完课学生还是思路不清等问题。
(2)学生根据教学案明示的基于《 课程标准 》与《 考试说明 》的知识要点,回顾课本,精确掌握复习内容,以夯实基础。以教师提问或学生互问互答的方式予以检测和强化,教师适时予以评点,对学生记不清、道不明的知识点予以解释,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3)指导学生将复习内容编成网络式知识系统图表,构建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在肯定学生思维创造的同时,注意把握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
(4)教师讲清易错易混点,凸显复习内容的重点难点,解决学生尚未解决好的问题。
(5)热点举例,将实际和理论相结合,使学生学会用观点统帅材料。教师适时地点拨,提高学生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精选课堂练习,注意选用近几年的高考题,特别是《 考试说明 》上的题型示例,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当堂讲评,实现学生对复习内容的再现和巩固,注意适时培养《 考试说明 》提到的四种能力,找答题特点,找答题规律。
四、以研讨课探索高三政治复习课的着力点
1.基础知识的梳理
基础知识的梳理,要紧扣《 课程标准 》《 考试说明 》和现有教材,找准理论逻辑基点,分清理论层次,把握理论内在联系,突出理论的实质和核心,捋线索,抓结构,抓主干,抓重点,同时也不要忘了抓学生对课本的全面阅读。在各个“理论单元”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有利于帮助学生抓住一个点,提起一条线,抓出一大片,形成“点线面”相融的知识网络。
2.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教学中需要特别注意研究《 课程标准 》提出的各项能力指标,明确“指认事物”“再现现实”“澄清概念”“审视价值”“支持某种论断”“采取某种行动”的深刻涵义,有针对性的训练;同时,高考《 考试说明 》提到答题所需的四种能力,即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论证和探究事物的能力,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部分怎样让学生真正领悟,需要用往年的高考题来示范。
3.重点、难点的定位
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重点、难点?要以《 课程标准 》《 考试说明 》《 教师用书 》为依据,同时注意根据学生知识掌握的现实状况抓易错点、易混点,根据知识在学科理论中的地位抓易考点、考试的高频点,根据当年的时事抓实际与理论的交叉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敏锐地去寻找。
4.思想方法的归纳
(1)内容浓缩法。所谓浓缩,就是使不需要的成分减少,使需要的成分增加。一方面是扩大教学容量,在单位教学时间内,教会学生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缩短教学时间,用一节课的时间完成一节半、两节,甚至更多时间的教学任务。前者重在“浓”,后者重在“缩”。
(2)归类比较法。政治课的许多概念、原理具有众多有机的联系,指导学生对它们按一定的标准划分类别,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迁移能力。
(3)探幽入微法。教材的内容并不等于教学内容,但教学内容的优化又必须以教材为依据,对教材探幽入微,挖掘出教材的教学意义。
(4)发散思维。教学内容的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揭示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发散思维则是其基本途径之一。
(5)综合分析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宏观的视野,对有些问题可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以帮助学生构建立体的知识结构。
5.练习的配备
练习要精挑细选,适当地进行原创或改造。练习题的基本要求是:形式灵活多样,难易度编排合理,取材贴近生活实际,有利于强化思维策略的训练。同时,要注重习题的潜在功能,教师也可以通过改变题目的条件或结论,或改变题目的解法,举一反三,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训练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还要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索,给学生时间和机会讲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想法和思路,哪怕是错误的,也要给予鼓励。
政治学习意义范文6
关键词 组织学习,学习型组织,单环学习,双环学习。
分类号 B849:C93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企业唯一持续的竞争力就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学得更快[1,2]。这是对组织学习能力提出的挑战。要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就要深入研究组织是怎样学习的。
组织学习的概念首先由March和Simon于1958年提出[3]。有关组织学习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增长。但我国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尚处于刚刚开始阶段,仅有少量的初步研究[4~9]。
目前,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存在着许多争论。下面就5个主要方面对组织学习研究的进展与争议加以概述。
1 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区别×
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和繁荣必须有其必要性。在对组织学习研究的必要性上存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对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与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的区别上。现在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管理界,人们往往混淆了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这两个概念。从而导致了学者们对“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二者之间差别的讨论。首先从字面上来讲,组织学习更侧重于组织学习的过程,而学习型组织则更侧重于描述一种具有某种类型特征的组织。在这方面有过很多经典的阐述和总结。
Tsang(1997)认为二者有以下差别[10]:(1)组织学习强调的是“一个组织现在怎样学习?”,而学习型组织强调的是“一个组织应当怎样学习?”(2)组织学习是一个描述的问题,而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诊断的问题;(3)从目的来看,组织学习是分析取向的,以研究为目的,而学习型组织是行动取向的,以诊断为目的。由此可以把文献分为两类,二者有各自不同的专业会议、杂志等;(4)组织学习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于经院学派的学者,而学习型组织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咨询者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者。因此,在学术会议上很少有实践者,而在实践者专业会议上也很少有学者参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参与探讨两个方面的主导人员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组织学习这个新名词一时未形成统一观点,以及其难以把握性,从而减弱了实践者对它的接受度。
Leitch等(1996)认为[11],二者之间存在以下差异:(1)作为分析研究的组织学习,主要是观察和理解组织学习的现状,而学习型组织主要是研究还没有存在的理想组织;(2)组织学习关注学习结果和成就,而学习型组织关注的是学习过程和学习目的;(3)组织学习的文献大都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目的是提出理论或者通过科学研究来验证理论观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成果往往是高层管理者的成功案例研究,而且它们利用的是组织学习文献中提出的概念和方法。
虽然可以把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的具体研究方面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但是实际上学习型组织是组织学习理论的一个领域[12]。学习型组织的研究者主要是探讨组织在什么条件下学习,是对组织学习条件的研究,而学习条件是组织学习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型组织所应用的大部分概念和方法是从组织学习领域中借鉴的,实践中创建学习型组织也会丰富这些概念。所以说,组织学习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对实践产生深刻的促进作用,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2 什么是组织学习
关于什么是组织学习这个问题,Argyris等(1978)认为[13],组织学习的本质依赖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组织。因此,如果一个人把组织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就会得出组织学习的核心就是信息的通道和信息的流动,以及反馈过程的方式。以上观点后来为许多学者所扩展[14~16]。不过,在各个学科间存在一些争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争论,是从个体/认知角度来理解组织学习,还是把组织学习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把组织学习看作是个体/认知过程的观点在北美的文献中很盛行,以Argyris(1978)、March(1996)[18]、Huber(1996)[19]为代表。这些学者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个体加工和解释信息的过程来发展组织学习的模型。Cook和Yanow(1993)[20]认为,因为个体学习理论本身就没有统一,所以这些学者不会找到很好的证据来把个体学习的理论外推到群体层次上。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并不存在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他们二人认为,组织学习中基本的分析单元应该是小组。也就是说,要分析共享主观意义的获得、保存或改变,或者分析小组的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二人的模型也可应用到大规模的正式组织,或应用于分析组织中的次单元。其实,在组织学习的理论和文献中,并没有对更大而更具有战略性集体的共享意义进行研究[21,22]。
第二个争论,组织学习是一个客观的技术过程,还是一个主观的情感过程。前者重视理性的、数据和信息加工过程,后者重视组织活动中非理性的、潜在动机、情绪和机会;前者在干预组织流程的时候,会采取诸如计算机辅助的决策和会议等系统,而后者则会从情绪和亚文化等方面来对组织进行干预。
虽然组织学习的诸多研究学科和诸多不同的研究者对组织学习的理解出现了上述的种种所谓的分歧,但是要完整地看待这么复杂的组织学习,必须整合这些观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组织学习。
3 如何研究组织学习
第三个有争议的方面,是组织学习的研究方法。缺乏实证研究常被认为是组织学习研究的一个主要缺陷。而强调数量的实证主义方法与强调语言和意义系统特殊性的建构主义方法之间的争议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歧。二者之间的主要特征见表1。
表1 组织学习的研究方法比较
实证主义方法
建构主义方法
数据形式
问卷、测量
故事、语录、文本
分析
统计关系
意义建构
样本
大的总体的随机样本
选择少数目标
研究者的角色
独立研究者
参与式合作研究者
推论
统计推断
理论延伸
研究风格
追随科学化
行动研究
这个分歧在社会科学中是普遍的。一般来讲,美国学术界更加偏好数量方法,他们在管理科学领域中的期刊风格和研究培训风格都强调实证主义方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的质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个争论存在于组织学习研究的主流中,但在咨询应用中,一般不采用数量方法。这是因为,企业希望用快而方便的方式来诊断和改善它们的学习能力[23]。
以Easterby-Smith等人看来,对组织学习进行测量常常会出问题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持有的根本假设。他们认为,“你如何把某事物分类并加以测量,依赖于你怎样看待这个事物和你把它与什么事物相区分。”在组织学习领域有很多不同的存在论观点,越想准确地测量组织学习的本质和范围,那么就越容易犯所谓的“分类错误”[24,25]。因为,对一个组织有很多种看法(如大脑、机器、心理监狱、系统等)[26],所以把一些不同的前提假设应用到组织学习模型时,就会有很大的方法论的危险。因此,研究组织学习时最重要的伦理道德是,首先需要严格地构建诊断问卷的结构效度,其次要提醒使用者和顾客明确其中可能的分类错误。在组织学习的理论探讨中,组织学习的多层次性已经得到了公认。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多层次的研
究方法也许是一种更为全面和综合的方法[27]。
4 怎样实施组织学习
在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这里,我们只讨论两个。
第一个,是对渐进式学习和激进式学习之间区分的争论。March(1993)就持渐进式学习的观点,他们认为渐进式学习在组织中最普遍,也相当有用。如根据顾客需求不断改善产品就是渐进式学习。在一些渐进式学习的行为中,如果要进行激进式学习就会花费很大,因为它需要充分利用组织中未利用起来的所有知识和数据。Argyris和Schön(1978)则是激进式学习的倡导者。他们认为,组织通常都可以遵循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浅层的学习,是渐进式变革中的主要表现)的原则,但是开发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深层的学习,是激进式变革中最核心的部分)的能力是更为重要的。Miner和Mezias(1996)认为[28],上述两种学习都是很有建设性的,因为他们都把各自所强调的学习类型加以清晰的界定,而且二者也慢慢地结合起来。现在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观点越来越被认可了。Snell等就发现,在相同的组织中会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职位低的职工趋向于单环学习。
从战略观点来看,授权下属来实施激进式变革,会提高组织的适应性;从心理学和组织发展观点来看,则会广泛地提高组织对职工的承诺;但是,从组织理论的观点来看,授权会因利益的不一致性而引起问题。Nielsen认为,接近高层的领导者的三环学习(triple-loop learning:对自己学习过程本身的不断反思和调整)会产生所希望的社会变革,而组织低层的双环学习和单环学习则必须在有权力的股东的支持下才会发挥作用。可以看出,没有权力的强烈支持,激进式学习就很难实施。
第二个分歧是组织发展(OD)领域中的阶段理论和循环理论之间的争论。Argyris等持阶段理论观点认为,组织过程和进程阶梯之间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阶段2的开始要以阶段1的完成为基础,高级的阶段要优于低级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还认为,存在一个组织希望达到的最终理想阶段。然而,Dixon(1999)[29]则持循环理论的观点,把学习型组织看作是不断努力和改善的过程。循环模型一般都来自于Kolb等(1971)[30]或Revans(1978)[31],他们把组织学习综合为数据搜集、反思、概括和实验等几个连续阶段。但这里也会有简单化的危险,即把个体学习简单延伸到组织分析的层次上。
每种模型都有其优点和不足,因此研究模型适合的条件是重要的。但是二者也有结合的可能:阶段理论用来做诊断,循环理论用来作为行动的基础。在描绘组织学习能力发展阶段上,线形模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法[32]。
5 必须的研究领域:权力
在组织学习文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研究,那就是权力的问题[33]。对权力的研究,既可以在群体层次上也可以在组织层次上进行分析。Easterby-Smith等(1997)认为,可以采取更为人性和质化的研究观点来研究权力,因为这些方法对差异和过程问题特别适合。Kanter(1989)认为,如果组织消除等级制度和结构界限,那么,人际关系将从纵向(命令)转为横向(同事关系)[34]。因此,群体将对正式的等级制度提出更为强烈的挑战,也更为反对将要建立的新的规范和框架。这就是学习型组织文献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尴尬:结构变化也会降低其操作性,除非有一个可以导致认可共同利益的相互学习的过程。渐进式学习和激进式学习之间的争论也反映了对权力的不同观点。前者反映了渗透的观点,而后者允许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合作和深度访谈。这与组织学习伦理道德的观点有关:企业究竟是想用学习型组织来使职工服从和承诺,还是代表了真正想在集体行动学习中建立一种协调的相互关系。
组织中的权力与组织政治不可分割。对组织中政治的理解有两种观点: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批评主义的观点。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组织中的政治就是获得、发展和应用权力以及其它资源来获得所需要的结果。而批评主义的观点对功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Senge(1990)就认为,组织政治功能主义的观点,对真理和事实的扭曲理解充斥着大多数组织。Knights和CaCabe(1998)认为[35],组织政治关注的是有意义的秩序如何建立的过程。Lave和Wenger(1991)认为[36],“学习”包括身份建构的过程,因为学习者在学习发生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为了分析这种形式的学习,需要考虑其所在的单位组织政治和社会因素。Coopey(2000)研究后认为[37],组织的政治活动可以作为创设组织学习心理空间的一种方法;组织间学习是社会层次上政治活动过程的结果。而创设学习空间对政治的启示是:可以激发创造和确保决策的警觉性,可以重构知识,可以保持动态平衡。可以通过自由的政治活动来激发多种观点,从而使决策更为完善。同时,通过一个开放的政治形式,可以创设差异和多样化共存的组织环境,这对于组织学习是相当重要的。Blackler等(2000)认为[38],政治既是集体活动的产物,也是集体活动的中介。也就是说,组织学习既可以使组织政治变化,而组织政治也可以影响组织学习。
6 新出现的研究趋势: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
任何领域研究的发展都有其相似之处,在对组织学习进行了这么多年探讨之后,在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构之后,现在很多研究试图建立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Vera(2004)[39]等试图探讨战略领导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以及组织的发展阶段、组织的规模等方面对组织学习可能造成的影响。Somech(2004)[40]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组织学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于海波等(2004)通过大规模调查探讨了信任气氛对组织学习的影响,组织学习对个体的满意度以及组织层面的组织创新、主观财务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当然,组织学习机制模型的建立有待于对组织学习各个方面的深入探讨,以及对这些研究结果的及时综合和验证。在我国条件下,只有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大规模综合研究的探讨,才能建立我国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建立对于理解组织学习在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中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由于对组织学习的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它们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都有许多区别,因此需要有一个整合的理论观点来对组织学习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便为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奠定理论基础。更为迫切的是,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来对组织学习进行更具说服力的探讨,从而逐步建立组织学习机制的综合模型,尤其是对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学习本质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Geus A P de. Planning as Learn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8, March-April: 70~74
[2] Senge P.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Doubleday Currency, New York, 1990
[3] March J G, Simon H A. Organ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58
[4] 陈国权.学习型组织的结构特征与案例分析.管理科学学报, 2004, 4: 56~67
[5] 陈国权,马萌. 组织学习过程模型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2000,3:15~23
[6] 冯建民. 企业学习行为及学习效应的理论研究. 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博士论文,1998
[7] 俞文钊,吕晓俊,王怡琳. 持续学习组织文化研究. 心理科学,2002, (2): 134~135(151)
[8] 于海波,方俐洛,凌文辁. 组织学习的整合理论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2): 246~255
[9] 于海波. 企业组织学习结构及其多层面作用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
[10] Tsang E W K.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a dichotomy between descriptive and prescriptive research. Human relations, 1997, 50(1): 73~89
[11] Leitch C, Harrison R, Burgoyne J, Blantern C. Learning organizations: the measurement of company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1996, 20(1): 31~44
[12] Lahteenmarki S, Toivonen J, Mattila M. Critical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oposal for its measur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12: 113~129
[13] Argyris C. And Schön D 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ssachusetts, 1978
[14] Jerez-Go´mez P, Ce´spedes-Lorente J, Valle-Cabrera 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 a proposal of measur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5, 715~725
[15] Snell R, Chak A A-K.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empowerment for whom? Management learning. 1998, 29(3): 337~364
[16] Easterby -Smith M. Discipline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ontributions and critiques. Human relations, 1997, 50(9): 1085~1113
[17] Lehesvirta T. Learning processes in a work organization: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and/or vice versa?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2004, 16(1/2): 92~100
[18] March J.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ohen M, Sproull L.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6. 101~123
[19] Huber G. 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 Contributing Processes and the Literature.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ohen M, Sproull L.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6. 124~162
[20] Cook S D N, Yanow D.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learn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1993: 2(4): 373~390
[21] Gherardi S, Nicolini D, Odella F. Toward a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how people learn in organizations: the notion of situat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learning, 1998, 29(3): 273~297
[22] Hult G T M, David J. (ed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in supply management.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3, 21: 541~556
[23] Templeton G F. Lewis B R. Snyder C A.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for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onstruct.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2, 19(2): 175~218
[24] Richter I.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t the executive level: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Management learning, 1998, 28(3): 299~316
[25] Araujo L. Knowing and learning as networking. Management Learning, 1998, 28(3): 317~336
[26] Morgan G. Images of organization. London: Sage, 1986
[27] Hofmann D A. Issues in multilevel research: theor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In: Rogelberg S G.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247~274
[28] Miner A S. Mezias S J .Ugly duckling no more: pasts and future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1): 88~99
[29] Dixon N.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ycle: how we can learn collectively (2nd). McGraw-Hill, Maidenhead, 1999
[30] Kolb D, Rubin I M, MacIntyre J M.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31] Revans R. The ABC of Action Learning. Blond & Briggs, London, 1978
[32] Huzzard T. Communities of domination? 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power.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2004, 16, 5/6: 350~161
[33] Lawrence T B, Mauws M K, Dyck B, Kleysen R F. The politic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tegrating power to the 4I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1): 180~191
[34] Kanter R M. The new managerial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9,67(6): 85~92
[35] Knights D, McCabe D. When life is but a dream: obliterating politics through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Human relations, 1998, 51(6): 761~798
[36] Lave J, 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 Coopey J. Burgoyne J.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0, (3): 869~885
[38] Blackler F. McDonald S. Power, master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0, (3): 833~851
[39] Vera D. Manor B. Strategic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4, 29(2): 222~240
[40] Somech A, Drach-Zahavy A. Exploring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rom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4, 77: 281~298
The Disputes of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Luo Weiliang1Fang Liluo1Yu Haibo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Management Colle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