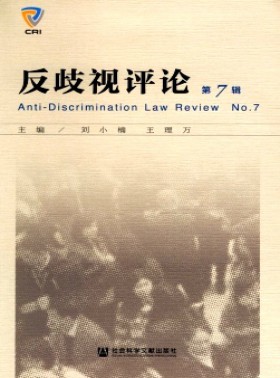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范文1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增加。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21亿,其中,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又以有配偶为主[1]。对已婚流动人口而言,夫妻一方流动或夫妻双方共同流动两种不同的流动模式,可能会导致家庭内部,尤其是夫妻之间资源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夫妻之间的婚姻暴力关系。婚姻暴力是我国政府、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对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家庭中的婚姻关系尤其是婚姻暴力关系需要给与特别关注,因此,本文将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通过描述分析、构建回归模型对此进行系统深入探讨,力求呈现夫妻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及其主体范围,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界定。从国际社会来看,家庭暴力主体范围仍以婚姻关系、血亲关系、姻亲关系等亲缘关系为中心,但是同居关系等非家庭亲缘关系也被一些国家纳入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规中[2]。对日本而言,婚姻暴力只是以婚姻为名,但是它可以指发生在已婚夫妻、同居男女、或关系等同于夫妻的男女之间的暴力行为[3]。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情况及公众接受程度,本研究将发生在同居关系或与婚姻关系等同的亲密关系之间的暴力行为剔除,将婚姻暴力(又称配偶虐待)具体定义为:一种强迫的行为模式,施虐者有意识对其伴侣实施包括身体、精神及性方面的虐待和控制。根据定义可知,婚姻暴力既包括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又包括妻子对丈夫实施的暴力。本文对婚姻暴力的测量囊括了身体、精神及性三个方面的形式,但没有具体讨论每一种婚姻暴力形式的分布特征,只要受访者遭受过任何一种形式的暴力,均视为“遭受过婚姻暴力”。
(二)理论分析关于婚姻暴力的触发机制,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提供了一系列理论解读。Coleman&Straus从相对资源论出发揭示婚姻暴力发生的风险性与夫妻资源的平衡与否直接相关,一般在家庭中拥有较多资源者拥有更大的强制力,也更可能施行暴力;而资源相对较少者会由于资源劣势难以阻止婚姻暴力的发生且因对资源较多者的依赖难以逃离这个家庭系统[4]。社会心理学家注重角色理论及与之相关的符号互动论在婚姻暴力现象中的解释作用。角色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将角色规范设定在文化、习惯、习俗、意识这个大系统中,并影响、制约着个人的人格、价值、态度和行为,每个人的角色行为都是由社会赋予或改变的。由此还发展产生了“身份不一致”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并不是制度规范本身引起家庭婚姻中的暴力行为,而是假定社会宏观的文化规范或角色期待与微观个人角色的实现或实践之间出现的不一致产生暴力行为。
二、文献回顾
依托相对资源论等理论,从夫妻相对资源和权力结构角度探讨婚姻暴力现象的研究受到国内学者的持续关注。女性作为婚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周林刚、陈璇对流动女性和农村留守女性做了比较分析,发现流动意愿和行为成为女性遭受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风险因素,城市文化对女性的影响打破了其所在传统家庭的原始平衡,致使夫妻矛盾愈演愈烈,进而提升了婚姻暴力发生的风险概率[5]。李成华、靳小怡从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入手,将目标投向有成婚困难经历的农村男性群体,基于2010年百村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由于资源劣势导致成婚困难的男性更容易对异性实施肢体暴力;“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家庭中的男性实施肢体暴力的概率显著较高[6]。赵延东、何光喜等摆脱物质资源的束缚和限制,将目光投向女性的社会资本方面,分析女性所拥有的作为支持性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遭受婚姻暴力的作用机制,发现女性的支持性资源会通过影响施暴者对潜在干预的顾虑而起到预防婚姻暴力发生的风险[7]。李成华、靳小怡基于资源论探讨了农民工家庭中婚姻暴力现象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相对资源对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女性,而情感关系则对女性实施婚姻暴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8]。风笑天(2014)、马春华(2013)的研究均揭示出,夫妻间的暴力呈性别对称现象,夫妻双方遭受暴力的路径模式类似,即只有夫妻权力关系平衡时,婚姻暴力才能得到有效制止[9-11]。在依托资源论对家庭婚姻暴力现象进行分析之外,不少研究还从社会角色及互动论理论出发试图揭示婚姻暴力发生的过程及其背后作用机制。佟新根据对婚姻暴力相关访谈资料分析,发现妻子遭受来自丈夫的虐待后会经历愤怒、绝望———反思丈夫施暴事件———将丈夫施暴行为合理化的过程;女性这一思维转换过程背后是受虐妻子对现有因性别角色差异导致“男强女弱”性别关系格局的“认同”和“接受”,丈夫施虐、妻子“接受”的互动过程带来婚姻暴力的持续存在[12]。不可忽视的是,妻子对丈夫施虐行为的“认可”固然有性别差异观念作祟,但背后还离不开妻子因资源缺乏而难以摆脱婚姻暴力这一境况。国内研究对相关理论提供了切实的验证和支持。同时可以发现,婚姻暴力现象的触发机制比较复杂,既有婚姻暴力关系中双方个人资源掌握程度的因素,也离不开社会性别关系结构宏观因素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可能会受到其它外界条件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婚姻暴力现象。当前城镇化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已成为我国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的流动会显著改变婚姻中双方的经济、权力结构等关系,成为婚姻暴力分析中需要考察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口迁移流动背景下婚姻暴力现象的特征既是丰富我国家庭婚姻暴力影响因素研究的要求,也是探索家庭婚姻关系稳定促进路径的现实需要。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调查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为深入分析不同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状况与变化,调查个人问卷部分采取主问卷与专卷相结合方式,主问卷面向居住在家庭户内的18~64岁中国公民,专卷面向儿童、老年、大学生、受流动影响人员和高层人才五个群体。主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受教育经历、工作/劳动经历、婚姻家庭状况、健康水平、生活方式、认知态度等方面的诸多信息。本次调查共回收18岁及以上个人有效问卷105573份。其中,个人主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6171份,受流动影响人员附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422份。本文关注的是夫妻流动模式是否显著影响婚姻暴力现象的发生,因此目标群体为已婚(包括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两部分)群体,样本来自个人主问卷和受流动影响人员附卷。剔除变量上的缺失值后,共得到19027人。
(二)变量测度婚姻暴力可以分为精神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辱骂、持续几天不理睬、经济控制)、肢体暴力(殴打)、性暴力三类。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询问被访者“F8您的配偶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这一问题,选项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殴打、辱骂、持续几天不理睬、强迫过性生活等,答案包括从不、偶尔、有时和经常。但是具体分析时,本研究不深入探讨每一种婚姻暴力类型的影响因素,而是把限制人身自由等六类选项均为“从不”的视为“没有遭受过婚姻暴力”,赋值为0;其余情况均视为“遭受过婚姻暴力”,赋值为1。对于自变量“夫妻流动模式”,结合流动人口专卷中受访者个人信息及配偶信息,可将夫妻流动模式分为三种:“均未流动”、“共同流动”、“一人流动”,分别赋值为“0”、“1”和“2”,其中“均未流动”为参照组。考虑到仅就因变量和自变量构建的回归模型会遗漏其它影响婚姻暴力的变量并导致结果有偏。为了准确和稳健起见,本文纳入了一组影响婚姻暴力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就业等人口特征变量,婚龄、夫妻相对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经济贡献、权力关系等家庭特征变量,以及户口性质等社会经济变量。
(三)模型设定针对因变量“遭受冷暴力与否”为二分变量的特点,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的家庭婚姻暴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模型具体形式设定。
四、夫妻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的影响
(一)我国家庭婚姻暴力基本现状数据显示,在本文关注的19027名受访者中,没有遭受过婚姻暴力的有14260人,所占比例为74.95%;遭受过至少一种婚姻暴力的有4767人,所占比例为25.05%。表2为模型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在遭受婚姻暴力及流动模式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女性(26%)遭受婚姻暴力的比例相比男性(24%)要高出2个百分点。从控制变量来看,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流动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更低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未就业比例可能是造成婚姻暴力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后文构建回归模型时,对性别进行了区别对待。
(二)实证结果表3是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婚姻暴力现象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的结果,模型的R方显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全体、女性和男性进行了估计。其中,第一列和第二列呈现了全体样本的情况,第三列和第四列是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第五列和第六列是男性样本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5仅对“流动模式”这个核心自变量进行控制;同时考虑到其他变量可能带来的干扰,模型2、模型4和模型6中加入了受访者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等控制变量。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夫妻流动模式对家庭中婚姻暴力现象的发生构成极为显著的影响。模型1显示,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夫妻均未流动者相比,夫妻共同流动和夫妻一人流动者遭受来自配偶婚姻暴力的概率分别高出53.7%和74.5%;而且,夫妻一人流动者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要明显高于夫妻共同流动模式下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这可能是由于夫妻一方的外出,造成双方在生活环境、人际交往方面的差异;此外,夫妻面对面互动频率的减少和互动深度的弱化,会对夫妻的婚姻关系产生复杂影响[13]。在模型2中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后,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现象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夫妻共同流动和夫妻一人流动者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显著高于夫妻均未流动者,分别高出42.1%和64.0%。此外,模型2还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自评健康状况良好、城镇户口对婚姻暴力的发生具有抑制作用。分性别的估计结果则进一步揭示了流动模式、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婚龄、经济贡献以及户口性质等变量对婚姻暴力现象作用的差异。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动模式对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现象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全样本和男性,夫妻共同流动致使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提高了65.5%;这一促进作用在夫妻只有一人流动时表现的更为突出,其概率提高了85.5%。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自评健康状况好、城镇户口对男性和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均有降低作用,但是对女性群体的作用力度要高于男性。
(三)作用机制上文已经证实了夫妻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产生显著作用。在此基础上,有待探讨的是夫妻流动模式这一作用的促进机制。根据相对资源论可知,夫妻资源、权力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夫妻婚姻暴力现象的发生。在检验相对资源论的解释力度时,本文有如下基本假设:如果夫妻流动模式通过夫妻相对资源及权力影响婚姻暴力现象,当在模型中纳入揭示夫妻资源及权力关系的相关变量时,夫妻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的作用力度应该有所减弱。本文在模型2、模型4和模型6的自变量中纳入“经济贡献”和“权力结构”两个变量,分别得到表4的模型2-1、模型4-1和模型6-1。从中可以得知,如果夫妻的经济贡献、权力关系出现失衡,婚姻暴力现象会加重。分性别来看,夫妻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出现失衡时,女性和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均有所提高,但是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概率提高的幅度更大,这一现象在男性经济贡献大时表现的最为明显。与此相反的是,虽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不平衡对女性和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现象均有正向促进和强化作用,但是权力失衡尤其是女性在家中有实权时,女性反而相较于男性更容易遭受婚姻暴力。
对比表3和表4可以发现,经济贡献和权力结构两个变量加入后,夫妻流动模式尤其是夫妻一人流动对总人口的婚姻暴力作用减弱(1.420<1.421,1.640<1.648),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夫妻流动模式经由改变夫妻资源权力结构而对婚姻暴力产生。如果分性别来看,两个变量的加入使得夫妻流动模式对婚姻暴力的影响呈现相反的结果。对女性群体而言,夫妻共同流动对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响因经济贡献及权力关系变量的纳入而减弱(1.515<1.522),但夫妻一人流动对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响则因上述两个变量的纳入而强化(1.833>1.832)。与此相对,经济贡献和权力关系变量纳入后,夫妻流动模式对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响在夫妻共同流动和夫妻一人流动时呈现与女性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夫妻共同流动对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响因经济贡献及权力关系变量的纳入而强化(1.32>1.306),但夫妻一人流动对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响则因上述两个变量的纳入而减弱(1.527<1.546)。
五、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