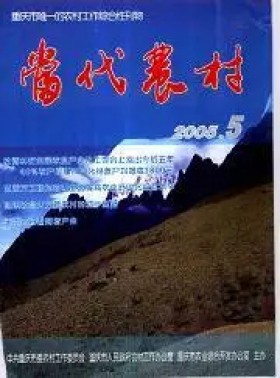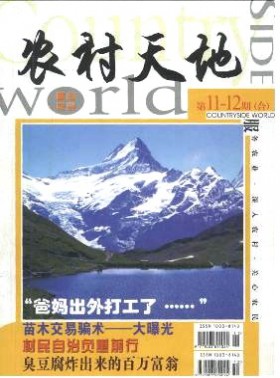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1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参考文献:
[1]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32, No. 125.(Feb, 1965):1-14.
[2]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3] Quiggin. John.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nomics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XXII,No.4(Dec,1988):1071-1087.
[4] Swaney. James. A Common property, reciprocity, and commun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4, No. 2(June,1990):451-462.
[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12.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67-173.
[7] 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27-35.
[8] 李建.农村公共品三维复合属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 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2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路径选择;建议
Abstract: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ies construction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re compared, still in a stage of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my ow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ocess i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me own views, hope to be able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level.
Keywords: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ath selection; suggestion
目前,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看,与城市之中社区建设相比较,还仍然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看,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新型指导理论正处于探索之中,从实践上来看,我们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之中在取得较好的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笔者通过自己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与规划之中实践与学习认为,为了更好的提升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对于与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亟待梳理与研究。例如,对于新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内涵、定位、建设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目前,从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新农村社区管理、服务、治理以及目前我国新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解决策略等方面进行探讨的。笔者结合的自己所学的规划专业理论以及工作实践,立足于对新农村社区概念的界定,对目前我国新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一梳理,进而希望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新农村社区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新农村社区内涵的界定
社区一词,追根溯源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相关著作与文献之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社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才逐渐增加,进而产生了“什么是社区”“社区的定义”的探讨。对于社区一词,不同的专家与学者从自身的经验、研究视角出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提出了自己认为的“社区”概念。总结与归纳后,笔者发现不同的学者所提出的“社区”内涵相差甚远。社区作为较早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研究的整体范围往往是城市,对于农村社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所谓“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焦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的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但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交通工具、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运用,使得我国的农村社区发展不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隔绝性与封闭性较强的社区,其与外界社会发展具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农村社区具有着诸多特征:例如,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而言,新农村社区的谋生手段主要依托于现代农业生产。第二、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新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农村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较,无论是从人口密度还是从人口的规模来看,都比传统农村社区要大的多。集中性是新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新农村社区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与城市的发展逐渐趋同,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与日俱减。笔者结合了传统农村社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目前新农村社区的相关成果认为“新农村社区”是指“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一定规模人口为基础、以一定产业为支撑、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区组织及相应的治理机制为保障、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农村社区”。
由此可见,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着较大的不同,这就要求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与建设,其在规划与传统的农村社区规划具有着一定的差异性。笔者认为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路径选择中,要能够立足于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实际,通过不断的治理与完善,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建设规划的整体水平适合新农村社区的发展。笔者认为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过程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能够依据科学的理论,辅之高效的实践,才能够更好的促进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科学性。
二?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规划主导思想不清晰
新农村社区的规划主导思想要与的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联。从新农村建设与发展来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及逐步改善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是新农村社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最为重要的问题。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以及核心即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进而提高我国农民的生活整体质量。但是,在具体的新农村规划实践过程之中,新农村规划更多的是对居住空间的梳理以及物质环境的改善,这就造成了新农村社区规划是优先发展生产还是优先改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规划主导思想在“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看似矛盾的两难境地之中徘徊。由于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之中的规划主导思想不清晰,直接导致了在具体的规划实践过程之中造成“规划失误”。众所周知,规划水平的高低甚至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未来发展,规划主导思想不清晰是影响目前我国新农村的社区规划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3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撤村并居优化农村环境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必然,探寻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修正农村社区的发展轨迹,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撤村并居;环境治理;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2003901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一部分农民不满足于现有“春秋两闲”的生活现状,纷纷到城市里打工、经商,甚至是开工厂,脱离了祖祖辈辈相守几千年的农民生活,告别了“男耕女织”的古老传统,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本来计划生育国策已经使农村人口呈稳步下降趋势,再加上农民家庭的不断外迁造成了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在村子里出现了大量的空闲房屋,搬到城市里去的农民院落外面的柴草等杂物成了无人管理的个人财产,时间长了便成了无人管的垃圾。大量人口的外迁使留在村子里生活的农民拥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的扩展却滋生了农民生活的随意性,乱扔垃圾和随意搭建的现象到处都是,村子的公共基础设施无人管理而日趋破败,形成了一个个环境欠佳的“空心村”,通过撤村并居优化农村环境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1撤村并居,造就新型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旨在改变现在农村严重的“空心村”和“环境脏乱差村”的现状,在倡导“大农业”的前提下,为农民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科学的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过上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不再用柴草做饭,不再自己烧煤取暖,丰富的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把闲暇时间只会打麻将的农民从自家的桌子旁吸引出来,在花草围簇的社区广场上扭起秧歌,划起旱船,跳起健美操、交际舞,甚至还有全国流行的乍看还真有点别扭的“僵尸舞”,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2治理环境的机遇
第一,由于农村社区一般都建在交通便利、没有居民建房的“原始地域”,所以在开始筹建农村社区的时候,设计者们可以科学地安排自来水管道、电线路径、排污管道、集体供暖管道,甚至是天然气管道的预设,避免了旧村改造过程中的重复建设和相互影响,社区内楼盘布局和道路规划相辅相成,彰显人性化设计,方便了入住农民的日常生活,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社区内的绿化带、草坪、鲜花、绿树、假山、喷水池等衬托出社区环境的优美,让习惯于田园美的农民享受到体现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之美,为农民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物质生活环境。
第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改变了农民原来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农民形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由过去“改善生活”中的大鱼大肉变成现在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科学饮食;社区内的文化广场为农民提供了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的好场所,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大大丰富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内容,健身器材设备的完善增强了农民的体质,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第三,撤村并居,建立农民集中居住的农村社区,加强旧村土地的复垦,有利于集中各类闲散土地搞承包,走大农业之路,提高土地的科学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粮食的产量和质量,还能再次解放一部分劳动力支援城市经济的发展。
3治理环境的挑战
第一,搬到农村社区生活的农民对于新的生活方式不习惯。大部分农民已经习惯于庭院式生活,在社区内出现了有些农民开垦土地种菜、养鸡,甚至在树上拴上绳子晒衣服等等不和谐现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农民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生活常识教育,还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惯,不适应城市人的生活,造成了人与环境的不协调,这种现状反映出主观部门工作人员的粗枝大叶,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有待改进。
第二,农村社区的某些农民有不满情绪。撤村并居的新举措造成一部分农民被强制离开他们热恋的土地,被迫上楼居住,再加上社区内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给他们生活上带来了不便,更加助长了他们的不满情绪。生活在自然村的农民家族观念比较强,让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难以割舍的土地,甚至还要面对祖坟被平的结局,他们的不满情绪尤为突出,极易造成,影响社会的和谐,这也反映出主管人员不注意工作方式人性化的问题。
4对撤村并居的一点建议
主管人员要注意工作的科学性,探究撤村并居是否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农村社区的位置、布局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构建内容丰富的社区文化,满足农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主管人员还要注意工作的人性化,注意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提高农民对社区生活的认识,耐心而细致地开展工作,消除农民的不满情绪,加快社区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
总之,研究撤村并居背景下农村治理环境过程中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有利于我们改进工作方法,端正工作态度,关注农民的情感感受,彰显人文精神,加快农村社区城市化,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王仁贵.“撤村并居”是与非[J].望,2010,(47).
[2]蔡建云.加强撤村建居社区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政策望,2009,(09).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4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区各部门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优势,做好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布局,提升发展体系、行政管理机制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力,使各地区能运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更好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环境。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重点提出:“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1]。”至此,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及文化发展体系,提升农村地区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及市场资源整合能力,为未来阶段农村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及发展条件,成为新时代农村地区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发展需求角度来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了传统城乡融合发展结构,提高了农村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网络构建的主导能力。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弥补早期阶段农村社区建设改革存在结构性缺失,解决使农村地区行政管理职权分化问题,为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卫生环境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夯实基础。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非单一在原有体系上进行改革优化,而是从发展结构上作出调整,将农村地区农户衣食住行与城镇地区进行对接,在不改变原有生产劳动方式及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升农户总体生活质量,强化农户生活幸福感及获得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环境经济及产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予以解决。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多数集中在行政管理及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做好对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并制定科学的资源分配方案,有助于深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
2.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要求在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好协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将多个行政村进行合并的基本模式。其中,各地区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制定福利补贴标准、规范社区服务体系及优化管理调度模式,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思考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使农村产业建设形成发展合力,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其社会福利标准、社区服务质量及管理调度执行性势必有所提升。但从实现环境的发展视角分析,部分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解决农村发展融合行政管理权限重叠的问题,加速农村发展环境现代化治理,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上限。但各地区乡村发展存在内部矛盾,仍然未能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得以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产生必然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影响[2]。新型农村社区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单一,管理调度时效性不足等问题,仍然困扰了后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应在充分了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特征的同时,做好对各项建设发展、管理工作的优化,进一步建立长效化发展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时展接轨,并有效吸纳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提升新时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水平。
2.2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问题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利益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及市场资源调度四个方面。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机构与企业提供支持。但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式分析,上行经济固然对农村建设创造便利条件,但政府机构及企业同样面临经济转型及市场产业升级的压力,如何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职权划分,并在合理范围内为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则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考虑的问题。利益分配主要指农户之间居住资源及经济资源的分配。部分地区大刀阔斧的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基于大拆大建进行农村改造。该方式的确加速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但不利于对农户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容易促使农户与政府机构之间产生嫌隙,从而,导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调配,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各个乡村产业优势及产业发展需求不尽相同,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居住条件等作为底层建筑。因此,有效发挥不同地区产业优势,强化产业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调配矛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3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诸多便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充分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中心化及统筹化三个方面。其中,不同建设特征也代表了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未来阶段,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充分做好对不同发展模式下建设经验的积累,开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视角,为未来阶段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总体实效性提供有利保障[3]。
3.1产业化
产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产城联动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该模式利用对产业资源的聚集优化,优化本地区产业资源配置,降低传统模式对产业发展的限制,使各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一体化联动。通过对人口资源的社区化集中,提升农村地区对部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改变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及居住资源紧缺的问题。基于产城联动模式的构建,充分加速土地资源的流转,优化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生态,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则给予农户更多的居住选择权,帮助农村环境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单一土地资源结构对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限度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需求,为后续阶段强化各地区产业建设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中心化
中心化是指由乡镇企业与政府机构协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产业资源、服务资源及配套设施的集中化管理,进一步打造以农村地区中心发展为载体的舒适生活圈,围绕对优美环境、良好服务体系及多元市场生态的建立,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面貌的改善[4]。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建立中心化发展模式,实现将资源共享理念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效运用。中心资源的共享可以更好控制成本支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位一体发展,使政府资源、民间资本及商业资本等均可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民间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加入,将为提升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及改造生活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需求与企业利益诉求充分契合。以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3.3统筹化
统一协调、统筹管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农村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结构单一及管理覆盖范围不足问题,部分地区由于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缺乏合理性,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三不管地带,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及产业结构改造因此受限。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统筹管理,则将管理职权进行统一分配,提升各地区行政管理执行力,实现行政管理全面性覆盖,为农村地区市场发展统一规划、社会资源统一调度及产业资源协同配置等奠定良好根基。因而,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化视角来看,统筹化管理是基于大局观视角,为农村社区建设及环境发展改造创造良好条件,实现农村生产水平、生活质量及生态治理等多方面提升,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农村地区建设发展需求,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对接。
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科学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面貌,提升部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突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优势,强化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的优化,明确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定位,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总体社会服务质量,有效为农户及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以此,排除农户及企业的后顾之忧,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为后续阶段政府机构进一步从多个视角提供发展政策的支持创造条件。
4.1优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
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做好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有助于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为农村发展资源的整合提供良好机遇。因此,各地区应围绕协同共助、合力助推的中心思想,优化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于充分发挥农村产业发展优势及助力产业融合,改变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结构,确保新型农村社区能持续为优势产业及支柱产业发展输送新鲜血液,进一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对于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不应采用一以贯之的发展改革理念,要在不影响当前产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做好多方面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试点改革,适时做好对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基于产业发展中弹性化策略的运用,为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5]。从而,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经济矛盾。
4.2明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精准定位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面向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及为农户生产劳作创造便利条件两个方面做好行政管理规划,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能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内容制定科学方案。在此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摒弃传统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理念,面向农村发展的城镇化对接构建行政管理新体系,并根据各个行政村行政管理工作现状,统一行政管理工作标准及内容,实现各个不同行政村之间行政管理工作的步调一致。避免在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及管理调度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差异化问题,使农户能真正意义上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降低外部因素干扰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的影响,促使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达到更高水平。
4.3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企业、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及农户等提供经济、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方面支持,降低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结构性阵痛问题,使企业、教育机构及农户等能尽快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新环境,排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中存在阻碍。为此,政府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第一,政府机构应面向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等做好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卫生发展、文化建设及环境治理等要求,做好与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对接,缓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中存在压力。第二,政府机构应为农户及农村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失业及医疗等方面经济补贴,加速农户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基于政府兜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6]。
4.4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传统农村发展结构,提升农村地区信息化及现代化发展水平。为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中农户生活品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对社会服务功能及行政服务功能的完善,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有效性,确保相关水、电建设及治安管理水平能达到较高标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做好铺垫。另外,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功能,不仅要面向外部发展做好合作,同时,也应针对内部经济发展循环及本地区农业资源开发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优势,从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认同感,使农户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下能更好履行自身义务及社会责任,提高农户基础生活幸福感。
4.5强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与政府支持
政府做好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可以更好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降低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制约,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多元化、系统化及科学化推进。对此,新型农村的社区建设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合理做好行政村管理融合的决策,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农户核心权益。在充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夯实基础的同时,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上限,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为未来农村发展转型做好充足准备。除此之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根据当前发展需求,持续做好合村并点工作的深化,既要发挥各个机构及各个部门社会服务功能,也要维持良好发展改革秩序,进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的良性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极大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迈入时代新纪元。各地区应紧抓时代机遇,积极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管理协调及发展优化,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改革,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总体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王俊.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7):6.
[2]王生章,崔佳慧.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初探[J].行政科学论坛,2018(10):47-50.
[3]张艺颉.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与转型路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8.
[4]魏文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探究[J].南方农业,2021(17):3.
[5]王思瑶,马秀峰.新型职业农民人文素养提升的应然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21(8):76-80.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5
关键词:村镇宜居社区;农村社区建设;PESREI
前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村镇宜居社区建设已经被提上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日程,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村镇宜居社区”只有本课题组的些微相关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村镇宜居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等相关文献研究和建设实践,提出并明确界定了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概念及其内涵,为后续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实践指导性。
1 相关研究
1.1 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
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各类社区建设工作,但未使用“社区建设”这一概念,而是更多地采用社区发展、社区组织、社区工作、社区福利、社区照顾等。联合国1995年发表的《社会发展经由社区发展》一书中,将社区发展定义为“一种经由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创造力,以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在我国,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并推行社区服务,到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和推进社区建设。由此我国“社区服务”的提法进一步延伸扩展为“社区建设”,这一概念相当于国际上所流行的社区发展概念。关于社区建设的含义有不同的界定,但大多强调社区建设是全方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建设必须利用社区资源,依靠和调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等[1]。
从区位和内涵上来说,社区发展则是社区建设的外部要求和保障;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局部任务,社区建设的成效取决于社区发展的水平,依赖于社区发展的培育;解决社区建设困境的出路在于社区发展[2]。细究二者的区别,社区建设着眼于“社区”这个小范围,社区发展着眼于“区域”这个更大的地区规模;社区建设侧重于硬件设施以及社区眼前的任务,社区发展更侧重于软件设施以及有关区域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建设。
1.2 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
对农村社区建设,国内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李增元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社区真正成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承担起促进农村政治民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载体[3]。黄小晶(2006)分析了农村新社区的五种主要功能,即发展社区经济和福利功能、传承社区文化和情感功能、促进社会文明和稳定功能、提供社会保障和共济功能;认为农村新社区建设应包括涉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六大任务:社区经济建设、社区设施建设、社区环境建设、社区服务建设、社区治安建设、社区组织建设[4]。陈建胜(2011)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把农村作为一种自然型的社区而进行的整体性的建设,包括经济发展、基层政权构建、文化团结建设及其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等多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广义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乡村社会发展建设,在很多国家又叫做农村“社区发展运动”、“社区复兴运动”、“社区重建运动”、“新村运动”等。而狭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借鉴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而在农村社会“移植和嵌入”的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5]。
国外对于农村社区建设,一般采取农村社区发展的概念。如Cavaye,D.J.(2001)分析了乡村社区发展的内涵,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发展是财富的衡量标准――财富意味着人们珍视的事物。它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改善。而农村社区发展取决于多个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1)支持经济活动和社区生活的充足的基础设施;(2)新业务或建立新的行业和企业、可获得的风险资本、高效率;(3)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竞争、社会公正和环境负责任的政策;(4)维持就业、人口和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的社区服务。但长久的农村社区发展也依赖于更多无形资产的发展,比如社区所有权、地方领导权、行动、“反思”和动机[6]。
2 结束语
由村镇宜居社区的内涵得知,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和小城镇宜居社区。相应的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亦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建设和小城镇宜居社区建设。即相比较村镇社区建设而言,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本质体现在社区的宜居性上,即社区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围绕村镇社区居民的需求完善社区的软硬件设施。
总之,我们认为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主要指社区硬件设施建设,如住宅、市政工程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而广义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不但包括硬件设施建设,更包括涵盖社区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软件设施建设,意即村镇宜居社区发展运动。文章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指广义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涵盖如下几个方面:社区人口(people,P)、经济社会(economy & society,E&S)和资源环境(resource & environment,R&E),简称PESRE。另外如果为了强调社区软硬件设施的区别,突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可以把基础设施进行单列,即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内容亦可以细分为社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I)四大方面,简称PESREI(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张明.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镇研究[M].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2]刘平.问题与思路从社区建设到社区发展[J].学习与探索,2002.
[3]滕玉成, 牟维伟.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述评[J].东南学术,2010(6):86-95.
[4]黄小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新社区[J].农业经济问题,2006(4):47-49.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范文6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结构与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97){1}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从集体层面给出了社会资本的界定,即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自此之后,学界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第一次从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及功效进行研究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95){2},他通过对意大利的南北部的比较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从此之后,社会资本被广泛用于解释经济发展、经济治理等诸多问题。福山等人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多的社区更能够应对贫困,解决争端,促进就业,提高组织效率,促进社区经济发展(Fukuyama,1996{3};Narayan,1999{4};Woolcock,1998{5})。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维持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指出社会资本的总理和分布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凝聚力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王思斌,2000){6}。正是社会资本的强大解释力使它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被广泛的运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测量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混乱(赵延东,2006){7}。因此,学者们从各自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如何测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普特南(2001){8}指出应该从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南(2001){9}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但更多的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是使用8维度法、7维度法、6维度法和5维度法。8维度法有按照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进行测量(Paul Bullen、Jenny Onyx,1997){10},但这种测量方法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Kawachi等(2004){11}通过回顾33篇文献发现,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至少有8个,即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社会支持、自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Desilva(2006){12}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议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包括8个主要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我国学者桂勇,黄荣贵(2008){13}确立了8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对8维度测量指标进行了检验,最终提取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7个因子、29个项目;姜楠(2009){14}提出了从信任与团结、团体、网络、社区凝聚、社区参与、信息交流、社区安全、政治参与8个方面对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且对城市单位型社区与非单位型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分析。7维度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纳拉扬和普里切特(2005){15},他们从村庄层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出衡量农村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具体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国内学者多用5维度法和6维度法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聚任等(2005){16}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贾先文(2010){17}提出应该从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宿感和社区凝聚力5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裴志军(2010){18}认为应该从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谢治菊,谭洪波(2011){19}提出了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此外,Harpham(2007){20}也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6大维度,即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别提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通过经验研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检验,从而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维度,但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何谓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有其基本的组成元素,那么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社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其组成结构又是什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如果不回答这一问题,测量指标的建构将会失去其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二,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检验和模型的建立,却忽视了对社区社会资本真实状况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缺乏关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更没有关于少数民族村落与汉族村落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要建构这些指标,其作用何在?测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第三,现有研究建构了多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但并没有指出这些指标受社区中哪些因素的影响,似乎这些指标就是决定社区社会资本的最终因素,从而预设了一个前提假设,即社区的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规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变量或者自变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本身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同类型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状况是不同的,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学者们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这些指标仅仅只是中介变量,其本身也是受其它因素影响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呢?从现有研究中显然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转型期的政府绩效、社区的效率与社会活力。但是,社会资本作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范式,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首先要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采取行动的习惯特质,给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界定。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农村,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为此,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和社区归属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是透过社区居民对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展现出来的。但是,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测量指标、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较少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对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故此,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以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客观地呈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实际状况。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入山东、陕西、甘肃、宁夏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获取了由2201个户主组成的数据库,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描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的分析。
二、研究设计
1. 结构测量指标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对其进行了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基本上存在着针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社区社会资本方面,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村民的行为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以集体为取向,将会更多地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从他者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即“一般社区参与”。反之,如果行动主体的行为以个体为取向,则将会更多地从个体利益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即“特殊社区参与”。为此,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同时,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因此,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对于体制内人员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
之所以选取谢治菊等提出的6维度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们提出的测量指标是针对“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村民们之间关系比较简单,村民们的‘信任、社区参与、互惠、共享、合作、社区归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谢治菊、谭洪波,2011);第二,在比较了国内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之后,我们发现他们提出的6维度法其信度是最高的,其中四个维度的信度系数高达0.9,只有互惠、信任两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在0.7以上。因此,可以成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第三,他们提出的这六个维度,既考虑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时也关照到了国内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还考虑到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其中,“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 、“互惠”、“信任”指标主要借鉴了国内外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相关维度;“合作”、“共享”指标则是充分考虑到了农村社会村民间互动的基本逻辑。虽然是“在集体层面界定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但是考虑到个体层面的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Harpham,2007),“也更加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而且在实践中也更加可行”(桂勇、黄荣贵,2008)。因此,关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变量值,我们仍然在“是村落内个体层面(村民)进行测量的,然后由村民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社区的特征指标”(裴志军,2010))。为了准确测量村民的态度,采用了李克特5点量表法,每个变量均设计了“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5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分。但考虑到我们的调查地点东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制定量表时,我们对具体的测量指标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具体操作化如下:
(1)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自愿自觉地参与社区内的各项事务和各种活动的过程。根据我们对调查地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在的31个村子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些村从未举行过“义务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也从未举行过“义务献血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协会组织。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仪礼或主要节日,农民很少会和亲戚、朋友一起聚餐。为此,我们将测量指标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了9个。“特殊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一般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2)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在操作化过程中,考虑到“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这一指标属于社区参与维度,同时,这是一个对别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态度选项,放在这里不合适,为此,我们取消掉了这一指标,操作化为: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为了村容村貌不会乱丢垃圾、我们村会越来越好。
(3)合作: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对于这一维度的测量指标,只是将社会中介组织中养鹅协会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了代替。操作化为: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合作。
(4)共享:共享即分享,既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操作化为:有好吃的食物会分给邻居与其他村民、买了农耕用具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自己认识的人。
(5)互惠:指互相给对方恩惠或者好处。操作化为4个测量指标:农忙时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红白喜事时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村民需要帮忙会不计报酬的帮助他。
(6)信任:信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以情感内容和因素为维度的一方对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种相信的主观态度。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为此,我们将“信任”维度系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除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农村还存在着对于领导、政府、媒体、警察、法院和法官和医生的制度化信任(赵延东,2006),及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化信任。“制度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院和法官”、“相信医生”;“熟人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家人说的话”、“相信自己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普遍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我会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在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省31个自然村,重点考虑的是自然村作为村落共同体保留着村落内习惯、民俗、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任的整体性(裴志军,2010)进行的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我们选取了山东省各市县20个自然村;陕西省的渭南蒲城县和铜川市印台区各1个汉族村落;甘肃省靖远县1个汉族村落;宁夏回族自治区8个村落(回汉杂居村3个、纯回族村2个(其中1个是移民村)、纯汉民村3个)作为调查地点。为了获取村庄作为整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在山东、宁夏、甘肃分别选取了1个村子进行了整体调查,在其他28个村落,先获取自然村户主的名单,然后按照村落农户的比例随机抽取户主作为调查对象,每个村共访问了30~185个户主,由于搬迁、外出打工、年龄太高、拒绝访问等原因,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集包含2201个户主组成的样本,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见下表(表1)。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地方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经济发展来看,山东省的整体经济状况能代表东部地区,陕西、甘肃和宁夏基本能代表西部省份,体现出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第二,从民族构成来看,有纯汉族村落(如山东省的大部分村落)、回汉杂居村落和纯回族村落(以宁夏的样本为代表);第三,从村落类型来看,有原来的传统村落,有移民村落,和“合村并居”后形成的新的小区;第四,我们的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构成,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村庄均为调查员的家乡,由于调查员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员,调查员的这种参与者的身份,既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能够获得真实的资料。
(1)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
首先,我们对前述的6维度38项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在0.4以上,其它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互相走动)”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为0.369,其它均小于0.3;“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没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为0.328。为此,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接下来,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剩余的33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结果见碎石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有9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F3、F4、F5、F6、F7、F8和F9来表示。从表2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我们村会越来越好”(0.438)、“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0.419)和“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0.402)以外,都达到0.5以上。9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1%。KMO检验值为0.861,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26 061.624(p=0.000
“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会有生意或合作项目”、“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合作”5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7、0.824、0.920、0.916和0.856,说明此5项指标很好地代表了F1。这5项指标都反映了村民与不同主体有经济上的往来。因此我们将F1命名为“合作”因子。
“有好吃的食物,我会分给邻居与村民”、“我家买了农耕用具(小四轮),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我认识的人”、“农忙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4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40、0.783、0.712和0.658。这4项指标反映了邻里之间对食物、农具、信息等的分享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共享”。
“红白喜事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相帮助”、“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3项指标对F3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03、0.531和0.507。这3项指标表达了邻里之间的相互报偿,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互惠”。
“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和“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这2项因子对F4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23和0.619。这2项指标更多反映了村民完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种诉求或发挥某种特长而参社区活动,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特殊社区参与”。
“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这4项指标对F5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38、0.715、0.777、0.684。这4项指标更多表达了村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如社区发展、社区卫生等)的关心,是从社区公共人的角度参与到社区日常事务之中的,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一般社区参与”。
F6对应着“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和“我们村会越来越好”,其负荷值分别为0.713、0.775、0.568和0.548。这4项指标均反映出了村民对自己所生活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故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社区归属感”。
F7对应着“相信我家人说的话”、“相信我的亲戚(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的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其因子负荷值分别为0.667、0.649、0.711和0.769。这4项指标反映出了村民对于家人、亲戚、邻居等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熟人信任”。
F8对应着“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官/法院”、“相信医生”,其负荷值分别为0.651、0.763、0.520、0.765和0.667。这5项指标表达了村民对于政府、体制内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制度信任”(参见表2)。
F9对应着“社会上的大多数是基本可信的”和“陌生人向我求助,我会帮助他”2项指标,其负荷值分别是0.736和0.683。反映出了村民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的不确定主体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普遍信任”。
(2)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以9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9个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数据表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Mean=40.09,S.D=13.48),其中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程度分别为52.59(S.D=20.99)、42.83(S.D=12.40) 38.57(S.D=10.28 )、25.37(S.D=6.99)、 26.70(S.D=7.38)、29.22(S.D=6.67)、56.88(S.D=10.25)、23.23(S.D=7.27) 、16.05(S.D=3.34)。这一结果表明,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并且合作的差异性最大,普遍信任的离散性最小。
(3)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具体因素,我们将、居住类型、民族、所在地区、年龄、家庭年打工收入、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等7个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2)。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性别、是否党员、受教育程度、户口等因素的影响,但都无统计显著性,在最后模型中未予考虑。为了简明起见,表2只报告了最后模型的计算结果。
从表2第10列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总体状况的解释力达到了显著水平(R2=0.024,p=0.005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08(p>0.05),说明无的村庄比有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对具体因子的影响来看,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3(p
居住类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90(p0.05)、-0.110(p
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24(p>0.05),说明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比汉族聚居的村落其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民族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1(p0.05)、0.095(p0.05)、0.061(p0.05)、0.135(p0.05)和-0.023(p>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族聚居的村落在共享、互惠、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0.031分、0.095分、0.061分、0.021分、0.135分和0.013分,在合作、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别低0.161分、0.002分和0.023分。其中民族对共享、特殊参与、社区归属、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汉族聚居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
所在地区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56(p>0.05),说明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比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要高,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在地区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社区所在地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4(p0.05)、-0.340(p
年龄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16(p>0.05),说明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其社会资本要高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村庄人口年龄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村庄人口年龄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74(p0.05)、-0.008(p0.05)、-0.054(p0.05)、-0.020(p>0.05)、-0.006(p>0.05)和-0.040(p
家庭年打工收入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22(p>0.05),说明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村庄比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要低,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打工收入对社区社会资本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家庭年打工收入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50(p
最后,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72(p0.05)、0.042(p>0.05)、-0.090(p0.05)和-0.003(p>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在5年以上的村庄比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在共享、社区归属、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0.002分、0.042分和0.049分,在合作、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别低0.100分、0.087分、0.029分、0.053分、0.090分和0.003分。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合作、互惠、熟人信任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1.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由9因子构成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在结构上由9个因子组成:合作、共享、互惠、 特殊社区参与、一般社区参与、 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如前所述,国内外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探讨,我们发现这些测量维度都离不开“网络”、“信任”、“参与”、“互惠”、“合作”、“共享”等指标,且当前学者们都是基于集体层面测量社区社会资本,我们结合以上学者(赵延东,2006;桂勇、黄荣贵,2008;裴志军,2010)的观点,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从而形成了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九种结构维度。
2. 影响村庄社会资本状况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村庄的自然特征和人口变量对村庄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一,有无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有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无的村庄。第二,不同民族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汉族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村落,而在其它方面汉族村落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村落。第三,不同地区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而在特殊参与、一般参与和社区归属方面却显著低于西部地区的村庄。第四,不同年龄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60岁以上占主体的村庄,而在共享、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第五,家庭年打工收入不同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上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而在一般参与、社区归属和制度信任方面却显著低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第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同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3.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偏低的原因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偏低,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基层结构。“差序格局”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由此,受“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有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但对于外人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
第二,村庄缺乏自组织。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组织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农村社会社区缺乏这种村民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没有村民兴趣小组,没有秧歌队,也没有什么能组织活动的协会。自组织的缺乏使村民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去进行社区参与,也没有机会去进行各种经济类的合作,这就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逐渐瓦解,村民社区归属感减弱,村民之间的互惠和共享行为也逐渐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现危机。而有的村庄一般能够形成组织(如宁夏地区的伊斯兰教组织),所以村民的同质性增强,相互之间的交往增多,在合作、共享、参与和信任上更能够达成一致,社会资本存量相对无的村庄要高一些。
第三,村庄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仍是从上至下的,村级事务由上级通知或由各级村干部讨论决定,最后下达村民,实现村庄治理。2006年我国政府提出要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变革的新目标,强调还政于民,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共同治理{23},但在村庄治理中能真正在村级事务中说得上话的村民不多,大多数村民都不了解村庄治理是如何实现的。村民在意识上比较愿意参加村级事务,但是在现在的村民选举和村级事务中能听到村民群众的声音比较少,村民自己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认为自己即使参加了选举或村级事务自己的建议也不容易被采纳,心愿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在涉及民利的参与方面表现出不积极的一面{24}。
第四,社会流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向{2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频繁流动,由此带来了人们生活面向的改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致富观念已经有很大改变,大多数人渴望新的致富途径,{26}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为主,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当农民“没钱途”,他们得以维持生活的资源基本是从城市通过劳动换来的,再加之近几年用工荒的出现,使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增强了他们继续留在城市的打算。为此,他们很少过问也基本不会参与村庄的事情,从而导致社区归属感,社会区参与的降低。同时,随着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务工,村里留下来的基本就只有老人和孩子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他们很少去关注村庄事务。从而导致村庄社会资本整体状况偏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流动加快,村民不再局限于在一块土地上种地为生,农村社区原有的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松动{27},越来越多的村民因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而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注 释: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2}{8}(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3}Fukuyama,Francis.“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Y:Free Press,1996.
{4}Narayan.D.“Bonds and Bridges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67.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5}Woolcock.M.“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 an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s and policy frame work”. Theory and Society,1998,Vol 27.
{6}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7}赵延东:《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9}“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Charleston,South Carolina,February 18-21,1999. Contact the author at nanlin@duke.edu.
{10}Paul Bullen;Jenny Onyx: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An Analysis.CACOM Working Paper Series(No 41),1997.
{11}Kawachi I,Kim D,Coutts A:“Subramanian SV:Commentaryncil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social capit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4,pp.33.
{12}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366页。
{13}{15}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4}姜楠:《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大连市S社区的调查》,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6}林聚任、刘翠霞:《山东农村社会资本调查》,《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17}贾先文:《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求索》2010年第7期。
{18}裴志军:《村域社会资本:界定、维度及测量――基于浙江西部37个村落的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10年第6期。
{19}谢治菊、谭洪波:《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概念、测量与计算》,《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0}Harpham T:“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Kawachil,Subramanian Sv,Danielk”.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Newyork:Springer,2007.
{2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22}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23}齐学红:《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与道德教育改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4}李绍伟、池忠军:《村民自治的功能主义二分法及统合》,《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5}秦广强:《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2003CGSS的实证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