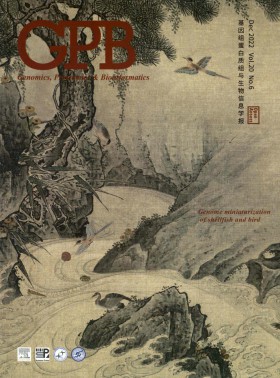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基因组学应用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基因组学应用范文1
1 药物基因组学的发展现状
药物基因组学是建立在药物遗传学基础上发展起 来 的 新 兴 学 科 。 通 过 对 患 者 个 体 基 因 型(genotype)的识别预测药物反应的表型(phenotype),从而达到个性化治疗的目的。而新的疾病基因的发现将会提供新的药物靶点。药物基因组学通过研究影响药物代谢等个体差异的基因特性,以及基因变异所导致的患者对药物的反应,提高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为开发新药、指导合理用药、提高药效、减少不良反应、降低开发成本提供信息平台,进而提高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质量。
2 个体化治疗的意义
任何药物都具备两重性,既能治病,也能致病。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最佳用药剂量对于每个个体也是不同的。由于用药过量带来的不良反应及用药不足导致的疗效欠佳都是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个体化用药是要充分、全面地考虑每个患者的遗传因素(药物代谢基因类型)、身体因素(性别、年龄、体质量)、病情因素(病理生理特征、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等基础上,综合制定全面、安全、合理、有效、经济的药物治疗方案。遵循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原则,予以适当的患者,适当的给药,适当的剂量和适当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效应,减少不良反应及降低医疗费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果显示,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由于不合理用药导致死亡。因而,推行个体化用药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3 药物基因组学与个性化治疗
合理用药的核心是个体化给药,目前最主要的方法是:测定药物的体液浓度,以药代动力学原理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设计个体化给药方案,这对于血药浓度与药效相一致的药物是可行的,但对于血药浓度与药效不一致的药物,如何达到个体化给药,目前并没有比较可靠的方法。
药物效应的差异与基因变异的关系,并不是提出药物基因组学的概念以后才认识到的。一些临床经常出现的现象,引起了临床医学工作者的重视。如两个患者的诊断相同,一般状况相同,同一药物治疗,血药浓度相同,但疗效却相差甚远,用传统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等原理无法解释,这时应考虑到与药物作用相关的靶点(如受体等)是否发生了变异,是什么水平的变异?药物作用位点的变异可能发生在基因水平,也可能发生在转录、翻译等水平,基因水平的变异相对比较容易鉴定,研究也表明基因的变异与药物效应的差异更具相关,研究基因突变与药效关系的药物基因组学正是适应了这样一个要求,因此药物基因组学在临床合理用药中的应用前景是好的。
个体对药物代谢和反应差异的15%~30%是由基因因素决定的,个别药物基因因素的影响高达95%。药物靶标的基因多态性、药物代谢酶类和参与药物代谢酶类调控的核受体基因多态性、转运蛋白和结合蛋白的基因多态性等遗传因素决定了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如奥美拉唑联合阿莫西林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对于基因型为CYP2C19PMS的治愈率为100%,而对于基因型为CYP2C129EMS的治愈率为60%(杂合子),20%(纯合子)。又如,将高血压和正常血压有关的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系统进行分析和比较表明,不同患者的基因组序列是不同的,高血压的发生以及对抗高血压药物的疗效与多种基因表型相关,这些个体差异模型数据将为高血压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药物相关基因的多态性及患者基因的变异是导致个体药物反应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个体基因的差异又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需进行个体化用药。药物基因组学从基因水平诠释了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效应的相关性,能帮助临床人员在进行药物治疗时,根据患者所属反应人群选择疗效最佳的药物和最佳的剂量。如异烟肼、磺胺类药物通过药物乙酰化代谢发挥作用,因此掌握患者是慢乙酰化表型还是快乙酰化表型很重要,若采用相同的剂量则可能产生中毒或药物作用很弱甚至无效。
药物基因组学是从基因组水平出发,研究基因序列的多态性与药物效应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个体遗传基因差异对药物效应的影响。药物基因组学应用到临床合理用药,弥补了以往只根据血药浓度进行个体化给药的不足,也为过去无法解释的药效学现象找到了答案,为临床个体化给药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患者对许多药物的反应性(包括药效反应与药物不良反应)与其基因亚型之间关系已被揭示,这种关系的确定能辅助临床人员在预测某一特定药物时,患者属何种反应人群,使医生为患者选择疗效最佳的药物和确定最佳剂量成为可能。文献表明药物基因组学知识已应用干高血压、哮喘、高血脂、内分泌、肿瘤等药物治疗中。高血压药物的不同药效和高血压患者的耐受性也与遗传变异有关。这种关系能辅助临床人员通过预先检测患者基因类型,帮助医生为患者选择疗效最佳、剂量最佳的药物,即通过对患者的药物相关基因检测,开出基因合适的药方,即基因处方。这种最恰当的药方,可使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从而达到真正用药个体化的目的。
药物基因组学的基因检测对象包括药物代谢酶、药物转运体和药物靶点基因3大类。通过检测以上3类基因的序列及表达变化,可以判断药物的有效性,代谢规律及毒副作用等。
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基因学研究,不需要发现新的基因。影响药物效应的基因经常是通过细胞生物学或生物化学研究已经发现了的基因,还可以使用药物作为探针发现已知基因有意义的功能与药物效应的关系,或者发现与药效相关的有意义基因。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的主要策略包括选择药物起效、活化、排泄等过程相关的候选基因进行研究,鉴定基因序列的变异。这些变异既可以在生化水平进行研究,估计它们在药物作用中的意义,也可以在人群中进行研究,用统计学原理分析基因突变与药效的关系。基因技术的发展已经给鉴定遗传变异对药物作用的影响提供了前提条件。已经有研究开始鉴定一些普通的基因变异,这些基因是药物作用的靶子,或者一些与控制药物作用、分布、排泄相关的基因。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预测患者药物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这种预测试验也可能成为医生在医疗实践中一种常规检查手段,去决定哪种药物对某个患者最有效、最安全,同时可以避免潜在的药物毒副作用,患者可以更快地得到有效的治疗药物处方,治疗将更有效、更经济。药物基因组学需要高效的基因变异检测方法,只花少量的费用就可获得患者某个药物相关基因的变异情况,这样才能有实用价值。最简单的方法是,检查从大量个体扩增出来的某个基因产物,检查是否有插入和缺失的变异,证明变异基因在序列中的位置和理想的特异碱基置换。更有意义的是,那种在一个基因中鉴定多个突变的相对位置,可以为每一个患者提供等位基因的单倍型,新的DNA芯片技术也有可能对药物基因组学有较大的意义。
因此,药物基因组学可以:(1)根据代谢酶、药物作用受体或靶点的基因多态性情况,指导合适的用药剂量。(2)确认具有某些基因特性的患者接受某种药物治疗更容易发生严重不良反应。(3)确认某些基因特性的患者采用某种治疗方案更容易获益,可以指导药物选择和剂量调整以达到最佳疗效。(4)检测病毒耐药性并选择合适的药物。
基因组学应用范文2
细菌遗传学的研究已经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而发生变革,这不仅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多临床和工业上重要细菌的基因信息,也开辟了比较基因组学研究。目前,细菌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加强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并能够引发基因组中不同组成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之间的讨论。这些发展加速了对于定量深度测序技术的广泛应用。同时,通过强大的技术以及细菌进化和适应性的多层面研究能够将比较基因组学与功能基因组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本书还提出了通过基因组学技术检测细菌的适应性,重点阐述了数据分析与诠释。本书中涉及的大部分资料来自本领域最新的重要文献,这也是在前沿及快速增长的细菌研究领域最强有力的工具。
本书共分6章:1.引言:细菌基因组及基因表达;2.在Sanger测序时代的比较基因组学,分别介绍了细菌基因组的组装与诠释过程、个别案例介绍、基因组大小、编码密度、基因顺序的保留等;3.通过微阵列芯片研究细菌基因组变化, 主要由浅入深介绍DNA微阵列芯片技术的原理、应用以及数据的分析,并通过案例分析介绍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4.应用下一代测序技术的细菌基因组学研究,介绍了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原理和数据处理过程,并通过五个细菌基因组测序案例来进行分析;5.细菌基因表达与调控的大规模基因组分析,本章通过介绍基因表达与调控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引入下一代测序技术在基因表达和调控中的作用与应用。同时,也通过七个案例详细描述了此研究目前在细菌基因组中的应用;6.在细菌中的DNA甲基化:一例细菌表观遗传学案例,主要介绍了细菌中的DNA甲基转移酶,在基因组中识别DNA甲基化,以及单细胞实时测序技术在检测DNA甲基化中的应用。
本书详细阐述了目前基因组技术在细菌适应性研究上的应用,提供了详细的宏基因组技术方案和细菌基因表达工具。本书的写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仅列举了大量的研究实例,还囊括了大量清晰的图片和注释,力求既能涵盖全面的细菌基因组学知识,又能反映现阶段基因组学研究的进展。本书既满足各高等学校微生物类、生物类、生物工程类学科本科教学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不同层次和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需要。
马雪征,助理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卫生检疫研究所)
基因组学应用范文3
【关键词】 全基因组扩增;多重置换扩增;肿瘤
1 多重置换扩增原理及特点
多重置换扩增已被证明既可应用于环状DNA模板扩增[4]也可被用于线性DNA模板[1]。多重转换扩增是一种非PCR,等温不需要经过热循环的基因扩增技术。使用独特的Phi 29 DNA聚合酶,对于模板有很强的模板结合能力,能连续扩增100 kb的DNA模板而不从模板上解离,平均片段长度>10 kb[2]。
多重置换扩增具有能直接分离样本和纯化样本均适用[3]、产量高且有长度保证[4]和无位点扩增误差等特点[5],保证了扩增产物的质量。
2 多重置换扩增应用于肿瘤研究及临床应用
多重置换扩增最先被应用于人类全基因组扩增[6],此后被更多地应用于真核细胞的研究,包括基因组测序和人类及灵长类的基因分型[7]、法医学中对低拷贝数DNA检验和混合斑中DNA扩增进行STR分型[8]等。以下将对多重置换扩增的肿瘤研究及临床的最新应用进展作详细说明。
2.1 肿瘤基因组学研究 MDA对于基因组或基因片段的均衡高效扩增用于癌症基因组学研究非常合适。因为为克服癌症细胞异质性,使实验结果准确可靠,常利用显微切割技术特异地选择靶细胞,所以获得的细胞数量有限。利用MDA对其进行扩增,即可得到足量DNA产物,从而满足基因组学高能量分析折需要。目前应用激光捕获显微切割(laser capture Microdissection,LCM)、MDA和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rray-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aCGH)三项技术联合应用于癌症基因组学的研究。如研究前列腺癌的染色体变化,致力于发现早期前列腺癌[10];家族性胰腺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全基因组等位基因的测定[11];国内亦有对于胃癌[12]、贲门癌[13]的杂合性丢失(1oss of heterozygosity,LOH)和抑癌基因的研究。
2.2 肿瘤流行病学研究 多重置换扩增可直接从全血、口腔细胞、组织培养细胞、血沉棕黄层细胞均匀地扩增人类基因组[3],因此可利用简单的样本进行大规模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对于明确肿瘤分型、人群发病情况等流行学特征有意义。如扩增口腔试子细胞DNA研究用于种群的乳腺癌基因分型[14]。
2.3 肿瘤的临床诊断应用 肿瘤基因组学中的LOH和微卫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已经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证实,如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膀胱癌、乳腺癌、结肠癌、恶性黑色素瘤及口腔癌等[9]。目前,分析肿瘤细胞染色体上的LOH情况,已成为检测抑癌基因失活和定位新的抑癌基因的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可成为特异的肿瘤基因标志,进而设计出相应的临床诊断实验。
如扩增分析血清中DNA通过多位点杂合丢失诊断头颈部肿瘤[9];早期前列腺癌的诊断研究[10];对家族性胰腺癌及其癌前病变的诊断及预后研究[11];对临床样本线的粒体DNA进行扩增通过点突变进行癌症的诊断[15]。
3 结论和展望
综上所述,多重置换扩增作为一种高效、完整、均衡的全基因组扩增技术,其在肿瘤学研究和临床的应用潜力已被人们发觉。而MDA本身也一直进行技术改进,如选择MDA和填充片段MDA。通过与其他技术的联合应用,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样本,从而提升肿瘤基因学的研究水平。同时,MDA为肿瘤的初筛实验和早期确诊实验提供了新希望,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但目前利用MDA的临床诊断实验尚不多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Dean FB,Hosono S,Fang L. Comprehensive human genome amplification using multiple displacement am plific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2.99:5261-5266.
[2] Serdar C,Osama A. 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 cation from a single cell: a new era for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renat Diagn,2007,27:297-302.
[3] Hosono S,Faruqi AF, Dean FB. Unbiased whole-genome amplification directly from clinical samples.Genome Res,2003,13:954-964.
[4] Lovisa L, Ann-Christine S. Multiple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To Create a Long-Lasting Source of DNA for Genetic Studies. Hum Mutat,2006,27(7): 603-614.
[5] Roger S L. Single-cell genomic sequencing using Multiple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Microbiology 2007, 10:510-516.
[6] Serdar C,Osama A. 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 from a single cell: a new era for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renat Diagn,2007,27: 297-302.
[7] Erik KB, Roger SL,Josh DN. Something from (almost) nothing:the impact of multiple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microbial ecology. The ISME Journal,2008,2:233-241.
[8] 陈玲,刘超,杨电,等.全基因组扩增技术最新进展及其法医学应用现状.国际遗传学杂志,2007,30(2):123-126.
[9] Daisuke N, Nobuharu Y, Ryo T, et al. Detection of Tumor DNA in Plasma Using 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 Bull Tokyo Dent Coll,2006 47(3): 125-131.
[10] Simon H,Maisa Y,Ben B,et al. The use of 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 to study chromosomal changes in prostate cancer: insights into genome-wide signature ofpreneoplasia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BMC Genomics,2006, 7:65
[11] Tadayoshi A, Noriyoshi F,Kieran B, et al. Genome-Wide Allelotypes of Familial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s and Familial and Sporadic 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s. Clin Cancer Res,2007,13(20):6019-6025.
[12] 吕志,徐岩,满晓辉,等.多重置换扩增结合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技术在胃癌基因组学研究中的应用.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07,24(11):1350-1352.
[13] 满晓辉,徐岩,王振宁,等.贲门癌中染色体8p21-p23杂合性丢失的研究.遗传,2006,28(6):641-645.
基因组学应用范文4
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涉及储多药物,本文仅以以下两类药物的基因组学研究成果来表述基因组学对指导临床用药的意义。
1.1氨基糖苷类药物与耳聋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自1945年问世以来,因其杀菌作用强、抗菌谱较宽且价格低廉而在临床上广为应用,但其致耳聋的毒性反应也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医生。我国有听力残疾2000万人,其中60%~80%为氨基糖苷类药物中毒所致。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致聋可分为两类,一类因接受了毒性剂量而致聋;另一类则与遗传因素相关。国内外学者均证实:线粒体基因第1555位点A-G的均值性点突变和氨基糖苷类诱导的耳聋关系非常密切。[1]即带有线粒体A1555G点突变基因,哪怕是仅接受常规剂量或仅一次接触氨基糖苷类即可致不可逆的听力损失。这类耳聋占全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致聋患者的30%左右。目前,我国已绘制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耳聋基因突变谱,也已开发出针对中国人的耳聋基因芯片检测体系。如能在新生儿出生时或出生后3天内采集脐带血或足跟血筛查聋病易感基因,[2]使易感基因携带者终生避免使用氨基糖苷类药物,则可避免“一针致聋”的悲剧。
1.2抗高血压药物的选择与剂量
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与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烟酒嗜好等)和遗传因素关系密切。目前,临床常用的抗高血压药可分为五类:利尿药、β-受体阻断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断药和钙通道阻滞药,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制定治疗方案主要根据病人的年龄、体重、高血压程度、有无并发症等,凭经验、试验性地选择药物和药物剂量,较少考虑遗传因素,很多高血压病人虽已用药,但并未能取得满意疗效。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发现:抗高血压药物的疗效与药物遗传多态性有密切关系,如能在用药前测定病人的基因类型,有目的地选择药物和药物剂量,既可使疾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也能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
1.2.1β-受体阻断药β-受体阻断药通过降低交感神经功能产生降压作用。影响大部分β-受体阻断药代谢的酶是细胞色素P450酶(CYP)系中的CYP2D6,该酶具有遗传多态性,其基因变异可高度影响CYP2D6的活性。[3]CYP2D6可分为弱代谢型(PM)、中间代谢型(IM)、强代谢型(EM)和超强代谢型(UEM)4种表型。PM的发生是由于CYP2D6基因突变造成酶活性的缺陷,此型患者代谢药物的能力下降,可导致血药浓度过高,易诱发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支气管哮喘、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对此基因型病人,临床用药应减少药量。IM型者属于强代谢者中较弱的一部分,因基因突变导致酶活性略微降低,此类病人用药也应适当减少剂量。EM是正常人群的代谢表型,故临床上使用常规治疗剂量有效。UEM则是由于出现CYP2D6的多基因拷贝,使酶蛋白高度表达,导致酶活性的显著增高,此基因型代谢药物能力强,从而使血药浓度降低而达不到治疗效果,故应适当增加药量,[4]或改用其他药物。
药效学机制对β-受体阻断药反应的影响较药动学机制更为重要。体内β-受体的数量和受体对药物敏感性的变化是造成个体对β-受体阻断药反应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5]目前已知β1-受体存在两种突变,一种位于受体蛋白N端49位,由甘氨酸取代丝氨酸(Ser49Gly),另一种位于C端389位,由甘氨酸取代精氨酸(Arg389Gly)。研究表明:突变型纯合子(Gly49及Gly389)对β-受体阻断药反应都不及野生型。[4]也就是说,由于基因突变,导致患者对β-受体阻断药的敏感性下降;另一方面,遗传背景不同的种族对β-受体阻断药或激动药的敏感性也存在着差异,[5]这些差异都影响到β-受体阻断药临床应用时的剂量选择。
1.2.2噻嗪类利尿药噻嗪类利尿药是最常用
的基础降压药物,其降压原理是促进钠水排出,减少有效血容量,并扩张外周血管使血压下降。与噻嗪类利尿药降压作用个体差异相关的基因有:α-内收蛋白(α-adducin)、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基因、G蛋白基因、编码WNK酶的基因,此外,NO酶、E298D突变也与噻嗪类利尿药的降压效果有关。[4]
目前发现α-Adducin具功能意义的突变为G460T,大量的研究表明,含至少1个460T突变基因的患者使用利尿药的近期效应是血压(包括平均动脉压)下降幅度更大,而远期效应则表现为相对其他降压药物而言更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风的发生率。[4]国内有学者[6]报道:ACE基因I/D多态性和氢氯噻嗪的降压作用密切相关,但目前研究结果还不太一致。有报道说:对同时携带ACE的I型等位基因及adducin的Trp460等位基因的患者氢氯噻嗪的疗效最好,而携带ACE的D/D等位基因及adducin的Gly/Trp等位基因的患者用氢氯噻嗪治疗后血压下降最少,[7]所以临床用药时如能联合分析ACE和α-adducin两方面的基因多态性,则有助于预测利尿剂的疗效。
1.2.3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ACEI的降压作用主要通过抑制周围和组织中的ACE,使血管紧张素II生成减少,同时抑制缓激肽酶使缓激肽降解减少,而达到降压目的。ACEI与基因多态性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RAAS,多态位点包括ACE基因I/D、AGT基因M235T和血管紧张素II-I型受体(AT1R)基因A1166C。[8]其中研究最广泛的是ACE基因I/D多态性,用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赖诺普利和培垛普利研究ACEI抗高血压的疗效,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说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对ACEI类药物反应的差异部分由遗传因素决定。有人发现AT1基因多态性(A1166C)与ACEI类药物的降压疗效相关,且此相关性在老年患者和超体重患者中尤为明显。[7]
1.2.4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药沙坦类降压药主要通过阻滞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产生降压作用。沙坦类药物在体内主要依靠CYP2C9代谢,该基因突变使酶活性明显下降,毒性增加,疗效降低。另外,CYP11B2的多态性被证实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药的降压效果相关,该基因突变引起机体对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药敏感性增加,表现为收缩压下降较无突变型明显。[4]
1.2.5钙通道阻滞药(CCI)钙通道阻滞药是近30年来广泛应用于临床的一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通过阻滞钙离子L通道,抑制血管平滑肌及心肌钙离子内流,从而使血管平滑肌松弛心肌收缩力降低,使血压下降。钙通道阻滞药在体内的代谢主要依靠CYP3A,该基因突变可引起CYP3A酶活性下降,可导致体内血药浓度增加,药物的毒性也相应增加,故应适当减少药物的用量。[4]
2药物基因组学的概念
药物基因组学是基因功能学与分子药理学的有机结合,是研究基因序列变异及其药物不同反应的科学,以药物效应及安全性为目标,运用已知的基因理论研究各种基因突变与药效及安全性的关系,药物基因组学强调个体化;通过它可为患者或者特定人群寻找合适的药物及恰当的剂量,改善病人的治疗效果。
3展望
药物基因组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药物代谢、转运和药理作用的基因多态性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在有些药物上有重大突破,如氨基糖苷类的耳聋问题,但更多的药物研究还都处在起步阶段,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病理、药理机制研究的深入、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方法及新技术的不断的完善,以及个体化用药基因芯片的研发,不久的将来,很多药物都可以实现以基因为导向、“量体裁衣”式的个体化用药治疗模式,使临床用药更具针对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实现治疗学上按基因选药的个体化用药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戴朴.聋病的临床基因诊断[OL]./content/200700003713/02/.
[2]王秋菊.新生儿听力筛查期待基因检测加盟[N].健康报,2009-08-07.
[3]樊晓寒,惠汝太.β受体阻滞剂药物基因组学研究进展[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6.34(10)947-950.
[4]唐强,刘海玲,刘昭前.抗高血压药物的基因组学研究进展[J].中南药学,2007.5(2)157-160.
[5]刘洁,周宏灏.遗传药理学个体化用药的科学依据[J].中国处方药,2007.(50):32-33.
[6]吴寿岭,李云,刘克俭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和醛固酮合成酶基因多态性与氢氯噻嗪降压疗效的关系[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5,33:595-598.
[7]李金恒.高血压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与个体化用药[J].中国处方药,2006.5(50)16-18.
[8]占伊扬,姜潇,黄峻等.抗高血压药物遗传学研究进展[J].中国全科医学,2007.10(4)329-331.
摘要:目的介绍药物基因组学对临床个体化用药的指导作用。方法阅读并分析近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药物基因组学的相关文章,对药物基因组学在指导临床个体化用药方面的作用加以归纳、总结。结果及讨论药物基因组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药物代谢、转运和药理作用的基因多态性研究方面有很大的进展,有些药物有重大突破,如预防氨基糖苷类的耳聋问题,但更多的药物研究还都处在起步阶段,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方法及新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个体化用药基因芯片的研发,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治疗学上按基因选药的个体化用药医疗模式。
基因组学应用范文5
关键词 药物;微生物;放线菌;基因组学;研究;研发
中图分类号 Q939.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21-0284-02
在临床药物学研发中,针对中药、化学药物及生物技术药物研究较多,而微生物药物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随着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研究的增多,有关微生物新药的开发也越来越多,而且微生物药物还具有条件温和、易工业化生产及污染小等优点,加强微生物类药物研究和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1 微生物药物的发展历程
人类认识微生物的历史悠久,但研究微生物药物的历史并不长,尤其是对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方面的药物研究历史更短,至今不过70年。微生物药物中的青霉素是由英国的细菌学家在1929年发现的,20世纪40年代初学者Chain与Florey将青霉素应用到了临床治疗中。随后,从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中发现了庆大霉素、红霉素、螺旋霉素及林可霉素等药物。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人们对疾病分子基础与药物作用机制越来越了解,还能在体外构建各类药物筛选的模型,极大地提升了微生物药物研制。微生物所筛选的生理活性物质中,除了抗生素外,在抗肿瘤用药、免疫抑制剂及酶抑制剂等领域也具有很大的药物开发价值。在近70年的微生物药物研究中,科学家从土壤、动物、植物、海洋中获取微生物,还有些微生物来自高寒、高温及高压等极端环境,而人类对微生物的了解仍然较少,还不到3%,在微生物代谢的产物当中,还存在着大量待开发的药物,需要人们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2 微生物药物的特点
微生物药物是指微生物在生命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生理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及其衍生物。近些年,随着其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生理活性的研究,微生物中靶位确切的多糖及蛋白分子等活性物质被发现[1-2]。次级代谢产物难以用化学法进行合成,即使能合成也无法有效实现工业生产,若把小分子的物质进行化学修饰之后,可获得含有使用价值更高的微生物药物。与化学药物相比,微生物药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微生物的生长周期较短,易选育菌种,易控制,可经大规模发酵进行工业化生产;二是微生物的来源非常丰富,筛选时不用特别考虑先导化合物,筛选几率也比较大;三是通过微生物药物合成改造,微生物药物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便于新微生物药物合成。微生物多样性使得临床医药的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3 微生物药物资源的研究
3.1 海洋微生物药物
在整个地球,面积最大的是海洋,海洋具有高压、高盐、高温及无阳光等自然特点。海洋中的微生物具有较特殊的遗传背景与代谢方式,可能产生功能及结构特殊的活性物质[3]。研究表明,海洋微生物中,近27%可产生抗菌类的活性物质,其分离出的代谢产物大多数含有生物活性。例如,Koyama等学者从海洋真菌中获得了新二萜药物。当前,从海洋微生物代谢产物当中,发现了很多结构特殊、新颖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在陆地微生物中未发现过,因此海洋微生物药物是非常具有开发潜能的天然药物。
3.2 稀有放线菌微生物药物
多数活性物质源于普通的放线菌,但从普通放线菌当中获取新的活性物质几率下降,研究范围逐步拓展至稀有放线菌中。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些稀有放线菌的代谢产物已应用到临床中,例如,庆大霉素、红霉素与安莎类等物质。目前,人类认知的放线菌种类不到实际种类的10%,放线菌微生物药物的研发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3.3 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药物
在高温、高酸、高盐及严寒等极端环境下,长期生长的微生物,其生理机制及基因类型均较为独特,代谢产物也比较特殊。现代所知的微生物药物资源种类占实际种类资源不到10%,而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更少,在极端环境中,更能发现未知的微生物药物资源。如近些年云南大学对青海及新疆等地区中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获得了很多未知微生物,有效推进了微生物药物的研究和开发。
4 基因组学研究下的微生物药物开发
随着人类和微生物基因组学的深入研究,近5 000种蛋白或功能基因被认成潜在药物的靶标,这给微生物药物筛选及发现打下了基础,其药物靶标和基因组学研究发展紧密相关。根据统计可知,在2009年之前,整个世界有2 500余种病毒,其中,完成基因测序的真菌有100余种,细菌约600种。随着微生物基因组学计划和蛋白基因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建起了相应的蛋白质数据库,对一些重大疾病的蛋白质结构进行了系统测定,剖析了蛋白质三维结构,并发现了一些具有药物作用的靶标[1]。从病原微生物看,功能性基因组的研究为致病基因及必需基因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一般性病毒,整个基因组能编码约10个蛋白基因,而功能蛋白中4~6个是药物靶标。从细菌方面看,细菌基因组要比病毒基因多,细菌基因组多在4 Mbp左右,编码蛋白基因约数千个,独特必需基因有数百个,为潜在药物的靶标奠定了基础,对于真菌来说,有些致病真菌基因组已完全测序出来,因此具有真菌生长的基因为人类非同源基因预测提供了可能性,如假丝酵母基因组的序列当中,就发现了200余个基因,但人的基因组当中有些没有同源性,运用其潜在靶标可寻找到药物的靶点[4-5]。
5 我国微生物药物研发思考与展望
随着我国生命科技不断发展,医学领域对微生物资源越来越重视,微生物药物研发不断增多,其药物靶点不断被发现,在现代化学实体当中,超过10%为微生物药物,并且属于新衍生物研发。我国微生物资源非常丰富,但对微生物认识有限,尤其是海洋、植物及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研究较少,运用基因组学技术获取微生物衍生物中的药物,这已成为微生物新药获得的重要方式[6-8]。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在微生物药物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政府部门也应给予重视与支持,加强我国微生物药物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为人类的生命安全做出贡献。
6 参考文献
[1] 朱宝泉,胡海峰.微生物药物研究中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J].中国天然药物,2004,11(4):3-8.
[2] 武临专,洪斌.微生物药物合成生物学研究进展[J].药学学报,2013,6(2):155-160.
[3] 王霞.海洋微生物药物研究进展[J].天津化工,2012,4(4):4-6.
[4] 陶阿丽,苏诚,余大群,等.微生物制药研究进展与展望[J].广州化工,2012,40(16):17-19.
[5] 刘飞,伍晓丽.生物技术在微生物药物研究中的应用[J].重庆中草药研究,2007(1):38-40.
[6] 陆茂林,司飞.微生物新药创制的思路与方法[J].中国天然药物,2006(3):17-20.
基因组学应用范文6
[关键词] 中药; 体内代谢; 中药基因组学; 肠道宏基因组学; 个体化医疗
Genomic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 vivo metabolism
XIAO Shuiming1*, BAI Rui2, ZHANG Xiaoyan3
(1.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College of Pharmacy and Chemistry,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
3.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Gene is the base of in vivo metabolism and effectivenes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 and the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and modification are used as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to perform the TCM multicomponent, multilink and multitarget in vivo metabolism studies, which will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TCM metabolic proecess, effect target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Humans are superorganisms with 1% genes inherited from parents and 99% genes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mainly coming from the microorganisms in intestinal flora. These indicate that genetically inherited human genome and "second genome" could affect the TCM in vivo metabolism from inheritance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respectively. In the present paper, typical case study was used to discuss related TCM in vivo metabolic genomics research, mainly including TCM genomics research and gut metagenomics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personalized medicine evoked from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above genomics (metagenomic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TCM); in vivo metabolism; TCM genomics; gut metagenomics; personalized medicine
doi:10.4268/cjcmm20162204
中药体内代谢研究是阐明中药作用机制的重要途径,也一直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难点。虽然同是用于疾病治疗的药效物质,中药是与化学药物迥然有别的复杂生物体系,它作用于人体时响应的是多维非线性的复杂效应[1]。很多中药的疗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已经得到证实,但进入体内发挥药效的化学成分及其体内过程并不清楚。研究中药体内代谢可以了解中药在体内的代谢途径、存在形式、影响因素以及药效物质基础。中药体内代谢及药效发挥的基本环节是药物分子与机体生物分子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引起从遗传信息到整体功能实现中的多个层面的结构与功能状态的改变,而决定这些层面的结构与功能的基础是基因。因此,以基因表达、调控及修饰为研究方向,进行中药多组分、多环节、多靶点的体内研究,可能有助于阐明中药体内代谢过程、作用靶点和分子机制[2]。同时,人作为一个超级生物体,只有1%的基因遗传自父母,其余99%的基因都来自分布人体各部位的微生物,其中肠道是微生物定植数目最高的器官[34]。因而,肠道微生物基因组被誉为“人类的第二个基因组(our other genome)”[5]。
近年来,基于“基因组学”的技术在中药体内代谢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将以典型研究案例为线索,探讨中药体内代谢基因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基因组学和肠道宏基因组学研究。
1 中药基因组研究
王升启[6]于2000年提出了中药基因组学(TCM genomics)的概念,即以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s)理论为基础,将中药的药性、功能及主治与其在人体内代谢/疾病相关基因表达调控相关联,在分子水平研究中药在人体基因组介导下的代谢转化、作用靶点、毒副反应、药效机制和中药整体化作用的规律。中药基因组学的核心内容是应用基因组信息和方法在人类基因组水平研究中药体内代谢和反应的遗传学本质。陈士林等[7]关于中药基因组学的理解,则侧重于中药本身,主要包括中药转录组学、结构基因组学、基因组标记解析和功能基因组学等,属于本草基因组学(herbgenomics)的研究范畴[8],旨在通过对中药原物种遗传信息的揭示,解析重要活性产物的生物合成途径,发掘参与生物合成的功能基因,推动对中药合成生物学、基因组辅助分子鉴定和分子育种及中药道地性遗传机制阐释的深入研究。
药物基因组学是基于药物反应的遗传多态性提出来的,表现为药物代谢酶、受体和靶标的多态性等。这些多态性的存在可能导致许多药物治疗中药效和不良反应的个体差异,这种情况在中药体内代谢过程中将更为复杂。传统中药以口服用药为主,中药成分在体内发生代谢的部位主要有胃肠道、肝脏、肾脏和肺等组织器官,其中肠道和肝脏是多数药物的主要代谢器官。除中药原型成分外,还可能有大量代谢产物的存在,其中的药效成分作用于受体、酶、离子通道等靶点,最终产生药效。中药体内的反应和代谢涉及多基因的相互作用,基因多态性导致药物体内代谢反应多样性,从而为从基因组水平研究中药体内代谢和药物反应奠定了基础。相比于遗传药理学(pharmacogenectics)着重于药物在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效应动力学方面单个或少量基因的研究,中药基因组学的研究范畴更广,包括全基因组上决定中药药物效应的所有基因,系统性地评价基因的相互作用及其如何影响疾病的易感性、药理学功能、药物处置和治疗反应,并以此为平台指导中药新药的开发及合理用药。
遗传药理学是药物基因组学的一种雏形,它从单基因的角度研究遗传因素对药物代谢和药物反应的影响,特别是遗传因素引起的异常药物反应。总体而言,个体对药物代谢和反应差异的15%~30%是由基因因素决定的,个别药物基因因素的影响可以占到95%[9]。中药基因组学目前主要关注中药作用机制、毒副作用、有效成分和药物靶点等研究[10],进一步从表型到基因型的中药反应个体多样性研究相对较少。Lee等[11]发现由芍药根诱导的肝细胞凋亡早期其BNIP3基因表达上调,而ZKl,RAD23B及HSPDl基因表达下调,提示芍药根抗肿瘤活性的机制可能与促进细胞凋亡相关;Watanabe等[12]通过观察服用银杏叶提取物(GBE)小鼠皮层及海马组织的基因表达变化,发现皮层内微管相关蛋白、钙离子通道及催乳素等多种与脑功能相关的基因表达的上调,而海马组织内则仅有甲状腺转运蛋白上调,表明GBE可能通过对淀粉样蛋白清除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Zhang等[1314]构建了栀子苷治疗缺血性模型大鼠的基因表达谱芯片,结果表明栀子苷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脑组织基因表达具有调控作用,从分子水平阐述了中药清开灵注射液成分栀子苷的药理作用机制;张立平等[15]筛选肝肾阴虚型晚期结直肠癌(CRC)患者使用六味地黄颗粒前后的显著差异表达的基因,干预后129个差异基因,其中128个上调,1个下调。基因功能(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前后共254个基因GO存在显著差异。在生物过程中,凝血功能相关的基因占41.5%;在细胞组成中,45.5%的差异基因与细胞质膜有关;在分子功能方面,64.9%的差异基因与结合有关。上述结果表明六味地黄颗粒可增强患者凝血功能,增加钙离子结合。
此外,随着中西药联用在我国临床上日趋广泛的应用,中药通过影响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基因表达和功能改变其底物药物的血药浓度,可能导致临床上药物毒副反应或治疗失败的发生,产生有重要临床意义的中药药物相互作用。高立臣等[16]对药物代谢相关基因介导的中药药物相互作用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Wang等[17]发现贯叶连翘Hypericum perforatum诱导细胞色素CYP2C19对奥美拉唑的羟化活性和CYP3A4对奥美拉唑的磺化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CYP2C19和CYP3A4基因型依赖性;同时贯叶连翘可诱导CYP2C9对降糖药格列齐特的代谢活性,但这种影响不具有CYP2C9基因型依赖性。
下列3个案例分别从青蒿琥酯抗肿瘤效应,莨菪亭抗药性以及银杏叶提取物对药物代谢酶CYP的影响以及对其他药物药效学的影响等方面,对中药基因组相关研究展开介绍。
1.1 青蒿琥酯抗肿瘤的作用机制研究 研发新的药物及治疗策略以克服肿瘤药物抗性是目前临床肿瘤学最紧迫的任务之一。Sertel等[18]在过去几十年里,系统分析了中药里的药用植物中具有对肿瘤细胞毒性活性的次级植物代谢产物。在诸多的天然产物中,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artesunate,ART)表现出明显的体内外抗肿瘤活性[19],但其抗肿瘤的分子机制并不明确。Sertel等[20]采用了基因芯片技术,在转录水平解析青蒿琥酯抗肿瘤机制相关的基因。再将表达谱数据导入信号通路分析和转录因子分析,结果表明cMyc/Max可能是作为肿瘤细胞应对青蒿琥酯效应基因的转录调控因子。
在确定青蒿琥酯对具有顺铂(cisplatin)、阿霉素(adriamycin)和紫杉醇(paclitaxel)抗性的卵巢癌细胞的细胞毒性后,采用基于基因芯片的转录组mRNA表达谱和COMPARE分析的基因捕获技术,鉴定出一系列表达量与ART高/低半抑制浓度(IC50)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涉及的生物学功能包括核糖体结构组成(RPL29),ATP结合级联转运(ABCC3),激酶(PRKCSH, ITPK1, IKBKG, DDR2),细胞抗氧化防御和致癌性(ATOX1),肌动蛋白细胞骨架(RRAS),致癌性(SMAD3, WNT7A),细胞黏附及恶性细胞增殖(ST8SIA1),细胞增殖与凋亡(CSE1L),细胞循环、分化(S100A10)和转移(HMGA1, RPSA)等,上述可能是肿瘤细胞应对ART的抗性或增敏因子作用途径。针对信号传导的通路分析表明,ART处理与肿瘤坏死因子(TNF)和肿瘤抑制因子p53信号通路相关,其网络结构涉及细胞形态、抗原呈递和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相关(图1 A),以及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细胞组装和架构(图1 B)。
另一方面,实验结果也发现与ART作用后细胞应激无明显功能相关性的基因,如耳蜗内外毛细胞相关基因。Sertel等认为ART影响转录因子活性,进而调节涉及肿瘤细胞应对ART的下游基因的表达。在之前的研究中,作者发现cMyc的表达量与ART药物敏感性相关[21],表明cMyc转录调节在介导ART细胞毒性效应中可能起作用。通过ConSite检测转录因子结合位点,56个基因中,大部分分别具有1~12个潜在的cMyc结合位点;只有3个基因启动子不具有cMyc结合位点,这提示cMyc可能是ART细胞反应重要的转录调节因子。Max基因作为cMyc二聚体伴侣分子,作者以关联分析验证了cMyc/Max的mRNA表达量与ART作用于细胞株的IC50的关联性。
综上,cMyc/Max介导的基因表达转录调控,可能有助于提高ART对癌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以及对肿瘤的治疗效果,同样也避免因为疗效无关基因表达差异导致的不必要的毒副作用。
1.2 莨菪亭在肿瘤细胞中的抗药性研究 抗药性和不良/副反应是抗肿瘤药物新药研发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莨菪亭(scopoletin),来自艾属植物以其他植物的香豆素类化合物,其化学名为6羟基7甲氧基香豆素。香豆素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如抗炎、抗菌、扩张血管、抗凝血、抗血栓、退热、镇静等,特别是抗肿瘤及防治尿酸血症方面活性,已引起广泛的关注。戴岳等[22]发现东莨菪素具有抑制体内外血管生成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这一环节起效。此外莨菪亭可引起细胞膜完整性缺失和细胞凋亡,具有细胞毒性作用,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23]。上述结果表明,莨菪亭是一个潜在的用于癌症治疗的抗肿瘤化合物。
Seo等[24]采用基于NCI细胞系的基因芯片RNA表达谱技术探究莨菪亭在肿瘤细胞中的药物基因组学反应。结果表明,细胞对于莨菪亭的反应与经典药物抗性机制(ABCB1,ABCB5,ABCC1和ABCG2)的ATP结合盒(ATPbinding cassette, ABC)转运蛋白的表达并不相关。同样不相关的还包括致癌基因EGFR的表达和抑癌基因TP53的突变状态。然而,致癌基因RAS的突变和以细胞倍增时间表征的增殖活性与莨菪亭抗性显著相关。基于转录组水平的mRNA表达数据经COMPARE和等级聚类分析鉴定出一组40个基因(图2),这些基因在其启动子序列上均有转录因子NFκB的结合基序(binding motifs),而NFκB已知和药物抗性相关。致癌基因RAS突变,低增殖活性和NFκB的表达可能妨碍了莨菪亭的药效。基于计算机模拟的分子对接研究发现莨菪亭与NFκB及其调控子IκB相结合。莨菪亭激活SEAP驱动的NFκB报告细胞株中的NFκB基因,提示NFκB可能是莨菪亭抗性因素之一。
综上,因其良好的抗肿瘤细胞活性,莨菪亭将成为肿瘤药物研发的关键化合物,哪怕NFκB信号通路的活化可能成为其抗性因素。目前需要更多的证据以探究莨菪亭的治疗潜力。
1.3 银杏提取物对不同CYP基因型的代谢影响 银杏叶提取物(Ginkgo biloba extract)含有160多种成分,主要为黄酮苷、萜内酯和有机酸等,具有调节血管、增强认知力、缓解压力等药理作用[25]。随着银杏制剂的广泛应用,与其他药物合用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研究银杏叶提取物对药物代谢酶的影响以及对其他药物药效学的影响在临床应用中具有实践意义。中药对细胞色素P450酶(cytochrome P450, CYP450)及其药物转运体的诱导和抑制是介导中草药药物相互作用和产生药物临床毒副反应的主要机制。中草药能够通过影响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基因表达和功能改变其底物药物的血药浓度,可能导致临床上药物毒副反应或治疗失败的发生,产生有重要临床意义的中草药药物相互作用[16]。CYP2C19是CYP450酶第二亚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对药物的Ι相代谢反应起着关键性作用,而研究表明银杏叶提取物引起具有显著的诱导CYP2C19活性效应[26]。
Yin等[27]研究了不同CYP2C19基因型个体服用银杏叶提取物片剂与奥美拉唑(omeprazole,广泛使用的CYP2C19底物,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等)后潜在的中草药药物互作关系。18位经过CYP2C19基因分型的健康志愿者纳入研究。在基线和为期12 d的银杏用药(140 mg)后分别服用奥美拉唑(40 mg),采集服用奥美拉唑12 h血样和24 h尿样。HPLC测定血样与尿样中奥美拉唑及其代谢物浓度,包括5羟基奥美拉唑和奥美拉唑砜,并计算非房室药代动力学参数。
相比于基线水平,服用银杏后,奥美拉唑和奥美拉唑砜血药浓度显著降低,3种CYP2C19基因型[纯合子强代谢型(HomoEM),杂合子强代谢型(HetEM)和弱代谢型(PM)]的奥美拉唑AUC0∞平均下降41.5%,27.2%,40.4%。相应地,奥美拉唑砜下降41.2%,36.0%,36.0%,两者AUC0∞无显著变化。同时,AUCOPZ和AUCOPZSUL在服用银杏提取物前后均显著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rs=0.88,P
2 肠道宏基因组研究
然而,遗传多态性无法单独解释相同剂量的同种药物在遗传背景一致的实验动物中不同的药代学和毒理学反应[28]。除遗传外,年龄、疾病、营养状况、生活习惯、肠道菌群均可能影响或参与药物体内代谢[2931]。正常成年人肠道内1×1013~1×1014个细菌,约1 000种不同种类,编码基因数为人体基因的100倍以上[3233]。肠道菌群基因组总和,即肠道宏基因组(gut microbiome)提供了宿主自身不具备的酶和生化代谢途径,参与外源异生物质的体内代谢,使肠道成为药物转化独特而重要的场所[28]。而肠道宏基因组学(gut metagenomics)利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借助高通量测序并结合生物信息学方法绕过纯培养技术研究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及功能,发掘微生物多样性结构和功能基因组、寻找新基因及其产物[34]。
中药进入消化道后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以原型形式被宿主直接吸收;经肠道细菌和/或内源性酶生物转化后以代谢物形式吸收;调节肠内微生态结构;作为废物随粪便直接排出体外[35]。不同类型细菌产生不同代谢酶,催化包括水解、还原、合成、杂环裂解和C葡萄糖苷CC裂解等不同的药物代谢反应,因此肠道菌群被视为药物肝脏代谢的补充或拮抗[36]。约60%的药物反应与肠道菌群相关:肠道菌群与宿主肝脏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通过直接生物转化或间接调节宿主药物吸收与代谢酶活性影响药物疗效与毒性(图3)[37]。中药大多数为口服药物,少则几十多则上千种的化学成分在进入体内后既有互相促进也会有拮抗作用,其在体内的药效活性成分既可能是原型成分也可能是代谢产物。通常认为,药物必须吸收入血,分布到靶器官,而且在相应的靶器官处在一定时间段内维持一定的浓度水平才可能发挥药效作用。然而很多中药成分难以被人体直接吸收,进入胃肠道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进行生物转化或者调节肠道菌群结构与功能,从而影响甚至决定中药的疗效与毒性(图4)[38]。
因此,Nicholson等人提出“系统生物学”(global systems biology)概念,将肠道菌群的代谢作用纳入宿主整体代谢系统,视宿主、肠道菌群和其他环境因素为一个整体,通过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方法等来阐明药物或其他异源性物质在体内的代谢过程[41],发现能够反映宿主遗传、代谢和环境因素变化的生物信息(标记物)谱系(bioinformatics profile)对患者分类并为其提供个性医疗服务。
肠道菌群作为“内化”了的环境因素,提供人体本身不具备的酶和生化代谢途径,催化包括中药在内的异源生物质体内代谢反应,因此肠道菌群被视为药物肝脏代谢的重要补充或拮抗,而人体全身的整体代谢,包括药物代谢实际上是其体内自身的基因组和其肠道内共生的微生物组活动的整合[42]。一方面,肠道菌群可以作为天然的生物转化器,影响中药疗效的发挥与毒性的改变。黄芩、葛根和豆豉中所含的黄芩苷、葛根素、异黄酮苷普遍存在于中药方剂和营养品中,体外研究表明,葛根素和异黄酮苷能被肠道菌群代谢为比前体物更加有效的大豆黄素和毛蕊异黄酮[43]。黄芩苷在肠道内难以被直接吸收,只有被肠道菌群水解为黄芩素后才能被吸收入血液而发挥作用,而口服黄芩苷的无菌小鼠与常规小鼠相比,肠道内的黄芩苷则几乎没有被代谢[44]。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人参皂苷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体外实验中人参皂苷的原始成分的生物活性很低,在血浆中的浓度未能达到药效浓度[45];其在肝脏内基本不被代谢,主要是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降解。研究表明,肠道中的双歧杆菌、拟杆菌、梭菌等能够代谢人参皂苷[46]。另一方面,肠道菌群还可以作为中医药的作用靶点,实现中医药对机体多靶点的治疗作用[42]。含有多糖成分的补益类中药对益生微生物和致病微生物均具有扶植效应,但对益生微生物的扶植效果明显优于致病微生物。因此,长势良好的益生微生物所产的代谢产物又间接抑制了致病微生物的生长[47]。例如,党参多糖在体外可促进双歧杆菌的生长,从而增加乙酸的代谢,增强双歧杆菌的定植抗力[48]。用党参、茯苓、白术等补气类中药制成的复方合剂灌服小鼠发现,与灌服前比较,乳杆菌、双歧杆菌数量明显增加,肠球菌数量明显减少[49]。此外中药含有的黄酮类、萜类、蒽醌类、生物碱类、甾体类等生物活性成分,以及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对肠道微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能直接或间接地调节肠道菌群失调。
作为了解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与代谢功能金标准的测序技术,在近几年来,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如454焦磷酸测序和illumina测序)朝着快速、高通量、低成本方向迅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宏基因组学的研究。宏基因组(metagenome)是指一个微生物群落内所有成员的基因组的总和[50]。宏基因组学是一种不需要分离培养微生物而直接发现和利用其基因的新的技术策略,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解析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组成,挖掘更多未知的功能基因和功能菌。研究策略上,全微生物组关联分析(microbi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MiWAS)通过对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与中药体内代谢/生理病理指征的变化进行全局性相关性分析。MiWAS策略已广泛应用于解析肠道菌群在代谢性疾病,如肥胖、2型糖尿病等中的作用研究[51],在菌群参与中药有效成分体内生物转化和代谢活性方面将是有益的借鉴。肠道菌群的结构变化用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对进化标记16S rRNA基因进行测序或者全微生物组的测序(宏基因组)来测量。中药体内代谢指征的变化以血液/尿液原型和代谢物含量、体外代谢活性和代谢酶活等来表征,辅以疾病相关生理指标。多元统计学方法(主成分分析PCA、冗余分析RDA、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PLSDA和UniFrac等)以对肠道菌群种类组成、功能基因/通路组成和中药体内代谢的变化进行关联分析。
下列案例将从中药口服进入体内后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即肠道菌群参与中药体内代谢和中药成分对菌群结构与功能调节方面展开论述。
2.1 肠道菌群代谢增强人参皂苷体内吸收 人参皂苷具有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抗疲劳、抗衰老、降血糖和保护心血管/中枢神经系统等药理作用。然而,人参皂苷口服后其原型药在肠道中的吸收程度低,如人参皂苷Rb1的吸收率仅约为1.0%,Rb2为3.4%,Rg1为1.9%,血药浓度难以达到充分发挥药理活性所需浓度[52]。口服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同样广泛存在于其他皂苷类、黄酮类(如大豆黄酮)、异黄酮类(如葛根素)、生物碱类(如小檗碱)和单萜类(如芍药苷)等中药有效成分中,成为制约相关中药制剂发展和临床应用的瓶颈问题[53]。作为“天然活性前体”的人参皂苷在肠道菌群分泌的各类糖苷酶(如β葡萄糖苷酶、α阿拉伯糖苷酶等)作用下逐级水解脱去糖基,转化成为药理作用更强的少糖基皂苷或苷元后吸收率大大增加,且体内分布广泛,在肝脏被酯化后发挥更长久、强劲的药效[54]。目前,人参皂苷Rbl的代谢途径研究较为清楚,即在C20,C3和C3位顺次水解1分子葡萄糖,依次生成人参皂苷Rd、人参皂苷F2,最终形成人参皂苷化合物K(compound K, CK),该化合物也是其他原人参二醇型皂苷在肠道内的主要代谢产物[45]。体外实验证实该过程由肠道细菌分泌的βD葡萄糖苷酶阶梯式地断开糖苷连接完成,Prevotella oris,Eubacterium A44,Bifidobacterium K506,Bacteroides JY6和Fusobacterium K60等肠道微生物协同参与了人参皂苷Rb1的代谢[55]。通过连续过度疲劳和急性冷应激(suffering successive overfatigue and acute cold stress, OACS)建立肠道菌群失调Qi缺陷型的小鼠模型,Zhou等[56]研究了人参多糖对人参皂苷肠代谢和吸收的影响,以及肠道菌群作为中介的作用机制。
HPGPC发现人参多糖具有1.00~1 308.98 kDa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并鉴定出11种主要的皂苷成分,包括人参皂苷Re,Rg1,Rf,Rb1,20(S)Rg2,Rc,Rb2,Rd,F2,20(S)Rg3和CK等。结果表明,人参多糖可有效调节色氨酸、苯丙氨酸、溶血卵磷脂、胆酸、硫酸甲酚、氧化三甲胺(TMAO)、异柠檬酸和4甲基苯酚等内源性代谢物,改善OACS诱导的内源性代谢失调。对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门水平上逆转OACS导致的菌群失调,增加厚壁菌门和减少拟杆菌门相对丰度。PCoA结果进一步证实:人参多糖,低聚果糖和空白组的聚集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模型组与之分离;与模型组相比,给予人参多糖或低聚果糖的小鼠体内拟杆菌属和乳杆菌属丰度增加(具有明显差异P
独参汤中的多糖成分使失衡的肠道菌群得以恢复,菌群的作用促进汤剂中人参皂苷的溶出与吸收。中药中的多糖成分一直以来被轻视甚至被忽视,现代工业化的中药制剂生产中将多糖作为杂质去除以达到符合要求的纯度;对中药汤剂的科学研究中也把多糖从主要的化学成分中排除。该研究有助于改变这种偏离传统中药的使用方法,也缺乏科学证据的做法,通过研究多糖和药效成分的协同作用,为中药汤剂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使用提供指导。
2.2 肠道菌群介导灵芝提取物的减重效应 在我国,灵芝的使用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大量药理研究表明,灵芝具有调节免疫、保肝、抗肿瘤、抗衰老、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等活性[57]。灵芝的化学成分复杂,从该属真菌中已分离得到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核苷、氨基酸、甾醇、生物碱等多种成分。其中灵芝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可抑制糖尿病小鼠的脂肪细胞分化及降低血糖[58];而蛋白聚糖则表现出抗血脂、抗氧化等活性[59]。血糖血脂代谢紊乱的核心,即肥胖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促进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癌症等并发症的发生。研究已经证明肥胖的发生常伴随慢性低度炎症以及肠道菌群生态紊乱,因此如何改善炎症,恢复肠道生态平衡成为肥胖研究的重要课题。
Chang等[60]向高脂饮食饲养诱导的肥胖小鼠食物中添加灵芝的水提取物(WEGL),发现肥胖小鼠表现出体重下降/脂肪积累减少(体重、附睾脂肪垫和皮下脂肪垫),炎症改善(TNFα,IL1β,IL6,IL10和PAI1),胰岛素敏感性增加等获益表型。PCoA分析和聚类分析表明高脂饮食和WEGL分别显著改变了健康/肥胖小鼠的菌群结构,WEGL降低由高脂肪饮食诱导的厚壁菌门/拟杆菌门(Firmicutes/Bacteroidetes)的比例升高以及产内毒素的蛋白菌(Proteobacteria)水平。而且通过恢复紧密连接蛋白ZO1和Occludin的表达,并保持肠屏障的完整性,进一步研究发现WEGL降低肥胖小鼠血清内毒素水平及Toll样受体4(TLR4)介导的内毒素体内信号通路,最终减少内毒素血症发生;同时还观察到,将处理过的小鼠粪便移植给其他肥胖的小鼠,可重现由WEGL所造成的减重等有益代谢效应。进一步地,从WEGL分离纯化得到大分子多糖物质(相对分子质量>300),同样表现出抗肥胖以及肠道菌群结构调节作用。
综上,这项研究首次发现灵芝及灵芝多糖具有降低体重和调节肠道生态平衡的作用,可作为预防菌群失衡和肥胖相关的代谢失调的益生元加以应用,同时表明灵芝补品对于肥胖和相关疾病的潜在治疗作用,但还需要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证明在人身上是否也有类似效应。同上一个案例相似地,中药中的多糖成分,人参多糖和灵芝多糖,都表现出对肠道菌群结构平衡的促进以及对相关症状的改善作用。
2.3 肠道菌群参与葛根芩连汤治疗2型糖尿病 肠道菌群通过调节宿主脂肪代谢和诱发代谢性内毒素血症引起慢性炎症等机制参与宿主肥胖、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61]。以中心性肥胖和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的代谢综合征是2型糖尿病(T2DM)、心脑血管疾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的高危因素[62]。中药复方葛根芩连汤(GQD)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由葛根、黄芩、黄连和甘草等组成,是含有小檗碱,并长期用于治疗急性肠炎、细菌性痢疾和肠伤寒等的经典方剂。近年的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研究表明,GQD具有显著的降糖、降血脂的效果,在2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是动物实验或者是开放、无安慰剂对照、样本量较小的临床观察,而且GQD的降糖机制目前也并不清楚。研究表明GQD在改善糖尿病大鼠血糖、血脂代谢的同时,显著调节了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但是,究竟GQD能否调节肠道菌群,以及菌群是否参与了GQD的降糖作用等问题仍有待回答。
Xu等[63]基于随机、双盲与安慰剂对照等临床试验规范,将187例T2DM患者随机分为4组,分别接受高(N=44)、中(N=52)、低剂量(N=50)GQD和安慰剂(N=41)治疗12周,并对治疗前后患者粪便样品中细菌的DNA进行基于16S rRNA基因可变区V3区的454焦磷酸测序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安慰剂组和低剂量GQD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未显著改善,Unweighted Unifrac PCoA和MANOVA分析结果相互印证,表明菌群结构也未发生明显变化。随着GQD剂量的提高,患者治疗后的菌群结构与治疗前的差异不断增加,即菌群结构样本点偏离得越远;T2DM诊断指标空腹血糖(FB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lc)改善也更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剂量效应。此外,用药4周后高剂量组患者的菌群已显著不同于用药前,并在此后的8周维持不变,但是血糖水平一直持续改善。冗余分析(RDA)从4 000多种肠道细菌中找到了146种响应GQD治疗的细菌种类,其中47个OTU被显著富集,且17个OTU与FBG显著负相关,9个OTU与HbA1c显著负相关。特别是产丁酸盐的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高通量测序及定量PCR结果都证实其丰度变化与T2DM症状指标(FBG,HbAlc和2hPBG等)改善显著负相关,与HOMAβ显著正相关。
研究表明,中药复方GQD可以有效地调节肠道菌群结构,特别是增加有益菌如Faecalibacterium spp.等的含量,且菌群改变与血糖代谢改善显著相关,提示肠道菌群可能参与了GQD降糖作用,也提示中药可作为以肠道菌群为靶点治疗T2DM的新药来源。该研究首次在人群试验中观察了GQD在治疗T2DM过程中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与糖尿病改善的关系,也表明严格质量控制的复方中药也可以做RCT试验验证其疗效,而且基于宏基因组学的肠道菌群结构变化监测为理解中药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途径。
3 研究方法
由于中药的复杂性,多种交叉学科技术被引入到中药体内代谢研究。基于从单一化合物到复杂体系的代谢研究思路与策略,对中药体内代谢的生化过程以及代谢物本身的研究,化学半合成及生物催化合成用于代谢产物的制备;体外代谢模型能更好地对不同组分的体内处置进行模拟并给出解释,常用的体外模型如细胞水平的Caco2模型、血脑屏障模型、酶水平的P450酶系、UGT/SULT酶系。此外,动物或人群试验,以及基于血清中含有的成分才是中药的体内直接作用物质的学说而建立的血清药物化学,是研究中药体内代谢过程的有效方法。
在上述体内外模型基础上开展的中药体内代谢基因组研究,本质上同样基于基因组学技术,主要为微阵列芯片技术和测序技术。以基因芯片为代表的微阵列芯片是研究分析基因的一种强有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是进行中药基因组研究的主要工具。在基因芯片的表面,以微阵列的方式固定大量并行的寡核苷酸或cDNA探针,对生物体整个基因组的基因表达进行测定。基因芯片以高通量、多因素、微型化和快速灵敏的特点而见长,能够针对中药的多成分、多途径、多系统、多靶点的作用特点而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除常规的微生物分子生态学技术,包括细菌16S rRNA基因克隆文库技术、PCRDGGE/TGGE和TRFLP等DNA指纹图谱技术外,近年来迅猛发展的454,illumina等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使得对肠道宏基因组的高通量、大规模深度测序成为可能,极大促进了肠道宏基因组学的发展。同时结合多变量统计方法,如主成分分析(PCA)、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等,可直接地获得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信息,鉴定出与中药体内代谢密切相关的特定的细菌类群和生物转化基因功能,从而为中药体内代谢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34]。
综上,中药基因组学和肠道宏基因组学从不同角度对中药体内代谢进行研究,但从药物研究和毒理学评价层面来看,基因组学研究的是生物体受外源性物质刺激后基因表达的改变,而基因表达调控与系统的整体功能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中药作用于人体,一方面自身会被肝药酶或肠道菌群代谢,产生活化或者失活的代谢产物;另一方面中药及其代谢产物会导致机体内源性物质应答的变化,引起全身水平复杂的代谢网络变化,体现在体液内/外源性代谢物的成分构成或相对浓度的变化,从而提供了药物作用机制和作用靶点的信息[34]。随着色谱质谱联用仪法、核磁共振波谱法、色谱核磁质谱联用等分析技术的发展,代谢产物鉴定及多成分药代动力学研究已有较成熟的平台。代谢组学(metabonomics)表征生物体整体功能状态的特点,与中药的“多组分、多靶点、整体调节,协同作用”的特点相吻合,因此是研究系列中药现代化关键科学问题的重要手段。张旭等[34]认为综合运用中药基因组学、肠道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生物信息学等技术对中药体内代谢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望为中药现代化研究打开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韩旭华, 牛欣,杨学智.方剂药效物质系统与单味药成分之间的非线性关系[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6, 21(5):289.
[2] 张昱,谢雁鸣.后基因组时代中医药研究思路方法新探[J].中医药学刊, 2001, 19(5):426.
[3] Lederberg J. Infectious history[J].Science, 2000, 288(5464):287.
[4] Spor A, Koren O,Ley R. Unravelling the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ost genotype on the gut microbiome[J]. Nat Rev Microbiol, 2011, 9(4):279.
[5] Qin J, Li R, Raes J, et al. A human gut microbial gene catalogue established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J]. Nature, 2010, 464(7285):59.
[6] 王升启.试论“中药化学组学”与“中药基因组学”[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0, 2(1):19.
[7] 陈士林, 朱孝轩, 李春芳, 等. 中药基因组学与合成生物学[J].药学学报, 2012(8):1070.
[8] 陈士林,宋经元.本草基因组学[J].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3381.
[9] Weinshilboum R. Pharmacogenomics――drug disposition, drug targets, and side effects[J]. New Engl J Med, 2004, 348(6):538.
[10] 荆志伟, 王忠, 高思华, 等. 基因芯片技术与中药研究――中药基因组学[J].中国中药杂志, 2007, 32(4):289.
[11] Lee S M Y, Li M L Y, Yu C T, et al. Paeoniae Radix, a Chinese herbal extract, inhibit hepatoma cells growth by inducing apoptosis in a p53 independent pathway[J]. Life Sci, 2002, 71(19):2267.
[12] Watanabe C M, Wolffram S, Ader P, et al. The in vivo neuromodulatory effects of the herbal medicine Ginkgo biloba[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1, 98(12):6577.
[13] Zhang Z J, Wang Z, Zhang X, et 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induced by oral administration of baicalin and gardenin after focal brain ischemia in rats[J]. Acta Pharmacol Sin, 2005, 26(3):307.
[14] Zhang Z, Li P, Wang Z,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baicalin and jasminoidin on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J]. Brain Res, 2007, 1123(1):188.
[15] 张立平, 马建文,张洪亮.六味地黄颗粒对晚期肝肾阴虚型结直肠癌患者基因表达谱的差异分析[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4, 18(17):52.
[16] 高利臣, 张伟, 刘昭前, 等. 药物代谢相关基因介导的中草药药物相互作用研究[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2012, 17(3):346.
[17] Wang L, Zhou G, Zhu B, et al. St John′s wort induces both cytochrome P450 3A4catalyzed sulfoxidation and 2C19dependent hydroxylation of omeprazole[J]. Clin Pharmacol Ther, 2004, 75(3):191.
[18] Efferth T, Fu Y J, Zu Y G, et al. Molecular targetguided tumor therapy with natural products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Curr Med Chem, 2007, 14(19):2024.
[19] Kelter G, Steinbach D, Konkimalla V B, et al. Role of transferrin receptor and the ABC transporters ABCB6 and ABCB7 for resistanc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 cells towards artesunate[J]. PLoS ONE, 2007, 2(8):1080.
[20] Sertel S, Eichhorn T, Simon C H, et al. Pharmacogenomic identification of cMyc/Maxregulated genes associated with cytotoxicity of artesunate towards human colon, ovarian and lung cancer cell lines[J]. Molecules, 2010, 15(4):2886.
[21] Scherf U, Ross D T, Waltham M, et al. A gene expression database for the molecular pharmacology of cancer[J]. Nat Genet, 2000, 24(3):236.
[22] Wang C, Dai Y, Yang J, et al. Treatment with total alkaloids from Radix Linderae reduces inflammation and joint destruction in type Ⅱ collageninduced model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J]. J Ethnopharmacol, 2007, 111(2):322.
[23] Kim E K, Kwon K B, Shin B C, et al. Scopoletin induces apoptosis in human promyeloleukemic cells, accompanied by activations of nuclear factor κB and caspase3[J]. Life Sci, 2005, 77(7):824.
[24] Seo E J, Saeed M, Law B Y, et al. Pharmacogenomics of scopoletin in tumor cells[J]. Molecules, 2016, 21(4):496.
[25] Ward C P, Redd K, Williams B M, et al. Ginkgo biloba extract[J]. Pharmacol Biochem Behav, 2002, 72(4):913.
[26] Zuo X C, Zhang B K, Jia S J, et al. Effects of Ginkgo biloba extracts on diazepam metabolism:a pharmacokinetic study in healthy Chinese male subjects[J]. Eur J Clin Pharmacol, 2010, 66(5):503.
[27] Yin O Q, Tomlinson B, Waye M M, et al. Pharmacogenetics and herbdrug interactions:experience with Ginkgo biloba and omeprazole[J]. Pharmacogenetics, 2004, 14(12):841.
[28] 徐凯进, 李兰娟,邢卉春.肠道菌群参与宿主代谢对医疗个性化的影响[J].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2006, 33(2):86.
[29] Kochhar S, Jacobs D M, Ramadan Z, et al. Probing genderspecific metabolism differences in humans by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based metabonomics[J]. Anal Biochem, 2006, 352(2):274.
[30] Holmes E,Nicholson J K. Variation in gut microbiota strongly influences individual rodent phenotypes[J]. Toxicol Sci, 2005, 87(1):1.
[31] Schnackenberg L K. Global metabolic profiling and its role in systems biology to advance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the 21st century[J]. Expert Rev Mol Diagn, 2007, 7(3):247.
[32] Ley R E, Lozupone C A, Hamady M, et al. Worlds within worlds:evolution of the vertebrate gut microbiota[J]. Nat Rev Microbiol, 2008, 6(10):776.
[33] Eckburg P B, Bik E M, Bernstein C N, et al. Diversity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al flora[J]. Science, 2005, 308(5728):1635.
[34] 张旭, 赵宇峰, 胡义扬, 等. 基于功能元基因组学的人体系统生物学新方法:中医药现代化的契机[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1, 13(2):202.
[35] 杨秀伟,徐嵬.中药化学成分的人肠内细菌生物转化模型和标准操作规程的建立[J].中国中药杂志, 2011, 36(1):19.
[36] 杨秀伟.中药成分代谢分析[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3.
[37] Lhoste E F, Ouriet V, Bruel S, et al. The human colonic microflora influences the alterations of xenobioticmetabolizing enzymes by catechins in male F344 rats[J]. Food Chem Toxicol, 2003, 41(5):695.
[38] Li H, Zhou M, Zhao A, et 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lancing the gut ecosystem[J]. Phytother Res, 2009, 23(9):1332.
[39] Nicholson J K, Holmes E, Lindon J C,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modeling mammalian biocomplexity[J]. Nat Biotechnol, 2004, 22(10):1268.
[40] Haiser H J,Turnbaugh P J. Is it time for a metagenomic basis of therapeutics?[J]. Science, 2012, 336(6086):1253.
[41] Nicholson J K,D Wilson I. Understanding ′global′ systems biology:metabonomics and the continuum of metabolism[J]. Nat Rev Drug Discov, 2003, 2(8):668.
[42] Jia W, Li H, Zhao L, et al. Gut microbiota:a potential new territory for drug targeting[J]. Nat Rev Drug Discov, 2008, 7(2):123.
[43] Kim D H, Yu K U, Bae E A, et al. Metabolism of puerarin and daidzin by human intestinal bacteria and their relation to in vitro cytotoxicity[J]. Biol Pharm Bull, 1998, 21(6):628.
[44] Akao T, Kawabata K, Yanagisawa E, et al. Balicalin, the predominant flavone glucuronide of Scutellariae Radix, is absorbed from the rat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s the aglycone and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form[J]. J Pharm Pharmacol, 2000, 52(12):1563.
[45] Wang H, Qi L, Wang C, et al. Bioactivity enhancement of herbal supplements by intestinal microbiota focusing on ginsenosides[J]. Am J Chin Med, 2012, 39(6):1103.
[46] Bae E A, Han M J, Kim E J, et al. Transformation of ginseng saponins to ginsenoside rh 2 by acids and human intestinal bacteria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ir transformants[J]. Arch Pharm Res, 2004, 27(1):61.
[47] 徐永杰, 张波,张t腾.牛蒡多糖的提取及对小鼠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J].食品科学, 2009, 30(23):428.
[48] 王广, 马淑霞, 胡新俊, 等. 党参多糖对双歧杆菌和大肠埃希菌体外生长的影响[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0, 22(3):199.
[49] 陈琛, 江振友, 宋克玉, 等. 中草药对小鼠肠道菌群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1, 23(1):15.
[50] Handelsman J. Metagenomics:application of genomics to uncultured microorganisms[J]. Microbiol Mol Biol Rev, 2004, 68(4):669.
[51] Raes J. The gut microbiome――a new target for understanding,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disease[J]. Arch Public Health, 2014, 72(S1):1.
[52] 李文兰, 南莉莉, 季宇彬, 等. 人参中人参皂苷Rg1,Rb1在体肠吸收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 2009, 34(20):2627.
[53] Gao S, Basu S, Yang G, et al. Oral bioavailability challenges of natural products used in cancer chemoprevention[J]. Prog Chem, 2013(9):1553.
[54] Hasegawa H. Proof of the mysterious efficacy of ginseng:basic and clinical trials:metabolic activation of ginsenoside:deglycosylation by intestinal bacteria and esterification with fatty acid[J]. Jap J Pharmacol, 2004, 95(2):153.
[55] Kim D H. Metabolism of ginsenosides to bioactive compounds by intestinal microflora and its industrial application[J]. J Gins Res, 2009, 33(3):165.
[56] Zhou S, Xu J, Zhu H, et al. Gut microbiotainvolved mechanisms in enhancing systemic exposure of ginsenosides by coexisting polysaccharides in ginseng decoction[J]. Sci Rep, 2016, 6:22474.
[57] 张晓云,杨春清.灵芝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J].现代药物与临床, 2006, 21(4):152.
[58] Li F, Zhang Y, Zhong Z. Antihyperglycemic effect of Ganoderma lucidum polysaccharides o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mice[J]. Int J Mol Sci, 2011, 12(9):6135.
[59] Pan D, Zhang D, Wu J, et al. Antidiabetic, antihyperlipidemic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a novel proteoglycan from Ganoderma lucidum fruiting bodies on db/db mice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J]. PLoS ONE, 2013, 8(7):e68332.
[60] Chang C J, Lin C S, Lu C C, et al. Ganoderma lucidum reduces obesity in mice by modulat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ut microbiota[J]. Nat Commun, 2015, 6:7489.
[61] Clemente J C, Ursell L K, Parfrey L W, et al. The impact of the gut microbiota on human health:an integrative view[J]. Cell, 2012, 148(6):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