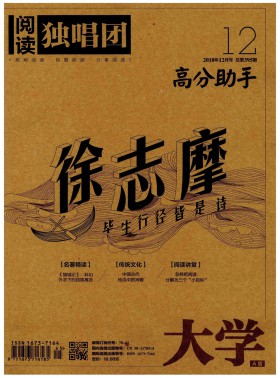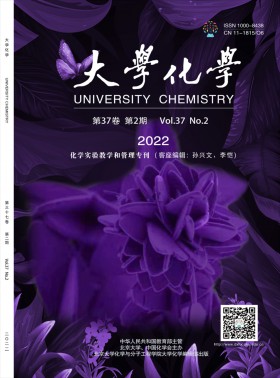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大学之道的逻辑推理特点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大学之道的逻辑推理特点范文1
关键词:认知与认识;认知与科学;认知与审美;戏剧审美;启示
一、认知与认识
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主要是逻辑思维,即人在认识过程中一般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现实。前人说过的话、一些定性的判断、结论等,往往又使人们形成一种定势思维。然而,逻辑思维、定势思维都是不宜用于诗词创作的。
认知和心理学联系比较紧密,具有诗性特征,为文艺诗性表达。而认识和哲学联系密切,具有理性和逻辑性特征,注重语言逻辑性表达。认知与认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里说:“当我们怀着这些想法站在怀疑论的最高峰时,便会有一种理智的焦虑所产生的颤粟之感。我们感到一种晕眩,因为我们窥见了一个似乎是无底的深渊。这就是认识论,心理学的理论道路与――我希望加上――形而上学的理论道路相交叉又突然断裂之点……在我们没有充分地测定认知意识的深度所处的位置之前,我们并不能指望重新沐浴科学的光辉。①” 他所说的“这些想法”,即对分析和推理的怀疑思考。他说“成熟的人儿童和傻子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差别,只有逐渐的过渡。②”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是变动不居,千差万别的,导致意识中出现的表象和意象也是变动不居,界限模糊的。而在成熟的人儿童和傻子之间,他们的“认知意识的深度所处的位置”是有很大差别的。
石里克接着又说“认知就是一个事物在另一个事物中被再发现。在不同的个人(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形形的关系中,通过这种方法所发现的是一种共同的次序;在大量的,混杂的主观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客观的世界。③” 这段表述中,他表述了量的知识(即认知的逐渐成形)和质的知识(即认识的逐渐成形),进而,“混杂的主观材料”达到一定的累积后,就会认识和发现一个客观的世界。关于认知是多维的,有空间或时间等的阐述,他举例到:“与我的右手相接触的,与我的左手有一定距离,又与我们的双眼有一定距离的,如此等等,正是同一支铅笔。④”
由此,认知是沿着心理学的理论道路,偶尔会与形而上学理论有交叉,并且认知意识处于无法测量的深度位置,是一个事物在另一个事物中被再发现,是量的知识,由于它的主观性,所以在科学中有时也很难对它做出明确解释。比如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规律发现是凭借他对音乐“八音律”而得来的认知启示。而认识是以分析和推理的哲学基础为主的怀疑性思考,它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是质的知识。但是,关于认知和认识的界线是无法测量得知的。因为认知要凭靠人们的语言习得去感悟,而认识则是与怀疑推理相并行而存在的否定之否定的科学理性和逻辑积淀。学者以为,认知在瞬间产生出光辉而永恒,而知识是永久的不易变动的恒星,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知识顺应时代而前行。
二、认知与科学
关于认知,人们也从科学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和推理,从神经从脑科学处理信息的逻辑推理和概括对人们的思维进行认知,从大脑处理信息的角度来看思维的操作,大脑的信息处理需要以下的三大元素:1)概念。一种指示信息内容的信息量。概念的模式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信息量携带信息的方式,其中包含信息的内容,内容可以是“象化量”,还是“量化量”,还可以是“图像”等。2)逻辑。调用这些概念的方式,逻辑就是一套规范概念作互动关系的法则,这些互动关系包括相消,相生,因果等作用。3)指示“概念”和“逻辑方式”的表记方式,最基本的是在大脑本身以大脑中的信号形式记录,这就是我们人类思维的内部形式,它通过外部世界作指示的方式就是“语言/语音”,“图画”,“文字”和“符号”。这三种就是研究思维模式的标准,以思维模式产生行为,乃至人类文明而论,这三大元素就是探讨以上问题的“钥匙’。在大脑中存在着思维元素,概念与逻辑方式,它们以“印象”的形式存在,从而使得思维得以实现和运作,第三种思维元素――表记方式,其实也是指示方式,指示方式把大脑中的思维反映在口语语言和文字中,还可以是图画和符号等,它最大的作用是通过外部媒体表记出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因为除了语言之外,文字更是思维的主要工具,这样以文字或符号的方式表记思维过程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通过符号或文字的方式,表记出大脑中在最初时以语音方式所携带的概念,从而使文字与符号有可能提供到提炼概念和精化逻辑的作用。
以上关于认知的科学分析和表述是基于对人类大脑和神经的探索,而目前对于人脑和神经的探索还处于一个进行式状态。人类是复杂的带有情感性特征的灵长类动物,而其脑的构造是极其复杂的,又受其民族地域种族文化先天语言习得和后天言语习得历史和进化等等诸多的因素影响,从科学的角度对认知的研究,犹如“冰山一角”,还是无法探知其秘密宗旨的。另外,科学的解释与探知也许对人们思维认知的开发会起到某些帮助,然而,相消相长的规律告诉我们,也许,这也预示着人类个体认知也会受到某些不易察觉的伤害而退化,再加上人类有情感特征这一现象,而情感和思维认知本是和谐相长的。由此,笔者以为认知不能因科学的分析而挤压属于它自己的空间,而是顺其自然,给予它诗性的自由。
三认知与审美
认知与审美的关系可以概述为石里克所言“心灵之外的被感知的直观的物体和心灵之内的知觉表象之间的区别。⑤”然而,往往心灵之外的被感知的直观的物体和心灵之内的知觉表象是契合而存在着,交感而相应,从而产生一种认知审美。
而在文学的创作和接受过程中,以心智为特征的认知审美悄然而存于每一个体。金元浦在《文学阅读――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一文中所言:“文学形象表现为一种存在认知的延伸。而对现实客体的想象仅仅是利用既定认知去创造非现实的存在。所以,现实客体不能控制文学想象,而‘非现实’客体则控制了想象的心理反映。⑥”也即个体在心灵之外的被感知的直观的物体和心灵之内的知觉表象之间的一种契合反映,而每一个体的契合反应又是不同的。根据这种不同,心理学家对个体所反应出来的表征性对象进行思维的分析,想以此赋予认知一个科学的解释显然不尽合理。然而,认知带给人们一种无言的美的启示,它是诗性的自由,产生认知审美的愉悦,并非仅仅是一种科学现象的表征,它或许会突破科学的樊笼而昭示给人们无法解说的诗意美。
四语言认知中的戏剧
由于,西方戏剧沿着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戏剧的定义而发展,再加上语言科学和哲学思维的探索,使得西方戏剧明显有着语言认知的特性。英国的语言学家奥斯汀将语言行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陈述式,一种为完成行为式。陈述式言语仅仅是陈述一件事,但它具有或真或假的属性。而完成行为式语言则不论真假,以语言的行为效果为准。西方戏剧的发展,就逐渐从剧本的叙述性的言语向行为展示性和完成性的言语转化,动作完成式的言语逐渐外显,而陈述式语言逐渐内隐,动作完成式的言语逐渐强势压过陈述式语言。而其戏剧的文类规范和发展也逐渐与之适应,使得戏剧表演的动作性特征也越发明显和加强。以致以后的不断产生的新的西方戏剧美学审美要求情节通过具体的可显的表演直接在舞台上展示出来。与之相反,而那些叙述出来的就被规划为史诗剧,或者是歌剧样态,又因为这些剧作形式不符合变化的时代审美而逐渐当成韵文和散文的精雅作品封藏于书库。
逐渐的规范使得西方戏剧注重理性和逻辑,而摒弃曾有的不逻辑和非理性,在新的认知语言中寻求戏剧的创作和符合理性的审美。他们对原有戏剧形式的否定和不推崇,使其逐渐淡忘了属于它的远古的一种声音,一种原始心智的诗性思维。由此,他们的认知由于太多的理性规范而其与现实并不相符和,他们变得焦躁和反叛,逐渐兴起反传统,反逻辑等的后现代审美,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戏剧中给人们一个等待的希望,而希望却迟迟未到。西方戏剧的理性追求似乎也是在寻求一种科学认定的美,然而,抛弃认知诗性的表达,希望却迟迟不来。
五、认知美学与西方戏剧审美
在西方,随着哲学的思考引发了诸多理性分类,亚里士多德根据人类活动在《诗学》 中分出理论性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实践性科学(包括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和创造性科学(包括诗学和修辞学)等三个类别。随着科学的理性的发展和不同分解,西方戏剧也发生着更加理性的变化,戏剧审美尤其注重对动作和语言的模仿,然而,关于“模仿”,对其的理解也不同,“……从柏拉图转入对亚里士多德的考察后,诗为‘摹仿’之艺,诗乐尤在‘摹仿之道’的说法,依然跟随在后。然相应于柏拉图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的差别,摹仿之说亦发生一变。柏拉图氏,‘以抽象存在之概念为起点 ’并用‘相’之世界以指涉真实存在之世界,可感之现象仅不过是那高于感知力的原型的复制品,这在艺术的领域内,显然不过是略对神界原始所化生的凡间摹本认知一二罢了。……亚里士多德其哲学整体的基本学说,不是‘存在’being而是‘生成’becoming,随处可见引起他高度重视的,是直观世界诸现象之生长发展的过程。因而它不仅关注于物理科学的研究,而且也热衷于评鉴模仿艺术的创作,包括诗歌与绘画。⑦”因此,鉴于戏剧是一种特殊的文类题材,是一种“活的文类”,它的外部要素包括导演,观众和舞台,内部要素包括剧作文本,作品中的角色和演员等。剧本中人物之间,演员之间,观众与剧本,剧作者与观者等等诸多的对话和行动是推进戏剧情节的主要因素,也即逻辑意志和行为发生是戏剧存在流动的血脉。戏剧将剧作者剧作文本观众 演员剧中人物现实舞台等诸多要素置于开放环境, 使其不断汇入认知审美带来的新启示,新认知,由于这种开放的对话环境,西方戏剧在不同时代对“模仿”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实践着以“存在”being向“生成”becoming的完美理想转换,并且在认知基础上实践了理论性科学,实践性科学和创造性科学相融合的审美。
其次,巴尔塔萨曾说:“戏剧学是美学与逻辑学之中介⑧(此种的美学是指神学美学)”。笔者认为,西方的和对科学理性的发展,使得戏剧成为美学与逻辑学之间的中介,以此来消除诗学和科学之间的嫌隙。戏剧中的剧作者,演员,剧中人物,以及观众等,每个人都有一种述说的方式和声音,这种比较讲究人事的个性使得西方戏剧的以个体认知审美为方式的叙事性特征很明显。西方戏剧中明显的对白艺术,使其戏剧的成形有明显的事构模式,重视戏剧冲突。而这种外现为多元性的事构是由内在的逻辑性的意构所推动发生的。在剧作家,舞台和演员动作,以及观众的接受等来看呈现出多元性叙事特征,多元性认知审美关照,每个人都在交互的对话中创造性的叙事,形成一种潜在的认知美学。其中话语的主体可能是剧中人物,也可能是演员,而话语对象可能是剧中人物,也可能是观众,而观众可能是听着,也可能是个旁听者。而在剧作文本本身来看,内在的语词逻辑演绎形成的多元指称的意义推动剧本外现的多元表现方式,接受和理解的方式,由于摒弃了诗歌的模式而逐渐形成理性的一种召唤。这是因为西方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始终对“逻各斯――语言”充满了研究的兴趣,把语言学作为一门认知学科,并建立各行各业的语言话语模式,而反过来,这种对话又成为文明的象征,它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和精神活动的标识。
再者,西方的神话历史发展中就逐渐形成了与中国古代哲学的“道”不同的“逻各斯”思想,而英文词汇表示对话的词“dialogue”又源于古希腊语的logos,前缀dia表示相互之间,logos被认为是万物的本源,是世界存在的规律,是人类繁衍和生存的智慧结构,是创世的规律秩序和万物有名有意义的核心。语言的研究,伴随着心智的认知审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灵魂。
六、对戏剧审美的启示
在桑兹的《古典学术史》中关于兰茨堡的赫次德的《欢乐园》的画作,以两个同心大环圈组成:“在内环上半部,哲学被描绘作女王形象,其冠冕上分出三个头像,被标识为‘伦理学’,‘逻辑学’和‘物理学’,看来可能是被授予至尊的地位,而下半环中,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坐于桌前,面前摊开书册。外环中列有七个穹拱,每拱下均有人文七科之一的人格化身形象,‘语法学’手中指标志乃是一册书籍和一根桦条教鞭,‘修辞学’则手持书写板和尖笔,其他学科亦类似如此。此外环之下方,有四位‘诗人或术士’,各据一张书桌而奋笔作书,每人耳畔有一化作盘旋之乌鸦的恶灵,对之加以指点和教唆。整个图版的适当之处装饰了许多箴言。⑨”显然,人们一看觉得是希腊时期对诗人和诗术不重视,然而却并非如此,此图也在告知着我们,诗人和诗术与那些“盘旋的乌鸦”之间的对话推动着产生了诗意,而正是这些诗性激发着认知的心智和灵魂上升,使得新的伦理,新的逻辑和新的物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实践一直以来的认知审美。
而席勒认为人性中存在这两种基本要素,即人格和状态。人格是保持不变的自我同一的理性形式,而状态却是人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动不居的感性内容,由此就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要求:前者要使多变的现象世界具有统一的形式,后者要使空洞的形式具有实在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为使人性实现完满与自由,他提出了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活的形象”,“活的形象”就是美。西方戏剧中创造“活的形象”,而戏剧这种“活的文类”是“活的形象”的创造土壤,戏剧文类的特殊性映证和实践了认知美学。
由于戏剧这种特殊的审美艺术,既要剧作家的创作,还需要演员对它的理解和创造,由此,认知审美使得人们通过艺术鉴赏活动,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因为首先,艺术对于社会,历史,人生具有审美认识功能,由于艺术活动具有反映和创造统一,再现与表现统一,主体与客体统一等特点,往往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人生的真谛和内涵,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特长,并且常常是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给人们带来难以忘却的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其次,对于大至天体,小至细胞的自然现象,艺术也同样具有审美认知作用。艺术可以帮助人们增长多方面的科学知识。
七结论
从哲学来看,认知美学诗性地将显白哲学(通俗审美)和显微哲学(高雅审美)结合了起来,既从灵魂的高峰向下俯视,又从浅俗的内心向上仰视,前者得到一种提升,后者得到一种宣泄。而从个体心理学来看,犹如俄罗斯套娃一样,在每个人的成长当中都是藏着一个,套着一个的曾经颇具自我色彩的娃娃,既一个思维套一个思维由原始思维渐渐累积套化下形成的娃娃,而最先原始的思维部分总是隐藏和被保护在现有形式的思维模式下,又受制于这种现有思维而逼迫最先原始的思维部分发生着种种变异。而这些或许正在变异着又不断地促生形成一个套着一个的现有形式的自我存在方式。变异是自我原始思维背叛的那部分和现有形成思维之间的通灵方式(空间)。异质是自我原始思维顺从着的那部分和现有形成思维之间的通变方式(空间)。因此,戏剧作为一种活的文类题材,应是回应远古和启示未来的特殊审美存在。用认知美学来分析戏剧中的审美,可以在戏剧审美中寻求一种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德]M・石里克著:《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0页。
②同上,第150页。③同上,第336页。④同上,第336页。⑤同上,第370页。
⑥金元浦:《文学阅读一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⑦[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著:《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87页。
⑧[瑞士]巴尔塔萨著:《神学美学导论》,刘小枫选编,曹卫东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
⑨[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著:《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下册),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618页。
大学之道的逻辑推理特点范文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到城市学校,带来了班额过大等现实问题。于是,近年来班额问题成为我国政府和学者思考的热点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在早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也遭遇过类似问题,因此也有许多针对班额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经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班额大小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面对我国大班额的现实情况,应当采取的解决之道又是什么?本文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回答。
一、班额对学生有何影响
对此问题,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我们主要作两方面的综合论述。
(一)班额与学业成绩并不构成必然联系
一般人认为班额越小,学生的学业成绩越好。但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有十几项知名研究成果均表明,这一认识并未有充分的科学证据。
约翰・海蒂综合探索了美国、英国、玻利维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自1978年至2001年间所进行的十多项有关班额减小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各个阶段,并运用了元分析、纵向研究以及交叉队列研究等统计方法。最终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如当班额由25减少到15人时,“规模――效应”的方差基本在0.13[1]400,也就是说班额减小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几乎没有影响。但就具体学段而言,小班额对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较大,但随着年级升高,影响就不明显了。
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班额在30人以下的情况。那么,对于像我国这样班额普遍在40人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研究结论又如何?富勒在9个发展中国家(博茨瓦纳、印度、泰国、智利、埃及、伊朗、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来西亚)开展了此方面的研究[2]。这些研究均以小学生为对象,班级平均规模在44人左右。研究发现,学业成绩与班额的相关度并不大,学生在大班级中比在小班级中的学习表现更加努力。
也有研究表明,对大部分中国农村学校的教师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班级大小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3]。不过,他们认为减小班额更有利于课堂管理,促进教学互动并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个体化指导,减少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时,他们对大班教学也持肯定态度,认为大班教学有一定的优势,学生之间能更好地形成相互竞争的氛围,从而提高其学业成绩。
(二)班额大小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状态
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小额班级中的学生课堂行为表现更为积极。这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生在课堂中更多的是进行与学习任务相关的个人行为[4],更专注于学习性任务[5];同学之间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课堂中的违纪行为相对较少[6];学生能更加主动地与教师交往,或更主动地参与学校生活。用芬等人的话说就是,班级规模减小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学生个体的可见度”,即在小额班级中,学生会更加轻易地被教师注意到,学生会更加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上课不易分散注意力,群体归属感和班级凝聚力都较高[7]。
相对而言,大额班级中的学生行为就显得更为复杂。以50个学生构成的班级为例,学生学习分为积极型的和非积极型的。学习积极的学生通常占班级学生的四分之一,约10位左右。他们学习成绩较好,注意力集中,经常主动举手发言,也经常被教师所关注。学习不积极的学生则情况较为复杂,约一半左右的学生处于被动与主动的中间状态,他们往往是课堂教学的旁观者,既不扰乱课堂,也不主动参与课堂,通常被教师忽视。剩下的学生则是课堂纪律的积极干扰者,也是教师最为头痛的学生。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小额班级的课堂中,那些学习积极的学生,学业成绩也未必好,原因何在呢?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班额大小与教师教学行为的关系。
二、班额大小何以对学业成绩影响不大
如果班额大小与学业成绩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是否可理解为真正决定学业成绩的是课堂教学方法?为弄清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首先研究了规模大小不同的班级中,其课堂教学方法是否存在差异。比如,2000年,亚力山大对英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法国等五个国家的课堂教学进行了大范围的对比研究,发现班额在36-70人的班级与20-30人的班级在课堂教学上的确存在显著差异[8]。2005年,艾尔顿B李综合了一些文献,也发现教学方法不同,学业成绩也会有所不同[9]。之后,海蒂又在亚力山大和艾尔顿B李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不同班额中课堂教学的基本特点,如下表1所示。还有的研究发现,教师会依班额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在班额为80人以上的班级中,教师更关注的是如何传递知识;在班额为30-80人的班级中,教师关注的是如何进行教与学的互动;在班额为30人以下的班级中,教师关注的是如何让学生个体进行自主学习[10]。
那么,如何理解在较大班额中学生学业成绩较高而在小班额中学生学业成绩却未必高,甚至可能出现学业成绩表现更低的现象呢?
高尔顿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教师为了抓住学生更多的注意力,对大班额班级采取更加严格的教学手段使教学过程更加严谨、教学节奏更紧凑、教学内容也更有挑战性。[11]所以,虽然班额很大,学业成绩仍然较高。相较而言,小班教学因有更多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通常不太注重教学过程的严谨性、教学节奏的紧凑性以及教学内容的挑战性等。也就是说,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激励方法可能导致学生降低对课程内容的学习期待。或者说,教师可以更为随意地选择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间,这也导致很多学生无法严谨而全面地掌握课程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教师也不太关注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的课程计划,学生盲目地跟随教师随性的教学步伐,并不清楚他们很可能错失了全面掌握课程重要内容的机会。对此,有学者表示认同,并指出美国大多数教师可能更擅长于小班额教学,即使班额由20人降到15人以下,美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并未改变。所以,即使班额有所缩小但学生学业成绩仍然不高。有人甚至批判小班化教育政策,认为美国的教学改革总是将目光聚焦在教学客观条件的改变上,很少想过如何引导教师从学业成绩提高的角度改进教学[12]。
三、应该如何抉择
(一)现实国情是决定班额规模的前提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似乎是在主张不必改变班额,而只需要致力于课堂教学改进便可。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因为这既取决于我们的教学宗旨,也取决于我国教育的基础性条件。
假使我们关注的只是学业成绩和升学率问题,那么,根据上述研究,未必需要缩小班级规模,再说,这还需要考虑经济成本与教育成效问题。例如,已有研究表明,新西兰中小学每减少1个学生,国家就多承担113元新币的教育成本[13]。而且,这还只是在一次性投资的意义上进行的估算,若考虑其他方面的教育投入,如教室数量、班级设施、以及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投入的费用等,则成本会更高。美国学者也做过同样的推算,如果把美国的小学1-3年级的班额减小至18个学生,那么,就需要雇佣100 000位教师,每年仅教师工资一项支出就需要花费5-6亿美元[14]。
但如果我们从促进课堂教学公平、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降低教师工作负担以及降低教师职业倦怠现象等角度出发,且在我国教育经费较为充足的前提下,那么,就应当适量减少班级人数。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中小学班额确实偏大,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增加教师工作负担的同时也影响了教师的身心健康。当然,这些都要从我国具体的现实条件出发,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将班额从25人降至15人以下。那么,如何基于我国教育现实条件合理减少班级人数这一问题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此方面研究,为我国确立合理的班级规模提供科学依据。
(二)教师因素是学生学业成绩和学生发展的根本
上文所提到的对大班额与小班额教学特征的研究描述中,除了告诉我们教师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之间有较大关系之外,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班额大小与教学方法之间存在这样一个因果推理链条:班额大小决定着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决定着学业成绩,因此,班额大小决定着学业成绩。其实这一结论并不可靠,因为这一逻辑推理所依据的信息基础并不完整。也就是说,班额的改变对教师只产生有限的影响,如可能影响着教师对学生个体的准确判断,或影响着教师对学生的个体化调控与反馈。但在有些方面班额大小对教师并无影响,比如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复杂教学活动的诊断力、指导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以及营造积极课堂氛围的能力。我们的研究发现,恰恰是不受班级大小影响的教学因素在真正影响着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业成绩。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思想方法理解班级与教学。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班级看作“学习者的集合体”,强调的是个体化学习,课堂只不过是个体学习者的集合场,虽在同一时空下学习,但每个学生都是独立而封闭的个体,相互影响的机率较低。这是一种机械整体观,把课堂教学理解为个体相加之和,但教学效果通常是“一加一”仍然是“一”、甚至是小于“一”(比如一位学生扰乱课堂,全班学生受影响的情况)。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从有机整体观的角度认识课堂教学,那么,我们就会把课堂教学理解为师生、生生相互作用的生成过程,这便是产生“一加一”等于“二”(学生之间是互补关系)或大于“二”(学生之间是新质生成的关系)的过程[15]。所以,如果我们不再把班级看作“个体学习者的集合体”,而是把课堂中的学生群体看作是“集体性的学习者”,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班级群体教学的内部丰富性,正是这种丰富性为集体智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只要教师教学方法得当,使班级内部的丰富性产生交互作用,就很可能产生超越于个体和集体的智慧。换言之,最终决定班级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是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情怀和教育能力。
参考文献:
[1]HattieJ.The paradox of reducing class size and improving learning outcom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5,43(6):87-425.
[2]Fuller B.What school factors raise achievement in the third world?[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987,57(3):255-292.
[3]DinF.S.The function of class size perceived by Chinese rurual school teachers[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Forum of the National Rural Education Association.Buffalo, NY,October,1998.
[4]BlatchfordP,Goldstein H,MartinC& BrowneW. A study of class size effects in English school reception year classes[J].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02,28(2):169-185.
[5]O’Connor J.E & CooneyJ.B.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alysis of expert and novice teachers’ problem solving[J].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90,27(3):533-556.
[6]Stasz C&Stecher B.M.Teaching mathematics and language arts in reduced size and non-reduced size classrooms[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2000,22(4):313-329.
[7]Finn J.D,Gerber S.B,Achilles C.M& Boyd-Zaharias J.The enduring effects of small classes[J].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1,103(2):145-183.
[8]Alexander R.Culture and pedagog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in primary education [M].Oxford,UK:Blackwell,2000:64.
[9]Alton-LeeA.Overview of key messages from quality teaching for diverse students in schooling:best evidence synthesis[R].Wellington, New Zealand:Ministry of Education.minedu. govt.nz/goto/bestevidencesynthesis/S.2005.
[10]Chan C.Are small class better? Or what makes small class better?[R]Paper presented at theconference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class size,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2005.
[11]Galton M.Class size:A critical comment on the research.International[J]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998,29(8):809-818.
[12]Hanushek E.A.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 performance:An update[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97,19(2):141-164.
[13]Buckingham J.Class size and teacher quality[J].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2003,19(1):71-86.
[14]Brewer D.J,KropC,GillB.P&Reichardt R.Estimating the cost of national class size reductions under different policy alternatives[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99,21(2):179-192.
大学之道的逻辑推理特点范文3
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学中,有一派思想家,比较重视心的认识功能,比如荀子,就是一个代表。后来有些儒学家如王充、王夫之等人,也很重视心的认知功能。他们所说的心,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认知心”。但是,他们都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认知学说,更没有把自然界的物理世界作为认识对象,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生与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
在儒家关于心的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心”的阐述,这方面,内容极其丰富,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是,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认识心”与“道德心”,只是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所说的心,归根到底是指“道德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学说就是一种心灵哲学,因为它不是把目光投向世界,解决世界的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而是指向人自身,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当然,在解决的心灵问题的同时,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世界、心与物或心与道的关系问题,但这主要不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问题,而是一种心通“感应”关系。它同自然哲学、认识论哲学有所不同,它的着眼点在于人的心灵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包括心灵的自我实现以及超越一类的问题。
下面就儒家关于心的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进行一些分析。
(一)心的整体性
儒家哲学认为,心是主宰身体的,也是主宰一切的,因为它无所不包、无所不通。心是主体范畴,是人的主体性的根本所在。人之所以为类,就在于心。但它不是与自然界(或世界)相对立的“孤立主体”或“相对主体”,就是说,它不是与客观世界完全对立的主观世界,而是与自然界完全统一的。这种统一具有绝对性,故可称之为“绝对主体”或“统一主体”。儒家喜欢讲“感应”或“感通”,实际上就是讲心灵与外界事物(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但不是“感知”与“被感知”的关系,即不是以心为认识主体,以外界事物为认识对象,通过感觉器官与外物接触,对外物有所认识。“感应”实际上是相感而互通的意思,外界事物的性质或意义,潜在地存在于心灵之中,只是未能显发出来,通过“感应”便能显发或显现出来。这就是儒家哲学所说的“寂”与“感”、“隐”与“显”的关系问题。《周易·系辞传》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看起来是讲自然界万物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讲心灵与万物的关系,因为二者本来是相通的。“寂”是静的意思,“感”是动的意思,但这不是物理学上所说的动静,而是指心灵的存在状态及其作用。《易传》又有“三才之道”、“参赞化育”等说法,便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关系。为什么讲“感而遂通”、“参赞化育”呢?因为心灵中潜在地具有天地万物之道,通过心的作用便能实现出来。在这里,心灵的主体作用是明显的。理学家便在“寂然不动”之后,加了一句“万象森然已具”,说明心的本体存在。这同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孟子没有提出“心本体”这一范畴,而理学家则建立了宇宙论本体论的架构,以此说明心与天地万物的“寂感”关系。理学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都明确提出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一思想。如果说,在朱熹思想中还夹带着认识论的成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说),那么,王阳明则完全是从心灵存在及其本体论上说的。此外,如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也是讲心物关系的。“大其心”就是使心不要受形体限制,不要有内外之别,即不要以心为内,以物为外,只停留在“闻见”一类知识上,而是要打通内外,去体会天下之物,这样,就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同上),而不是与我相对而存在。程颢则提出“只心便是天”(《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的命题,认为心是其大无外的,心与万物根本没有什么限隔,所以,只能在“当”与“不当”处认取,“更不可外求”(同上)。他的弟弟程颐也提出“不当以体会为非心”(同上)的说法,重视以“体会”为心,而不以知识心、认知心为然。“体会”之心与“感应”之心是同类的,都强调打破主客、内外的界限,主张在心灵的体验中实现与天地万物的统一,因为心灵本身就有无限性。“此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它,不可将心滞在知识上,故反以心为小。”(同上)这同其兄程颢所说的“只心便是天”没有什么区别。正
因为心与天地“无异”,所以便能包举万物,与天地万物本无限隔。如果以心为“主”,以物为“客”。以主体之心去认识客体之物,这就是“将心滞在知识上”,凡知识都是以心物对立为前提的,心只能成为认识主体,而不是绝对主体,这就是“以心为小”。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心无限量”(见《尽心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唯心无对”(《朱子语类》卷九十八)等命题,更加明确地肯定了心的无限性、绝对性,这决不是“认知心”所能说明的。“无限量”不是指认识能力的无限性,而是指“本心”即本体心而言的,本体心就是道德本体,又是宇宙本体,它有无限创造力。“无对”也不是指认知心之无对,认知心从来是有对(对象)的,“无对”是说本体心是绝对的,其作用也是无所不在的。至于陆九渊、王阳明,更是以“心学”标榜,他们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象山全集》卷二十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传习录上》),无不是以心灵为绝对主体。
心既是绝对主体,又具有整体性特征,它包括知性、情感、意志、意向等等于一体。用王阳明的话说,本心良知“当下具足”(《传习录中》),“不可分析”(《传习录上》),这个说法是符合整个儒家精神的。儒家认为,心是整体性存在,不仅不可分析,而且不必分析,最多在功能、作用方面有所区分。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形上与形下、本体与作用等层面上作了区分,但即使是这样的区分,最终仍然归于统一。心不可能只是形而上者或形而下者,耳是“贯通”形上与形下;心也不可能只是本体或作用,而是本体与作用统而言之,兼而有之。关于心的绝对、整体性的学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主观世界的普遍有效性,它打通了天人、物我、主客、内外的界限,主张人“为天地立心”(张载:《拾遗·理性拾遗》,《张载集》)。但是缺乏合理的相对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它重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与和谐,轻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它重视主体间的道德伦理的调节作用,缺乏客观的理性精神与社会架构理论(如法治与民主);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它重视心灵的自我完善与自我修养,缺乏心智的开发与运用。总之,它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特别是德性主体或道德主体,却没有分化出认知主体、审美主体与社会政治主体等等。
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指出,儒家所说的心,是绝对的“无限心”(《现象与物自身: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说,儒家的心灵哲学是“超绝的心灵学”(同上),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绝对是对相对而言的,无限是对有限而言的,但它并不排除相对和有限。儒家认为,人是有限的,但可达到无限,心灵也有有限的一面,但可进至无限。心灵与世界相通,没有内外物我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绝对的;心灵具有无限作用与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无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灵是完全“超绝”的,更不是形而上的“实体”。心灵与万物之间的整体性,不能必然地成为“超绝的关系”。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当然不是说万物都存在于我的心中,他是承认万物的客观存在的;但也不是说,我的心灵超绝于万物之上,从而创造出万物。因为心本身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而“天”并不是完全超绝的。人的身与心都是“天”所给予的,儒家是身心合一论者,“形色”也是“天性”,只是有“大体”与“小体”之分。所谓“无限”,也只是说明心灵存在的可能性或极限而言,其功能或作用是无限的,凡存在者都可“感通”,甚至可以归于“虚寂本体”,但这并不是说,心灵是神一样的绝对主体即实体。这里所说的“绝对主体性”,不同于宗教神学所说的绝对主体性,后者是唯一的,具有创造世界的功能;前者只是就心灵与万物的整体性关系而言,它能够创造“意义世界”,却并不能创造客观世界。儒家的心灵哲学确实具有形而上的特点,因而具有超绝性,但不能完全归结为“超越的心灵学”。
(二)心的内向性
心灵作为完满具足的绝对主体,只是就其潜在性、可能性而言,并不是完全现实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需要返回到自身,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成的工作。这就构成儒家心灵学说的内向性特征。人格心理学有“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之分,这是就个体人格、个体心理而言的,就哲学与文化而言,也有这种情形,儒家哲学就是属于内向型的,但不完全是个体的,宁可说是民族的。中国的儒家哲学反映了大陆型农业社会的民族性格,同样造就了这样的民族性格。
前面谈到心灵的整体性特征,但是其中有许多心理要素,对于这些要素,儒家哲学十分重视,并且很注意相互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与联系。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心灵的整体性内容。儒家的心灵哲学,有很多心理学的内容,不只是形而上学
的问题。比如,人有生理欲望,又有心理情感,还有道德理性,进而还有性与情的来源(命)的问题,欲、情、性、命的关系问题,这些都属于心灵哲学的范围。又比如,心有意识、意向和意志,意会和思虑,还有知觉、知性、理性、直觉、体验等等,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保持心灵的平衡,实现整体的和谐,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儒家提出了许多修养方法或“心地功夫”,这些方法或功夫,成为儒家心灵哲学的重要内容,这是西方哲学很少或没有的。其所以如此强调内向功夫,就在于通过自我修养,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培养一种理想人格。“心者一身之主”,人的一切言行都发自心灵,由心灵所决定,人生的问题不靠别的什么力量,而是靠心灵自身来解决,人生的幸福,只能靠心灵的自我提升来实现。因此,需要进行自我修养。《大学》所谓“修身”之心,关键在“正心”、“诚意”等修心功夫,“修心养性”是儒学的核心。
修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就是提倡内省。孟子的“求放心”(《孟子·告子上》),就是保持道德本心而不要放失,如有放失,就要收回来。道德本心是自家所有的,无所谓放不放,这里所谓“放”,就是因“桎梏”而丧失,丧失了就要恢复过来,并不是到外面去求个“本心”。孟子还提出“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方法。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精神,所谓“养”,就是“集义”,而“义”又是心所固有的,只需不断培养,不断积累。一直培养下去而不要伤害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儒家重要经典《大学》、《中庸》,都提出了很多类似的修养方法,如“慎独”、“戒慎恐惧”、“正心”、“诚意”等等,都是在内心作功夫。后来的理学家又提出“静”与“敬”、“涵养”与“省察”、“存心”与“尽心”等方法,其实质都是“反求诸己”,在内心求得问题的解决。
这种返回到心灵自身求得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说明心灵所是千变万化、不可预测的,因此需要自持;另一方面说明,心灵是能够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也是能够自我超越的,并且最终能够达到理想境界。
内向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我反思。儒家哲学很重视心灵的思维特征,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就是对理性思维的重视。通常人们说,哲学就是反思,即思维的再思维,但儒家所说的“思”,是回到自身,思其在己者,因此具有直接性,可称之为直觉思维。“在己者”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人的“性”。心性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孟子更是以心为性,这样,心之思也就是性之明。他又说:“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同上)这所谓“得”,完全是自得,并不是在心之外有一个对象,思而得之。后来的理学家也很重视“思”,但在他们开来,“思”已经是“已发”,而不是“未发”,“未发”是心之体,即本体存在的性,“已发”则是其作用。“思”既是作用,就只能是实现“未发”之体即性,不过,这种实现同时也是一种自觉。这是“为己”之学,“成己”之学,“修己”之学。“修己”才能“成人”,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理想境界。因此,“反身内求”、“反而思之”就成为儒家心灵哲学的根本特点之一。至于天地万物之“故”,即自然界的所以然之理,虽可以思虑推致而知之,但那不是主要的,与自家身心性命没有多大关系。宋明儒家的“即物穷理”之学,也需要“致思”,但最后仍然要返回到自身,思其在己者,即明心中之性。
心灵的内向性特征,使人有一种自足感,不必向外探求什么。它防碍了认知理性的发展,缺乏探索精神;但是,它在“任何做人”这一点上,确实有某种自觉。它要解决“人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最终实现心灵的超越,进入“天人合一”境界。
(三)心的功能性
在儒家哲学中,心是存在与功能范畴,不是静止的实体范畴,心具有无限创造力,处在永无停息的活动与过程之中。心是活动的,不是死静的,其中有情感、意志、意会、欲望、感觉、知觉、思维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正是心的活动与功能体现了心的“存在”。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体用一源”、“动静合一”。体是“静”的,用是“动”的,但这所谓“静”,并不是在作用之外有一个绝对静止的本体即实体,它就在作用之中,活动之中,且只能通过作用、活动而实现出来。儒家要把道德本体、道德理性落实到现实的、活泼泼的心理活动中,而不是变成“观念”、“理念”高悬在那里,因此,它很重视心的观念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心”字有多中解释,多种用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解释和用法是活动与功能。如前所引孟子的“心之官则思”,就是如此。思是指思维活动,不是指思想观念。所谓“本心”,是在“思”的过程中实现出来的;所
谓“四性”(仁、义、礼、智),是在“四端”之情(恻隐等等)的活动即“扩充”的过程中实现的。
就其功能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人最重视生长、发育之义,这一点实质比“思官”之心,“神明”之心出现更早,也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心”字指木的尖刺与花蕊。《诗经·邶风·凯风》所描写的“吹彼棘心”,就是指棘木之尖刺,这正是生长点。《周易·说卦》说:“坎,其于木也,坚多心。”虞翻注说:“坚多心者,棘、棘之属。”棘、棘之类,初生时都有尖刺,其发育生长即见于尖刺,故名心。坎是卦名,代表水,水是生命之源,其在木,就表现为尖刺,尖刺最能表现生长的过程。《尔雅》说:“漱朴,心。”这同《诗经·凯风》、《周易·说卦》所说,是同样的意思,漱朴之类,最能见其尖刺,也最能表现其生长义。《礼记·曲礼》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这也是指竹之笋尖,松柏之木尖而言心。以木尖为心,正神明心的根本意义是生长和发育。生长、发育是一个过程,因此也可以说,心是过程,在过程中表现其生长的功能。对此,清代学者阮元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考证,他的考证和解释是符合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精神的。(见《研经室集·释心》)
“木心”虽不等同于人心,但有相通之处,而且人心的诸义,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不仅如此,从“生”的观点解释人心,更富有哲学意义。儒家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仁学,而仁的根本意义就是“生”,“生之谓性”,“生之谓仁”,儒家的心灵哲学就是建立在这些解释之上的。它从人的生命推到宇宙生命,再由宇宙生命神明人的生命,最终落在心上。《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既是讲宇宙生命,更是讲人的生命,这一切都是通过“神”即“心”来实现的。“神”决不仅仅指天地“阴阳不测”之神,而且指心之神明,是“神妙不测”之神。心之神明是实现“天德”即“生德”的根本所在,因此才有天以“生物”为心,人以仁为心的学说。这里已经引入了目的性意义。人心不仅是活动过程,而且是有目的的活动,其最高目的就是实现“天德”即仁。“天德”之仁不过是“生生不已”的过程,是一种“生意”,其在人心便是仁。理学家程颢说:“万物生意最可观。”(《二程遗书》卷十一,《二程集》)这所谓“生意”就是仁,在人则为心。客观地说,是“天德”,主观地说,是仁心,二者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他又说:“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同上)人之所以不可“自小”,就在于人有仁心,而仁心就是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人与天地是“一物”,不是相对而存在的“两物”。贯穿天人的只是一个“生”字,而心的根本意义又就是“生”,以“生”为仁,就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程颢所说的“观”,不是纯客观地观察,而是生命体验式的直观,通过这样的直观,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程颐说:“心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又说:“心,生道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这些说法都是以“生”释仁,并且与性联系起来,进一步从哲学上说明心的功能与过程这一特征。朱熹则进一步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天地并无心,如果说有心,就是以“生物”为心,人是天地之所生,但人有心,人心不是别的,就是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就是仁。儒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但良知的根本意义也是生生之仁。“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传习录下》)“所谓汝心,都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个性之生理,便谓之仁。”(《传习录上》)原来心就是性,性便是生,生便是仁。儒家关于心的学说,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
由此可见,儒家哲学并不承认心是实体,既不是“一团血肉”(王阳明语,同上)也不是精神实体或观念实体,更没有不死的“灵魂”。儒家哲学所说的心,是“那能知觉的”,是“灵明知觉”之心,“虚灵不昧”之心,“神妙不测”之心,“操舍存亡”之心,一句话,是处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心。正因为如此,它有无限的创造力,有巨大的主动性。孟子曾引述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其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这正是对心的活动性的描述。至于后来的宋明儒学所说的“心无内外”、“心无限量”,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了。心虽然在腔子内,不在其腔子外,但其功能、作用则是没有内外的,是贯通万事万物的,它能创造一个意义世界。
儒家哲学之所以重视心灵的功能与活动,并不是表现在逻辑推理和认识能力上,而是表现在直觉体验和实践活动上。它讲“神识”,讲“体会”、“体验”,讲“觉”,讲“穷神知化”、“出神入化”,讲“豁
然贯通”,这都是直觉体验和顿悟一类的活动,其中既有理性活动,也有非理性、超理性的活动,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理性或非理性。就连宋明儒家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其中确有认识论的内容,但不能被归结为纯粹的客观认识,因为它所“致”的,归根到底是心中之知,它所“穷”的,归根到底是心中之理(性)。所有这些,同西方的认知理性学说确实不同,有它自己的特殊意义,特别在道德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创造过成就。
前期儒家如孟子,讲道德本心;后儒特别是宋明儒,讲“本体心”或“心本体”,但这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而是指本体存在或存在本体,它是本源性的,但又是潜在的,没有实现出来的,被称之为“未发”,要实现出来,则必须通过“作用心”或呈现为“作用心”,即“已发”。体和用,“未发”和“已发”,决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完全统一的。由作用而显其本体,由功能而显其存在,本体必然表现为作用,存在必然表现为功能,这就是儒家的体用论。对此,熊十力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见《新唯识论》、《体用论》),但它没有同实体论划清界限,因而认为本体就是实体。就中国哲学的特点而言,所谓“本体心”或“心本体”,无非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原初动力和最高目的,无论就道德创造或艺术创造而言,“作用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作用即功能,所谓“本体”,就变成“孤悬”之物,不可捉摸,不可把握。“本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其作用实现出来,使其作用有一种方向性、目的性。宋明儒家曾不断批评佛家是“有体无用”之学,只有“上一截”,没有“下一截”,其原因就在这里。
儒家重视心灵的功能特征,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一种人格类型,即“圣人境界”。儒家哲学不承认外在的绝对实体,不承认上帝存在,但是肯定“圣人”的价值和意义。“圣人”并不是神,而是人,更准确地说,只是心灵的最高境界。“圣人”同上帝的最大区别是,上帝是绝对实体,而“圣人”则是处在不断实现的过程之中;上帝是异在的人格神,而“圣人”则是心灵所创造的境界。“圣人”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人人都可成为圣人。“圣人”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理”,就是“性”,即道德理性或道德本体,它来自宇宙本体。所谓宇宙本体,无非是“天道流行”的过程,“赋予人”而为性,则成为心之本体,它只能在作用中实现。通过心的功能和创造性作用,实现“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境界,就能成为“圣人”,“天人合一”境界就是“圣人境界”。儒家哲学之所以重视心灵的创造和作用,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哲学,缺乏外在的神圣裁判,使人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但它有无限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使人能看到自己的伟大。正如心学家陆象山所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要顶天立地作个人。(见《语录下》,《象山全集》卷三十五)“作人”和“成圣”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原则分别,二者都是心灵的提升。王阳明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传习录中》)良知固然是心之本体,但只能在“致良知”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致良知”便是心灵的目的性活动。
当然,这种学说也容易产生自满自足的心理,比如心学派所说的“当下具足,不假外求”(王阳明语,见《传习录上》),就是如此。但那是就道德自主性而言的,并不是就知识的获得而言的。何况,儒家并不认为“圣人境界”就是现成的,相反,必须进行自我修养,自我实现,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四)心的情感意向性
儒家哲学十分重视心灵的情感意向活动,这同西方哲学理智化、心智化的主流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缺陷,但在实践方面却有重要贡献。
意志、意向活动是心灵的重要功能,二者是同一层次的范畴。意志、意向具有定向性、方向性、目的性和实践性特征,特别是同实践有直接联系。很多学者认为,儒家哲学是“实践理性”学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同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康德在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时指出,理性在认识领域是有限的,只有在实践领域才是自由的,但他所说的“实践理性”,同样是“纯粹理性”的;他所说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一个理性的“公设”,“自由意志”如何可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儒家哲学则是通过心灵的意向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向活动既是心理活动,又能通向“意志自由”即道德理性,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理念”或“观念”。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心灵哲学可称之为“心理学--形上学的心灵学”,而不是完全“超绝的心灵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既有经验心理学的内容,又有超越的形上学的内容,实质有宗教方面的内容,关键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说的“欲”,实际上是一种意向活动。并不是所有的“欲”都能“不逾矩”,也并不是所有的“欲”都是善,孔子、孟子之所以这样说,固然有仁心、仁性的保证,但同时也有后天的学习与修养,象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同上),就是一种心灵修养,而“寡欲”之欲,则是感望。两种欲虽然不同,但都是现实的心理活动。为了保证其所欲之为善或向善,还要“立志”。“立志”确实是自由意志的问题,但必须在意向及其实践活动中才能变成现实。
如前所说,儒家又有“未发已发”之说(《中庸》),宋明儒从中发展出心之体用说,“未发”为体,“已发”为用,但从“未发”到“已发”,便有意向活动。“未发”之体只能是潜在能力或最初动力,它具有善或向善的目的,但意之所发却未必是善,这里确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或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未发”之体虽善,却不能保证其所发必善,“未发”为“中”,却不能保证其所发必“和”(“中和”问题是儒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只有“发而皆中节”,即处处符合“中”的原则时才能“和”。“中节”与“不中节”,则由各种心理因素所决定。这确实不象康德所说,有先验的道德法则即纯粹的“理性原则”,就能保证其为善。也不象牟宗三先生所说,“自由意志”就是“道德法则”或“纯粹理性”,二者是“同义语”、“一个意思”(见《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它自身即保证了是“能够实践的”。这里并没有任何必然性的保证,因为意志、意向不是就在现实层面上,而且有自主性,有时不受“理性法则”的支配。儒家讲“体用一源”,特别是心学派如王阳明更强调“大头脑”,即在“本源上”用功夫,但这功夫本身就是坚定其意志和信念,而且必须从经验上下手。即便如某些儒家所说,心本来即善,不善者仅仅由于“习染”,但是现实中的人心不能没有“习染”,这些儒家本人也并不主张与外界隔绝(只有个别人例外)。善良意志是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不能完全依靠先验的“理性法则”。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志自由,也是一生培养和锻炼的结果,并不是靠某种先验理性便自然如此。儒家凡主张“性善论”、“良知说”者,似乎持一种先验理性学说,但实际上他们都主张“存心”、“养心”、“尽心”、“持志”、“立志”、“正心”、“诚意”等实践功夫,这才是实现道德理性的根本途径。可见,善与不善的关键,并不在于绝对的实体性的“先验理性”或“纯粹理性”,而在于心灵的意志、意向及其实践活动,在于目的性的追求。就是说,自由意志是同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不是靠“道德实体”决定的。儒家哲学是不是主张有“道德实体”,实在是一个问题。仁心、良知实际上是意之所向,是一个目的范畴。
如果说,要用“实践理性”指谓儒家哲学,那么,它同康德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康德的重点在“理性”,而儒家的重点在“实践”。实践真正是一个意志、意向的问题,意志、意向必然表现在实践上。当你说“意志自由”时,已经在实践了,当你说“知”是,已经在“行”了。所以,功夫全在实践上,在意志的选择上。正如王阳明所说,“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这个“物”是指事物,即实践活动,而不是静止的对象物。“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同上)“事亲”作为意向活动,同时已是“温清定省”之类的实践活动。如果意在别处呢?良知虽然规定了意之所向,但并不能保证其必然如此,所以才有“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传习录下》)的说法,也才有致知格物的说法。只有致知格物的实践活动才能贞定意志、意向活动的正确方向,实现道德理想。这就是儒家哲学强调实践的原因所在。
总之,儒家虽然主张“本心”即是性,即是善,但必须通过意志、意向活动才能实现出来,而意志、意向活动本身就是实践的,只有实践才能使其变为现实。实践的自由与不自由,固然由向善的内在潜能所决定,但与社会环境也有密切联系,“习染”、“物蔽”的问题决不可忽视。儒家以“心无内外”、“性无内外”为理想追求,但心毕竟在内不在外,如果内外阻隔不通,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受“躯壳”的限制而流入“自私用智”,“私心用事”。孟子所谓“几希”之辨(见《孟子·离娄下》)、“牛山之木”的比喻(见《孟子·告子上》),是有深刻道理的。主体的意向活动、实践活动与客观的社会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正因为如此,儒家更强调主观意志的培养。“本心”、“心体”、“良知”等学说的提出,就是为了确定一个终极性的目的,是意志、意向活动有所遵循。
从“意志”的角度说,心确实能够创造事物,创造世界,但不是创造出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创造出意义世界,道德世界。意义世界并不是主观的,它有客观普遍性,用陆象山的话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杂说》,《象山全集》卷二十二)理能通行天下,是人间普遍适用的,又是人心具有的,是为“本心”。但本心通过意志、意向活动,最终落实为“践履”,才能实现出来。
儒家心灵哲学虽然承认善良意志,主张培养善良意志,但同时也承认恶的可能性,因为意志本身并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只是后来的刘宗周,主张以意为本体,认为意是“善根”。)这种学说,一方面为自我修养、自我实现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为自由选择留下了余地。由于意志、意向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观念构成的问题,因此,它又是历史性范畴。这就意味着,随着历史的变化,意志活动的内容是有变化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所说的意志、意向,是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是由情感需要决定的,因此,它是“情感意向”,不是“观念意向”,或别的什么“意向”。这同西方哲学有重要区别。关于情感问题,我们要单独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五)心灵的超越性
前面说过,儒家的心灵哲学不是“超绝的心灵学”,但这并不是说,心灵没有超越性,正好相反,儒家心灵哲学的根本目的正是实现超越,实现一种心灵境界。
“境界”是心灵的存在状态,不单纯是某种客观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儒家所说的心,是存在意义上的心,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心(或主要不是认知心)。但最高境界的实现,却要靠心灵的自我超越,在自我超越中进入一种存在状态,这就是“境界”。在儒家看来,这种超越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心是活动的,不是静止的,但这所谓活动,是就心的现实的、形而下的层面而说的,那么,心有没有形而上的存在根据呢?有的。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本心”、“本体心”或“心本体”。这是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
“本心”、“本体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是内外合一的。因为它本身来源于“天”或“天道”,是“天道”之在人者。就内在的方面说,它是人心所具有,而人心与形体是不能分开的。所谓“自我超越”,就是使“本心”、“本体心”完全实现出来,体用合一,即全体是用,凡用皆体,没有任何限隔。这就需要超越有限自我,实现“真我”、“真己”。对形而下的感性自我而言,这是一种超越,对形而上的“真我”而言,这是一种自我实现。其实,“真我”就在感性自我之中,只是一种心灵境界而已。“真我”对自我的超越,就在于虽在形体之中而不受形体限制,虽在感性之中而不受感性制约,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心与“天道”的合一。也就是说,个体生命虽有限而可以达到无限,虽暂时而可以实现永恒。
如果说,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更重视心理经验的作用,主张通过“下学而上达”、“尽心知性知天”,建立其自我超越的境界论,就超越感性自我,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经过《大学》的“明明德”到“止于至善”,《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易传》的“三材”、“参赞化育”、“天人合一”之学,到了宋明儒学,即完成了形而上的心灵境界说。宋明儒学最重要的发展在于,把心与宇宙本体直接贯通起来,完成了“心本体论”。这样,心之本体就是宇宙本体,宇宙本体也就是心之本体,“心即道”,“心即理”,“心即太极”,“心与理一”等说法,都是指“心本体”而言的,问题在于,如何使之实现出来,成为现实的心灵的存在状态,即心灵境界。
最主要的方法是直觉体验与意向活动。关于意向活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着重谈谈直觉与体验的问题。
直觉不同于对象认识。后者是以主客对立为特征,以理论推导为中介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充分发挥了人的理智分析能力及形式化思维,无论先验的逻辑数学,或是经验的实证科学,以及理念论的哲学,都是走的这个路子。对于人自身的认识,也是如此,它要把人对象化,如同自然对象一样。儒家的心灵哲学则不是如此。它不是把人作为对象去认识,而是作为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的生命主体去对待,如果说这也是认识,那么这种认识是直接的、整体的自我直觉(或直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存在认知而不是对象认识。它同时又是一种价值认识或意义认识。所谓生命主体,不是从生物学或单纯心理学上说,而是具有生命意义的价值主体,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同宇宙的关系一类形而上学的问题。人的价值之源是宇宙本体即“天道”,但“天道”内在于心而存在,尽管是潜在的,却又是具有价值的,是人生价值的根源。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即“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要进行“溯本穷源”式的全体把握,此即所谓直觉。从心灵的本然状态或本真状态(即“心本体”)而言,它是自我呈现或自我实现;从心灵的活动层面而言,它又是“返本还原”式的直觉,也就是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