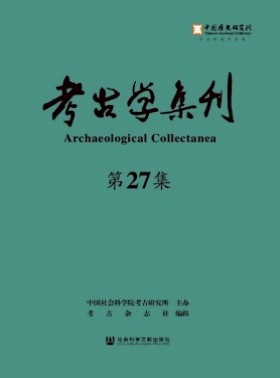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瓷器文化传播的历史意义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瓷器文化传播的历史意义范文1
很显然,一个条件良好城市的存在,是容纳四方商旅和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于是,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随着海商进入泉州,并把他们的宗教文化也全面地传播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海港城市。其次,泉州的海外贸易越来越发达。其表现主要有六:一是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如五代时泉州地方统治者王延彬被称为“招宝侍郎”,成为令泉州海上贸易获益不浅的福星。宋代有蔡襄、真德秀等地方官,均十分重视海外商贸,特别是真德秀,他深知:“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真德秀《祈风文》[2])宋末元初,统治泉州的蒲寿庚更是以从事海外贸易起家,对泉州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在宋元祐二年(1087),经过多方人士的努力,市舶司在泉州得以成功设置。市舶司是一个管理海港经济兼有政治功能的政府机构,它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是泉州海外贸易发达的重要标志。三是在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均十分发达,以泉州海船为代表的福建尖底海舶通往海外各地。据考证,当时泉州主要有3条外航线,包括东北线、东南线和西南线,均十分畅通和繁忙。四是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宋代泉州应制开展了著名的祈风活动,并勒石以记之,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又一重要证据。五是进出口商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和贸易之频繁,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瓷器和丝绸,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物品的精品。六是外商来泉州非常多,他们在泉州有长住、有短住,以常住人口居多,以至于有许多人在泉州世代繁衍,成为地道的泉州人。例如,当时外商聚集的泉州东南隅就成了“蕃人巷”,而其中是以阿拉伯人为绝大多数。总之,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海外贸易的繁盛,为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大批的阿拉伯人在泉州落户,使伊斯兰教能够在泉州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成为泉州最大的外来宗教。再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泉州形成了无限包容多元文化的局面。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宋元时期,多元文化(包括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在泉州生根开花,无疑是泉州“有容”的结果。可以想象,当时的泉州如果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则泉州不仅无法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同时也难以形成经济繁荣的局面。泉州的“容纳”有这几方面:一是自然形势的容纳,包括山的容纳、海的容纳。二是统治政策的容纳。从五代到宋元时期,泉州的地方统治者在容纳四海客商的同时,也容纳了多元文化,包括市舶司和“来远驿”的设置,蕃舶入港时举行“阅货宴”并“设蕃致语”,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了十分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是社会的容纳。包括“蕃汉杂居”,外国人与汉人通婚,不同习俗与信仰的普遍存在,呈现出泉州社会诚信待人和宽松容纳的社会环境。总之,容纳的环境使泉州迎来了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局面。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传播,其实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容纳品质的直接体现。基于以上因素,伊斯兰教于宋元两朝在泉州的传播达到,这主要以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存在为标志。清净寺是泉州现存仅有和全国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根据寺内阿拉伯文碑记载,它创建于回历400年,即公元1009年。清净寺作为众多阿拉伯人的殿堂在泉州创立,显然又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使他们有了纯粹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心灵寄托和信仰活动的地方。其历史意义是使众多阿拉伯人形成了经济利益与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人心灵里另一个更为久远的圣地———灵山圣墓,虽已在荒野中沉寂了几百年,但在元代却因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区别对待的政策,开始也得到高度重视。因为,在元代,阿拉伯人被提高到仅次于蒙古人的地位,称“回回人”;加上“海上丝绸之路”所打开的商贸局面至元代达到顶峰,阿拉伯人在泉州居住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述的那样,“因回回人在元政府和地方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外人聚居众多的泉州,伊斯兰的势力发展很快,元至正十年(1350)吴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说:‘今泉造礼拜寺僧为六七。’泉州的伊斯兰教公会,为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于元至治三年(1323)修葺了东门外灵山的三贤四贤墓,这就是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只有元碑以后遗迹的原因。”[3]其中所谓吴鉴的碑记,是对灵山圣墓有记载可见的最早的修复活动。这一修复,说明了灵山圣墓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地位已被确认,它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总之,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及其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有最直接的关系。
二、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
印度教渊源久远,其前身是产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为婆罗门教;后再历1000多年,婆罗门教逐渐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纪,婆罗门教经过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时期,泉州海港发达,印度商人与泉州贸易频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参与经商和传教活动,“印度教也于本时期随着泉州与印度经贸的发展而传入”。这就是说,印度教传入泉州,在时间上与伊斯兰教的传入相差无几。但从总体情况看,至少从规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动程度远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则很少。所以,在泉州传播的印度教,在影响结果上也就不如伊斯兰教。不过,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也有突出的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其一,从五代至宋元时期,因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许多印度佛教徒来泉州传播佛教,他们在泉州传播佛教的业绩虽不太显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宝林院则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印度佛教虽与印度教不同,但两个宗教活动同为印度人所为,两个宗教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较为紧密。无论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宝林院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终。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在泉州任“港主”,并获元朝廷的御赐执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这说明当时印度人在泉州活动的势力不小,这对于他们在泉州传播宗教文化是相当有利的。其次,这说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在泉州港不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还有许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虽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样有机会当上“港主”。再次,这说明印度教的传入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产物。因为,作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庙,这是有记载可见的一个印度商人在泉州传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证。其三,印度教的早期传入在泉州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标志物,即今泉州临漳门外的“大独石柱”,俗称“石祖”或“石笋”,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湿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该神祇缘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这一“大独石柱”,虽说比产生于12世纪后的湿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该教的原教《吠陀经》所崇拜的神像湿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笋”从其本源观念来讲,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为崇拜物它可算是湿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说明: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渗入泉州;印度人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贡献不小,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过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极盛的标志,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产物。但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该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战火中被毁。它原址在泉州南门校场附近,即今泉州汽车总站,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该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业绩,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来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命运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印度教在泉州的历史命运,成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历程的缩影。蕃佛寺无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过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无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遗忘。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国的不幸命运。然与此不同,泉州的“大独石柱”却没有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较之印度教本身要显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与泉州人的社会环境、习俗与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总之,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历史命运,包括其地位的确立和宗教文化传播的规模,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密切相关。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传播,其历史命运也基本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盛衰过程相始终。但从传播的路线看,它却是自北而南,从内地陆路传入泉州,而不是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传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泉州的摩尼教与“海上丝绸之路”无关呢?答案是否的,因为泉州的摩尼教虽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产物,却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也就是说,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推动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纳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发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该教崇尚“光明”,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斗争性明显,故长期以来累遭封杀,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摩尼教在泉州活动的空间也相应要大得多,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压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虽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纳的气度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这个时候,当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肃清的时候,泉州的摩尼教却尚存一脉,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草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意外收获,无疑应主要归功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容纳大环境,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包容品质的惯性影响力。与摩尼教的历史命运有所不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传播的历史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们且不说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传播中所出现的是非功过,但就宋元时期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则应有一定的认识。基督教传入泉州,大约在宋代,但当时所谓的基督教实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派别,承袭唐代称“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势力支持,称“也里可温”,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鼎盛期,各种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温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几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及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泉州基督教传播的文化影响力,同时更反映了元代泉州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当时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力并不大,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响,以致基督教的所谓“上帝”也要用“佛”来称呼,主教也要用“僧”来称呼。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容纳的环境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称谓,又有什么值得去计较呢?正如吴幼雄先生对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证认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再现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腊、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景教受佛教的影响至深;它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而且是一个文化的焦点。”元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温教)亦趋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虽又有新的基督教在传播,但这与之前的景教已无多大关系。因此可认为,早期传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