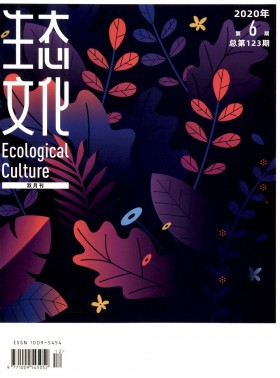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文化艺术形式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文化艺术形式范文1
一、楚人哲学思想对汉画像构图的影响
作为楚国旧地,南阳汉画像中明显活跃着楚文化的遗传因子。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首先吸纳苗蛮文化,兼融百越文化、夷濮文化、巴蜀文化和氐羌文化,加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多神崇拜,神仙方术和“黄老道”,致使在楚文化中既有对长生的追求,又有幽冥之界的想象,渗透着幻想怪诞的浪漫色彩。楚人精神世界与中原人迥异,其思维方式、观察方法和情感取向明显受惠于楚地的巫、道、神、骚的文化底蕴。楚人往往以整个宇宙为“观”的对象,其视线是流动的,目的在于求得人生的解脱与自由,这不仅是一种哲理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宇宙化的审美意识。它包含了楚人对自然、宇宙、人生的看法,朴素肯定了天人合一观念,是对人生回归自然意向的充分认同。[2]楚地先哲老子,视“道”为先天地而生的混沌之物;其后的庄子,“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色不变”,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和绝对的精神自由。正是这种以宇宙为观照对象的审美意识,使楚艺术构图形成了不局限于一事—物的宏大气魄。楚人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影响了南阳汉画像构图表现手法。在汉画像构图中,制作者是以“道”的观点去观察审视万物,而不是以“眼睛”的固定视角去观察世界。这种构图技法搅乱了时间的衔接顺序,将各种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事物在同一平面中自然地组合在一起。汉画像艺术以流动的视角,将世间万物纳入画面之中,让不同时空中的人、事、物展开对话,形成一个上天入地、天道相通的宏观结构,可谓“咫尺之图,写百里之景”。在天地之间,将现实生活、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错落安排,使其呈现出瑰丽、灵动的美学魅力。[3]如在《泗水捞鼎》画像石中,人物、车马、建筑、龙凤等皆安排在统一的平面中,多而不乱,画面内容丰富,视角流动,各处描绘皆面面俱到,呈现出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精神境界。
二、楚地图腾崇拜对汉画像题材的影响
中国传统崇拜物中,自汉以后,龙凤并重。《山海经•南山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由此可见:凤,是楚人的图腾崇拜物。楚人尊凤爱凤,常以凤鸟自喻。《史记》曾记载楚庄王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飞天,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凤鸟。楚人认为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在凤的引导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游八极。在楚文化艺术中,凤是无可争议的主角,楚人对凤的钟爱和尊崇无出其右。[4]除凤之外,熊、虎、鹿也是楚人的图腾崇拜物。《史记•五帝本纪》释曰:“黄帝号有熊,其氏族以熊为图腾……”,《山海经》又曰:“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这些被楚人认为具有通天彻地本领的神奇动物,既是巫师作法的助手,又是楚艺术中的重要母题。南阳汉画像中以凤鸟为题材的图像极多,仅于南阳汉画馆就珍藏着十余幅。它身腹浑圆,头或三、或五、或七,正中凤首较大,腿修长有三爪,其形象或华冠卷舒、修颈引吭;或足踏虎背、气宇轩昂;或振翅欲飞、伟岸英威。其造型、神韵与战国时期楚国刺绣上的三头凤鸟形象无异,清晰显示出南阳汉画像对楚文化造型与题材的继承。[5]在唐河县出土的《朱雀白虎辅首衔环图》中,凤在上、虎在下,中为衔环的铺首,其铺首长喙环眼,雄锯中端,凤鸟展翅于上,轻灵洒脱。这种凤鸟与铺首的组合既有肯定自身、堡护墓室的祥瑞意义,也是一种巫术的继续和变幻。画面布满S形的动荡曲线,整个图浑然一体,将戏剧性的画面效果与严格的秩序感完美结合起来。图中高高在上的凤鸟,反映了楚人尊凤贬虎的心理意识。画面造型饱满、线条飞扬流动,可以明显看出其中深厚、诡异的楚文化痕迹。由此可见,楚人的图腾观念在汉代人的审美观中依然存在,南阳汉画像中的凤鸟形象是楚人图腾观念的延续与发展。
三、楚人信鬼好巫之风对汉画像风格的影响
楚人信鬼好巫,《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信巫鬼,重祀。”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人,因其长期落后的生产水平,以及与北方中原地区商、周缺少交流等原因,长期以来与北方黄河流域走着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整个楚国仍保留着某些人类远古遗习,如神话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宗教巫祭气氛仍然炽烈,伦理道德观念比较淡薄等,整个楚地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6]生存在荆楚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楚人认为万事万物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天与地之间、神与鬼之间,乃至兽与人之间,都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于是在生存的斗争中便伪托产生了能洞悉此中机理者,这就是巫。
巫风盛行的楚国社会环境,把楚人导入一个狂热、怪诞的思维状态之中。在这一状态中,情感和想象是异常活跃的,而情感的调动和想象的活跃又刺激了楚人的创作欲望和热情。一方面,楚人从巫术活动中获得了审美;另一方面,又因巫事活动能满足其审美需要而需大振巫风,从而产生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楚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也因此得到体现和发展,其艺术表现也越来越荒诞浪漫。受此影响,汉代艺术家将楚文化意象趣味的幻想融于写实性之中,创造出奇诡、洒脱的浪漫主义新风格。他们把现实和神话交融在一起,祟尚感觉、祟尚热情,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和其他生命威胁,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便是极度的浪漫和活泼。
四、楚人飞升思想对汉画像线条的影响
汉代艺术家们很少根据自然界的知识来解释自己,而是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解释世界。南阳汉画像中许多人物形象,变形生动大胆、颇具匠心。众多面目狰狞的神人、高鬓细腰的女伶,为汉画像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它按照不同的审美需求,恣意运用表现形式,取得了浑然一体的绝妙效果。汉画像保留了楚风原始宗教思维,造型、风格尽管荒诞不经、迷信玄怪,但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不是恐怖消沉,而是乐观积极。在汉画像中,人间的生活乐趣不仅没有因向往神怪世界而消沉暗淡,相反却是更为生意盎然,充满了尘世情趣。如在《风伯雨师图》中,雨师和风伯指使众仙人在空中扬起大风,将雨缸倾向人间,画面取自神话传说,幻想与趣味相结合,画面中不是神对人的征服,而是人与神的和谐相处。尘世、灵魂升天时把龙作为所乘之物:“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囿”。《楚辞•哀时命》中有“仙人骑白鹿而容与”之句,把鹿作为升仙乘驾的神物。可见,浪漫的楚人善于幻想,他们对升仙确信不疑。汉画像中大量的升仙画像,揭示了楚人升仙之说对于汉人的深远影响。由于谶纬迷信和推崇道家学说,汉人对升仙更加迷恋,史书载汉武帝曾多次遣使去传说中的蓬莱仙岛寻求不死之药。南阳汉画像中不仅有乘龙升仙、乘鹿升仙、骑虎升仙等画像,还有众多羽人形象。羽人之说最早见于《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羽人即仙人,长生而不死。南阳汉画像中的羽人均为肩生羽翼的瘦小人形,大多手执仙草,引导升仙。由此可见,源于楚文化的飞升思想在汉画像中得到了明显继承。除去题材之外,汉画像中线条的灵动、飞扬感也是这种飞升成仙思想在创作中的最终体现。汉画像中那些表现神灵、祥瑞的画像,诸如日月交辉、龙凤呈祥、伏羲女娲等图像中,均由富于动势和韵律感的曲线缭绕盘旋,使画面充满生机和活力。[8]在各种曲线生动流畅的穿插、交织中,将流动之姿和韵律之美展示得淋漓尽致。在南阳市七孔桥出土的《羽人戏龙》汉画像中,右刻一应龙,曲颈振翼,张口向左行,龙前一羽人左手托物,递向龙口。这些充满活力的曲线既婀娜多姿又动荡不宁,处处化静为动,展示了韵律之美和轻灵升腾之势,铭刻着汉人自由活泼的生命激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
文化艺术形式范文2
关键词 龙文化 艺术符号 装饰与造型 比较
龙在中国古代人的信仰中是最神异的灵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富魅力的形象。无论是最早的岩画上,还是各朝各代的青铜陶器:无论是丝织绣染与服饰,还是金银器皿与玉石雕琢的手工艺品。龙纹都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演绎着各种风格和形式的装饰与造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龙已和原始中华龙相差甚远了。但在贵州黔东南一带苗民族的苗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保留了远古中华龙的本质和造型特征。苗民族的龙自然化。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神性,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民族精神,反映了苗民的生活情感、理想和审美趣味:汉民族的龙则与权势相结合,阶级宫廷化。2006年,本人承担了湖北省科学研究项目“民族民间服饰文化资源与现代设计的开发”课题,课题组成员对湖南、贵州和云南等地的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对“苗汉民族龙文化艺术符号的装饰与造型之比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
一、苗汉民族的龙纹是一种文化的艺术符号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新进化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L・A怀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建立一门“文化科学”的构想。他在《文化的科学》中说:“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全部文化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他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所创造的符号的总和,而服饰则是人类这种符号能力的最为重要的形态。
汉苗民族的龙纹是一种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是时代和民族的标志,并包含着其文化内涵。汉苗民族的龙纹是有着明显的“艺术符号”。艺术符号作为一个传达媒介只有在与艺术意象及艺术形式达到最佳结合时才能建构起来,也就是说,艺术符号的生成必须构成双重契合:与审美意象的契合和与艺术形式的契合,要达到这种双重契合,设计师还必须对这个未来的艺术符号进行文化和审美的挖掘。只有这样,这个艺术符号,才具有文化与审美的特殊性。汉苗民族的龙纹艺术构成的元素符号:造型、材料、工艺、色彩等。从不同角度传达出民族文化心理:同时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它有着明显的“艺术符号”的典型特征。
苗族龙纹装饰也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符号世界,对外是民族象征的符号,对内是分支区别的符号。对个人是年龄和性别的符号,而最清晰的符号显示则莫过于对婚否的识别。
二、苗汉民族龙文化艺术符号装饰与造型的比较
(一)、汉民族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龙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身的吉祥神物,来源于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神奇色彩。考古学上发现最早的龙是岩画上的“鱼尾鹿龙图”(山西吕梁山南端古县柿子滩石崖)以及史前时期龙之形体的实物发现。把中国上古传说的龙由虚幻变成了实体,为中华龙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史前距今6000年~5000年间,神州大地出现了以“神龙”、“祥凤”为主流的原始图腾文化。原始彩陶以其彩绘纹饰的神奇独创取胜,丰美特异的“龙纹”蕴含着极为复杂神秘而丰富深邃的社会内涵。在这类无一雷同的纹饰中,透露出原始混浊的宗教意识、社会民俗、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以及避邪祈福、寓意祥瑞象征,同时从中又可窥见源于造化(现实)又高于造化的装饰化意象,表明这种原始装饰的审美创新,似由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化轨迹,达到相当成熟的设计思维和比较熟练的表现技艺。这种“以虚拟实”的审美创新,使之装饰美化与器形造型有机融合,实用与艺术适当统一,而且较熟练地创造了写实、写意、夸张、象征、分解、综合、抽象、变形、重组等系列的装饰美化表现技巧与基本法则,对后世有着深广的影响。特别是“天人合一”的寓意以及部族标识的“图腾”开创了龙凤装饰纹样的种种神化祖型:“神龙”、“祥凤”的审美创造。从此广为流传扩展以至走向全世界,成为华夏民族精魂的光辉象征。流传至今更发扬光大了民族吉祥装饰文化传统。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礼玉”、“神玉”多在商周以来继承发展。唯“良渚文化”独创的神徽玉,豕龙纹等神秘怪异的玉雕至此已消失。从此却开创了极为丰硕的“神龙”、“祥凤”等以及复合的“龙凤”、“人龙”与“人、龙、凤”等组合或融合一体化设计的“祥瑞纹”的装饰玉雕的创新。
秦汉时期龙的艺术风格更为精细,西汉龙的造型变化大:龙纹多呈一种蟠螭图案: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造型的龙增多:龙出现双翼,飞翼紧贴身体前胸和前腿处,与躯体并行向背部施展。状如奔腾。体现出浪漫遐想的动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的结龙形象逐渐消失。龙的形象呈现出身尾分明,体似狮虎、龙脚前卷,四肢细长的特点。身躯雕琢鳞纹趋密,大多数的龙有飞翼、鹰爪,有的飞翼夸张成细长的飘带形,造型风格与以前稳重沉着的静态相反,一般呈匍匐爬行状较多,线条流畅讲究行云流水,龙的造型兽腿犬爪,张口结舌的造型。四肢兽毛飘起,颈背衬托焰环,上唇长干下唇的新艺术形象,一改过去的静卧弯曲蛇鳄之形。
唐代龙作为一种吉祥纹饰,居于“灵物”、“瑞兽”地位,且涂上浓重的神话色彩。各种龙的造型风格,在继承前代造型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动态多于静态,常奋力疾走状或腾飞状,龙身以猛兽体态为主,腿部丰满,强劲有力,龙首口角特别深,上唇上翘,眼睛炯炯有神,形容为“龙骧虎视”四肢筋骨,双翼位于前腿与身躯关节处,网格状鳞纹布满龙身。
文化艺术形式范文3
1、文化属性,是指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的习惯的定性(基本的文化素质表现)。这是一种思想程序,不以意志为转移;可以形象地说:“你的衣、食、住、行、言,处处都在从侧面折射出你的基本层次”。
2、文化属性,通俗的说法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表现,一眼就能看透你骨子里的东西,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掩饰什么,因为这毫无意义!文化属性对个人来讲,是透视一个人的受教育情况及生存环境情况的理想工具。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艺术形式范文4
楚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
楚文化中的造型艺术,融汇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其主要类型有青铜器皿、丝绣帛画、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等,无不体现出楚人的精神特质与审美情趣。
(一)青铜器皿
在楚文化中楚青铜器艺术辉煌灿烂、敦实厚重、秀丽飘逸,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楚人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创造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这些楚器外型奇特精致,纹饰典雅灵动、富于变化,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中的精品。楚国青铜器大部分发现于楚墓内,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这些青铜器皿用途广泛,造型精致,楚文化特征明显,其类型以青铜礼器、乐器最具代表性。从楚青铜器出土分布地域来看,主要集中于现今湖北的江陵、襄阳,湖南的长沙,安徽的寿县,河南的浙川、固始等地,这些区域正是楚国活动的要地,也是楚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早在宋代,就有楚青铜器被金石学著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各地楚墓的发现和楚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批的楚青铜器皿不断出土,为探究楚人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皿,在造型上比较敦厚,体积较大,工艺纹饰考究华丽,铭文一般词句不多,显得古朴有力。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于简朴,形制放达随意,纹饰也多为粗线条的几何形图案,但篇幅较长的铭文却比以前增多,或许是这一时期文字较之前发达所至。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是楚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器形和纹饰图案一改过去的设计,大胆突破宗教的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器形的改变表现为鼎上增加了盖等;而纹饰的改变表现为从过去奔放的粗花改变为工整的细花,最常见的是蟠螭纹,这些纹饰具有华美繁缛的艺术效果,纤细生动地浮现在器物的表面,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记忆。与之相配的其它纹饰也都向图案化方向发展,形制轻薄精巧,纹饰除动物纹和几何纹外,还出现了反映人们渔猎、宴饮等场景的新题材,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铭文方面则极其简单化,笔道细长。此时青铜器皿无论是在形制、造型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工艺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且楚文化特征明显。例如,“河南浙川下寺楚墓群出土青铜器多达四百多件,其中大部分青铜器体现了楚国青铜器高超的技艺水平和特殊的装饰手法”[3]。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是从中原传入的,在此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分铸焊接技术的应用和失蜡法的发明,这两项铸造技术都与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分铸焊接法最早见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河南浙川下寺楚墓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器,这两件佳作,精美绝伦,可谓是古代青铜工艺中的极品。这一时期的楚青铜器皿,从其中的精神层面和审美情趣来看,主要是满足人们巫术的需要,而不单单是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加之宗教礼仪的正统性决定了其青铜器也必须与之相符,必须具有神圣性。因为这样既可以维护当时楚国国家的统治,又可以增强社会的亲和力。因而,楚青铜器皿在其价值取向上就呈现出以神为主、以人为辅的审美特征。
(二)丝绣帛画
楚国的丝绣品以它浓郁、夸张的色彩和严谨的构图形成了独特的楚域风格。从现今发现的丝绣品来看,其颜色种类众多,在同一类纹样上搭配有多种颜色,采用色彩相似的绣线,使得纹样搭配统一和谐。例如,在湖北荆州市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绣有龙凤虎纹的单衣,这件丝绣品尽管历史久远,颜色有所褪变,但仍可清楚地看出用红、黑两色构成的虎的纹样。同期出土的“龙凤相搏纹绣”、“飞凤纹绣”、“凤鸟花卉纹绣”也都是选用当时较为流行的红、黑、蓝、灰等颜色的绣线。楚国的丝绣品色彩缤纷、稳重、统一,纹绣的造型丰富多样、华丽典雅。无论是丝绣品的样式,还是其品相和颜色,都表现出楚人独特的天赋和才华。可以说,楚国的丝织刺绣是生产技术与审美艺术的完美结合,反映了当时楚国高超的工艺水平。纺织帛画是古代中国画的一种,就是在白色的丝织品上创作图画。当今发现的帛画多出土于先秦到汉代,至西汉时期帛画发展到高峰。尽管帛画是汉代的艺术品,却具有浓郁的楚域风格,可以说帛画是一种典型的区域特色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标志。秦朝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实行残酷的“焚书坑儒”,从而使得秦朝的帛画发展受到影响。但是,由于地处偏远,远离秦朝统治中心,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生生不息、默默成长,并发扬光大。据有关文献记载,楚国的帛画共发现了二十四幅以上,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和长沙子弹库一号楚墓。《人物龙凤帛画》长三十一厘米,宽二十二厘米,此画最能体现楚人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帛画上的女性肖像,侧身站立,眼睛平视,头发高髻,婷婷玉立,双手合掌作祈祷状;整个人物秀丽、可爱、亭亭玉立,并不给人一种媚俗妖娆的印象,在她沉静的表情里有一种坦荡而又自尊的神态;在她的面前,人们感到的是对人的完美和生命自由的向往,这也正是楚造型艺术精神特质的生动写照。《人物御龙帛画》长约三十七厘米,宽有二十八厘米。画面正中绘有一位戴冠穿袍、侧身而立的男子,腰身配剑,驾驭着飞龙,整个画面有种浓郁的神秘奇幻色彩。这两幅丝织帛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意义非凡,它是迄今最早的具有独立性、主题性的帛画作品,不附着在任何建筑和工艺品上,在风格上也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流行样式。帛画上的内容主要是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楚人对生命精神的理解与认识。除了画面意境深远、夸张怪异之外,在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中国画用线造型的方式,以墨线勾勒为主,只在局部涂上颜色,涂颜色的手法除了平涂外,已经采用了分层渲染的技法,由此可见绘画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三)漆器艺术
楚漆器是以天然大漆为原料,经过特殊的工艺,髹涂在特制的竹、木等胎体上,晾干打磨,然后在胎体上雕刻、镶嵌、绘制图形的一门综合性艺术。楚人对漆“情有独钟”,在楚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漆器比较适合表现丰富含蓄的色彩,随着年代的久远,仍能保持完美的色泽,这是当时其它质地的器物无法媲美的。楚漆器艺术是楚人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一种艺术,一方面有着生活所需的实用性,另一方面也显现了某些审美情趣。楚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富于幻想、有自身独特艺术气质的国度,楚人往往采用直观的、想象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其中的审美情趣甚至是用宗教巫术的形式来呈现。所以楚漆器的外型特征不能不受到楚民族自身固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的影响,在楚漆器制作中常常表现为以一种圆融贯通的构成方式去塑造形体,去展示自我。楚人在制作漆器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相当成熟的制作工艺,尽可能利用各种材质,例如竹木、骨角、金属、皮革等制作形体。在制胎技术上已经出现了镟木、卷木和夹贮法;在工艺技法上采用素面单色的造型,或者雕刻与彩绘结合的造型手法。单色漆器与彩绘漆器相比,彩绘漆器本身更具有色彩的质感,使得楚漆器形体本身更加艳丽、优美,从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审美感。楚漆器一般有着明亮、艳丽的色彩,其中黑色与红色是主要基色。红色热烈奔放,黑色含蓄深沉,两色交相互衬,相得益彰。楚人在色彩表现方面有着独特的艺术天赋,其共同的心理特征和美学基础都超越了单纯的临摹,超越了对客观对象的简单表现。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创造了精美绝伦的楚漆器艺术,也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楚人坚韧执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特质和崇高的审美情趣。
(四)建筑艺术
建筑的艺术性昭示着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审美情趣,它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文明与历史的光辉写照。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时光流转、岁月更替,成就了辉煌、独特的中国古代建筑。作为楚造型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式建筑多采取多层宽屋檐、斜坡式的屋顶,气势恢宏。楚式建筑最早起源于长江中下游,随着楚文化的传播,其建筑样式逐渐在大江南北扩展开来。楚建筑文化展现的是“人的精神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这一特点体现在“人居和谐”的建筑观上。楚讲究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在建筑风格上常以造型奇特的木结构为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楚国建筑体系。楚建筑依托自然环境的有利因素,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审美特征与其他楚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令人叹为观止。由于楚人继承并融合了商周、蛮夷等多种文化,在其建筑样式上与黄河流域高台建筑融合,逐渐演化、形成了有自身独特风格的楚式建筑,其建筑类型包括:王宫庙宇、贵族府第、祠堂楼阁等。王宫的建造则以“楼台亭榭”为主要特色,成为当时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房屋建筑的主要类型。例如,楚国晚期的都城寿春就具有典型的楚域风貌——城内建筑布局合理,建设有很多市场,商业手工业相当繁荣。从现有的资料可以考证其建筑材料品种相当齐全,有板瓦、筒瓦、半瓦当、圆瓦当、槽形砖、大方砖等。一些瓦当有纹饰,较之先前的素面瓦当更精美细致。槽形砖、大方砖的大量使用,使得地面平整而美观。由此可见,这时期楚人的建筑和装饰水平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讲究与自然的融合、对自然美的推崇,也是楚文化中造型艺术的精神之一。在中国古代其它建筑中往往注重“风水”学说,而楚式建筑则普遍崇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建筑意识,这些建筑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风水”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今虽然我们没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楚式建筑,只能从遗留下的历史文献、诗辞歌赋中去揣摩楚建筑的样式和风采,然而我们依然能从楚辞文学中感受到楚人在建造“楼台亭榭”时拥有的乐观、充满幻想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情趣。
楚造型艺术的精神特质与审美情趣
“一个民族能否另辟蹊径,创造出风采卓异的文化来,取决于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独创性,亦即历史的独创性。[2]38”楚人在建国初期,国弱民穷,然而楚王率领族人,在一片荒芜之地,拓荒垦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家园,谱写了楚人自强不屈的精神特质。楚人立国以后,及时制定颁布国策纲领,开疆拓土,安抚臣民,选拔贤能,融合各方面思想,团结各方力量,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进而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起初,它们往往是由众多宗教巫术文化表象形成的“社会宗族活动”。那一时期的宗教礼仪、歌舞音乐成为这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表现方式。由于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使得本来所具有的艺术性被神秘的宗教巫术所掩盖。因此,久而久之,当他们幻化成一种文化积淀时,就会演化成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绪反映,这种情绪反映,就是古人在审美和文化内涵上的认知与表达。
楚文化在楚人的心理行为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崇龙拜凤、眷念故土、喜欢幻想,反映在楚造型艺术中也是个性分明。楚人尚火尚赤,青铜器皿、丝绣帛画、漆器、建筑、均为以赤为贵,婚丧嫁娶都会用火和红色。楚人有崇拜“凤”的传统,从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帛画”、“凤踏虎架鼓”便是最好的例征。楚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感官享受的欲求,在欣赏动态美的同时,也对惊艳的色彩有着强烈的爱好。在《楚辞》中,我们看到了楚人对色彩美的赞赏与追求,而在楚造型艺术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追求。不管是青铜器皿、丝绣帛画,还是漆器、建筑艺术,无不体现出丰富而又绚丽的色彩。“尚赤,爱绿,喜五彩,楚人追求的乃是惊采绝艳的意境世界”[4]。在楚造型艺术中,其主要的营构造型是对线条的运用,器物造型的统一与和谐、节奏与韵律全靠线条来表达。可以说,楚人喜欢优美的曲线,在实际的运用中也是曲线多于直线,这一特点在造型纹饰的表现上显得最为突出。例如,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青铜器大府铜牛,可谓是线条艺术的杰作。这件青铜器长十厘米,高五厘米,铜牛前腿跪姿,后腿曲于腹部,作卧伏回首顾盼状。通体装饰云纹,以脊背为左右对称,纹饰四面卷曲,线条流畅,把流动的曲线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飘逸、跳动之感。牛的眼、眉、鼻用白银镶嵌,充分反衬了铜质材料的特性,使作品的艺术形象更加充实、完整。弯曲丰满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充满弹性的身躯各部分的审美透视,传递了生命的动感和力度,体量感和肌理感表现得相当出色,显示了青铜造型持久的生命力度。“通过这件器物,我们可以看出楚人青铜工艺的精湛和浪漫的审美情趣。[5]”
楚造型艺术在纹饰上的表现,体现出一种如浮云般流动的飘逸美感。那些装饰纹样和动物造型,既奔放又多样。例如,楚造型艺术中常见的云纹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这些回旋卷曲的纹饰,俊秀洒脱,有一种十分鲜明的动态美感,好像每一个纹样都蕴涵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具有活泼、旺盛的生命力。显然,这种表现生命运动之美是与楚人乐观的性格以及热爱大自然的特性分不开的,因为楚人确信到的自然界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盎然的世界。楚造型艺术是在独特的地域环境、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中国艺术史上的明珠,它是楚人心灵历程和楚国时代精神的记录,表现了楚人独特的创造精神和非凡的艺术智慧,它蕴涵着楚人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情趣。楚造型艺术在其造型、纹饰、色彩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圆润、鲜明和艳丽,如同古老神话中显现的奇幻场景。那种达观、热烈、神话般的审美情趣,正是楚人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和其精神特质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楚造型艺术具备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卓越的艺术水准和极高的社会文明,也使得当今社会的人们受益匪浅。
文化艺术形式范文5
斗方语言的风格以清丽顺畅、简洁明快著称。以“五味……”“……五味”成句的有:五味声香、厨青五味、五味六合、五味鲜美、香生五味等,描摹了菜肴味型多样、让人赏心悦目的特点,使人如闻其香,食欲顿增,折射出厨门号字的序列化特征和共同的审美情趣。以“……味声”成句的有:和女味声、三餐味声等,从声音角度切入,有的描摹了事厨者劳动形态,有的介绍了饭菜制作的工作规律,使人如闻其声,给人的心理和视觉带来强烈冲击。
意境创设:生动别致,充满想象
旧式菜厨的另一热门斗方,非“山珍海味”莫属。该句呈现出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美食方面的意境营造,大多基于真实,着意表现在菜肴的材料、菜式、加工方法、饮食习惯等方面所呈现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也有的通过理想化的描述,即对绝世佳宴的幻想实现。无论如何,均将感彩融于其中,赋予大众人本主义的温暖。如“庖有肥肉、厨里盐梅”,创作者捕捉到的美的画面,在旧时是老百姓致力实现的目标。作者旨在体现对食者的关切和挽留,或表明家境殷实。如“琳球琅玕、二膳八珍”,创作者用精当的词语传神地勾勒出贵族阶层佳肴满桌、形美味醇的生活状态。前者喻指菜肴丰盛,菜品繁多。后者涉及烹饪体系和拿手好菜,是对最佳美食的生动状写,且还运用了典故“八珍”。八珍出现于周代,原指八种珍贵的食物,为后世之八珍筵席先驱之作。语见《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饮用六精,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1]
思想内容:从生活积淀到道德修养
通过对斗方的赏读,不仅可以丰富对菜点的感官体验,增进对美食的了解,而且还可以深入了解饮食风俗、风土人情和文化特征。还有些斗方可品味到更为深远的立意,能体会到孜孜以求的道德修养追求,其开启心志、陶冶性情的理性火花让人震撼。如“仁义礼智”,我们可理解为,人类首先应在饮食方面讲究礼仪,汲取智慧,善施仁义,要让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在饮食上达到很高的境界,过上幸福的生活。斗方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最堪适口、玉食羹鲜”,此类着意表现百姓家庭鲜美可口的菜式,使受众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第二类,“肴仁豢饭、尝列珍厨”,此类表情达意更进一层,描绘了饮食高档精致、花样繁多的未来社会图景,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愿望。作者题写此语,最主要的还是图个喜庆、吉利和祥和,而并非要实现虚构的乌托邦。第三类,“元亨利贞”,此类系最高层次的斗方,融物质追求与精神诉求于一体,或咏志或戴德或理喻或警示。例句指人的运气很好,交好运。四个字本来是分开解释的,宋程颐在其所著《易传》中解释道:“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2]属《易经》中乾卦的卦词,是哲学家用来表述事物从始到终发展阶段的术语。古代的中国人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用在厨门上,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渴慕和对家庭餐饮达到更高品级的追求,突显了哲学内涵。
艺术特色:极尽夸张之能事
菜厨小斗方风格五色杂糅,有的显示本色,有的则重于工丽,有的趋向高雅,成为以厨门为载体的、抒发民众情绪的民俗样式。可以说,菜厨斗方在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修辞手法上都很有特色。如“含英咀华”,很明显地用了夸张修辞格,对人们未来的食文化作了一番瑰丽神奇的想象。“积兰芝玉、厨中积玉”,运用了比喻修辞格,以美玉之润泽喻菜肴之形与色,以幽兰之清香比喻菜肴之风味,达到形象生动、化实为虚的艺术境界,表达了对人类厨艺的赞美。“珍出玉瓯、味调金鼎”,运用了想象,“玉瓯”“金鼎”为贵重奢华的盛器、炊具,属皇家或贵族享用,运用在斗方中,是形容所制菜肴味道如出自朝廷厨师之手,鲜美异常,大饱口福。这些例句都直陈了人类对饮食质量的不懈追求。再如“海味藏金柜,佳馐启玉橱”“庖中多鲜味,厨内冒异香”“日制声香味,时炮山声鲜”这些例句均以出神入化的描法取胜。作者运用了平仄有韵的语言,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农村富豪家庭的厨艺活动或菜肴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讴歌了农家怡然自乐的生活情调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文化艺术形式范文6
【关键词】 新形势;群众文化艺术;发展
一、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
1、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逐渐渗透出社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一直是处于一种比较开放的发展状态,我国政治政策的开明,让我国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也逐渐地呈现开放性。一个地区的群众文化是代表着这个地区文化的整体特征,某一地区的群众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会逐渐地形成具有当地特点的文化,这时就会逐渐地向外发展与传播,当向外发展的群众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很难再发展了,这主要是因为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局限,此时的群众文化就会不断地汲取外界的发展经验,通过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同达到一定的发展。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就逐渐地表现出社会化的特点。
2、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逐渐规模化、产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那么在文化的发展上也逐渐地国际化,群众文化艺术逐渐地形成“市场文化”以及“产业文化”,这就是说,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群众文化艺术发展形势不断地改革中,群众文化艺术已经逐步的规模化、产业化,与国际相连的群众文化也在逐渐地完善,我国将群众文化艺术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而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也逐渐地涉及了绿化、建筑、科学以及民间艺术等,这一系列的文化发展逐渐地演变成了群众文化产业,在以后的发展中,群众文化艺术也会呈现出更大的发展规模。
二、发展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策略
1、注重通俗文化的发展
所谓通俗的文化,也就是指群众通俗易懂、能够尽快接受的一种文化。通俗易懂的文化是特别接常人的心态的,群众之所以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化,是因为通俗易懂的文化能够让人放松自己的情感,能够直接的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然而,在我国群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通俗文化的发展是受抑制的。新形势下,发展群众文化艺术就要注重通俗文化的发展,要改变以往群众文化的旧的工作模式以及旧的体制。在以往的群众文化工作中,工作的开展往往是围绕各种类型的文艺比赛,然后一级一级的评定奖项,但是在群众的眼中,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有这一类的比赛都是一个模式,并不能为群众带来任何意义上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氛围,因此,发展新形势下的群众文化艺术就要改变以往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与制度,这样才能调动群众的情绪,实现群众文化的意义。其次,要想发展通俗文化,还要注重发展群众中间的人才,通俗的文化艺术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的,真实的生活中,群众是主人翁,培养群众中间的文化艺术人才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不断地汲取外来文化艺术,将文化所需的设备,诸如音响设备、器乐设备等,都要准备齐全,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群众中间的文化艺术人才,发展通俗文化,进而发展新形势下的群众文化艺术。
2、拓展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
新形势下,发展群众文化艺术要拓展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不能拘泥于一种方式或者一个环境下的发展,而是应该尽可能多的发展多形式化、多空间的发展模式。在目前流行的文化中,包括老年文化、校园文化、街头文化、企业文化或者商业文化等等,其实都可以作为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空间,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发展形势,对于新形势下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例如,在街头文化中,街头文化是现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是最接近通俗文化的一种文化。街头文化是多种多样的,那么群众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借鉴街头文化的发展,让这些文化逐渐地渗透到群众中去。再如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满足学生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文化,学生从校园走进社会,将校园文化反馈给社会,这种高素质的文化逐渐地影响到社会文化中,进而影响社会中群众文化。因此,新形势下,发展群众文化艺术就要不断地拓展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
3、注重城市广场文化的发展
广场文化,其实是由城市广场中逐渐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由广场逐渐展示出来的一种文化。在广场文化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广场内建筑本身的一种文化,一般在广场中都会有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或者雕塑,这些都是广场文化的一种,其二则是指以广场为地点,在广场上进行的文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发展城市广场文化,要尽量避免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色彩的影响,广场文化主要是为了放松人们的心情,减轻高强度下、高压力下工作的人们的疲劳以及压力,让人们享受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广场文化还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审美以及承受能力,尽管目前的社会发展中,物价上涨,群众的娱乐消费支出比较高,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也是不断地在增加的,这并不是代表广场文化就可以不考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而且,在发展广场文化中,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主,坚决消除低级、垃圾的精神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高尚的文化艺术。
三、小结
新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而在精神生活上越来越注重文化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建立我国特色的群众文化艺术,培养我国群众的文化意识,进而改善我国城市文化的品位,这样才能不断地与国际文化接轨,达到群众文化艺术改善人民精神生活水平的目的,缓解群众的压力,进而达到真正的全民娱乐的目的,提高我国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江续兵,谈基层群众文化现状[J],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01期
[2]谭国玲,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群众文化建设[J],科技资讯,2009年18期
[3]邵淑月,姚晓勇,郎爽,我国文化娱乐产品开发经验与休闲体育项目开发的思考[A],第二届全民健身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C],2010年
[4]石岩,浅析城市群众文化工作创新[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0年11期
[5]王慧军,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20届年会论文集[C],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