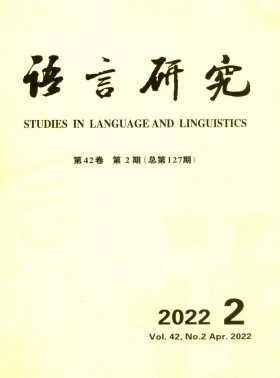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1
(一)文化理解力《培养标准》中(2)对文化理解力的阐释为:候选人(candidates)理解目标语文化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1)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够将外语学习目标中的文化知识框架整合到教学之中。文化理解力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候选人应获得从目标语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中所反映出的文化观知识。文化观是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本的学习、电影以及其它媒介、直接体验目标语文化而直接获得。这些知识和体验使候选人能够识别文化原型,并将文化知识与体验融合到教学之中;第二,呈现对文化观、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产物之间关系的理解力。文化观、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是外语学习目标语中文化知识框架的三个构成因素。文化知识的范围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地理、历史、宗教和政治体制、文学、艺术、媒体以及各种文化产物。候选人具备对目标语以及自身母语文化差异和共性的理解力,并能在教学中恰当地使用地道的文化素材;第三,鉴于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关于文化的概念,候选人能够对动态的文化进行了解并提出假说。候选人追求新的文化观,并通过分析新的文化信息拓展和完善自身的文化知识。新的文化信息来自文献和社会制度框架等;第四,候选人能够识别文化原型以及它们对学生文化概念的影响,并认同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体系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进行文化比较,包括:识别、分析、评价与目标语文化产物和实践相关的主题、观点和文化观。候选人能将目标语文化观、文化产物和文化实践信息呈现给听众;第五,候选人不仅将文化观、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作为自身的文化习得,还应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化,并将文化教学融入课程教学以及评价内容之中。
(二)文学修养《培养标准》中(2)对文学修养的阐释为,候选人识别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的价值与作用,并使用它们阐释和呈现目标语文化观。文学修养的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候选人广泛地理解和欣赏目标语传统。候选人能够识别主要文学作品作者、思想家、艺术家以及各种文化形象、文化角色和文化参照物。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和各种成人当代文学。候选人熟悉并能够在不同话语中诠释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这些作品和文本通常代表了目标语文化的传统和时代的变化;第二,分析、诠释和整合性阅读。使用文学传统知识诠释文化的时代变化。候选人能够将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与其它文学传统相比较。另一方面,候选人能够选择和调整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资源以鼓励学生参与为提高自身目标语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的活动之中。候选人通过独立和持续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阅读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和拓展文化知识。
(三)文化教学评价《培养标准》中(5)对文化教学评价的阐释为,候选人认定评价是持续的过程。同时,他们具备通过实施有效措施,根据学生年龄和语言水平,采用多种方法给予学生恰当评价的能力。文化教学评价的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尽管一般性测试可以达到评价的目的,但是外语交际和文化能力的评价需要独立的过程和评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方式均可使用。候选人应该理解正确评价学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时有意识地识别和使用上述两种评价方式。候选人还应该熟悉并正确陈述各种语言教学的能力标准指南,例如:《全美外语教学协会K-12学习者能力标准指南》(ACT-FLPerformanceGuidelinesforK-12Learners1998)、《全美外语教学协会能力标准指南———口语》(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Speaking1999)、《全美外语教学协会能力标准指南———写作》(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Writing2001);第二,候选人能评价学生习得的目标语文化观、文化实践、文化产物以及与自身文化的比较。寻求机会评价学生如何在课堂之外的文化语境中正确地使用语言。候选人也能将评价方式融入到常规课堂教学,并理解形成性评价常常包括在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多个领域。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启示
美国的《培养标准》从文化理解力、文学修养、文化教学以及文化教学评估四个方面对于职前外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内容阐述和衡量标准。职前外语教师文化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过程,即,基于文化知识的了解和积累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候选人文化分析能力、鉴别能力、比较能力和实践能力等,继而将这些能力与教学整合用以指导文化教学,并掌握多样的方法对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能力实施恰当的评价。《培养标准》对美国职前高质量外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培养提供了基于标准的指导。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也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在针对四川省中小学优秀英语教师跨文化意识现状的一项调查中[3],笔者发现目前在职的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现状不容乐观,存在如文化知识不足、缺乏系统性等问题;英语教学中对文化教学有所认识,但是尚未有系统的教学理论来指导具体教学实践;英语教师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环境和有效渠道。上述问题除了可以通过教师自身加强学习和参与职业发展培训得以逐步解决外,职前英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培养则是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的突破口。第一,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培养标准细则,明确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标准和内容。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英语教学应有利于学生理解外国文化,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进而拓展文化视野,形成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初步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4]英语教师作为英语教学的实施者,在英语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关注语言和语用中的文化因素、了解文化差异、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刘润清教授认为,外语教师培训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教什么”和“如何教”。“教什么”是对外语本身的培训;“如何教”涉及外语教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5]《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培养目标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
《大纲》将英语专业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英语专业技能类课程和英语专业知识类课程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其它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怎么教”的问题,但并未给出细化的分类指导。2011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虽然对于“如何教”,在教育类课程上给予了指导,但是并未有针对不同的学科教师教育课程的细化标准。显然,结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培养标准细则,明确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标准和内容,对于职前英语教师培养的教学实行更细化的分类指导,将有利于我国职前英语教师的培养在今后能有全面和更健康的发展。第二,逐步培养职前英语教师的思辨能力。2001年Anderson和Krathwohl对美国教育心理学家Bloom早期思辨能力的分类进行了修正和升级,形成了由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组成的改良版思辨能力类级模型。[7]根据此分类,笔者认为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中思辨能力的培养即是在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文化理解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其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来评价、分析和比较文化,批判地认识和接受各种文化观,从而能够客观地看待文化并接受文化本来的样子,继而尊重和欣赏多元文化,在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例如:大量文学作品、文化读本的阅读与赏析、结合各门课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组织课堂讨论以及增加文化时事评论等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敏感度、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文化意识等。第三,拓展文化视野、增加文化体验。语言是社会文化现象,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此文化也是动态系统。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除了依托文化知识类课程之外,应该将文化教学拓展到其它课程的教学之中。例如,结合课程中出现的文化点,通过英文报刊和杂志的拓展阅读来增加对文化现象的了解。同时,突破文化教育和体验主要限于文本与教学之中的现状,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交流类讲座,邀请外教或有海外留学或教学经历的英语教师分享英语文化和经历等;同时,积极开发与英语国家高校校际间交流合作项目,包括文化交流、海外教学实习项目等,增加职前英语教师对目标语文化的切身体验和教学实践经验。
三、结语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2
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在原来实验稿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基础上,将实验稿在“教学建议”部分提出的“在教学中努力体现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1]教学要求,直接放到了语文课程性质中进行了表述,而且在“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之前又专门加上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限制性定语。也就是说,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表述上,由原来实验稿提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四种基本属性(工具性、人文性、综合性与实践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语文课程的目标、任务与基本特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上述的这些变化?如何正确理解语文课程的这四种基本属性?在教学实践中,又如何正确处理这四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上面的这些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做如下解读:
一、“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生共进的关系
实验稿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关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基本理念,但对“工具性”和“人文性”究竟应该怎样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验稿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并没有作出具体阐释。所以,自实验稿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者究竟是谁统一谁的质疑。而事实也确实像质疑所提出的问题那样,一段时期,因为我们一味地强调语文课要姓“语”,强调语文是基础,是工具。结果造成语文教学只有语言文字训练,而“见语而不见人”,造成语文的“人文性”被“工具性”所“统一”;而另一段时期,又因为我们过分强调语文要育人,语文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与情感价值观的熏陶和教育,结果又造成了语文课成为思想政治课、品德教育课,造成语文的“工具性”被“人文性”统一的事实。如此这般,语文教学一直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摇摆不定,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厘清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要厘清这种关系,我们必须回到语文的源头,从语文课程的目标、任务和特点出发来进行分析和探讨。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是教学生学习母语,语文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此,从这两个基本点出发,语文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过程。语文作为母语的学习过程应该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对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只有正确理解并掌握了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具备了较强的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公民才能更好地进行交往和交流,才能培养起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的发展提出的文明要求。二是学生个体精神世界不断丰富。母语学习过程是学生精神自我培育的过程,是学生形成自我个性的生命体验过程,又是学生接受本民族精神文化熏陶的过程。[2]所以,课程标准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其实也就是强调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必须要有意识地把上面的两个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我们认为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也不是两者谁依附于谁的从属关系,更不是谁统一谁的消除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生共进的关系。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这种关系就像“工具性”与“人文性”两者在共同构筑起一座富丽堂皇的语文教育大厦,“工具性”是语文教育大厦之“基”,“人文性”就是语文教育大厦之“本”。只有首先引导教育学生把“运用语言文字”这个基础夯实了、打牢了,语文教育这个大厦才能真正矗立起来,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尽窥语文大厦的堂奥。“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关系。“工具性”若离开了“人文性”就像是只有地基却没有高楼大厦的“半拉子工程”,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地位与价值。“人文性”若抛弃“工具性”,那么,金碧辉煌的语文大厦就很有可能成为失去了坚实根基的空中楼阁,尽管看上去很富丽堂皇,却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二、“综合性与实践性”为我们指明了通向语文教育殿堂的正确有效的路径
如果说“工具性”和“人文性”共同构筑起了语文教育大厦的根基和殿堂,那么新课标提出的“综合性与实践性”,则为我们指明了通向这座教育殿堂的正确有效的路径。语文教育的殿堂巍然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又应该如何引领学生走进这座金碧辉煌的语文大厦,去领略其中美不胜收的精彩呢?
首先,强调“综合性”就是告诉我们,语文与数理化等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语文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语文课程的学习不能像数、理、化等学科那样单单追求建立完整学科知识结构体系为目标。语文课程虽然也有内在知识体系,但语文课的学习却不以追求知识体系的完整为主要目标,而以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核心目标。
其次,新课标对核心理念“语文素养”的阐释也进一步体现了语文课程的综合性。新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中对“语文素养”作了比较详细而具体的阐释:“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3]透过上述关于“语文素养”内涵的阐释,我们必须明白,语文学习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学习,语文学习必须实现“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多个维度的融合,必须进行“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学生的语文素养才能得到全面提升。
第三,强调“实践性”则告诉我们语文能力的提升、语文素养的形成,不是仅仅通过语文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就能获得的,语文知识的获得与语文素养的提升是不完全同步的,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与素养,在注重知识掌握的同时,必须依靠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语文教育必须树立“生活处处有语文,语文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大语文”教育观,语文教育要多让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在实践中学语文、用语文,而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在课堂上学习语文,学生的语文素养才能真正获得迅速有效的提升。
三、“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是对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更加明晰的界定
新版课程标准在“综合性与实践性”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定语。新课标为什么要特别加上这样一个具有明确指向的限制性定语?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这样一个具有明确指向的限制性定语?
首先,新版课标之所以强调“语文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这既是对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更加明晰的界定,也是对语文界一直争论不休,但一直又很难得出个一致结论的——“语文究竟是什么?”问题的正面回应。1949年,在叶圣陶先生给语文科命名的时候,因为叶老并没有给“什么是语文”作出清晰而明确的定义,所以关于“什么是语文”的问题,至今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有人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有人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有人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章,还有人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化等等。[4]诸如此类,当前关于什么是语文的解释大约不下十数种,而且一直在相互争鸣,并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本次课标修订组本着对语文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当前语文教育的实际出发,正面直接地对问题作出回应,应该说对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起到了一种正本清源的作用。
其次,新版课标强调“语文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个定语,其实也是对后面的“语文是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作出的一种限制。无论语文课程多么开放,无论语文课程进行怎样的跨学科的渗透与综合,语文课程必须坚持引领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这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立足点,也是语文学习的基本出发点,偏离了这个基本的立足点,语文课程就会丧失其应有的地位,沦为其它学科的附庸。
第三,新课标强调“语文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也是针对实验稿课程标准颁布以来,不少地方和学校,一味强调语文的“人文性”,而导致人文性甚嚣尘上,工具性严重弱化,致使许多语文课堂充斥着大量的“伪语文”和“非语文”的元素。语文“工具性”的严重弱化,致使中小学语文教学背离了语文课程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个根本的目标指向。本次新课标专门加上这样一个限制性的定语,也正是对实验稿课标颁布以来出现的新的认识偏差的一种及时而有力的矫正。
《论语》记载,子路曾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的话归纳起来表达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语文教学的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正名”的问题,只有把“什么是语文”、“语文的根本属性是什么”等问题搞清楚了,语文教学的目标才会更加明确,语文教学的任务才更加具体,语文教学的路径才会更加清晰,我们的语文教学也才能更加扎实有效。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
[2]王云峰.略谈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J].中学语文教学,2012(4).
[3]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3
本文试图从解构的概念、语言的重复性、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言语行为几个方面梳理德里达的文学批评实践。作为批评策略,“解构”就是通过重读、重讲和重新阐释发现某一系统内的功能失调,而功能失调的场所恰恰是这个系统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生机、进行新的发明和产生新的可能性的场所。重复或被重新占用就是“踪迹”作用的方式,也是决定文学作品之“文学性”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德里达 解构 批评策略
在《德里达的遗产》一文中,J.希利斯·米勒提出的问题是:德里达去世了,我们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产?这里的“遗产”当然指的是文化遗产,是他的全部著作,他的所想和所写,也就是可以用“德里达”这个名字称呼的单一个体的“全集”。所谓“处理”当然不是变卖,而是关乎其能否得到继承,能否得到正确的理解或“正确地占用”的问题。这是德里达在生前就曾经担心并在若干重要场合和后期几部著作中详尽讨论过的问题(其实也是米勒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他自己说从不在乎死亡和死之后别人会如何对待他的“遗产”)。现在,德里达已经去世近三年了,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产”呢?实际上,“处理”还为时过早,我们所面对的应该是如何整理他的遗产问题。本文试图简要梳理德里达的文学理论遗产,即他的文学批评解构策略。
一、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
在1992年6月30日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解构”这个问题①。德里达认为,应该首先把“解构”看作一种“分析”,分析的客体是“积淀起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话语因素,即我们用以思考事物的哲学话语性”②。在继续描述这个分析客体时,德里达说这个“哲学话语性”就是“思想的话语性,”是“我们”实际上进行操作的结构,它是通过语言发生的,因此与哲学史相关,也与整个西方文化相关。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在德里达的批评理论中,语言并不就是一切③。对德里达来说,语言是理性的,是他解构的对象;但当质疑西方哲学传统的时候,当挑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时候,当把柏拉图、海德格尔和马拉美拿来作为分析客体而证明某种不可能性的时候,他也必须使用同一种理性的语言。没有人能够摆脱语言的牢笼,没有人能够在语言之外达到解构语言本身的目的,更没有人能够在摆脱理性语言的情况下去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才说“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这也是他生前就力图澄清的一个误解。在德里达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解构”不过是他使用的一系列关键词中的一个。早在1982年“写给一个日本朋友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不愿意使用“解构”这个标签或不喜欢人们给予“解构”以种种特权,其实他所暗示的或许是“解构”这两个字不可能概括他的全部思想,不可能总结或“再现”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解构“是对不可能的事物的一次经验”,“承认解构是不可能的并不失去解构的任何意义”④。
实际上,德里达的“解构”所要破解、分析和对抗的恰恰是“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结构主义语言观⑤。解构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对抗”,“对抗语言学的权威,对抗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权威”⑥。本杰明认为这种对抗的立场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一种批评形式,对抗就是拒绝接受,而拒绝接受的对象是一种占主导的语言观,传统上语言与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第二个是拒绝接受传统在对抗的客体与对抗的立场之间拉开的距离,从而打开了另一个不同的空间。“其意义在于它含蓄地承认没有外部,所以,构成所对抗传统的一部分的语言和术语就成了参与和发明的场所”。这意味着所对抗的传统并没有被消除,而成了一个新的发明的空间,行动的空间,或者说是介入的空间。最后,场所的这种不可消除性就是解构的部分定义⑦。解构始终是一种介入形式,一个参与的策略,“解构不是用来发现抵制系统的方法的;相反,它包括对文本的重讲、阅读和阐释,使哲学家能够建立系统的东西不过是某种功能失调或‘失调’,无能封闭系统的表现。无论在哪里,当我采用这个研究方法时,都是要展示某系统不发生作用,而这种功能失调不仅颠覆了系统,而且本身激起了对系统的欲望,是从这种脱臼或失调中汲取生命”⑧。如此说来,“解构”就是通过重读、重讲和重新阐释发现某一系统内的功能失调,功能失调的场所恰恰是这个系统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生机的地方,可以从事新的发明的空间,也是产生新的可能性的希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也是一种重构、重写,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只不过它所重构、重写和肯定的系统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具有单一性、特殊性,因为不同系统的“功能失调”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同一系统在不同时间的“功能失调”也是不同的,因此重构和重写的结果也不同。于是又可以说,“解构”不是方法,不是工具,不是简单地把分析客体从属于某种机械的操作。“解构”是一种策略。
作为策略,“解构”具有使用的灵活性,定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多元性。正因如此,德里达才说“‘解构是X’或‘解构不是X’所有这类句子都先验地误解了解构的要义”⑨。“解构”的要义在于解构的过程所展示的生存困境,一种双重束缚,即在可能性中看到的不可能性,或相反,在不可能性中看到的可能性的希望。“解构”打开了无限重复的一个空间,使作为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哲学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质疑的空间,在对抗的过程中予以肯定的并在封闭时马上开放的一个空间。“它是行动的场所,因此也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场所”⑩。
二、作为语言之重要特征的重复
米勒帮助澄清了过去对德里达的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他的“解构”不是关于语言的思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没有关系,与“语言学转向”没有关系,因此不提倡“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绝对语言观和文本观。在语言与文本之间,德里达看重的是文本,而文本指的不是语言,不是语言结构,而是文字和文字的结构。最终,语言是通过文字结构而被理解和发生作用的,这是形而上学时代的一个历史必然。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说,“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问题。但它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侵入到最多样的研究和最异质的话语的全球景观中来”。“(语言)仿佛不顾自身地表明一个历史—形而上学的时代最终将把语言确定为它的总体问题的视野……语言本身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它已不再是自信的,平静的,不再受到似乎超越它的无限所指的担保”⑾。语言何以受到威胁?是什么威胁了语言?文字的出现颠覆了言语的君主地位,打破了语言的逻各斯即语音中心主义,摧毁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传统认定的那个纯知性的秩序,即语言符号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能指与一个可理解的所指之间的统一。然而,德里达证明,这样一个纯知性的秩序根本不存在,理想的、一看就懂的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文字本身的重复性宣告了符号的神学时代的结束,由于这种重复性,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都成了地位平等的交流形式:书面语言(文字)不再是派生的了,口头语言也不再由于其直接性而凌驾于文字之上了,二者都可以在接受者或说话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言语和文字一样也是可重复的记号。对如此理解的语言交流的一个必然发现是:凡是有语言交流的地方,就必然有误解(误读);没有误解,就不可能有交流,因为记号(语言符号)的重复决定了意义的不确定性。⑿
然而,这种重复性却也决定了文字的可读性,决定了口头语言的可理解性(这在电话、录音机、视频聊天的时代就更不难理解了)。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到语言的生产者的缺场:作者和说话者的缺场。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可以在其生产者缺场的情况下发生作用,这正是语言的主要特征,又由于这是文字或语音的重复性造成的,所以重复性就成了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它的基本条件是:文字要想成为文字,即成为一种可重复的记号,就必须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消失的情况下正常发挥作用,即被阅读,或在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不在场时仍被阅读,换言之,当信息的发送者或接受者不在场时,作为信息的语言(书面的和口头的)都应该具有在逻辑上仍然能被阅读的可能性;而当经验上可确定的发送者或接受者不在场时,结构上不可重读的、不可重复的信息就不是语言交流的记号。⒀
这种重复性也是“事件”得以交流的惟一条件。就结构而言,“事件”就像一个词,或一个文本,是可重复的,因为可以对“事件”单独加以阐释、讨论、讲述或重讲,而每一次重讲或重复都是一次增补,在述行的意义上都是与原事件相关的另一次“事件”,都在差异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事件的属性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的“书写”或“文字”就不纯粹是人们所误解的“纯文本”,而成了具有历史内涵的一个公共空间:就其重复性而言,作为事件的书写必须脱离原作者才能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才能成为它应该成为的语言的记号,就是说,话一出口就具有了被重复的特征,就脱离了说话者而面临着多次的增补和重复,也就是对所说的话的“绝对的重新占用”。⒁由此可知,任何符号系统都不能只被一次使用,任何话语或书写事件都不能不被重复,而在理论上,只被一个人说过的话而不被重复就不能算作语言的记号。
这种重复或被重新占用就是“踪迹”作用的方式。“踪迹”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相区别从而使符号具有意义的一个因素。要理解一个符号的意义,首先必须承认或认出与这个符号相左的东西,然后将其抹去,这个被抹去的因素就是踪迹,没有它,语言作为差异系统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因此,在德里达看来,踪迹是意义得以产生的绝对源泉,但这样的源泉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踪迹都必然是另一个踪迹的踪迹,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要想在正常的语境中发挥符号的作用,就必须转换或被重复而改变其语义的或述行的价值,成为另一个语境。实际上,语言符号的踪迹是决定文学作品之“文学性”的关键因素: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作品边界的位移;绘画的“艺术性”取决于“画框”的位移;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经验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的内部,而主要取决于作品的外部。外部渗透进来,决定了内部,而这个外部就是规定作品之单一性的习俗。
三、作为哲学研究之客体的文学
文学的存在就是要证明一种单一性,一种在哲学思想发生之前就存在的东西。⒂这不是说文学先于哲学而存在,也不是说哲学研究必以文学为无条件的客体或惟一的客体;而是说文学是德里达哲学研究的最重要客体之—:“我最长久的兴趣,应该说甚至先于我的哲学兴趣,如果这可能的话,始终是趋向于文学的,趋向于那种称作文学的写作。”⒃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才有一个被误读的德里达。罗蒂认为德里达是文学的哲学家,因此不是规范的哲学家,因为他把哲学看作一种写作,而不遵守哲学的规则。哈贝马斯也认为德里达“出于文学的、美学的或毫无根基的决定而放弃了真理的标准和判断”,即为了刻意的“书写”而放弃了“活的语境”,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因而没有认识到交往的理性。⒄米勒则认为,无论怎么看待德里达,都必须首先把他看作“20世纪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行为”见于他的全部著述,贯穿他的整个哲学和理论的写作生涯。⒅米勒进一步分析说,德里达对文学始终如一的兴趣并不是为了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而是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坚持语言的“重复性”,从而解构文学与哲学由来已久的对立关系。“对德里达来说,文学能够在无数的语境中重复任何话语、文字或标志,而且能够在缺少明确的说话者、语境、指涉或听者的情况下发生作用”⒆。实际上,这种重复也正是文学所要证实的那种单一性。
—般认为,这种单一性就是哲学和文学相互区别的地方,而实则不然。不妨说,文学是用语言构成的东西,是以各种样式或体裁虚构的东西,正因如此,文学才似乎与哲学划清了界限——哲学探讨的是真理,它研究的客体是真实的世界,是实际存在,对立于虚构和虚假的东西,因此也对立于作为虚构之结果的文学。然而,文学虽然是虚构的,但不等于不存在;虚构是存在的,不然就不能对立于真实。哲学探讨的是原始的真理,文学探讨的是“超越真理的真理”,即超越哲学真理的真理。文学的确是虚构的,这种虚构含有真实或至少是源于真实的成分,也有纯粹虚假的成分,但决不缺少真理。对德里达来说,文学不是可以拿在手里阅读的一本书,也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某种再现。文学创造自己的语境,发明自己的环境、事件或赖以存在的条件;它不去挖掘潜藏在某一文本内部的本质,而是用文字、词语、声音、踪迹、言语行为等建构一种单一性、偶然性、意外事件,从而使思想成为可能;它不再现外部存在或超验现实,而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声音呼唤人们去思考书写、文本性和互文性;去思考引语、重复、界限、隔膜、存在与非存在;去思考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法律、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所揭示的东西必然成为哲学思考的条件,文学所描写的东西必然是已经留下了踪迹的经验,文学所陈述的东西也必然是抵制我们阅读的东西。在德里达看来,完全可读的东西不具有文学的单一性。不可读性、不可译性或完全他性才是文学的根本。⒇
正是在这里,德里达看到了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共同点,同时也消解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文学之所以具有文学性,是因为它具备语言的最典型特征——重复;而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延宕造成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使之成为异质的、不透明的、不断延异的缕缕踪迹,所以,文学的文学性存在于文本之中,存在于书写文本的人的精神之中,也存在于书写的行为之中。这样的文本反映的不是人的原始感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所用的言语也不是作者或其文本所特有的,而具有历史性,受制于制度和习俗,也因此而拥有了说一切话的权利。在德里达看来,哲学是通过对文学的“模仿”才确立了哲学思辨的优越地位;用来讨论文学的一切话语,都可以用来讨论哲学,因为和文学一样,哲学也是一种书写,它本质上具备文学的全部结构。文学的书写反映真理,哲学的书写陈述真理。然而,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哲学中,总有无法接近的真理,总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总有意义的无限延宕或生成。如果说文学中的重复是创造场景、环境和事件,那么,哲学中的重复就是创造概念,能够重复的、可证实的、超越其具体现实而揭示真理的概念。
所以,文学和哲学一样,也不是模仿的艺术。德里达讨论的柏拉图的“药”和马拉美的“模仿”就力图从哲学和文学两方面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模仿论。“模仿既是艺术的生,也是艺术的死”(21)。在自然与艺术的等级制中,柏拉图的模仿论把艺术的模仿排在第三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把艺术的模仿排在了第二等,但无论如何,二者都设定了一个先于符号而存在的理式,一个有待模仿的自然,这个理式、这个自然也就是艺术家如实描写、如实反映的真理。然而,德里达认为这种先于符号的“世界”并不存在,纯粹的感知并不存在,所揭示的“现实”也不存在。我们所知的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符号污染了现象的原生态,符号创造了自己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创作)的主体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系统”(22),由精神、社会、世界组成的一个关系系统。马拉美的“模仿”从文学的角度证明了模仿的客体的模糊性,呈现了文本镜像的生成游戏,展示了“模仿”本身在书写过程中的空间生产。它所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是:模仿者最终没有模仿的对象;能指最终没有所指;符号最终也没有指涉。模仿、能指和符号最终都是用来理解真理的工具。(23)
《柏拉图的药》讨论的是希腊术语pharmakon(药)的翻译问题,分析了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即从翻译问题入手进入哲学的探讨,指出该词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思(良药和毒药),从而反驳了苏格拉底高扬言语(对话)而对书写(文字)的攻击。(24)在德里达看来,翻译起源于翻译或任何可译的命题。一方面,翻译的可行性取决于意义的确定性,而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真理和意义,所以,在翻译无法进行的地方,哲学也必然陷入死胡同;另一方面,哲学有自己具体的语境。西方哲学有史以来始终以希腊哲学为基础,使用的大部分是希腊哲学的概念,一旦脱离了希腊哲学这个语境,pharmakon的意义不确定性问题就出现了,给异质性或他性留下了缝隙。因此,与文学一样,哲学的语境不可能是封闭的,而必然是向另一种语境敞开从而创造出新的语境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哲学的阅读和理解就如同文学的阅读和理解一样是以播撒为形式的。播撒不是意义的丢失,而是无穷的替代、增补和肯定,是片断的、多元的、分散的,一句话,是文本意义的生产。
四、作为言语行为的文学
德里达在学术生涯的中期就开始关注文学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问题。米勒认为要了解德里达如何定义文学,捷径是理解他的言语行为理论。(25)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ABC有限公司》等著述中最早提出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是针对J.L.奥斯丁对戏剧独白等文学言语的排斥而提出来的。(26)如上所述,在德里达这里,重复性是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因此也是文学语言的最重要特征。一方面,重复是语言借以使自身脱离现实的语境而进入虚构空间的手段;另一方面,重复又是文学借以使自身脱离虚构空间而进入民主的空间、自由的空间以及话语、符号和书写得以不断重复的一个空间的有效途径。这个从现实到虚构、再从虚构到现实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重复,而重复的结果既是述愿的又是述行的,既是阐述真理的又是可以促成具体行动的。这是德里达所说的真正的文学性:特定作家在特定社会中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用语言虚构的东西发生了特定的社会作用。正因如此,他才说文学的文学性不在文本之内,而在文本之外,也是他所说的文学文本的大门“向完全的他者敞开”的意思。这种文学性也以其他方式见诸政治、伦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文本,《文学的行为》一书通篇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按此理解,文学中的言语行为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独立的宣言或他者的发明”(27)。这种言语行为是用词语和符号建构起来的形象、场景和环境,是内在印象和经验的具体化,因此是异质的、矛盾的,包含着言语与行为、逻辑与修辞、已知与未知、可见与不可见等二元对立的因素。作为美国的解构主义大师,米勒发展了德里达的文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阅读理论,不仅强调文学的述愿方面,而且强调文学的述行作用。这意味着,读者在建构文学文本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聚焦于文本的“言语”本身,理解其真正的意思,而是它的潜在意义,试图把它重构成新的东西,结果必然是言语向行为的转化,虚构空间向现实空间的转化,也即文学向社会的转化;通过伦理的和政治的阅读过程,这种转化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新事物的出现。这种文学批评不再把语言看作能指的聚合,不再聚焦于文本的结构和形式的分析,而着重于文学语言如何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世界观进而创造新的社会生活范式的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里达发表了许多论纲式的小册子,如The Other Heading, Force de loi, Archive Fever, Monolinguism of the Other, Adieu to Emmanuel Lévinas和Demeure等,讨论言语的述行概念,述行话语的实践,以及言语行为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并将其与决策、行动、秘密、证据、好客、谅解、义务和责任等政治和伦理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德里达晚年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探讨的是文学或文学研究在政治和伦理责任中的作用,言语行为在文学中的作用,而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人文学科以及大学的未来。在《无条件的大学》中,他说“文学是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也可以是保守秘密的权利,哪怕是以虚构的形式”(28)。他认为今天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人文学科,正面临着种种威胁,因此“要求无条件地说一切话的权利……也包括文学……”,“这种假定的在公共空间里说一切话的自由,是所谓人文学科所特有或独占的地方——对这样一个概念的定义还要加以精炼、解构和调整,使之超越一个也需要锤炼的传统。然而,这个无条件的原则原本而且最突出地在人文学科中呈现出来。它占据一个本源的、特殊的位置,即在人文学科中表现、显示和保存的位置。它也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重新叙述的空间。所有这些都通过文学和语言(即被称为人的科学和文化的科学的学科)表现出来”(29)。这或许是德里达终其一生研究文学进而研究哲学的宗旨,也是他利用“解构”进行的一次“策略性赌博”。如米勒所预测的:“如果他赢了这次策略性赌博,那么,这将意味着他的著作将改变所有世界规模的不同语境,这样,他的著作,虽说独特和个异,但却能在未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广泛的不同语境中取得述行的效果。”(30)
*本文为纪念德里达逝世三周年而写。
①②⑥⑦⑩Benjamin, Andrew, “Deconstruction,” in Malpas, Simon and Wake, Pau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81, p.82, p.82, pp.8283, p.89.
③Cf·J. Hillis Miller, “Derrida’s Remains”.
④Derrida, Jacques, “Psyche: Inventions of the Other,”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n Peggy Kamuf (ed.),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209.
⑤Cf·J. Hillis Miller, “Derrida’s Remains”, 和Benjamin, “Deconstruction,” p.82.
⑧Derrida Jacques, with Maurizio Ferraris. A Taste for the Secret. Trans. From French and Italian by Giacomo Donis. Giacomo Donis and David Webb (eds.), Cambridge: Polity an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1. Cf·J. Hillis Miller, “Derrida’s Remains”。
⑨(12)Thomson Alex, “Deconstruction,” in Waugh Patricia (ed.), An Oxford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01, p.305.
(11)(21)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 p.297.
(15)Ranolds Jack and Roffe Jonathan (eds.) Understanding Derrida (Continuum, 2004).
Ranolds Jack and Roffe Jonathan (eds.) Understanding Derrida, p.76.
(16)(25)转引自Hillis Miller, “Derrida and Literature,” in Tom Cohen (ed), Jacuq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20)(23)Colebrook Claire, “Literature,” in Ranolds, Jack and Roffe, Jonathan (eds.) Understanding Derrida, p.77, pp.7677, p.80.
(18)(19)Miller,“Derrida and Literature.”
(22)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1978), p.429.
(24)Derrida,Dessemination (London: Althone, 1993).
(26)Cf·J.L. 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注重
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学进行深入验证,并从中思考历史问题,更好地引导学生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思想,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加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树立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对民族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感情,协调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使二者更好地接轨,有利于促进文化传承中进行创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现状不容乐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实用主义以及功利思想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逐渐导致中国古代传统文学发展面临着困境,一些学生完全为了考试、求职去学习相关知识,但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较远的距离和差别。因此,许多中文专业学生单纯地为了修满课程学分来进行学习,没有深入研究和探索这门课程的精髓。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地,无法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必须加快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才能改变当前现状。
一、注重专业课程间的关联性
在我国高职院校中,开设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包含的课程种类比较多,在所有的课程类型中,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分别分为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等各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大学生入学之后的四个学期,然后在每个学期中分别设置了54-72个学时的课程时间,教师对这些时期的文学史进行讲授,能够让学时清晰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学生对不同历史时期下的文学作品展开深入学习,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对作家的思想观念有着更加深入的认知,从而更好地掌握我国古代文学特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在中国古代汉语课程完成之后,继续开设现代汉语课程,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主要为了让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文字、音义和字形语法,深入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从而具备良好的汉语言文化修养。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所以在第一学期同步开展古代文学和汉语教学,才能让两门不同课程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在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不同课程的教师需要加强沟通、交流,加深二者之间的联系,才能从整体上培养学生的语言和文学素养,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
二、注重培养教师的授课能力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分为四个阶段的内容,所以需要安排四个不同的教师来分为不同阶段进行讲解,虽然教师在不同阶段的文学课程讲解上非常优秀,但是也会把整体的汉语言文学史进行割裂,不同阶段的教师只会负责自身范围内的教学任务,非常熟悉某一专门的课程,但是没有深入了解其它分段的文学史内容,结果导致各个分段的课程内容无法联系起来,讲授过程中产生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造成了不利影响,经常导致前学后忘的现象出现,把汉语言文学史知识结构打散,无法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素养。因此,高职语文教育专业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产生,开设了古代文学的课程,基于高职语文教育专业需要和关于古代文学课改革思考,及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全面培养,以改革和发展要以学生能力训练为宗旨,除了情境教学,教师也可以大胆尝试项目化教学。
三、注重处理文学史和作品之间的讲授关系
目前,在高职语文教育专业开设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大多采用文学史和作品进行密切结合,对文学史和作品进行同步讲授,这种授课的方式能够节约大量的课时,而且能够使教学内容更加凝练,但是无法协调处理文学史和作品之间的讲授关系,讲授过程中比重很难进行平衡控制,如果多讲文学史,或者多讲作品,都会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记忆出现偏差。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以学生诵读文学作品作为出发点,在诵读中积累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让教师更加精简地讲解叙事作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
四、注重应用情境教学法
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非常枯燥、乏味,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必须加强应用情境教学法,教师根据课堂内容需要设计合理的教学情境,因材施教开展教学活动,利用音乐、画面、语言以及表演来呈现古代文学作品,才能加强学生的情感认知。例如:在学习《离骚》时,教师可以设置《离骚》的背景音乐,通过采用独特的音乐旋律,能够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屈原的爱国精神,体会作者丰富的感情思想,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达到知、情、意合一的教学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四个“注重”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教学改革工程中,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手段,不断探索,才能提高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杨钊.基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高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25(6):135-137.
[2]张亚军.试论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为中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98-101.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5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包括凤凰网、新浪网在内的各大门户网站,也迅速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喜讯,并配以专题报道,其内容之齐备、角度之多元,令人叹为观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堪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说到底是一场体育的盛会,而上海世博会,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工业文明的展览,这两项盛事虽是崛起后的中国的集中亮相,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中国文明的最深的内核,中国更渴望在文化而不是体力或者器物的层面被世界所认同。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人们自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多了一份更深的感情和期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作为一个民族精神魂灵的文学和文艺对于一个急于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已经厕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来说,它太需要一张世界文化殿堂的入场券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来得正是时候!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似乎只有放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百年旅程中加以审视,才能窥见其意义。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习惯了以西方为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或者一路狂奔或者茫然四顾的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似乎就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理不清扯不断的关系的某种隐喻。似乎只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文化才能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才能在西方的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中国作家所形成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因期盼而失望,因失望而怨恨,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世纪隐疾,年年发作。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法持有正常的心态,要么极力吹捧,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故作讥诮之语,莫言获奖,无疑缓解了这种世纪心病。相比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全国之力,莫言的获奖,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力量,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似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然而,文学说到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对莫言获奖的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他作品的解读才能加以体味。不可否认,莫言的成就,与他的包括《红高粱》《檀香刑》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品中立足于地方文化的精神原乡中,所展现出的奇崛而瑰丽的想象力、肆意而丰饶的语言有关。他的为他赢得巨大文学声誉的作品,恰恰都是与现实、政治和主流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作品。不仅如此,莫言的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的文学世界所有意秉持的一种退步的、民间的、反启蒙的文学审美立场,恰恰是与百年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的、启蒙的、进步的文化方向相左的。这种倾向隐藏在莫言的创作轨迹中,从早期向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学习,到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莫言表现了一种东方式的智慧,一个本土作家的文化自觉———基于对本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清醒认识之上的文化自觉。深蕴于作家创作底气之上的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谦卑、内省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信。正如评论家葛红兵先生所说,“莫言的获奖,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失败,他正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之外,为21世纪人类文明开掘出另外一种新路来?
然而,要清晰认识莫言作品的价值,我们还必须将之与诺奖竞争对手村上春树作一点比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呼声最高的两位作家是莫言和村上春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关于中日这两个作家水平之间的评判,又夹杂着非常复杂的民族感情。因为虽然文学可以超越国家和种族,但是文学评奖受到文学之外的政治、国族等因素的干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向来以小资作家示人的村上春树,自前年推出三卷本的《1Q84》,借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以隐喻的方式、感伤之风格对人类受到极权统治的威胁给予深切的关注,其呈现出的现实关怀让人为之震撼。而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在莫言的新作《蛙》中读到这样的震撼,虽然莫言看上去很讨巧地选择了一个很让西方人感兴趣,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的主题,但是他的立意中所谓的演义式的救赎,并没有石破天惊式的创见,而对于自己最拿手的东方式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却又因为毫无节制,而流于飘忽。今年在中日两国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村上春树在日本最大的、最主流的报纸《朝日新闻》中著文《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对日本政客的行径提出了批评,表达了对狭隘的民族情感可能会带来中日文化交流之路的阻隔的担忧,这大概是东亚领土之争以来,在政府和民间之外,最为独立和清醒的声音。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表现,特别是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中的一些过激的行径的失语,其高下立现。
二
莫言获诺奖,既是一件文化事件,又是一件文学事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事件。区别在于,作为一件文化事件,人们关心的是文学之外的作家的身份、荣誉、经历等文化因素,它们要纳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序列中,与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消费文化运作方式紧密相连。而作为文学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莫言作品本身,是莫言小说中那些明显具有个人烙印的文学气质———恣肆的语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和肆意燃烧的生命热力,以及在复杂的文学意象之后所要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深彻的洞察,特别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的纠葛中对于人文中国的深度挖掘。
但是,从网络传递的信息看,莫言获奖越来越成为一件文化事件。几乎从传言开始,网络媒体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几乎与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同时,凤凰网推出专题,刊登了许子东、程永新等一些学者对莫言获奖的评论文字,时间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感觉这是早已精心策划、安排、导演好的游戏,一切安排就绪,只待主角粉墨登场,而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莫言获奖消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2300万次。在获奖之前,莫言的关注度仅仅是韩寒的十分之一,获奖后,莫言的搜索量瞬间反超韩寒10倍。与此同时,莫言获奖后,作品洛阳纸贵,即使出版社开足马力,也是一书难求,而且一夜之间,莫言的手稿也暴涨百万元。而莫言的故乡也似乎嗅到了这种商机,正下大力准备整理莫言的旧居,试图作为红高粱文化品牌的一个景点挖掘出来。不仅如此,语文出版社也不失时机抛出绣球,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莫言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似乎更像是一场迟到的文化追授,意味着莫言作品正式进入了官方承认的经典体系,并正式被“写进了民族阅读的伟大传统”中。而莫言和张艺谋、姜文20多年前在《红高粱》拍摄现场光着上身的一张旧照片,也被翻了出来,被娱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回。更有消息传出,莫言作品将登上明年的春晚,与赵本山同台演出。
莫言和韩寒,一个是纯文学作家,一个是偶像作家,分属两个类型,莫言跟赵本山,更是扯不到一起,其在网络上关注度的变化,更像是大众的一种应急反应,并不能说明什么。然而,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一朝成名天下知,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却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文化现状。人们对莫言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真实的文学审美趣味,特别是对于具有精神探索性的文学艺术的真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纯文学萎靡现实的原因。在这场狂欢式的大众礼赞中人们各取所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至于莫言作品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的内涵的挖掘,恐怕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去关心。
大众如此,再看看文化精英的反应。曾几何时,随着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公布揭晓,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指责和批评便一浪高过一浪,其所表现出的集体性的焦虑和狂躁,也算是一道风景。而今莫言获奖,评论家们却集体转向,众口一词唱起诺奖的赞歌。其实,诺奖的评奖标准和口味并没有变化,只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么?
不仅如此,莫言的获奖,无论是曾经的批评者还是赞成者,都不吝用最美的词语加以礼赞。莫言获奖的消息甫一公布,就有人撰文称这是诺奖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其实,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授奖词中就可以看出,诺奖选择莫言,更多是基于西方世界所认为的莫言所建构的东方乌托邦神话的好奇,而不是基于中国当下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由衷接纳和认同。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又有人跳出来说,多年之前就曾预言莫言会获奖,甚至有人放言中国文学的第二春来了。此的心态真是了得,要知道两年前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论引发的争论还言犹在耳。从自卑到自大,中间只隔了薄薄的一层纸,中国人的心态转变得也太快了!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奇卡诺文学;后现代主义;解构;重构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美国新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杂糅特征,兼具拉美文学和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特征,体现了西班牙殖民文化和美洲土著文化的杂糅,以及美国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和西语裔文化的交融,这就是其独特的“三种文化”渊源和“二次杂糅”的经历。
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沿袭了拉美文学的某些手法,结合美国多元文化的现实,综合运用多种非传统的叙事手段。尽管学术界对于“后现代”的定义存在较多争议,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些手法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的文学再现手段,鉴于其鲜明的“去中心化”、“反讽”和“解构”等特征,将其认同为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在文本中的具体运用,来解读奇卡诺文学如何利用语言和多重叙述来书写以文化杂糅为基础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
一、颠覆与重构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语言和表达的扭曲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者社会”中,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抹杀一些重要的分界线,特别是高雅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之间的传统界限”[1]。当代奇卡诺文学采用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手法对中心和权威进行解构,采用詹明信所说的“零散性”结构表现主体的消亡,将众多的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物穿插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西班牙语的穿插使用外化小型叙事的功能,实现对元叙事及其权威的消解。
当代奇卡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另类话语”和“自我历史”的叙述方式。文化差异及政治、经济矛盾冲突曾使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带有很大的偏见,韦伯(walter webb)在《德克萨斯骑警》中使用“凶残”、“野蛮”和“贪婪”等字眼来评价墨西哥裔美国人,集中体现了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帕雷德斯(américo paredes)的《枪在手上》对德克萨斯边疆的科瑞多民谣《科尔特兹之歌》进行了整理,从墨美人的角度重述科尔特兹和德克萨斯骑警的冲突,塑造了敢于反抗压迫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形象,有力驳斥了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的歪曲。赛勒斯·帕特尔对此类现象评论道:“美国新兴文学作品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多里斯所称的‘自我历史’:由于某些特殊群体的故事被美国‘标准历史’排斥在外或者加以篡改而在这些群体内部撰写的历史……美国历史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自我历史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它通常延伸到美国立国以前很长时间,而且往往发源于美国边界以外的各个领地”[2]577。创造“自我历史”包含着对权威和霸权的颠覆,同时也包含了自我身份的重建。
“重构”同样是当代奇卡诺文学的重要特征。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真理、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挑战,是一种“深奥的、去中心化的、没有根据的、自省的、谐谑性的、衍生性、折中的以及多元性的艺术”[3]。哈桑(ihab hassan)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解构”和“重构”。奇卡娜作家、理论家安扎尔多瓦(gloria anzaldua)在《边疆:新生混血女儿》这部“自传作品”中提出了“边疆”意象和“新混血儿意识”,其基本意旨遵循了“解构”与“重构”两个过程的整合。虽然大多数学者把安扎尔多瓦的批评理论划归到后殖民主义批评,但是《边疆》“支离破碎”的叙述结构、看似随意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交叉使用以及通过这些手段所强调的“中心的消解”都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这印证了韦斯特(cornel west)将种族问题嵌于后现论之中的观点,他强调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所强调的差异性、边缘性和异质性是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中心问题。由此来看,那么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的确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尽管很多奇卡诺作家和批评家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影响了墨美人对主体性的追求,但事实上,奇卡诺作家在创作中又借鉴了某些后现代主义手法,如上面所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因为这些手法可以为“他者”提供话语空间,实际上使族裔文学获得主体性。胡克斯(bell hooks)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身份”的批评恰恰有助于重构不同的身份,而所谓的族裔身份不过是主流文化群体对族裔群体的偏见。她说:“后现代主义总的影响就是,现在其他许多族裔群体即使没有相同的境遇,但是也和黑人一样有着孤立感、绝望和怀疑,没有归属感。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唤醒人们去关注这些超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共同情感,而这些情感能够成为构建相互认同的沃土,促使人们认识到共同的义务,并成为团结和联盟的纽带。”[4]墨美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实践了这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言都带有明显的解构性和重构性,较鲜明地反映奇卡诺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
《边疆》为这种颠覆与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应用实例。这部所谓的“自传”包括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语言以英语为主,夹杂着西班牙语、南德克萨斯方言和土著语言,这种“语码转换”集中体现了作者所谓的“边疆语言”。另外,文字的编排打破传统,采用了“拼贴画”风格,外化了文本的“反传统”主旨,展现了叙述者/作者作为“奇卡娜”、“女性”、“作家”和“女同性恋者”多重复杂的身份。很多评论家把安扎尔多瓦称为“激进的女同性恋者”,然而叙述者却明确地说:“同性恋是我的选择(对有些人却是遗传特征)”[5]。显然,叙述者对同性恋身份的“选择”是其主体性的体现,是对奇卡诺主流思想的宣战:作为“他者”中的“他者”,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可以让她进一步了解历史之外的历史,使她得以了解与平衡奇卡娜的二元性身份,反抗主流文化和奇卡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伤害。她生活在各种边缘文化身份的交集之中———既不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也不完全认同于墨西哥文化价值观,而是综合不同的身份,克服多重边缘身份的局限,对不同的文化身份进行全新的阐释。所以,她希望用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来综合多重身份所产生的张力,汇集出更强大的合力,赋予自己主体性和话语权,从而实现对男性权威和文化霸权的挑战和颠覆。
二、去中心化叙述
与“颠覆”和“重构”主题密切相关的叙事方式就是解构权威的“去中心化叙述”,较常见的叙事形式有多个叙述视角的转化、“碎片式”叙述,复调叙述以及梦境叙事等。“碎片式”叙述相当普遍,希斯奈罗斯(sandra cisneros)的《芒果街上的房子》等文本通过这些形式表现了对叙事权威的挑战和文化杂糅为基础的自我重构。
《芒果街上的房子》由46篇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墨西哥裔女孩雅斯贝兰莎作为叙述者将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讲述其在墨西哥裔社区中成长的故事。小说有别于欧洲传统成长小说,也不同于奇卡诺文学经典中的成长小说和家族历史小说,而是反映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杂糅,并从女性角度对种族和性别身份加以界定。一方面,“芒果街的房子”象征着贫穷及其对主人公心智发展的束缚和伤害;另一方面,“房子”是归属感,也是墨美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羁绊。小说开始时雅斯贝兰莎对房子的渴望代表了她对自身物质生活的追求,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在她身上得到内化,破旧的房子成为她的自卑心结。即便如此,她已开始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在“我的名字”中,她接受了祖母的名字,但是也决心冲破家庭对女性的局限:“我继承了她的名字,但是我不想继承她在窗前的位置”[6]。雅斯贝兰莎还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希冀的房子不仅属于她本人,书写的自由也代表了无数沉默的兄弟姐妹。在“阁楼上的流浪者”中,她表现出要为流浪者提供庇护的希望,因此这里的“房子”已经成为她和奇卡诺民众交流的桥梁,是叙述者用文字创造的奇卡诺人的精神家园。
去中心化的叙述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权威的解构,尤其体现在奇卡娜文学中对墨西哥女性原型形象的重构,如“哭泣的女人”,玛琳琦和瓜达卢佩圣母等。安扎尔多瓦在《边疆》中将这些女性形象追溯到阿兹特克地母神科亚特利库。
这个掌管生死和善恶的女神是矛盾的综合体,安扎尔多瓦提倡的“地母神的境界”是对三个女性原型的综合,剔除了消极、被动的因素,褒扬其积极成分,创造出女性新形象“蛇女”。这既是对基督教“蛇”之形象的改写,也是对阿兹特克文化中雄鹰与蛇之间关系的颠覆。奇卡娜文学就采用了这种综合矛盾、跨越边界的立场,通过使用“碎片式”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确立多种叙事声音和多重身份。
阿纳亚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创造神话,通过梦境叙事和普通叙事的交替来实现。小说中运用土著信仰、民间医术等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神话暗示的手法,在传统上被解读为“魔幻现实主义”。希克斯(emily hicks)认为这个术语没有摆脱西方思想中二元对立的束缚,而事实上,此种手法只是消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本文以此采用“创造神话”一词,从消解二元中心的多元化视角对现实和人类在“矛盾中生存”这一论题进行探索。就文本而言,它强调奇卡诺文化中的土著传统,提倡人们只有重拾历史的记忆,才能从现实的矛盾中找出契合点,从而探索生存的现实。民间药师乌勒蒂玛是神话原型中的“智者”和奇卡诺文化中被神化的祖母形象,是连接现实世界和灵性世界、基督教和土著信仰、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在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斯的成长中发挥了精神导师的引导和媒介作用。小说中穿插的十个梦境叙事是安东尼奥无意识的体现,存在于他理解自己族裔身份的集体记忆之中。“创造神话”的手法使得文本超越了奇卡诺群体的经历,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奇卡诺群体超越矛盾、寻找和谐的经历。堪诺莎(theresa m.kanoza)也强调了文本的普遍性意义,即智慧与经历允许人们超越差异、寻求和谐。一定程度上说,文本通过梦境叙事和现实叙事的穿插交替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实现了对现实的解构。看似神秘的民间医术其实根植于印第安文化中对灵性世界的信仰,即世间万物的灵性和人类的灵魂相通,自然和人类融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也颠覆了主流文化中的“人类中心论”。
三、“反讽”在虚构性自传中的运用哈桑认为“反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哈琴(linda hutcheon)同样视其为后现代表现手法的一个核心。
《记忆的饥渴: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的教育》是罗德里格斯三部自传作品中的第一部,一直是奇卡诺文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由于叙述者在自传中反对双语教育和赞行动,作者本人受到严厉抨击,被视为奇卡诺文化的背叛者。这部“自传”被奇卡诺文学界视为背叛族裔文化的宣言,而被主流文化群体视为美国平等与自由理念的成功实践。这部作品反映出部分奇卡诺作家从文化边缘向中心靠拢的事实,以及奇卡诺人在寻求社会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罗德里格斯把《记忆的饥渴》称作“自传”,但是这部作品螺旋式的叙述结构和多重叙述声音使叙述者和作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暗示了叙述的不可靠性。同样,迈克坎娜也提出一个“反论”:“正是因为罗德里格斯的第一部自传,我们才不知道他到底是谁”[7]。这就证明了奇卡诺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虚构性自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述策略,本身就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
表面看来,自传描述的是叙述者从“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孩子”成长为“美国化的中产阶级”的上升过程。而事实上,深层叙事结构却是循环式的,这就产生了文本最基本的一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叙述本身的真实性。同时,叙述内容自始至终以奇卡诺文化为中心展开,分别从教育、自我奋斗、宗教、肤色和职业等六个方面对奇卡诺身份进行论证,文本因此成为奇卡诺文化身份的一种话语表征。自传的螺旋式叙述结构、多重叙述声音、叙述中的矛盾与空白都能够证明叙述具有不可靠性。表面看来,叙述者接受了主流文化、背弃了奇卡诺文化。然而,学业的成功却带来了记忆的饥渴和一次次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述者接受的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状况:他背叛父母的文化,将自己局限于中产阶级的主观自我之中,话语权没有使他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他才通过语言再现这种异化。叙述文本成为叙述者构建“边缘”文化身份的媒介,同时也是对“记忆的饥渴”的否定,再次证明了叙述结构中的矛盾。通过叙述话语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看出,自传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也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者将自己在上流社会中的形象比作棕色皮肤的“怪物”,凸显他格格不入的“无部落者”身份,也是他对自我背叛的嘲讽。撇开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差距不谈,仅仅从叙事结构的前后矛盾中就可以证明自传文本事实上是哈桑所说的“反讽”与伊格尔顿所谓的“谐谑性”[8]。
这种反讽与前面所论述的颠覆和重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美国的白人主流文化要保持权威地位,势必要努力消灭族裔文化的影响,利用其权威地位对边缘文化进行主观性的规划和改造。虽然这部自传作品表面看来从语言到文体和主题都遵循西方文学的传统,但其深层叙述结构却反映主流文化对墨美文化的同化压力。叙述者必须在父母的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做出选择,然而这两种文化不是势均力敌的,归根结底,主导他生活的就是一种文化———主流文化。他要么接受主
流文化的改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要么被其淘汰而成为无形的、没有声音的奇卡诺民众中的一员。实际上,对于任何有机会进行选择的奇卡诺人来说,这种选择几乎不带任何悬念,但也是无奈的。相比之下,白人中产阶级无需做出这种选择。因此赛勒斯·帕特尔认为:“它(自传)所记述的内容(几乎不管它承认与否)正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所造成的损害”[2]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