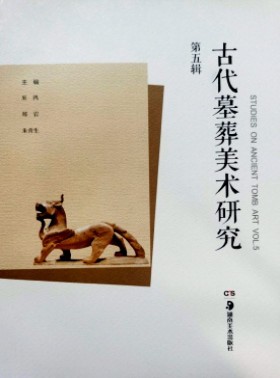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古代文化常识大全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古代文化常识大全范文1
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古代文化常识大全范文2
关键词:先秦;道家;庄子;礼学;秩序;礼乐制度
正像任何文明、文化现象是双刃剑一样,礼在真实的情感被逸出,只剩下外在形式的时候,也就是礼走向工具化的时候。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一般学者提到庄子的礼学观,多根据外、杂篇少数篇章的激烈言辞,认定庄子学派反对仁义礼乐的立场。其实,当我们将庄子放入战国的礼崩乐坏的文化背景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是多数人直接践踏礼乐制度,使得昔日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乐制度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是部分汲汲于推行“世俗之礼”的儒者,在片面地维护礼中,使得礼的形式化乃至异化的情势更为突出。这样,践踏礼与维护礼,都不同程度地使礼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状况使得儒家阵营里“大醇而小纰”的荀子,也忍不住对当时的“俗儒”、“贱儒”发出强烈的指责,更何况是崇尚“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庄子呢?
庄子指斥礼主要是针对礼的种种弊端而发的。从礼存在的合法性看,世俗的礼往往成了“禽贪者器”(《庄子·徐无鬼》,以下只注篇名)[1]。在仁义礼乐被肆意践踏的现实中,执政的统治者都是“大盗”,无论圣人发明了什么好的规章制度,他们都会巧妙地据为己有,并用来奴役、剥夺他人,使他人失去自然之性。圣人与“禽贪者”之间,往往展开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智慧较量。当圣人“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胠箧》)。于是,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同是偷窃的行为,大盗与小偷承受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成功的大盗,可以作威作福,号令天下;小偷小摸却要冒着杀头的风险。作为理论的“圣人之道”表现出了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普通人得不到圣人之道,固然无以立身处世;另一方面,像盗跖这种恶人,如果没有圣人之道的指导,同样是难以成为大盗的。从现实来看,“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胠箧》)。所以,所谓圣人之道,充其量不过是为窃国的大盗提供理论基础而已。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仁义仅仅是权势者替别人设置的行为规范;他们自己是不受此约束的,权势者甚至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本身就是人伦关系的践踏者。庄子对这类言不顾行的儒家礼学理论更加深恶痛绝。“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盗跖》)无论明君贤臣,还是各代推崇的圣人,他们给人们作出了极坏的榜样。儒家在推行仁义的过程中,明显地执行着双重标准,他们口头上将亲疏、贵贱、长幼等五纪六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把这些抛在一边。在庄子的慧眼中,尧杀长子、舜流母弟时,他们有谁讲究过什么疏戚有伦呢?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那里还讲什么君臣之义呢?而“王季为适,周公杀兄”,不同样是践踏了长幼之序吗?如果儒家所鼓吹那套疏戚之伦,贵贱之义,长幼之序,本身就被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所践踏,那又怎能指望百姓去遵从呢?庄子借盗跖之口,抨击儒家心目中的尧、舜、禹、汤、武王、文王,认为此六子“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盗跖》)。这里除非议了儒家心目中圣王的非礼行为外,还认为他们所作所为的动机,都是为利所惑,是为了私利而不惜违反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是对人本性的一种侮辱。
庄子对那些“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的行为是极为鄙薄的。他认为那些“掌权者”往往看重自己的权力,凭借一己的好恶,对于敢于不顺从自己意愿的不合作者,则大开杀戒,这是一种典型的“欺德”行为,尤其在他们自己的作为与其言论背道而驰的时候,更是如此。在庄子心目中,“圣人之治”不是靠外在的规矩强民就范的,而是让百姓依据自己能力的大小去干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因而,庄子不主张用“仁义”之类的东西来救世,认为那是多此一举。他认为,“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徐无鬼》)。因而要求让百姓充分发挥“自化”的功能。
在庄子看来,百姓是易治的,百姓的要求是很低的。一旦统治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利仁义者众”就是说庄子并不是反对仁义本身,而是感慨于仁义成了人们取利的工具,这样后世若出现“人与人相食”的惨剧,那正是尧这类统治者“畜畜然仁”(《徐无鬼》)的结果。庄子把神农氏时代的治道与尧舜禹文王的“仁义礼乐”治道相较,认为神农氏的作法更符合人性,更能体现道的精神。在神农氏时代,他们对神按时祭祀,极尽恭敬,却不祈福;对人民,极尽忠信,却并无他求,这种治世策略,真正地体现了礼学的精神,因为它是一种尽义务的治道,而不是强扰百姓的治道。
由于礼往往被权势者用作实现自己贪欲的工具,导致了礼的制度设计与践履礼的主体人的性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关系。一般情况下,庄子是通过否定仁义、肯认性情来表达他对礼乐制度的外在形式的否定态度的。
庄子对于儒、墨各家的治世学说,均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儒墨所鼓吹的仁义,其效果与动机是完全相反的。《在宥》篇称:“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于是乎……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黄帝行仁义的初衷是想治好天下,结果把人心扰乱,仁义不足以收服人心,尧舜以下,就企图以礼乐刑罚整肃人心,而使用礼乐刑罚的结果,人心更加动荡不安,就连君主也忧栗乎庙堂之上,这种人心摇荡,所换来的只能是人的本性的沦丧,是人的异化。从文明的发生意义上看,有虞或黄帝的世代也就是庄子心目中以“仁义挠天下”的时代,也即是人类自身试图用文明将自在人世间加以改造的开始。于是,人的本性的沦丧与文明的诞生一同来到人间。当人性被外在的物性所支配时,“撄人心”也就成了文明的基本功能。
庄子指斥“以仁义易其性”,他是把“性”与“仁义”看作相互对立的存在,“性”内属于人,“仁义”非人性所固有,是人性的附加物。即使有曾参、史鰌这种“属其性仁义者”,仁义之于个体的人来说,也不过如枝生一指的特殊情形,而不是人性的常态。真实的人性,庄子从常识的角度作了阐发,它通常表现为对于“声色、滋味,权势”的爱好,人们往往是“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盗跖》)。但是,人的这类性情,并不是庄子所要满足的,相反,它们是庄子要摒弃的。因为满足这类性情,仅具有为形体打算的意义,但它们适足以伤害形体本身。庄子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至乐》)。人们为形体所做的种种打算,在庄子看来,正是愚蠢透顶。虽然庄子对世俗所为性情作的打算是瞧不起的,但在礼学史上,却开启了荀子的“称情立文”的思路。庄子所提出的人情说有着浓厚的任性命之情的意味,他称述“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盗跖》)。在承认人的生理器官耳、目、口、舌等的自然感受方面,庄子的观点与儒家的制礼理论尤其与荀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庄子要求任情、不受外在规范的束缚,使人以此通道、通德,这一点又恰为荀子所扬弃,荀子要求满足人的感性愿望,但又将这种感性的生理感受,看作一种必须予以规约的恶,不能任其泛滥。
在这里,庄子将人情划分为世俗的“耳目之欲”与通道的“性命之情”两个层次。他把耳目之欲看作是防碍性命之情的恶。性命之情与耳目之欲处在相互排斥的状态,人们若“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相反,若“黜耆欲,掔好恶,则耳目之欲病矣”(《徐无鬼》)。在这种人生两难的选择中,庄子对于耳目之欲采取坚决摒弃的态度,对性命之情则持完全肯认的心态。在后来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那里,他将庄子的“性命之情”与“耳目之欲”混称之为人情,并认为需要礼的节文来制约它。
庄子认为礼乐制度对人的性情的背离,表现在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用世俗之礼来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以此达到媚世、谀人的目的,这种以制度的形式使人的性情发生背离,具有莫大的危害。庄子从人生的普遍经验出发,揭示了世人的共同心理,即不愿他人说自己是一个巧言令色、曲学阿世的马屁精,但人们往往又不自觉地充当着“谀人者”的角色。他认为谗媚有“谀人”与“媚世”的两种形式。在人世中,“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用礼来满足人们耳目之欲,这是一种媚世的行为。庄子以为阿谀奉承一个人是可耻的,阿谀天下同样也不怎么高尚,它依然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不过,庄子对儒家以礼为旗号来鼓动天下,主要不是作一种道德判断,而是作一种自然生命判断,在于它是否有损于人的性命之情,是否有利于人们全性保真。
儒家用礼乐制度来使人的性情发生背离,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礼乐制度恰恰是在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上下功夫,这种把自然人性中的欲望推到极至的作法,其后果是鼓动天下大多数人,虽不像曾参、史鰌那样具有优于仁义的禀赋,却纷纷向曾、史的做法看齐,天下喧攘,如簧如鼓,以奉不能企及的法式,这就大大地扰乱了人的本性。在《骈拇》篇中,庄子认为“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在制度的鼓励下,人们内心只得忍受“趣舍声色”等欲望之火的煎熬,外表又依靠“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规约人们的行为,儒家的礼乐文化使人们“睆睆然在纟墨缴之中而自以为得”(《天地》)。但一般人生活中要忍受的礼乐约束,是自由的吗?是人的正常生存方式吗?在庄子看来,人的这种生存境遇与罪人披枷戴锁,虎豹装进兽槛是没有两样的。确实,在世俗之礼的支配下,人们内心要遭受取舍、声色这些是非、欲望的煎熬,外在的肉体又要被皮弁、鹬冠等绳纟墨捆绑,在这种内外双重的约束之下,人的精神自由就被世俗之礼蒸发殆尽。“故目之于明也殆,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给改。”(《徐无鬼》)人们很难明白个体的种种特异才能,适足以损害自身的道理,他们仅是在感官的泥潭中打转。事实上,即使百分之百地满足了人的所有本能需要,也并没有完全解决“人”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最迫切的热望与需要,并不是那些根植于肉体的东西;而是那些根植于他生存特质里的东西,用庄子的话讲,就是人通乎道、合乎德的性命之情。
庄子认为礼乐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性情的过分耽溺,是导致性情背离的首要原因,针对这种使性情过分扩张的情况,庄子将仁义礼乐标准重新厘定为“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缮性》)。人们失性的原因在于将自己的德性强加于人,礼乐遍行天下,就是用一个模式来规范天下人。用一种德性来约束别人的德性,自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因而,礼的推行,其实质是使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所以,庄子称“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天运》)。
“役其德”的礼,就是将人的主体性淹没在世俗的繁文缛饰之中,因而人们之间以“礼相伪”(《知北游》)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外物》)。盗跖更以“矫言伪行”作为痛斥孔子的主要理由,认为孔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跖》)。这种注重仪节技巧,华而不实的礼,不过是人们用以获取官爵与求取富贵的工具。
庄子还从抑制人性的层面批评了礼对性情的背离。礼既会把个别人的优长确定为天下奉行之法,将耳目之欲鼓动起来;又会忽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客观普遍的事实,将纷繁的人性限定在同一个框框之中,这本身就是对人的不尊重。这种从礼为人性设限的角度来批判社会,很明显地表现出了无君论的倾向。《在宥》篇中,庄子指出:“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唐尧这样的贤君与夏桀这样的昏君,一个苦天下,一个乐天下,但都破坏了人的恬愉无为的自然之性,因而没有高低之分[2]。如果说人乐其性代表的是对人性中耳目之欲的过分扩张的话,那么,人苦其性则代表的是礼中对人的性命之情的压抑。
《庄子》一书在很多地方将礼与自然人性对立起来。“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于心,宰乎神,夫何以上民”(《列御寇》)在孔子的学说中,礼对人性的压抑表现为“忍性”;在唐虞始为天下的历史经验中,是“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缮性》)在这种人世与大道相互背弃的历史中,被抛却的人性就难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了;正是“文灭质,博溺心”的外在力量,使百姓陷入惑乱的状态。但是,人们往往是在打着保持其性情的幌子下来粗暴地对待性情的。庄子哀怜世人在“治其形,理其心”方面,“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则阳》)的种种作为,他们往往不顾天然,肆意妄为,任凭这个妖孽恣意将本性引入邪路。
礼乐的压抑,还造就了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在他们的控制下,普通人的天性就会发生向“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天道》)相反方向的偏斜,因而在庄子看来,要使人达到外天地、遗万物的至人的境界,只有“退仁义,宾礼乐”(《天道》),人心才会找到自己的归宿,人的本性才会以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3];庄子不是不要人的聪明、巧知,而仅仅是要与自然本性相一致的聪巧。
当然,导致人的性情背离除了礼乐对人的耳目之欲的扩张以及对人的性命之情的压抑外,还有社会分工的因素,将人的才智从属于某一个方面,使人丧失了对道的感受,对德的追求,使得“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达生》)的精神自由,从普通人的生活里隐遁得无影无踪。敏感的庄子感到人真的变成了马尔库塞眼中的单向度的人:“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贱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徐无鬼》)这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共同之处就在于“囿于物”,“驰其形性”,将自我交付给外物,听任外物主宰自己的形性。他们共同地把受操纵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来接受,把压制性的社会需要当作个人的需要,把外物的强制当作个人的自由,终身不返,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不是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这是真正的“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就是一种对环境盲目地接受,不知道反思自己身遭心受的外在处境。对此,庄子每每要发出一声沉痛的叹惜:“悲夫”
在消解礼乐及外物对人的压抑方面,庄子首先要求人有一个符合人性的生存环境。这种符合人性的生存环境在远古时代曾存在过,那时“先王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至乐》)。在一种凡事讲求适宜,作事通情达理的制度下,人们生活就可以幸福安康。相反,就会产生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端:“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则阳》)在这种背景,要想把人从文明的压抑下解脱出来,适是南辕北辙。在这种扰乱人性的生存环境下,人们的期望与结果即使不是每每相反,至少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庄子看来,一种符合人的“自然”之性的社会就是至德之世,就是“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胠箧》)等上古氏族社会,在这个理想国中,既没有舟车、甲兵这些“现代”物质文明,也没有仁义忠信等精神分别。人与野禽亲如一家,人与自然处在一种天然合一的状态。在至德之世,人“同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其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正是在这种人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状态中,人像万物一样,有着“通于天地”的自然秉赋,从而使民性复归到“素朴”的境界。由于至人通于德,至人也就能让人性的光芒与物性的光芒一同呈现,不去做任何人为的干预。
消解礼乐对人性的压抑,就要将中国之君子从“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价值取向中解脱出来。在庄子看来,要明于知人心,就要抛却繁文缛礼的种种外在束缚,做到“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山木》)。在性命之情与礼文的关系中,也即人与文化的关联中,顺从天性,本于人情,让人体器官发挥自己的本来功能,“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徐无鬼》)。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庄子强调的是人际本身的融洽,亲密无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天属”而不要“以利合”,因为人际关系若建立在以利相交的基础上,那么,一旦“穷祸患害”来临的时候,人们就会像同林之鸟,大限来时各自高飞,各自相弃;相反,“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山木》)。而所谓的“以天属”就是以发自天性的真诚相处,这样就可以做到患难相扶,死生与共。
当人们从礼义这种社会意识中解脱出来之后,人际关系仿佛失去了规则,但在庄子那里,从天而理,则是一种更有价值的交往原则,“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而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园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盗跖》)。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规则,最恰当的替代物便是“从天而理”、“与时消息”、“与道徘徊”这些天人之际的原则,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在大道之中相安无事,同时,又“相忘乎道术”。这样,庄子将性命之情与“天道”相联系起来后,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可以迳直化约为个体自身中形、性与道之间的关系;社会交往关系的法则,内敛为一种使生命不受伤害的保性法则。人生在世做到“纯粹下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人的对外交往关系被调适为一种心灵的自我安顿。因而追求一种高远、阔大、平和、恬淡、宁静的精神境界,造就一种超凡脱俗、桀骜不驯,伟岸不羁、洒落坦荡的精神人格,就成了庄子人生的目标,而他心目中的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就是摆脱了礼义羁绊、性情不离的完美人格的形象。
庄子反对礼的外在形式,但肯认礼的内在秩序,认为礼的内在秩序与天道是相一致的,礼作为大道之序,圣人的作为必须与道相符。在应礼而作方面,庄子肯定了“臣之事君,义也”(《人间世》)的合法性,同时,强调君臣的职分,认为在上的人君其职责是无为,在下者的职责是有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天道》)
礼的合法性在于礼蕴含在大道之中,应于礼也即是合于道。在庄子看来,“以道观分”是确定君臣义务的前提条件。由于礼别异,是讲求“分”的,他这种“分”对于大全的“道”来讲,并不是不相容的,相反,是“道”的组成部分[4]。从道的立场来看,明确君臣的各自义务正是应礼而行。“礼”作为道的绪余,是治国的工具,“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让王》)。道的根本功能在于治身,治国,治天下,则是含蕴在道中的仁、义、礼这些绪余,或土苴的功用,由于它们是大全“道”的组成部分,所以,庄子把天、道、德、义、事、技等之间定位为一种“兼于”即包涵的关系。“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地》)技作为万物的末用,是“道兼于天”的必经环节。
在人世间的种种不可不为的事物中,庄子认为,尽管法、义、仁、礼、德、道、天,均是“物者莫是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的,但是,它并不要求人们去刻意造作。所以庄子强调“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在宥》)。这种以万事为天然而去顺应的态度,是把“无为而尊”的天道原则,贯彻到人间事务的结果。应于礼而不违,就像一个普通的百姓一样,“入其俗,从其俗”。它反对那种卖弄一己的小聪明,“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达生》)的标新立异、扰乱人性的种种作为,相反,“唯圣人乃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外物》)。
在论述治世的手段时,庄子对于礼是认可的。在内篇《大宗师》中有“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在这里,庄子强调礼作为治国的辅翼,主要是为了顺世随俗,而将人类智慧的圆融与四时的代换相类,把德行修养看作是因循天性,这一切正是承认、遵从现世的制度,以为在顺世随俗的层面上,可以达到对大道的体悟。
从以礼体道的层面上看,礼像大道一样,是无形迹表现的。“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渔父》)虽然无礼文作招摇,无世俗的礼为其外在形式,但代表真实礼意的真,即“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渔父》),却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人们对礼形迹层面的遵循,往往是一种应礼而违的表现,但对礼意层面的遵循,则可能是一种无声的心灵感应:“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庚桑楚》)最高的礼是不见外的,人们在大街上不小心踩了他人的脚,连连道歉,但不小心踩了自己家人的脚时,是无须道歉的。这正说明,当人们之间需要礼来维系的时候,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关系上。这也揭示了应于礼而不违,在公共空间和私性空间是有差别的。当然,在严格的礼治规范下,私性空间也是有礼的束缚弥漫其中的,只是与大亲相较,陌生人对礼的要求可能更严格、更规范些。
应于礼而不违,还必须依时而行,没有对时代情势的考虑,我们就很难知道某种作法是合礼还是非礼,是符合礼的精神,还是仅用古代的服饰来禁锢真实礼意在新形势下的展现。“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天运》)从功用的角度看,不同时代礼义法度之所以值得赞美,就在于它们治世的功效,而不是它们在礼乐威仪这种外在形式方面是否一致。“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天运》)应时而变,就可以使人们避免古代梦魇的纠缠,避免死的拖住活的苦楚。对于未陈的刍狗,我们必须“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对于用过的刍狗,人们是可以任意践踏,甚至可以当作柴火的,人们对于过去的陈迹若一定要恭敬有加,那么,就像王先谦所注解的那样,即便不致恶梦,必当屡屡遭遇恶魔[5]。同时,在礼的精神层面做到应于礼而不违,在礼的形式层面上做到“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还可以避免借穿着古代的盛装,请来过去的亡灵,来上演新时代喜剧的尴尬。
庄子不注重礼的形式,因为礼的形式充其量只是古代治世的糟粕、是土苴,人们对礼的形迹的追求,恰如“求马于唐肆也”。在散场的马市求马,必然是一无所获的。庄子以为“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运》)将陈迹与所以迹区分开来,就是不要把礼的外在形式,当作礼的本身,礼除了外在的节文外,还有更主要的礼意即“所以迹”的内容。
总之,庄子对待礼的态度是有着不同层次的,主要表现为礼的形迹和真实的礼意两个层面。而真实的礼意则表明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世俗关系外,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人与天之间构成的天人关系,即阴阳之于人是一种构造性的关系。在宇宙之中,阴阳恰如人的父母,人的生死表现为气的聚散,正是听命于自然气化的结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礼意的因顺关系;作为真实的礼意,它蕴含在大道之中,是大道之序的体现,也就是在“至礼有不人”的世俗之礼中,礼体现的人间秩序,正是大道之序的反映。而礼的形迹层面,则是“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马蹄》)的有意造作。对这种行迹层次的礼,庄子一方面批评它们违背人们的性命之情,是“擢德塞性”,“残生伤性”(《骈拇》)的工具,对此,他有时甚至不惜将世俗礼乐的那套规范还掷给强加者的身上,用儒家的礼乐原则,来否证儒家心目中圣人行为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在和之以是非的顺世态度下,把人间的君臣之义与父子之亲,当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宿命,因而因循世俗之礼。正是对世俗之礼,采取一种“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充符》)的态度,可以使人在顺从礼意的同时,达到“忘礼乐”的安适境界。这样,以“两行”之法,处于因顺与反抗之间,正是庄子对待礼的主要态度。
注释:
[1]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本文所引庄子的文句均出自该书。
[2]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3]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古代文化常识大全范文3
关键词:王船山;阴阳;阴阳之气;阴阳之撰;阴阳之化;
阴阳之道王船山乃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涉猎广泛,阴阳思想颇具特色,且构筑了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关于船山阴阳思想研究的成果颇丰,但并未形成系统性、逻辑整体性。船山阴阳之道着手阐释的是阴阳运动发展的规律及其层次性,这种层次性构筑了船山阴阳思想的逻辑体系:此体系使阴阳之气、阴阳之理、阴阳之撰、阴阳之化四个逻辑层次得以构成并成为可能。船山阴阳之道体现了其阴阳思想之内在的逻辑性、系统性。船山阴阳之道的逻辑展开由阴阳之气而始。
一、阴阳之气:船山阴阳之道开显的逻辑前提
船山阴阳思想脱胎于古代素朴的阴阳思想,其阴阳思想是在两个对立面基础之上的延续,船山认为阴阳思想源自于阴阳二气,此乃阴阳思想开显的逻辑前提。在中国哲学史上,阴阳并非一开始就归结为阴阳之气的。罗光认为:“《六经》没有以气为哲学名词,用以解释宇宙和人生。《易经》讲阴阳,但没有与气联系在一起。至于阴阳两气,已经是后代的词汇,属于注解《易经》的用词。”①阴阳与气相结合,是在两汉注经、解经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我们今天从中国哲学史所了解的阴阳观念,是指气的两种类型,这一含义不是阴阳的原初含义,基本上是汉以后出现的,特别是宋明儒学赋予的。”②阴阳作为对立的一对范畴,与气相挂搭,是两汉经学以后的事情。阴阳思想虽然出现较早,但并没有与气联系起来,究其原因在于先秦时期在本体论建构方面欠缺思考。直至魏晋新道家对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而导致儒学在信仰层面的缺失之时,如何重振儒家的纲常伦理成了当时的核心话语。阴阳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颇具特色的核心范畴之一,重振对儒家文化的信仰,此乃当时有识之士考虑的核心话语。宋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将阴阳思想与气联系起来,并赋予其在形而上层面的特质,从而将阴阳与气挂搭,实现了阴阳之气的转换,船山是将阴阳与气结合之典范。基于此,船山阴阳观得以升华。
阴阳之气是船山阴阳思想得以开显的逻辑前提。船山是典型的气本论者,他所说的气乃为太虚之气。太虚、太和乃阴阳之气的异名,实乃一气。船山依托于形而下现象世界的“太虚”描绘了本体之气的稀疏状态;借用稀疏状态描绘太虚,是为了更详尽、更形象地阐释本体之气,因为太虚之气“不可道”、“不可名”、亦不可状。以形而下的方式断想本体之气,这是不科学的,现实中的实然状态表现为气,但不能名之曰气(本体意义上的气)。船山曰:
太虚即气,sA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虽其实气也,而未可名之为气;其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于此言之则谓之天。气化者,气之化也。阴于太虚sA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则物有物之道,人有人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处之必当,皆循此以为当然之则,于此言之则谓之道。③
作为形而上的太虚之气,船山从形而下的角度描绘了气,并运用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思辨分析了太虚之气并非可名之气,亦说明了阴阳居于太和sA之中。鉴于阴阳调和搭配,阴阳协和,最终成就太和。太和sA之气中,究竟何为阴、阳。船山曰:“阴阳者二气sA,轻清不聚者为阳,虽含阴气亦阳也;其聚于地中与地为体者为阴,虽含阳气亦阴也。凡阴阳之名义不一,阴亦有阴阳,阳亦有阳阴,非判然二物,终不相杂之谓。”④从常识看来,阳气密度小而上升,表现为阳,阴气密度大而下沉。阳气上升与阴气下降均蕴含着相反性质之意味,但气的性质是由占据主要成份的气之性质决定也。可见,阴阳之分别泾渭分明;虽然阴阳二者区分明显,但船山认为“阴亦有阴阳,阳亦有阳阴”,又表明了阴阳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可见,船山认为阴阳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矛盾统一,“‘气’是阴阳二者的矛盾统一体。”⑤阴阳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与区别。
阴阳之气具于太虚sA之中,太虚之气是作为本体之气的可言、可状而言的。太虚sA,“s媪浑合,太极之本体,中涵阴阳自然必有之实。”⑥太虚sA,sA之气交织混合于一体,则构成了太极之本体。在船山本体视域中,太虚s媪,也即二气s媪、二气浑合,构筑了太极之本体,依此意而言,太极孕育于阴阳之中,离阴阳则无太极,由此阴阳与太极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引文看出:
阴阳之外无太极,得失顺逆不越于阴阳之推荡,则皆太极浑沦之固有。⑦
阴阳,无始者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⑧
《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⑨
太极不离阴阳,阴阳即为太极。在周敦颐的太极图中显示出太极动而生阳、静止而生阴的阴阳二气。周敦颐的太极图已勾勒出阴阳之气的一体两面,《太极图说》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与阴阳表现出一体两面的关系,所谓“一体”即为太极,两面表现出“阴阳之气”。太极与阴阳不可分割,阴阳之中有太极,太极之中有阴阳,阴阳与太极不可离。船山之太极阴阳思想,实质在于证实本体论一元性之纯洁度及其逻辑展开。太极阴阳的逻辑展开,在宇宙之中表现为和谐之气,是“和之至也”的太和之气,于是又称之为太和之气,因为“太和之气,阴阳浑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纯粹,故阳非孤阳,阴非寡阴,相函而成质,乃不失其和而久安。”⑩从阴阳之气所处的状态而言,阴阳之气则表现为太和之状态,故此,阴阳之气是真实的存在,阴阳之气为实,不是虚,“气之诚,则是阴阳”,阴阳为实。
船山阴阳思想以阴阳之气为逻辑起点,此阴阳之气从本体层面来说,表现为太虚;如若太虚之气浑合,则阴阳之气表现为太极;如若阴阳之气阴阳调和,阴阳和合,则阴阳之气称之为太和之气。无论是阴阳太虚之气,阴阳太极,阴阳太和之气,均是对本体之气的不同的理解而呈现出的太和之气的模式。无论是何种理解,最终都离不开阴阳二气的实存,是阴阳二气在不同状态之下发生作用使然。陈来说:“气体即气之体,亦即气之实体,气之本体,指传统宇宙论中的太极、阴阳。”船山之阴阳二气,是指气的实存模式,是对实存之气的现象超越。船山阴阳二气思想,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阴阳思想:将阴阳简单地规约为矛盾对立的两个层面;船山之阴阳思想实际上已经在本体层面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超越,是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意义角度的阴阳,这种阴阳之气思想的发生,是以万物质料的形式出现的,因此阴阳之气又可称之为阴阳之质。“阴阳,质也”,阴阳之气,已超越了阴阳之矛盾对立的层面,转向了本体层面的阴阳之气,从而为阴阳之气化生宇宙万物奠定了坚实的质料因。那么宇宙万物究竟何以化生,阴阳之质的质量因只是一个层面,更多的则是依赖于阴阳之间的内生作用,即关涉到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也即阴阳之理的问题。
二、阴阳之道:船山阴阳之道展开的逻辑理路
阴阳之气作为s媪之气(太虚),太极、太和之气的内蕴成份,阴阳之气运动必然要具备阴阳之理。阴阳之气,作为本体在生化万物过程中,究竟如何运动,阴阳之间究竟遵循着何种逻辑呢?船山认为存在着阴阳之道,这种道不是简单的阴阳之间的对立,而是在阴与阳之间存在道,我们称之为阴阳之理。就本体而言,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均由阴阳之气产生,而这种阴阳之气的逻辑展开与阴阳之道紧密相联。船山曰:“阴阳之外无物,则阴阳之外无道。”阴阳之气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且万物产生都遵循着阴阳之道。阴阳之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阴阳二气运动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法则、调理、秩序等。阴阳之道,天下之大道;阴阳之道,周遍了天下万事万物之达道。宇宙这个大生命场的发生、发展变化等,最后均遵循着阴阳之道。易言之,阴阳之道是人世间、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本之道,船山曰: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求之阳又求之阴,周道备矣。
天地之间,皆因于道。一阴一阳者,群所大因也。
阴阳之道乃为普遍大道,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绝对之道,此大道应用于万事万物的生成,人伦道德规则的实践检验。阴阳之道的存在,开启了宇宙这个大生命场的普遍“真理”;阴阳之道,是天地之达道,阴阳之道作为宇宙间普遍性真理,适用于事事物物。“凡天下之事物,一皆阴阳往来之神所变化。物物有阴阳,事亦如之。”阴阳之道作为宇宙间的普遍性真理,不仅在事事物物上彰显出来;反之,事事物物的出现又彰显出阴阳之道。阴阳之道,必然是事事物物之阴阳之道;事事物物存在,那必定是蕴含着阴阳之道的事事物物。阴阳之道与宇宙间事事物物不可须臾离也。
阴阳之道与宇宙间的事事物物紧密相联,系事事物物得以生长的内在动力。实现阴阳之道的动力为阴阳消长与阴阳动几,由阴阳之气化生的宇宙万物由此实现。在产生宇宙万物之时,阴阳消长决定着事物的性质。船山曰:“推本万事万物之所自出,莫非一阴一阳之道所往来消长之几所造也。”一阴一阳乃宇宙万物产生之道。若阳占据主流,则产生事物凸显为阳性;若阴占据主流地位,那么因之而产生的事物则呈现出阴性。因此,事物的性质取决于阴阳消长,事物的性质与占主流地位的阴或者阳息息相关,即事物的性质是由占据主流地位的事物的阴阳性质的矛盾主流的一面决定的,决定事物性质的阴阳层面显得非常微妙,“一屈一伸,交相感应,人以之生,天地以之生人物而不息,此阴阳之动几也。”阴阳的微妙变化,决定事物的性质;事物的产生,亦反衬出阴阳之间的微妙变化。
宇宙间这个大生命场,不能脱离阴阳之间的合力,阴阳合力决定着宇宙这个大生命场万事万物的产生与发展,决定万事万物的性质。阴阳之间相须不离,阴阳之间只有合力搭配,才能实现阴阳之道,使得天地万物得以生,天地万物得以成。在船山看来,阴阳之间相须不离表现为阴不离阳,阳不离阴。只有阴阳搭配,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船山曰:“阴非阳无以始,而阳藉阴之材以生万物,形质成而性即丽焉。”阴依阳而得以始,阳依阴(阴因温度低,气之凝聚而成为材质也)之材质而化生宇宙万物。故此,阴阳之间只有合力搭配,才能奏出最美的华章。阴阳相合,相得益彰,如此实现阴阳无限之“神’力。正所谓“阴阳合为一德,不测之神也”。阴阳合力,宇宙万物得以生,《周易》“生生之谓德”阴阳合力之美妙。阴阳合得(德),故能神力,故能和生,宇宙万物得以生,宇宙万物得以生的内在力量船山曰之为“神”。阴、阳从字面含义上看,表面偶立;可在化生宇宙万物层面看,同则相继、阴阳相合。阴阳相合则生生,造就宇宙万物“和生”。阴阳之气始于太虚、太极、太和之气,本一也,是何种动力将阴阳一分为二而偶立。船山曰:“阴阳之始本一也,而因动静分而为两,迨其成又合阴阳于一也。如男阳也而非无阴,女阴也而非无阳。以至于草木鱼鸟,无孤阳之物,无孤阴之物,唯深于格物者知之。时位相得,则为人,为上知;不相得,则为禽兽,为下愚;要其受气之游,合两端于一体,则无有不兼体者也。”阴阳既对立、又统一。阴阳只有合一,方可造物,此乃自然之则也;有合必有分,分的动力在于动静:动而分为阳,静而为阴,一动一静,阴阳始成;有分则有合,分久必合;一分一合,构筑了宇宙万物之普遍法则。阴阳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一分一合的逻辑运动,最终奠定阴阳之理。有阴阳之理,如此彰显出阴阳分合之道。通晓阴阳之撰,通过阴阳分合之活动,明阴阳之撰化生宇宙万物。鉴于万物产生与阴阳分合之道不可分割,故此船山非常重视此道。船山曰:“天地阴阳之撰,分合而已矣。不知其分则道无由定,不知其合则方体判立而变化不神。故君子之学,析之以极乎万殊,而经纬相参,必会通以行其典礼,知分知合,而后可穷神而知化。天之教,圣人之德,未有不妙其分合者也。”在阴阳分合之时,船山其实更多强调的是阴阳之间的协同,淡化阴阳之间的偶立,在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中寻找万物的生长点。王船山“注意从阴阳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去寻找其统一性”。阴阳合一表明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阴阳相分则表明了阴阳之间的偶立,但阴阳之间的偶立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合一中相互依存,在动静中实现阴阳转化。
综上,阴阳思想乃宇宙生态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天地之间均是宇宙阴阳之道的作用,阴阳之道内蕴的阴阳思想,既对立、又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阴阳既分立,又合作,共同构筑了宇宙生命场中的阴阳之道。在宇宙这个大生命场,阴阳之道如何化生宇宙万物,这依赖于阴阳之撰。
三、阴阳之撰:阴阳之道展开的运行动力
阴阳之撰即阴、阳之间如何运动、发展,探讨阴、阳活动孰先孰后,阴阳活动谁主动活动、谁被动活动的问题。在船山本体视域中,在阴阳之气的规约下何以产生宇宙万物,阴阳之撰功不可没。船山曰:“唯万物之始,皆阴阳之撰。”阴阳之气乃宇宙万物化生之质料,阴阳之撰乃万事万物产生之动力。阴阳之撰,更多关注阴阳之间的合力,阴阳之间是内在合作,而不是偶立。
在阴阳运动中,阴阳究竟如何运动以协和二者之间的关系,阴阳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如何实现的。船山阴阳思想的矛盾运动中,一是阴阳互求以成生化。船山曰:“升降相求,阴必求阳,阳必求阴,以成生化也。sA相揉,气本虚清,可以互入,而主辅多寡之不齐,揉离无定也。二气所生,风雷、雨雪、飞潜、动植、灵蠢、善恶皆其所必有,故万象万物虽不得太和之妙,而必兼有阴阳以相宰制,形状诡异,性情区分,不能一也;不能一,则不能久。”阴阳有互入意愿,进而造就阴阳相吸之势能。阴阳之间正是在这种势能的影响之下,积极成就了阴阳交合化生宇宙万物之潜能。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在《周易》中,主张阳爻为尊、为贵,为主动等的代名词。在船山哲学思想中,船山亦认为阳为尊、为贵、阳应主动。船山曰:“阳气先动,以交乎固有之阴。”阴阳活动中,阳占据主动地位,以积极的方式推动固有之阴的交合;阴则居于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配合阳的运动,最终实现阴阳二气的交合而完成阴阳化生万物。阳气先动,以积极的、扩散的方式向阴气靠拢。阴气由于密度、温度等相对阳气而言较低、较沉。因之,阳气凝聚于阴气之上,而阴气则吸住阳气,阴阳之间形成了一聚一散之模态,阴阳二气之间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势。“其中阳之气散,阴之气聚,阴抱阳而聚,阳不能安于聚必散,其散也阴亦与之均散而返于太虚。”阴阳相合之时,阳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阳气上升,阴气下沉,在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对立的阴阳关系,但统一性始终占据阴阳思想的主流地位。阳气主动先动,阴气被动后动,最终形成阴抱阳而聚的局面。阴阳均作为一种动力而存在,因为“阴阳、五行都是动力”。因阴阳之撰而有阴阳之间交互吸引,交互运动,进而成就“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反观:孤阴孤阳不能成为道,无道则不可能成就阴阳之撰。“自太和一气而推之,阴阳之化自此而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原本于太极之一,非阴阳判离,各自孳生其类,故独阴不成,孤阳不生,既生既成,而阴阳又各殊体。”阴阳之撰必然是阴阳合力使然,阴阳交动,从哲学层面看,其合力的原动力在于天。船山曰:“阴阳交动,变化之合,天之教也。”船山视域中的天作为主宰之天,主宰着阴阳之气的内在活动。作为阴阳之间交合,有内外两种动因:一是阴阳二气本身运动之动因在其中,可归结为内因;二是天作为阴阳二气交合的外在动力,可归结为外因。内外合力作用,最终导致了阴阳交合的顺利完成。
综上,船山阴阳交合思想的完成,是基于阴阳并建完成,而不是阴阳偶立。阴阳搭配,阴阳相交,成就了阴阳之间相互吸引的内在吸力,船山称之为“神”。船山曰:“阴阳合为一德,不测之神也。”“神”可理解为神妙莫测,神秘之力量。此力量来源于阴阳并建,船山亦称之为“乾坤并建”,乾为阳,坤为阴,乾坤并建,也即阴阳并建完成。“考之于万事万物之当下存在,莫不是阴阳并建成其因,成其实。”由阴阳并建催生巨大的、旺盛的生命力,进而催生万事万物的化生。船山在创生万物之时,始终没有脱离阴阳并建、也即阴阳之撰的基础性作用。阴阳之撰,乾坤并建是阴阳之化产生万物的前提与基础,万物化生取决于阴阳之化。
四、阴阳之化:阴阳之道完成以实现逻辑度越
船山阴阳之撰描绘的是阴阳之间谁主动、先动,谁被动、后动,以及如何动,因何而动的问题。船山更多关注的是阴阳运动的过程哲学,属于哲学上的量变过程哲学。陈来说:“比起周敦颐,船山更是强调阴阳变合的环节。”此语比较透彻的谈及了船山关注更多的是过程哲学。阴阳之撰的变合环节中,船山更多关注的是阴阳相吸的动因,相吸的过程以及相吸后所产生的“神”的力量,关注的是阴阳变合之环节。船山关注阴阳变合的过程,但在过程之后更多的是关注阴阳变合的结果――阴阳之化,因为过程积累必然转向质变,即由阴阳二气活动促使万物化生。方克曰:“阴阳交感而成‘法象’是事物的发展的必然法则和趋势。”阴阳之撰,阴阳变合过程固然重要,但阴阳量变必然要向质变转变,阴阳之撰必然要向阴阳之化转变,进而化生宇宙万物。
阴阳之化依靠阴阳之体之质料,也即必然要有阴阳之气才有阴阳之气的气化。因为“天之生物,人之成能,非有阴阳之体,感无从生,非乘乎感以动静,则体中槁而不能起无穷之体”。无阴阳之体则不可能有阴阳之感,无阴阳之感便不能产生阴阳之间相吸之势能;阴阳之化唯有阴阳之体,方可产生阴阳之感;有阴阳之体,才有阴阳之化。有阴阳之体,则有阴阳之化,那么何为气化?船山曰:“气化者,气之化也。阴于太虚sA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阴阳之气化,经由阴阳之撰,阳气主动而先动,阴气被动而后动。在合适的时间节点,阴阳之气化生宇宙万物,即不同的化生物存在着不同的阴阳化生之临界点,此乃船山所说的“乘其时位”也。陈来认为:“气化即气之用,在气化阶段阳变阴合,生成万物,生成善恶,理作为气化的调理得以呈现。”气化即本体之气分殊出来,通过阴阳之撰,生化出宇宙万物,同时也生化出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规范。
就具体的阴阳气化方面,船山认为气化过程中有阴阳气化构形,也就造就宇宙万物之基本轮廓,构成宇宙万物之基本模型。船山曰:“二气构形,形以成;二气辅形,形以养。能任其养,所给其养,终百年而无非取足于阴阳。是大造者即以生万物之理气为人成形质之撰,交用其实而资以不匮。”阴阳气化构形,奠定了阴阳之气在化生宇宙万物的基础性地位,奠定了气化万物之形式因。形式因形成之际,阴阳二气在成就形式因的过程中的分工与作用是不同的。船山曰:
阳以生而为气,阴以生而为形。有气无形,则游魂荡而无即;有形无气,则h骼具而无灵。乃形气具而尚未足以生邪?形盛于气则壅而萎,气胜于形则浮而枵,为夭、为怠⑽不慧,其去不生也无几。惟夫和以均之,主以持之,一阴一阳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
凡发生畅遂,皆阳之为而用夫阴;收藏成形,皆阴之为而保其阳。天地、水火、四时、百物、仁义、礼乐,无不然者。
升降飞扬,乃二气和合之动几,虽阴阳未形,而已全具殊质矣。‘生物以息相吹’之说非也,此乃太虚之流动洋溢,非仅生物之息也。
阴阳构形过程中,阴阳之间表现出通力合作的关系,阴阳相须不离,方能构形;在构形过程中,阳虽然起到主导性作用,但阴才能真正呈现出构形之模态;构形的完成不能是阳盛阴衰,亦不能阴盛阳衰,必然是阴阳之间的平衡才能完成阴阳构形。阴阳构形,阴阳之间的均衡和谐异常关键。阴阳均衡,阳作为以其“神”支持阴,阴最终显形。船山曰:“阴气化而为形质,阳气化而为妙万有之神灵。”阴阳构形,显示形式因,但却不是的目的因。阴阳之撰,阴阳构形,促使阴阳合以成物,由起初的阴阳相分转变为阴阳合一。船山阴阳思想的逻辑展开,从最初的一分为二,最后又回归到合二为一。在阴阳二气的不断分合中完成由“气一分殊”而生成万物的逻辑过程。阴阳构形而后,最终目的因的完成仍然是阴阳合一成物、合一成象。由阴阳构形。船山曰:
阴阳合以成物,而物各有阴阳之分,本天亲上,本地亲下,形类殊而性命亦别,柔刚静躁,明暗分焉,秩序之象也。天垂象而吉凶昭,地成形而平陂立,常变之则也。故礼以法天地之体,而别尊卑,辨大小,连其类,分其等,各正其性命,而吉凶常变莫不行焉者,皆因天地自然之别而立也。
阴阳构形,阴阳之化而生成万物,进而实现太和、太虚、阴阳之气的目的因。由阴阳构形,到阴阳合成万物,阴阳成象。从气本源来说,均是本源之气借用阴阳之撰之合力使然。船山曰:“使之各成其象者,皆气所聚也,故有阴有阳,有柔有刚,而声色、臭味、性情、功效之象著焉。”阴阳合成万物,万物之中亦有阴阳之因子在期间。阴阳合撰,乾坤并建而化生宇宙万物,万物之象依然孕育着阴阳之种子。万象之“合者,阴阳之始本一也,而因动静分而为两,迨其成又合阴阳于一也”。由阴阳构形到阴阳合成以生万物之过程中,本体孕育着阴阳,一分为二,阴阳之撰,阴阳合成万物,万物之中也必然孕育着母体内的基本因子。船山曰:
天地之法象,人之血气表里、耳目手足,以至鱼鸟飞潜,草木华实,虽阴阳不相离,而抑各成乎阴阳之体。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
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来源于本体之气,本体之气蕴含阴阳之气。阴阳之撰、阴阳之化所生的宇宙万物,阴阳二气之特质孕育于宇宙万物中间。宇宙万物在阴阳二气的化生、合成以后,活动不止,永不停歇;生死不断,必无止息,并形成完整的生物链。“阴阳之撰具焉,s媪不息,必无止机。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兴,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生无穷,而尽天下之理,皆太虚之和气必动之几也。”阴阳之撰而后,有阴阳之化,必将化生出宇宙万物,宇宙万物灭失以后又返回太虚。易言之,由太虚所产生的宇宙万物在生灭过程中并没有消失,灭失即是返回太虚,期间阴阳特质仍孕育期间。陈来说:“阴阳二气从太和分化而出,动静摩荡交感,阴阳二气凝聚为物,每一物皆具阴阳……万物在一个或长或短的存在时期之后,均要贵返于太虚。”由太虚之气,分出阴阳二气,继而生化宇宙万物,最终又返回太虚,表面上又回到了原点,实质上是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周期,从而完成了阴阳之气在质上的飞越。
五、结语
船山阴阳之道系指阴阳思想运动发展的规律、调理、秩序等等。船山阴阳之道的逻辑开显是建立在阴阳之气的基础之上,阴阳思想的运动发展即是气之阴阳运动发展的逻辑规律。阴阳乃气之阴阳,离气无阴阳,阴阳不离气,阴阳与气相须不离。阴阳之道的逻辑开显通过四个逻辑过程而展开,具体逻辑开显线路图为:阴阳之气阴阳之道阴阳之撰阴阳之化,最终完成了阴阳之气运动变化发展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性、条理性、有秩序性等。船山阴阳思想的逻辑开显由气始,最终完成的是由阴阳之化,生化成天地万物,最终实现了阴阳之气运动、变化、发展,彰显了阴阳运动变化的逻辑性与规律性等。阴阳之化完成了阴阳二气的质变,生化了宇宙万物。万物历经宇宙的“生死轮回”,最终又回归到宇宙万物之源,表面看来又回到了“原点”,实质上却是对阴阳之气运动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了阴阳之气在更高意义上的运动变化,完成了阴阳二气运动变化否定之否定,实现了船山的阴阳之道的逻辑展开与逻辑度越。
【 注 释 】①罗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册,台湾先知出版社1975年版,第409、177页。
②陈S:《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脚注部分。
③④⑥⑩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2011年版,第32―33、57、45、54、107、108、82、37、54―55、57、47、82、366、32、56、27、358、37、27―28、57、364页。
⑤方克:《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9、94页。
⑦⑧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78、562、629、76、42、92页。
⑨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24、1112、1092、892、1043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55、523页。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70、25、26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16、609―610、609―610、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