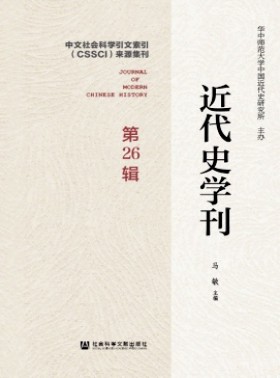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1
[关键词]“女国民”;启蒙;“新国民”;近代女性意识;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3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14-06
[收稿日期]2012-04-25
[作者简介]崔玉山,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韩国文学、中韩比较文学。(北京100029)
一
“女性”意识与“国家”、“民族”观念一道成为东亚近代舆论的焦点,不能不说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近代法则面前,传统男权国家濒于崩溃瓦解,一些近代启蒙先驱者们面对这种社会变革,积极探寻解决的良策。由于将女性与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相联系起来,所以有了对“女性的发现”,并开始了迈向探寻“近代女性”的艰辛的变革过程。申采浩便是走在近代韩国改革前列的一位先驱者。
“女英雄”、“新贤妻良母”、“国民之母”、“女国民”、“新女性”等时代用语,无不蕴含着当时知识分子为重塑女性形象而进行的无尽思虑。要想将屈从、愚昧而不觉醒的传统女性改变成为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行为主体实非易事,所有这些无非是全新的挑战和探索。因此,申采浩眼中的“近代女性”究竟呈现出何种样貌,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不仅是为了“解读申采浩”,即便是为了“解读近代”,本文都应论及女性。在此之前,除金柄珉和崔元植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很少有人研究申采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申采浩笔下传统的儒生形象和犀利的男性笔触,很容易使研究者们淡化申采浩思想中的女性意识。另外,迄今为止的申采浩文本收集整理工作也给此项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发掘并再现申采浩文学中鲜活的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创作表现则显得更为迫切。
本文将在回顾申采浩心目中的“男国民”形象的同时,集中分析申采浩对“女性”的认识与论述。继而通过考察申采浩作品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现及创作意义,真实、鲜明地展现爱国启蒙者申采浩所勾勒出来的“近代女性”形象。
二
申采浩面对无能政府统治下的混乱局势和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力求启迪愚昧、屈从的国民,以此建立崭新的、富强的国家,他为开拓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孜孜以求。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他对于参与、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认识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轨迹。
直至1909年,申采浩一直宣扬“国家的强弱在于英雄的有无”,并致力于“起草英雄论,唤起新人物”的启蒙事业。他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是英雄,渴求克服万难的救国英雄能够横空出世。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时的申采浩而言,所谓的“国家”已不再是当前即将崩溃的大韩民国,而是屹立于适者生存的世界秩序之中、具备自立与自强实力的民族民主的“国家”。所以说,他的英雄论是建立在与“国家”、“民族”相联的基础之上,与以往希冀由具有超人似的救世主降世的旧英雄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换言之,申采浩所渴望的英雄是人人皆可“学习的典范”,是国民中的一员。“以爱国忧民四字为天职,视独立自由为生命”,只要不懈奋斗,无论是谁都将成为英雄的这种坚定信念正是申采浩英雄论的核心所在。在较短时间内,申采浩对于历史主体的认识之所以从英雄观过渡到新国民观,其原因在于他意识到了近代社会存在的普遍条件正是以国民为基础。以下引文便向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古代社会的原动力通常在于一、二豪杰…(中略)…时至今日,一国的兴亡不再取决于一、二豪杰,而是决定于全体国民的实力……
呜呼,只有国民英雄的存在,宗教才能成为国民的宗教;只有国民英雄的存在,学术才能成为国民的学术;只有国民英雄的存在,实业家才能成为国民的实业家,美术家才能成为国民的美术家…(中略)…国民乎,英雄乎?
如上所示,申采浩高呼民族生存、国家独立,深感国民团结的力量,通过呼唤具有过渡性意义的“国民英雄”形象的出现,完成了由“英雄”到“国民”的历史主体的认识转变,从而开启了焕发新气象的“新国民”时代。直至他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把目光转向“民众”为止,这一“新国民”理论足足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
1910年2月,申采浩发表了“新国民”论的集大成之作《二十世纪新国民》。这一理论的提出,与梁启超的“新民说”,即以人之更新、培养民族的团结精神、对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引导国家走向富强的主张不无关联。然而,申采浩之所以把“新民”概念巧妙、灵活地转化为“新国民”一词,正是由于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的缔结所带来的亡国局势促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紧要课题在于恢复国家的。“新国民”一词实际上融入了申采浩对于“国家”浓厚的执念。亡命后的申采浩在《大韩新民会趣旨书》一文中谈道:“只有唤醒新精神,创建新团体,方可重新建立新国家”,并且明确指出了“新国民”说的最高目标旨在于新国家的建设。不仅如此,他还呼吁“我民不欲新,谁还爱我大韩;我民不欲新,谁还护我大韩”,以此强调创新国民也是建设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特别是直接把国家之名“大韩”两字放置于前,把“新国民”改称为“大韩新民”的举动,更是彰显了申采浩力求恢复、维护国家的强烈愿望与意志。
事实上,自1908年起,申采浩便开始使用“现在国民”、“未来国民”等词,与此同时,他还一直使用代表了“国家公民”之意的“国民”一词。另外,“新国民”这一称谓也早已在呼唤国民英雄的《二十世纪新东国英雄》(1909)一文中出现。
嗟尔,新东国、新英雄呀,你要想做英雄,那就用你的喉舌去日夜高呼新国民吧。嗟尔,新东国、新英雄呀,你要想见英雄,那就用你的心血去日夜祝福成为新国民吧。旧国民不再是国民,旧英雄不再是英雄。
以上引文,仅表达了申采浩对“旧国民”的否定之意和对“新国民”的期盼之情,但是并未具体言及“新国民”的概念和,为之实现的相关条件等。然而,在此之前,申采浩不仅阅读过梁启超的《新民说》,而且还在1907年加入了“新民会”。这一系列的行动正是表明申采浩早已对“新民”报有极大的关注。基于这种考虑,申采浩的“新国民”构想有可能在当时便已开始酝酿成熟。可以说,《二十世纪新国民》一文便是他这一构想的最终结晶之作。“新国民”一词之前之所以添加“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概念,就是为了强调当代与前代的不同,使人能够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国权丧失状况下的国民,增强明确的时代意义。因此,对于申采浩而言,实现民族生存和恢复的独立国家建设,最关键的还在于引领“国民同胞走向二十世纪的新国民之路”,从而达到其理想的彼岸,建立一个雄踞于20世纪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盛国家。
申采浩对历史主体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实地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往往借作品中的人物充当自己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和理论实践者。因此,他所勾勒出的“新国民”形象实际上萌动在作品中,而他借助于塑造抵抗外来侵略、展现民族气概的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形象,强调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憧憬着洗刷国耻、富国强兵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包括申采浩的《乙支文德》、《水军第一伟人李舜臣传》以及《东国巨杰崔都统传》在内的大部分历史传记作品,都是在1908年和1909年,即申采浩开始频繁运用“国民”一词时创作出来的。这段时间正值申采浩加入新民会(1907年)开始思考有关国民性问题之时。1909年至19lO年,《每日新闻》连载了申采浩的《东国巨杰崔都统传》。
崔都统乃檀君贤孙,扶余族之代表也。其口可喝除积氛,其手可挽回落日。挥舞凛凛雪白大剑,高呼国家独立之人也。凡我国民,若人人尸视之,人人梦寐之,人人向公之怀抱而迈之,则我国之光照耀天壤,东西列强又岂敢来侮。
在这部作品中,申采浩标榜的“英雄期望论”鲜明地展现了自身所具有的新国民特征。我们从作品中“檀君的贤孙,扶余族的代表”、“为国独立的呐喊者”等称谓中可以看出,主人公崔莹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与民族意识,是一位致力于国家独立的英雄人物,极具新国民的特征。然而,由于当时申采浩的思想依然倾向于所谓的“英雄期待论”,因此,在他笔下的崔莹同样也闪烁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换言之,此时申采浩眼中的历史主体之像还只是停留在《二十世纪新东国英雄》一文中所提出的由“英雄”到“新国民”的转变阶段,即具有过渡性意义的“国民英雄”的认识。行将亡国的严峻现实无不期待扭转时局的伟人出现,刻不容缓的危难时局更不会给申采浩带来更多思考“新国民”问题的余暇。因此,这一时期申采浩的历史传记作品,特别是像《东国巨杰崔都统传》,即便出自与《二十世纪新国民》一文相类似的分析视角,也仍未完全、形象地展现出有关“新国民”的构图。
《二十世纪新民说》发表之后,申采浩便开始了难以回首的亡命生涯。因生活的困境,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以文学树立“新国民”之像的工作,直到1916年,他才创作出展示自己新国民思想的小说作品——《梦天》。作为其代表作,《梦天》讲述了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成长为“天国百姓”的过程。在作品中,申采浩利用炼狱——地狱——天国的三界构造,借助梦幻形式,形象地描绘了其艰险的历程,与此同时,自由展现了新国民的构想。“不论肉界还是灵界,皆是胜利者的棋盘。天堂也只是拳头大者的乐园,拳头无力,便只能落得撵进地狱的下场。”
申采浩对国民性的探究,实际上是对朝鲜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次自我剖析、自我挑战和自我整合,它的核心就是要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近代国民的形象。当然,朝鲜近代初期出现的这一创造性课题把男性作为首选研究对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也恰恰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的男权思想体制下的必然结果,此后,申采浩由“男国民”转而关注“女国民”的可贵之处也在于此。
三
在儒教经典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申采浩之所以将其目光投向女性,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传统的价值观体系已无法解决当下韩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他切身感受到世界已不再仅仅是男人的天下,两千万韩人想要真正独立自主,离不开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的参与,他所倡导的“拯救国家与民族”理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申采浩眼中,女性也是恢复国家的重要参与者,因而期望她们踊跃加入。
彼一般女子深锁闺户,不得出门一步之自由。如此,若想求得体力强壮,无异于却步图步而已。
女性丧失的不仅是自由,丧失的还有对抗世界列强所需的基本体力。很难想象让她们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参与到完成“近代”与“启蒙”这个双重课题的事业中来。为此,申采浩首先把启蒙的目光聚焦在历史与爱国心的关系上。这是由于作者认定历史是决定民族盛衰的重要因素,国民,缺乏爱国心恰恰是由于他们对历史毫无所知。
想要使人们爱国,须使之阅读历史。不仅要让男子阅读历史,也要让女子来阅读历史…(中略)…女子不读历史,恰如堕掉胎内的论介,杀掉襁褓中的罗兰夫人,又等于是残杀掉两千万人口中占据半数的女子,不让她们成为国民。
申采浩以上的论述,切实让人感受到了女性启蒙中“历史阅读”的迫切性。尤其颇具意味的是,申采浩借此表露了自己的心愿,即希冀韩国也能出现如同法国大革命时的女英雄、素有国民之母称谓的罗兰夫人式的女性。这一夙愿与当时申采浩所提倡的“英雄待望论”一脉相承。当然,在申采浩“起草英雄论,唤起新人物”的过程中,目光主要集中在崔都统、乙支文德、李舜臣等男性英雄身上,对于女性人物则是以括号圈之,以示附加之意。或许在申采浩看来,作为当时启蒙对象的韩国女性仍处在襁褓当中,离时代所召唤的英雄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把女性纳入“国民”范畴的这一举措本身,就已经预示了新一代女性正在登场,他非常期望她们能够摆脱过去的愚昧,不断走向成熟。十年之后,申采浩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韩国的罗兰夫人——柳花。
另外,申采浩还积极鼓励、倡导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参与。1907年,他在自己发行出版的《家庭杂志》中,塑造了许多活跃于法院、学校等男性专属场合下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介传统儒生,申采浩能够把女性视为顺应近代化潮流的时代产物,确实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强调女性不应成为男人们的负担,应该“懂得各司其职,自食其力”,而且还把“女工为生力军的纺织社会”作为近代化社会发展的标志。同时提倡了女性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这不仅能够减轻男性的负担。而且也有助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与女性的独立生活相比,申采浩最终还是将着眼点放在了男性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上。事实上,当时申采浩所策划的女性启蒙工作,其重心仍是以男性为主,这点通过女性启蒙的引导者亦为男性这一点也将得到印证,而这并不是申采浩一人所具有的局限性。
伴随着1910年《二十世纪新国民》一文的发表,申采浩眼中的20世纪已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世界,也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世界。为了洗刷丧失所带来的屈辱,建设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寄希望于新国民的申采浩自此正式迈入了一个塑造与构建“新国民”的思想历程。据申采浩所言,20世纪的新国民应区别于以往的旧国民:他们既是具有平等、自由、正义、义勇等公共道德的人格主体,同时也是具有“巩固国民国家基础”实力的竞争主体。由于新国民的实验对象是全体国民,所以,女性也成为了新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申采浩指出“人类是平等的,愚妇也是人”,强调应该将女性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由此,我们也能多少了解到申采浩女性观的变化趋势。由于申采浩艰辛的亡命生涯,使其在作品中暂时停止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其中仅有1916年创作的《梦天》,还多少彰显了有关女性的人格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宁可跳崖葬身于落花岩,成为冤死水鬼,也不愿被强盗玷污、羞辱”的百济宫女们以其坚贞、高洁的操守演绎了亡国的悲壮与惨烈,为主人公“他”点亮了通向“新国民”之路的精神航道。另外,将壬辰倭乱时以巧计砍杀倭将而自杀殉国的义妓桂月香与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德的人们一同置入天国的情节设计也是大有深意。在“恢复国家”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前,树立女性人物作为典范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这也预示着申采浩思想深处的创新,他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意识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应该说,这对后期申采浩女性观的巨大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0年代末,申采浩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女性。“三一”运动和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以及与朴慈惠的幸福相识,无不使申采浩为之心动、深受鼓舞。与此同时,申采浩更加心仪于那些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而涌现出来的20世纪的新女性,尤其是兼备“从容洒脱、坚韧独立”人格魅力的新式女性朴慈惠。这一时期的申采浩还钟情于塑造一心为国培养栋梁之才的“良母”形象,金庾信的母亲和妻子便是申采浩所追求的传统“良母”典型。前者对“出入妓院,尽享浮华”的金庾信严加管教,并使之最终成为建功立业的国家栋梁;后者则把有违家训的小儿子元述拒之门外,使之沙场杀敌、为国建功。归降新罗的伽f耶国后裔金庾信为其完成统一三国的大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十分强调气节的申采浩明知金庾信归降敌人一事,却仍将他塑造为新罗忠臣的原因在于,“凡我韩人,无论内外,只有统一联合方可决定进路,又有独立自由方可树立目标”。所以对于申采浩而言,金庾信是爱国英雄的化身。而金庾信所以能够成为爱国英雄,在申采浩看来,是由于金庾信的母亲引领他走上了正途。早在1908年发行的《家庭杂志》中,申采浩就发表了《金庾信之母》一文,申采浩称颂“金庾信母亲”是“国民之母”,这不仅因为她具有儒家的贤母之德,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引领民众走向正确的“国民”成长之路。伴随着对于朱蒙母亲柳花的再发现,申采浩的这一认识也随之得到深化。从启蒙初期便一直渴望发现韩国式罗兰夫人的申采浩,最终通过对柳花的再认识,找到了这一原型,并最终把她塑造成国民之母的典型,正式引入到自己的文学评论与创作活动之中。譬如《柳花传》,我们首先从题目本身就可发现申采浩力求打破朱蒙神话历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局限性,以此确立起女性意识。
小女姓张,名柳花。住河上流右岸的张大吉乃小女家父…(中略)…月前,北扶余王海慕漱出游。见我三兄弟在川边浣纱,招呼于前,冒犯了小女。父母得知,为申雪陋名,不损家风,将小女投之水中。这是小女命运崎岖,又怎能怨得于你。
为塑造“国民之母”的柳花形象,申采浩可谓煞费苦心。特别是由历史著作中记述的“水神”河伯之女转变为文学作品中的庶民张大吉之女,便使柳花具有了平民性格和现实元素,这也是柳花由王朝国母向“国家”之母转化所必需的第一步。另外,柳花对待解慕漱的求爱不仅没有加以拒绝,反而与之大胆地共享云雨之情;面对父母的薄情,不但没有埋怨,反而默默承受着自己的不幸命运,其中体现着她追求爱情、幸福、光荣的自强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苦苦斗争的精神。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支撑着柳花,使她后来能够审时度势,选择继承檀君一脉的东扶余国国王金蛙王作为保护者,并依靠自身智慧、勇气战胜一切嫉妒、憎恶,甚至是死亡,将朱蒙解救于危难之中,并传输给他远大的理想和不断奋斗的信念,从而使朱蒙最终成为伟大的建国始祖。作为一名柔弱女性,柳花承担了建设崭新国家的重任。与旧时代制度下生活着的后宫们相比,柳花已不再是仅有慈善面孔而毫无智慧的“慈母型”的皇后形象,而是超越了那些时代人物、富有挑战精神的女性形象。柳花身上所拥有的正是危难时代“女国民”们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柳花之所以能够走进申采浩的视野,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在作品中,像仙女乘鹤下凡、护其分娩的柳花出生传说和“柳花并非凡骨,将来必有大贵之兆”的先知预言以及达摩山百岳道人相助和仙姑赐符而险象环生等虚幻情节的设计,都还未能摆脱古代神话创作的神格化色彩和偶然性因素的窠臼。因此,不仅随之产生过分神化、强调“国民之母”神圣性的质疑与疑惑,而且,也从中反映出前期“个人主义英雄”论的残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倘若柳花仅仅是作为养育建国始祖朱蒙的“贤母”形象出现,她不但不能成为历史上为万民敬仰的仁慈王妃,而且也不会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之母”。柳花在成为伟大母亲之前,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妻,她具有体恤丈夫、为其谋求国政安定的“淑德、贤哲”的品性。因此,柳花身上所体现出的尽职尽责的聪慧“贤妻”的形象,同样为申采浩的“女国民”像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据推测完成于1910年代末的《一目大王的铁锥》,也可说是申采浩为塑造近代“贤妻”形象而创作的又一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弓裔的妻子——王后康氏承担了作为一名“贤妻”的职责。
弓裔意欲武力统治百姓,完成统一大业。妻子康氏却力主以“德治”、“仁爱”加以引导百姓,康氏的这一睿智之举可谓跃然纸上。在申采浩笔下,曾经极具革命精神的弓裔逐渐变为崇尚暴力的统治者,而出身微寒的王后康氏正是为帮助弓裔恢复其原本的革命面貌,并树立起一代女性的风范。正如作品中康氏塑造了弓裔的形像,申采浩的这一构思、创作正体现了女性存在的“力量”,肯定了女性成就时代所需男性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无条件服从男性的传统贤妻形象不同,为丈夫出谋划策并助其改邪归正的贤妻康氏无疑是申采浩启蒙思想所酝酿出的杰作。
面对恢复与民族图存的时代课题,申采浩不仅认识到了女性存在的力量,而且还把女性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为将其纳入国民行列而积极努力。尽管申采浩极力倡导西方的近代思想,但他毕竟还是一位传统的儒者,不仅头脑中深烙着儒家思想的印记,而且其内心深处仍存有一种作为精神贵族的优越感。因此对于申采浩而言,转变对女性的意识更属不易,具有圣母性格的柳花和作为大王弓裔之妻的王后康氏之所以首先被选定为“女国民”的典范,恰巧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申采浩构建“女国民”像的下行趋势。譬如,申采浩把桂月香推崇为国民“守节”的化身,柳花和康氏的出身被分别设定为庶民和“农家丫头”等。其中,申采浩创作的《百岁老僧的美人谈》中,被叫做俏丽的贱民女性形象更加凸显了这一下行趋势。与柳花和康氏的形象相比,作为卑贱女仆的俏丽形象更是承载了最终完成构建近代“女国民”的使命。
国家都被敌人征服了,简直是生不如死……你算什么男人?国家都被掠夺,你都不知道夺回来。那你又怎会找回你自己的女人?你算什么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