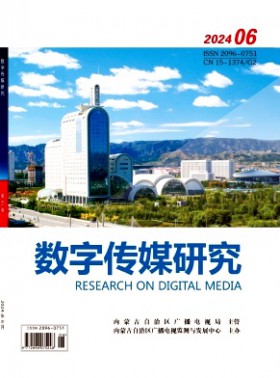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数字孪生在教育中的应用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数字孪生在教育中的应用范文1
【关键词】技术哲学;教育技术;技术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27-0023-04
【作者简介】陈向阳,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南京,210013)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各领域高歌猛进,并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改造。在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同样呈现出一片眼花缭乱的“概念丛林”,人们对多媒体教室、智慧校园、慕课、翻转课堂、微课、混合式教学、大数据、云计算等不断涌现的新名词趋之若鹜,尤其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之后,这些新名词更是伴随着行政介入、资本运作和运动式操作进入到教育技术和信息化实践中去。在这种种合力的推动下,倘若谁不知这一波又一波的时髦概念,俨然就是教育变革的落伍者。然而,当前教育信息化的喧嚣和非理性狂热,不仅未使教育产生预料的系统性变革,反而带来了更多新的问题,要真正理解并把握教育技术的未来,需要审慎的理论自觉与哲学思考。
一、技术乐观论与怀疑论的局限性
在《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中,米切姆指出:“技术和哲学是像一对孪生子那样的孕育的,工程的技术哲学明显具有技术哲学孪生子长子的特点,更偏向于亲技术并注重对技术进行分析,第二个孩子则更倾向于批判和解释技术。”[1]
工程技术哲学的倡导者多是技术专家或者工程师,他们着眼于技术的合理性,坚信由技术的自然逻辑必定会导向其价值逻辑,技术只是实现外部目的的工具与手段,技术专家的使命就是如何使技术更“先进”。这种技术乐观论投射到教育领域就表现为,盲目追逐物化的新技术,认为其必然会推动教育的文明、进步与现代化,由此,在使教学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趣的宣言之下,各种花样翻新的技术不断被引入教育教学中,尤其是博客、移动学习、MOOCs等新技术一时成为时髦话语。当这些新技术不被教师所认可和接受时,技术乐观论者总是把问题归结为教师因循守旧,教师因此成为被指责和培训的对象。这种技术的乐观主义延续了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对技术所持的一贯态度,他们多从工具的视角来看待技术,追求技术至上。
然而,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是否可以如此乐观对待而不加任何批判?在人文技术哲学看来,技术越发展,就越成为一种自主的、异己的力量。波兹曼就始终警惕电子技术对文化素养的侵蚀。在《童年的消逝》中,他抨击新技术,尤其是电视文化,认为电视文化抹杀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危害,影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揭示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人类文化的危害。波兹曼对于技术的批判与质疑的确有助于对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消极作用保持警醒。比如传统的PPT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教学与听讲方式,大家都成为受某种技术逻辑影响的工具,甚至有教师没有电就没办法进入课堂教学,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对人的异化。课件控制了教学过程,从而控制了学生,也成为教师自身的桎梏。
从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来看,以上诸多乱象和观点纷呈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技术哲学。但是,这两种技术哲学都有其突出的缺陷,那就是用工具和实体的思维来看待技术,正如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所指出的,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没有掌握技术真正的本质就无法在人与技术之间显出一种自由的关系。由海德格尔开端,面向具体“技术实事”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将为我们思考和分析教育技术实践提供第三条道路。
二、教育技术应用的技术现象学考察
在教育实践领域,人们已基本形成共识,即教师和学生对于信息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仅要掌握“器、术、法”等层面的有效使用方法,还要构筑“道”层面的关于技术与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等教育技术哲学问题。技术现象学以其人技关系的独特理论,为我们对教育技术实践的学理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援。
“首先,工具不是具有一定属性的简单对象,相反,所谓的工具依赖于一种使用的情境,技术是与具体的使用情境有关的。”[2]海德格尔极力强调情境对于技术存在的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用具的存在方式与情境的关系非常独特:一方面,如果没有情境,用具无法存在;另一方面,只有借助情境,用具与世界现象之间的通达才具有可能。“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单独‘是’用具。存在的一向是用具器物的整体。只有在这个整体中一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3]这实际上启示我们,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仅仅只是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还不能称之为教育技术,唯有在教育世界诸要素(如教育价值、教育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的聚集中,它才真正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现象学分析,为我们深刻理解教育技术的本质开辟了道路。然而海德格尔还主要是从“之外”与“之上”来研究技术,从形而上的抽象层面来反思技术,这种分析方式无疑具有深刻性,然而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固有缺陷。因为他只停留在抽象的层面,把技术处理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而对于教育技术本身所呈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仅靠这种形而上的分析是不够的。从电影、电视、计算机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只有对他们进入教育领域进行具体的经验描述,技术的社会批判才有存在的空间。在技术现象学看来,技术不再只是单纯的、裸的工具,它既向自身敞开,同时也向人与教育敞开,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思考教育技术自身、技术与教育、技术与人等诸多的理论命题。通过对这些命题的揭示,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技术之于教育的深层次意义。
在当代,现象学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以伯格曼和伊德等为代表,使技术哲学出现了经验转向。在伯格曼看来,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适当经验描述上,他的“聚焦物和聚焦实践”的思想正是对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把对“物”的思考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转向了伦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层面。“当我们所用的东西仅仅是用品的时候,我们就剥夺了世界公民的权利。所以我们要通过聚焦实践回归到这个世界的深处,回归我们作为存在的完整性。”[4]在这里,聚焦实践体现着一种“参与的实践”,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技术与教育互动发展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伊德将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体技术和案例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后现象学”。用伊德自己的话说,后现象学是“现象学+实用主义+经验转向”。伊德最著名的经验研究就是其提出的“人-技术”关系四种模式,即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通过这一研究,伊德认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就在于技术与人和世界的相关性”[5]。
通过对现象学技术哲学家观点的简要考察发现,尽管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各异,所提出的克服现代技术的可能路径也不完全相同,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可以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关切,那就是超越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局限,回到技术本身,从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出发,直面人的存在这一根本问题。而这无疑为我们思考教育技术实践提供了极大的启发。
三、教育技术可能方向的现实分析
上述现象学技术哲学发展进路的分析,为我们思考教育技术实践提供了理论背景,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技术宰制,我们既不是天真地接受技术,也不消极地逃离技术,而是深入技术实事本身,洞悉问题的根源与解救之道,这不仅是这个时代紧迫的问题,也是当前教育必须做出回应的问题。
(一)对教育技术的认识:由“装置范式”到“聚焦物范式”
虽然新技术应用之下的教育改革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原有教育中一些本真美好的东西似乎失落了。以伯格曼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根源或许在教育场域中“装置范式”的技术本质观。这一范式揭示了现代教育技术真正的本质,一方面,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知识的传递,另一方面又隐蔽与缩减了事物牵连的整个世界。这一范式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纯技术的运作上,它对人的力量、注意力和思考方面要求愈少,远离了那些富有教育价值与意义的事情。例如,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兴起,黑板在教室里的使用越来越少,代之以硕大的多媒体控制台,教师常常被束缚在台前操作着程序化的PPT,原本在讲台上谈笑风生、充满智慧的教师,成为照本宣科的操作员,课堂不再被作为诗意的存在,教学的艺术世界轰然倒塌。更进一步的,随着传统教室被多媒体教室取代、印刷书本被移动终端取代、学生管理被各种监控技术所取代、师生的面对面交流被虚拟交往所取代……教育最终所追求的目的被丢失了。
面对这样的问题,伯格曼同样给我们提供了解救之道,他并没有简单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回到聚集“天地神人”的“物”的前现代技术之中。在伯格曼看来,物的转变不能是一种取消,更非对技术的逃离,而是要构建一种“聚焦实践”,这种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应为聚焦物和聚焦实践清理出一个核心位置;二是简化围绕和支撑聚焦实践的背景;三是尽可能扩大亲自参与、身体力行的活动的范围”[6]。这也就意味着,教育虽然被各种现代技术所控制,但只要人们仍然从事各种围绕“聚焦物”而展开“聚焦活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当今教育中的技术问题。诸如重构多媒体教室的布局,引入融传统黑板与多媒体功能为一体的交互式白板,打破技术对师生活动限定的可能,营造适合师生互动学生学习的环境等。只有守护着“聚焦物与聚焦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技术教育化。
(二)技术与教育关系的新认识:由“消费”走向“设计”
对于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著名教学设计专家梅瑞尔(Merrill)曾形象地比喻:“教育技术领域的许多参与者很像买新奇玩具的孩子们,总希望他们所在的学校能够启用一些新的技术设备或应用程序,但新鲜感慢慢褪去后,这些最新最好的技术就被蛛网尘封,完全过时了。”[7]回顾20世纪的教育技术史我们很轻易就会发现这一事实,电影与电视教育20世纪初曾获得极大的关注,爱迪生在1913年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在公立学校里,书本将很快过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门类都可以通过动态影像来进行教学。我们的学校系统会在十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8]与此同时,一些影片制作厂家则从中寻求商机,他们“打着视觉教育的旗号,兜售其产品”,并大肆渲染电影在教育中的作用。但这一预言并未得到验证,电影或者电视没有取代传统的教科书。今天,人们同样认为网络将对学校教育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有学者预言,MOOCs将使教育受到颠覆性影响,进而引发系统性的变革。但据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对国内96个慕课平台统计,千余门课程80%基本无互动,只是传统课堂搬家,跟过去的电视教育没有太大差别,慕课越来越像是教材的附赠光盘,没做任何设计就放在网上。
由此看来,技术与教育结合的重点不在于引进最新颖、最酷炫的新技术,亦非教会师生使用和操作这些技术。“仅仅把学习材料放到网上不构成‘学习环境’,仅仅把以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电子化不可能产生显著的学习效果”[9]。只有让技术应用回归教育的本质,围绕学习者进行有效的设计,才有可能避免20世纪教育技术的历史重演。芬伯格正是从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提出“计算机设计不仅在工具意义上是重要的,而且还具有人性的意义,因为在设计工具中我们设计了存在的方式”。[10]这种设计是一种存在论的设计,它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还需要更成熟的人类情感,而这恰恰呼应了当今时代对学习本质的认识,对学习来说,最核心的是情感、情境或者高质量的启发式技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设计”将成为教育技术未来关注的重要议题,每当引入一种新的教育技术时,必须在其设计时就要考虑到对话和情感参与,这种设计活动需要转向艺术化,只有通过艺术化,才能在教育发展的暗礁中走出一条“回归自己的路”。同时,其设计主体绝不能仅限于少数技术专家或者工程师,更要发动广大师生参与其中,他们不只是教育技术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进行消费和表演,而是作为设计者、生产者参与着开发的全过程,他们的价值观念、设计思维通过博弈转化为技术代码。惟此,才能真正设计出更加人性化、受学习者欢迎、充满生命活力的新一代教育技术,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激发无穷的教学智慧。
(三)人-技关系的新认识:从“离身”走向“具身”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不直接发生交互作用,而是需要借助相关技术的支持方可进行。”[11]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正在进入教育的方方面面之时,师生、生生的关系,更要通过人与技术的关系来实现。人们在熟悉数字化技术提供工具、空间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构建一种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文化,由此,揭示人与技术的关系,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至为关键。伊德关于人与技术之具身关系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识框架。在他看来,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总是被技术所中介。在具身关系中,技术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抽身而去”,它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暗中与人发生交互,正是这种方式使技术具身成为可能。当然,完全透明的技术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技术总是呈现部分的透明性或准透明性。教育技术的目标就在于努力实现人、技术与环境的具身,从而让学习者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获得更强的在场体验感。
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看,教育技术发展史体现的正是从离身到具身的转化。从书写、印刷到黑板、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莫不如此,如柏拉图曾强烈谴责,书写技术具有破坏对话关系的能力,而这种对话关系是师生之间的纽带,但随着书写变成习惯,它与人走向具身关系,并开始退居背景,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发展远不像当初书写技术那样缓慢地发展,它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一种技术进入教育领域还未被教育化,就很快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引入技术,把技术作为外在于人存在的一种工具,这种变革注定要失败,诸如目前实施的多项教育信息化工程,包括多媒体教室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都还只是形式上的“新瓶装旧酒”,这种技术根本上还只是离身的技术,即使是当前被认为是开启未来教育的大数据,“如果没有人的加入,依旧只是促使人类快速做决定,依旧是资本大爆炸、技术大爆炸,那么人类是没有未来的”。[12]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这番振聋发聩的忠告,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在将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技术既然已经深深嵌入教育世界,就必须努力实现教育技术的具身转向,构建一个与技术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的教育世界。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3.
[2]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2-43.
[3]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M].北京:三联书店,1999:49.
[4]傅畅梅.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86.
[5]舒红跃.技术与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1.
[6]傅畅梅.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M].辽宁: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88.
[7]戴维・梅瑞尔.玩具、原则和数字化学习[J].开放教育研究,2016(1):4.
[8]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M].赵中建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6.
[9]董丽丽,吕巾娇等.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问题与未来走向――2014-2015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专家视点述评[J].开放教育研究,2015(5):16.
[10]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