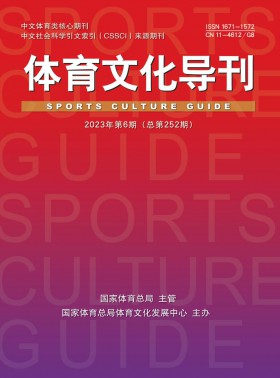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1
角做的研究就寥寥无几了。正如此,笔者对《文心雕龙》正文当中同义词;《文心雕龙》主要版本中同义词以及同义词辨析举例做试探研究。
关键词:文心雕龙;同义词;辨析
中图分类号:G6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一、 《文心雕龙》正文中对同义词的辨析
同先秦其它典籍一样,《文心雕龙》正文当中有不少是为某些体裁的名称作了辨析性的解释或者解释词义的文字,其中更是不乏同义词方面的辨析的内容。这些辨析的材料,其分析角度、分析观点、思
想观念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值得我们加以重视。例如:
“达旨”与“该情”。《征圣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
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
文中既对“达旨”和“该情”涵义的解释,也是对二者涵义的辨析,作者告诉读者,两词相同之处,即都表达意旨,畅述情感。其区别在于方式不同,“达旨”要用简练的语言,而“该情”却用繁赡的
文辞。
“诗”与“歌”。《乐府篇》:“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此段文字中,刘勰对同义词“诗”和“歌”的区别作了总括的解释。其认为凡是乐歌的歌辞叫做诗,把诗唱出来就叫歌了,而古人往往配上音律来演唱歌辞。但是,歌辞太繁多时,便难以配适了。唱与
不唱的不同是二者本质区别。
《文心雕龙》中还有不少同义词辨析的材料,不一一分析,谨择取一二罗列如下,以备参考:
《诔碑篇》:“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谐篇》:“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诏策篇》:“敕戒州郡,昭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昭者,告也。敕者,正也。”
《议对篇》:“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
二、《文心雕龙》主要版本中对同义词的考察
各版本中对刘勰《文心雕龙》的语词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常用的语词上,而且这些语词往往与刘勰的文学文艺思想是结合非常紧密的。从这些常用同义语词的研究中,各家往往站在自己研究从事的角
度上各抒己见,值得后来学者总结及参考。比如对围绕常用语词“切”相关同义语词,诸如“要切”“切今”“切至”“确切”等的研究阐释中,就可以看出各家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情况。例见《辨
骚》:“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各家有不同解读,关系到刘勰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的文学思想是与其普遍的文学思想观念是否相一致,还是与之相反的问题。
现将一些诸家之解读举要如下:
陆侃如、牟世金注:“原文‘切’是割断,‘切今’和‘空前绝后’的‘绝后’两字意义相近。”此句作者译作:“而辞藻又横绝后世。” [1]
周振甫注:“切,切断,绝。”此句他译作:“文辞超越后代。”[2]
祖保泉:“切,恰合。”然其句子解释为:“作品……辞采可润饰后人。”[3]
武汉大学的吴林伯先生对此句解释,其肯定“‘楚辞’的‘辞气’能超越、切合古今。”[4]
詹注曰:“按‘切今’当指切合当前的情景。下文说:‘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可证。”[5]
王运熙、周锋注:“切今,切合今人,意为适合今人学习。”其句子译作为:“《楚辞》气势超越了古人,辞采切合于今世。”[6]
按:陆氏、周氏以及赵氏、冯氏四家注释基本相同,为“切断”之义;祖说“切”为恰合,于义可通。然又释“切”作“润饰”,“恰合”与“润饰”,又无可通了。吴氏释“切”为切合,于义亦可通
。但作者又将“切今”释作“切合古今”,则有悖于刘勰原文的意思。
查“切”字在《文心雕龙》中凡例有三十处,除“辞来切今”外,还有:浅切、实切、要切、清切、新切、激切、辨切(各一例)、确切(二例)共九例与“切今”的“切”无关,另作别解外,其余十
九例,如切至(四例),“切”均不宜作“切断”解。
综述所述,以上数则注释“切”字,虽有所指微有差别,如詹指切合当前情景;王氏说辞采要切合当代需要;王运熙则指切合今人学习。但观点基本分相反两派:一译为切断;一为切合。我们理解句
义时,也要结合刘勰这个时代的思想及文风特点。按照骈文特色“气往轹古”与“辞来切今”两句对用,语词中的“气”与“辞”、“往”与“来”、“轹”与“切”、“古”与“今”等都是一一相反
对应的关系,所以,理解“切”要知晓与其相反的“轹”的意义,而“轹”指车轮碾过,即超越。“切”译“切合”较合适。
三、《文心雕龙》同义词辨析举例
同义词类聚的各个词之间,其意义相同或相近,这是同义词建立的前提。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异才是同义词存在的价值所在,它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准确、
更丰富、更细腻以及更多文采,这就显示了我们祖先高超的语言才能。下面就择取两组同义词加以详细分析,以窥刘勰《文心雕龙》同义词面貌之一斑。
言-謇谔 这组同义词都有正直言论的意思,但语气轻重不一样。“”是说话中理,敢于正言。“言”是正直之言,直言。见《奏启》:“又表奏确切,号为言。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
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言也。”如《汉书・叙传上》:“吾久不班生,今日复闻言!”颜师古注:“言,善言也。”而“謇谔”亦作“謇鄂”。亦作“謇愕”。正直敢言。比“言”又更进
一步表明作者的态度以及操守。例如《隶释・汉绥民校尉熊君碑》:“临朝謇鄂,孔甫之操。”又《后汉书・陈蕃传》:“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华首弥固。”
悲-恸-恻怆-恻怛-怛惕-怊怅-惆怅-怆怏 这组同义词都有表示悲伤、悲痛的含义,但悲的心理轻重程度是不同的。“悲”字在《文心雕龙》出现十例,基本意思为一般的悲哀、悲伤心情。如《
诔碑》:“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哀吊》出现四例,以“悲”、“悲苦”、“会悲”语词出现。“恸”,表达一种极度的悲痛。比“悲”更深,只有一例,见《哀吊》。先前
如《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同时代的《梁书・王份传》:“袁粲之诛,亲故无敢视者,份独往致恸,由是显名。”“恻怆”与“恻怛”都表示悲痛,忧伤。均见于《哀吊》。“怛惕”,
悲伤,忧惧,带有某种恐惧的心态。例子见《养气》。“怊怅”与“惆怅”语义相同,表达一种心情惆怅,失意的样子。出现三例,分别例见《明诗》、《风骨》、《序志》。“怆怏”,形容悲愁失意
的状态。见于《辨骚》:“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
总之,此组同义词在表达悲痛,忧伤,失意的状态时,其语义轻重是不同的。悲的程度“悲”与“恻怅”、“恻怛”轻于“怊怅”和“惆怅”,其中“恸”和“怆怏”是最重的。
参考文献:
[1]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选译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
[2]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4]吴林伯.义疏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2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017-01
令沈约“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的《文心雕龙》著成以来,始终在文论的天空牵动着人们的视线,由于“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跟着文学风尚的不同而变化的”,所以才会有“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才略》)的现象,进入西风“浸润”的二十世纪,“龙学”的研究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计论文共2900多篇,研究专著215种,但面对“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的“文囿之巨观”,我们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仍有很大的分歧。
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将《征圣》、《宗经》置于前,整部著作都充盈着对“圣”、“经”俯首帖耳的形象,一个最典型的证据是在《辨骚》篇中分析楚辞与经典的异同时,他评价神话传说是“诡异之辞”、“谲怪之谈”,认为屈原投水是“狷狭之志”,《招魂》中所述的宴乐是“荒之意”,其实这些都是“以管窥天”,缺少前后联系的辩证思维,没有真正把《文心雕龙》当做“体大思精”的系统理论著作。
对于神话的态度,刘勰在《正纬》篇里指出纬书的价值方向时就已经明了了,可从用典和辞采的方向考虑纬书中一些神话故事的价值。至于所谓“狷狭之志”,刘勰在《程器》中明确赞美屈原的忠诚:“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至于“荒之意”可联系当时刘勰的创作背景即可理解。即使是这样,刘勰还高度肯定了楚辞在文体方面的开创意义,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楚辞异于经典之处,正是刘勰指出来的新文体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他并不是要否定楚辞汉赋,而是反对由楚辞汉赋所产生的流弊。
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面对文学的发展,虽然许多人会固守前篇,但大部分还是持革新的发展观,刘勰的《通变》正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文论。“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风骨》),他讲了通变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那么同样是“通变”,是像时期某些“全盘西化”论者那样下猛药,丢弃一切文化地基而筑空中楼阁,还是如吴宓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智态度?刘勰的“望今制奇”加“参古定法”(《通变》)就给出了最智慧的答案,一些指责刘勰的“通变”脱不掉圣人的“紧箍咒”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时至21世纪,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呼求,是在我们的学术与文化遭遇到外来文化“空降兵”之后水土不服而发出的,那么通变观理智的做法应如吴宓所言“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以此来反思刘勰的通变观,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大的文学发展观上去看待“通变”,它的地位无可厚非。即使是从小的方面处理创作中的小问题,“通变”也会显示出能斩开死结的神奇作用。例如“章句”的处理,总的要求是“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但问题是复杂而不一致的,所以刘勰又指出要“随变适会”。而且他能辩证地看到“变”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黄唐淳而质”到“商周丽而雅”是积极发展,从“楚汉侈而诡”到“宋初讹而新”(《通变》)是趋时倒退,他能看到文学发展之路的曲折,极力要求把变而衰挽到变而通。所以他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而有些东西是非变不可的:“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弗莱有相同之处,弗莱从文学的整体性、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来看,“艺术既不进化也不改善,这是批评领域的一种常识:艺术仅生产经典或典范作品”,他认为变化的只是技巧。
既已确立了通变观,那么接下来就是怎样去“变”的问题了,刘勰提出了“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度”之法,突出了情理与才华,并非把儒经作为亘古闪亮的恒星。对于“词赋之英杰”的楚辞,作者认为它的变化是“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时序》)。楚辞的成功,不论是在文体创新方面,还是文辞的新变方面,作者都将之归因于“纵横之诡俗”,这里就离儒学更远了。为什么刘勰会有这种对儒学若即若离的态度呢?石家宜的观点似乎更能令人信服:“并非‘通’、‘变’对举,而是以‘变’求‘通’。”他指出了“变”只是手段,而“通”才是目的。
这种“通变”观遭遇到实际问题时,刘勰是怎样处理的呢?比如是否会弥合文学的分流与融合,即各个时期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的对流。《时序》中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他认为属于俗文学的“歌谣文理”会成为“风”而引起“波震”,所以牟世金所言刘勰“坚定不移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来立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刘勰思想上不可能有什么地位”就不那么确切了。刘勰若不是停止企首而望并蹲下身来审视同是下层阶级民众的感情,怎会有“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谐隐》)的对普通受迫人群的文化认同感?他在《颂赞》中指出俗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意在微讽”、“抑止昏暴”,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美刺观,所以“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颂赞》)。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俗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明诗》)这句话在五言诗的起源探索方面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所以有人说“实际上,刘勰的很多表述证明了他是雅俗互补的”。
总的看来,刘勰的“通变”观渗透在文学发展的各个方面,那么对于儒经,他不是以“敷赞圣旨”为目的,而是以“通变”为筛子来选取利用某些儒经观点,并进行改造与发展,他严守师说、溺于儒经的可能性非常小。“把刘勰的理论放在当时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刘勰文学的进步意义就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所谓《文心雕龙》在政治上‘搞复辟倒退’,在文学上‘搞颂古非今’的种种责难,是一种违背历史的苛求。”我们从刘勰的文学通变观溯至他的“宗经”问题,认为此说比较中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进步意义,对待《文心雕龙》的正确态度是“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征圣》)。穿过“精义曲隐”、“微辞婉晦”,真正看到“正言”与“体要”。
参考文献:
[1]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319页.
[2]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3]张少康等编.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5页.
[5]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97年.
[6]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24页.
[7]石家宜.〈文心雕龙〉系统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8]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第8页.
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3
[关键词]理解(understanding);视域(perspective);原道;文;终极依据
一、《文心雕龙·原道》篇对“原”与“源”的区别使用
《文心雕龙·原道》的首段经常被看作是概括地说明了作者对文学起源问题的看法①。按照这样的理解,刘勰在这里是确立了自己“文源于道”的观念。可是,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之“原”为:“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1]《稗编·文艺》解“原”为:“原,按韵书,原者本也,一说推原也,……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2]从《序志》篇“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一句来看,对刘勰《原道》篇之所谓“原”的意义的理解当取高诱注为宜。此处之“原”用作动词,“本于”之意,亦即“探究(根本)”的意思。“原道”就是本于“道”,若就刘勰此处论“文”而言,则“原道”之意为“探究文之根本”的意思。而且,从整部《文心雕龙》来看,刘勰对“源”与“原”的使用是有明显区别的。《文心雕龙》中在要表达source或origin的意义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使用了“源”字,而且这样的用例很多。“原”字在差不多所有的场合,都是用作意为“探究(根本)”的动词,如《原道》篇“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定势》篇“原其为体,讹势所变”等。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详细论证。他认为:“刘勰把‘原’作为意为‘探究’的动词,‘源’作为意为‘本源’的名词,在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3]因而,我们在此首先确立《原道》之“原”意为“探究(根本)”的观点,“原道”就是本于“道”,刘勰此处论“文”言“原道”,其意实为“探究文之根本”,即“文原于道”而非“文源于道”,《原道》篇讨论的是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问题,而不是文学的起源问题②。
其实,清代学者纪昀对《原道》篇的点评也是意在揭示此篇“探究根本”的实质的。纪昀在此篇开头眉批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4]纪氏在此明确指出,刘勰以“原道”作为整部《文心雕龙》的理论起点,实际上已显示了其胜人一筹的卓越的理论天赋,这同时也是其作品得以高于汉魏六朝其他文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纪昀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5]这就进一步明确指出刘勰之“原道”意在论“文”而非“载道”,并且,“原道”的目的在于“明其本然”。这一评语,已明确道出了刘勰《原道》篇的主旨在于“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而非“文源于道”。所谓“明其本然”,亦即“探究根本”之意,而所谓“根本”,实际即是探寻“终极”的问题。在自己整部作品的首篇首段,刘勰开宗明义,探讨文学的本原,明确自己关于文之终极的观念,即“文原于道”,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道”是天文、地文、人文得以存在的终极依据,即本体。
刘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是使《文心雕龙》在当时及后世的文论著作中得以胜人一筹的重要原因之一。罗素思考为什么智者哲人于思想的运作中无法逃避对本体论的建构时,曾把这一疑惑归结为生命主体对“永恒”的追示:“追示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研究哲学(本体论)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6]其实,刘勰思考“文原于道”的时刻,也正是他追示“永恒”的时刻,在刘勰的观念里,“永恒”就是“道”,“道”是天地万物得以安身立命的终极。
二、“文原于道”是刘勰对“圣人之道”作出的“现在”的“不同理解”
“道”的原初意义,就是指涉“道路”。许慎在《说文》中所诠释的“道,所行道也”[7],《尔雅·释宫》的“一达谓之道路”,即是在“道路”的意义上对“道”进行的阐释[8]。在这里,“道”是一个描述形而下之客体的实物名词。以后,“道”的意义从规定人的行动方向的道路,引申、转型为主体所遵循的一种抽象的道理、准则、规律、道德、道义与信念等。但是,同为抽象名词的意义,在具体不同的语境中,“道”的使用已经含有本体与非本体的区别。如《孟子·尽心上》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9]在这里,“道”应该只是作为非本体的道德伦理意义上使用的儒家之道。而《周易·系辞上》言:“一阴一阳谓之道。”[10]《韩非子?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辑也。”[11]此处所言之“道”则是在世界的终极本体的意义上使用的。
刘勰的《原道》篇有七处使用“道”,其中只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句,是说明由“道”派生、衍化而形成文学的过程和方式,即自自然然的道理,其“道”的意义的使用是在现象界层面的使用;而其余六句均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的使用,指的是宇宙万物(包括文学)的本原和终极,是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
可是,问题在于。刘勰在《原道》篇中所“原”之“道”,即作为天地万物的终极依据之“道”,并不在儒者所理解的居于现世的“圣人之道”中。在《灭惑论》中,刘勰有关于形上之“道”的论述。他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12]而这一形上之“道”,在思想上显然更为接近道家之“道”。《庄子·大宗师》篇有叙述万物因道而生化的一节[13],《韩非子·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辑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14]《淮南子·原道训》曰:“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鳞以之游,凤以之翔。”[15]《庄子》、《韩非子》与《淮南子》都认为万物因道而生化活动,《韩非子·解老》篇和《淮南子.原道训》之说显然属于《庄子》的理论范畴。
可对儒家而言,我们知道,尽管孔子有所谓“一以贯之”之“道”,但由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之“不可得而闻”[16]。所以,至少在先秦儒家的观念里,对“圣人之道”的理解还是限于处理现世实际问题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思路。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7]可见,曾子所体察到的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乃是“忠恕”。《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8]这里明确“孝悌”是本。荀子释“道”也强调:“道也者,治之经理也。”[19]“忠恕”、“孝悌”及“治之经理”之“道”,终究未能脱离以具体阐释和实践伦理道德为特征的窠臼。到了汉代,依翼奉的解释,“道”是“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示圣人”的“天道”[20]。这种“天道”可以直接映射于社会政治,可以“知王治之象”[21],其实也还是一种现实性极强的思路,并未达到宇宙的终极问题的讨论。显然,刘勰所谓之“道之文”之“道”,并不是儒家所谓“忠恕”、“仁义”的“圣人之道”;而就“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夸饰》)而言,作为万物、包括“文”之终极依据的“道”,根本就不在文字描摹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刘勰的“文原于道”呢?
伽达默尔以为:“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22]“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3]这也就是说,理解不仅仅是单纯的重复过去,而是要参与到现在的意义中来。这也是本文所谓之“现在”的“不同理解”的立论根据。
刘勰生活的六朝时期,正是经学的玄学化时期。这一时期,面对着“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的尴尬[24],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们援道入儒,以道家思想去融摄儒家思想,从“以无为本”立论,将“圣人之道”理解为“无名”与“无体”之“道”,以《老》、《庄》解释《周易》和《论语》,对儒家经典做出了“不同方式”的理解,使儒家思想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重新”的、“创造性”的诠释和发挥①。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刘勰也不得不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是凭靠着怎样的依据,上达“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崇高地位的?而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刘勰对“圣人之道”作出了“现在”的“不同理解”,即援用经学玄学化的思路,将“圣人之道”理解为“无名”与“无体”之“道”;再经由圣人体道而有“经”的途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从而完成了对圣人之文——“经”的本体论意义的建构。
在此,正是借着“圣人”这一中介,刘勰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文”联系了起来。尽管,作为本体的“无”或“道”是无名无形、无声无奥、超言绝象、不可感知的,而言象究竟出于“道”,正所谓“形器易写,状辞可得喻其真”,形器、万有是可以感知、摹拟、界说和规范的,加以圣人天成、智慧自备,圣人体“道”而有“文”,“道”凭借“文”而得以显明,圣人之文就是“经”。这样,本体之“道”就经由圣人显现在“经”中,“经”是圣人所著而体现着“道”的,所以“经”也就是“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的命题得以成立。以“经”为“宗”,也就是以“道”为“本”。汤用彤以为:“宇宙之本体(道),吾人能否用语言表达出来,又如何表达出来?此问题初视似不可能,但实非不可能。”[25]“滴水非海,一瓢非三千弱水,然滴水究自海,一瓢究为弱水。若得其道,就滴水而知大海,就一瓢而知弱水。故于宇宙本体,要在是否善于用语言表达,即用作一种表达之媒介。而表达宇宙本体之语言(媒介)有充足的、适当的及不充足的、不适当的,如能找到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媒介),得宇宙本体亦非不可能。”[26]
在刘勰的观念里,所谓“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媒介)”,就是“圣人之文”——经,刘勰又称之为“恒久之至道”。这一“恒久之至道”——经,由“圣人体道”而来。圣人是真正把“道”和“经”认为一体的人,本体即在万有之中,非在万有之外而另为一物。因而,“原道心以敷章”,则“道”和“经”自然是统一的,即“经”是“道心”与“圣人之心”合二为一的“道之文”,是终极本体的显现。在这样的高度,万世之文的典范只能是“经”;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经”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作为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的崇高地位就能够得以确立。
很显然,刘勰《原道》、《征圣》、《宗经》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儒家之“经”找到终极的形上依据。他之所以对“经”之形上依据进行追问,并最终以“原道”做出回答,其真正目的正在于显露“经”的真正强大——“经”是世界之终极本原在现世的显现,“经”是“道之文”。有了这一依据,“经”作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地位就自此更加坚固而不可动摇。
三、“文原于道”之“文”作为“道”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
《文心雕龙》首句言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就已经为“文”确立了一个远远高出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的崇高地位:“文”与“天地并生”。
刘勰认为:“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天地之文”“盖道之文也”,“文之为德”之“大”即在于“天地之文”是“道”本体的外在显现。那么,“人之文”又是什么呢?
刘勰先给人的位置定位:“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位于天地(两仪)之中的,是天地灵气之所钟聚的人,天地人合称为“三才”,人在天地间处于与天地并立的地位。天地本身是“道”在现象界的显现。那么,与天地并立的“人”的位置,也只能立于现象界而成为终极本体“道”的一种显现。“天之象地之形”为“天地之文”,“人之言”即为“人之文”,这样,“天地之文”和“人之文”,都是“道”本体的显现形式。天文、地文、人文之“与天地并生”的地位是由于它们都是“道之文”的缘故,是宇宙终极在世界、在现象界的显现。同样的道理,“人之言”之有“文”,即有“文采”、有“文饰”,也如同天、地之有“文”一样,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文原于道”之“文”作为“道”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实际上也就是汤用彤所谓之“表现天地自然之充足的媒介”[27]。于是,“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龙凤、虎豹、云霞、草木”,自呈“形文”;“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又显“声文”,这些“无识之物”尚且“郁然有采”,作为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当然必有其文——“情文”。这一“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到“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的模式,与《情采》篇所谓“形文”、“声文”、“情文”的模式是一致的,天地万物都有“文”,天地万物之“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在于“道”。汤用彤用一句话明确了这一观念:“宇宙之本体(道)为一切事物之宗极,文自亦为道之表现。”[28]
纪昀所谓明“当然”与明“本然”的不同及黄侃《札记》所说“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29],不仅在于明“当然”与明“本然”的不同,而且也在于“道”的含义的不同。范文澜指出:“按彦和于篇中屡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综此以观,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30]从“自然”的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这是正确的。但接着又说:“亦即《宗经》篇所谓‘恒久之至道’。”[31]“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32]这就又把问题搞糊涂了,读来难免“汗漫”之极①。真正明白这一问题的是刘永济。《文心雕龙原道篇释义》在解释“道之文”时解释得更为明白,他说:
此篇论“文”原于道之义,既以日月山川为道之文,复以云霞草木为自然之文,是其所谓“道”亦自然也。此义也,盖与“文”之本训适相吻合。“文”之本训为交错,故凡经纬错综者,皆曰文,而经纬错综之物,必繁缛而可观。故凡华采铺芬者,亦曰文。惟其如此,故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兽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乱者,皆自然之文也。然则道也,自然,文也皆弥纶万品而无外,条贯群生而靡遗者也[33]。
在此,刘永济首先明确“文原于道”,随后确定“道”即“自然”,而且,这一“道”“条贯群生而靡遗”,对“道之文”做出了准确的解释。另外,在《文心雕龙校释》中,他又强调:“舍人论文,首重自然。……此所谓自然者,即道之异名。”[34]
刘勰生活在一个玄风大盛的时代。当玄学家们的目光由对社会伦理和天地起源等具体问题的规范和描述,进而深入到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和终极原因的时候,当他们开始研究万物万事万有即现象界之上、之后是否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的时候,处身其中的刘勰在构筑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厦之时,也禁不住地要追问“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很显然,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根”即“本”,即“原”,而“源”就是“经”,也就是要“宗经”之前必须先以“原道”、“本乎道”,而“原道”、“本乎道”也就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态度,即“文原于道,明其本然”。在这里,刘勰至少认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回答了文学的本体问题,才足以“立家”。事实上,正是刘勰对“立文之本”在于“道”的思考,使刘勰的文学理论得以在理论与逻辑上更加严密与周全。惟其如此,《文心雕龙》才能够赢得“体大虑周”的美誉。从“本体”、“终极依据”的视域透视刘勰“文原于道”的文学观念,可以从形上角度对这一观念做出“更好”的“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1][15]高诱.淮南子注[M].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pl,p1.
[2]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M].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日]兴膳宏.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4.p8.
[4][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l,p1.
[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p74.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75.
[8]郭璞,邢昺.尔雅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p2598.
[9]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p2770.
[10]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p78.
[11][1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p107,p107.
[12]僧佑.弘明集[M].四部丛刊初编(子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p12.
[13]王先谦.庄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p27.
[16][17][18]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p2474,p2471,p2457.
[19]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p423.
[20][2l]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p2372,192372.
[22][23]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 The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NewYork,1975.p264,p264.
[2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p240.
[25][26][27][28]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99,p199,p200,p197.
[2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p3.
[30][31][3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p4,p3.
[33][34]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p4,p2.
①按:王元化、陈伯海、孙蓉蓉等皆持此说。参见王元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见《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陈伯海《(文心)二题议》(见《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4页)。孙蓉蓉《“文原于道”与“文以载道”》(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编,文史哲出版社民国八十九年版,第127页)。
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4
关键词:评“曹”;“扬”非全“扬”;“抑”非全“抑”;《明诗》;《乐府》
本论题的直接启示源于《文心雕龙》的乐府篇和明诗篇中对曹氏作品的文字评述。《文心雕龙・乐府》篇指出:“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认为,到了魏国的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虽然“气爽才丽”,但他们“宰割辞调”,实在是音调浮靡,节奏平庸。看他们的《苦寒行》、《燕歌行》等篇,不是叙述宴会,就是感伤羁戍之苦,情志放荡,文辞哀怨,“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贬抑之辞,可见一斑。然而,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刘勰却称赞建安诗(以曹氏集团为代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等,褒扬之情,溢于言表。同一位评论家,同样的品评对象(曹氏作品),前后的品评差异竟如此之大,颇令人费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笔者结合《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文艺观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就文本自身来看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诗、乐、舞三位一体,都是因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产生,且互生互补,达到对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可见,诗与乐相融在一起的传统在我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源远流长,谈诗常涉乐,论乐也每每谈及诗,这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事实决定了这一点。《明诗》篇言“诗”,大家都很明确,自不必赘述。那么,《乐府》篇呢?《乐府》篇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本心术”,“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等,《乐府》篇在强调一种可以入乐的诗,其着重点在“乐”上。然则,诗乐一体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具体把诗和乐府分开来确实不易。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通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混淆也”。黄氏还说:“诗乐界划,漫汗难明”。可见,把诗与乐府作一区分实非易事,而刘勰肇其始做了这份工作,在《明诗》篇之外再作《乐府》篇,把乐府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来看待,与诗相区别。“抑”非全“抑”和“扬”非全“扬”便是在这样的文论语境中实现的。
(一)“抑”非全“抑”
《乐府》篇中道:“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在批判“魏之三祖”的作品是一种浮靡的音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的风格与作品,说他们“气爽才丽”是很不错的,只是在改作歌辞曲调时,难免“音靡节平”。并且,刘勰还肯定了他们的乐调,称其为“三调之正声”。在《乐府》篇的后半部分,刘勰提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夸曹植、陆机都有好的乐府诗,这明显是对曹氏家族之人曹植的乐府诗创作有褒扬的意思。另外,刘勰在对“魏之三祖”品评的态度上,语气缓和,言辞客观,只是站在一个评论家的立场上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出来而已。总之,从全文的语境上和文本自身来看,刘勰对“曹”(包括曹操、曹丕、曹植、曹)作品的品评,绝不全是贬抑之辞,其有自己内心的尺度。此所谓“抑”非全“抑”。
(二)“扬”非全“扬”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所同也。”刘勰在《明诗》篇中赞建安诗(以曹氏集团为代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妨仔细推敲一下此段文字的表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肯定的是曹丕(文帝)、曹植(陈思王)的为文气势与才力,称赞他们为文的气势“慷慨”,才力“磊落”;在表达感情,述说事理方面,他们不空谈,即“不求纤密之巧”,只求把自己要表达的感情、事理充分地表达出来,即“唯取昭晰之能”;此外,刘勰对他们的文思驰骋而有节制也有肯定,如“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那么,“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又该作何解呢?这实际上是对“文帝陈思”等建安文人的写作内容的某些方面的客观陈述而已,并不具备褒扬的色彩,确切来说,刘勰对建安文人的写作内容是没有做具体评价的,以沉默来表示“中立”的观点。并且,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来看,刘勰是有着很明确地反对浮靡文风态度的文人,自然,他并不赞赏文学创作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为内容。本段可以说明刘勰赞赏“曹氏”等人的为文气势与才力等,但并不代表刘勰也赞同“曹氏”等人文学创作的某些内容。所以,可以说,刘勰在褒扬建安文人(以“曹氏”等人为代表)创作的时候,也是有选择性的,此即“扬”非全“扬”。
(三)凸显了刘勰文艺观的理性意识
由以上论述很容易得知,在刘勰的心目中,“诗”与“乐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刘勰在《明诗》篇之外再作《乐府》篇,把乐府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来看待,与诗相区别,这便是一个明证。在《明诗》篇和《乐府》篇中,刘勰对以“曹氏”为代表的作品创作的品评态度前后不一样,这恰恰是“诗”和“乐府”的两种不同标准在刘勰文艺思想中的具体显现。再者,在具体的品评过程中,刘勰是有选择性的,“抑”非全“抑”,“扬”非全“扬”,一切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尽量给出客观实际的评价,就事论事,就作品论作品,尽量不过多地参杂作者本人的主观臆断或感情,尽量还原作品本身所昭示的文学因素等。这一切,正是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家伟怀的体现,凸显了刘勰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家其文艺观的理性意识。
二、“抑”和“扬”:刘勰不同的“乐府观”和“诗歌观”在双重展现
通过对刘勰评“曹”的前后矛盾性分析,可以看出刘鳃在《文心雕龙》的《明诗》篇与《乐府》篇中表现了不同的诗学态度, 在《明诗》篇中,让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出其对建安诗人(以“曹”氏为代表)的褒扬之情(虽“扬”非全“扬”),在《乐府》篇中却颇有贬抑之词(虽“抑”非全“抑”)。这是为什么呢?前文已经论及,诗与乐是不分家的,刘勰却肇其始把诗与乐府作了区分,把乐府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来看待,与诗相区别。这就决定了刘勰的“乐府观”和“诗歌观”是不尽相同的。在刘勰的评论体系中,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其的文艺观中同时展现。
刘勰在《乐府》篇中贬抑“魏之三祖”的乐府诗,实际上是从“乐”的角度来考虑的,批判他们“宰割辞调”时,“音靡节平”。这里的“乐”实际上是指可以配乐演唱的乐府诗,特别是被朝廷音乐机关采撷、加工的配乐诗歌。在这里,刘勰是从社会政教的层面来看待乐府诗的,重视乐府诗的社会作用。刘勰把乐府诗独立出来,就是要让乐府诗承载诗歌的社会政教作用。“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刘勰认为,乐府音应该就是像《韶》、《夏》一样的“中和之响”,可以“化动八风”,雅正的音乐可以教化人心, 可以杜绝放荡之风。又说“师旷觇风于盛衰, 季札鉴微于兴废”,贤明之人能从乐歌中体会国家的治乱兴衰;换言之,乐应具有反映国计民生、以资施政借鉴的功能。刘勰如此强调乐府诗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当时的南朝之际,浮靡之风盛行,统治阶层的许多人也都沉浸在靡靡之音中,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 王侯将相, 歌伎填室;鸿商富贾, 成群, 竞相夸大, 互有单奇。”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诗坛的绮艳之风自然盛行。为救时弊,刘勰的“乐府观”自然是有现实意义的。刘勰对“魏之三祖”乐府诗的批判,实际上隐含了对当时统治者的劝谏之情。“魏之三祖”都曾担任过三国时魏国的最高统治者,刘勰希望当朝统治者能对时局有所反思。
在《明诗》篇中,刘勰充分地肯定“文帝陈思”的为文气势与才力,称赞他们为文的气势“慷慨”,才力“磊落”;在表达感情,述说事理方面,他们不空谈,即“不求纤密之巧”,只求把自己要表达的感情、事理充分地表达出来,即“唯取昭晰之能”。这充分说明刘勰对一般的诗歌的评判标准与乐府诗不一样。对于一般的诗歌,刘勰重视其作者创作风格的张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重视其作者感情的抒发,“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换言之,刘勰认为一般的诗歌评价标准,应该注重个性,注重诗人真实的情感的抒发,不刻意去强调其社会政治作用。在《明诗》篇首句,刘勰已经为一般的诗歌定好了基调,“人禀七情, 应物斯感, 感物吟志, 莫非自然。”所以,刘勰在《明诗》篇中对“曹氏”的肯定,是因为他从诗歌是用来抒发感情的、表达个性的纯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品评的。这正是刘勰区别对待“乐府“与“诗”的具体表现。
总而言之,刘勰在《明诗》篇和《乐府》篇中对“曹氏”作品的品评前后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前者重“扬”,但“扬”非全“扬”;后者重“抑”,但“抑”非全“抑”。前者采用了评诗的标准,重视抒情,重视个性;后者采取了评乐府诗的标准,重视回归乐府的社会功用,注重政治教化。确切来说,刘勰对于诗,虽也考虑到其社会功用,但他更偏向于诗言志抒情的一面,注重个性;而对于乐府,则极力强调回归乐府本身的教化职能,期望中正和平之音的出现。这两者的区别对待,表明了刘勰对于诗与乐府本质的理解已不相同。这正是刘勰不同的“乐府观”和“诗歌观”在作品品评中的双重展现。
三、结语:刘勰评“曹”的启示
通过对刘勰评“曹”的前后矛盾性分析,让读者体会到了刘勰对文艺品评的理性思考,体会到了刘勰不同的“乐府观”和“诗歌观”在作品品评中的双重展现。但是,前文已经提到,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的传统就是诗、乐、舞三位一体,具体来说,乐府与诗根本就是无法绝然分开的。刘勰非要把“乐府”独立于“诗”以视区别,特为重视“乐府”的政治教化的社会功用,要求缔造“中和之音”,以正“风化”。这在许多人看来,颇有不尽妥善之处。然而,我们的思维为什么非要局限于此呢?许多文艺现象因为曾经是一体的,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就不能成熟而独立么?就意味着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衍生出其他的一些标准么?答案当然是否。刘勰在评“曹”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乐府”与“诗”的不同的品评标准,给世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惑与不解。“乐府”与“诗”怎么能分开呢?恐怕刘勰也不能绝然地把“乐府”与“诗”分开,他们始终是同宗的。言及于此,似乎有点意思了,同一宗室下是可以派生出很多支系来的。刘勰“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乐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来研究的开创之功则还是很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的”,这体现了一个文艺批评家的理性意识和敏锐眼识。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新1版.
[3]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06年5月第1版.
[4]詹著:《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5]单书安:《乐府文学研究的开启――浅议刘勰的乐府论》,《南京社会科学》(总第57期),1993年5月.
[6]赵红爱:《诗声合一,中和之响――刘勰乐府观探赜》,《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26卷第4期.
[7]赵明正:《刘勰的汉乐府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5 年第5 期(总第1 3 4 期).
[8]李瑞卿:《刘勰篇研究――与篇比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第25卷第1期.
[9]张云婕:《诗声合一,中和之响――试论刘勰乐府观》,《社科纵横》,2006年7月(总第21卷第7期).
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5
【关键词】曹丕;曹植;文心雕龙;刘勰
刘勰《文心雕龙》凡十卷五十篇铺排论文,是于古未有之盛事。自斯时起,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崭新而越发自觉的时代。其中引上古即今作家逾二百余家,其论精当准确,处处表现出了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评论家的风度与博大。其中对曹氏兄弟――曹植、曹丕兄弟二人,更是有饱满的情感。通读《文心》,可以看到刘勰对于陈思、文帝的不同论述,本文便意欲在《文心雕龙》的视域下,通过解析,来还原在刘勰时代对曹氏二兄弟在诗文创作、文学批评不同领域的优劣得失,以此来更好的认识刘勰的文学观。
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文心雕龙》关于曹植的论述共有23条,分别出现在:《明诗》、《乐府》、《颂赞》、《祝盟》、《诔碑》、《杂文》、《谐》、《封禅》、《才略》、《章表》、《神思》、《定势》、《声律》、《事类》、《炼字》、《隐秀》、《指瑕》、《时序》……而提及曹丕的论述却只有8篇之多,分别在《明诗》,《时序》、《诏策》、《才略》、《总术》、《知音》、《程器》、《书记》……其中兄弟二人一同出现的,是在《时序》《明诗》、《才略》中。
在二十三和八这两个数字中,我们不能认为作者对兄弟二人的厚此薄彼,相反,他抓住了植丕的不同特点,精当准确的评价了他们对于当时时代文学风气所付出的责任。
首先,是在创作论上,刘勰完全表达了他的很精准的文学敏感,尤其表现在对曹植作品的恰当评价上。
曹植的诗歌才能是刘勰最欣赏之所在,而至今陈思古诗乐府也依旧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佳制。他甚至不惜篇幅的去赞美:“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乐府》)
而至于文章,刘勰则保持了一种批评家的冷峻,他除了对曹植的表,进行了“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的称赞外,对其它都有不同的微词,如言诔碑则曰“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言封禅则说:“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至于杂文的“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则逐渐接近了曹植为诗为文的本质――才子气。
因之具有“子建援牍如口诵”神思的曹植,就难免会犯一些诸如用错典(“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措辞不当(“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的纰漏了。
即便如此,在《文心》的字里行间依旧可以看到刘勰对于这位文采飞扬,天下才独占八斗的文人的喜爱之情,对他在艺术创作中的笔法、声情并茂的作品往往都以一种典范的态度介绍给世人。
比较而言,对于曹丕――魏文所在创作方面表现出的才华,刘勰却并没有过多的溢美,除了说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外,便说了他的辞赋“妙善辞赋”。妙善二字与前面所述对曹植的不遗余力的赞美是大不同了。而对他的贡献更专注了在“副君”之位上。作为一种号召力,曹丕对于其他周边文人的创作应该是建安时期文学的更重大的关键。
陈思魏文在他们各自的地位上,承担了建安一代文学创作上应有的责任,我们今天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不说是刘勰对于文学客观而精准的评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在文学批评上,《典》《书》之间。
曹丕的最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便是《典论・论文》了。这一点,刘勰虽然说“魏典密而不周”,却在很多观点上对他表示了强烈的认同感。如“?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便是《典论》中核心文论思想之一的“文气说”。再如《程器》云:“《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施,垣墉立而雕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是《与吴质书》不护细行之意的扩展,其他如文人相轻(“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文体论等,无不是刘勰在《典论论文》这块沃土上继续完备而来的。
反而对于曹植的某些文学观点,刘勰是不大赞同的。《与杨德祖书》是可以代表一些曹植文学观点的文字了。而他以“辩而无当”冠之,这其实也确与曹植的文学观有关,他以辞赋为小道,这种无当便是确然存在的。他在《知音篇》提到:“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文学评价的态度,刘勰对于这种文人相轻的文学批评态度是颇有微词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陈思以情胜,而魏文以理长,刘勰说:
“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是千载之中正之论。
刘勰的客观敏锐的文学批评感觉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对于曹氏兄弟的评价客观公允,这种批评方法及批评态度成为以后文学批评家的很好的参照系。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绎旨》.(梁)刘勰撰 济南 齐鲁书社出版 1984.3
[2]《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著 北京 出版社 1979.11
文心雕龙的作者范文6
关键词:物感说;物;情;情景交融
一、 “物感”说释义
中国古典美学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人心与“天”(“道”)“一气流通”融为一体,无有间隔。在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中,天地自然如人一样,充溢着生命气息,而且人的生命就是宇宙生命的凝聚,因而人可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的审美理论不可能是主体与客体对立的认识论,而只能是主体与客体交感的体验论。[1]5“物感说”正是这样一种体验论。
大体上看,所谓“物感”,一是“感兴”,即主体的情感由外物触发,这是一种感性的兴发活动。二是感会,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这是一种不分主客的交融互渗。从深处看,“物感说”实际上论述的是审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关系,即主客、物我、情景的关系。而在这之中,“情”又是物我、主客之间的桥梁。审美就是在这种物我一体,主客交融的状态中产生的。
二、 “物感”说发展轨迹的研究现状
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物感说”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其理由主要在于《文心・物色》将“物感说”从“感兴”发展到了“感会”,即由外物对人情感的触发发展到了人以情观物,物我交感。翟传霞在其《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感说》[2]148中就持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无懈可击,但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这种观点只注意到了“物感说”的表层含义,即“感兴”与“感会”两个方面的含义,而没有考虑到其深层含义,即“物”与“情”都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殊不知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物”虽取得了独立地位,摆脱了秦汉时期“比德说”中的道德修养的附属物这一地位,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而“情”还没有从儒家传统的园囿中解放出来,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这一点后文将会具体论述)。在“情”尚未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情况下就说“物感说”已经成熟,是值得再度思考的。
本文拟从“物感说”的深层含义出发,从“物”与“情”的逐步独立成为审美对象的过程中去论述“物感说”的奠基、发端、发展与成熟。
三、“物感”说的奠基、发端、发展、成熟
“感”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凡论文学创作缘起者,多言“感物”。而“感”的含义,却是在《周易》中最初展示出来的。
(一)“物感”说的哲学奠基
《周易・系辞上》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3]370大意是说,《易》之道,弥纶天地,人能随感而应,便可通晓天下之事。这讲的是人如何得“道”的。《周易》中讲“感”最为集中的,是“咸”卦。“感”是这一卦的主要含义。现将《彖》辞摘引如下: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3]164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这是对宇宙普遍规律的概括。天地万物,无不是既相互对待又相互需要的,只有双方相感相和,才能达到稳定而美好的状态。“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是说天地万物又都是在互相感应中生存发展、在互相感应中表现自己的。在这里,一切都是互相感应,相互感应化生一切。
中国文学理论中的“物感”说,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物感”说的“感”是感应或感发,而不是西方文论中的反映。正是这种观念奠定了“物感”说的基本含义。
(二)“物感”说的理论滥觞
据现有资料记载,最早在文艺理论中谈到“物感”的是《乐记》。《乐记》中说: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4]271
《乐记》中的这段话以动态的模式:物动―心动―声应―变音―成乐,谈论音乐的产生。这段话在《乐记》这部音乐理论文献中第一次谈到“物感”,虽未明确提出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物感”,但其在理论上的发轫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已经明确提出“音”之起在于“人心之感于物”,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作为儒家乐论的先天弱点。
先秦秦汉时期,儒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把个人正常的自然之情视为洪水猛兽:“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4]274他们认为个人感情是天理的对应物,所以对“情”进行了严格的伦理规范:“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43]282这里,儒家提出用礼乐来节制“人情”,“情”有“天”“人”之别。可见,这里的“情”更多的是“天”情,是儒家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情”,而非人的自然之情。
结合儒家在先秦至秦汉时期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乐记》的“物感”是有其特定限制意义的。“物”虽不排除自然风物,但更多的却是以儒家的“人事”,即与社会伦理有密切关系的社会人事;是“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论语・雍也》)之下的“物”,即君子“比德”的对象。“情”也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情感。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物”还是“情”,都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这也为“物感”说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
(三)“物感说”的发展
宗白华在其《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的一个时代”[5]208。随着人的觉醒,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物感”说也得到了发展,其代表为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
陆机《文赋》论述构思时说道: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6]170
《文赋》明确指出了“物”的内涵为自然景观,即四时景物。“物”在这里已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和独立,不再是仅仅具有人事、伦理意义上的“物”。但从整体上看,这里的“情”仍限于自然物所感发的“悲喜”之情,其论述仍语焉不详。但《文赋》已初步提出了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物感说”。
《文心雕龙》有许多篇谈到“物感”,并有意于将“物感”由“感兴”发挥到“感会”。如《诠赋》篇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7]92,已经由“感兴”发挥到了“感会”。这些言论的基本宗旨,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感物”说。当然,这之中还是《物色》篇谈得最多: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7]519
这段话的主题是论述“心”与“物”的关系,即“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而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微虫犹或入感”说起的。微虫应节律而动,说明天地万物深微而普遍的、息息相通的内在的生命关联。进而谈到作为最有生命灵性的人,人具有最敏锐、最丰富的感应力,无时无处不与万物相通,一叶一虫皆足感志。
《物色》篇的“赞曰”,是对上面这段话的精确概括:
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7]526
心物之间,亲密交往,互相应答,情趣融融,诗意盎然。文学和审美就是这样萌发的。这样,《文心・物色》就把“物感”发展到了“感会”,这种论述是较为全面的,完整的,整体上达到了“物感”说的完整意义。
但这个意义上的“物感”说似乎显得不够深刻,“物”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和独立,但仍没有超越其自然属性而获得完整的意义。“情”相对于《文赋》也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仍局限于自然物色之变所引起的“悦豫”、“郁陶”之情。“情”没有获得独立的主体地位,这个意义上的“物感”说没有真正理解“物感”的意义,也没有给“物感”说以应有的地位。而《诗品》则在深度上作了很好的发挥。
(四)“物感说”的成熟
《诗品》的序是这样开始的: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8]15
这里把诗、情、物、气,四者联系起来,指出诗是情性的表现,性情是物之感人的结果,而物之感人源于气的运动。在此之后,《诗品序》又对“物之感人”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8]20
可以看到,钟嵘所说的“物之感人”的“物”,已不限于自然景物,甚至主要不是自然景物,而是社会生活、人生遭际。人的心情自然会受到自然景物的触发,但其真正的根源显然是人生遭际。主要以社会生活、人生遭际为“物”,这样的“感物”说就不再是景物描写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诗如何产生,诗的本质与宗旨的层次了。“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只有诗与文艺能够抒发人生的感慨,能够呈现人的内心世界。“情”在这里也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人之所以需要诗与文艺在于此,世界之所以会产生文艺亦由乎此。这个意义上的“物感”说才是“感物”说的本意,才是“感物”说的真正意义所在。正如王夫之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刘勰虽屡次谈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却没有真正理解“物感”说的意义,也没有给“物感”说以应有的地位。
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物感说”,哲学奠基于《周易》,理论发端于《乐记》,但在此时无论是“物”还是“情”都还未取得独立的地位,其意义也是有很大局限的。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物”的内涵在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中得到了扩大,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物感”的含义也在《文心雕龙》中由“感兴”发展到了“感会”,获得了完整意义。但此时的“情”还囿于自然之物所感之情。成熟于钟嵘之《诗品》,“情”的内涵在《诗品》中得到了深化,人生遭际之“情”获得了独立审美价值,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在此处得到了体现。(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望衡:《中国美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翟传霞:《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感说》,《文学教育》,2011年11月。
[3]郭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06年版。
[4]陈戍国撰:《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
[5]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