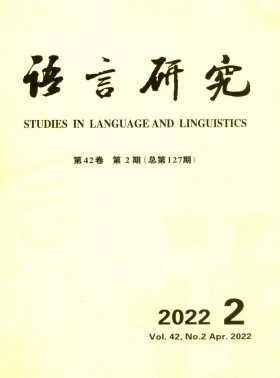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1
一、陶渊明诗词中的空白及其翻译
陶渊明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之一。生活在东晋末期的陶渊明被认为是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他给魏晋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和自然的风气。他的诗歌代表着“人性的觉醒”,强调物质上的舒适和精神上的愉悦对人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陶渊明将简朴的田园生活和繁重的田间劳作作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他在诗中用平实而美妙的诗句描写了平静惬意而又艰苦劳累的乡村生活,凸显出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平常而又美好的乡村景致,讴歌了普通乡民之间真挚而诚恳的情谊,表达了自己志存高远而又随性恬淡的心境。陶渊明用间接而深刻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平实简洁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与理想赋予我们身边最平常的景物上,自然景色,动植物,人等都是陶渊明诗词中的描写对象。他的诗歌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空白”。按照其特点,可以分为四类:语言空白、句法空白、意象空白和文化空白。
1.语言空白众所周知,诗词是诗人借助诗句中的模糊性和跨越性来抒发自己思想情感的特殊文学形式。诗人会使用一些语意模糊的诗歌语言来为读者留下一些文本“空白”。修辞方式是产生文本空白的主要形式,包括双关语,借代,转喻,重复,象征等等,除此之外,词语的数,词性和词语歧义都会形成诗词中的语言“空白”。例1.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ThefartherfromhomeinmyboatIgo,Thestrongermythoughtsforthecountrygrow.(tr.WangRongpei)叠词是诗人为了营造和加强美学氛围而重复某些词语的很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陶渊明的诗词中有几十次出现叠词的现象。而这种叠词对于尽量避免重复的英语来说却恰恰是表达中的一种“空白”,是需要译者做出填补的。上面的两个译文,汪榕培先生用了“themore,themore”句式来代替原诗中的叠词,既保持了原作的修辞美感又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双赢”的译法;是对词语空白的很好的填补。
2.句法空白句法空白主要是指由于缺少某些词语导致缺少句法成分,句子结构不完整而形成的空白,如缺少主语,谓语,介词等。一些功能性词语的省略,如人物,时间,地点等,会给读者造成没有时空概念的理解上的空白;一些非功能性词语的省略,如介词,限定词等,则会让读者对诗歌的时空关系理解模糊。例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Myhouseisbuiltamidtheworldofmen,YetlittlesoundandfurydoIken.———DrinkingWine(V)(tr.WangRongpei)《饮酒》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这几句诗句中没有主语,这种无主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十分常见的,结构灵活,句式铺排流散正是汉语巨大魅力的源泉,诗人用以动词为核心的无主句来描写景物,创建生动具体的意象。但这种无主句在英文结构中是不多见的,英语的语法结构相对严谨固定,所以诗词中省略的主语必须填补出来,才能真正将原诗的意义表达出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中的“庐”是诗人自己的小农舍,需要填补物主代词,即“Myhouse”,听不到“车马喧”的也是诗人自己,所以填补出“I”。诗句中的词语空白需要根据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特点来分析并填补出被省略的句法成分和词语。
3.意境空白意境被视为是诗歌的灵魂,是表达诗人思想感情的美学元素。诗人通过选取自然景物和客观事物来进行描绘,抒发自己的情感,进而创建自己的审美世界。诗人内在的情感都赋予在了所选取的外部事物上了。
例3.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青松”和“芳菊”在中国人,尤其是诗人的眼中是有着深刻内涵的。青松和芳菊都能够在百花凋零,枯木残柳的寒冷冬季昂首挺立,傲然绽放,象征着坚韧内敛,气节高尚;诗人明是描写青松和芳菊,实是借此抒发自己远离虚伪尘世,安于清贫而又品行高洁的隐士情怀。而在西方人的眼里,“青松”和“芳菊”只是自然界中的两种植物,无论美丑都没有任何的意境想象,这就形成了诗词意境上的空白,需要适当的填补以再现原诗中的高远意境。这种空白在“贞秀姿”和“霜下杰”的译文“lofty”和“showthebestsigns”中得到了填补;读者既可以懂得词语的含义,看到文本意义的连贯性,欣赏到诗词意境的高远,又可以体会诗人的情感和异域的文化。
4.文化空白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从狭义上看,文化就是对人类有益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以及技术成功的总和;从广义上说,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而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文化上的空白势必会造成交流上的障碍,那么这种空白的填补就对交流的成功意义重大了。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中国人喜欢饮酒,也把饮酒看作是一种习俗,一种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或是重要仪式的组成部分。“忘忧物”就是指“酒”,尤其是我们的白酒,虽然西方人也喜欢饮酒,酒也有表达情感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与浪漫的事情相关,尤其是葡萄酒,这就形成了中西方酒文化理解上的空白。汪榕培先生将“忘忧物”译为“Asipofwine”,正是依据西方文化和读者的期待视野顺应过来的,文化空白得以填补,诗词的意义得以再现。
二、结语
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2
【关键词】结构技巧 诗歌鉴赏 表达技巧 新题点
表达技巧,又称为艺术技巧或写作技巧,是高考诗歌鉴赏命题中涉及最多且较为复杂的内容。有单独考查的,也有结合形象、思想、感情来考查的。对其鉴赏,就是要分析诗歌运用了哪些表达技巧,这些表达技巧在诗歌中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等。历年高考的诗歌鉴赏试题,以主观表述题为主要呈现方式,数年来已形成三个相对稳定的设题点,即鉴赏所运用的修辞方法、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
修辞手法是诗歌表达技巧鉴赏相对容易的一个题点,一般分为修辞格辨识和表达效果阐释两例考查形式。辨识修辞手法,解题需要掌握考纲列举的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七种常见修辞手法;表达效果的阐释,一般要求结合具体内容作相应的具体分析,而不能就共性的作用说说而已。
抒情和描写是鉴赏诗歌表达方式的两大重点。抒情方式又分为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其考查侧重于揣度间接抒情借用景或物或史的真正用意,即梳理写景抒情诗景与情的关系;看明咏物诗借咏物而寄寓的志或理,揣透咏史怀古诗因古迹史事而触发的现实感慨。描写考查则多趋向诗歌的局部,从正侧结合、动静结合、虚实结合、远近高低变化、细节描写、白描等常规角度思考多为省力。
表现手法是有着较大争议的概念,高中语文教材没有把它解说清楚,高考命题者也是见仁见智。笔者建议表现手法的鉴赏备考要以掌握对比、烘托、衬托等常用技巧为宜,不宜过多纠缠概念。
细梳一下近年高考的诗歌考题,除了上述修辞方法、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三个设题点外,我们还能发现以“结构技巧”为鉴赏设题点的若干考例。
2010年高考就涌现出三例:全国Ⅱ卷选择宋诗《梦中作》,要求考生鉴赏“这首诗在写作上有什么特色?(参考:①一句一个场景;②以景写情,情景交融;③对仗十分工巧。)”江苏卷要求考生就王昌龄《送魏二》“三、四两句诗”“具体分析”陆时雍的诗评“代为之思,其情更远。(参考:由眼前情景转为设想对方抵达后的孤寂与愁苦,通过想象拓展意境,使主客双方惜别深情表达得更为深远。)”辽宁卷选择的是陈与义的《雨》,要求考生对“前人认为这首诗写雨时妙在‘若即若离’”的说法作出评判。(参考:同意。除了诗题和首句直接点明“雨”,其它都是通过写动植物和人在雨中的感受来写雨,这就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2011年,这类考题更是多见。浙江卷要求鉴赏《蝶恋花·出塞》“这首词开篇有何特点?(参考:①以情相问,以景作答。②化抽象为形象之景,增强了全诗的抒情效果。③“深山”“夕照”“秋雨”三个意象连用,委婉地表达出词人心中的孤寂、惆怅之情。)”天津卷要求就“《暴雨》‘第五、六句可以放在开头’的说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参考:不好。开篇写骤雨至,先声夺人,和结尾雨的骤然停止形成呼应,体现出作者谋篇布局的艺术匠心。如果把第五六句放在开头,牧童就成了描写的重心,冲淡了艺术效果。)山东卷要求“结合全诗”《咏山泉》,简要分析“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的妙处。(参考:从声与色的角度描写了山泉的情态。与前两句构成抑扬,前两句写山泉的平淡无名,为抑;这两句彰显泉流山中的奇观,为扬。为诗歌最后两句赞美山泉做了铺垫。)”全国卷则要求从周邦彦《关河令》的“上、下两阕的首句看,这首诗是以什么为线索来写的?”(参考:时间推移。上阕写的情景发生在日间“渐向暝”时;下阕写作者难以入眠的情景已经推移至深夜(更深、人去、寂静时)。江苏卷要求说说《春日忆李白》“这首诗的构思脉络。”(参考:立足于诗,怀念李白:从赞扬李白的诗歌开始,转为对李白的思念,最后以渴望相见、切磋诗艺作结。)湖北卷说《登城》《望湖楼晚景》“两诗第三句都描写相对静止的画面”,要求“分别说说它们在原诗结构中的作用。”(参考:①刘诗第三句承接前两句,并与蒙蒙细雨叠加,以形成下句江南水墨图意境;②苏诗第三句从“横风吹雨”转入“雨过潮平”,为描写雷电蓄势,承上启下。)
散文的布局谋篇,因其篇幅长度和体裁特点早已聚焦了众人的目力。“散文写作笔法分类目录”,在第一大块“布局谋篇”中就列述了“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志”、“从背面入笔”、“以小见大”、“过渡巧妙,转折灵活”、“紧密呼应,互相衔接”等别具一格的构思技巧。而诗歌的篇章结构或因其篇幅的短小还未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其实,从诗歌的篇章结构也往往能看出诗歌构思立意的精心高妙来。鉴于此,本文权且把此点称作诗歌表达技巧鉴赏的“新题点”,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之意和警惕之情。也为了便于备考,笔者结合历年考例把诗人常常借以提高诗歌的表现力的几种“结构技巧”逐一梳理,略述如下。
一、扣题呼应,统摄贯穿
2006年高考广东鉴赏诗歌选择了谭敬昭的《粤秀峰晚望同黄香石诸子二首(其一)》,考题——“诗中哪些意象体现了题目中的‘晚望’?请分别从‘晚’‘望’两个方面回答。”——明考意象实指题文相扣的要求。这与诗歌鉴赏模式“一词领全诗型”颇有相似之处。一个字或一个词就构成全诗的线索或全诗的感情基调,抓住这个词命题往往可以考查出考生对全诗的把握程度。比如2005年江苏考题“诗以‘微风’开头,并贯穿全篇。请对此作具体说明。(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和2006年四川考题“本诗是怎样以‘夜归’统摄全篇的?结合全诗简要赏析。(周密《夜归》)”,答题分析时都要抓在内容上能起总领的句子或结构上能承上启下的句子。
二、以景结情,卒章显志
特殊的位置可能存在特别的结构技巧。以景结情和卒章显志,就是诗歌结束处经常用到的两种结构技巧。七绝《从军行七首(其二)》前三句叙事抒情,后一句“高高秋月照长城”以景作结,在写景中寄寓了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这就是作者王昌龄构思的高妙。卒章显志,顾名思义,即指在诗歌的末尾点出诗歌蕴含的情感主旨。《梦游天姥吟留别》写梦境也写现实,将神话传说和实境交织在一起,直至尾句才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现实呼喊,在全篇结构上起到了卒章显志的作用。
三、以小见大,着眼细节
“看似寻常最奇崛”,扣住寻常的细节,以小小景传大境界,以平凡细微的事情反映重大深沉的主题。2004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试析张籍此诗写了生活中哪个细节?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情感?(《秋思》张籍)”就是要分析作者所写“临发又开封”这样一个细节。而金昌绪《春怨》摄取的仅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课题。四句小诗,句句设疑,句句作答,看似只是一首抒写儿女之情的小诗,却反映了当时边疆战事频仍下广大民众所承受痛苦的时代内容。
四、抑扬转承,铺垫过渡
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3
关键词:李商隐;隐晦诗;阐释;表现模式;说话者:主人公
中图分类号:1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63-08
作为一个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风格可谓多样。然而李商隐之所以成为今日读者心中的李商隐,主要却还是因为他那些隐晦难懂的诗。这些诗的语言并不艰涩古怪,有时甚至近乎直白,然而我们却不能清楚地理解它们的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隐晦诗的难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确定性,即同一首或同一句诗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特性,以及诗人的主观处理,李商隐诗歌的不确定性往往源于说话者和主人公的模糊性。从说话者和主人公的关系着眼,本着除了有变化标记之外保持说话者同一性的原则解读李商隐的诗歌,从而确定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不确定的,以及不确定性的成因,便是本文主旨所在。除此之外,本文也会试着分析这种不确定性是如何使不同的阐释成为可能的。
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说话者与主人公
刘若愚先生认为,作为一种“完全没有语尾变化的语言,中文没有‘格’、‘性别’、‘语气’、‘时态’等等的重荷”。这一特点一方面“使作者能够集中于主要重点而且尽可能地简洁”,另一方面“却容易导向暖昧不清”。就中国诗歌语言而言,这种“暧昧不清”的特性常因主语的省略而增强。基于中文是一种以话题为主的语言,而非像英文那样是一种以主语为主的语言,本文选择广义上的“主人公”(即主要描写对象)而非“主语”一词与“说话者”相对应。
就唐诗而言,虽然一首诗可以有多个主人公,若无变化标记,一首诗的说话者却往往是同一的。当然,说话者并不一定是诗人自己。诗人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说话,也可以用他人的身份说话(代他人说话或者投入他人的角色说话)。当诗歌中无代言标记以及当诗歌的说话者性别与诗人相同或者性别问题不影响对诗歌的理解时,说话者一般被等同于诗人自己。
因为本文旨在讨论说话者(无论说话者是不是诗人自身)与主人公的关系,所以不会深入探讨说话者的身份问题。不过,在李商隐的一些隐晦诗中,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或者爱情的诗中,说话者的性别问题与主人公一样会成为理解这些诗歌的关键。
中国古代诗歌中说话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可以依表现模式概括为以下三类:
1.第一人称表现模式:主人公即说话者。在此模式中,或隐或显的主人公都以第一人称呈现。这种模式加强了描述的可信性,并拉近了说话者与受话者、读者之间的距离。而当说话者为诗人的时候,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亦强化了诗歌的自传性。
2.第二人称表现模式:主人公即受话者,或隐或显皆以第二人称呈现。这种表现模式因说话者对受话者的直指性而时刻吸引着受话者(有时即读者)的注意力。
3.第三人称表现模式:主人公既不是说话者,也不是受话者,而是以第三人称呈现的另外的人或事物。在此表现模式中,说话者因置身于其描述的内容之外,故能以全知全能的方式展开叙述。
二、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确定
的李商隐诗歌
在李商隐大多数的应酬、咏物、咏史诗,以及部分关于女性、爱情的诗歌中,说话者和主人公的关系都较易从以下几种途径推断出来:
1.从诗题上推断
一些诗歌的题目(尤其是应酬诗)往往包涵着丰富的信息,可供我们确定诗歌中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如:
《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
新人桥上著春衫,
旧主江边侧帽檐。
愿得化为红绶带,
许教双凤一时衔。
由诗题可知这是一首代言诗:诗人是以官妓的口吻写这首诗的。因此,此诗的说话者是官妓,受话者是新旧两任从事。第一联的主人公表面上虽然以第三人称的词“新人”、“旧主”指代,但此二词所指的是受话者(两个从事)。因此第一联用的实际上是第二人称的表现模式。第二联中,我们不难看出被省略的主语就是主人公(即本诗的说话者官妓),因此第二联的表现模式是第一人称表现模式。
虽然诗人通过题目表明他是在为官妓代言,仿佛置身于整首诗歌之外,但第一联中对两从事风流形象的戏剧化描写以及第二联中官妓所直接表达的有“猥亵”之嫌的愿望,却使此诗更似诗人假借官妓之口对两从事的调侃之作。
2.从人称代词上推断
一首诗中的人称代词也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主人公与说话者的关系。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人称代词最常见于应酬、叙事、咏物及咏史诗中。比如《蝉》一诗,其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由于第一、第二代词的对举而十分明晰:
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
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
通读全诗不难发现,尾联中的“君”即指蝉,“我”指说话者。首联的主人公即省略之主语“蝉”。虽然颔联的主要描述对象是蝉的声音及蝉的栖身之所,但二者皆以蝉为中心,故其主人公还是可以被认为是蝉。因此首颔二联所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颈联被隐含的主人公即说话者,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包含第二人称代词“君”(即蝉)的第七句的主人公和受话者都是蝉,但与以第一人称为表现模式的末句联系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第七句的主人公“蝉”是作为末句主人公“我”的参照物或者铺垫而出现的,因而尾联的整体主人公仍可被认为是说话者。
此诗无代言标志,由“薄宦”可知说话者为男性,所以说话者可以被认为是诗人自己。全诗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表现模式的转换,使被咏之物“蝉”与吟咏之人“说话者”(在此处即诗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不仅蝉鸣对诗人有警戒作用,蝉的存在本身也让诗人看到了自己。许多评论家将蝉视为诗人的自喻:蝉的高洁秉性可被视为诗人的自指,而蝉鸣也往往被比作诗人的苦吟。因而首二联中对蝉的特性及其生存环境的描写成了诗人第三联中回忆自身仕途漂泊而无家可归的引子。而诗之末联中作为“我”之参照物的“君”又与首联之蝉相呼应:“我”及“我家”的清贫正似蝉之高洁难饱。全诗如纪昀所云:“前半写蝉,即自喻;后半自写,仍归到蝉。”
3.从上下文推断
当诗题无明确指示,诗中亦无人称代词时,说话者及主人公的关系有时亦可从整首诗的内容上推断出来。如李商隐之《即日》:
一岁林花即日休,
江间亭下怅淹留。
重吟细把真无奈,
已落犹开未放愁。
山色正来衔小院,
春阴只欲傍高楼。
金鞍忽散银壶漏,
更醉谁家白玉钩?
第一句描述的是一日之景,而其主要描述对
象是“林花”。二、三句的主人公即被省略之主语,也就是说话者。第四句的主要描述对象虽为省略之主语“林花”,但其又通过“未放愁”与说话者联系了起来:林花被拟人化附上了说话者的情感。颈联又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开始描述自然景物。经过第七句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描述的离别景象之后,说话者又以第一人称表现模式回到了末句。虽然整首诗交叉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但由第三人称模式所描述那一日的场景都是与说话者的行为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整体而言,整首诗的主人公可被认为是说话者,写的是他的所见、所为,及所感,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
4.从虚词上推断
李商隐是好用虚词表达情感的诗人之一。如下《偶题二首(其二)》所示,一些虚词的使用也可以帮我们判断诗中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
清月依微香露轻,
曲房小院多逢迎。
春丛定是饶栖夜,
饮罢莫持红烛行。
首联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说话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时、景,及“曲房小院”中的人来人往。第三句中的副词“定”表明说话者在对主要描述对象即春丛中隐藏的一景作一种猜测,而末句的副词“莫”也表明说话者在对主人公即受话者提出一个建议。
全诗前三句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主要描写对象是景;末句采用的是第二人称的表现模式,主人公是诗的受话者,无论是说话者自己还是参加宴饮的其他人。
三、说话者与主人公关系不确定的
李商隐诗歌
李商隐诗歌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及爱情的诗,其表现模式是模糊或者无法确定的。我们称这些难以理解或者难以确定其内容的诗为隐晦诗。这些诗中往往没有上述能帮我们推断说话者和主人公关系的因素。而且这类诗由于内容涉及女性,所以说话者的性别常常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些诗歌的理解。在分析这些诗时,“说话者同一性”原则无疑成了诗歌阐释的向导,减少了不同阐释的可能性。下文将本着这一原则着力解释说话者与主人公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使我们对这类诗歌产生不同理解的。
1.在李商隐描写女性及爱情的一些隐晦诗中,说话者的性别是可以确定的。左右这些诗歌内容甚至表现模式的是受话者或者主人公的不确定性。如李商隐著名的《无题四首》其一便是此例:
来是空言去绝踪,
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
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
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
与人称代词相似,尾联中的“刘郎”典故是推断此诗说话者的关键。说话者用刘郎与自己比较:说话者离所爱的距离比刘郎离蓬山的更远。由参照者刘郎的性别,可以断定说话者为男性。
如脚注所示,此诗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以“说话者同一”原则为基础对主人公(或主要描写对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确定的信息。
第一句中的主人公一定是说话者想见之人(如他所爱之人),她或的确曾经来过,或答应来实际上却没有来,或只在说话者梦中来过。由于无题诗缺乏信息,这一句采用的可以是第二人称表现模式(若此诗写给说话者所爱之人),也可以是第三人称表现模式(向别人描述所爱之人)。第二句的主要描写对象是时间,即采用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指示说话者至五更还未睡着或在五更时醒来。
第三句以梦的形式展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人经历,因此主人公很可能就是说话者:他在梦里哭泣,但却无法唤回远去的爱人。不过我们仍无法确定一些细节:这描写的可能是说话者常做的一个梦,也可能是五更以前他做的一个特定的梦。第四句的被动语态暗示主人公仍是说话者,写信可能是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抑或是他在五更梦醒后做的一件特定的事。总之颔联所采用的主要是第一人称表现模式。
第三联中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描写的细节都与一个潜在的人物息息相关。它可能是说话者(他在凝视着卧室中那些令他回忆起他与所爱之人度过的欢乐时光的痕迹,或者准备好了这一切在等待所爱之人的来临可她却没有来),也可能是说话者所爱之人(说话者描述的是想象中她的卧室的场景)。无论是哪一种阐释,卧室中的这些细节都传递着说话者对他所爱之人的思念。
第七句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但它是采用第一人称表现模式的末句的铺垫,故尾联总体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
由于每一联意思的不确定性,全诗可以有多种阐释。但一些基本信息,无论是有关爱情的抑或是有政治寓意的,在不同的阐释中保持不变:说话者与其所爱之人分隔两地,他于深夜绝望地想念着他的爱人。
不考虑《无题》诗代言标题遗失的可能性⑤,此诗尾联说话者的男性标志使读者倾向于将说话者等同于诗人自己。而此诗颔联和尾联所采用的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及此诗说话者与其所思之人的恋爱关系使读者很容易将此诗作为诗人对自我感情经历的真实写照。
2.李商隐一些隐晦诗中,主人公是可以确定的,但其表现模式不可确定,说话者的性别也影响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如:
《无题二首》
其一
凤尾香罗薄几重?
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
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
断无消息石榴红。
班驹只系垂杨岸,
何处西南待好风?
与前一首《无题》一样,此诗描写的亦是一段爱情故事。
诗的首句描写的是一个场景,而次句省略之主语――缝“圆顶”的女子,正是首联的主人公。若如大多数评论家(包括《集解》作者)所言“圆顶”是婚嫁时所用之物,我们可知主人公在缝“圆顶”之时期盼着婚礼。
颔联无人称标志,但我们从“扇”之典故与“羞”不难推断出第三句的主人公应为首联所述之女子,而第四句的“语”应发生在女子与她所爱之男子之间。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坐车的是女子还是男子,结合两句之意,颔联的主人公应为女子。此联亦无时间标志,但根据颈联中标志过去的“曾”及尾联中男女不在一地的现时状态,我们可以推断出颔联的这一场景很可能发生在过去,如回忆初见之情形。
第五句中的时间标志“曾”暗示此句所写一方寂寞地等着另一方的场景发生在过去;而第六句则回到了现实并呈现了时间的流逝:自那以后另一方毫无音讯。由第七句中的“班驹”我们断定离开的是男子,因此颈联描写的是等待离开男子音讯的女子,即主人公为女子。
第七句中的班驹显然是男子的坐骑,而末句中待好风之人即为待男子之女子,因此末联的主人公仍可被认为是女子。
虽然我们推断出全诗的主人公为女性,但由于缺乏信息的诗题及很多诗句中省略的主语,全诗的表现方式有三种可能性:若此诗采取的主要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说话者的性别则不成问题(全诗从旁观者角度描写了一个女子回忆、思念她所爱的男子,并期待他的归来);若此诗采取的是第二人称的表现模式,说话者的性别也不是
大问题(全诗以第二人称描写一个女子对她所爱之人的思念);此诗还可能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是女主人公(诗人以女主人公口吻描述对她所爱之人的回忆、思念和期待)。
虽然此诗描写的是明显的男女恋爱关系,但诗人不是以第一人称表现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故大多数传统评论家赋予了此诗政治寓意,而非将其当做诗人亲身经历的一段感情描述。
3.在李商隐的一些更为复杂的隐晦诗中,主人公、表现模式及说话者的性别都不能确定,每一联甚至每一句都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模式。这种多重不确定性无疑使诗歌阐释有了更多可能性。如下列之《促漏》诗,标题因取诗文首二字而不含任何信息,所幸我们本着“说话者同一”原则可以从上下文及一些关键语词推断出主人公及说话者性别的可能性:
促漏遥钟动静闻,
报章重叠杳难分。
舞鸾镜匣收残黛,
睡鸭香炉换夕熏。
归去定知还向月,
梦来何处更为云?
南塘渐暖蒲堪结。
两两鸳鸯护水纹。
通读全诗,虽然我们可以知道此诗讲述的是一对已经分离或即将分离的男女的故事,却无法确定前三联的主人公。
由于首联中动词“闻”和“分”都是被动语态,并无明显性别标志,因此我们无法断定与之相联系的主人公的性别。不过由感官动词“闻”和心理副词“难”可知第一联很可能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表现模式。
颔联描写的是同一人房中的细节。由于注解所提及的“收”字的多重含义,此处描写的可以是男子住处之女子用过的镜匣(主人公为男)、女子闺房之镜匣或女子合上镜匣的动作(主人公为女)。
颈联为全诗最不确定之处。第五句由于“归去”、“向月”两动词主语的省略,我们不知道说的是男子的离开还是女子的离开。若此句的主人公是男子,可以是男子表达自己离开后还是会望着月亮思念女子或女子想象男子离开后一定会望着月亮思念自己;若此句的主人公是女子,可以是女子预测自己离开后很孤独或男子想象或者预测女子离开后的孤独。第六句虽然主语又被省略,但根据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典故,我们可以断定主人公是女子。由第五句中的关键动词“定知”可知说话者揣测的是自己所恋之人,或表达的是自己的决心。而五、六两句中动词方向补语“来”、“去”的对举,更佐证了此联的说话者为男女主人公之一。此诗无转换说话者的标记,故全诗的说话者即男或女主人公。
尾联是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所写的一个春天日景,旨在传达动植物适时团圆,反衬男女主人公业已分离或即将分离的事实。
由于全诗的说话者为男女主人公之一,所以全诗的受话者可以是另一个主人公(主人公一方写给另一方)或其他人(主人公之一将自己的故事写给其他读者)。按受话者分类,下列两表总结了对此诗的不同阐释:
由以上两表得知,无论受话者是不是男女主人公,全诗主要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此诗诗题无代言标志,所以当说话者是男主人公时,很容易被等同于诗人自己,全诗亦成为作者对自己所经历的一段感情的描述。而当说话者是女主人公时,与《无题二首》其一类似,此诗的“闺怨”易被传统评论家披上政治外衣。
4.由上述隐晦诗所示,当诗中说话者的性别、主人公或两者皆不确定时,我们通常需要从诗歌内容上判断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可能关系,并根据各种可能的组合对全诗进行阐释。这种内容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出这些隐晦诗重在传达细腻的感情,而非落实的内容。就诗歌赏析接受而言,这种不拘于事实的细腻情感的抒发具有一种普适性,即很容易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这或许也是李商隐的隐晦爱情诗受历代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传统时刻推动着传统评论家们赋予这些写女性或者爱情的隐晦诗“更深刻”的政治寓意或者把它们与诗人生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对应起来。当诗人与其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并无个人关系,或者当说话者为女主人公时,女主人公常被看作是诗人的自喻;当说话者为男性,并是诗中所描写之爱情故事的男主角时,虽然这种男女之情亦可被看做诗人与上级关系的比喻,但更多的还是被当做诗人真实的情感经历。
四、结语
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4
关键词:托马斯・哈代 自然诗 生态整体观 人类中心主义
基金项目: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托马斯・哈代诗歌的生态意识研究”,项目编号:QS2015011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批评思潮出现的直接原因。“生态批评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批评”。[1]47通过重读文学经典,深度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从而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这是生态批评家的重要使命。指导生态批评家的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1]10
托马斯・ 哈代( Thomas Hardy,1840-1928)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在早期和中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诗歌,从《居住》(Domicilium)到《他决意不再说什么》(He Resolves to Say No More),哈代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终于诗歌。近千首含义深邃、意味隽永的诗是他对英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其中百余首描写自然的诗更体现了哈代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描写自然的能力,因此得到评价“在诗歌创作中,托马斯・哈代则无疑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诗人” [2]38。
一、维护整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
哈代生长于宁静美丽的多塞特郡,家乡是哈代创作的灵感之源,他的处女诗作便是描写家乡春意盎然之景的《居住》(Domicilium)。诗中的家乡和谐、静谧,是哈代身体的归宿也是他灵魂的寄托。家乡亦是哈代寻求慰藉的疗伤之所。当哈代在城市遭遇了误解,内心感到孤独无助之时,他来到了威塞克斯高地,写下《威塞克斯高地》(Wessex Heights)――哈代诗中的家乡:“威塞克斯有些高地,似乎由仁慈的手开辟/ 供人思索、梦想、安葬,紧要关头我常去那伫立/……/ 仿佛那是我生前的所在之地,和死后的归宿”。[3]185
哈下的自然不仅是人类身体和心灵的庇护所,也同人类一样,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主体。正如哈代自己所言:“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自然风景中的景物,例如树木、山冈和房屋,都有表情和脾性”。[2]28 《树木与女士》(The Tree and the Lady)中的树木为了所爱的人甘愿付出:“我为熟知的女士已经做完/我能做的一切。冒着炎热,我为她遮荫/当酷暑使她疲倦,我为她的鸣鸟/提供了林中的家园”。当它的付出受到了所爱之人的青睐,树木满心欢喜:“她默默地把我当作良朋”。[4]155而最终当“她”为了追求温暖而不带一丝留恋地转身离开时,它绝望诉说:“她走了,对我一身裸枝不屑一顾”。树为人倾心时的爱与奉献,能为所爱之人遮荫避暑时的欢欣与骄傲,被所爱之人抛弃时的委屈与不甘都是植物的“表情和脾性”,它向读者展示着一个鲜活的存在,一个不该被人类无视的生命。
哈下的自然不仅体验着自身的喜怒哀乐,还关注着自身之外的人类社会。《孤屋前的一头V鹿》(The Fallow Deer at the Lonely House)用轻快的笔调生动地勾勒出一头对人类社会充满好奇的V鹿。它用那双“神采飞扬,扑闪扑闪”的眼睛好奇的打量着人类世界:“趁着皑皑白雪的光亮/它在夜幕下朝屋内张望”。[4]169探索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动植物也非只能作为被探索的对象。相反,一头V鹿亦会踮起脚尖,在雪地中窥探那个对它来说充满神秘的人类社会。这头V鹿体现出哈代诗中的动物从来就是和人类一样感受相同情绪,并具有相同地位的主体。
在《一个八月的子夜》(An August Midnight)中,哈代把“长翅膀的,带角的,和背着脊刺”的“长腿蝇”、“飞蛾”、“黄蜂”和“昏昏欲睡的苍蝇”都视为“宾客”。虽然这是不速之客弄脏了他刚刚写下的诗行,可哈代毫不在意,并把他们称为“上帝最恭顺的孩子”,“因它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尘世之谜”。[3]82在哈代看来,昆虫也有着人类无法企及的聪慧。因此,人类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而应把自己和它们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体和平共处。
因此,哈代诗中的自然不只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而存在,更不是供人类消遣和征服的对象,而是有思想、有灵性、有情感的生命。它与人有着亲属关系:“树是人类四肢的一骨,动物和各种肤色的人都是同类本属一家”,[3]296自然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
二、抨击人类中心主义行为
生态整体观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认为人类应该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5]相反,人类中心主义是与其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它将人类视为地球的主宰,并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对人类中心主义行为的批评是生态批评家的共识。哈代诗中的自然有着独立于人类需求之外的意义,其存在的意义绝非是为了服务人类的发展,而是享有与人类同样追求稳定与幸福的权利。因此,哈代痛斥人类以万物主宰的身份肆意征服和破坏自然的行为,认为人类 “一贯杀戮、破坏、压制 / 这无异于自杀自毁”。[3]296这种对破坏整体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人类中心主义行为的抨击是哈代生态整体观的又一体现。
《伐木》描述了一对父子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砍倒了一棵两百年来生长茂盛的树。随着电锯割破皮肤,切入身体,大树因恐惧和疼痛而战栗,而伐木人并未因大树的痛苦而停下他们的暴行,大树只能在伐木人的暴行中绝望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哈代把伐木的父子比作扛着冰冷阴森的斧头和锯子,潜入森林,寻找受害者的“刽子手”。“刽子手”原是处决犯人,夺取他人生命的人。哈代用“刽子手”代指父子俩,意在指出:结束大树生命的行为如同刽子手夺取他人生命的行为一样残忍、血腥。锯倒一颗长了两百年的大树,这对父子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人类惊人的破坏力让哈代愤怒与震惊。对于大树在面对“刽子手”时的恐惧和痛苦,哈代感同身受却又无可奈何。
除了关怀植物,作为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成员,哈代还用行动和文学创作参与动物保护。他写了多首保护动物特别是鸟类的诗,如:《供捕猎的鸟的困惑》(The Puzzled Game Birds),《失明的鸟》(Blinded Bird),《红腹灰雀》(The Bullfinches),《捕鸟人之子》(The Bird-Catcher's Boy),《关在笼中的金雀鸟》(The Caged Goldfinch)等等。哈代诗中的鸟形象多变,它们既歌唱对生命和自由的憧憬,也控诉人类无视其他物种的自私行径:“哈下的鸟是孤独的鸟、失去自由的鸟、受虐的鸟、荒凉中歌唱的鸟、自然之鸟”。[6]
哈代时期的欧洲流行一种叫“禽戏”的游戏。游戏玩家把多只苍头燕雀关在笼中比拼哪只鸟在一定时间内鸣叫的次数最多。为了不让鸟分散注意力,玩家用烧红的针残忍的刺瞎它们的双眼。《失明的鸟》正是描写了这样一只“为赤红的针所刺”而双目失明的鸟,它“永陷于黑暗的劫数/摸索着度过漫长一生/遭受了灼伤的刺痛/又囚于无情的铁丝笼”。人类为满足自己低俗的趣味,全然不顾鸟的痛苦,极其残忍地夺去了它的光明,使它“活着犹如遭埋葬”。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只失明的鸟“久久受难而仍善良/……/毫无恶念只知歌唱”。[3]294人类刺瞎鸟的双眼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戕害,而鸟的宽容和乐观更反衬了人类内心的肮脏与黑暗。
《捕鸟人之子》描述了一对对鸟有着截然相反两种态度的父子。具有生态整体意识的儿子质疑父亲捕鸟的行为,他认为鸟属于天空,而非樊笼,鸟与人一样渴望生存与自由,而“每只关在笼里的夜莺/很快会死亡或憔悴”。但在父亲的眼中,鸟是他获取金钱的途径,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作为他谋生的工具。他甚至叫嚣:“鸟就是任逮任捕”,[3]443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诗歌结尾,捕鸟人之子的死亡展示了自然对捕鸟人的人类中心主义行为的报复。哈代用捕鸟人之子的死向世人敲响警钟:人类定会为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付出巨大代价。
三、小结
在英国文学史上,哈代是一位具有超前生态意识的诗人,多首描写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歌体现了他的生态整体意识。利奥波德指出判断生态整体主义的最具本标准是:“有助于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1]93哈代热爱并颂扬“和谐、稳定和美丽”的生态环境,这份热爱并非出于人类的优越感,把自然中的非人类生命作为同情和保护的对象,而是把它们摆在与人类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兄弟手足来尊重。同时,哈代深刻认识到:人类破坏和谐生态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在诗歌中对其进行严厉控诉。对“正确的”事物的支持和对“错误的”行为的批判这两种一正一反的态度,体现了哈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折射了他明确而深刻的生态整体观。
参考文献
[1]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吴笛.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 (英)托马斯・哈代.哈代文集8诗选 [M].刘新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英)托马斯・哈代.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M].飞白,吴笛,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5
首先,谈谈对“赋”的继承。“赋者,铺也。”铺,就是铺排,也就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下面我们就从内容的角度分类来谈赋在乐府诗中的运用。
一、景观物象的铺排
即通过多侧面地描绘景观物象,以渲染环境、气氛、情调。如汉代乐府诗《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可能是一首武帝时所采的《吴楚南歌诗》,是江南水乡渔家儿女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诗中以“莲”谐“怜”(怜爱,爱恋),又以“鱼”谐“女”(女郎、渔家姑娘)。后面四个铺排句,仅仅换动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却富有情韵地反映了男女青年在采莲劳动中互相嬉戏追逐的情态。
二、事态现象的铺排
在叙事诗中常以排比的句式铺陈其事。如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好几处着意铺排渲染。这位古代巾帼英雄代父从军的典型事迹。诗中铺写她在出征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出征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瞅瞅”;归来时“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阀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通过这些铺排抒叙,有力地突现了花木兰保家卫国、居功不傲的劳动妇女的质朴本色。读之,使人感到畅酣达意、痛快淋漓。
三、人物服饰的铺排
即通过铺写人物的服饰装扮,借以显示人物的身份、外貌乃至心理。如《陌上桑》中描写秦罗敷的装束:“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意在突现罗敷的端庄和美貌。又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即将离开焦家时的打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描写一方面突出了刘兰芝的美丽,同时也表
现了她镇定、坚强的内心世界。
四、铺写人物的年龄教养
通过铺写人物的年龄特征借此以显示人物的成长过程。如《孔雀东南飞》中对刘兰芝的描写:“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以突现兰芝的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铺排的主要特征就是淋漓尽致、畅酣达意。
其次,谈谈对“比”的继承。“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即比喻。是三种手法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言:“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这是焦仲卿听说刘兰芝要嫁给府君之子时对兰芝说的话。在此,他将自己比作磐石,借以表明对爱情的坚贞;将兰芝比作浦苇,责怪她不能坚持到底。比喻的主要特征就是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最后,谈谈对“兴”的继承。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诗词中凡用“触物以起情”、“感物而动”的兴笔开篇或收束,谓之“兴起兴结”。它具有触发联想、渲染气氛、调动情绪的功能。古代诗词中,兴起,用得较为普遍;兴结,相对地说来用得较少;而兴起兴结,有时合用于一首诗中,则更为少见。而比和兴又往往结合在一起,所以重点谈谈兴中含比这种情况的运用。
兴中含比,即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起兴句中也兼含有“以彼物比此物”的比喻在内。兴中含比,多用在诗篇的开头。用来起兴的物象本来与主题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起触媒作用,也含有一定的渲染铺垫之意。但若与比一旦相结合,兴中含比,那就和本题直接挂上钩了。兴中含比,要比单纯地起兴或单纯地用比,则诗中意味倍增。兴中含比,以兴为主,比则从之。
兴中含比,常见于表示情爱、亲情、离别之类的诗作中,多从外界景观物象中触发联想。从兴中含比所取的兴象类型来看,有以动植物作比兴者,也有以非生物或自然现象作比兴者。如《孔雀东南飞》开头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激发读者想象,不由得人不从美禽恋偶联想到夫妻分离,这样就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起了统领全诗、引起下面故事的作用。
又如,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中兼含比喻。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劝故人应当念旧。兴的主要特征就是渲染铺垫、营造氛围。
描写植物的诗歌范文6
摘要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表达诗歌主旨最活跃的因素。而动物意象作为一种具体意象在狄金森诗歌中反复出现,是诗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本文重在分析动物意象在狄金森诗歌中的表现及其功能,探索动物意象与狄金森诗歌主旨表达的关系。进而说明,狄金森主要运用动物意象诠释她对自然的感知,表述她对自我的认知。
关键词:动物意象 狄金森诗歌 重要载体 功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意象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诗歌艺术构造的形象元件,是构成诗歌整体意境的基本单位。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擅用具体、凝练、奇特的意象,被誉为意象派先驱。作为一个极少远行的维多利亚时期的隐居诗人,狄金森所能直接观察的仅限于草地、森林、山、花朵,和极小范围的一些动物,也因此她所用的意象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些意象却非常适合表现她个人的思想和内心冲突。她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其瞬息间的思想感情融入在诗行中。
动物意象作为一种具体意象在狄金森诗歌中反复出现,含义丰富,是其诗歌中自然意象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使狄金森的诗歌时而灵动,时而瑰丽,时而神秘。本文将尝试分析动物意象在狄金森诗歌中的表现及其功能,探索动物意象与狄金森诗歌主旨表达的关系。
一 动物意象与狄金森对自然的认知
在狄金森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她三十多岁选择归隐生活时,父亲的花园成为了她休憩的领域,大自然成为她仅有的亲密朋友。自然不仅如母亲一样安抚着狄金森,还召唤了小生物来陪伴她,带给她欢娱或慰藉。在第348首诗里,诗人自诩“苦难国的女王”(The Queen of Calvary),正是蜜蜂、知更鸟、水仙花这些自然的造物陪伴并慰藉着孤傲、苦难中的作者。由此,狄金林的诗歌里有大量的植物和动物的意象就不足为奇了。狄金森认为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能作为自然本身的一个象征。诗人用人们熟悉的事物定义自然,而动物意象则成了诠释狄金森诗歌自然主题不可或缺的元素,生动传递着诗人对自然的认知。
1 美丽生物,理想自然
首先,动物意象勾勒了狄金森精神世界中理想的自然景象。根据本文作者统计,狄金森诗歌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动物词汇是鸟(Bird-260次,Robin-40次)、蜂(Bee-109次,Bumble bee-14次)和蝴蝶(Butterfly-28)。这些词汇出现远高于其它动物词汇。由此,我们不难判断,狄金森偏爱可爱的、自由的、体型小的、会飞的动物。狄金森曾在诗中直接将朋友比作小鸟和蜜蜂,因为它们“会飞翔”和“有羽翅”。这些小巧喜人的动物配以花草,加上狄金森的奇思妙想,构建着和谐自在、妙趣横生的自然画卷。在狄金森看来,“造就一片大草原需要一朵红花草和一只蜜蜂”,她熟识蜜蜂与蝴蝶,“丛林中美丽的居民”待她都十分亲切。狄金森诗歌中有较多的蜂蝶嬉戏的欢乐景象。如“草儿要做的事儿不多/只有一方纯绿的天地/仅让蝶儿流连/专供蜂儿嬉戏”。诗中不乏作者与蜂蝶同乐的场景:“‘店主’把酩酊的蜜蜂/驱赶出毛地黄花的门庭/蝴蝶/也不再浅酌慢饮/我却要喝得更多更凶!”;“告诉我蜜蜂品啜多少杯/纵饮花露长酩酊”。与蜂蝶相伴,使作者得以逍遥自得,忘怀得失。
在狄金森的诗中,动物意象演绎着季节轮回。季节轮回在狄金森诗歌中占有一定比例。诗人描绘着四季的不同色彩、景物以及一些标志季节更替的典型动物。在狄金森的诗卷中,我们看见早春三月沾着泥浆的小狗和冬日里孤独的小鸟,我们得知当夏日即将结束,“鸟儿活跃过后”,蟋蟀“在草丛里悲声迸发”,大黄蜂“飞过太阳的那一边”。诗人以一只苍蝇的身份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写信给蜜蜂,勾画出了和谐的大自然在春天里的生机与活力。可怕的苍蝇与美丽的蜜蜂共同分享着春天到来的喜悦。这封“信”中也提及了其它一些典型的动物意象――青蛙,鸟儿。狄金森打破传统人类文化中“苍蝇”贪婪、邪恶、肮脏的象征,赋予苍蝇一种新的含义,它代表了和谐与生命力。可见,即便是一个人见人恨的微小生灵在诗人的诗歌中亦获得一席之地,在狄金森眼中,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灵魂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蜜蜂对于狄金森来说,是诗意自然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描写夏日景象不可或缺的意象。除前面提到的第1775首,第19首也强烈突出了自然画卷中蜜蜂这一动物意象。作者自比玫瑰,配以蜜蜂、清风与其他植物,构建了一幅动态的、清新美好的、夏日清晨的画面。而蜜蜂的衰老理所当然地象征夏日的逝去。
我们可以用狄金森的“自然是我们所见”一诗总结诗人和谐自然这一主题:
“自然”,是我们所见
山峦――午后的风光――
松鼠――日月食――野蜂
不――自然就是天堂――
“自然”,是我们所闻――
食米鸟――海洋――
蟋蟀――雷霆
不,自然就是和声(Harmony,又可译为和谐)――
‘自然’,是我们所知――
我们却无法说明――
要道出她的单纯――
我们的智慧无能――”。(668)
诗中运用了一些典型的动物意象,即松鼠,野蜂,食米鸟和蟋蟀。这些动物意象在《狄金森全集》中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15,14,9和8。这首动物意象和其他自然景象构筑的自然诗卷,阐述了大自然的一切事物与人类之间关系融洽、和平共处这一主题,也言明了大自然的神秘和不可知。
2 神秘生物,敬畏自然
狄金森的自然诗歌色调多变,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因时、因地、因心情而变化的,是前后矛盾、互相对立的。在日常观察中,她发现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不可逾越的疏远感:人们可以感受自然、崇敬自然,但不能揭示自然的奥秘,也不能完全融入自然。
自然对人类及其它生物的漠视态度令诗人感到既神秘又敬畏。在她的名篇“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中(328),诗人不仅刻画了自然界生物间的弱肉强食,而且强调了自然界对一切生命的生死漠不关心并泰然处之。更重要的是,诗人指出人与自然完全契合的境界永远无法达到。如“蜜蜂的喃喃声”一诗中,诗人将蜜蜂的喃喃声比喻作巫术,揭示了自然的神秘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狄金森的视角不仅仅停留在美丽的自然事物上,她还刻画了那些易被人忽视的、外表可怕的生物,如老鼠、苍蝇、蛇、蜘蛛、蝙蝠等,用以揭示自然的神秘、冷漠、危险。在“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中,诗人提到了与蛇的相遇,试图与之亲近却受拒绝。“我”与“蛇”的相遇象征和暗示着人与自然的一种原始的冲突关系。自然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对人根本漠不关心。两者之间的疏离感永远无法打破。诗人对蛇的情感正表露了诗人内心深处面对“自然之谜”时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感:恐惧、崇敬以及困惑。在诗人的笔下,这些丑陋的生灵也深深打上诗人的情感烙印,成为具象征性且包涵有丰富心理文化内涵的典型意象。
狄金森运用动物意象诠释着她对自然的复杂甚至矛盾的感情。在退隐之后,自然几乎成了她的最为亲近的朋友,但诗人眼中的自然却呈现着两张不同的面孔,或是温柔可爱美丽善良,或是暴戾善变冷酷无情。狄金森心中既有对和谐自然的诗意歌颂,也有对自然的冷漠和不可知的质疑和敬畏。也许狄金森这种矛盾情结不可避免,因为美与丑交织,弱与强共存才是完整和谐的自然。
二 动物意象与抽象复杂的概念和关系
在诗歌中,意象是具体有形地传达抽象的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媒介。狄金森曾表示,“要说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说”。所以诗人常用比喻性和描述性的意象,表现哲理或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其中不乏动物意象的运用。
1 动物意象与抽象概念
狄金森常用动物隐喻阐述抽象或是复杂的概念。诗人将“一点小名声”比喻成“一场刺痛甜蜜的短暂斗争”,暗示对名声的追逐犹如追逐蜜蜂,可能享受甜蜜的战利品(蜂蜜喻指名声),但必须忍受刺痛的苦难。在第319首中有一个类似的比喻,“我们追求的天堂,像六月的蜜蜂”。诗人指出世人追逐的世俗快乐可能不过如夏日的蜜蜂一样喧闹和短暂。在第254首诗中,狄金森把希望比作“长羽毛的东西”,借“那温暖可爱的小鸟”在凶猛的风雨中被打得发愣,表明希望的美好和脆弱。
狄金森也运用动物意象探讨死亡、宗教。诗人厉声谴责上帝的不公和世事的荒唐,因为上帝对信仰虔诚的“我”和只知索取的“小鸟”持同一态度。“我”不仅虔诚地祈祷,还有“雅致”的风度和仪表,时刻关注着上帝是否在意;相比之下,小鸟却显得浮躁而缺乏教养,它不仅急躁地“顿足”,而且还高叫“给我”,迫不及待地要求得到上帝的“仁慈”。在狄金森死亡诗歌的精品之一“我听见苍蝇嗡嗡叫――当我奄奄一息――”中,苍蝇这一意象让读者难忘。卑微的苍蝇出现在叙事者弥留之际、上帝应该出现的庄严时刻。上帝不垂顾弥留之际的受难者,而一向为人不齿的苍蝇在这一刻表现出勃勃生机,讽刺了上帝的冷漠。苍蝇也暗示了诗人对永生的怀疑。
2 动物意象与复杂的人类关系
诗人以大自然为背景,借助动物意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复杂的人类关系。狄金森常用动物意象比喻男女情爱。蜂与花演绎的情人模式是比较稳定的意象组合模式。蜜蜂常以变化无常的情人形象出现。蜜蜂与花时而为甜蜜的恋人,关系融洽:“蜜蜂向花求爱,鲜花接受了他”;时而又轻率地背叛爱情,频频离婚。在第565首中,一群凶猛的雄狗追逐一头无助的母鹿,最终“排满女主角两侧”的雄狗蜂拥扑向母鹿,对其施行轮番侵害。诗人用简洁含蓄的语言,借助雄狗和母鹿的形象描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画面,影射了人类社会残忍的行为(刘守兰,2006)。除了狗,狄金森还借用其它兽性动物意象展现施虐者的形象。其中描写出色的则是蜜蜂、蜘蛛和蛇。如蜜蜂残忍地摧残“盛开的红玫瑰”,并把它一口吞到肚里(1154);而纯洁的玫瑰不仅因此丧失性命,而且还遭到名誉的诋毁。狄金森生动地表现出受害者为此做出的反抗,她们用如“天鹅绒般的”柔弱的身体筑起围墙,抵御侵犯。
三 动物意象与诗人的自我认知
有些动物意象承载着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即象征诗人本身。狄金森运用一些动物意象直接表述自己的主观感知,使读者在想象世界里直观感受作者形象。狄金森将自己与一些会飞的生物作比,如蜂、鸟甚至蚊子。她曾声称“只当一只蜜蜂”,“在空气的筏子上畅游/整天里在乌有乡划行/”。诗人自比筑窝的麻雀(84),表明她的心易守着家。诗人把生性温良的知更鸟看作自己的化身(刘守兰,2006),坦言“知更鸟是我的标准调”。虽然她梦想能够如蜂和鸟一样自由飞翔,可残酷现实让她沮丧,诗人禁不住感叹她连卑微的蚊子都不如:“活得像我一样寒酸,就是蚊子也会饿死”,“我也不像蚊子享有特权飞舞”(王冰,2010)。狄金森自比作断翼的诗歌精灵,只能孤独、无助地孑孓在现实和诗歌世界之间。
结语
狄金森创造意象的技巧娴熟,其动物意象的意义之丰富恐怕难以一文尽述。来自日常生活的动物意象在狄金森的诗歌中超越了它们的世俗的形象,准确生动地传递了狄金森的诗情、诗意。本文认为狄金森的动物意象是其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诠释了诗人对自然的复杂甚至矛盾的认知,清晰阐述了诗中抽象概念和复杂关系,巧妙传递了诗人的自我认知,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艾米莉・狄金森,这位“苦难国的女王”,借诗歌的翅膀,与形形的动物朋友相伴,得以翱翔想象的天空,尽情演绎悲喜诗情。
参考文献:
[1] 毕凤珊:《艾米莉・狄金森的自然视角》,《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2]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刘守兰:《狄金森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蒲隆:《狄金森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5] 王冰:《折翼的诗歌精灵――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矛盾情结》,《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