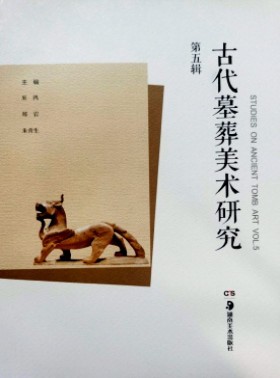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古代痴情女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古代痴情女子范文1
关键词:情感 理智 世俗 爱情
从主题上来说《氓》是一首弃妇诗;从情节上来说《氓》是以女子的口吻来追述其不幸的婚恋经历,其以凝练的文字概括了中国女性在婚恋变更中的不幸。美丽的爱情缘何总归毁灭,《卫风·氓》为什么最终以悲剧收场,答案是:女主人公用情太深,理智的砝码太轻;男主人公过于世俗,庸俗的思想挤兑了爱情的空间。
一、越陷越深,爱难遁逃
当我们的蚕桑公主躲过家人目光,冒着世俗苛责的危险,应约来到汤汤淇水之际,悲剧的种子就在这看似甜蜜的恋爱时期生根发芽,因为在与世俗理智对立的道路上,我们的主人公走得太远。同样深陷爱河,与恋人贸然约会,《诗经·将仲子》中的少女却一再劝告她的恋人不要翻越墙院来与她幽会,因为她在意父母和兄长的责骂,也在乎旁人的闲言碎语。心怀浓浓爱意,却不失时机地提醒对方保持恋爱季节应有的距离,不失为明智之举。而我们的蚕桑公主在恋爱季节却不曾说出半个“不”字,千依百顺也必将被人掌握。
1.“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这个叫氓的帅小伙,看似老实,却一肚子花花肠子,一脸憨笑、耍着花招,假装卖丝,向女主人求婚。一方面说明氓求婚心切,敢于大胆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更说明了氓的狡黠。而女主人公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情人眼里出西施”,误把狡猾当真诚,把阴谋诡计当甜言蜜语。爱情就是这样,它来时你根本无从知晓,知道时却已被套牢。
2.“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按照先秦的传统,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氓只身来到姑娘面前,就想把姑娘娶到家里,不免操之过急,是一种轻浮的表现。而且,当氓没有马上得到姑娘的答允时,就恼羞成怒。可见此人不是怜香惜玉之人,他大男子主义,有严重的性格缺陷。我们的蚕桑公主面对恼羞成怒的恋人,却没有半点责备,而是妥协退让,私下许诺婚姻。氓的易怒是细节,而不幸的婚姻往往是在恋爱时忽视了细节。
3.“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从这六句来看,该女子在爱情的大泥坑里陷得太深,难以自拔。告诉大家“在爱情中迷失自我的人,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婚前女热男是小鸟依人似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的蚕桑公主婚后仍是痴心绝对,将丈夫锁定在视线范围之内,原本就大男子主义十足的氓,怎么会受得了。氓不是神话中温柔十足的董永,更不是传说中彬彬有礼的许仙,他是带着忠厚老实面具、满肚花花肠子、性情暴躁如雷、奴隶夫权社会背景中的氓。
4.“以尔车来,以我贿牵。”——本诗没有提到氓送什么样的彩礼给女方,女主人公出嫁的时候却有大量的财物相陪。俗话说的好“门不当、户不对,过了日子也受罪!”如果我们不把这“门当户对”看作是婚配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的齐头并进,而将它指向婚姻当事人的成长环境、文化层次、受教育程度、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等等,这些元素旗鼓相当、基本匹配,更容易保持婚姻天平的平衡,那么“门当户对”也不无道理了。这也是下文“我的兄弟不知道我的处境,都讥笑我”的伏笔。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女主人公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二、创伤再三,苦难言说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所以古代的女子寻找归宿的欲望是十分迫切的。《诗经·召南》中就有一些诗句表现大龄女子未及时出嫁的恐慌,女子希望求婚男子及时到来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迫切。但是,这些对婚姻充满期待的女子,果真能在婚姻的天堂安然栖身么?答案当然是不能。对我们的蚕桑公主来说,婚姻不是天堂,而是粉碎梦想的坟墓。只字未提婚后的幸福生活,而是写氓的变心,婚姻的彻底失败,那么,氓变心,婚姻失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1.蚕桑公主体衰色减,美貌不再。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女主人公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光彩照人的少女在岁月中蹉跎了美丽的容颜。氓的所作所为与婚前背道而驰,不念旧情喜欢上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
2.采桑女沦为家庭主妇,失去了少女时代的天真浪漫。周国平说:“爱情是浪漫的,婚姻很现实,婚姻就是在一起过日子,很现实,而且日常生活是很琐碎的,就浪漫不下去了。”我们的蚕桑公主想到过氓家庭贫困,但对“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的劳作还是缺少足够的心里准备,再加上氓本身就不是懂得心疼女人的“贾宝玉”,婚姻里的朝夕相处很轻易地让他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何况蚕桑公主的容颜美,已经在岁月的打磨中大打折扣了呢!因此,被抛弃的命运便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3.氓在婚姻中彻底撕掉了他温情脉脉的面具——脱掉羊皮,它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心愿满足之后,开始虐待妻子。当这个本应饱含温馨和睦的空间被内部暴力侵蚀时,婚前所有的希冀都将成为永不结束的噩梦。
4.娘家人笑贫——亲人、娘家人都笑话采桑女,并且看不起她找的女婿!这使得她们的婚姻关系雪上加霜。“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娘家人对遭受家庭暴力的采桑女不管不问,只能使其陷入更深的孤独,有苦难言,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三、无爱不立,愤然决绝
在婚前,我们的蚕桑公主怀着对氓炽热的深情,勇敢地冲破了礼法的束缚,与心爱之人执手走入婚姻的殿堂,期待更加美好的生活。但事与愿违,她却成了氓的玩偶甚至是虐待的对象,面对这样一个负心的丈夫,她终于识得氓之真面目,斥责氓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亦已焉哉”成为古代女子铿锵有力的独立宣言。
《卫风·氓》的悲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这是由社会特点决定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附属地位,她们的生活天地都很狭小,生活的幸福与否都维系在丈夫身上,如果遇上一个对感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丈夫,那她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痴情女子负心汉”这哀婉的旋律如同魔咒一般,在中国文学长廊中反复回旋,直到如今。
参考文献:
[1]康怡然.千年前的婚姻之殇——浅析弃妇诗《卫风·氓》中的悲剧美及审美价值[J].金山,2011,(8).
古代痴情女子范文2
关键词:超凡脱俗;多愁善感;聪慧过人;至纯至真;才华横溢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43-02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巅峰之作,是一部了解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其中的主要人物林黛玉以她独有的魅力深得读者的喜爱,她的容貌才情令人赞叹,她的悲惨命运令人同情。她虽泪尽而逝,但她的美好形象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我们可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这个人物。
1 超凡脱俗的美天仙
在大观园众多的美女中,林黛玉的美也是出类拔萃的。她的魅力在于她具有独特的气质,在她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曹雪芹为了突出这种美,采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的方法,在宝黛初会时,作者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正面描写了她的美貌:两弯似蹙非蹙 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是作者第一次正面描写林黛玉超凡脱俗的美,难怪宝玉看后称她是“神仙似的妹妹”。
除了正面描写之外,作者更多的是从侧面烘托黛玉之美。林黛玉初到贾府,王熙凤第一次看见黛玉便夸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虽有讨好贾母之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黛玉确实美丽不凡。在二十六回中,黛玉去怡红院找宝玉,见院门关着,便在门外叫门,偏偏晴雯等丫头没听出她的声音来,不给她开门。黛玉便疑心宝玉不让丫头门开门,又不便前去质问,因此独自站在花阴下,悲悲戚戚地哭起来,由于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之美,她这一哭,使那附近柳枝上的宿鸟栖鸦都飞起远避,不忍再听。这里的写法和古代形容美女具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可谓异曲同工。
2 多愁善感的病西施
林黛玉由于自幼丧母,父亲年近半百,又无姊妹兄弟扶持,因此被外祖母派人接往贾府抚养。没过几年父亲又去世了,小小年纪过早的经历了生离死别之痛。贾府里黑暗龌龊的环境,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遭遇使她形成了多愁善感的性格,又由于多愁善感,使得天生病弱的她更加多灾多难。
花开花落是自然界中的正常现象,这在常人会熟视无睹,而林黛玉看见花落了,就去葬花,为的是使花“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正因为她有着敏感的内心世界,所以这样惜花,护花。有一次因和宝玉发生了误会,黛玉由落花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如泣如诉的《葬花吟》充分表现了林黛玉伤感的内心世界。
不仅是自然之物的荣枯兴衰会牵动她的愁肠,人际之间的交往也常使她伤心落泪。宝钗命女仆在雨夜给她送来调养用的燕窝,黛玉非常感激,一时又羡慕宝钗有母亲兄长,再加上听见窗外竹梢焦叶之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不觉又落下泪来。当宝钗把哥哥从南方带来的笔墨纸砚、香袋扇坠之类的东西送给她时,黛玉看见家乡之物,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人篱下,不觉又伤心起来。正所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个闺中弱女哪里禁得住如此经常伤悲,因此黛玉更加体弱多病,虽多方医治,万般调养,但仍不见好转。虽和宝玉真心相爱,愿同生共死,但又怎奈无人做主,前途渺茫,这更使她愁肠百转,加重了病症。因此在他们的爱情毁灭之后,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3 聪慧过人的可人儿
林黛玉可谓天资聪慧,冰雪聪明。她不仅能写诗作词,还会抚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她的聪慧也胜人一筹。她初到贾府时,贾母命人带她去见两个母舅。当到了贾政的房内,王夫人坐在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料定这是贾政之位,便向椅子坐了。这个细节中的“料定”二字突出地表现了黛玉的聪慧。黛玉的聪慧还表现在她的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上。贾府中有几张厉害的嘴。如凤姐的“嘴”,贾母的“嘴”,晴雯的“嘴”,红玉的“嘴”;黛玉也有一张更利害的“嘴”。宝玉的奶妈李嬷嬷说:“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利害。”但凤姐等人的“嘴”与黛玉的“嘴”又有文野之分:凤姐多是“世俗取笑”;黛玉则显得典雅别致。正如薛宝钗所说:“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言为心声,心慧则言巧。
4 至纯至真的痴情女
林黛玉的纯真痴情,更集中更强烈地体现在她对贾宝玉的爱情之中。这种爱情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基础之上的,表现得非常纯真、深挚、坚贞。她爱贾宝玉是因为他俩情投意合,并不是贪图贾家的富贵。因为林黛玉是一个清高的女孩儿,她视权贵为粪土,就连皇亲国戚也不放在眼里。当宝玉把北静王赠的香串转赠给她时,她说“什么愁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并扔在地上。其傲骨令人赞叹,使须眉汗颜。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至死靡它。宝玉挨打之后,她的眼睛哭得和“桃”一般;宝玉夜间冒雨前来探望,她虽恋恋不舍,但仍劝宝玉回去歇息,当得知仆人打着灯笼来的,忙将自己的玻璃绣球灯送与宝玉,以防夜黑路滑失脚跌倒; 紫娟试探宝玉对黛玉是否真心,宝玉因吃惊而痴呆,袭人前来问罪,当听说宝玉生命垂危时,黛玉悲痛欲绝。然而,他们的爱情又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这就难免有痛苦、有折磨,甚至要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
5 才华横溢的女诗人
林黛玉才华横溢,有着浓郁的诗人气质。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于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出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别人作诗都冥思苦想,她却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然后一挥而就。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推崇,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例如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的“柳絮词”,缠绵悱侧,优美感人,语多双关,句句似咏柳絮。字字实在写己,抒发了她身世的漂泊与对爱情绝望的悲叹与愤慨。尤其她的“诗”,连咏三首,连中三元,艺压群芳,一举夺魁。她的诗不仅“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而且写得情景交融,菊人合一,充分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满纸自怜题素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谐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等句,更写出了这位少女的高洁品格和痛苦灵魂。
林黛玉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美貌纯情、多愁善感、聪慧过人、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女性形象。她是封建社会贵族少女的一个典型代表,她的不幸遭遇是封建社会贵族阶层女子悲惨命运的反映。正如作者所说“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曹雪芹是蘸着血和泪塑造的林黛玉这样一个悲剧形象,这个形象自诞生之日起,不知使多少人为她倾洒同情之泪,她的纯美形象会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打动无数喜欢她的人。
古代痴情女子范文3
关键词:刘巧珍 赵巧英 爱情 婚姻 封建思想 教育
路遥,这位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陕西作家,以一部名为《人生》的中篇小说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普遍关注,这部他“反复折腾了三年”才写出的《人生》将一位没有文化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农村少女刘巧珍带到了世人面前。耕耘在山西土地上的作家郑义也在自己的成名作《老井》中成功塑造了出色的农村姑娘赵巧英。本文就这两位农村姑娘形象进行比较,试图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一
刘巧珍在路遥笔下是传统美的化身,她善良、美丽、质朴而又纯情,“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卑而不自贱”。[1]她如金子般纯净,又有流水般的柔情。赵巧英身上有同巧珍一样善良、美丽的美好品质。不同的是,她是新型的农村女性,是巧珍羡慕的像高加林那样的文化人。她不像巧珍那样甘于一辈子在土地上耕耘,“自小‘怀在省城’而‘生在老井’,嗣后又念高中,因此对现代城市文明有着一种天然的理解和向往”,[2]出去闯荡一直是她的梦想和追求。
爱情是人类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因而成为许多文学作品中重笔描写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生》和《老井》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展开的。
巧珍和巧英都是勇于追求爱情的姑娘。面对教师被下、成为农民的落魄高加林,巧珍大胆向他表白:“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过,你在家里呆着,我给咱山上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3]为了爱情,她不顾忌世俗的眼光,勇敢面对父亲的粗涉和村里人的蜚短流长。巧英“对旺泉的爱的追求是真挚热烈的,她自诩自己是‘狐狸精’,想方设法同旺泉结成爱的伴侣,为此她不畏惧传统道德的束缚,勇敢地、执着地要把旺泉夺到自己身边来”。[4]当他们的爱情遭到阻挠时,她大胆地和旺泉一起去县里登记。
“爱情,在巧珍的心目中,那应该是奉献,是将人生的甘露斟满,捧给心爱的人,是埋藏下所有的苦痛,献给爱人整个的春天”。[5]她把高加林看得比自己的父母还亲。加林失意时,她替拉不下面子的他卖馍;为他买烟、买碘酒;把家里的蛋糕、鸡蛋偷偷拿给他吃。当加林有第二次进城的机会时,明知等待她的将是分离的相思和失去的担忧,但她终因不忍加林痛苦,选择了支持他出去工作。即便最后被抛弃,她仍跪地乞求准备奚落加林的姐姐不要整治他,并求姐姐拜托高明楼为再次成为农民的高加林谋得一份教师的职业。
爱得热烈、无私的赵巧英同样将自己的“整个春天”奉献给了孙旺泉。孙旺泉不得已“嫁”入喜凤家后,她痴情依旧。在山路上遇到口渴难耐想讨水喝,却因对她心怀愧疚而欲躲开的旺泉时,她主动喊住他。旺泉把碗往嘴边送时,她故意摘下花头巾,将上面的草种、草屑抖进碗里。这一举动看似是对旺泉的报复,实则因为她担心跑出汗的旺泉喝凉水喝得急会喝出毛病,为让旺泉边吹边一丝丝抿,才故意为之。为帮孙旺泉实现打井的愿望,对打井并不感兴趣的她一次次冒险上山勘察井位。面对塌陷,她舍命护住旺泉,自己受重伤昏死过去,险些命丧烙饼崖。即便如此,她也没有退缩。
二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6]的确,在刘巧珍的世界里,高加林的坎坷与烦恼就是她的痛苦与灾难,她情绪的钟摆始终随他摆动。她眼中的高加林志向远大、才华横溢,如神明一般。而现实中的高加林却是个具有双重性的矛盾人物,他自卑而又自负、自觉而又盲动,是强者又是弱者。
高加林进城卖馍见到熟人时的躲闪足见他的自卑;农民出身的他又自负忘根,看不起乡下人。他眼界开阔,不满于父辈在黄土地耕耘的命运,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可他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却又割断了与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联系。他才华不凡,无论是教师还是通讯员,他都干得如鱼得水;然而他的才能却得不到施展,教师被下,通过“走后门”得来的通讯员职位也被撤。试图摆脱黄土地的他最终又被投回了黄土地。
孙旺泉与高加林一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努力奋斗着,但与高加林带有自利色彩的奋斗所不同的是他的奋斗带有利人的性质。他本可以离开老井村追求自己的生活,但为了完成老井人寻觅水源的目标,他选择留在老井村,把打井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甚至为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井”。
在爱情上,高加林被动接受了巧珍的爱,他们相恋的过程中虽有甜蜜,但他们的心灵并未真正的沟通交融,这源于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源于他们精神追求上的矛盾差异。高加林有追求,爱幻想,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刘巧珍则满足于与高加林组建一个欢乐的农民家庭,绝无非分之想。高加林待在农村时,这种矛盾差异被暂时压抑,但当他进入县城后,面对新的诱惑,权衡比较后,他接受了对自己发展有利的黄亚萍的追求。虽然说“爱情也是需要发展的,它不仅仅是靠曾产生过的爱,更需要不断有新的内容来补充、扩展”,[7]但又不可否认,高加林的决定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前途和追求考虑,抛弃巧珍的行为带有一种自私自利的色彩。
孙旺泉对赵巧英的爱是专一的,虽然他三次“闪脱”了巧英。第一次,他迁就了祖父,成全了弟弟;第二次,因老井村找水一事非他不可,他当选支书;第三次,井打成后,面临“一头,是支撑几十代人苦挣苦熬下来的理想、儿子,加上贫困的故土和没有爱情的家,一头,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自由富足的生活,加上失去了存在依据和没有理想的陌生世界”[8]的两难选择,理想和故土的召唤左右了孙旺泉的决定。三次“闪脱”绝非是他对爱情不忠,而是在客观现实影响下,他不得不割舍对巧英的爱。他的割舍是源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并不带有自利色彩。
三
古代社会,男女青年的结合往往会受旧传统、旧习俗的影响。那时的婚姻大多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的爱情常会遭到家庭长者的阻挠。《天仙配》中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被王母娘娘强加干涉;《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横遭焦母拆分。时至近现代社会,家庭长者仍是阻挠年轻人自由爱情的主要力量。《家》中觉新与梅芬的爱情就断送在封建长者手中;《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三仙姑横加阻挠小二黑与小芹的结合。历史的车轮驶至当代,许多封建陋习已被文明之风吹散。但在许多农村,人们脑海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并未被彻底清除,仍有不少家庭长者或多或少左右着年轻人的自由爱情。《人生》中的刘立本不仅阻挠巧珍去读书,而且试图在婚姻上为她做主。他以打骂的方式阻止女儿与穷小子高加林自由恋爱。孙旺泉的爷爷万水老汉为了实现他“娶一嫁一”,不让老孙家断了香火的心愿,宛如恶神般割断了旺泉和巧英的爱情,逼迫旺泉“嫁”入喜凤家。
婚姻是爱情美满的归宿,如此而言,巧珍和巧英的爱情都未能走向美满。巧珍嫁给了自己不爱的本分庄稼人马栓,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接受了父亲当初对她的婚姻所作的安排。巧英带着一身伤痛离开了老井村,她也许会嫁人,但却不会是她唯一一个“真正动过心思的”孙旺泉。
巧珍与巧英的婚姻让我们意识到,虽然八十年代的农村正被文明唤醒,但人们观念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短时间内还是很难被彻底消除,无形之中,它仍在左右人们的心。相比以前,八十年代的农村妇女开始敢于追求自由的爱情。但当这种追求的支撑点消失以后,她们仍无法彻底摆脱强大的世俗压力和无形的道德规范的影响。这在巧珍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她曾为了爱情不顾忌世俗的眼光,不畏惧父亲的粗涉;但当被高加林抛弃,追求的动力消失以后,她接受了自己不爱的马栓,开始了一段无爱的婚姻,向世俗低了头,也被自身潜意识中的种种陋习击败了。
相比巧珍,巧英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她渴望出去闯荡的梦想,她不同于巧珍,她的能与爱人在精神上沟通爱情以及她在最终抉择上的进步都与她受过教育有很大关系。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贞节观念,委身于已婚的恋人孙旺泉。经过自己多次努力争取,最终在对自己与旺泉的未来绝望后,她没有像巧珍那样随便找个人嫁掉,而是走出了老井村,去开始一种未知的、崭新的生活。她受传统封建道德规范和世俗压力影响的程度要远弱于巧珍。也正因为此,从刘巧珍到赵巧英,我们虽然看到了封建礼教思想、封建道德规范对农村女性在爱情与婚姻选择上的影响,但也看到了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农村女性进步的希望。
刘巧珍与赵巧英这两个痴情的女子都未能与自己深爱的人走到一起,很难说谁幸,谁不幸。她们这种“不肯把自己的失望和痛苦留给心爱的人,只希望自己的牺牲能使对方过得愉快、过得舒心,自己则爱得痴心、爱得苦涩”[5]的痴情女子形象,将长存于文学作品的人物长廊中。
注释:
[1]路遥:《路遥文集》(第二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2]魏威:《山•井•人中篇小说爱情描写赏析》,名作欣赏,1985年,第6期,第14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华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4]张侯:《不同的追求与抉择――读郑义的》,小说评论,1985年,第5期,第66页。
[5]耿英春:《新女性形象的重塑及其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巧珍与珍妮的形象之比较》,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25页。
[6]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一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7]郑义:《老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古代痴情女子范文4
时下一方面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一方面又是“我自用我法”。在这样的创作风气下,“形”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而又苍白无力,谈论形好像只有在评述写实一路画家时,才有价值和意义。有一部分画者特别是经过学院教育,或是正在接受艺术高等教育的,他们认为形的训练是作为绘画创作的初级课程。当绘画实践从习作阶段发展到创作阶段,“形”也就变成不重要的元素,甚至可以完全不用理会,造型能力的好坏在“创新”概念的掩饰下被伪装和粉饰。再将创作实践与理论相联系,我们又会发现在中国传统古代绘画理论中,如苏轼就曾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同类论述还有“气韵为先,形似为末”(汤逅《画鉴》)等。字面所反映的信息似乎是形的无足轻重,是对谢赫“六法论”中“应物象形”这一原则的反驳。于是不求形更是变得“理直气壮”,“有根有据”,更不用说还有诸如“试验性”、“表现性”、“意象性”等等时髦又深奥的现代概念做后盾。
我本人很赞同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说法,也并不反对“试验性”、“表现性”、“意象性”等现、当代艺术观念及其艺术实践成果。只是不成熟的认为:在绘画实践发展了数千年的今天,如果仅仅将“应物象形”理解为外形的相似,或是单纯的形的复制,似乎是不够全面,甚至是有些片面、静止思维的味道。中国艺术不论是文学方面、书画方面、亦或是戏曲方面,始终都是围绕着“言志缘情”的思想性进行发展的。“精神的符号”、意象式特征是整个中国传统文艺共有的、基本的特征。正如《尚书》所述“诗言志,歌咏言”。在此前提下,形体不会只是指单纯的外形。仅以戏曲为例,在京剧中曾经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出经典的浪漫爱情悲剧――《霸王别姬》,在唱腔的婉转迂回之中,虞姬的挥泪舞剑令人难以忘怀,将项羽这位末路英雄与痴情女子虞姬之间的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作为观众,我们又是如何从舞台外了解到她的悲伤呢?是语言吗?或许有,但真正让我为之动容的仅仅是一个动作,一个简约到极致称得上是符号性的动作――兰花指在眼前轻弹两下。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发觉京剧的简约竟具有如此生动的表现力。“兰花指”在此时不仅仅是一种形态或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在瞬间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一个动作发展为一个过程、一种情感――是对人世的留恋、对爱人的不舍,又是对自刎的决心。同样的抽象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京剧反映千军万马时的“以一当十,三五成群”等方面。简约却极富有表现力,表现得更为突出。既然自然界的形体是笔墨与情感的载体。那么六法中的“应物象形”也应该指的是绘画的过程,它不仅仅止于形似,而是始于形终于写神,达到形神兼备。进而为“气韵生动”做好铺垫。必须说明的是六朝人以“气韵”作为品评绘画的审美标准,根源还在于当时的绘画中要求充分再现现实世界中的人物(这个历史阶段的绘画仍以人物题材为主,山水之类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是这种再现是从志容相貌到内心世界的如实描摹。因此,在绘画全面发展的今天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应物象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二十世纪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个性,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然而几百年来,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对中国画的认同还大多停留在中国画是指宋元以来形成的文人画为主流的水墨画。这就形成当今画坛上的不同阵营,一方面传统性较强承袭古人的中国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继续受到青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画家正在苦苦地进行中国画创新的思考和探索。
古代痴情女子范文5
关键词:汉乐府 叙事 抒情 缘事而发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众多学者把这句话单纯地理解为汉乐府的叙事性,这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汉乐府“缘事而发”发的是情。因此,在研究汉乐府时,不能单纯地认为它是叙事性的还是抒情性的,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一、中国古代“由事生情”的传统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这305篇作品中,有很多抒情诗,但是也有不少叙事诗,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叙事还是比较早的。其实,从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人们表达“事”远远比表达“情”要早。
“事”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古至今,人们都生活在“事”中,虽然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动物,但在人类社会早期,“抒情”这个意识并没有非常普遍。相反,古代结绳记事却非常普遍。人们用绳结表示事情或者挽一个绳结来提醒自己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但是,从来没有人用绳结来抒情,没有人会因为心情好或者不好去结绳,也不会去记录下来。这就足以说明,古代叙事还是比抒情早的。其实,人类生存的本身就是无数个事情串联而成的,“事”是人类记忆的延伸,后世的文化是围绕“事”的言说形成的。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当代史官在“事”的书写中建构历史,历史学家才能在记录本朝或考察前朝的历史中得到教训,总结经验。坦白地说,通过分析历史得到教训,从中总结出经验就是一个抒情的过程。如杜牧写的《阿房宫赋》中“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呼!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通过秦朝二世而亡的史实抒发感情。
文学是“事”的诗性言说,人或物之间形成的事件,要是不记录下来,它就只能是一种潜在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被慢慢淡忘,甚至湮没在历史洪流中。东汉《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白居易《与无微之书》中也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诗经》来说,《诗经》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叙事诗,《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是周王朝的史官和乐工根据民间传说进行的再创作,可视为我国古老的民族史诗。这些诗虽然是叙事诗,实际上也离不开抒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远古祖先的膜拜景仰。可见,“由事生情”的传统本身就是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二、汉乐府“缘事而发”中的叙事与抒情
前面说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少人就从“缘事而发”这四个字判定汉乐府的叙事性,这是不确切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说:“‘缘事而发’常被解释为叙事性,这并不确切。‘缘事而发’是指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发为吟咏,是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事’是触发诗情的契机,诗里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也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缘事’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袁行霈的观点给了笔者启发,其实汉乐府“缘事而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叙事,其实发的是情。这样,在看待“缘事而发”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必须把汉乐府的抒情性和叙事性结合起来研究。
(一)汉乐府的叙事性
叙事诗是用诗歌来叙事,它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有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但是只有这些还不能称为叙事诗,它的情节过程要完整,人物要具备一定的形象性,事件要具有典型性的叙事成分,这样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
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说:“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说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诗经》多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而汉乐府所描绘的则是广阔的生活画面,现实性和社会矛盾穿插其中,使汉乐府所描绘的内容更有典型意义。《陌上桑》是汉乐府中比较轻松诙谐的诗篇,极有喜剧色彩,整个故事主要是罗敷与太守的冲突,场景虽然单一,前后时间也不长,但仍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矛盾冲突。《妇病行》有三个场景:病妇亡故弥留托孤,丈夫在路上遇亲友哭诉,亲友在病妇家见孤儿啼哭索母。在这三重场景中,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以生动的人物对话展开,这样一个由病引起的家庭悲剧几乎是汉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乐府中除《孔雀东南飞》以外,篇幅都不长,这种短篇作品,往往对所要表现的事件不作全面的有头有尾的叙述,而是恰当地选择足以充分表现生活矛盾和斗争的一个侧面,加以突出集中地来描写。由于所选择的正是能够承载诗人强烈情感的片段,因此,虽然篇幅短小,却能给人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东门行》是一首表现老百姓在穷困、饥饿、压迫下铤而走险,以反抗求生存的诗歌。作为汉乐府中一种独特的写法,它没有很多说明性的文字,省略了前因后果类的台词,选取最精彩的片段,犹如一场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以人物对话展现心理活动和矛盾斗争,揭示了当时政治腐败、徭役繁重、农村破产、民不聊生的社会图景。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矛盾冲突和包含的思想冲突、性格冲突却非常尖锐深刻。“出东门,不顾归”,开头六字突兀,统摄全篇;“来入门”是片刻的动摇;但是家中“无斗米”“无悬衣”,已经没有退路,只能下定决心,这一番冲突包含其中。一个小小的镜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实质和症结,这样的乐府诗,虽然只是选取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片段,但却能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
至于叙事情节中的人物,更是具有“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有事件就有人物,人物是事件的中心构成,汉乐府中最多的就是通过矛盾冲突表现人物,不论是聪慧机智、蔑视权贵的秦罗敷,还是勤劳善良、忍让坚贞的刘兰芝,或是凄凉的老人、悲苦的孤儿,在乐府诗中,创作者都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表现特定的人物性格,同时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
(二)汉乐府叙事性中的抒情特征
“缘事而发”正如袁行霈说的那样,“缘事”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所发的是情。汉乐府诗歌叙事性的特点,是与言志抒情的紧密结合,也是“感于哀乐”。汉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复杂的社会,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多彩的精神生活,也有阶级对立和强权压迫,这些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人们有感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很容易发出各种感慨,特别是借用某一件小事的契机去抒发感情,这便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最初来源。
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汉乐府每一个事件中都有发出的情,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叙事。我们都知道《孔雀东南飞》,它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最完整、情节最生动的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宏伟的叙事诗。全诗由遣归、惜别、抗婚、殉情四个部分组成,时间空间跨度大,多条线索交织而成,“叙事如画,叙情若诉”。从小序“时人伤之,而为此辞也”来看,这篇诗作好像是诗人耳闻目睹,在真人真事和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写成的,是一部有人物、有场景、有过程、有事件、有剧情发展的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也有抒情在其中。总的来看,《孔雀东南飞》是一首抒情意味很浓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意味很浓的抒情诗。
汉乐府中有很多“缘事而发”的抒情,同时,在事件的叙述中抒情特征十分明显。如《孤儿行》,详细写了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被兄嫂虐待的故事,生活凄惨悲苦,痛不欲生。结尾“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是对起始句“命独当苦”的照应,是孤儿绝命诗的完成。这首诗通过对孤儿悲苦命运的描述,揭示了整个社会重金钱、轻人情,人与人之间充满虐待和欺压的黑暗现实,是对惨无人道、尔虞我诈的世道的血泪控诉。前面提到的《东门行》《妇病行》也都是“缘事而发”的典型。除了这些,乐府诗《有所思》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由热烈的相思,到对负心汉的痛恨绝决,以及绝决又犹豫彷徨的缠绵过程;《上邪》表现了坚贞不渝的爱情,这些诗作都有明显的抒情特征在里面。纵观汉乐府,缘事而发中的抒情与叙事是分不开的。
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后世影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集叙事和抒情于一体的,它直接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与诗歌的抒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种诗歌独有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影响社会,像《汉书·艺文志》中说的“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余冠英《乐府诗选》中也说:“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中,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在汉代当时,这样的诗作反映了社会生活,或是欢乐嬉戏,或是凄惨悲苦,用社会现实“缘事而发”,表现各种情感。
魏晋时期三曹七子等诗人,大多饱经董卓之乱的忧患,敢于正视现实,悲悯世人,反映离乱。如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面貌,深得汉乐府精神。不过,作为汉末动乱的目击者与亲身经历者,建安文人的叙事诗不像汉乐府那样以旁观者的语气作客观的描述,而是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所见所闻,同时也书写自身在现实中的主观感受。在这方面,蔡琰的《悲愤诗》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就堪称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典范。
唐代时期,杜甫是真正贯彻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种叙事抒情模式的典型。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原因,杜甫不像李白能写出《蜀道难》《将进酒》这样节奏的诗篇,而是从其切身的流离之痛、深入的社会体验以及真挚的怜悯之情出发,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创作精神,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这样的诗篇,特别有汉乐府中《东门行》《孤儿行》的情感意味。到后来的白居易、元稹,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乃至明清时期甚至近代,都有不少以事抒情的佳作,由此可见,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抒情模式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郭茂倩.乐府诗集(一卷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张永鑫.汉乐府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