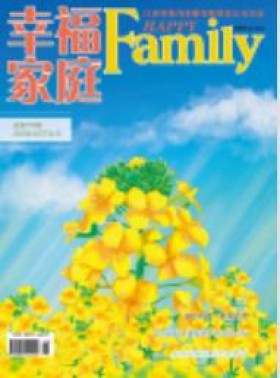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第一炉香小说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第一炉香小说范文1
论文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国民劣根性 凡人软弱性 冷静 传统 现代 影响力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 发展 的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 历史 、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 艺术 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 发展 。
第一炉香小说范文2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冷”;人物角色
用“冷”的笔调写作是张爱玲独具的写作手法,冷言冷语,仿佛一切与她无关,她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述说者而已;冷冷清清、冷酷的世界,没有一点儿温暖,人情淡薄;而让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张爱玲所塑造的一大批经典人物形象的身世命运的凄凉和悲惨所隐射出来的彻入心骨的寒冷,这种冷,冷得让人心寒,冷得让人心惊。
一、女性角色的“冷”
1. 想改变却改变不了的“大家闺秀”
这类女性角色以《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最为典型。她受过教育,是传统家庭里淑女式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大家闺秀。从表面看,她追求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其实被传统法道德束缚,地位十分尴尬。在香港潜水湾饭店上演了与范柳原的情感对弈,最后瓦解了自己的价值观,完全失去独立人格,成为依附男人的寄生虫。张爱玲通过这部小说想要表达的是那些守旧的女性会渐渐被社会淘汰,难以自处。但是,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封建传统思想、女性的附庸地位始终扼制着女性的发展,即便提倡恋爱婚姻自由,也改变不了女性的卑微的地位与命运。
张爱玲小说的特点是从一个世俗的角度去展现普通人真正的情感状况:人与人之间未必尽是誓死的相爱与信任,对于女性来讲,感情就是投资。这与传统做法大相径庭,自古以来凡是提到爱情多半是以极其崇高的角度去歌颂、赞扬,感情是纯粹的、理想化的,一旦得不到,必以死赴之。作为一部抒写爱情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的爱情不再崇高,流苏看似改变了范柳原对婚姻的想法,却改变不了自己被别人主导的命运。
2. 天真却无知的“梦幻女孩”
张爱玲从不以美的角度去所塑造角色,不会去歌颂爱与真善美,反之以“丑”为切入点,用老道的文笔刻画出人性的灰暗面。这类女性毫无自我意识,愚昧却大胆、单纯却无知。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游走于多个男性中的的娇蕊、《心经》里有恋父情节的小寒。他们固守着不被认可的情感幻想,活在自己的梦里,这样的作品里是能看得见道德伦理的,压抑的欲望呼之欲出。
张爱玲从容地把爱情故事从天上拉回人间,女人们不再是女神或观音,是无处不在且真实的人。小说里无论哪类女性,生活的主题从未离开过金钱与男人。他们经常受金钱与的折磨,在灰色的人生道路上,自导自演一出出哀婉的悲剧。我们一方面从这些女性身上看到世俗悲情,另一方面得到的是冰凉彻骨的人生感悟。
3. 性格畸形、自我毁灭的“变态女人”
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作为女性,曹七巧这样带有毁灭人格的形象在中国文坛上是不多见的。而作为一个母亲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更是极其具有颠覆性的。她不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慈悲与善良,还是荼毒自己儿女的邪恶凶手,她没有道德标准,痴迷于物质上的追求,用金钱满足自己的膨胀,所作所为总是渗透出阵阵寒意。
另一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梁太太与曹七巧相似,以荼毒自己的侄女来满足。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女性生活单调,精神匮乏,他们大多扮演着受虐者与施虐者的双重角色,所作所为构成一组现实的悖论,真切的萦绕在现实的周遭。
费勇在《张爱玲作品集》前言里说:“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寒冷、荒凉。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单的,在自己的家里,也永远有着异乡人的凄楚。”张爱玲的笔下没有温暖的家,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冷酷和虚无。
二、男性角色的“冷”
1. 懦弱虚伪的假绅士
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表面上看他,出身清白,工作体面,为人谦恭有礼,是知识分子的典型。内里他膨胀,与朋友的妻子娇蕊暧昧不清,可真正面对这份情感时又无法担当。他也会忖度行为是否正确,还按照理想的标准娶了孟烟鹂,可最终还是觉得不称心。于是他破坏之前营造的正确世界,以公开、疯狂地变本加厉地宣泄来砸碎妻子、砸碎自己、砸碎这个家。
2. 风流成性的花花公子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展示了许多这样的人。如有二十多位姨太太的乔成、多金放荡的司徒协以及男主人公乔琪。乔琪混迹于贵妇中间,靠吃软饭过活。张爱玲给乔琪的定义是带点丫头气的阴沉脾气。但纵观整部小说,乔琪调情、取宠都是为了钱,是带有特点的男性,这样的角色是很少有的。
3. 自私敏感的小市民
《茉莉香片》中20岁的聂传庆,病态、懦弱,一心寄托于老师言子夜能给他关注和父亲般的关爱。他嫉妒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遂以疯狂的殴打她作为报复。聂传庆对言丹朱施暴后,言丹朱说他跑不了。这里的“跑不了”,说的是那个时代的男性,他们在时代变迁中苦苦挣扎,他们是女性悲剧的制造者与参与者,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制造悲剧。
这些人物,一遍一遍的展示自己失败的人生,弥漫出浓厚的清冷之感。每个人背负着 “不得不然”苟活,上演人性的悲剧,这既与张爱玲创作惯以苍凉为底色的原因有关,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2].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3].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第一炉香小说范文3
2009年7月1日-9月30日,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文学资料室举行“难得团圆: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展览。 展览展出了由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博士赠给香港中央图书馆的《小团圆》手稿影印本,以及宋氏借出其它与张爱玲作品相关的重要物品。
此前,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内地版首发仪式在北大百年讲堂举行,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其生前挚友宋淇、宋邝文美夫妇之子的宋以朗,在首发仪式上出示了张爱玲的日记以及张与他父母的通信。对于那封要“销毁《小团圆》”的书信,宋以朗说,“我要提示一下,这封信不是遗嘱,不是法律文件,它是众多书信里面其中一封的其中一句。我想请你们想想,如果你收到一封信是说《小团圆》要销毁,后面说‘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你会怎样?你会不会去找根火柴,把它销毁呢?我想不会吧。”不管这本书的出版是否“合法不合理”,宋以朗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还原一个完整的张爱玲。
民国临水照花人
《小团圆》近日在港台两地出版,极速登上畅销榜首位。昔有专程赴港“色戒游”,今有翘首盼台“团圆邮”(台版《小团圆》因内地读者纷纷邮购而脱销)。
《小团圆》之前,张爱玲绝少在作品中讲起自己的身世。与胡兰成那场惊世骇俗的“倾城之恋”,更从未写过只言片语,这给了“张迷”无限的想象空间。
胡兰成曾写过,“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就是因为这种光芒,13年后,张爱玲还是一个传奇。
张爱玲从未为自己出版过传记,这本书的面世,间接令坊间所有关于张爱玲的传记都要丢进垃圾筒。盛九莉是不是张爱玲?真实的张爱玲当真如此吗?
关于《小团圆》,一直有告诫的声音说,不要搞对号入座,但是,《小团圆》里的首次“自白”还是惊讶了许多人的眼睛。香港专栏作家迈克认为,《小团圆》中,张爱玲连自己的生日星座都懒得虚构,所以,有理由对全书作索隐研究。
“恐怕所有的作家一生都在痛苦地选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隐藏自己――按照E.B.怀特的说法,这就像是在火车卧铺上脱裤子――你既得脱,又不能露出关键部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免疑心,断定张不愿公示‘团圆’的,并不比擅自发表‘团圆’的,更正义一些,更善意一些。”上海翻译家黄昱宁说。
张爱玲笔下的角色历来是感情上的“骨灰级”人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乔琪乔给的那点冷冷的快乐燃尽了自己;《金锁记》中,曹七巧“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来按捺对姜季泽的爱,最终却将他赶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平凡的好人佟振保,贪恋带来的欢愉,又不想承受随之而来的责难,直至被痛苦和无奈淹没。她唯一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倾城之恋》,范柳原与白流苏这对俗世男女还是借着战争倾城,在生死交关之时,才得以真心相见。
正在法国读研究生的Lydia第一次读到的张爱玲作品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真正特别喜欢她的作品是十六岁,经历了初恋,能看懂些了,忽然觉得好苍凉。”Lydia说。年少时,除了《红楼梦》和张爱玲,她不怎么爱看其他的中国小说,在她的感觉里,两者有着相似的氛围。
“张的小说里有一种很少见的虚空的感觉,但并不是虚空那么简单,虚空之后还有热情。”
张爱玲曾在信中告诉友人:“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回千转,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句话被出版商印在《小团圆》一书的腰封上,成了不可多得且引人遐思的宣传语。
“团圆”非“圆”映轮回
13年前的9月8日,中秋节前夕。这天,张爱玲在洛杉矶一间极简陋的单人房之中,被发现气绝身亡,终年75岁。
其实,她早就预示了自己的命运,十多岁时写《天才梦》,她说:“生命是一个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对于世上千千万万的张迷来说,除了看书,只能睹物思人。《小团圆》以女主人公盛九莉的心理描写为主线,辅以其他人物与九莉的交往,盛九莉既有照片里见到的那个瘦高叉腰女子的冷傲,也有“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的小女人娇憨,同时,还能看到她在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和莫测的情场风云时,从未暴露的敏感自卑与焦虑不安。
这是一个很难概括的主人公,她在完稿30年后最终进入读者的视野,颠覆了张爱玲在之前作品里留给人们的印象。
“我们常说张爱玲爱胡兰成很深很深,那是受胡的传记《今生今世》所影响,他把所有感情升华至爱情小说一样,一切枝节在他笔下都美化了。可以这么说,她的确爱他至不能自拔。”节目主持人谭艾敏说。
在那个乱世,胡兰成跟张爱玲两人一见钟情,几乎每天都到她家里看他。遇到张爱玲以前,胡已是结过两次婚而且儿女成群的人。为了张爱玲,胡兰成与太太离婚后,两人亦随即结婚,婚纸上写道“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是墨还未干透,他就要到武汉办报,而且随即看中了年轻的护士小周。日军投降后,在政府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被迫逃走,逃难期间,再次遇上了范秀美。后来胡兰成逃难到温州,张爱玲想念他,专赴温州探望,这样又发现了他的乱情。
“在爱情权力的天秤上,张爱玲输光了所有筹码。”谭艾敏说。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张爱玲看得要比普通人通透,年幼时父母不和的家庭阴影,母亲弃家留洋的离别之痛,使得她过早地习惯于理清那些表面浓厚但实质脆弱的感情。
刚过二十岁的“张迷”小羽第一时间买到大陆版的《小团圆》,熟悉张爱玲传奇人生的她,能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那些人一一对号入座,她坚信张爱玲内心的高贵。
“张写《小团圆》有着她自己复杂的原因,但可以肯定,不是为了报复。不论作为作家的她有多么理智,她始终是一个女人,一个悉心描绘自己的爱情的女人。”
第一炉香小说范文4
摘要张爱玲及其作品以持久的艺术魅力几十年来影响不绝如缕,在港台地区甚至出现了一批追随张氏创作风格的“张派”作家。亦舒作为香港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虽自称“师承于张爱玲”,对张的继承却不在标志性的“张腔”――绮丽繁复的意象和阴暗而疯狂的艺术世界。在上海/香港的“双城”背景下,她以都市叙事和女性书写,与张爱玲的都市/女性文本构成了某种对话。
关键词:都市叙事 女性书写 张爱玲 亦舒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的小说内蕴丰富,影响深远,近几十年来,港台的女性作家,鲜有不受其影响者,无论作家承认与否,论者却总能从其文本中找出与张爱玲的相似之处,“弱水三千,取饮一瓢”则足以扬名于文坛。亦舒自称师承于张爱玲,却一直未有研究者将其并而论之。艺术水平的差距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亦舒缺乏标志性的“张腔”,恐怕是根源。颜纯钩在《张爱玲的天地因缘》一文中,指出二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对练达人情的描摹,以及文本中的世故之气,终究肤浅。笔者用时下颇为流行的“双城”理论观照二人的都市文本,发现二人在都市叙事和女性书写两方面彰显出相暗合、相纠结,可供比照的关系。确切地说,张爱玲和亦舒从都市细部到整体,以充满了鲜明的性别意味的女性对话,演绎了上海/香港的“双城记”。其中,亦舒学张又能走出张的影响,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一种新的都市女性叙事文本。
一 雅俗共赏的定位
古代自《诗经》以降,唐诗、宋词、戏曲剧本、明清小说,一流的艺术作品必然同时具备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在张爱玲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而亦舒作品贯通雅俗的特色,也成为其小说几十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特征在学术界早有定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这样的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的出现,标志着沦陷区文学(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共赏’的时代美学追求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而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中,同样把张爱玲作为借鉴雅俗文学各家所长而自成风格的典范,并对其所借鉴的中外雅俗文学作品一一列举,令人信服。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她对中国通俗小说有“难言的爱好”,她说那里面的角色是“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是一样艺术呀。”张爱玲很注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为迎合读者趣味,她愿意“将自己归入读者中去”,这样“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 “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司,对白,颜色……”。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能长时间获得读者的青睐,许子东认为有四大原因:1、迷恋都市,小说集中讨论城市的变化及其百彩多姿,写城市生活的狂野刺激;2、把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字结合,以古典华丽的字词迷住读者,字里行间尽是春光;3、有通俗的商业包装,又能肯定小市民的价值观,把纸醉金迷的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4、以女性的感官意识细致描述恋爱问题,尤其把两性的悲欢离合刻画得覆天盖地。许子东将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特色阐释得可谓十分透彻。张氏小说的成功在于有效兼顾了现实生活与个人愿望,同时配合了商业的包装,把文学的元素与环境结合,缩短了流行小说只写灯红酒绿与纯文学追求文字秀丽、讲究形式创新的差距。因此,在香港,无论严肃作家还是通俗作家都将她奉为圭臬。
而亦舒往往被内地学者们视为流行小说家,是因其作品具有流行小说的要素:别致的开头,跌宕曲折的情节,言情、历史、侦探、异域风情糅合于一体,这一切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亦舒突破了言情小说写情而不言志的局限,剥去小说言情的外衣和通俗的形式,她有着比一般流行小说家“多一点”的文学思考。她将都市职业女性作为表现对象,对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内核做了深层观照和思考。在香港本土意识高涨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亦舒以其极具“港味”的都市故事,参与到了香港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之中。在流行文学占主流地位的香港,亦舒将严肃的文学思考置于流行形式的创作策略,无疑成为其作品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雅俗共赏的文学定位,成为张爱玲和亦舒文学创作比较的基点。而将张爱玲、亦舒作对举比较,是因为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沦陷时期的上海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的人生观、艺术观的形成、写作基调的奠定又与其早年的香港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亦舒生于上海,童年时到了香港,虽自称香港人,但生命里的上海背景挥之不去。上海的美食、上海话、上海的老电影以及老上海的繁华所象征着的某种神秘都蛊惑着她在小说中不断地将其想象。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香港在经济地位、城市风貌和文化气质上的暗合,以及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为镜像”的关系,为两位作家的都市/女性文本对话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上海和香港的“双城”关系就不能不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
二 书写双城:“他者凝视”和“自我探寻”
从1939年7月张爱玲到港大读书至1941年“港战”爆发,张爱玲在香港度过的时间统共只有三年半。对于香港,无论如何她只能算是个“他者”。香港于她,是个光怪陆离的异域,匆匆一瞥,留下的只是刹那印象。而她偏偏为香港写了一本“传奇”。她将它描述成殖民者眼中的东方,“荒诞、精巧、滑稽”;上海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半中半西、半洋半土,具有异国情调但缺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张爱玲津津乐道的是此中人“不甚彻底的道德感”。以香港为背景的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为例。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小公馆坐落在半山上,花园外就是荒山,园子仿佛乱空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的杜鹃花,园子外面的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薇龙从梁家出来,感觉犹如《聊斋志异》里的书生只身前往鬼域,而此时“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成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香港所代表的现代都市性被忽略了,诡秘阴森的场景成为人物活动的幕布,一切仿佛被抛到了现代文明之外。而在《倾城之恋》中,见惯了城市风景的白流苏,一下船,却被香港各种巨型的广告牌扰乱了心思,自忖“在这个夸张的城市里,只怕摔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一路走来,火一样的“野火花”、冷而粗糙的墙,犯冲的颜色,或张扬得刺目或冷酷到荒凉,显得与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而灯红酒绿的舞场、饭店又使这个城市显得摩登而“洋气”。古老与现代就这样矛盾共存,而这样的背景,少了羁绊和压抑,主人公的行动似乎可以放肆一点,故事似乎可以离谱一些。于是,张爱玲让葛薇龙、白流苏、聂传庆等“参差对照”的人物穿梭其间。在“他者凝视”之下,香港成为“传奇”。无独有偶,40年后,另一位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也作了类似的想象:“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的大相遇”,她将个人经验提升到所谓的“香港经验”,唤起了无数内地人对香港的憧憬与向往。
比起香港,上海是张爱玲的“家城”。去掉了“他者”视角,她一支笔出入于上海的里里外外,描绘出世俗烟火氤氲弥漫的都市民间。古老而颓败的家族尽收眼底,它是真实的、亲切的,也是传统的、压抑的。在张爱玲看来,它依然是“老中国”。传统的、式微的大家庭成为“老中国”的缩影,就像《倾城之恋》中的白家,《创世纪》中的匡家,阴暗、压抑、沉闷,有人的地方,人影幢幢,形如鬼魅,无人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而空气中飘散的是老中国的鸦片香。在张爱玲这个上海人看来,香港是传统的、道德的、沉闷的“老中国”――上海的“他者”,是一个可以逃离到的地方。
三 亦舒:“世俗”与“传奇”
亦舒的生命历程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她的书写摈弃了外人加诸于香港身上的种种传奇色彩,她笔下的香港是势利化的香港,极少浪漫也绝无幻想。香港发展出一种中西混杂、又非中非西的文化。
90年代随着经济的转型,香港步入了后工业时代,文化形态上也相应出现后现代的景观,人们普遍陷入一种消费的迷狂,亦舒这样形容港人惊人的消费能力:
“香港没有一样东西是贵得不能流行的。”
正如张爱玲所言:
“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
物质上的丰裕与享受,并不能掩盖精神上的贫乏,香港人在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深深地遭受到由此带来的道德价值的沦丧。因此,都市市民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生的种种精神病象,成为亦舒都市文本的主题。如《喜宝》中的姜喜宝,喜宝的堕落就是对金钱的追求导致的有意识的堕落。喜宝们享受着出卖自身所换取的物质享受,却丧失了爱人与被爱的能力,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动力。
都市人的出路在哪里?面对都市人的迷失,亦舒孜孜以寻。她没有张爱玲虚无的精神背景,不会让她的人物陷在虚无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因此在小说结尾处她总会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设法为主人公寻找到出路。“逃离”成为亦舒为其主人公选择的出路之一。与内地扯不断的亲缘关系,使得她笔下的人物下意识地选择了往回转,逃离当下,回到与她们有着或浓或淡的血脉联系的故乡,现实的逃离即是如此。《曾经深爱过》中,迷失于“我城”的周至美在遥远的东北――一个不发达的北方小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在那里她重温了淡薄已久的人间亲情。《喜宝》中的勖聪慧在厌倦了香港的尔虞我诈之后来到内地,在贫困地区做了中学教师,在天真稚嫩的童心包围中,用勤勉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现代的张爱玲,当代的亦舒,将上海/香港互为映照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二人笔下的所谓上海与香港,传奇与世俗、“他者”与“我城”的交相变换,并非作者创作的偶然对应,或是论者的牵强附会,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正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城市文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只初露端倪,而物质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都市景观和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方式引起的都市人的情感反应,更多的是新鲜和震惊,都市物质文明虽然来势汹汹,但尚未撼动这个农业文明的古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而牢固的根基,却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已经失去生机的古国带来现代的鲜活的气息。张爱玲出身名门,没落贵族的家世使她深深地感受到了古国的腐朽、颓败和对人的压抑,对于刚刚到来的都市文明她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喜爱。相比较于上海,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芜杂、鲜活又不乏都市味道的香港便受其钟情,她将其“传奇化”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与张爱玲相比,亦舒生活的香港已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业都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上呈现出后现代景象,无深度、无历史感,理想破灭,价值陷落,都市文明的弊端愈发凸显。传统文化的根基太浅,新的文化、价值观又没有建立起来,而香港尴尬的文化身份更加重了港人精神的无所归依感。因此,曾为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不中不西的香港文化此时却为亦舒所诟病,香港叙事的“去传奇化”成为亦舒突出的写作策略。怀旧,是上世纪末一道流行的文化景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怀旧风潮中,老上海是香港人不会遗忘的一道风景。而昔日沉闷压抑的“老中国”又成为亦舒眼中的“传奇”,这似乎是历史所开的玩笑,但实际上则有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许子东、梁秉钧:《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亦舒:《喜宝》,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炉香小说范文5
张爱玲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连环套》、《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在这里完成,因此当时的上海媒体嘲笑她是“公寓作家”。“张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子,比如“这世界上的感情,哪一样不是千疮百孔的?”“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等等,也都出自爱丁顿公寓六楼65室那张书案。张爱玲还写了记述爱丁顿生活的《公寓生活记趣》,她骄傲地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不仅如此,她与胡兰成的秘密爱情也在六楼65室发生、酝酿,终致结婚,张爱玲用她那支派克自来水笔在婚书上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如今的爱丁顿公寓已经更名为常德公寓。这座有着75年历史的楼房,外型散发着旧上海非常流行的“装饰艺术”(Art Deco),即使在今天,其建筑外观依然十分醒目,引人留恋。然而我们进入大楼后,却发现在里面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关张爱玲的痕迹。她当年住过的两套房子好似压根就是别人的公寓,若要追寻张爱玲留在上海的渺茫信息,只能通过油漆斑驳的报箱、房门上的黄铜把手以及老旧的拉栅式电梯进行怀想。带着满腹失望,我们来到楼顶,幸好那座小小的亭子间还在――这就是小说《心经》主人公小寒的住处。张爱玲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出了上世纪40年代最绝望的句子:“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上海与天与小寒。”
我们之所以在张爱玲六处故居中选择爱丁顿公寓,理由只有一个:这里是唯一悬挂“张爱玲故居”纪念铭牌的地方,其他五处没有任何有关张爱玲曾经住过的标识,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即使知道地址找上门去,结果也是一片茫然。最近几年,张爱玲的作品不仅没有随着历史的久远被人淡忘,反而散发出越来越强的文学魅力。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北美的“张迷”们和张爱玲的研究者纷纷来到上海寻觅张爱玲的踪迹,但是上海却用失望迎接远道而来的人们――除了常德公寓门前这块简陋的铭牌,再也没有什么以资纪念的东西可寻。
事实上,在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和标识上,并不止上海一座城市表现得如此冷漠。现代化浪潮下快速发展的城市,缺乏文化意识和历史责任,这已成为一个通病。前几年在北京,去新街口附近的百花深处胡同探访齐白石故居,初进胡同的感觉竟然与董桥的文章出奇的一致:“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幸好白石老人会画花卉,百花都在丹青里。”其实,这条破烂不堪的百花深处胡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大名鼎鼎,在这里住过的名人不仅有齐白石、汪曾祺、陈凯歌,还住过一位英国人哈罗德・艾顿(Harold Acton),这位牛津大学的美学家1932年起担任北大英国文学教授,是齐白石的崇拜者和挚友。
百花深处胡同还是中国当代摇滚乐的摇篮,北京第一批玩摇滚的如唐朝、张楚、何勇以及后来居上的陈升、窦唯都在这里咆哮过寂寞的青春。1983年夏季的一天,年轻的诗人顾城去什刹海找北岛碴诗,不成想误入百花深处,竟被这条青砖灰瓦的胡同死死迷住。他从地上捡了一截脏兮兮的粉笔,在厕所的墙上写下《题百花深处》:“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小院半壁阴,老庙三尺草。秋风未曾忘,又将落叶扫。此处胜桃源,只是人将老。”
第一炉香小说范文6
老爸和老妈是阴阳的两极,没他,我有可能看不见月亮,领会不到简单的美好。印尼排华的时候,老爸就带着七个兄妹回国。老爸从小没见过雪,他就去了长春。老爸差点没被冻死,又从小没见过天安门,他就来到北京,娶了我妈。在北京,的时候,差点没被饿死,他就卖了整套的Leica器材和凤头自行车,换了五斤猪肉,香飘十里。改革开放后,老妈开始躁动,像一辆装了四百马力引擎的三轮车,一个充了100%氢气的热气球,在北京、在广州、在大洋那边,上下求索,实干兴邦,寻找通向牛逼和富裕的机会,制造鸡飞狗跳、阴风怒号、兵荒马乱、社会繁荣的气氛。我问老爸,老妈怎么了?“更年期吧。”老爸说。从那时候起,老爸开始热爱京华牌茉莉花茶。老妈漫天飞舞的时候,老爸一椅,一灯,一茶杯,一烟缸,在一个角落里大口喝茶,一页页看非金庸非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侧脸像老了之后的川端康成。
老爸喝茉莉花茶使用各种杯子,他对杯子最大的要求就是拧紧盖子之后,不漏。“你喝茶的尿罐儿比家里的碗都多。”老妈有时候说。有老爸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茶喝,我渐渐形成生理反射,想起老爸,嘴里就汩汩地涌出津液来。老爸对茶的要求,简单概括两个字:浓,香。再差的茶放多了,也可以浓。通常是一杯茶水,半杯茶叶,茶汤发黑,表面起白沫和茶梗子。再浓的茶,老爸喝了都不会睡不着,老爸说,心里没鬼。我问,我为什么喝浓茶也不会睡不着啊,老爸说,你没心没肺。因为浓不是问题,所以老爸买茶叶,就是越便宜越香,越好。老爸在家里的花盆里也种上茉莉花,花还是骨朵儿的时候,摘了放进茶叶,他说,这样就更香了。小时候的薰陶跟人很久,我至今认为,茉莉是天下奇香。
我对我初恋的第一印象,觉得她像茉莉花。小小的,紧紧的,香香的,白白的,很少笑,一点都不闹腾。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她的香气不全是植物成分,有肉在,和茉莉花不完全一样。后来,她去了上海,嫁了别人。后来,她回了北京,进出口茶叶。我说,送我些茶吧。她说,没有茉莉花茶,出口没人要,送你铁观音吧,里面不放茉莉花,上好的也香。
十几年来,我的初恋一直买卖茶叶,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六小罐,每罐六小包。“好茶,四泡以上。”她说。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闲字,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每天一封信,信里没有一句“想念”。
我偶尔问她,什么是好茶?她说,新,新茶就是好茶。我接着问,还有呢?她说,让我同事和你说吧。电话那头,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开始背诵:“四个要素,水,火,茶,具。水要活,火要猛,茶要新,具要美。古时候,每值清明,快马送新茶到皇宫,大家还穿皮大衣呢,喝一口,说,江南春色至矣。”我把电话挂了。
香港摆花街的一个旧书铺关张了,处理旧货。挑了一大堆民国脏兮兮的闲书,老板问,有个茶壶要不要,有些老,多老不知道,不便宜,300文,我二十年前买的时候,也要200文。壶大,粗,泥色干涩。我付了钱,老板怕摔坏,用软马粪纸层层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