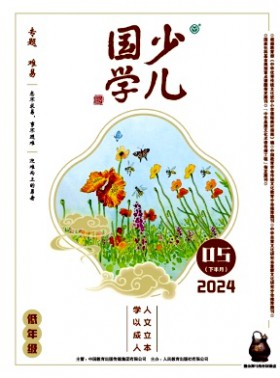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古诗草的解释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古诗草的解释范文1
这是我曾经无数次梦到过的场景,此刻是梦中的一切再现了么
一直都觉得最好的景色不在景区,而是在路上,此次草原之行更加印证了这个观点,一行人、四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奔赤峰原而去。虽然路途中从不晕车的我吐了个一塌糊涂,但是到达草原后,看着窗外绿油油的大地和随风摇曳的小花,心情大好,各种晕车反应也神奇消失。
自驾游的好处是景色优美的地方可以随时停车拍摄、玩耍,路边的景色太美,让我时时都有大叫“停车”的欲望,当地的朋友笑着让我“淡定、再淡定”,但还是终于在经过一片鲜花满地,牛羊成群的草地的时候忍不住了,大叫着停下车,抓起相机飞快地冲下去。
说来也怪,那草地上开满了我最爱的淡紫色小花、温顺的牛儿安安静静的吃草,还有一群小牛犊懒洋洋地卧在草地上,见我靠近,便好奇地打量,似乎在辨别我是否有敌意,他们是不是需要起身逃跑。远远地,牧牛人赶着三只牛慢慢走来,三只牛儿按体型大小一字排开,连步伐都一致,仿佛爸爸、妈妈和宝宝一家三口在慢悠悠地散步,安静和谐的画面差点让我掉下泪来。
牧牛人走近了,热情的邀请我们去他的帐篷里喝酒聊天,黝黑的皮肤、爽朗的笑容让人不忍拒绝,可惜我们只是路过,停留的时间有限。
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淑女形象全无,身边随风摇曳着不知名的小花,微风送来她淡淡的香气,萦绕在身边;阳光正好,暖暖地照在身上;远处的牛儿间或低叫一声,向我传递信息;那一刻我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轻松与喜悦,亦有些恍惚,这是我曾经无数次梦到过的场景,此刻是梦中的一切再现了么?那就让时光就此停留于此吧,留我在梦境成真的时光里独自享受,留我在这天地自然之间静静变老。
我们去时,主人家的两位女儿刚刚出嫁,婚礼就在同一天
去草原,如果没有机会去牧民家做客,不能喝到牧民家浓郁的奶茶、吃到香甜可口的炸果子,那是十分遗憾的。于是在从达里诺尔湖回赤峰的路上,我们到了当地朋友的家里,朋友家的房子建在贡格尔草原深处,房子周围还有自家的小菜园以及一条活泼好动、热情好客的狗狗。
贡格尔草原,水草丰美,风光秀丽,数条河流牵沿串泊,春天,野花点点,丹顶鹤、白天鹅、大雁等候鸟大批集合在此。夏天,碧草连天,湖泊水碧。秋天,墨绿的蘑菇圈遍布原野。冬天,原野茫茫,一片银白,所以我们笑称朋友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我们去时,主人二哥家的两位女儿刚刚出嫁,婚礼就在同一天,鲜艳的大红“喜”字让家里还保留着浓浓的喜气。看着两位新人身着蒙古传统服饰在鲜花开遍的草地上举行婚礼的照片,心里那个羡慕啊,草原儿女的豪爽与洒脱、幸福与甜蜜自是我等外人只能羡慕的。
淡远的传说中,是否有一处是你魂牵梦绕之地?随风摇曳的淡紫色花朵、随大地起伏的绿油油青草、随天空延伸的朵朵白云、随牧马人脚步行走的牛羊成群,粗犷又细腻的风情让人沉醉,这里就是我的梦中故乡!离开那已被世俗的喧嚣所淹没的风景吧,跟我一起来这里!
TIPS
交通:
1.北京—京承高速—滦平—转101国道到围场—走县道到赤峰
2.北京—京承高速—承赤高速—赤峰
3.北京—京承高速—承德—围场—塞罕坝—乌兰布统(此路线不推荐,过路费太高)
美食:
古诗草的解释范文2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二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三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五
古诗草的解释范文3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上,“才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才情”更是成为古典戏曲学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词汇。可以说,晚明是推崇“才情”最为突出的时代之一。之所以如此,这主要得力于汤显祖对“才情”这一戏曲审美范畴的理论自觉与创作实践。
在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史上,汤显祖已经被公认为最富“才情”的剧坛第一人,汤氏戏曲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剧作之“才情”。如沈德符《顾曲杂言》云:“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1]206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里所谓的汤氏“才情”呢?李昌集先生在《中国古代曲学史》中曾对此作过一番解释:“分而析之,‘才’指超乎一般的想象力、广博的文化修养和突出的文学创作能力;‘情’则指丰富而纯厚的情感世界和不拘程式、不受束缚的性格风采。合而释之,即独特的个性化思想光辉、情感境界和艺术创造的能力。”[2]519其实,这种解释忽略了汤显祖“才情说”的独特性与思想渊源,因为汤显祖的“才情说”与一般语义上的“才情”概念存在着差异,有着特定的理论内涵,其思想渊源来自六朝文论中的“情采说”。事实上,正是因为汤氏对于
“才情”理论的个性解读与自觉实践,才导致了“临川四梦”独特的审美风范,而晚明剧坛“才情”论的兴起亦离不开对汤显祖剧作的探讨。本文拟就这样一些问题展开论述。
纵观各家对于汤显祖剧作最富“才情”的定性,可以看出他们所谓的“才情”,其实侧重于剧作的文辞美。在明代剧坛,对汤氏剧作的“才情”定性,除少数曲家如臧晋叔持反对意见外,大多对此无甚异议。如王骥德批评臧晋叔:“谓‘临川南曲,绝无才情。’夫临川所诎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胜场,此言亦非公论。”[1]170王骥德认为汤氏剧作擅“才情”而拙于“法”,这其实代表了当时剧坛以“才情”与“音律”品评曲家的剧坛风尚。如王世贞《曲藻》就屡用“才情”、“声律”二语评论曲家得失。如他认为元曲作家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等人“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1]25;评周宪王杂剧、散曲时云:“虽才情未至,而音调颇谐”[1]34。明人沈宠绥在总结本朝曲坛家数时,更是以“才情”、“格律”二语概论之。如他在《弦索辨讹•序》中云:“昭代填词者,无虑数十百家,矜格律则推词隐,擅才情则推临川。”[3]19在他们看来,“才情”与“格律”的“双美”,才是戏曲创作所应追求的审美规范。如吕天成《曲品》云:“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4]37理论总是后于实践,明代中后期剧坛以“才情”与“格律”并举,并以之作为评论戏曲的标准,这主要得力于汤显祖与沈的戏曲实践。王骥德认为:“词隐之持法也,可学而知也;临川之修辞也,不可勉而能也。”[1]166晚明汤剧论者总是喜欢将“修辞”与“才情”并列,可见“临川之修辞”与“清远道人之才情”是相近的概念。吕天成曾说:“才人笔,自绮丽。”[4]303吴梅先生说:“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直是赵璧隋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惟其宫调舛错,音韵乖方,动辄皆是。”[5]33也就是说,古今论者对于汤显祖的“才情”评价,主要是着眼于汤氏剧作的文辞之美而提出的,即晚明一般语义上的“才情”论的侧重点在文辞。
在一般人看来,“才情”与“声律”,“合则双美,离则两伤”[6]263,但在汤显祖看来,“才情”与“声律”很难调和,宥于格律者必损“才情”。他在《徐司空诗草叙》中云:“余尝为友人分诟而作词。因知大雅之亡,祟于工律。南方之曲,北调而齐之,律象也。曾不如中原长调,隐隐,淙淙泠泠,得畅其才情。”[7]1146在他人看来,汤氏剧作富有才情而短于矩,但在汤氏那里,矩往往是才情的障碍,“大雅之亡,祟于工律”,用清代袁枚的话说就是:“但多一分格调者,必损一分性情,故不为也。”[8]489在汤氏看来,过度讲究声律会影响作者“才情”的表现。他在《答费学卿》中云:“文赋可通于时,律多累气。”[7]1412另如《与喻叔虞》云:“学律诗必从古体始乃成,从律起终为山人律诗耳。学古诗必从汉、魏来,学唐人古诗,终成山人古诗耳。”[7]1536这些都是在强调为文不能受律所制,应该以“立意为宗”,即《序丘毛伯稿》所云:“词以立意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经生之常。”[7]1141在汤氏眼里,“以法为宗”者乃“拘儒老生”。他在《合奇序》中云:“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像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7]1138汤氏以“苏子瞻画枯株竹石”为喻,所要阐述的就是他“以意役法”的文学主张。在他看来,只有“以意役法”,才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7]1134,使文章有“音外之音,致中之致”[7]1128。至于剧作是否合乎音律,在创作中大可不必太在意,因为歌者可以在演奏时“上下纵横取协”,即汤显祖在《花间集》卷三《酒泉子》评语中所云:“填词平仄断句皆定数,而词人语意所到,时有参差。古诗亦有此法,而词中尤多。即此词中字之多少,句之长短,更换不一,岂专恃歌者上下纵横取协耶!此本无关大数,然亦不可不知,故为拈出。”[7]1650在汤显祖看来,“祟于工律”将不能“畅其才情”,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声律之道,而是指戏曲声律应“变通促”,取舍决定于“才情”。汤氏于声律之学素有研究,他在《寄嘉兴马乐二丈兼怀陆五台太宰》中自云:“往往催花临节鼓,自踏新词教歌舞。”[7]567在《七夕醉答君东二首》其二云:“自掐檀痕教小伶。”[7]791由此可见汤氏的音乐与声律素养。他弃官家居后,与当地宜伶有着非常亲密而且广泛的接触,这在汤氏文集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汤显祖在《答马仲良》中云:“不少颇能为偶语,长习声病之学,因学为诗,稍进而词赋。”[7]1516汤氏“长习声律之学”,在他的文集中,保存有不少的论律之作。如《夜听松阳周明府鸣琴四曲》、《出松门回忆琴堂更成四绝》、《周长松琴堂晓发》等诗摹写琴音非常精彩;《答刘子威侍御论乐》、《再答刘子威》、《答凌初成》等篇论律均见解独特。如他在《再答刘子威》中云:“安足承问乐理。……仆前妄云因胡证雅,其音,非为准论。南歌寄节,促自然。五言则二,七言则三。变通促,殆亦由人。古曲今丝,未为绝响。圭葭所立,号云中土。南西音,要为各适耳。必欲极此悟谭,似以‘声依’为近。”[7]1317所谓“变通促,殆亦由人”,这代表了汤氏的戏曲格律观。在他看来,“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7]1302也就是说在戏曲创作中,九宫四声的“变通促”取决于“意趣神色”,即“才情”。
在“才情”与格律的问题上,汤显祖的“才情说”与当时一般语义上的“才情”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另外,汤氏的“才情说”并不仅限于此,它包括“才”与“情”两个方面,并以“情”为内核,有着具体的理论内涵,我们可以从他的相关文论中找到答案。如他评友人郑豹先《旗亭记》曰:“其词南北交参,才情并越。”[7]1151论友人虞长孺曰:“妙于才情,万卷目数行下。”[7]1158在《答凌初成》中云:“乃辱足下流赏,重以大制五种,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熳陆离,叹时道古,可笑可悲,定时名手。”[7]1142又如汤氏《戏答宣城梅禹金四绝》(其四)评梅禹金曰:“才情好似分流水。”[7]121汤氏论文,最重“才情”,他在《次答邓远游兼怀李本宁观察六十韵》中云:“尊酒灯,久阔谈燕,而良书美韵,其来。情无泛源,藻有余缛。至于商发流品,归于才情,雅为要论。”[7]634此语在《答邓远游侍御》中再次重申:“良书美韵,其来。至于商发流品,归于才情,雅为要论。”[7]1385汤氏所谓的“才情”,即针对“情无泛源,藻有余缛”而言。也就是说,汤氏“才情”论的核心在“情”,即“情无泛源”,这是从思想内容上立论;其外在表现是“才”,即“藻有余缛”,这主要着眼于文艺的外在形式,特别是文辞之美。
综合考察汤显祖著述的艺术特色,“情无泛源,藻有余缛”确实是汤氏诗文特别是戏曲的显著特色,这是他的“才情”论的重要内涵,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六朝文论中的“情采”说。六朝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情采”,这是古典文学在当时发展的自然结果。朱自清先生认为:“‘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9]223对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说法,李泽厚、刘纲纪先生认为:“缘情”与“绮靡”构成陆机所说诗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一切称得上是文学艺术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特征。尽管就文体而言,具体的要求对不同的文体可以有所不同。从《文赋》中可以清楚看出,陆机在论述各种文体的写作须注意的共同问题时,他所强调的也正是“缘情”与“绮靡”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即一个属于“情”(它和陆机所说的“意”不能分离,是构成“意”的最根本的东西)的方面,一个属于文辞的美的方面。……此外,陆机对诗之外的其他文体的特征的评论,分析起来也不外“情”与文辞的美两个方面的结合。[10]261—262
实际上,陆机对于“情采”的论述还比较碎乱,在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于“情采”的论述较为系统集中。如《文心雕龙•情采》曰:“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清人纪昀评之曰:“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而陈其弊。”[11]1145虽然在理论上六朝文人对“情采”的论述比较透彻,但落实在实际创作当中,却往往是“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12]180,作品大多“繁采寡情”。诚如陈钟凡先生所云:“南朝文学,诚中国美文全盛时期。惟其过于繁华绮艳,不免‘文胜’之讥。”[13]111六朝文学将“情”与“采”相结合,表现出了与传统儒家文论有别的审美趣味,使得古典文学的抒情性得以正式确立。到了明代,文人们对于六朝“缘情而绮靡”的文论主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明代顾起元《锦研斋次草序》谓:“绮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绮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饰情而为绮靡,或谓必汰绮靡而致其情,皆非工于缘情者矣。”[14]2789这实际上进一步道出了“缘情”与“绮靡”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汤显祖的著作将“情”与“采”相结合,正因如此,他才以“才情”光耀剧坛。吴书荫先生认为汤显祖:“诗赋能摘艳六朝,文采斑烂。”[4]35其实,汤氏不仅诗赋如此,戏曲亦然。他的早期戏曲如《紫箫记》就过耽绮语,带有六朝文学“采滥词诡”的弊端。如徐复祚《曲论》谓汤氏剧作为“字觋、句鬼”[1]245,徐渭亦曾批评汤氏早期著作《问棘邮草》:“有古字无今字、有古语无今语,……此似汤氏自为四夷语,又自为译字生也。
今译字生在四夷馆中何贵哉!”[7]154汤氏后来创作的“二梦”将“缘情”与“绮靡”结合得比前期作品要好。他在《答罗匡湖》中自云:“‘二梦’已完,绮语都尽。”[7]1401王骥德亦云:“《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径。”[1]165汤氏所谓的“才情”,是在六朝“情采”论的浸染下形成的。吕天成《曲品》谓汤氏:“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艳六朝,句叠花翻之韵。”[4]34从汤氏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六朝文学的热爱。如《初入秣陵不见帅生,有怀太学时作》:“才情偏爱六朝诗。”[7]213《送淮扬分司吴年兄并问谢山子》:“吾怜小谢最才情。”[7]753《送前宜春理徐茂吴》:“不惜风流频取醉,君来看见六朝人。”[7]354《送何仲雅入对》:“三殿云霞邀丽藻,六朝人物映轻华。”[7]381汤氏对于六朝文学的喜爱,从他弱冠之时就已开始。他在《与陆景邺》中云:“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未知其法。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7]1436在汤显祖看来,六朝文学最富于“才情”,所以他才“规模步趋”,并且“久而思路若有通焉”。
在汤氏看来,如果为文强调声律至上,讲究按字摸声,那么就会“不能成句”。艺术创作应当“畅其才情”,不能为法所役。汤氏这种思想与“公安派”文学主张有相近之处。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云:“自宋、元以来,诗文芜烂,鄙俚杂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