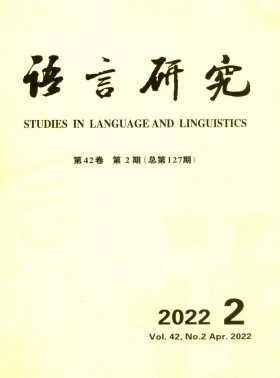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1
作为杂志主持人和诗歌选编、评论家,李少君给人的印象是积极有为,勇于开拓,而且个性鲜明,风格独特。他主编的杂志,深深地介入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论争,呈现了激烈变动中的当今社会的精神面貌。他的诗歌选编和评论,也积极介入当今诗歌混乱而充满活力的现实,试图影响、推动、并塑造对当今诗歌形态的认识。他宣称古代中国是诗教文化,极力推崇诗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他宣称现在是新诗发展最好的时期,称赞当今新诗取得的成就。他还以一种浑然无畏的精神,提出了广受非议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的概念。他的这些命名,似乎并非来源于学理深思的周全,而是来源于直觉的敏感与敏锐,内心热情的勇敢与奔放。而思想,就其惊醒人心的根本立意来说,不正是对时代精神的敏感直觉吗?就像有些动物出于本能的敏感,嗅出暴风雨来临之前空气中微妙的气息变化,而预先发出警示声?以直觉与热情的启示来论断,而不是以知识的汇聚与推论来思考,是诗人的天性。诗人的理论自有其非理性或非史实之处,却也有惊人、准确的洞察力量。因此,李少君就其天性来说,更是一个诗人而非评论家。因此,他的主张总是因其强烈、鲜明又留有漏洞而惹人注目、广受争议,完全不像很多评论家,写了很多四平八稳的文章,却没给人留下任何印象。那么,作为诗人的李少君,他当行的诗歌又是怎样的呢?
李少君的诗面目清晰,很容易就能看出其风格与取向。与他的思想评论文章的风格相反,他的诗歌非常沉静,主题单纯,所写几乎都是自然之美或内心(之爱)的微妙,音调和谐,气息徐缓。他诗歌的整个风格可谓温婉柔曼,幽静闲适。在具体写法上,他的诗语言干净,篇幅简洁;没有细密的描写与铺陈,只是用简洁的笔墨把主客融合的基本感受描画出来,留出大量空白,留下意义回荡的空间,使余味悠长;这是一种空灵之诗。总的来讲,他的诗是一种风格鲜明,成熟稳健的诗。它有自己的伦理基础,美学追求,有自己从属的传统谱系。这是一种高度自觉,根植于文化与教养的极为文雅的风格;是一个心智全面成熟的诗人,认识、经历、修养各方面都成熟之后的诗人高度自觉的选择。这种风格尽管有着自己独立的整体面貌,让人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来,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它不激烈、不炫目、不突兀、不喧闹、不极端,它显得温和幽静,偏于保守,是一种单纯的诗。
事实上,这种单纯的诗,在其表面欺骗性的简单之下,隐含着种种复杂的动机与意图。当今时代最风行最喧腾的诗潮,一是那种诉求解放与进步(先锋),追求平民化、本地化与反文化,语言质野粗放(包括粗口)而现实感强烈的宣泄愤怒的诗歌。一是那种相伴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而来的现代诗歌观念(均自西方来)影响下的诗歌,充满智性的反讽,复杂的隐喻,互文映射和语言游戏的诗。李少君选择写一种极为风雅闲适、山水农业、传统文人色彩很重的诗,显然有别于时代氛围,有点固执,有点危险,有点一意孤行。这种选择事实上也是一种富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表态,因此,在李少君单纯的诗风之下,他的诗和他的评论其实一样激进,一样单刀直入,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可称之为“保守的激进”。正如他自己说的:“创新有时要从‘复古’开始”①(《诗歌的草根时代》)。当然,在现代诗歌史上,复古是一条始终相伴的路线。比如被视为英美现代诗代表的T·S·艾略特宣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②。还有帕斯捷尔纳克晚年也一再强调自己的“古典主义”态度。但同样,简单的“复古”旗帜之下,仍掩盖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在李少君的“复古”诗风之下,依然有为什么复古?复什么“古”?如何“复”古?等等问题。我想结合李少君具体的诗歌文本,来分析他诗歌中的复古取向,肯定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能给我们启发的事。
二
当代诗歌中,可以说一直隐现着一条不太为人注目的“复古路线”。很多诗人在言谈中流露过对中国古诗传统(或文化传统)的追慕、向往与回归的消息。我仅举俩人:萧开愚和柏桦。萧开愚在2002年的《大江南北》发刊词中说:“新诗凝滞,概不通古”。对新诗的写作主张:“一,当代诗;二,通古”。原因是:“百年来,诗家始于学舌,专攻他人语言的局面日趋自然”。目的是:通古可以“维来历中之今日,维群中之我”,可以“重见文章精神”,可以“与其他语文交相惠悦”③。他的文字很古奥,意思很简单:新诗一开始就学外国诗(实际是欧美西方诗),一直学外国诗,未能继承本国古典诗传统,导致成就不高。接续古典(诗)传统才能为当今(的诗)定位,为世界(诗)中的中国(诗)(人群中的我)定位,才能恢复中国诗的精神,与外国诗进行双向互惠交流。柏桦在《水绘仙侣》和解说中,要接续古代中国诗的“逸乐”传统,一种理想的江南风物世界,一种才子佳人神仙眷属的文人生活:有钱,又有闲,又有才华风雅,又有漂亮、温婉、善解人意的女人,又在气候温和、有秀美的人工造就和控制的园林风景。他强调这是一种和“革命美学”,和刻画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斗争美学相对立的个人逸乐美学,是大时代之中更真实的个人情怀,个人小日子的美学。柏桦的传统,可谓文人才子“美梦文学”传统,一种个人的自我满足与享乐臆想。而在萧开愚的写作中(从《向杜甫致敬》到《破烂的田野》)体现的是一种儒家精神: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承担(清理外来思想),对国家政治伦理,群体与个人命运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出,同是对传统的回望与致敬,柏桦和萧开愚所针对的现实,所表达的内容却完全不一样。那么,李少君的传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呢?我们来看他的《玉蟾宫前》。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两节是一幅安宁恬静的田园风景,后一节是看到这风景的描述者(我、诗人、读者)的感受议论。前两节所写让我们既觉惊异、新鲜,又觉得熟悉。惊异来自这境地的真切、清新、安静,与描写这境地的白话语言的表现力:准确,精细,微妙,传神。“一道水槽横在半空”,进入得非常直接,自然,如口头语,下一句“清水自然分流到每一亩水田”也接续得极自然而有韵味。实际上,我们把第一行去掉一个字,第二行去掉四个字,就成了这样:“一道水槽横半空,清水分流水田中”。同样“牛在山坡吃草,鸡在田间啄食/蝴蝶在杜鹃花前流连翩跹”节奏的变化也很好:两个短句,接一个长句。古诗歌行体中,两个五言句,接一个七言句,比如:“山坡牛吃草,田间鸡啄食。杜鹃花前蝴蝶忙”之类。这些都在现代白话文中被融合与自然语气之中。这种惊异又熟悉的感觉最突出的当然是最后两行:“桃花刚刚开过,花瓣已落/枝头结出一个又一个小果”。熟悉是因为这精细入微的观察、语言的传神与诗意完全承接谢灵运的名句:“初篁苞绿籜,新蒲含紫茸”(《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所启动的中国古诗中对植物萌发、生长的细微体察与注目;惊异是桃花落后结小果这印象的鲜明、深刻,还有现代汉语表达此景的从容、自然。第二节写到山下零散的房子,敞开的门,门上的福字。这两节总共写到了水槽,流水,水田,牛,鸡,蝴蝶,杜鹃花,桃树小桃,房子。这是万物生长茂盛的暮春时节,田园风光的一切,就差人出场了。但在第三节,李少君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让诗中的描述者、观看者(我)出场宣告这田园风光中没有人!——“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因为他要强调的是:“却看到了道德,蕴涵在万物之中/让它们自洽自足,自成秩序”,他突出他看到了道德,秩序,在万物中“自洽自足”。这是他诗歌的目的和终点。我们可以看出他这首诗有两点:一、田园自然风光;二、自足的美好的道德、秩序。
类似的还有《咏三清山》、《黔地》、《贺兰山》等,这些诗在李少君的诗中具有代表性,它显示出李少君所要传承的古典传统既不同于柏桦富裕的才子佳人的逸乐,也不同于萧开愚克制的儒家精神(社会群体关系中的礼义仁智信),而是田园自然,山水自然,以及道家的清静无为、放任自由的道德与秩序。李少君把自然当作他诗歌的核心。他把自然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价值。在诗集《草根集》的序《在自然的庙堂里》中,他对此有充分的说明。当然李少君的诗歌所写的自然和他所指的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自然,与老子“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所指不一样。老子的自然,显然是一种无形而弥散的至高原则,在道之上的最高之处维系、主导天地的一切存在与运行。而中国古诗中的自然是处于道之下的天地之中的,为人接触、目睹、可知可感的具体、有形之物象,被称之山水自然或田园自然之类。但李少君的敏感无疑抓住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中国古典诗被称为“十诗景”,就是说,十首诗有九首是涉及自然风物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古代论诗套话。自然之景,在古代中国诗中既是审美对象(其唤醒诗人内心惊叹的形态与变化的新奇之美),更重要的是寄情抒怀的媒介,是抒情的方式。自然之景当然也是论道的场域,但就这点来说,在古诗传统中,并非主流,相反常被批评。东晋玄言诗一直受攻击,累及谢灵运的山水诗的论道结尾,还常受人诟病。实际上谢灵运山水诗更多是以孤独个人的呼吁、呼吁理解与友伴为结尾:“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园树园激流植援》),“不辞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欢,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非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石门新营所住》),“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登石门最高顶》),“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王维的山水诗被认为充满禅味,但并未脱离山水形态的准确描摹,只做实写看,佛意于诗意无关紧要。因此,即使是山水田园风景为中国古诗传统,而李少君的解读也实为他自己的发明,这也恰合了他的“创新有时要从‘复古’开始”。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人的活动,休息或劳作,愁苦或欣慰,居中心位置,是写“人在自然村社中的生活(包括交往)”。但李少君的诗,在这些田园自然或山水自然中,宣称“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他的风景中没有人(如这首《玉簪宫前》,《某苏南小镇》,《春》等)或人很小(如《鄱阳湖边》)。他把这人所占的空间腾出来,留给他的“道”。因为对有意识的“复古”主义者,这古典诗境首先是一种价值,一种道。对李少君来说,这种道正是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反面:当今社会形态与价值(城市、工业、)的混乱,压抑,焦躁,污染,异化,空虚,无根。而那个充实、清新、有序、在山水自然中充满生机的农耕村落生活,正是对当今现实的批判。因此,李少君的传统所针对的是现实社会状态。就这一点来说,既不同于柏桦针对的革命美学,也不同于萧开愚针对的新诗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处境。因此,复古也可以是一种激进的现实批判。
三
在李少君直接追慕古代诗歌精神的诗中,《南山吟》极为突出。这大概是现代汉语写的禅诗中最为奇妙的篇章之一了。“菩提树”,“打坐”,“大境界”,“轮回”,这些词,无疑带着佛教味。第二节白云的变化与循环和时间中的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强烈而恍惚,非常美妙。这种诗,既是作者的经验和领悟,同时很明显又是自觉地归属于一种精神传统,是一首“向传统致敬”的诗。同样,在李少君的诗中,他所强调的自然直接就体现在他诗歌的题材中。他的《玉簪宫前》,《咏三清山》,《南山吟》诗题就有道家味道。还有众多关于时间与地点的诗题(时间与地点正是自然的两大属性),如确定季节与时辰的诗题:《春寒》,《仲夏》,《北国之秋》,《傍晚》;如指定地点的诗题:《南渡江》,《佛山》,《石梅小镇》,《鄱阳湖边》,《青海的草原上》,等等。这些有关时间与地点的诗题,都是即景式的题目(与此相对,有纪事、抒怀等类的题目),也就是与自然面对,在自然之中。这都表明我们前面所提到李少君诗歌在承继传统时的两点价值判断:一是自然,二是自然(自然中的生活)所体现的道德、秩序、善与美等等伦理理想。这可谓他诗歌的出发点,价值与伦理基础。
当然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止于伦理价值的阐明,更重要的力量与影响来自其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当然也更隐蔽而不容易辨识,它完全潜含在诗歌的每一肌理之中。这种美学风格的确定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在众多的传统可能性中,独取此格。当然同时也与个人精神气质、性情有交互关联。李少君诗歌的风格偏于幽深,寂静,如《夜深时》这样的诗:
肥大的叶子落在地上,触目惊心
洁白的玉兰花落在地上,耀眼眩目
这些夜晚遗失的物件
每个人走过,都熟视无睹
这是谁遗失的珍藏?
这些自然的珍稀之物,就这样遗失在路上
竟然无人认领,清风明月不来认领
大地天空也不来认领
这是一种“触目惊心”,几乎让人脱口惊叫,又只能被寂静深深笼罩的诗境。这是心灵上的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应:心被深深的刺中,被如惊雷般的寂静刺中。这么珍贵、华美、灿烂,又这无声无息,这么彻底地不受人注意地独在一隅发生,消逝。这是无人进入之境的清幽和寂寞。这种寂静,孤独,幽深,有些清冷的诗风,不仅体现在他此类有关植物花木的自生自灭的诗之中,甚至也体现在他有发现的欣喜的诗中,如《山中》,这首诗非常清新,但仍是幽秘之境。这是木瓜,芭蕉,槟榔密集,没有行人与车辆的旧公路(废弃了一般),虽然出现了人家(我们前面说过他的诗中经常无人,或人很小),但“门扉紧闭”(人还是没有出现),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即使如同“一枝红杏出墙来”一般,“一枝三角梅探出头来”,热带鲜艳的深红色三角梅应该比南宋的红杏更热烈,但依然让人感到清幽。或者这清幽就来自这无人之境中植物(花)的灿烂与热烈。他的很多诗,都是抒情主人公一个人独自在一种充满意味却始终未有其他人出现的世界中,独自感受。也许是这个特别的“我”总是独自面对世界,独自一人行走、感受,给他的诗这种清幽,寂静之感?比如《偶过古村落》是单独这样一个人,《江南小城》是,《偈语》是,还有很多诗都是。这种幽静不止体现在这自然的描写中,也体现在写“心事”之诗中,心事的寂寞,如《可能性》:
在香榭里大街的长椅上我曾经想过
我一直等下去
会不会等来我的爱人
如今,在故乡的一棵树下我还在想
也许在树下等来爱人的
可能性要大一些
一个孤独的、等待着的人,一个在不同的地方总是在里对自己说话、对自己期望、说着自己的决心的人,当然是孤寂的,清幽的。这个爱人,在心里,是那么的不确定,飘忽不明。这心事当然是难以述说的。即使那些有明确的想念的对象,不确定的“爱人”成为了确定的“你”,如《在江南的青山上》,这种心事还是在自身之中,在自己的心里回旋,并未真正到达远方的“你”那里,还是在想象中对你说,还是止于自己说给自己。
李少君还写有一些极为幽静的居家诗,如《三角梅小院》、《隐居》等,这当然是一种文人趣味很重的诗,写的都是幽居与闲情,按白居易的分法,这些属于“闲适诗”(那两首写年轻女孩的诗该属“感伤诗”)。这种文人诗的自得其乐,与其追求生活的自适与精神文字的传达之快乐,在下面这首《早归人》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个诗人直接出现了,出现了他对诗句获得的喜悦:
我在细雨蒙蒙的清晨归来
担心打搅尚在梦中的年迈父母
静静地站在院子里,等候鸟啼天明
想起这么一句诗,兀自微笑
总的来说,李少君的诗,似乎蒙上了一层被薄云过滤后的光,总是有点幽暗,寂静。不是那种特别明亮,开阔,热闹的诗。诗中的情绪总带着寂静,有时是落寞。表面极美之境,也有一种空寂之感,幽深如古寺一般。我觉得他的诗在美学风格上混同了古代风流才子诗歌的纤细柔情,佛道诗歌的幽暗空寂,文人诗歌的闲适自在。他有一首诗《安静》,最后一句是:“全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了”,这好像是他自己诗歌的写照。他一直致力于写出一个“全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的诗歌之境,是不是因为有感于当今世界太嘈杂,当今人们内心太凌乱的一种诉求?他接续的是山水田园诗的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平民化(陶渊明)和贵族化(谢灵运,王维)传统,并演化出一种文人趣味的余流。他为自己的诗确认了“道德与秩序,善与美”的伦理基础,在美学风格上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江南文人才子味很重,有些甜软、温润,也有些绮丽、清新。
对新诗发展的展望、批评与反思中,一直有人提出要接续传统,但这些说法只是说法,因为缺乏成功的例子而没有信服力,让人觉得只是一种空洞的态度,就是郑敏这样的人如此说,也没有人真正当回事,因为不能在实际的写作中体现出传统的话。很多当代诗人表明了他们对古代诗人的追慕,但他们似乎只知道李白、杜甫这些名头大的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并未表现出对古代诗歌历史细部的、与个人性情相投的深入专注的理解与精神归附。但是变化确实在发生,我前面提到的萧开愚,柏桦,李少君,确实在身体力行。其他还有很多诗人也在这么做。这些实际写作,可能有很多不理想,失败之处,但这加深了我们与古代传统的亲近。我想一大批诗人今天都在默默致力于这一方向,这种努力并不那么轰动,引人注目。这也与我们国家今天在世界上的处境相关: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在调整中适应这种新的关系。真是难以想象:仅仅二十年前我们的诗歌唯西方是瞻,仅仅十年前我们的诗歌充满反文化腔调,那时难以想象会有人如此标举“复古”旗号。也许今后的十年,当代诗人将极力深入古典诗歌之中,使之现代化,而使新诗历史与古典诗歌历史接合起来。就这点来说,我认为李少君的写作是极为敏感的,探讨他诗歌中的传统影响也非常有意义。
注释:
①李少君,《草根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所引李少君诗均出自该书。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2
摘 要:本文从余光中的风物诗中挖掘出其特点,对诗的表现手法和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使人更深刻地理解余光中风物诗的意境。
关键词:余光中;风物体;散论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4006605
一
所谓风物,一是指风光景物,二是指风俗物产。前者如晋代陶潜《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宋代张升《离亭燕》词:“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后者如宋代梅尧臣《送俞尚寺丞知蕲春县》诗:“应见言风物,于今有贡虵。”中国历代诗歌作品中,风物诗或咏物诗占有相当的比例,含义往往也相当广泛,有人甚至将咏人之作也列入其中,但通常还是以一般意义的物为吟咏对象。因此,除了吟咏动植物如花鸟虫鱼以及生活器物、服饰、建筑等类作品之外,一些写景诗、山水诗以及咏怀自然现象的诗歌都可以归入。
余光中先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一生写下了许多可以归为风物之咏的诗作。本书选录了其中九十五首,第一首是1953年写的《鹅銮鼻》,最后一首是2004年写的《永春芦柑》,跨度达半个世纪。这些诗以1980年代最多,约六十首,1970和1990年代各有十余首,其他年代则比较少。全书依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车过枋寮”咏山水风景,第二辑“红叶”咏花果草木,第三辑“雨声说些什么”咏时令天象,第四辑“漂水花”咏生活器物,有些组诗兼有不同类别则依其主要内容归类。
余光中对地理兴趣浓厚,自幼养成看地图画地图的习惯,他曾谈到:“在现代诗人之中,我自觉是甚具地理感的一位。在我的美学经验里,强烈而明晰的地理关系十分重要,这特色不但见于我的诗,也见于我的散文。”[1]。他在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中说其中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2],他和夫人游踪遍布世界,其歌咏风光景物之作数量多,内容广。其中,当然尤以歌咏大陆数量为多,在本诗丛怀乡卷及怀古卷中已有收录,举其要者,如咏北京的《访故宫》、《登长城》,咏东部的《藕神祠》、《重登中山陵》《厦门的女儿》,咏中部的《桂子山问月》、《汨罗江神》,咏西部的《漓江》、《望峨眉金顶》、《嘉陵江水》、《成都行》,还有咏大江大河的《大江东去》、《黄河》;另外,咏香港的则有《九广铁路》、《看山十年》、《老火车站钟楼下》、《火车怀古》,等等。至于本书未收录的外国题材的同类作品也有不少。和其他各卷平衡选目的结果,本书台湾比重更突出一些,第一辑除最后一首《地平线》外,全收咏台湾风光之作。余光中的笔下既有闻名遐迩的台北、高雄等城市和玉山、兰屿、鹅銮鼻等名胜,也有枋寮、惠荪林场等带有乡土气息的景观,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正是通过他的诗,才得以知道其中一些地名和它们的故事。第二辑所咏水果及花木也多以台湾为主。其中水果诗全是诗人移居高雄初期的作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从定居高雄以来,我就一心归命做定了南部人”,[3]“岛之南部,素有水果王国之美誉,一位诗人在齿舌留香之余分笔歌颂一番,该也是应尽的本分。”“也算是一点‘本土化’吧”[4]。如今,随着两岸交流的热络,作者写到的槟榔、莲雾、石榴、芒果、荔枝、柚、桃等台湾水果,不仅早已在大陆登堂入市,而且大陆游客入岛也可随处尝鲜,诗人对其美形美味的描写及其中寄托之意蕴,不免激起大陆读者的共鸣,这或许是诗人写作之初所没有料到的。第三、四两辑的作品因题材所致,没有明显的地方背景,但也不时流露出对特定地方的情愫。如《邮票》中,作者自香港思念台湾,称后者为“一座长翠的灵山福岛”,从而“细细地咬着乡愁”;《一把旧钥匙》中,作者自台湾牵挂香港,表达了对居住十年之久的香港的特殊眷恋和对其未来命运的惆怅;而《六把雨伞》中对江南、四川等地的儿时记忆也是那么清晰和亲切。
在所谓“乡愁诗人”余光中的心中,乡愁所系当然首先是祖国大陆的山山水水,但对于自己长期生活的台湾以至客居多年的香港,他都饱有一份浓浓的乡愁情思。以对台湾而言,他对宝岛山川景物、草木花果的一叹一咏,无不寄寓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把这种对乡土的情怀,与对国家的深切热爱结合在一起。《垦丁十九首》的《灰面鹫》中,即使是匆匆来去的候鸟,他也希望它们能“带着温暖的记忆回去∕‘我到过一个,哦,可爱的岛屿’”。《埔里甘蔗》把甘蔗比作“仙笛”,把吃甘蔗比作吹奏“一支可口的牧歌”:“每一节都是妙句∕用春雨的祝福酿成∕和南投芬芳的乡土”。在《初嚼槟榔》中借画家君鹤的话“不咬槟榔,怎么会晓得∕南部的泥土有什么秘密”。诗人在诗集《安石榴》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些作品在题材上虽然多般,但是在主题上仍然辐辏于三大焦点:中国结、台湾心、香港情。”[5]这也正反映了诗人风物诗的主题焦点。
二
诗人1985年到高雄定居,十五年后,他在编辑诗集《高楼对海》时写道:“无论如何,这寂对海天的场景,提供了我诗境的背景,让我在融情入景的时候有现成的壮阔与神奇可供驱遣,得以事半功倍。”诗人在高雄时期写了不少以海天一色为背景的风物诗,他的其他风物诗也表现出与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世界的种种关系,构建出形形的诗的境界。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3
>> 有机杂合,和谐共生 有机共生的设计 有机栽培稻鸭共生 基地带动三农和谐共生的有机农牧业园区建设 追寻“简单”与“有效”的和谐共生 强化有效渗透 促进和谐共生 有机食品,倡导绿色和谐 师生有效互动,构建和谐共生美术课堂 和谐共生的城市 城市.自然.和谐.共生 和谐与共生 语境再现和谐共生 绿色中国 和谐共生 与鸟儿和谐共生 唤醒自主,共生和谐 和谐共生,演绎精彩 与自然和谐共生 蔚蓝传承 和谐共生 读写结合,和谐共生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因此,只有消除全球化中的西方话语一元主宰局面,建立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才能维系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则肩负着在全球意识背景下维护并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重任,必须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能动性阐释和传递。从事翻译研究也应超越语言的界限, 从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思考翻译的精神和使命。目前中国文化尚处于世界文化多元体系的边缘,理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整体文化建构,既要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胸襟积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营养,又要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及精神财富贡献给世界文化生态。中国古典诗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品格和智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把中国古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传达出去,使之成为世界共同财富?这是古诗翻译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提出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即通过杂合显异的译介途径,使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译语文化和谐共生,从而使世界文化生态圈保持繁荣昌盛。
二生态翻译学对古诗英译的启示
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近年来,“生态”一词被不断用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
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就是多样化和异质化的生物体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中的和谐并存关系,即有机体之间的紧密联合,这种联合往往对每个有机体都是有益的。生物学意义上多样性是指生命形态的丰富程度。当其中某个物种过于强大时,就会吞噬其他物种,致使其他物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从而破坏生物多样性。同样,就世界文化生态而言,作为有机体的各民族文化在整体文化生态场内应该以平等互融、共生共荣的方式和谐并存。如果某种或某些民族意识过强,就可能形成恶性膨胀的文化霸权意识,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改造或者归化,从而损害文化多样性,导致整个世界整体文化生态环境失衡。因此,对任何文化的狂热追求都将成为破坏文化生态、造成世界文化生态灾难的根源。
民族文化既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又必须依赖整体生态资源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与互释的基础上凸现自身价值。正如任何低级生物体的出现或消亡都可能会带来整个生物链的重组或断裂,任何貌似弱小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因此,必须以健全的心态对待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解构霸权文化的权威性和普适性,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从而建构丰富多彩的和谐文化生态环境。翻译就是要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互认、互补,使人类文化处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带来的生态问题不仅涉及自然生态,而且涉及语言的生态。要想保持生态平衡,就有必要引入生态翻译这一概念。”[1]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2](P167)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就是要促进语言和文化地位的平等,保持文化交流的平衡。肇始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种生态学途径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3]其基础理论中提出的“译有所为”,以及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之下的“三维”转换翻译方法,[4]对中国古诗英语译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主观动因,作为由原作文本到译作文本的重构者的译者,他们所持据的文化理念及译介宗旨直接影响译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国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译者在英译中如果一味地就范于英语的表达方式, 就会产生文化归化,使原有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发生扭曲,淡化原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文思想色彩。如加布里埃尔・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所言,“如果没有对另一文化的全面了解,要进行阅读就必需对异域文化他者进行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使之进入自己的言说方式。”[5](P11)因此,从文化维来说,译者必须在承认和肯定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利哈乔夫的《文化权利宣言》指出“国家负有保存文化价值和文化本身的责任”[6](P478)。承认并尊重差异是保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良往的必要条件。生态翻译学就是强调用整体、和谐、平衡和相互联系的观点来认识翻译问题。就古诗英译而言,就是要强调对差异性和多元文化的尊重,关注中英两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和谐与共生,以维护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下文拟从求异与杂合两方面对生态翻译观进行阐释。
三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结构、文化源流以及思维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学翻译,如何在跨越文化异质性的同时,充分展示文化相异性,并且表现出兼容并收的文化创造性,这是文学翻译是否能扩展成为文化翻译的关键。”[7](P115)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有责任展现而非遮掩不同的客观存在。从生态翻译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要通过传达文化差异性,促进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识。中国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就是强调译文在可理解性基础上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语言文化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体验差异性的同时体味原诗的艺术魅力,丰富译语文化。
“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民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http:///static/files/pact_to_protect_diversity.pdf。语言是表现思想内容和传递文化内涵的载体,句式结构是文化内涵的直接体现。中西诗歌无论在语言文字表达、诗行布局形式,还是诗意的凸现方式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求异就是力求保持原汁原味,将原作信息移至译文中,包括不同的表述语言、表现形式和表达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汉文化情感表达方式的独特性, 激发读者的新奇想象, 使其自觉感受原诗的意境,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实现文化精神的传输。
语言上的差异,如句法结构与修辞方面的差异,彰显了文化的特异性,而文化多元性的创造是以文化的特殊性为基础。因此,“翻译必须依赖与译入语文化不同的规范和资源”,[8](P28)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影响目的语文化。例如,“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性、词性模糊和多元功能”,便于读者解读时在物象和物象之间“自由浮动的空间”中进行“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9]中国古诗这种语法关系的弱化特性,若移植到英语诗歌里,对英语诗歌偏重语法逻辑的传统就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策略以及对于美国现代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译著《神州集》中,庞德大胆摆脱英语固有的表达习惯和语法结构,有意识模仿中国古典诗歌文法模式和修辞艺术,有时甚至直接照搬源语形式,从中国诗歌中引进本土文化缺少和需要的东西。例如,他将李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直译为:“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这种“直搬中国句法”[10](P256)的译诗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一时的理解困惑,然而,他引进的陌生化的句法形式给英诗创作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
语句形式和意象组合方式所透出的气息,是构成作品意义的有机成分,体现不同文化类型和精神取向对客观事物不同的观感态度。汉诗的意象是“在一种互立并存的空间关系之下,形成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但不将之说明的境界”[11],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物方式。如果原诗这种异质特征在翻译中得以保存,西方读者就能更好领略到中华文化特有的诗情画意。通过研究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笔记,庞德深谙中国古诗通过意象并置直接体现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奇妙手法,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在《神州集》中,大量使用意象并置的手法,如把“荒城空大漠”(李白《古风》其十四)译成“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将“惊沙乱海日”(李白《古风》其六)的诗句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很明显,庞德正是刻意打破西方严格的语法规范, 拒绝使用任何连词来表明诗句中各个意象之间的关系,采用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手法,让诗中每一个词都创造出鲜明的意象,凸显出真实事物的瞬间表现。虽然由于理解上的偏误,对于他的译文尚存争议,然而,他通过意象并置所构造的画面和意境却很是传神。尤其可贵的是,由于庞德的大力提倡,意象并置的技巧逐渐被西方诗人在创作中加以承袭。《神州集》也因此成为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大大地推动了意象派诗歌在西方的发展。庞德实际上是通过翻译,有目的、有选择性地吸取中国古诗中的精髓,为美国诗坛注入清新异样的元素,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语言体现了文化传递性,在古诗英译中尽可能采用保持原文差异性的做法,有助于打破汉英两种文化之间交流不平等的态势,摆脱英语文化审美观、价值观对汉英翻译的制约,使中华民族文化精华更好更真实地呈现于人类文化之林。
四古诗英译的杂合策略
“杂合”(hybrid)这一概念最初用于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12](P523)后来也逐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学科使用。在文学理论界,巴赫金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杂合化(hybridization)问题时,把“杂合化”界定为“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13](P358)而在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看来,“杂合化”(hybridization)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14](P118) 翻译活动同时受两种文化的制约,面对两种迥异的语言规范、文化背景和叙述模式时,无论译者如何努力,其译文往往出现两种语言文化的“杂合”现象。沙夫娜(Christina Schffner)和阿黛柏(Beverly Adab)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体”。[15](P325)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翻译是个“杂合的语言与文化认同过程(hybrid identification)”或 “不同文化的混合过程(mixing)”,而不是 “离散文化的整体交换(an interchange between discrete wholes)。”[16](P69)韩子满把杂合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在充分借鉴翻译界及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从多方面证明译文杂合的普遍性。[17](P204)
近年来, “大多数后殖民写作对后殖民文化的杂合性表示关注,并把这种杂合性看作是一种优点而不是弱点”[18](P183)。文努蒂认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19](P178)。换言之,翻译是一种文化间性(in-betweenness)的行为,这种间性不是简单的将两种文化或语言相加,而是在杂合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形式[20]。孙会军等认为,“处于‘杂合’状态的语言文化汇合了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经过吸收与融合过程后,常会获得一些本不曾具有的优点,实现对原来文化的优化与超越”[21]。以庞德的翻译为例,《神州集》翻译之所以被西方文化接纳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使用意象并置的异质手法外,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杂合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庞德一方面尽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汉语句法结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采取适当的杂合策略,以便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蕴和意境,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精髓。我们不妨以李白《送友人》的译文为例看看其杂合策略的运用。
原文: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庞德译文: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
在译文第一、二行中,庞德既发挥了英语介词和分词短语的优势,又摆脱英语句法结构的羁绊,将“青山(blue mountains)” “白水(white river)” 两个意象并置突出;第三、四行添加了主语“we”,强调动作主体,拉近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接下来两句又模仿汉语诗歌的句法特点, 省去冠词、动词及连接词,让活生生的意象并列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最后两句根据英语句法要求,借助代词“who”“our”“we”和连接词“as”,将人物时空关系交代清楚,避免英语读者产生理解困惑。可以说,整首译诗通过杂合处理,突破成规,标新立异,既直接传译出原诗的意象,又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正是因为庞德的良苦用心,《神州集》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才能为众多的英语读者所接受。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林语堂先生可谓是另一位值得称道的“文化使者”。在对外“输出”中国文化时,林语堂先生“两脚踏中西文化”,将中华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译语,从而提高了中华文化的生机与力量。他的译介策略,开创了中西杂合互补的成功范例。且看他对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翻译,原诗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林语堂译为:
The light of water sparkles on a sunny day,
And misty mountains lend excitement to the rain.
I like to compare the West Lake to “Miss West”,
Pretty in a gay dress, and pretty in simple again.
原诗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前两句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和雨天的山色,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后两句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拿西施来比西湖,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译诗具有明显的杂合痕迹,既保留了中国诗歌的结构,又采用了英语句式,节奏基本上是抑扬格五音步,尾韵为aaba,读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很好体现了原诗的形式美和音韵美,从意蕴上讲,译文尽量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尤其是对于中国“西子”这一文化意象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在直译“West”的基础上加上一个“Miss”,既传达出原诗意象,又填补了译文语境的文化空缺,让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古典美人增添了几分熟悉和亲近感,从而产生更进一步“认识”的好奇。于是,这位戴上了“Miss”帽子的“异质”的东方小姐便自然而然地从审美层面进入到西方人文思想建构中,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功能。如果简单地将“西子”直接音译为“Xi Zi”,译文读者将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涵义,即使用注释来弥补,也会减少阅读的,毕竟诗歌不是文化读本。这正如孙艺风所说,“如果翻译愿意做到表述充分,使他者性显现于目的文本中,那么自我和他者的混合将在重写文化政治交流的活动中,以更嬉戏式、更富创造性的形式相互对位。”[22]这种杂合的策略有助于中国文化借英语的“外壳”进入他乡,与译文读者直接接触,随着英美人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多, 他们的文化心态将变得更加宽容和开放, 更加正视并吸收中华文化的异质因素以便丰富自己的文化,而目的语读者视野的变化又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在异国文化交流中的深入。从生态翻译视角看,借助于杂合的力量,可以保持语言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促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状况。
五结语
多元性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角度来看, 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生与融合。翻译使中外文化的衔接与交流出现优势与活力。然而,中国文化在汉译英中的传播一直面临着顺应目的语文化的严峻挑战。我们提倡生态翻译取向就是要从传承与建设中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汉译英问题,通过张扬共生性和多样性来否定强势文化单一的文化取向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扭转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通过古典诗歌的对外译介,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播撒,使世界整体文化结构更趋多样化、立体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民族文化自身特质得以保持、发展和优化。
[参考文献]
[1]祖利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翻译 [J].中国外语,2007,(6):89-92.
[2]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