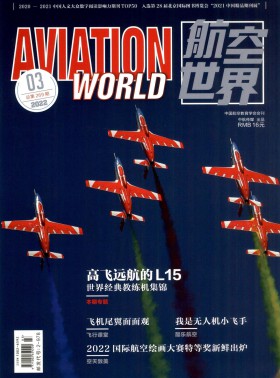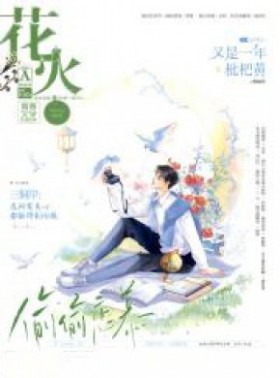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云想衣裳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云想衣裳范文1
2、原文
清平调·其一
唐:李白
原文 译文对照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3、译文:
云霞是她的衣裳,花儿是她的颜容,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
云想衣裳范文2
综艺节目《天天向上》20181221期有双云。在这期节目中王晰、郑云龙、阿云嘎、翟李朔天、高天鹤、蔡程昱、陆宇鹏七位《声入人心》成员加入“天天时光派对”,以音乐为载体,一起分享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生活方式与流行经典。
所谓的“双云”也就是指郑云龙、阿云嘎二人。郑云龙是中国内地音乐剧男演员、歌手,2014年加入松雷音乐剧团,成为一名签团演。阿云嘎出生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中国内地音乐剧男演员、影视演员、歌手,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
(来源:文章屋网 )
云想衣裳范文3
原文:
《夜泊严墓镇灯下闻歌》朝代:明 作者:郭谏臣
客路黄昏后,移舟近钓矶。
夜长频剪烛,露冷欲添衣。
云想衣裳范文4
在火线抢救和卫勤训练时,卫生员需将伤员搬到地形比较隐蔽、敌火力攻击不到的地方时,就可以用担架后送伤员。
将伤员搬上担架的方法:两名担架员跪下右腿,一人用手托住伤员的头部和肩部,另一手托住伤员的腰部;另一人用手托住伤员的骨盆部,另一手托住伤员的膝下。伤员清醒、上肢没有受伤时,可用手勾住靠头部一侧担架员的颈部,另一名担架员同时起立,将伤员轻放于担架上,将担架上的吊带扣好。向担架上搬动脊柱骨折的伤员时,应由3~4人一起搬动,一人专管头部的牵引固定,使其头部保持与躯干成直线的位置,维持颈部不动。其余3人蹲在伤员的同一侧,两人托住躯干,一人托住下肢,一齐起立,将伤员轻放在担架上。对腰胸部伤员要由3~4人搬运,都蹲在伤员的一侧,一人托住肩部,一人托住腰部和臀部,另一人托住伸直而并拢的两下肢,同时起立把伤员放在硬质担架上。如果一人进行搬运,也应做到从一侧,把胸部和骨盆部连成一块,把伤员轻放到担架上。
伤员在担架上的:重伤、中度伤、胸部伤伴呼吸困难的应取半卧位;对颅脑伤、颌面伤及全麻的伤员,应使其头部转向一侧,以防其舌根后缩引起窒息。颈椎骨折伤员应取仰卧位,并在颈下放一小枕。为防止头部左右摇摆,要有软垫或沙袋固定在两侧。伤员后送途中,每隔半小时必须翻动一次,截瘫及大面积烧伤的伤员,翻动时可用一副较软的担架覆盖在上面,并用带子系牢,然后将伤员朝一个方向翻过去。伤员翻动后,要对其突出部的皮肤进行按摩护理。行进时,应使伤员头在后、脚在前,以便观察伤员的面部表情、脸色及呼吸。
运输带有输液管、输液瓶的伤员时,必须有护士护送。护士的任务主要是保护输液管及引流管,并注意观察伤员面部表情及动作。火线上采用担架运输时,担架员应辨别枪炮声,适时进行隐蔽。在寒冷条件下用担架运送伤员时需注意保暖,可用热水袋和军用水壶装热水放置在被子内。夜间雨季搬运伤员时,应盖好雨布,防止雨淋湿伤员。炎热条件下搬运伤员,应避免伤员受到日晒,以防止中暑。运送途中还要不间断地观察伤员的伤情变化,对伤口出血较多者应进行加压包扎止血。对剧烈疼痛且无腹部伤的伤员可给予止痛剂,对清醒且无胃肠道损伤的伤员可给予温水饮用。较远距离运送时,应调整包扎及固定物,协助伤员大小便、进食、翻身等。对烦躁不安的伤员,可用绷带捆绑其手足,防止其拔除流管、揭去敷料,并防止其滚下担架。
将伤员抬下担架时搬运者的手臂应从伤员身下伸到对侧,先将伤员上抬,使伤员离开担架,然后再将其移到床上。
云想衣裳范文5
[关键词]相互依赖;权力运用;影响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24-04
一、导 言
权力运用是渠道内最重要的控制和沟通机制[1][2],在渠道关系的开发与管理中扮]关键角色[3][4]。鉴于它的重要性,学者已探讨了多个影响权力运用的前因,比如权力、依赖、渠道结构、决策结构等,但是少有研究考虑相互依赖这一重要因素。相互依赖与权力运用之间关系尚不清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研究目的就是探讨相互依赖对制造商权力运用的影响,即考察总体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非对称对权力运用的不同维度作用的差异。在本文的后续部分中,首先进行文献回顾,讨论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然后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接下来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假设并进行分析与解释。
二、文献回顾
(一)依赖与相互依赖
渠道成员依赖指一个渠道成员A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产生的保持与另一个渠道成员B合作关系的需要。目标指的是A期望从B处得到的效用,包括价值、利益或满足感等内容。A对B依赖程度取决于B提供效用的多寡与效用替代提供者的稀缺性。如果A从B处得到的效用越多并且A从B那里得到的这些效用的替代来源也越少,那么A依赖于B的程度可能越高。
依赖不是单方面的,渠道成员彼此相互依赖。渠道成员变得相互依赖,是从事经济交换以取得超出其控制但对于其目标的实现来说必不可少的资源的结果。相互依赖既有程度上的区别,也有结构上的差异。依赖程度标志着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依赖水平或互依水平的高低,而互依结构则表示互依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相互依赖结构必须包括总体相互依赖和相互依赖非对称两个维度[5][6]。
总体相互依赖指一个交换关系中双方依赖的总和,它代表关系的凝聚力。相互依赖非对称被定义为一个交换关系中双方依赖之间的差额。Kumar(2005)指出这两个维度可以独立变化,即当关系双方间相互依赖非对称保持不变时,总体相互依赖可发生增加或减少变化,而在总体相互依赖保持不变时,相互依赖非对称亦可发生同样的变化[7]。
(二)权力运用
渠道权力是一个渠道成员A影响另一个渠道成员B决策变量的能力。换言之, 权力体现A影响B的信念、态度与行为的潜能。这种潜能被与其他渠道成员对自己的依赖相联系,也就是说,当其他渠道成员依赖自己时,自己就或多或少地对于其他渠道成员拥有权力。渠道成员通过不断地对特定的资源进行投资,就可以创造并不断扩大自身的渠道权力,从而加强对其他成员的控制能力。
一个渠道成员拥有权力,只能说明它有产生影响力的潜在能力,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对另一方的控制。Leonidou(2005)指出,单纯的权力占有只能对权力客体行为产生有限影响,权力客体行为或决策的实际改变是权力主体有效使用权力的结果[8]。当一个渠道成员想真正改变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时,就必须运用各种战略去影响它――即在运用权力时要采取一定的交流方式,比如威胁、许诺、法律、请求、建议、信息交换等[9]。
Frazier和Summers(1984)首先将这些交流方式术语化为“影响战略”(influence strategies)[10]。通常把试图实施影响的渠道成员称为源企业,而将接受影响的渠道成员称为目标企业。依据这些战略的使用是否直接改变对方的行为,Frazier 和Summers(1986)将其分为强制性影响战略与非强制性影响战略两类[11]。其中,前者包括威胁、许诺、法律等三种战略形式,而后者包括信息交换、建议和请求等三种战略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考虑威胁、许诺、信息交换和建议战略,因为与国内渠道成员的访谈发现法律与请求战略在实践中被使用的频率较低。
三、研究模型与假设
(一)总体相互依赖与制造商权力运用
当制造商-经销商间呈现低水平总体相互依赖时,一方所占有的资源对于另一方而言或是没有吸引力,或是能轻易地从替代者处获得,关系解散与重建的成本均很低。既然如此,制造商或经销商都有较强动机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双方势必都怀疑对对方的帮助不能获得回报,将倾向于以输赢方式对待权力,即当对方赢,自己则输。在这种背景下,为实现各自预期目标,它们都会较多地使用威胁、许诺等强制性影响战略。相反,非强制性影响战略使用频率将会降低,因为它们需要耗费实施者大量的时间、精力等资源,并且若无长期盈利前景或其他补偿,获得收益将不能弥补相关成本。
相反,高水平总体相互依赖则意味着制造商-经销商间处于彼此高度依赖的状态。这将使制造商或经销商相信它们的目标高度相关,当一方走向实现目标时,另一方也趋向达成目标;同时也使各方都共享渐增的担忧――损害关系。在这种情景下,使用非强制性影响战略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非强制性影响战略可以强化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认同,使用方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以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相反,强制性影响战略的使用会在渠道中形成冷漠紧张的氛围[12],造成成员之间频繁冲突的发生[13]。这一观点被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所支持:Lusch和Brown(1996)研究显示,高总体相互依赖导致渠道成员较多地使用非强制性影响战略[14];Kumar等(1998)指出,当总体相互依赖增加时,出于防止损失的动机,一方不愿意对另一方实施惩罚行为[5]。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总体相互依赖的增加,制造商将倾向于使用更多的非强制性影响战略,而较少地使用强制性影响战略。
H1:制造商-经销商间总体相互依赖越高,制造商越倾向多使用信息交换战略。
H2:制造商-经销商间总体相互依赖越高,制造商越倾向多使用建议战略。
H3:制造商-经销商间总体相互依赖越高,制造商越倾向少使用威胁战略。
H4:制造商-经销商间总体相互依赖越高,制造商越倾向少使用许诺战略。
(二)相互依赖非对称与制造商权力运用
传统渠道结构中,制造商对渠道的支配能力远远大于经销商,制造商处于权力优势地位,因为制造商拥有经销商实现目标所必需的资源。制造商的权力优势越明显,制造商-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越大,经销商保持关系的意愿越强,因为它的目标实现愈发依赖制造商提供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制造商相信经销商不会为了实现自身需要而轻易使用强制性影响战略,因为这样做肯定会招致制造商的报复,同时经销商也不具备实施强制性影响战略的资源和能力。制造商势必会大幅降低被经销商攻击或者抵制其要求的预期。这样,制造商就没有必要实施具有消极影响的强制性影响战略;相反,制造商可能会多使用非强制性影响战略,通过增强经销商对自己期望行为的认同感来改变经销商的行为。Frazier和Rody(1991)对工业品渠道的研究发现,供应商权力与强制性影响战略使用负相关,而与非强制性影响战略使用正相关[13]。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命题:
H5:制造商-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越大,制造商越倾向多使用信息交换战略。
H6:制造商-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越大,制造商越倾向多使用建议战略。
H7:制造商-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越大,制造商越倾向少使用威胁战略。
H8:制造商-经销商间相互依赖非对称越大,制造商越倾向少使用许诺战略。
根据上述的8项假设,我们得到以下研究模型:见下图:
四、研究方法与检验结果
1.样本
本研究选择一家木地板业制造商的分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考虑了三方面的原因:(1)调查单个渠道系统,也就是关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分销渠道是大多数渠道研究的传统[15];(2)该公司管理者对本文所研究问题有较大兴趣,因而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3)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产业是权力运用研究的良好环境,一方面渠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与合作程度适中,这不同与以往的渠道研究背景;另一方面制造商与其经销商互动频繁,并且较多地使用权力来影响经销商的行为或经销决策。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占返回问卷的92.3%;无效问卷10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7.7%,抽样时间历时4个月。
2.量表开发
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7点计分的方法来度量,数值从 1 到7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在设计各变量的具体度量指标时,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使用过的量表,并且所有构念都使用多项目测量,然后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修改作为收集实证资料的工具。以下针对研究当中的每个变量,说明选择的度量指标及其依据。
(1)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的操作化需要测量渠道成员依赖。依赖是一个多维度构念,但本文只关注替代性这一维度。一个渠道成员向另一个渠道成员所提供重要资源的替代来源越少,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越大。经销商依赖及其感知的供应商依赖各自使用3个项目加以测量,这些项目改编自Lusch和Brown(1996)的量表[14]。总体相互依赖等于经销商对制造商的依赖和制造商对经销商依赖之和,相互依赖非对称等于经销商对制造商依赖与制造商对经销商依赖之差的绝对值。
(2)权力运用
权力运用量表测量经销商感知最近一年内制造商使用各种影响战略的使用频率。强制性影响战略的使用包括了如下两个方面:当经销商依从制造商的要求时,给予其一定的奖励;当经销商不依从制造商的要求时,则给予一定的惩罚。根据Boyle等(1992)、Boyle与Dwyer(1995)和Bandyopadhyay(2004)的研究[12][16][17],从许诺战略、威胁战略两个方面设计了6个测量项目。非强制性影响战略的使用包括了如下两个方面:制造商向经销商传递相关信息,提供有助于改善经销商经营状况的建议。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从建议战略、信息交换战略两个方面设计了7个测量项目。
3.量表信度分析
信度主要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本研究采用学术上最常用的Cronbach’sa系数来评估样本数据的内部一致性。一般认为其值应在0.70以上,最低门槛值不能低于0.60。本文采用SPSS13.0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根据以上统计原则,六个多维变量的可靠值(Alpha)均大于0.70,说明测量题项的可靠性较高。题项与量表的相关系数(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TC)反映了维度的内部结构。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题项与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均接近或超过0.70,高于公认的门槛值0.50。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为了探索相互依赖对于制造商权力运用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总体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非对称作为自变量、四种影响战略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强行进入式回归分析,报告共线性诊断结果,见表2。
表2显示,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高值为1.629,远远小于10;而容许度(Tolerance)最低值为0.601,大大高于0.1的常规界限,这充分表明多重共线性不是太大的问题。
从表2 可以看到,相互依赖的两个维度对制造商权力运用的影响。总体相互依赖对非强制性影响战略的影响存在差异:它对建议战略有积极影响,假设H2得到验证,但对信息交换战略的影响不显著,假设1被拒绝。还发现,总体相互依赖与强制性影响战略间负相关关系没有得到验证,假设H3与H4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相反得到两者之间正相关的结论。
相互依赖非对称对强制性影响战略的影响也存在不同:它对许诺战略有负面影响,假设H8得到验证;但对威胁战略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7没有得到足够支持,这与Kumar等人(1998)的研究相一致[5]。我们还发现,相互依赖非对称与非强制性影响战略间正相关关系没有得到验证,即假设H5与H6被拒绝,相反得到两者之间负相关的结论。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制造商-经销商间相互依赖维度对制造商权力运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相互依赖对于制造商建议战略的使用有积极影响,相互依赖非对称对于许诺战略的使用有负面影响。同时,还发现两对与假设恰好相反的结论:(1)总体相互依赖对强制性影响战略的使用有积极影响。这可能与国内木地板业市场竞争环境相关。相比于其他行业,木地板经销商有较多可供选择的替代者,这降低了经销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成本。制造商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即使在双方间存在高程度总体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也会使用或保留使用强制性影响战略以协调相互之间的行为。(2)相互依赖非对称对于非强制性影响战略有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制造商预期经销商会自发地依照己方要求行事,因此主观上认为没有必要再使用这些非常耗费时间、精力与资源的影响战略形式。
尽管本文的结论明确了国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间相互依赖状况对渠道成员权力运用的影响,为企业在既定的依赖结构中如何运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与改进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在样本的选择方面,仅选择了木地板业中的制造商-经销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在样本上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所得到的结论不能推广到更加一般的层次上,未来的研究当中应该在其他行业展开实证研究,使数据更具代表性,以便更加深入分析相互依赖对权力运用的影响的问题;其次,在指标设计方面,尽管本文参考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所采用的度量,然而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在西方环境下得出的,今后尝试建立本土化的量表非常必要;最后,权力运用是一个多因素驱动作用的结果,今后研究还可以探讨其他前提因素对渠道成员权力运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Kim, Keysuk. On Interfirm Power, Channel Climate, and Solidarity in Industrial Distributor-Supplier Dyad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0, 28(3):388-405.
[2]Weitz, Barton A. and Jap Sandy D.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5, 23(4): 305-320.
[3]Gundlach Gregory T. and Cadotte Ernest R. Exchange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firm Interaction: Research in a Simulated Channel Setting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4, 31(November): 516-532.
[4]Brown James R., Lusch Robert F. and Nicholson Carplyn Y. Power and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Their Impact on Marketing Channel Membe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5, 71(4): 362-92.
[5]Kumar Nirmalya, Scheer Lisa K., and Steenkamp Jan-Benedict E.M.Interdependence, Puitive Capability, and the Reciprocation of Puitive Actions in Channe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8, 35(May): 225-235.
[6]Kim Stephen Keysuk.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or Attitud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oup Orient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03, 20(2): 193-214.
[7]Kumar Nirmalya. The Power of Power in Supplier-Retailer Relationship[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5, 34(8): 863-866.
[8]Leonidou, Leonidas C. Industrial Buyer’s Influence Strategies: Buying Situtation Differences[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2005, 20(1): 33-42.
[9]Stern, L. W. and El-Ansary, A. I. Marketing Channels[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2.
[10]Frazier Gary L. and Summers John O. Interfirm Influence Strate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within Distribution Channel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4, 48(Summer): 43-55.
[11]Frazier Gary L. and Summers John O. Perception of Interfirm Power and Its Use Within a Franchise Channel of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6, 23(May): 169-76.
[12]Boyle Brett A., Dwyer F. Robert, Robicheaux Robert A. and Simpson James T.Influence Strategies in Marketing Channels: Measure and Use in Different Relationship Structure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2, 29(November): 462-473.
[13]Frazier Gary L. and Rody Raymond C. The Use of Influence Strategies in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ial Product Channel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1, 55(January): 52-69.
[14]Lusch Robert F. and Brown James R. Interdependency, Contracting, and Relational Behavior in Marketing Channel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October): 19-38.
[15]Lee Don Y. Power, Conflict, and Satisfaction in IJV Supplier- Chinese Distributor Channel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1, 52(2): 149-160.
[16]Boyle Brett A. and Dwyer F. Robert. Power, Bureaucracy,Influence and Performance: Their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Channel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5,32: 189-200.
[17]Bandyopadhyay Soumava. Interfirm Strategies within Distribution Channels in the Emerging Indian Market[J]. ACR, 2004, 12(1):1-9.
Interdependence and Manufacturer’s Use of Power
Hu Baoling
(Business School of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520,China)
云想衣裳范文6
关键词:海上货物运输;船货利益博弈;利益平衡;权利义务
在法律范畴内,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互为消长,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决定其所处的地位。因此,在制订海上货物运输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积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款。
一、船舶利益平衡协调原则相关概念
"船货利益"是指双方在从事海上货物运输商业活动因从权利义务的变动所带来的利益,船方当事人和货方当事人利益因此而消彼长。然而从海上货物运输法所涉及主体来看,应当认为"船"指的是以船为中心的利益方,而"货"指的是以货为中心的利益方。
船货利益平衡原则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具有调整船货利益冲突、平衡贸易航运产业利益互动和国际博弈、保护国家产业利益功能的基本准则,是体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根本价值、指导思想、精神以及经济基础本质的法律原理。
二、船货集团利益博弈分析
船货利益博弈表现在海上货物运输法中时是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但笔者为求简便, 仅以船方的立场来分析关于船方的权利义务及其他涉及双方利益相关规定的变化对货方义务权利的影响,以及两者所形成的利益博弈格局。
(一)基本义务。承运人的基本义务的规定是关于在海上货物运输途中承运人应尽到的最基本职责。任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条款都不能减轻或免除此种义务,被称为"最低的法律义务"。合同有约定减轻或排除的,视为无效合同。在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过程中,未尽此基本任务的,承运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二)责任期间。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的期间。责任期间长,承运人基本义务负担加大,成本增加,面临的风险也更高。同样作为既得利益者,包括收货人、发货人在内的货方更期望责任期间延长,从而减少自己的义务和风险。
(三)免责原则。免责原则是通过对特殊情形免责的规定以减少承运人责任风险,实质上是承运人的保护条款。尽管此类条款是出于船货双方公平合理分担海上货物运输风险的目的,但是其免责范围的大小不同将产生不同的效果。
(四)责任限制。责任限制的规定往往决定着船方赔偿责任和货方货物损失得以弥补的程度。船方为尽可能的降低自己责任和货方尽可能的弥补自身损失都将不遗余力的参与到关于责任限制规定的制定中来。
三、历史变化下船货利益博弈对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影响分析
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发展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划分为四个时期:(1)海上冒险时期,即海牙规则产生前时期。(2)《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时期。(3)《汉堡规则》时期(4)鹿特丹规则时期。每个时期都涉及一项或数项影响力巨大且体现当时船货利益集团博弈结果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与制度。
(一)《罗德海法》和中世纪三大海法时期
《罗德海法》和中世纪三大海法时期此时处于中古时期,航海技术不发达,海上货物运输也仅仅局限在区域性的活动。当时由于海上货物运输处于不发达阶段,货方在海上货物运输活动中所面临的的风险更大。为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通常采取一些有利于货方的做法。在《奥列隆惯例集》中我们可以发现船主的责任从船舶和航运安全扩展到了管货,要求船主必须履行有关适航(适货)义务,赋予了船主比较重的义务,同时就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贸易商人的利益。
(二)《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时期
通常来说,《海牙规则》更多的体现承运人的利益,并被广大货主和代表货方利益团体所抨击、指责。 因为承运人借助"合同订约自由"原则在提单中增加大量的免责条款,严重损害了货方的利益及影响了提单的流转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此,代表货主利益的美国1893年通过《哈特法》,对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免责、权利和义务等进行规制。1924年《海牙规则》采纳《哈特法》的规定,明确承运人两个最低的基本义务:适航和管货,以及17项最大限度的免责事项。此后又于1968年通过《维斯比规则》,并在1979年进行修改,将承运人单位赔偿责任限制计算单位由金法郎调整为特别提款权(SDR)。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此时的海上货物运输制度仍然侧重于保护承运人的利益,因为承运人责任基础---不完全过错责任没有任何动摇。但值得注意的是,货主利益慢慢得到中体现如承运人单位赔偿责任限额的已提高、明确规定提单的证据效力,保护提单受让人的合法权益等。
(三)《汉堡规则》时期
虽然维斯比规则的出台解决了船货双方利益的部分纠纷,但是双方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的斗争并未终止。在这一背景下,《汉堡规则》应运而生。
《汉堡规则》对《海牙规则》做出以下修改:第一,废除了航海过失免责制度并采用了完全过失责任制。但该规则规定对承运人过失造成火灾的举证责任由货方承担,但货方很可能因举证不能而丧失向承运人索赔的机会。第二,较大幅度提高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第三,明确规定了承运人在迟延交付货物下的义务和责任,但赔偿责任以该迟延交付货物运费的2.5倍为限的规定不失为一种对船方的妥协。第四,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扩大,从"钩到钩"延长到"港到港"。第五,为保护货主的索赔权利,诉讼时效延长至2年,仲裁时效的期限也为2年。第六,增加对舱面货、活动物等货物的规定。第七、明确了提单的含义、作用、积载的事项及证据效力。总体而言,《汉堡规则》是货方在博弈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获得的成果。
四、《鹿特丹规则》时期
《汉堡规则》生效后形成三个国际公约并存的局面,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利益选择适用不同的国际公约。此种公约不统一的局面,违背了制定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以促进国际贸易开展的初衷。为此又制定了《鹿特丹规则》。
《鹿特丹规则》在对船货双方的权利义务、争议解决及公约的加入与退出所做的一系列的规定都体现的在船货利益博弈新的特点。(1)在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上,为适应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发展的需要,将承运人责任期间扩大到"门到门"运输,实行网状责任制。 (2)在承运人责任上,该规则延长了承运人的适航义务时间,规定在开航前、开航当时和海上航程中均要恪尽职守使船舶处于且保持适航状态。(3)在对无单放货的规定上,规定了承运人可凭托运人或单证托运人的指示交付货物,从而解决了航运实践中承运人凭收货人保函与提单副本交货无法律依据的问题。(4))在对货物控制权与权利转让上, 规则充分的保护卖方利益及单证持有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鹿特丹规则》相对于前几项国际公约而言,在船货利益分配上更加的公平。
结语
从《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内容和国际公约的发展轨迹来看,船货双方利益的博弈不仅影响海上货物运输法制度建立,同时也反过来作用于船货双方利益的分配。追求船货双方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是未来海上货物运输法及其他相关制度所追求的目标。我国应当结合本国的国情,平衡船货双方的权益,以适应我国航运和贸易发展实践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天生.《船货利益平衡原则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0
[2]尹东年 、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3]傅廷中.《海商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7:206。
[4]杨良宜.《国际货物买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郭瑜、朱珂.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变革看船货双方利益的博弈[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