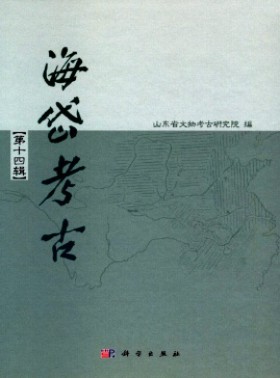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远古的传说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远古的传说范文1
元宵节的传说故事:
窃国大盗篡夺了成果后,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又怕人民反对,终日提心吊胆。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嗓子在喊:“元宵。”觉得“元宵”两字谐音“袁消”,有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粉果”。然而,“元宵”两字并没有因他的意志而取消,老百姓不买他的帐,照样在民间流传。
(来源:文章屋网 )
远古的传说范文2
【主题词】占卜传说 变文 文化观念
藏族学者蔡巴.贡噶多吉作于公元1346年的《红史》是西藏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全书有相当章节概述了汉地、蒙古、吐蕃、木雅等地的王统,这些内容虽然不尽符合史实,但在文化史上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笔者对此书第七章记叙的木雅(党项)国开国皇帝出生传说的来源尤感兴趣,试图利用河西及中原的汉文典籍的同类记载对其中一个细节的来源略作阐释,希望能揭示它们在文化传承上的联系。书中有关部分记述如下:
最初木雅地方都在汉人皇帝的统治之下,在北面都城和迦(gha)地方之间有一座叫做闷日(smon shri)的山,该山有一尊地方神叫做格呼(gai hu)。有一天,凉州城中有一名妇人那里来了七个骑马的白色人,他们的首领与这妇人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天上出现了一颗前所未有的星星,汉人占卜者说:“在此城中,出生了一位将夺取社稷的人。”皇帝下令寻找这个小孩,妇人将小儿藏在一土坑中,盖上木板,木板上再放一盆水。占卜师说:“在一大海的下面有木头的大地,小儿就在那下面。”因此没有找到这小孩。
文中接着叙述了该小孩躲过追杀,以后被人抱养。他长至七岁大时遂联络与其年龄相仿的小孩六人在北面都城附近的山里造反,最后果然带兵杀死了汉地皇帝从而成为了木雅的首位帝王,应验了先前的预言。他取其父格呼神的格字,名为格祖王。[1]成书年代稍晚于《红史》的《雅隆尊者教法史》(1376年)也记有类似故事,仅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书中称当汉地皇帝下令占卜师寻找该儿时,有一老妪将其藏于地穴达一年之久。还在处盖以木板,上面置以满水之碗。诸占卜师卜后,称其在湖底树木之地下。[2]而由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作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则称地方神名叫智呼(si-vu),其余情节悉同它书。[3]此外,由班钦.索南查巴作于1538年的《新红史》虽然记叙简短,但却直接称小孩之父为名叫斯呼(se-vu)的龙魔。[4]显然上述藏文史籍所记载的木雅王故事应具有同一来源。而据《红史》所称,它是先由木雅禅师喜饶意希(shis rab ye shes)口述,后又在贡塘地方成文的。禅师是凉州的高僧,可能生活于十四世纪。[5]最近研究者注意到12世纪的西夏文史诗《夏圣根赞歌》也记有类似内容,提到其开国君王se ho的名字以及西夏王为龙之后裔等。研究者业已指出,se ho实际上是西夏借用的汉语,意为“细皇”,即指太祖李继迁。但在晚期的藏文文献中,该词又被用来泛指西夏前期的三位君王。[6]这一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澄清了藏文史籍中的早期西夏王传说的渊源问题。下面即在此基础上就其中木雅王故事中的占卜情节问题略作补充性的分析。
应该注意到,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伍子胥变文》(伯2794)在记叙伍子胥奔吴情形时,也有相似占卜情节的描写:
(伍子胥)行得廿余里,遂乃眼润耳热,遂即画地而卜,占见外甥来趁。用水头上攘之,将竹插于腰下,又用木剧(屐)倒着,并画地户天门。遂乃卧于芦中,咒而言曰: “捉我者殃,趁我者亡,急急如律令!”子胥有两个外甥:子安、子永——至家有一人食处,知是胥舅,不顾母之孔怀,遂即生恶意奔逐:“我若见楚帝取赏,必得高迁。逆贼今既至门,何因不捉?”行可十里,遂即息于道旁。子永少解阴阳,遂即画地而卜。占见阿舅:“头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间有竹,冢墓城荒;木剧倒着,不进傍徨。若着此卦,必定身亡。不复寻觅,废我还乡。”子胥屈节看文,乃见外甥不趁,遂即奔走,星夜不停。[7]
将此段文字中提到的伍子胥为欺骗其外甥而采取的诈死方式与《红史》中所记载的妇人为瞒过汉地卜师而采用的隐藏婴儿的做法相对比,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变文》里的伍子胥“用水头上攘之”,因而使其甥占卜后相信其“头上有水,定落河傍”,《红史》里的老妇人则在男孩藏身处上面放一碗水,使卜师误以为其处在大海之下。又《变文》中伍子胥还将竹插于腰间,诱使其甥相信他已进了坟墓(所谓“冢墓城荒”),《红史》中的妇人则把婴儿埋入土坑,并在上方盖上木板,实际上也是为了使卜师们确信他已死去并被埋入棺材中了。总之,二者所采用的假死手段几乎在细节上完全一致,结果也都成功地骗过了占卜者。由于《红史》的成书年代远晚于敦煌变文的时代,故我们可以初步认为,《红史》中出现的这一具体细节当源于汉地的民间故事。下面拟再从该类题材在汉文记载中的流传情况和它所隐含的文化观念这两方面入手加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故事在汉地出现的时间非常早,以后又长期流传不辍,这使我们能在不少作品中都可发现它的痕迹。周绍良先生曾指出,与伍子胥诈死骗过卜者情节类似的故事更早则见于南朝宋人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文学四》中。[8]其文如下: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水下土下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9]
同一故事又见收于《语林》,但情节稍显简约。此节内容现保存在《太平御览》卷六九八中,文字如下:
郑玄在马融门下,业成辞归,融心忌之。郑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矣。[10]
《语林》里的“玄在土下水上”显系“玄在土下水下”之讹误。此外成书于14世纪的“讲史”类的话本小说《武王伐纣平话》卷中曾叙述姜尚一日偶遇樵夫武吉,他预言此人有不测之祸。后武吉果因误伤他人致死而被收系下狱偿命。武吉方信姜尚所言不虚,遂以辞别老母为由,求得文王七日宽限。翌日武吉母子二人前去渭水求姜尚搭救。姜尚遂教武吉一法以避此难:
渔公言:“放公次到家中,买粳米饭一盘,令食不尽者,拈七七四十九个粳米饭在口中,至南屋东山头,头南脚北,头边用水一盘、明镜一面,竹竿一条长一丈二尺,一通其节,令添水满,顿在头边,用蓬蒿覆身;但过当日午时三刻,汝已得活,不妨也。”子母二人拜辞,归到家中,依渔公之言,用其妙法。至当日午时,武吉不去赴法。却说文王怪武吉不来赴法,遂发一课,知此人避法去投水也。口内生蛆,有丈二水在身,痛死也。文王再不言武吉之事。[11]
显然,《平话》所记的这一诈死情节与前引《伍子胥变文》、《世说新语》的相关故事在具体细节上如出一辙,据此可知该类轶事在民间长期流传而未中断。归纳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诈死者常制造出自己“身(头)在土下水下”的死亡假象,以达到迷惑卜者的目的。而这一办法之所以得以奏效,显然又和古时汉人的死亡观是分不开的。在传统汉族社会中,人死后所去的地下世界即被称为“黄泉之地”,埋葬死者也被叫做使死者“入土为安”。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卜者看来,“身在土下水下”预示着人的死亡了。相反,如果在卜者看来,某人是“身在土上”,那么此人就必生无疑。关于这一点,我们检出以下几段文字作为佐证:
唐代释大觉的《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记有:
蜀有智将,姓诸葛,名高(亮),字孔明,为王所重。刘备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后乃刘备伐魏,孔明领兵入魏,魏国与蜀战,诸葛亮于时为大将军,善然谋策。魏家唯惧孔明,不敢前进。孔明因致病垂死,语诸人曰:“主弱将强,为彼所难,若知我死,必建(遭)彼我(伐)。吾死已后,可将一帒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言已气绝。后依此计,乃将孔明置于营内,于幕围之,刘家夜中领兵还退归蜀。彼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蹋土照镜,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战。刘备退兵还蜀,一月余日,魏人方知,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军兵尽散。[12]
又释景霄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一六也说:
孔明即诸葛亮之字也,襄阳人也,为蜀主之所重。自三往召之方出……后令孔明领兵伐魏,因得病垂死,语诸军曰:“主弱将强,为彼可难,若知若知(衍二字)吾死,必遭彼伐。可将帒盛土,安吾足下,取镜照吾面。”言讫而终。置相营内,依语为之,至半夜抽军归蜀。经月余日,魏王有将司马仲达,善卜,卜云:“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知在也。”不敢进兵。至后方委卒。时人曰:“死诸葛亮怖生仲达。” [13]
此外,晚唐人陈盖(9世纪后期)曾对胡曾《咏史诗》中的《五丈原》一诗作过注释,其注云:
《志》云:武侯诸葛亮将蜀军日北伐魏,魏明帝遣司马仲达拒之。仲达、蜀军于五丈原下营,即死地也,遂关城不出战,武侯患之。居岁,夜有长星坠落于原,武侯病卒而归。临终为仪曰:“吾死之后,可以米七粒,并水于口中,手把笔并兵书,心前安镜,下以土,明灯其头,坐升而归。仲达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云武侯病死,仲达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遂全军归蜀也。”
以上三段文字都是叙述的在民间久已流行的有关诸葛亮的“死诸葛走生仲达”故事。但除了“足下踏土”这一共同点外,在其余的细节上陈盖的注解与《续藏经》的说法又稍有差别。他在注解里增加了“明灯其头”等内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又影响到后来《三国演义》的创作。[14]据日本学者小川阳一检索,所谓“头上置明灯”的描写常见于明代的小说中,用于术士为人向北斗星祈命作法的“厭命”场合下,而这一点又与人们相信北斗星主宰人的生命有关。例如,前引《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武吉躲祸情节在后出的《封神演义》即有相当改动:姜尚让武吉睡入土坑中,其头、脚处各置一灯,身上撒米;而姜尚则“披发仗剑,踏罡布斗”以挽救武吉的性命。这正是元明时期北斗信仰的日常化表现。[15]不过小川氏的论文未检及上述陈盖的注文,故没有注意到这一做法早在唐末已露端倪。至于以上文字都提到的“取镜照面”的细节,则可能与古人为取光明破暗之意特地以镜照尸体的观念有关。[16]
综上所述,与《红史》等西藏史籍中的占卜故事类似的情节实际上更早约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汉籍中,此后又长期流传不绝。本文的分析表明,这类情节的流行和传统社会中汉人的死亡观念密切相关。而敦煌变文则为我们提供了该类故事在河西这个自唐代以来就是汉、藏、党项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流传的直接例证,由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藏文史料中也会有与汉地故事这么近似的情节了。与此类似的汉地文学题材影响到西藏民间故事的例子还有一些,如敦煌变文中的《茶酒论》、《孔子项橐相问书》里的基本情节后来也曾出现在藏族民间文学中。这些例证均有助于我们理解河西地区在汉藏两族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所起到“窗口”作用。
[1]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东噶.洛桑赤列校注《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23-24页。按:关于引文中出现的藏文专用名称,原译者未加考释。据聂鸿音师意见,应作如下还原:gha=夏 smon-shri=天山(可能是天都山的省称) gai-hu=夏皇
[2]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26页。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65-66页。
[4]班钦.索南查巴著,黄灏译注《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47-48页。
[5] R.A.Stein, “Min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Extrême-Orient,1947-1950, p265.
[6]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民族研究》1996年5期。
[7]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9页。
[8]周绍良《读变文札记》,收入所著《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年,99-100页。
[9](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45页。
[1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3115页。
[11]不著纂人《武王伐纣平话》,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55-57页,该段内容的英文译文见Liu Ts‘un-Yan(柳存仁),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Wiesbaden 1962, pp52-54。
[12]《续藏经》(第一编)68. 30a,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13]《续藏经》(第一编)68. 988b—989a。
[14]周绍良《读唐代的三国故事》,同周氏前揭书,229-231页。
远古的传说范文3
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些内容的本身是一段远古传说,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对远古历史的认识。没有学生心目中那种严格的“证据”;二是刚刚进入初中的学生,他们的抽象理解能力没有达到必要的高度,求知欲强而对神话传说意义的认识还不够,甚至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培育。产生以上的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可能也因为教材编写的原因。从教材对黄帝事迹的文字叙述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能是因为篇幅制约,或考虑到初中生接受能力以及知识点不宜过多等问题吧,有些给人一种不太确定的感觉。加之“动脑筋”中有关问题的设置,目的是引导学生朝着历史方法性方向思考的,如果教师不注意正确引导或者不作处理,学生会因为认定它“不科学”,而妄自菲薄的。
通过新课程教学中的尝试,我们觉得,历史教师在讲解这段内容的时候,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照应本课主题,突出黄帝是“中华之祖”的一个代表
本课一开始就涉及到三个人物:炎帝、黄帝、蚩尤。然而学生在这里容易产生误解,有的以为黄帝是“华夏之祖”,就是唯一的祖先;或者认为既然是“华夏之祖”,就是汉族的祖先了。教师应当在讲解“炎黄战蚩尤”的时候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们有的老师在这里作了些看似“加负”的补充:
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我们知道了黄帝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联合炎帝部落,平定了蚩尤的扰乱,统一了远古三大部落,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个共主。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祖先,我们中华民族将黄帝作为代表,作为华夏始祖,是在中华民族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的。
但是,一般人把黄帝仅仅看作汉族人的祖先,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但不是全部。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包含了华夏、蛮、夷等中国境内大多数原始部落的血统和文化,是一个有别于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炎帝和黄帝是汉族的祖先之一,蛮、夷诸部族的祖先也应是汉族祖先之一。同样,后代那些分别源于蛮、夷等原始部族的少数民族,也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亦有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成为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
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庭,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56个兄弟民族都是在汉、唐、宋甚至更晚的时期形成的,距离炎黄时代有三四千年之遥。由于迁徙、杂居、通婚等原因,子孙繁衍,支系无谱,很难在血统方面准确判别几千年前的某部族首领是某民族的祖先。与其把炎帝、黄帝或其它某个原始时代的英雄人物看作是某族的祖先,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更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
通过以上老师介绍,可以消除学生在本课学习中的误区,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民族意识。也为今后学习有关民族问题的历史内容做铺垫。
二、引入时代观念,从三个文明理解“人文初祖”
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是就文化创造、文明初创说的。什么是文化或文明,真正定义起很难。我们查阅了有关传说中黄帝的“事迹”内容,发现从分类角度进行归纳,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一概念。今天,我们讲“三个文明”,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我们引导学生也通过今天对文明的内涵的认识,从三个方面让学生找找看,传说中黄帝及其周围的人有哪些贡献?学生们非常踊跃。
然而,教材在对传说故事的取舍上,没有选入政治(制度)文明方面的。我们觉得这是个遗憾。于是,我们给学生补充讲解了一些查阅的资料,说明黄帝还创立了别尊卑,定礼乐,创官制、财产、嫁娶和丧葬等制度,在制度文化方面把我们的先民带入了文明的门槛。
从这个教学环节,我们感觉到:学生动手,活跃了课堂氛围;资料充实,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归纳整理,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方法。
三、利用教材小字,体会“传说”与“史实”
《黄帝──“人文初祖”》这一目小字内容很重要。我们认为,正是它联系着正文和“动脑筋”,成为引导学生体会“传说”与“史实”区别与联系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学生阅读过这段小字后,教师可问:为什么我们远古的历史会留下许许多多的传说?传说会是真的吗?我们怎么才能证实传说是否可信呢?
学生的答案是非常多的,他们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不管是请学生发言还是组织学生讨论,最后,还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结合他们的思考,介绍怎样区别“传说”与“史实”这一方法性问题。如有的教师是这样总结的:
“传说”与“史实”的最终区别在于有没有实物证据,比如小字中的考古发现,就有力地证明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了这些文明成就。结合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还能够互为印证。这样,“传说”尽管不会每个细节都令人信服,也能从“史实”的角度确定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这么做了。
远古的传说范文4
冬夏两季,一冷一热。关于这一自然现象,蒙古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一位司寒老人(寒神)要和司暑老人(暑神)比试威力。司寒老人说:“我在九天之内能把大地变成冰雪世界,你能熔化吗?”司暑老人应战道:“我只要八天就能把你的冰雪世界化为海洋。”于是立下誓约,败者须受胜者的支配。司寒老人果然在九天之内使大地变成了冰雪世界。接着司暑老人修炼出一轮红日,从四面八方发出强大的热量,果然在八天之内将冰雪世界变成了大海。两人神威相等,只得将一年分为寒暑各半,从此,人间有了冬夏季的轮换。
蒙古人关于牲畜保护神的传说
“吉雅其”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牲畜保护神。传说中讲道:“吉雅其”是一位深知马的习性的牧马人。他一生放牧头人的马群,年老病死时还舍不得与马群告别,因而久久不能咽气。头人前来探望时,他说:“我死后把我平时穿的衣服给我穿上,在我胳膊上挂上我用过的那根套马杆,之后把我放在那匹黄骠马上,送到西南山去,让我背靠着额尔敦本贝山,眼望阿拉坦本贝山,静卧长眠。”头人答应他要求后,吉雅其就闭上了眼睛。几个月后,头人的马群里发生了瘟疫,并且发现夜夜有人把马群赶进西南那座深山里。头人揣摩出事情的原因后,就走进山里,对着吉雅其的遗体许愿祷告,并答应把他的像画在牛皮上供奉起来,好让他每天都能看到心爱的马群。这样,第二天起,一切事情平息下来了,吉雅其在山中的遗体也从此不见了……
蒙古人的狩猎天神祭词
“玛纳罕”是古代蒙古人心目中的狩猎天神。每逢狩猎,古代蒙古人都要祭拜“玛纳罕”神,祈求他恩赐猎物。其祭词中说道:……把锅里放不下脑袋的猛兽/赐给我们/把门里挤不下犄角的野兽/赐给我们/把没有经过放牧的驯鹿黄羊/赐给我们/把没有带嚼子的黑熊/赐给我们/把没有围猎驱赶的灰狼/赐给我们/把没有追踪猎获的狐狸/赐给我们/我们慷慨的玛纳罕天神/把进来的大门敞开/把出去的大门关闭/我们的玛纳罕天神/呼瑞,呼瑞,呼瑞!
蒙古人的祭火词
古代蒙古人视火为天之圣物。所以每逢祭火,都要诵念诚笃的祭火词。其祭词道:喳,闪光的火神/祈求赐予/吼声震天的犍牛/肥得走不动的犍牛/乳汁像泉水喷涌的母牛/哞哞嬉戏的牛犊/呼瑞,呼瑞,呼瑞/旺盛的火神/祈求赐予/长鬃拖地的儿马/鼓胀的母马/步态漂亮的骟马/跳跃玩耍的马驹福禄/呼瑞,呼瑞,呼瑞/运气升腾的火神/祈求赐予/颈鬣巨大的公驼/年年下羔的母驼/勇往直前的骟驼/没有不幸的驼羔福禄/呼瑞,呼瑞,呼瑞!
蒙古人的草木纪年法
远古的传说范文5
神话和民间传说,作为传达初民意识的载体,一直是史学家们考证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一般来说,神话的确有助于人们解释古人的习俗、信仰、制度、自然现象、历史名称、地点以及各种事件。在整个日本,特别是以大和为中心的地区,就广泛流传着关于大国主命的传说。《大国主》的故事从由太安万侣撰写的《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以及由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合作撰写的《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里就能找到。这两本书在性质上应该接近于中国的《山海经》,详细记载了日本远古神话和英雄传说。
在《古事记》中,大国主除了大国主命以外,还有四个名字:大穴牟迟、苇原色许男、八千矛、宇都志国玉。这四个名字,是随着他的成长不断变化的。最初的名字叫大穴牟迟。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身份相当低微,被描绘成一个成天背着个大袋子,跟随在众神后面被当做奴仆来使唤的神。但此时的他性格非常亲切和蔼,关心弱者。在去稻羽(因幡国)的路上,还救了一只受了伤又被众神戏弄的裸兔。正是这种亲切和蔼的性格使他赢得了因幡国美女八上比卖的爱。对他来说,男人总是迫害他,而女人总是拯救他的。众神由于嫉妒他赢得八上比卖的芳心,设计用烧红的石头烫死他的时候,是他母亲派来的蚶贝比卖和蛤贝比卖这两位以贝壳作象征的女性救了他的命;当他被众神欺骗夹死在大树里时,又是他的母亲救活了他。接着,走投无路的大穴牟迟在大屋毗古神的指点下从苇原中国(大和)逃到了根国――阴曹地府。在这里,统治者速须佐之男命给了他第二个名字――苇原色许男。“色许男”的意思是指粪便男人。在日本古代,为了避免灾难往往给小辈取一个肮脏的名字,希望这孩子好养活。速须佐之男命送给他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觉得这个从苇原中国来的小子肮脏不堪,另一方面又看他可怜兮兮的有点怜惜他。这是一种交织了憎恶与怜爱、迫害与保护的复杂感情。速须佐之男命给他设置了一系列的难题。这时,又是速须佐之男命的女儿须势理毗卖爱上了这个色许男,帮助他通过了层层关卡。其中还有一次,是一只草原上的老鼠帮助他躲过了速须佐之男命放的大火。最终,苇原色许男通过了种种考验,使这位根国统治者也对他产生了怜爱之情,给了色许男以可乘之机,夺了他的大刀、弓箭和天沼琴这三样象征着权力的武器逃出根国。在黄泉比良坂(黄泉国与苇原中国的分界处),速须佐之男命正式将他的武器和女儿交付给了苇原色许男,从此,苇原色许男成了八千矛神。在他被称做八千矛的日子里,他用神刀神箭驱逐了曾经迫害他的兄弟众神,建造了雄伟的宫殿,征服了高志国(越国),又娶了三位夫人,成为了苇原中国的统治者。而所谓宇都志国玉神,大概就是颂扬这位苇原中国的统治者的美称。
接着,就出现了让国的故事。对突然从天而降的天神未作任何反抗,而让出了自己苦心缔造的国家,这一点显得非常不自然,与之前大国主建国的故事很不连贯。由于《古事记》的后世编撰者出于政治需要而对远古神话进行了部分改编,为了说明天皇是天照大御神的后代而作了一些删改,所以它“虽然仍以远古神话传说为基础,但却不是古老神话的原始形态”。同时从日本神族谱系中可得知,大国主并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他的故事又刚好是在天孙民族子孙侵入大和之前广为流传的。这一切恰好可以说明,后来的让国故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且“这次让国绝不是和平进行的”。由此可推断,现在我们看到的《故记》中大国主故事的后半部分不能作为我们了解古代日本社会生活的史料。
用神话学家戴维・利明的话说,远古故事只有“作为隐喻起作用时才是神话,即它们表达了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东西”,“真正的神话是对人类共同特点的记录,它和纯意识形态相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精神、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联络媒介。”大国主四个名字的演变,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原始部族在争夺领地时所经历的一系列过程。从最初对他人唯命是从,到接受帮助与其他领主抗争,到最终驱逐曾经的迫害者成为苇原中国的一代霸主,大国主神话正是一部原始时代某一部族称雄的斗争史。对这则神话背后隐喻含义的分析与推断,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原始社会形态无疑是有帮助的。
远古的传说范文6
[关键词]彩陶;中华文化;起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2-0023-03
中华文化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是什么?当前学术界尚无比较一致的看法。以人定格,如以伏羲为“中华人文初祖”,以炎帝、黄帝、女娲等为中华人文始祖,都是根据传说确定的,传说的来源,是远古以来的中华先民在回忆自己文化起源时的一种寄托,久之几成定论,但究其内涵,如伏羲“制嫁娶”,①制甲历,分季节,②制作琴瑟、乐曲,立九部,设官制。③黄帝“迎日推策”,④即推算朔望、节气、日辰等,令其臣“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仰天地置列侯众官”,⑤等等,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佐证,因而显得恍惚迷离,难以确定,急需我们从考古和理论两方面予以充实和论证。
的确,要讲清中华文明之源的问题,光凭历史传说和由传说转变而来的文献记载是不够的。因为传说误差很大,记载、转抄又有歧义,加上古今不少传播者、解释者都想与这些古先哲人套近乎,将古先哲人的生地或活动区说到自己的家乡,忽视了远古先民“迁徙往来无常处”,⑥不会长久定居的特点,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窃以为论证中华文化产生的标志性成果的问题,彩陶文化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彩陶是发现于黄河上游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陕、豫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形式。它的文化价值非常明显和重大。彩陶本来是原始先民的一种工具、饮食或贮藏器,但先民在制作这一器物的时候,也把它当作一种书画工具和精神文化的载体,将自己对周围自然、社会的感受、认识和期许,经过思维想象和加工,或直观或抽象地描绘在了陶器上,形成陶画、陶塑、陶符等艺术图像和表意符号,使其不仅带有远古先民物质文明的信息,造型、颜料、烧烤等科学技术知识的信息,而且还表征着丰富的哲理、艺术、史学、宗教、文字等方面的文化要素,是远古先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性表现形式和成果,也是远古社会流传至今的最直接、最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下面仅从精神文化方面做一些分析。
一、哲学
原始先民通过观察、想象和构思,乃以陶器为书画材料,用兽毛做成的笔和矿物质颜料,将自己对自然环境、社会事物、氏族来源等的感受和认识,直观或抽象地描绘在陶器上,形成一定的文化形态,流传下来,就使今人能够通过这些彩陶图像了解到原始先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感悟。比如,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壶(或瓶)口周围缠绕地画着一个圈,圈下有许多匀称的直线,像是以陶壶(瓶)的器口为太阳,向四周射出的光芒。竖线下方,器腹部又画上一圈波纹、旋纹或草叶纹,以象征大地、流水、万物等。彩陶上类似的花纹还有很多,如蛙纹、鱼纹、鸟纹等及其图像组合。这不就是原始先民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反映和重塑?不是代表了他们思维想象的能力和水平吗?由太阳、水波、动植物合成一体的图画,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天地和谐、万物一体、“物吾与也”等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原始先民或许尚没有这样高的理论思维能力,但这些图像却能孕涵和启导上述传统哲学思想的形成。1958年,甘肃省甘谷县西坪出土了一件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红陶,黑彩,上面画着“人面鲵鱼纹”。⑦1973年,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出土了一件石岭下类型的彩陶瓶,高18厘米,口径5.5厘米,红陶,黑彩,画的是“人面鲵鱼纹”。⑧这些动物与人合为一体的形象,又很像是一个氏族的图腾,它是神灵、宗教崇拜产生的基础。还有黑白、上下、左右对称的图案构思,也能启发人们对事物对立统一、对等和谐、均衡协调等观念的建立;统一布局、通体彩绘的一贯性又容易启发人们的“会通”精神。⑨此类哲学意涵,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分析,就会从彩陶上发现、体认得更多。
二、艺术
黄河中上游和渭河流域发现的彩陶,其花纹式样多得难以数计,既有形象的又富于抽象的构思和表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使用线描的作画手法,内容丰富,质朴神秘,这种绘画的技法和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洋画重堆彩、重传神;而中国画自始就用线条勾画法来表现各种图像,同样可以产生传神动人的艺术效果,这一绘画风格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的彩陶文化。至于彩陶器物的造形,盘胎、打底、挂彩及器物附件的塑雕、各种纹饰图案的选用,绘画的工具笔、砚,绘画的颜料等等,自从原始先民发明创造以后,万世流传,增删改进,直到近代似还能看到它的流风遗韵。今天,我们所用的陶器,无论造型还是文饰都保留着彩陶的一些特点。从普通人家到豪华宾馆,人们也都愿意收藏一些彩陶器,摆在最为显眼的地方,搜罗不到真品,哪怕找几样复制品也是倍加珍爱,这除了反映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珍重外,彩陶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三、史学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是从磨制和深加工石器开始的。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也正是从这一时轫。因此,如果说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代表,那么,彩陶当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器具的标志性发明创造。考察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的状况,除了石器以外,彩陶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陶器工艺以及陶纹中的绳纹、网纹、锯齿纹、鱼纹、鸟纹等,反映着当时人们渔猎、畜牧、手工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制作、雕塑、绘画,烧制技术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与史书、口头流传并列的用实物表达的史学形式,是甲骨、金石、简帛等史料形式出现以前,先民应用最普遍、使用时间最久的一种史学载体。1977年,甘肃榆中县马家q出土的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罐,高10.2厘米,口径8.8厘米,红陶,黑白彩,下部通绘平行线,像是一片阔地,上有网格纹,网格旁边有鸟纹等,图案反映的当时先民张网套鸟(兽)的史实。⑩其他如彩陶上描绘的抬物图像、舞蹈图像等等,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我们考察原始社会的历史,石器负载的信息量太少,以致于让人难窥古人的实际。在这方面,彩陶文化的遗存可以弥补许多的缺憾。距今3000~7800年左右的彩陶文化,包含着极多的物质、精神文化的信息,是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史料。
四、宗教
彩陶中所见点、线、水波、鱼、鸟、蛙、蛇、人头以及绳纹、网纹、旋涡纹、花瓣纹、圆圈纹、星形纹、锯齿纹等等纹饰,反映了人将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个体以后,继续亲近、热爱和崇拜自然,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人对自然的反映越多越深刻,其主体意识就越强;而主体能力的有限性,又使人们容易产生向外界力量比如神力求助的念头,彩陶在这方面给今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再说,能够想象和画出无数复杂线条、花纹和陶符的脑和手,就完全能够以无数陶画、陶符作为思维的材料,概括出同样是反映客观事物,但形式却更加简单、内容更加复杂、意涵更加深邃的八卦之类的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1不难想象,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变,再到卦、爻辞的确定等,需要更高的理论思维和概括能力,而作为起点,陶画、陶符之于八卦符号的产生,至少是起了启导的作用,而且,两者在文化地理、思维特点等方面也有内在的联系。彩陶上的图腾图画,更是宗教文化最为明显的表征。
五、文字符号
人们在用最早、最简单的笔触描绘客观世界,反映自己的思维构象和思想观念以前,是以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的方式来保存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先民经过不懈的摸索和实践,在陶器上画出了几十种符号,这不论在甘肃大地湾,陕西庙底沟、半坡等地出土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活动空间的扩大,作为人们交流工具的文字,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亟需。彩陶时代的先民,无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思维能力上,都已经具备了抽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条件,陶符不一定就是文字,但陶符加上陶画,已经为真正意义上文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
综上,形状各异、纹饰绚烂的彩陶,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结合的形式,它当之无愧地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彩陶还是中国远古文化流向的一个风标。中国远古文化的流向,是从中国西部往东部传播的,还是从东部往西部传播的?对于这个问题,从古到今,学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既然彩陶文化的发育是那样的饱满丰腴,辉映四五千年之久,在青铜时代到来以前,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就能够以它为风标,测知中华远古文化的流向。
众所周知,我国的陶器文化,除了黄河上中游的彩陶文化外,还有山东等地的灰陶、黑陶即所谓素陶文化。我国西北的彩陶出土比较集中,素陶相对较少;而山东等东部地区出土的素陶比较多,彩陶出土量相当少。从文化内涵上看,素陶主要反映物质文化的状况,而彩陶还反映更多的精神文化的内容。从形成时间上看,素陶出现的年代距今不超过6000年左右,而彩陶形成的年代比素陶要早1000多年。从陶器的制作时间及水平看,所谓东夷(部)文化高于西戎(部)文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再从黄河中游和上游的情况看,黄河中游河南等地出土的彩陶,没有早于距今7000年的,而黄河上游大地湾出土的彩陶,最早的距今7800年,由此可见,在彩陶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容有黄河中游地区向西扩展,在风格、形制等方面影响黄河上游、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可能,如考古学界多认为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就是仰韶文化的分支,其与陕西、河南的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彩陶文化的起源上看,则肯定是大地湾彩陶早于黄河中游的彩陶。因此可以说,陕、豫等地的彩陶文化,是以大地湾为代表的渭河上游早期彩陶文化东传、影响下出现的,而后才有陕、豫彩陶发达以后,向西传布而影响甘、青彩陶文化的事实。这一远古文化的起始流向,应是从渭河上游东移到陕西,再到河南等地的。这一估计,与传说和文献记载中伏羲文化的传播方向相一致,因而可以佐证伏羲氏族、部落迁徙的走向。12
[注释]
①《易・系辞下传》。
②《周髀算经》云:“伏羲作历度。”《太平御览》卷78引《春秋内事》云:伏羲氏“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
③司马贞《三皇本纪》云:伏羲“都于陈”。马X《绎史》卷3引《易纬・坤灵图》云:“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太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论语摘辅象》云:伏羲氏设六佐,“金提主化俗,乌明主建福,视默主灾恶,纪通主中职,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
④⑥《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⑤《史记》卷1《五帝本纪・正义》。
⑦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图版第15及说明。
⑧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图版第20及说明。
⑨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⑩见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图版第35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