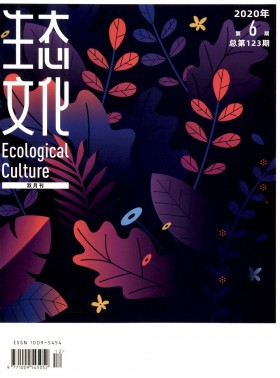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文学话语生成环境探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黄立华 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生态文学话语是以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生态批评运动为嚆矢。进入21世纪,它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几乎与“诸如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相颉颃。”[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现代主义为了生态批评的需要强调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对立二元和等级的不稳定性。这就为各种二元范畴,特别是自然和文化范畴创造了生产语境。本论文拟就两部后现代小说文本中的环境隐喻进行分析解读以揭示出后现代语境是怎样通过语言产生出来,语言又是怎样和语境相联系的。
生态文学话语生成环境虽然生态批评直接关注自然和环境,但是努力将自然现象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会引起概念问题,因为生态本身就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赖于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质疑本体论论证,生态批评努力研究约翰•本内特所称谓的“多有机生物概念”。也就是说,创造“一个整体实体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这一意象当做真正的实体:如‘环境’、‘人类生态’、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首先,生态批评需要包容的、跨学科的方法。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发现包括多种环境问题的理论方法。实际上,任何对文学理论中的生态问题的质疑都需要理论支撑。改变目前批评理论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扩大理论系统;其次,如果批评重点专一于特别的文学作品,如自然诗歌、小说,那么,在分析的过程中批评的透镜必须加宽。最后,如果在生态批评中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在解决生态问题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学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都要分析,生态理论需要某种比较复杂的生态文学话语,因为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统的内容。困难在于选取一种将自然和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的恰当的批评视角。因而,今天的生态批评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改造自己的过程;需要不断从其他学科和自然科学借鉴的过程。从文学政治化的视角来看,环境思维所引发的意识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所提出的美学困境迫使文学批评家去认识文学和批评在理解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将文学视为斯汶•伯克兹所谓的“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为前提的。伯克兹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理解生态文学分析的过时的批评方式的危险性的时候是有意义的。
他质疑:“文学可以作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实际关系加以研究吗?文学应该公众化去帮助提高自然环境的原因吗?”[3](Birkerts1996:4)虽然生态批评的确应该探索文学和生态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应该以牺牲文学文本而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临摹为代价。文学不应该用作研究生态问题的借口。生态批评读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学文本看成仅仅是反映现实的透明介质的境地。因此,生态批评真正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过时的表现主义的模式,而应该是自然怎样在文学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创造有助于产生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径的生态文学话语。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强调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发声的在社会实践中很有意义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认为自然知识总是受到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和威廉•鲁克特所谓的“文学生态”是探究自然边缘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辙。它表明生态文学是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负有责任心的人类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态文学话语致力于研究文学文本时怎样说明自然的沉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生态批评正好起到中间媒介的作用,因为它探索我们在话语上称之为可以操纵的文学中的非人类世界,讨论自然是怎样边缘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样被融入人类语言的。况且,生态批评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构,同时也包含语言、欲望、知识和权势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话语建构,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为敌对荒野。特别是小说和诗歌中的自然话语往往是对自然灾难性的虐待的观念的证实。为此,生态批评不只是观察和阐释而是作为一项积极保护生态的行为。自然话语要让人类在消弭人类和非人类区别的矛盾心态中替自然说话。正如凡尔•普鲁姆伍德所讨论的:“我们作为人能够替非人类的自然说话的假设似乎影响着包容的、独有的‘自然’意义,还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区别,不仅仅克服其二元建构。”[6](Plummwood1997:349)尽管有这样的问题矛盾,生态批评家们认识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为排除话语的他者,而是作为需要对人类地位的非二元知觉和阐释的主体。与自然的对话就预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构一种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对立的理解和认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态批评努力解构自然语言对话中的特权人类主体性也许会创造可持续的文学生态视野。虽然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有很大争议,但是生态批评却是一种“人类已经创造性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畴。[7](Gruen1997:364)因此,生态批评提倡对已经确立的信仰、观念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创立“一种所有生命必然联合的意识”。[8](Eisler1990:26)为了做到这一点,生态批评需要从现存的批评理论中吸取精华去编码文学生态,去定义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学话语。这就是所谓的奠定生态批评的概念基础的生态文学话语。《洼地》的主体间性建构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一些后现代小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然环境成分,呈现出叙述中语言的生态文学作用。
正如苏珊•斯特拉赫尔所认为的;“摆脱错误的和限制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的二元性,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努力进行一种独创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这些生态环境成分构成后现代语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洼地》是一部关于历史呈现的元小说。叙述者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学生争论。他的学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灾难所威胁的现实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国革命。小说一开始叙述历史和讲故事之间的问题的元小说思考与沼泽地区的沼泽地联系在一起。小说的主要生态环境隐喻是“淤泥”。“沼泽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损害陆地;淤泥一边形成陆地一边又破坏陆地;淤泥同时增加侵蚀;淤泥既不进展也不腐烂。”[10](Swift1983:7)小说利用这一隐喻对历史的虚构表现进行评论,同时通过诉求自然历史使得历史知识概念疑窦重重。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沼泽地发出有关自然的新的世界观的象征性表现的信号。用达纳•菲利普的话说,在《洼地》“确定有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的更为严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标记“缓慢而又艰巨的过程,无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垦的过程,也即人类淤泥化的过程”。[12](Swift1983:8)这一过程和“宏大历史变化”相对立。沼泽地决定叙事本身的本体论现实,强调这样的生态文学话语是怎样与元小说所引发的挑战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体论结构而言,自然的和虚构的两个不同领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诉他的学生,“在模糊的蕨类土地背景中,历史和小说相融合,事实由于无稽之谈而变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泽地的历史叙述还和小说的历史表现交织在一起。克里克对荷兰工程师考奈尔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纪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叙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态文学阐释:“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开始破坏他的工作。因为淤泥一边集聚一边又停止;一边形成一边又消失。”(ibid.:9-10)这样,作为生态隐喻的淤泥可以通过文本自我参考进行研究,并且赋予小说中自我决定的地位。#p#分页标题#e#
《洼地》的叙述结构基于生态文学隐喻范例的重复,如土地再垦、水、沼泽地、欧洲鳗鱼以及历史性、文本性、间断性和循环性的元小说范例。这样,元小说的、地理的和生物的因素联合起来生成生态文学元小说话语。正如克里克所说,“自然历史、人类自然。这些古怪的、奇妙的商品,这些解法解决的是神秘的神秘。因为试想一想……这一自然物质总是使得人造物质变得更好。”(ibid.178)只有这一生态研究能够再提出文本连贯性的形式。这一形式与历史进程中破碎的、间断的人类经验的混乱相对立。《洼地》中的自然和环境隐喻作为元文本意义而起着作用。这一意义与生命的量子相回应。如果历史是间断的,自然延续性向历史挑战,形成小说中显著的后现代矛盾。人类关系的这种文学表现将生态思维投射到小说的中心文学文本上。在这种情况中作为他者的自然受到挑战;作为主体的自然得以接受。这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然和人类融合形成相互联系的主体,或者更精确的说,主体间性。突出这样的主体间性必然导致生态文学话语。《洼地》充分体现出这种主体间性。这本小说通过自然和环境隐喻,将自然和人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地理、生物等生态问题主体化以突出周围现实的变迁。
《石头的礼物》的自然话语建构自然的话语建构,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为敌对荒野,特别是以诗歌和小说形式。其目的就是赋予自然以说话主体的隐喻地位。吉姆•格雷斯的《石头的礼物》中的故事发生在石器时代的一个海滨村子里,其善变过程深深根植与于自然风景中。叙述者的父亲小时候中了一位弓箭手致命的一箭而失去了一只胳膊。此后,父亲长大以后成为该村子的一名讲故事的人。也就是“自编故事以解释人们所受到的伤害”。[12](Grace1997:1)叙述者称赞道:“她的父亲讲故事用词华美。”(ibid.:9)并警告说,“当心父亲的语言,他已经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我们吸引到山上、草地、金雀花地和石榴地……。”(ibid.:9-10)叙述者在讲述她父亲的经历的过程中自觉地利用自然隐喻:燧石的制作和使用。父亲失去一只胳膊以后,他在村子里就失去了干石头活的能力。于是,他就长期在外游玩。回来后,他就把自己的冒险经历编成故事。他的故事就“像梦、像蜻蜓,来了又去,去了又来”(ibid.:56)换句话说,他的语言本身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基本上是小说式的语言。他有讲故事的天赋。他能够“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村子里的擅长讲故事的人”。(ibid.:57)这些表明小说的语言媒介挑战着自然和文学,特别是后现代小说,具有不可通约的思想。小说话语处在决定生态文学模式的后现代小说的生态信息语言中。父亲从自然编造故事创造了“不可建构”的自然本身的版本。换句话说,父亲已经成为自然风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中含有他的语言:独特的、非人类的话语。这样,小说《石头的礼物》是由自然构成,获得了大量的小说意义。通过这些意义,小说将后现代视角和生态视角巧妙地结合起来。情节里没有将人类和自然地关系再概念化,因为自然不被看成是讲故事者文化的他者。实际上,石器时代本身象征着一个自然和文化之外的世界。村民们没有自然和文化分离的感觉。他们就像“石头。你准确地击打他们,他们就像贝壳一样打开”。(ibid.:48)制作燧石,这就是他们全部所知。这也给了他们勇气。
这是保持繁衍生息的仪式。这充实了他们的时间。这又储满了他们的食品柜。这同时又使他们增添自豪。工作使他们舒适……。他们坚如磐石,勇敢、有心计。他们草率地打造燧石。海鸥产下中心不稳的蛋。风从海面上吹来。这就是世界,永不停止思考。(ibid.:35)小说特别强调村民们和自然相处的思想。村民们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二元形式。他们融入自然风景之中。他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被当做颠覆当今自然的结构思想的概念框架的策略。因此,小说能够把自然表现为挑战自然和文化二元对立的生态文学话语中故事的积极主体。因为该故事情节取自石器时代,内外现实之间的界限消除了。因此,人类感情和自然意象融合起来创造了“由生活组成”的故事。(ibid.:105)况且,生态文学叙述不适用那些陈词滥调的术语,如原始的、野蛮的、异教的等,展示其与后现代策略的关系,即违反小说创作的策略。换句话说,自觉的叙事者对讲故事的过程进行轻松的评论,并以此来奚落读者:故事的力量逐渐停止了。我听到他的声音。我知道他的技巧。我想起父亲经常使用的短语。他说:“我们从不知道。
我们只能猜测。”草地中一位小伙和一位女人……。他的听众鼓掌。他使他们高兴。他们如此适应于以大地为依托的事物的心思像云雀、昆虫一样在飞行、跳跃……。要是生命就像一个如此简单、自由、不受约束的故事一样就好了。(ibid.:58-59)整个故事情节中,海鸥、风、岩石、海洋和许多其他自然元素起着小说的后现代创作模式的后生态文学方式的作用。自称为“以大地为依托”的、没有恰当名称的人物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然和文化联通的世界。小说在父亲正要开始讲述一个新的故事的时候戛然而止:他闭上眼睛。他所看到的是叠瓦状海边。傍边是野性的、没人骑的马。他努力想把一只船推到海上去,但没能成功。他尽力用人的声音充斥空中。但是他所看到的一切是风中的马,海滩上激起的一串串浪花。被海水打湿的岩石和石头映射出空中的奇妙变换。没人注意到也没人欢呼。(ibid.:169-70)此时此地,形成父亲叙述的意义完全变成了对人类既不能征服也不敢沉寂的大自然的展现。用这种方法,《石头的礼物》预示着生态意识:自然不是用作社会或语言建构,而被认为是人类经验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可以说《石头的礼物》开辟了后现代小说的生态批评的新的道路,使得自然环境和后现代小说关系研究成为可能。
由于现代生态学对人类和非人类进行明显的划分,后现代小说变得越来越以生态为中心了。本文首先讨论了生态文学话语的生成环境,然后分别对两部后现代小说中的环境隐喻进行了分析解读。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文学研究成为不是与环境相区别的东西而是通过将整体概念、所有有机物、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语境化的方式成为环境不可分割一部分。况且,文学生态主题的语境化,如环境污染、物种的灭绝、滥伐森林、有毒废物污染以及热带雨林的破坏等等,将导致越来越多的生态批评分析。因此,生态文学话语研究在生态批评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采用生态概念进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在促进在文学领域发展更广阔的视野过程。第二,运用生态学相关生态概念和主题于文学批评证明是文学研究的优化过程。后现代小说已经使用生态学和文学之间的平行范式。就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研究而言,该范式亟待详尽的批评研究和评估。随着越来越多的环境理论家们呼吁人文学科的内在转变,文学理论家们不能忽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表现,特别是文学的文化多维性的确影响着环境或被环境所影响这样的事实。因此,现在理论家的脑海中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允许文化和自然作为不可分割的过程来进行研究。这一过程需要接受新的观点和新的领悟:“但是深层生态自我感需要更加成熟和进一步发展,需要超越人类达到非人类的认同。”[13](DevallandSessions1985:65)这严格的思想毫无疑问能激发许多批评家的新的见解和开辟生态批评领域的新的批评道路。#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