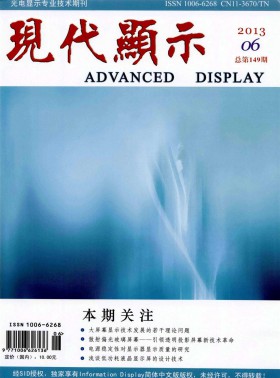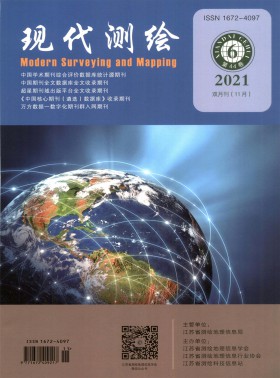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小说的虚构性论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赵攀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一、小说对虚构的演变———从对虚构的回避到对虚构的全面认定
曹文轩在《小说门》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小说史是以虚构开始的。“小说的起源被推至神话,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说法。如果这一说法果真成立的话,那么,小说史的第一步就是踏在虚构的苍茫大道上”[1]86。毋庸置疑,神话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被慢慢演化为小说,作为一种虚构能力预示着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完全可以被创造出来的。然而,在小说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都对虚构躲躲闪闪,努力营造一个小说等同于历史的逼真感。华莱士•马丁曾在《当代叙事学》中写道:“在最好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中,我们为其真实感所震惊:我们也许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翻开书页时会出现什么,但当它出现后,我们感到这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们历来所了解的,尽管也许是极其朦胧地了解的,经验的真实。”[2]67然而,到了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家们终于对真实感到了疲惫,面对哲学上“真实观”的崩溃,小说家们也终于摒弃了真实,开始了对虚无、背离、荒诞、陌生化甚至是零度写作的追求。作者不再扮演“在场者”和“目击者”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形象,而是承认“上帝之死”的事实,小说家不再是上帝,小说家必须直面“说谎者”的身份。戴•赫•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这才是要紧的事。”[3]224米兰•昆德拉也说过:“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的。我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不喜欢太肯定的态度。”[4]66普鲁斯特居然声称,在整本书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5]345。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则更胜一筹,在小说中直接讨论小说写作的虚构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把他看成是英语世界里最伟大的现代作家和第一个后现代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下文简称《法》)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有评论家说,福尔斯的声名大振,不仅仅因为他像托马斯•哈代那样是一个讲故事、描摹景物的高手。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他的小说从不重复同一个内容,文体也因书而异,给人以不断推陈出新的新鲜感。有关《法》的评论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叙事策略,从自由主题到女性主义以及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互文性解读数不胜数,足见其在评论界受重视的程度。笔者在此只对福尔斯在《法》中对小说创作的虚构性进行解读,以凸显虚构性在小说中起到的强大功效。
二、虚构的功效
虚构的功效之一:弥补现实或逃避。虚构就是为了弥补现实。“现实是远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甚至是千疮百孔的,造物主的设计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么多的缺憾,我们一直未能找到补救的办法。而小说的出现,却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与哲学和诗不一样,小说擅长的就是描绘实状。这个实状完全可能是虚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当初出现,就是带了这种弥补现实的天任的。这也成了它存在的理由”[1]96-97。福尔斯在《法》中对莎拉的虚构是为了弥补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莎拉。小说以哈代的诗歌《谜》开篇,女主人公莎拉是一名在眺望大海的神秘的黑衣女子,进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个与维多利亚时代淑女形象格格不入的另类形象。而莱姆镇上的人又把她描述成“悲剧”、“法国中尉的婊子”、“堕落的女人”和“被社会遗弃的女人”各种名词的混合体。而站在她的对立面的欧内斯蒂娜却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淑女。用一个充满争议而且并不漂亮的另类女性莎拉来弥补美丽聪慧看似完美的传统女性欧内斯蒂娜似乎有些荒诞,而这恰恰是福尔斯创作的精妙所在,他在告诉读者一个哲理:世界无真实,缺憾即完美。而具备这么多“缺憾”的莎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希望呢?作者这样来描述莎拉的外貌:“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女人面容是文静、柔顺、腼腆。那张脸不像欧内斯蒂娜的那么漂亮。不论什么时代,也不管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衡量,那确实不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儿。
但那却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一张悲凉凄切的脸。那张脸上所流露出的悲哀,正像树林中所流出的泉水一样,纯净、自然、难以遮拦。那张脸上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情假意,没有歇斯底里,没有骗人的面具,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经错乱的痕迹。”[6]35作者宣扬的是莎拉的一种自然美,悲剧美。而她对男主人公查尔斯的吸引又远非如此,莎拉具有和男人一样的思想和情怀,查尔斯对莎拉不仅有同情还有敬佩和某种相近的感觉。而莎拉本人对莱姆镇上的人对她的误解和诋毁却抱一种漠然的态度,她心里想,“侮辱也好,指桑骂槐也好,都不能动我一根毫毛,因为我已把侮辱和指责置之度外了,我一钱不值,我几乎不再是人了,我只是法国中尉的娼妇”[6]177。莎拉具有在逆境中生存的决心和勇气,她在“法国中尉的娼妇”的恶名下获得了一种自由,她的离经叛道、不合时宜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她的恶名成了她的避难所。也恰恰是这一点让她不仅对男主人公查尔斯而且对读者都具有一种像谜一样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说福尔斯虚构的莎拉是对现实中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众多莎拉的弥补,那么男主人公查尔斯身上却有很多“逃避”的痕迹。当然我们首先要重新理解“逃避”。曹文轩的观点是“小说带领我们背弃现实,而逃避到它所构造的世界之中。小说成了焦灼心灵的港湾和荒漠面前的绿洲”[1]97。在《法》的前十二章,福尔斯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写作方式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模仿,其中在第四章他全知全能地告诉读者查尔斯个什么样的人,“读者们将会看到,查尔斯有好高骛远的毛病。聪明的懒汉为了证明自己懒得有理,总是要好高鹜远的。总而言之,查尔斯有着拜伦式的游手好闲,却没有拜伦那些发泄情感的途径:作诗和寻花问柳”[6]56。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查尔斯无法逃避作者对他的安排和评价,这是传统小说的惯用手法。然而到了第十三章,福尔斯完全换了一种口吻,承认作者的无能为力,他不仅不知道莎拉是谁,她从哪里来,而且对查尔斯也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在文中写道,“一个计划的世界是一个僵死的世界。只有在我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开始不受我们的约束时,它们才开始变得活生生的。#p#分页标题#e#
当查尔斯离开站在悬崖边缘的莎拉时,我命令他直接回莱姆镇去,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转身走下坡,无缘无故地到牛奶房去了”[6]128。当代小说里的查尔斯逃避了作者固有的安排,小说人物从作者笔下逃脱出来,有了自己的主见,获得了人物该有的选择和自由。然而查尔斯对莎拉的态度却是一直有所回避的,尽管莎拉的叛逆和孤独、不明的身世和复杂的经历对他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可他总在提醒自己不能和这个女人太过接近。在第十九章的末尾作者道出了他的心声:“而经过自然选择的查尔斯却非常聪明,头脑清醒,自由自在,像永远闪烁的明星,对一切都能理解。唯独莎拉,他不能理解……”[6]163对于查尔斯最初对莎拉的逃避读者无可厚非,那个时代的查尔斯就应该是那样的,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安度一生。然而作者笔下的查尔斯却要横跨两个时代,现代的查尔斯不允许他总是躲着,查尔斯重新开始了思考,面对莎拉对自己境遇的漠然态度,他惊住了,“查尔斯在那儿呆呆地站了半晌。那女人好比是大门,男人却没有钥匙”[6]205。后来莎拉主动联系查尔斯,说是引诱也好,她在帮助查尔斯打开桎梏,找到那把“钥匙”。从《法》中的第十八章中读者可以了解到查尔斯的多种性情,“对于这一现象,从生物学上解释,就用得着达尔文的一个术语,叫做‘保护色变’,即学会与环境协调一致,以便求得生存。年龄变了,社会地位变了,相应的变化也就势在必行。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保护色变已成公理,极少有人提出疑义。然而,莎拉的目光却充满了疑义。它直射查尔斯,但也有着胆怯的成分。这种目光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现代术语,叫坦白交代,‘查尔斯,坦白交代!’它要求他去掉自己的保护色变,迫使他的内心失去了平衡”6]155。查尔斯最终在莎拉的目光下妥协,放下防卫,具备了新的勇气。他最终解除了和欧内斯蒂娜名存实亡的婚约,放弃了一成不变的生活。然而莎拉并非只为了拯救查尔斯而存在,莎拉注定要离去。莎拉的离去却让新时代的查尔斯毅然决定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小说至此,莎拉拯救查尔斯的任务已经完成。查尔斯的“逃避”有了新的意义,他不仅从一成不变被安排好的婚姻中逃避出来,从贵族的身份中逃避出来,也从作者的笔下逃避出来,在新女性莎拉的帮助下成为一个追求梦想、敢于直面一无所有的人生的人。
虚构的功效之二:保持人类的想象力。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过:“想象力的自由除了受制于感性外,从有机结构的另一极看,它还受制于人的理性。崭新世界或崭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大胆的想象,仍然是由概念指导的,仍然遵循着代代相传的、精织于思维发展中的逻辑历史。”[7]111这一论断无可厚非,然而与此同时也恰恰是因为概念太多反而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关于这一点曹文轩说过,“知识史,实际上是好知识与坏知识对抗甚至是恶斗的历史”[1]99。他认为“坏知识最可诅咒的地方,是它破坏了人的想象力。它让无数的僵死的、违背人性的甚至是充满恶毒的概念,成为数不胜数的可怕的藤蔓,对人的想象力进行千缠万绕,甚至使想象力枯萎。我以为人的最大悲剧,既不在于爱情的毁灭,也不在于事业上的一事无成,而在于想象力的损伤与衰竭”[1]99。而这正是小说存在的意义,“因为小说是对想象力的操练,并激发起人对想象力的留恋。它是为数不多的可将人的想象力保持住的办法之一”[1]99。《法》中最具想象力的虚构当推它的三个迥然不同的结尾。第一个结尾在第四十四章,查尔斯选择离开莎拉,仍与欧内斯蒂娜结为连理,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第二个结尾在第六十章,查尔斯历经磨难后终于找到莎拉,找回了梦寐以求的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三个结尾在第六十一章,查尔斯虽然找到了莎拉,莎拉却拒绝了他。莎拉选择在一个叫罗赛蒂的拉菲派画家家里从事艺术工作,作者此时还设计了一个叫“拉拉治”的小孩出场,查尔斯在懊恼和疑惑中离开,真正开始了在生活洪流中的自由选择。对于“拉拉治”的出场,作者给予了这样的解释:“时间已经证明,小说家是不在自己作品的结尾引进新的人物的,除非这个人物无足轻重。我想,拉拉治的出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6]521拉拉治的出场虽说无足轻重,但是也增加了莎拉的独立精神。
无论是莎拉还是查尔斯都没有什么最终的结果,福尔斯给了他笔下的主人公以充分的自由,也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他不再去操纵小说里任何人物的命运,虚构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作者只想说明世上并无“决策者”这样一个道理:“我绕了一个大圈子,实际上还是回到了我本来的原则:像本章的第一条引语所说的那样,世间万物的背后,并没有支配一切的神仙。”[6]545其实早在第十三章里,作者就承认了他的虚构:“我讲的故事纯属想象中的虚构。我塑造的这些人物只存在于我的心目中。如果迄今为止,我仍然假装我对我创造的人物内心深处的种种思想深有了解,那是因为我写作的手法是我写的这个故事的时代所普遍接受的。在那个时代,小说家仅次于上帝。他不见得什么都懂。可是,他总是想方设法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什么都懂。但是,我却生活在产生了阿兰•罗布—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时代。如果这是一部小说,它不可能是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6]101这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元小说”创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8]238。李丹在其论文中也说道:“福尔斯在1973年出版的《诗集》中论述了小说的虚构性和游戏性:‘小说与谎言是最亲密的表亲。’”[9]90然而这种虚构和谎言却意义重大,曹文轩曾阐述过,“小说家是骑士,是堂吉诃德式的骑士。他们骑在虚构的马背上,不仅走遍了现实,还走进了现实疆域之外一个无边无际的虚空”[1]101。福尔斯在《法》的结尾处其实也彰显了这种虚空,既像是在劝说查尔斯,又像是自言自语,更像是告诉读者要用新的眼光来欣赏小说:“虽然莎拉在某些方面似乎完全适合扮演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的角色,但生活并不是一个象征,并不是一个谜,不是一个猜不透的谜,生活并不是执着追求某一个人,不能看作一着失算便满盘皆输,更不能立即轻生;生活应当是忍受———尽管在这无情的城市中忍受是何等的无益,何等的无效,何等的无望。再说一遍,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那深不可测的、苦涩的、奥妙无穷的大海———”[6]556福尔斯在小说创作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毋庸置疑,更可贵的是他的创作带给读者以无尽想象的空间并激发了读者和其他作者或许早已缺失的想象力。#p#分页标题#e#
三、对虚构的现代性理解
关于对虚构的现代性理解,笔者想再次引用曹文轩的观点:“对虚构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最彻底的理论支持是:存在即虚构———存在便是不真实的。”[1]107被称为“哲学小说家”的福尔斯自然受到过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僵死的哲学,而是一种实用的个人主义哲学,它帮助人们在特定的处境中得以生存。莎拉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即她可以在一系列虚构的名分下生存。她虚构了自己和法国中尉有一段不堪的恋情,虚构了不为众人所接受的一些虚假事实,当查尔斯真正走近莎拉时发现她原来还是一个处女,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她却从不去辩解。也就是说莎拉可以活在虚构中,却不能活在真实中。正如陈静所言,“莎拉似乎只有在假面之下才能真实地安置自身。她似乎是同性恋者,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查尔斯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他的陷害者;她似乎是贞女,又似乎是荡妇。福尔斯不断地建构她的形象,又不断地消解她的形象”[10]99。莎拉实存的表面真实与实存的底部真实完全不一致,甚至是互相拆台、互相消解的。福尔斯在《法》中对莎拉的创造彻底揭露了存在的虚构性。现代小说的虚构也体现在它的反逻辑倾向上。
“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被保守势力视为反理性主义,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对逻辑的回避与轻视。由反逻辑而生发了其它许多现象:反说教,反解释,反清晰……”[1]111《法》这部小说无论是人物的创造、情节的安排,还是极具特色的结尾都具有很强的反逻辑性,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似乎不按常规,都似乎超出了读者的预料。对小说本身加以怀疑是现代小说推出的重磅炸弹,“它把世界的虚构性推向了极致”[1]113。在《法》中福尔斯不仅揭露了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而且还混淆了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书里书外分不清楚。“一切变得不可确定,如雾中之人,梦中之事”[1]114。作者与人物的混淆主要体现在作者时而是叙述者或者是讲故事的人,时而又跳进书中扮演一个角色。《法》中的第五十五章,作者就以一个大胡子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福尔斯和男主人公查尔斯在同一列火车的车厢内不期而遇,双方都抱以冷漠的目光。查尔斯对作者福尔斯的印象是:“这家伙肯定是个让人讨厌的男人,一个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因此,如果他想同我谈话,我一定会断然拒绝。”[6]316福尔斯原本打算“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生涯,让他永远地停留在去伦敦的旅途中,以此了结这个人物的存在”[6]316。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对人物进行了放手,把自由交给人物,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和命运。人物和人物的混淆主要体现在一个人物的多重身份上。小说的第三十八章中这一特点最为明显,三个时代的查尔斯同时出现:“一二六七年,查尔斯带着法国人的新观念在寻求圣杯;六百年后,即一八六七年,查尔斯对经商颇为反感;今天的查尔斯可能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他对那些善良的人道主义者的大声疾呼充耳不闻,那些人自身已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人们可能觉得这三个查尔斯之间毫无联系。事实远非如此。他们都反对‘占有’是生活的目标这一见解。”[6]248当然这里的查尔斯并不指某一个人,而是指当时的任何一个英国人。
主人公查尔斯与三个时代泛指的查尔斯完全混淆,小说的虚构也达到了极致。福尔斯在《法》中对小说虚构性的探讨无疑是现代小说写作的典范。推而广之就可以说虚构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现代小说,那么现代小说作为一种虚构之物有何存在的意义?再次引用曹文轩的一句话,小说带给我们的“仅仅是精神上的快感、智慧上的磨砺、美感上的熏染,而并不能帮助我们去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小说不能成为研究所、勘察队与移民事务局”[1]110。彰显虚构的小说也是一种文学欣赏,而“文学欣赏,本就是一种非功利、非物质性的精神遨游,它们到底是实在还是非实在,一切都无所谓”[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