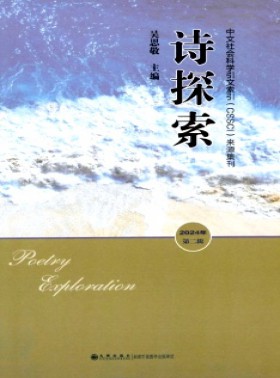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探索国外后现代小说翻译策略,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温玉霞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1.引言
后现代主义作为全球性的文化思潮,倡导怀疑、颠覆、否定、反思、批判、解构等理念,影响到语言、文学、哲学、文化诸领域,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股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和美学模式,向文化研究转向。翻译的功能发生转变,翻译“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述功能,而带有了范围更广的文化翻译和理论阐释功能”(王宁2009:168)。翻译研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和文本结构分析层面,而更多关注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翻译与接受,即关注翻译文本背后隐藏的各种文化、政治、人类学等意识形态,从广阔的文化层面审视和研究翻译。翻译研究领域扩大,视野拓宽,翻译研究呈多元趋势,也“更富审美成分”(谢天振2007:9)。
可以说,正是翻译研究这种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从跨文化角度进行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才成为可能。本文拟从跨文化的视角,以当代翻译理论为依据,就跨文化“混杂—引文”(гибриды-цитаты)表现方式的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等展示出的后现代小说特征,说明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实质和翻译目的,研究在小说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力图将宏观的翻译理论思考和微观的后现代小说的具体翻译操作结合起来,避免翻译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拓宽翻译者研究视野,为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应对策略。
2.俄罗斯后现代小说与翻译行为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再现过程,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活动。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创作出带有“混杂—引文”特征的后现代小说。这是一种跨文化、非线性、开放性、多元化的文本。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就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书写行为。而这种书写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功底、储备有关的文化知识、相应的“语言能力”、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和“文学能力”,并在正确地识别和理解(解码)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准确地阐释和表达(重新编码)。解码和重新编码是翻译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都是一种翻译行为。识别和理解既是翻译活动的必经之路,也是译者准确阐释和表达的前提。翻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翻译行为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传播。
“混杂—引文”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被广泛运用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创作中(Скоропанова2000)。它以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拼贴等跨文化文本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互文性”特点。“混杂”(hybrid,гибрид)也可译作“混合”或“杂合”。“引文”(quot,цитата)是结构主义发展到早期的后结构主义的结果,由此引出了“互文性”。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分析作品中存在的混杂的多语现象,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阐释了同一部小说中不同语言方式的共存交互作用,以及使用这种多元语言评价现实的不同方法的共存互动,即“多声部”或“复调”现象,并以文学狂欢化的观点支持对话理论。法国理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受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狂欢化理论的影响,从巴赫金的狂欢化概念中找到了在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由此推导出“互文性”这一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作为任何文本的成文性在于同该文本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联,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在差异中形成自身的价值。随后,法国理论批评家罗兰•巴特又提出“主体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的概念。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理论批评家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受前经典的影响,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文本发生作用,有前文本的痕迹。无论是吸收、肯定还是破坏、否定,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或文本间性。
“互文性”旨在打破结构主义文本的孤立和封闭性,具有开放、动态、多元、各种文化兼容的特点,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将翻译研究的对象从文本内引向文本外,从跨文化和对话的角度对翻译作品、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行为和特征等进行研究。译者主体地位的突出,显现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说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1987:137)、勒弗菲尔认为的“翻译是一种改写”(王宁2009:173)。译者的翻译行为,即翻译的基本机制中的理解和诠释,以及表现机制中的决策和表达,彰显了翻译学的综合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和狂欢化理论、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将这种“互文性”运用在文学创作中,称其为“引文的文学”,或“混杂—引文”。“混杂—引文”体现了将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中的互文性关系,是一种具有跨文化特点的文本。因此,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实质就是语际间的另一种二度书写行为,是跨文化文本的转换,是一种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交流和传播的行为。识别和理解是阐释和表达的翻译活动的前期准备,也是翻译活动交流和传播的前提,它们都是一种翻译行为。在“原作者—原文—译者(读者)—译文”这条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互动链上,译者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一名特殊的读者,译者只有在正确识别、理解和解读原文、与原作者和原文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阐释原文,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原作者的创作主旨。在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关系、跨文化特质、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后现代诗学特征熟悉和了解,为翻译活动的理解作前期准备并进行各种调研,以便获得“一种自上而下的把握,一种阅读前的语境准备”(王东风2009:22)。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以“混杂—引文”的跨文化文本建立了特别的文化地带,如尤里•洛特曼(ЮрийЛотман)所说的文化“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即多个文化符号体系的总和,建立了具有“根块”①特点的跨文化模式。其中韦涅季科特•叶罗费耶夫(ВенедиктЕрофеев)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就是一部由文化符号组成的“混杂—引文”文本。小说以游记的形式写成,每个章节的标题都是途径的地名和站名,小说中大量的引文、熟语形成了内涵各种文化编码的文本,构成了后现代的“根块”文本。小说不仅引用《圣经》故事、古希腊神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历史文化典故,还引用了文学作品中的忏悔和游记形式,引用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献、教父的警句格言、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论文、马列经典话语、苏联官方文化中各种政治宣传性文字、口号标语、现实生活话语等,这些引文在语言内层面和文本生产层面有了跨文化的符号,构成了多种文化符号融合在一起的跨文化文本。原作者在征引典故、再现神话原型的同时,解构和化用②了人物,其中既可见到对“亚伯拉罕迁居迦南”、“摩西出埃及”、“约伯记”等的模仿痕迹,又可见《新约》中有关基督耶稣“福音书”的影子。一切模仿痕迹和改写都消融在原作者“讲述”和“显示”的人物、情节的叙事戏仿里。这种“混杂—引文”虽然给译者或读者的理解和阐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一个展示意义的开放式、流动性文本,但原文本中大量引语和典故的运用增加了译者或读者阅读、识别和理解的难度,特别是破坏性的模仿和改写甚至使“混杂—引文”成为“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增大了对原文本互文性隐喻的破译难度。如果译者不了解引文和人物对话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作者的用意,也难以将原文的内容准确地翻译出来。译者要忠实而准确地将原文叙事的信息挖掘、显示出来,首先要跳出语言和文本结构层面的分析,从文化层面解读原作者创作的意图、戏仿《圣经》的目的。#p#分页标题#e#
原作者试图从人类文化根基开始看待人生存的意义,通过戏仿《圣经》讲述的人类发展史向读者展示“一神论”、绝对权威的“上帝观”③对人类思想、行为影响至深的原因和过程,结合现实的黑暗从“原罪”的根子上更深刻而巧妙地剖析苏联一元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绝对权威、唯一真理对个人行为、思想、心灵的影响乃至扼杀的整个过程。只有认识到翻译文本背后隐藏的对某种文化的质疑,(即对当时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小说模式、以及价值层面上体现出的各种道德和追求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是对僵化概念式的文化思想和思维模式的挑战,又是对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解构、否定和反抗,)译者才能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从事翻译活动,明确翻译态度和立场,才能将原作者解构、否定和颠覆思维方式的权威性、理性的绝对主义的创作理念准确地挖掘、转述出来,将原文解构“为何好人命运多舛?”、“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何在?”的道德说教性寓言的戏仿内容显现出来,以达到与原作者和原文本信息“动态对等翻译”(廖七一2006:87)的“审美”互动。
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主人公维涅奇卡(Венечка)与醉鬼们在车厢里的聊天、对话,从俄罗斯音乐家、艺术家,到作家、社会活动家,从俄罗斯歌剧、文学艺术到西方哲学、世界文学艺术等,涉及范围颇广。原作者将“我与我”、“我与你”、“我与他”的对话形成的互文关系作为文本书写的一种策略,这种互文对话里包含着许多文化寓意,显现了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杂合功能,即语言指涉意义和特定文化描述意义的功能。这些“互文性”的文化隐喻既要求译者(或读者)具有熟悉文本语言指涉“意义”的“语言能力”,又要求译者熟悉特定文化和文本描写系统,即要求读者在转译文本、解释文本“意义”符号、破译文学文本意义时,译者与原作者一样置身于各种对话中,运用译者储备的文化知识和经验,调动译者的审美感受力和描写的“文学能力”,这样,阐释和表达才能准确、忠实和顺畅。俄罗斯后现代小说还体现了文本之间复杂的内在交互关系,消解了传统文本、文本结构、文本意义和作者,导致“作者之死”、“文本之死”。作者不再是原创者,他的写作只是在无数个互文交织体上对前文本回收、位移、改造、修正和重组,传统意义上可谓作者“死亡”。这种隐藏着无数个互文织体的文本,既期待着读者的阅读、理解和阐释,又期待着译者和译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阐释。译者的主体地位得以显现,他不仅是阅读者,还是文本的阐释者、创造者,甚至就是文本本身。译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翻译文本都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翻译是理解的过程”(廖七一2006:136)。弗拉基米尔•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Сорокин)的小说《罗曼》(Роман)引用了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品的情节、人物和作家的创作风格。
作者既借用屠格涅夫式的爱情和风景描写、冈察洛夫笔下的乡村生活细节描写,又借用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布宁小说中的贵族庄园描写等,这些经过改造的情节的描述形成了一种肯定的内在互文关系。而勇敢、坚定、道德完美的男主人公罗曼(Роман)和圣洁的女主人公塔季扬娜(Татьяна)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罪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形象的改写,是对他们的戏弄,这个戏弄又显露出小说否定的互文关系。由肯定和否定形成的内在的互文关系就是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的反思、解构和颠覆。面对这样复杂的“混杂—引文”,译者既要熟悉原作者引用的前文本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又要了解内在互文中每个被借用的作家的风格,理解原作者是如何对前文本再现、位移、修正和重组。在翻译的理解过程中,译者解读原作者如何为自己创造“凶杀”、“死亡”情节的想象力开辟空间,在译文中以“异化”中的“直译”完全保留和再现主人公罗曼野蛮、荒诞的杀人行为,而在翻译的表达过程中以“归化”中的“意译”阐释“混杂—引文”文本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并将原文本崇高变成低级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仪式的“解构”主旨转译出来。
俄罗斯后现代小说既有高雅的诗歌、小说、戏剧文学语言,又有低俗的性行为描写、骂人话、官腔,高雅的谈吐和庸俗的语言、行为混合在一起,显示了文本的间杂性,构成了多重的反讽。翻译的任务就是在这种差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语言和文化的转换中准确地将文本的间杂性和多重意义传递出来,根据译入语接受的文化语境,对小说中的各种叙事话语变通、转换,即保留原文人物对话构成的叙事内容,压缩、增减类似精神分裂者使用的超现实叙事话语,同时也没有破坏原文的跨体裁的反讽话语的后现代风格。
3.跨文化“混杂—引文”的表现方式与翻译转换策略和翻译方法
俄罗斯后现代小说是一种跨文化的“混杂—引文”,它以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的方式表现出来,展示了俄罗斯后现代作家文化对抗解构和重构的策略,呈现出非线性、不确定性、片断性、对话性和多元化等后现代小说的诗学特征(温玉霞2010:69-73)。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引起译者(或读者)从文化角度理解和阐释的欲望。从这个角度论,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跨语际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也是对跨文化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再现和表达、交流和传播,即语言和文化信息在转换过程中译者与原作者和原文内在意义共鸣互动。这种翻译展示的“不仅是语言文字层面上的意义转述,同时也是文化层面上的文化阐释和再现”(王宁2009:34)。德里达主张用“转换”替代翻译,主张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廖七一2006:78)。正是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翻译中的跨文化文本功能的转换和翻译交际目的所需,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转换”。从宏观上看,翻译转换策略是对文本的文化阐释和再现,从微观上论,翻译转换策略就是对文本翻译的具体操作和方法。因此,本论文探讨的翻译转换策略既是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文化价值取向的翻译,又是其语言和文化信息转换的具体翻译操作,更是对跨文化“混杂—引文”诗学特征中表现方式的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的具体应对,或者说,是一种对策、方法或技巧。#p#分页标题#e#
3.1体裁种类间杂与翻译“增值”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超越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各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超越各类艺术传统的界限,模糊和衍化了文学艺术边界。在他们的小说中以事实与虚幻结合,科幻与虚构结合,神话与虚构结合,小说与诗歌、戏剧、书信结合,小说与非小说形式结合,高雅文化与通俗艺术结合,小说与音乐、绘画、多媒体等结合,形成了跨体裁、多意义、开放性、多元化的体裁种类混杂的文本。这种文本意义多重,意义难以确定,因为文本不是固定和封闭的,而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创作理念的复杂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形象的多义性、语言表达的不确定性等给译者或读者提供了理解、阐释和创造的开放空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阐释原文,以德里达所谓的“嫁接”方式,在“延异”和“痕迹”中寻找文本的多重意义,将翻译行为变成一种“增值”、“增添”和“播撒”,将那些不在场或语言中被丢失的、遭压抑的信息传递出来,进行多意义的选择、删除和补充,在破译蕴涵其中的多重含义中进行语言转换。韦•叶罗费耶夫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式的跨体裁小说,既包括神话、史传、小说,又包括抒情诗、戏剧等,是集智慧文学、先知文学、启示文学于一体的体裁种类混杂的文学读本,具有多意义、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异化”的方法保留原作中的“我与我”、“我与他”的复调对话内容,保留原作者以哲学笔记谈论哲学家,以回忆录谈论革命历史人物,以诗体小说谈论歌德、普希金、屠格涅夫的爱情小说,以侦探小说的手法寻找装酒的手提箱,从回忆历史上沙皇戈杜诺夫杀死王子的历史事件联想普希金创作的《鲍里斯•戈杜诺夫》话剧,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来谈论街道的命名,以酒的配方谈论对人生的看法等。然而,原文在引用民间文学、经典作品、官方报纸宣传语中糅合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家的格言、名句等“痕迹”中,进行了改写,译者以意义“增殖”的方法填补各引文间留下的意义空缺,从主人公对“引文”评论中以“注解”和“阐释”方式传递出原作者对一元真理的怀疑、否定和批判的思想。译者以主人公的鸡尾酒配方作为文化转换的“增值”对象,对配方的组成元素一一“增注”或进行阐释,在阐释中破译配方隐含的“重构”意义,即原作者建立一个自由、公开的和谐世界的愿望,将“重构”的创作主旨翻译出来。索罗金的长篇小说《蓝油脂》(Голубоесало)是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种类间杂的文本。从西伯利亚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的日记开始,叙述者话语由观察克隆人生成的过程转为克隆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及其作品的话语,出现了诗歌、戏剧、小说各种体裁种类混杂的叙述话语。同时,小说的叙述者又承续、发挥着双语词典阐释的功能,在俄语叙事中加入了汉语—俄语音译、未来语、地方方言、法语和德语词典,多语言扩展了跨体裁的空间,使小说文本成为种类间杂的多变体,也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具有时空不确定性、叙事非线性、结构片断性、体裁合成性的特征。面对这样一个多语言、多文体的“混杂—引文”,译者在译文中要以“套盒”效应保留原作中的文本套文本的文体综合形式,以“误读的误译”将被克隆的作家的新作缺少章节间的过渡,以及被篡改了的作品名称、人物台词、时间、地点等信息转换出来,以便保留原文的“混杂—引文”风格。在翻译过程中,以“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中的汉语—俄语音译、未来语、地方方言、法语和德语的多语现象,并采取补偿措施,如用括号中的解释性成分或注脚等方式,使译文保留原文多语混杂的特色。译者在文类转换、游移、交错、合成的过程中以“增殖”、“增添”的转换方法,将原文所叙述的情节毫无关系的那些模拟的小说、戏剧、诗歌、学术味十足、用语庄重的试验配方和菜单所隐含的多重意义传递出来,以保留原文的“解构”特征。
3.2语言游戏与翻译对策
苏联学者鲍里斯•格罗伊斯(БорисГройс)说,“任何语言,包括艺术语言,都只是我们潜意识的形式,基本不受最终记述的控制:不是我们在支配语言,而是语言在支配我们”(Гройс1993:8)。俄罗斯后现代作家追求语言的差异性和多元化,运用语言游戏及其相互之间不可化约性对抗传统社会寻求统一性和同一性的力量,创造出多语混杂的文本,在“世界如文本”的游戏中显现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多元性。译者要将这样不确定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信息转换,分析、调整原文中各种“异质材料组合”,将原文中杂乱无章、毫无关联的多语成分重新整合,根据目的语(译入语)接受的语境,采用相应的翻译对策,有选择性地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进行调整,对重复的句子和语篇进行简化、压缩、增减或删除,并尽可能地揭示文本隐含的许多可能的意义、隐藏的程式及文本的潜意识面。语言游戏展示了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话语特征———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杂合。俄罗斯后现代作家通过语言游戏表达其“解构”主旨。后现代小说的语言游戏使得文本的意义多重、不确定,结构不完整。在德里达看来,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的翻译行为都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译者面对的是句法不规范、语义不一致、句子中断或语句连续不断、无标点符号的语篇和段落、字句重复、任意分行、字谜游戏等组成不连贯、碎片性和开放性的游戏文本。以后现代作家索罗金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混杂和引用了诸多的语言游戏和符号游戏,几页里玩弄不成语句的“a”字母重复组合,用字母组合拼贴成毫无意义的新词,甚至干脆出现连续的空白页,或是连篇重复一个字母,或用一个不断重复的词或词中的字母拖延的“结巴语”,这些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的病句类似精神病患者语言,恰恰表现了文本的不连贯性、随意性,保留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原创作的后现代风格。如短篇小说《达华一月》(МесяцвДахау),每个篇章、段落以顶格开始、无标点符号,以俄文元音字母“а”、“о”、“е”与辅音字母组合的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甚至是空白和无内容的片段、由“ненадо”文字游戏组合的金字塔图案和倒三角图案。这无疑增加了译者的理解和解读、阐释和表达的难度,也是对译者翻译能力的一种挑战。翻译是语言间和文化间差异的调和,在这种差异调和中,译者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接受语境,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和禁忌、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对原文本中多篇幅的空白页码的文字游戏进行解码,在解读过程中,以文化信息的“删减”或“增值”,对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进行删除,或对文本隐藏的信息空缺进行增补,对原文被重复字母断裂之处进行修复,将重复语句压缩,将其内涵的多重意义破译出来,在信息转换中以“归化”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改译。#p#分页标题#e#
3.3拼贴与翻译“连贯”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运用时间上的“精神分裂症”或句法上的“符号链条的断裂”(拉康语),将各种典故、引文、外来表达法等拼贴在一起,以“梦中套梦”、“小说套小说”等“套盒”形式展示由谎言、混乱和虚像构成的现实,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线性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小说凝固的形式结构,创造出了时序交错、空间不定、片断性和非线性的拼贴文本。翻译操作既是语言的操作过程,又是信息的传递过程,即对不同编码符号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在这个解码和编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连贯”对具有拼贴特点的后现代小说的翻译活动起着决定的作用,它既是对原文正确性的理解和解读,又是对原文忠实和顺畅的表达。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代表性作家维克托•佩列文(ВикторПелевин)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ЧапаевиПустота),完全是由梦幻穿插、组合、拼接的一副后现代文化图景。原作者在“与文本游戏”和“与读者游戏”的文本中留下了空白和缺环,等待读者去弥补和填充,对原文的编码进行解码和重新编码成为翻译的主要任务。原文本的不连贯性、随意性、颠覆性的改写和颠三倒四的拼贴打破了译者(或读者)常规的阅读心理和习惯,译者也游荡在原文本的主人公彼得的两大梦幻记录中:一个梦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国内战争时期的恰巴耶夫部队,一个梦是苏联解体后不久的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翻译“连贯”指译者的正确和准确的理解、忠实和顺畅的表达。面对这种由两大时空大叙事和各种梦幻小叙事拼贴而成的文本,作为特殊身份的译者,“连贯”的解读首先就是要理清拼贴文本的非线性结构,可将原文的时间和空间的跳跃适当调整,理顺原文本叙事结构,分析主人公彼得的往来穿梭的梦幻情节以及梦幻中的梦呓,其意识的内在现实与周围外在现实世界的交织构成了两个时空层面上的叙述。其次,要对大叙事和小叙事梦幻穿插构建的文本结构的“空”进行正确的解读,整个小说始终在表达一个“虚空”的思想,即由生命意识的“虚空”和精神状态的“虚无”主题拼贴而成的文本。也许出于此考虑,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将该小说书名翻译成《夏伯阳与虚空》。最后,译者在详细分析、正确“连贯”解读、准确把握原文信息内容的基础上,进入翻译的“连贯”表达阶段,即用目的语的顺畅语言将原文信息转译出来,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本中的后现代文化图景,将原文本“空”表现的苏联解体后社会失衡、伦理失衡导致普遍精神危机的内涵忠实而顺畅地表达出来。
4.结语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再现过程,是译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活动。翻译研究涉及范围广,它作为一种复杂的跨语际、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活动,具有综合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俄罗斯作家创作出带有“混杂—引文”特征的后现代小说,具有跨文化的“互文性”特点。对其翻译就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书写行为,是语言和文化信息的传递、再现、交流和传播。在跨文化视域的翻译活动中,一切都是文本,原作者、原文、译者(读者)和译文都是文本,处在相互作用、开放的、动态的、杂合的互文运动中。译者作为特殊身份的读者,其主体地位正是在翻译活动中得以“显现”和确定。译者的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都是一种翻译行为,它们彼此关联、互为前提。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翻译中的文本文化转换功能和翻译的交际目的决定了翻译的转换策略,它既是宏观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翻译,又是微观的具体的翻译操作,更是对跨文化“混杂—引文”诗学特征等表现方式的一种应对。译者以实现翻译交际目的为前提,在翻译活动中采取相应的翻译对策,运用具体的翻译方法或技巧,忠实地将原文的创作主旨转译出来,达到交流和传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