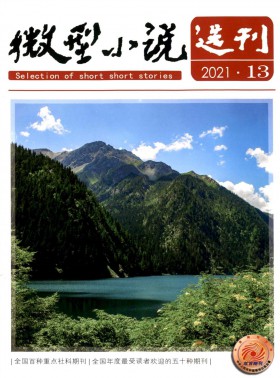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说透露的叙事理论和文学史意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毕飞宇自1991年《孤岛》的发表走向文坛,在早期写作中,带有明显的“先锋实验”色彩,虽然在文学史中毕飞宇被冠以“新生代”作家,可他的前期写作如《那个男孩是我》、《五月九日或十日》、《充满瓷器的时代》等小说则显示了和1980年代的先锋写作者们遥远的呼应,而长篇小说《上海往事》的历史叙事和《那个夏天、那个秋天》的青春叙事则被淹没在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海洋中。但自2000年的转型之作《青衣》始,毕飞宇的写作开始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世界与叙事风格,此后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从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到长篇小说《平原》,更是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当代文坛重要小说家的位置。本文试图探讨的正是毕飞宇的这一系列写作所构建的文学世界、呈现出的叙事伦理,及其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 一、“启蒙”叙事之外的复调民间史 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乡土书写从新文学的开端时期就成为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一翼。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作家以现代知识者的“启蒙”姿态回望乡土,发现了乡土的“蒙昧”与“麻木”,寄予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与焦虑。 以30年代的沈从文为典型“,离乡者”通过对乡土的“田园牧歌”想象,寄寓了对当下中国的“深忧隐痛”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与热望。 而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赵树理”方向,则呈现出乡村叙事与“左翼”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乡土文学的政治化书写的先河。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三个重要脉络,这三个脉络上的乡土文学书写在知识谱系上分别与“启蒙”“、审美”“、革命”的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知识谱系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式的乡土书写,在被不同的知识资源和精神姿态重新建构。 在这样的知识脉络上来考量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乡土小说,就会发现毕飞宇的乡土书写的独特之处。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乡村既不是承担被“启蒙”的蒙昧与混沌之地、不是美丽的田园牧歌,也不是“革命”主题下新旧势力的冲突或“明朗的天”的“解放”叙事。“王家庄”虽然在时间序列上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密切相关,但毕飞宇的乡土书写搁置了“”的苦难和悲情叙事,而是还原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史。 在毕飞宇建构的“王家庄”的小说世界中,启蒙话语遭遇了对抗与质疑。在“王家庄”这个封闭的空间中,“乡村”和“城镇”并未构成乡土书写中典型的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也并未在文明/落后、现代/传统、乡村/都市等话语谱系中展开叙事。你很难用蒙昧、落后等来定义“地球上的王家庄”。在“王家庄”,琐碎的日常生活和被政治浸染的生存状态共时存在,青年们旺盛的生命力与青春无处安放的躁动缠绕在一起,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革命伦理互相渗透又互相背离。叙事者似乎就是生活在“王家庄”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是“玉米”、“玉秀”“、端方”、“曼玲”的邻居,是他们的朋友。他娓娓讲述着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讲述着民间大地上混沌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讲述着青年们内心隐秘的激情和在世界面前左冲右突但不免再次陷落的处境。可以说,“王家庄”作为一个完整的美学意义上的乡土世界,并不是写作者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写作者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是在对乡土民间的书写中,透视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的乡土书写从个体经验出发但超越了个体经验,从乡土出发但同时也超越了乡土。 在20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不管是“启蒙”“、审美”还是“革命”的乡土,在小说中往往有一个作者的声音在说话,或在启蒙理性下召唤古老的乡土中国的觉醒、或在美学意义上对田园牧歌的由衷抒怀、或在革命实践中对乡土进行询唤。但在毕飞宇的乡土小说世界中,不是“独语”而是“复调”构成了他小说的基本言说方式。从《玉米》、《玉秀》到《平原》,毕飞宇让他笔下的人物自我说明,也就是说,在毕飞宇的乡土小说中,人物不是他表达自我理念的对象化存在,而是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意识和心灵体察。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复调时,认为“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①。 他们是他们自己,甚至于他们的人生选择并不受作者意识的支配、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在《玉米》中,玉米的精明老到,使毕飞宇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爱玉米吗?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怕她。”②为什么玉米让作者“害怕”,我想,因为玉米不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不能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来控诉黑暗的封建礼教,玉米也不是《边城》中的“翠翠”,以那个湘西如此纯美善良的女孩来指认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玉米也不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通过她可以书写革命的合法性和崇高意味。玉米是生长于苏北大地上的一棵“玉米”,她汲取天地精华、汲取阳光雨露,但也汲取了乡村日常的种种不堪而被扭曲,但她依然努力地向上生长。她和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她警惕地像一个机智的松鼠一样窥视着她生活的世界,并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紧张。而对于毕飞宇来说,他和作为自己小说创作对象的“玉米”之间的“潜在的战争”,也使他感到了“自己的紧张”。因此,毕飞宇“玉米”系列的小说意义,“不在于他用独白方式宣告个性的价值,而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并能客观地艺术地发现它、表现它,不把它变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声音同它融合在一起,同时又不把它降低为具体的心理现实。”③玉米、玉秀、玉秧们的“个性”只能是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立的“个性”,而且,她们应对世界的方式、她们内心涌动的隐秘的生存力量,各自构成了独立的“风景”。#p#分页标题#e# 而在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中,政治、革命、宗教、封建迷信等更是构成了多声部的对话关系。他以生活的“平视者”展示了根植于民间大地上的各种话语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共同构建的复调的乡村世界。在小说中,以支部书记吴曼玲为首的“政治”和“革命”话语虽然在表层上掌控了王家庄的日常生活,但“革命”话语却常常被其他的话语方式所僭越。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并没有使地主的女儿孔素贞“洗心革面”,她依然在佛的极乐世界中寻求超越现世生存的精神寄托。外来的知识者顾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布道者”,坚守着精神的“纯粹”,从来不吃集体一个鸭蛋。但顾先生的精神“纯粹”却在乡村女子姜好花的肉体引诱中迅速失守④。精通天地鬼神的许半仙一直是王家庄的积极分子,什么事都参与,什么事都少不了她。而保证了许半仙存在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的是她的“雇农”身份,是她政治上先天的优势。她不再是《小二黑结婚》中被改造的落后分子“何仙姑”,而成为民间生存的另一种保障,因为“某种意义上说,许半仙的存在捍卫并保证了王家庄,她使王家庄的许多人有了寄托,有了安全,有了私下的、秘密的精神保障”。因此,在《平原》中,革命、宗教、迷信、唯物主义等奇异地缠绕在一起,使“王家庄”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巨大的镜像。 如果说20世纪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多是知识分子的“他者”目光,是对“不在地”的乡土世界的回望与观照,那么,毕飞宇就是以“在地”目光注视着苏北大地上最为沉重但也是最为丰盈的日常生存。他不是那个黑暗的乡土中“持灯的使者”,而是和天地万物一起生长在大地上的一个平凡的个体,他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体察并体恤乡土生存的沉重与无奈。“在世界的黑暗时代,人们必须对世界的黑暗有所体验。为此,需要有敢于进入深渊,身历其中受其煎熬的人。”⑤他不在乡土之外悲悯地注视,而是根植于乡土之中和他笔下的人们一起“进入深渊,受其煎熬”,并以鲜活的个体经验解构了“革命史”、“启蒙史”、“现代史”所创造出来的群体经验,以“疼痛”的生命感受逼近历史现场,还原乡土生存的某种真相。 二、残酷的青春成长经验 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从玉米、玉秀、玉秧到端方、吴曼玲等,都经历了他们生命中残酷的青春成长,但时间的流转或空间的变迁并未曾带来个人青春成长的最后完成,他们或者甘心屈服于权力的驯服、或者无处逃离历史和他人的剥夺、或者无望地抗争却最终陷落。青春经验不再是现代历史叙事中的个人成长,如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中,终于“长大成人”,演绎了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青年们的青春成长在性、政治、权力的压抑和规训下逐渐枯萎、或者扭曲地成长。毕飞宇提供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内心有美好的一面同时也晦暗不明,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伤害别人的同时也自我伤害;他们有美好生活的梦想,但历史并没有提供给他们个人成长的机缘;他们渴望逃离沉滞的乡土,但无路可走或者即使有幸逃离但却不免再一次陷落。 巴赫金在论及“成长小说”时,认为在成熟的“成长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⑥那么毕飞宇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呢?他们经历了岁月的变迁、时空的流转,但不变的却是不曾完成的青春成长。因为在沉滞的时间和封闭的空间里,他们身上依然带有历史的沉重负累、内心的挣扎也一如既往。玉米从“王家庄”嫁到“断桥镇”,不变的是对权力的热望,是“人在人上”的梦想的延续。而在王家庄被众人强暴无路可走的玉秀到了断桥镇,内心依然摆脱不了这一梦魇般的过去,并直接导致她失去了两次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缘。玉秧是王家唯一一个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上了师范学校的女孩,但“学校”这个意味着成长为“新人”的现代空间却成了告密者的天堂,玉秧这个看似纯朴的乡村女孩不仅未曾幸免,而且深陷其中却不自知。在《平原》中,高中毕业回乡的端方,也不再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家林,带着不容于乡村的“现代文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挣扎。端方在王家庄虽然靠“力气”和“沉默”赢得了在家庭和在村中年轻人中的威信,但在当兵这唯一可以离开王家庄的可能性丧失后一度沉沦。总之,在这些年轻人的青春成长中,历史显示了它的冷酷与荒凉,历史的荒谬、政治压抑、权力掌控,使青年们的青春成长始终处于一个没有未来指向性的时空中。他们不仅没有美学意义上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就他们每个个体而言,也不曾显示在不堪的环境中的人性光辉。 不是个体和时间一起成长,而是个体和时间在晦暗的历史深处一起陷落。 对于毕飞宇“王家庄”系列小说中的女性而言,在残酷的青春经验中,女性唯有以“身体”向历史和男人献祭。 福柯曾说:“自古以来身体一直都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身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⑦玉米正是靠着“在床上又心细又巴结”,讨得了郭家兴的欢心,借机安排了自己和妹妹的工作,“身体”“、性”、“权力”在这里是同构的。《玉秧》中身体的献祭则更为震动人心,如果说玉米、玉秀的遭际是在荒谬和扭曲的“”时代,玉秧青春成长的岁月已经是1982年的师范学校,但历史的灾难并没有结束。魏向东这个惯于搞政治运动的保卫科老师把肮脏的手伸向了懵懂的玉秧,而玉秧面对魏向东“想尽一切办法”把她留在城里的许诺,觉得“这个大交易,划得来,并不亏”。显然,不管是精明能干的玉米、还是木讷懵懂的玉秧,无一例外都以青春成长中惨痛的身体经验?过破碎的历史之河。身体的懵懂或觉醒并没有伴随着精神的成长,而是以单纯的“身体”的献祭或“身体”的被剥夺作为跨越生存困境的唯一载体。在《平原》中,因为政治对“身体”的拒绝和“身体”对日常冷暖的渴望使吴曼玲处于一种撕裂中,小说中吴曼玲与狗“无量”的相互依偎既让人心酸也让人震动,吴曼玲的青春成长不仅被政治异化,最后也成为政治的无辜的牺牲品。#p#分页标题#e# 在“王家庄”系列小说中,残酷的青春成长还呈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中。在一个促狭的空间中,他们为了生存的权利,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构成了对他人的伤害,而“不经意”或者说自以为“正确”的伤害更显示了人性的晦暗与幽微,显示着青春成长的艰难。当这种伤害发生在亲姐妹之间时就更显示了它的冷酷,玉米与玉秀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从王家庄一直延续到断桥镇,为了留在断桥镇,一向骄傲的玉秀给自己的姐姐下跪磕头,而玉米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王家和郭家的“脸面”,对郭左透露了玉秀被强暴的经历,直接导致了玉秀爱情的破灭。“嘴讷,手脚又拙巴、还不合群”的玉秧在师范学校里成为魏向东安插在同学间的一个“告密者”,因为她的告密,诗人楚天精神疯狂,班主任因为恋爱也精神崩溃。更为可怕的是,玉秧是在“不自知”或者说自以为“正确”中在从事这项工作,就更显示了埋葬在人心深处的黑暗。 青春成长的晦暗和扭曲,在玉秧的身上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女孩,内心对尊严的重建却是身体的献祭和对他人的伤害。而在《平原》中,青春成长更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进行的,混世魔王不管是积极表现还是消极反抗都无法逃脱自己被规定的命运,最后绝望的混世魔王强暴了吴曼玲,而吴曼玲因为担心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无奈同意了混世魔王去当兵。 人与人之间外在的搏斗与内心的较量,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并没有疾风暴雨式的正面冲突,而是以一种隐秘的、日常的方式在进行,惟其如此,才更显示了青春成长的艰难与逼仄,也使毕飞宇小说中的青春成长经验超越了特定的历史空间而成为一种恒久的人性诗学。“青春”不只是受到了历史的压抑,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人内心的黑暗,这种黑暗不是大恶,而是生活潜流中本来就蕴藏的、甚至连自我都未曾真正意识到的“荒凉”。在毕飞宇的乡土小说中,现代性的启蒙叙事再次陷落,他改写了现代性叙事中漂移的时空带来的个人长大成人,而是提供了民间大地生存的沉重与无奈,在漂移不定的青春成长经验中,无望与宿命成为成长的最后风景。 三、隐秘的乡村政治 在乡土小说中,对乡村政治的书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从五四新文学到“”后的新时期文学,乡村政治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息息相关。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则常常以虚构或想象来解构和颠覆政治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乡村政治,表现乡村“权力”对民间生存及民众精神的伤害。 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也书写乡村政治,他的《玉米》、《玉秀》书写的是“1971年”的乡村与小镇,而《平原》书写的是“1976年”的苏北大地,但他小说中的“乡村政治”并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也没有以感伤的笔调抚摸乡村的“伤痕”,甚至没有以戏谑与嘲讽的方式颠覆“”中的乡村政治。在他的小说中,政治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和民间生存融为一体,它有时是赤裸裸的,有时看似无形又无处不在。 毕飞宇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虽然乡村政治无处不在,可政治并没有成为凌驾于日常生活、掌控着日常生活唯一合法性的存在。或者说,政治话语与民间生活所构成的对话和互动关系,成为毕飞宇小说颇有光彩的一个面相。如在《平原》中,因为秘密从事“佛事”活动,沈翠珍一行被游街,但游街并没有“伤痕”和“反思”文学常见的阶级专政的惨烈场景,而更像一场民间狂欢,游街的工作交给了十来个七八岁地孩子在闹剧似的暴力中完成。在苏北平原上,遥远的政治中心“北京”对“王家庄”的掌控是通过“高音喇叭”来实现的,但在《玉米》中,“高音喇叭”除了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外,也和诙谐的民间生活联系在一起。通过它,支书王连芳广播来自上级的一切指示,同样通过它,王连芳生儿子的消息和玉米未婚夫来相亲的消息通过它得以传播。在王家庄封闭的空间中,虽然“北京”政治无处不在,但民间生活、民间伦理更像波涛汹涌的暗流,沉默地、坚定地涌动。 政治、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在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中,最为症候性地体现在性或者说身体与政治、权力的纠葛中,“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⑧,政治权力以隐秘的方式建构着身体经验。在《玉米》中,村支书王连芳因为是乡村政治权力的掌控者,他的性经验史穿越了王家庄的“老、中、青”三代,而且无往而不胜。可是当王连芳因为“破坏军婚”被开除后,人们同样把魔爪伸向了无辜的玉秀和玉叶,她们在看电影的夜晚被村里的年轻人轮奸。村里人甚至写信给玉米的未婚夫,说玉米被人睡了。隐秘的乡村政治不止体现在权力对身体的伤害,同样体现在权力的被压抑者更为黑暗的报复“,身体”成为人们进入晦暗的历史和穿越残暴的历史的唯一通道。在《平原》中,政治对身体的规训则体现在对具体的物质性肉体的拒绝,“身体被纳入了政治的轨道。身体和生命一并被纳入到政治学的规划之中。现代国家从功能的角度积极地强化身体、训练身体、投资身体和管理身体。强化身体是为了将身体纳入到国家理性的轨道内,并让身体服从于这种理性逻辑,使身体成为国家理性实践的完美手段。”⑨在这样的权力政治对身体的驯服中,“男人能做的事妇女一定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疾病在精神之外,在革命之外。说到底,疾病是可耻的,它是软弱和无用的挡箭牌。 懈怠和懒惰才是病。”权力、政治话语压抑身体,贬低身体,让感性的身体经验从视野中消失,在政治、权力的话语空间中,身体成为一种政治美学的象征仪式。 毕飞宇曾经说过:“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⑩这个“人在人上”的“鬼”在他的小说中就是对权力的掌控,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从家庭到乡村甚至在从事“现代”教育的学校,对权力的迷恋无处不在。#p#分页标题#e# 在《玉米》中,“玉米任劳,却不任怨,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在家庭遭遇变故后,玉米更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所以她嫁人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而村支书“王连芳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怕他。 他喜欢人们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在《玉秧》中,魏向东整个寒假过得极其漫长而孤寂,因为“没有人向他汇报,没有人向他揭发,没有人可以让他管,没有工作可以让他‘抓’,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目标。实在是难以为继”。 那么,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权力的迷恋来自哪里呢,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脉络检视哪些事件塑造了我们,哪些事件帮助我们认知所谓自我主体,就是正在做、正在想、正在说什么。”???毕飞宇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异化的源泉,而是通过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展示了“人性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暴露出阴暗凶残的一面”???,丰富了乡村书写中的人性诗学,并以文学书写反抗这种人性的暴力与阴暗。 当然,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书写中,关于政治、权力、革命、性的书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毕飞宇表达这一系列主题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身体、性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始终和民间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正是通过政治、革命、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伤害,毕飞宇消解了宏大历史叙事中政治、革命、权力的“斗争”意义,消解了政治、革命所建构的暴力美学,在日常叙事、民间伦理的意义上反抗权力的规训并反省人性的异化。 总之,通过《玉米》、《玉秀》、《玉秧》、《平原》等“王家庄”系列小说中的乡土书写,毕飞宇成了当代文坛上独特的“这一个”。他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在于构建了“地球上的王家庄”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王家庄”小说世界中远离现代性启蒙叙事的民间生活的丰富性、他贡献给中国文学史的未曾完成的残酷的青春成长经验、他在革命、政治、权力、身体、性所构建的话语空间中对固有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拆解。 在这个意义上,“王家庄”系列乡土小说成为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完整的美学世界,并改写了启蒙、审美、革命等叙事规范中的乡村经验。毕飞宇式的乡土书写因此成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标签,标识着他带给文学史与当代文坛的独特的叙事伦理与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