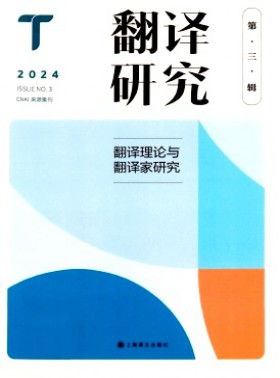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翻译伦理的理论悖论,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杨荣广,孙媛,李铮 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安托瓦纳•贝尔曼关于翻译伦理的论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并且直接启发了皮姆和韦努蒂等其他学者关于翻译伦理的论述。国内外近年来探讨“翻译伦理”的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便是一个最为直接的佐证。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诸多亟待深入和改进的地方。 1.翻译伦理与翻译中的伦理问题:理论的误读还是理论的发展? 贝尔曼关注的是翻译本质上的伦理规范问题。贝尔曼批评翻译中常用的一种“自然化”(naturalization)(基本上等同于瓦努蒂的“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认为这种策略抹杀了原文的异质性。在他看来“翻译的合乎伦理的目标是以异为异”[4][P285],“翻译伦理包含着对翻译之为翻译的纯目的(pureaim)的阐释、证实和辩护,是由如何定义‘fideli-ty’而构成。”[3][P5]。在他看来,译者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决定了译者“翻译的欲望”和目的语的最终面貌,只有通过心理分析式的剖析(psy-choanalyticanalysis)才能使译者意识到这种力量。这种欲望也可以看成是翻译的形而上的哲学,后者与翻译的纯伦理目的相关联。纯翻译的欲望应是翻译伦理目的的心理基础,是要通过与非本土的、优良的、更加灵活的,更加游戏的,更加纯的语言的正面的冲突来改变本土的语言。但是真正的翻译伦理目的并不仅止于此,而是要“在外来语言和本土语言之间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施奈尔马赫、荷尔德林、本雅明等有关翻译的论述对贝尔曼有着深深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贝尔曼意识到了翻译过程中所蕴含的“自我”对异质的“他者”的暴力,提倡保持原文异质特征的翻译方法,并将其作为抵抗我族中心主义暴力的手段。贝尔曼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字面翻译”(Literaltranslation)的策略,要通过“忠实”和“准确”的再现原文。“字面翻译”忠实”准确”这些在翻译研究中最普通的几个字眼,被贝尔曼提到了伦理的高度,“对译者而言,‘忠实’和‘准确’是两个附在他身上的精灵。它们是译者的激情所在,这个激情既不是文学的,也不是美学的,而是伦理的。”[16][P81] 那么什么是“字面翻译”?贝尔曼是这样解释的:“这里‘字面’的意思是:紧贴(文本的)字(letter)。翻译时在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恢复作品的特定的意指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仅局限于原作的意义),另一方面,改变译语”[4][P297]。贝尔曼在另一篇文章《译与字-遥远的客栈》中给出的答案是“翻译即是译‘字’,翻译以‘字’组成的文本”。西奥•赫尔曼斯对此的理解是:贝尔曼提倡“字对字的翻译(word-for-wordtranslation),以求尊重原文与身俱来的他异性”[17][P98]。那么怎么理解“字”(lalettre),贝尔曼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说明。瓦努蒂在讨论“字面”的理解时将“Letter”解释成“目的语中一系列意指的可能”[8][P146-147]。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将翻译与契约作了一个类比“忠实于一个合同意味着遵守合同的条款,而不是合同的‘精神’,忠实于一个文本的‘精神’是自相矛盾的”,“翻译伦理的目的是以接纳他者的肉身来接纳他者”[16][P81]。“肉身”是什么呢?原文的形式?是否合乎伦理的翻译就是要字对字的翻译呢?贝尔曼之后的论述就显得含糊其词。为了使这一近似于乌托邦式的设想得以实现,他又提出了“翻译的分析”的概念,认为只有通过翻译分析才能真正实现翻译的伦理目的。在1995年出版的《关于翻译批评:约翰•多恩》[18]一书中,贝尔曼力图是自己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翻译批评模式,将伦理和诗学作为翻译批评的两个标准条件,其中伦理标准即在于对原作的尊重,而诗学标准则要求译作必须能够具有原文的语篇性,这样才能保证译作既尊重了原作又具有创造性,从而丰富和发展目的语。 国内对于翻译伦理的论述更多的是从微观的、文本对照的层面上展开,采用的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是翻译实践过程中,伦理因素(如:译者个人伦理动机(实现政治目的等)、目的语文化的社会伦理等)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以下两个案例:一是,彭萍博士的专著《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该书以中国佛经翻译、明清科技翻译以及耶稣会士的基督教经典翻译为分析对象,探讨不同时代的伦理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译本的接受[14]。二是,王大智教授的《翻译与翻译伦理-基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思考》。他基本也是将伦理因素纳入到中国传统的翻译活动中,分析了“以夏变夷”和“立夏夷之防”的族际伦理和儒家伦理、实学伦理对当时的翻译实践的影响以及明清之际西学汉译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伦理价值判断[15]。对比上述国内的两本专著可以看出,国内基本是文化转向研究思潮的结果,更多的是探讨的是伦理因素影响下造成的译者对文本的操纵与改写,这与贝尔曼的初衷相去较远,可以是对贝尔曼思想的误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却又是对这一理论的补充。 贝尔曼专注于拉美小说和德国哲学的翻译,他的思想源自于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关注的中心是翻译活动的伦理目的,以及翻译所必须具有的尊重“他者的”义务。对贝尔曼来说,翻译伦理既是是理论的起点,也是问题的焦点。但是从所有的论述来看,他对于翻译伦理并未加以准确、清晰的界定。也许正如AlexisNouss为他辩护的那样:“当伦理是对他异性的接受时,如果它要保持自身不变,就必须是不确定的,也不能够被准确表达的”[19][P133]。他的研究将哲学观点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直接启发了瓦努蒂的研究,但是瓦努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贝尔曼,这不仅仅是因为贝尔曼是用法语写作,因而读者接受起来相对困难,更重要的或许是贝尔曼的逻辑思辨性过强,反而忽略了对自己的核心术语体系做清晰的界定而造成的。这种模糊性一方面客观上促使了当前翻译伦理研究多角度、多元化的现状,另一方面又使得研究者缺乏统一的术语而阻挠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发生变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多向性,是从本土文化出发对翻译伦理研究的有益尝试。#p#分页标题#e# 2.“翻译伦理”本身存在的理论悖论 翻译与伦理有极大的相似性。任何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都必然受到自身所处的语言、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伦理问题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在做出价值判断或者说伦理判断的时候也往往受到根深蒂固的文化框架的约束。同样的,翻译研究要回答两个问题“应该怎样翻译?”实际上怎样翻译?”伦理研究者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伦理学所关心的主题,主要不是有关事实的问题,而是属于价值或价值判断”[20][P11]。翻译伦理所给出的价值判断,在面对翻译事实或者说指导翻译实践活动时往往会发生背离。 从贝尔曼的理论本身而言,翻译的伦理强调译者要尊重原作,对原作负责。这种尊重有两个层面:一是保留原文的异质性特征;二是要用目的语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作,以延续原作的生命。尽管“尊重”、“负责”这样的道德标准消解了忠实与再创造之间的二元对立,却仅仅是掩盖了矛盾,而非提出一个可行的实践方案。从伦理学本身来说,道德规范规定了人们应该怎样去做,但是这种先验性的规定并不能强制人们实际上去按照这种规范来行事。这种先验的规定性和实践的多样性之间的悖论必然导致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主观动机和最终结果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比如:鲁迅先生的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几乎是完美的体现了贝尔曼对于再现原文异质性的强调,其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外来的文学、语言改造社会和本土的文化风俗。然而,小说两册各卖了20本左右,影响甚微。相比较而言,林纾的归化翻译可以说是人尽皆知(若用贝尔曼的标准看确实是不好的翻译),但其译本却“风行海外”,且“传播了西方资产民主、自由的新思潮”[21][P200]。 3.翻译伦理研究的分类 在贝尔曼之后的众多关于翻译伦理的讨论尽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却在本就“众声喧哗”的理论争论中增添了更多的不同声音。究其原因,翻译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系统,众多的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从某一个侧面展开讨论。尽管吕俊、侯向群提出了建立翻译伦理学的呼吁,杨洁、曾利沙曾试图从学科层面对拓展翻译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做出了有益尝试。当前这种自说自话的局面丝毫没有改观。唯有从伦理学视角来整合现有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推进翻译伦理研究的进展。根据现有研究的内容,笔者试图用图1(见文末)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 元翻译伦理学就是要以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为理论基础,运用逻辑和哲学思辨的方式,讨论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术语(如“不正但/正当”的翻译(unethical/ethicaltranslation)等)、反思建立翻译伦理的理论前提和依据,批判和考察翻译伦理研究的其他分支相关理论是否合理有效。判断元伦理学主要有两个较为重要标准(1)元伦理学主要讨论论学术语或命题如“正当”不正当”、“善”、“恶”等的意义和定义、这些术语或命题的规则及其使用的功能;(2)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否被证实、证明、或显示其有效性?如果能,怎样证明,在什么意义上证明?[22][P197]从细读贝尔曼对于翻译伦理的论述不难看出,贝尔曼主要是从语言和逻辑上,通过哲学分析的方式阐释了翻译伦理,并且通过翻译解析来证明自己这些术语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贝尔曼翻译伦理说归结为“元翻译伦理”是有道理的。规范性翻译伦理研究则主要是研究翻译伦理价值判断的标准,确立价值判断规范,探讨这些标准和规范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译文最终的形态、对原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以及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等,目的是找到和明确表述具有一定普适性意义的翻译伦理规范体系,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研究应该就属于此类。应用性翻译伦理研究则主要是研究规范性翻译伦理在翻译实践中应用的问题,并将应用性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认识升华成理论,改进和提升规范性翻译伦理的研究。贝克有关翻译伦理的讨论可以划分到此类中。 描述性翻译伦理研究主要是对翻译活动中所出现的与伦理价值判断相关的行为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描写,目的在于描述或解释翻译操作现象或提出与翻译伦理问题有关系的本性理论,为翻译伦理学研究积累研究的素材。国内很多利用切斯特曼的五个伦理模式对翻译文本进行分析的论文大多属于此类。这五个大类之间相互关联,互相渗透,在具体的研究中很难将其完全的分割开来。整个框架是开放式的,随着翻译伦理研究的深入,或许还会出现翻译伦理比较研究等新的领域。在应用性翻译伦理研究之下还有很多的小类,限于篇幅,暂且言尽于此。 综上所述,翻译伦理研究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理论自身在概念界定、体系构建方面还不够完善,因而引起各种批评的声音。与任何理论一样,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变异,从而促使研究者往往会从不同的侧面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难免会造成分散、混杂、众声喧哗的局面。翻译伦理研究在国内外呈现出了不同的场面,关注的焦点也不太相同。尽早理清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廓清翻译研究的不同方向和类别,对当前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才有利于翻译伦理研究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