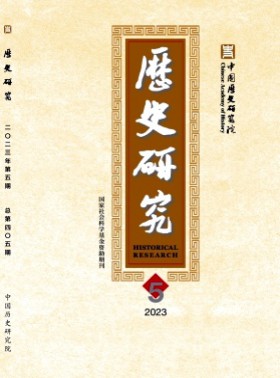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研究中图像学的作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姚霏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19世纪中叶,德国思想家德罗伊森(J.G.Droysen)曾不无偏激地断言:“只有当历史学家真正开始认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材料,并能有系统地运用它们,他才能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以往发生的事件,才能把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1](P72)在中国,随着史学的“社会史转向”,图像之于历史的特殊作用逐渐为史学家所注意。诚如小田在《漫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以丰子恺漫画为对象的分析》中所言:“(丰子恺)给我们提供了往昔存在的情境;出现在情境中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某类角色;发生在情境中的,不是特定的事件,而是常态行为;展示在情境中的,不是即时见闻,而是时代风尚;隐现在情境中的,除了具体实在,还包括‘实在’所象征的抽象意识。”[2]与关注特定人物、事件的政治史不同,社会史所追求的“真实”,不是“人物———事件事实”,而是“符号———行为事实”。[3](P56)图像完全可以作为获取“符号———行为事实”的基本素材。1884年,晚清著名画家吴友如创作出版了《申江胜景图》。该画册收入以上海城市景观为对象的绘图60余幅。其中,女性是与上海城市息息相关的“景观”。其后,在担任《点石斋画报》主笔期间,吴友如十分留意与女性相关的新闻,《点石斋画报》中的女性主题比比皆是。1890年9月,吴友如将创作的重心从《点石斋画报》转移,创立了《飞影阁画报》,每期第一幅即为“沪妆仕女”。3年后,吴友如又出版《飞影阁画册》,其中仍有“时装仕女”单元。这些都市仕女图在吴友如逝世后,被收入《吴友如画宝》的“海上百艳图”中刊行。和传统仕女画不同,吴友如将目光投向晚清上海都市中的女性。当西方城市文明的标志———西洋建筑、玻璃窗、路灯、马车和中式装扮的女性出现在同一画面并取得惊人的和谐时,我们似乎找到了晚清上海城市的魅力所在。
一、活跃于城市空间中的晚清上海女性
1.远眺下的女性:从四马路到郊外创作于1893年的《沪游梦影》在提到上海租界娱乐区时写道:“盖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焉。”[4](P156)事实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四马路已经成为租界娱乐区的核心地带。《申江胜景图》中的“四马路中段”描绘的是山西路和福建路之间的四马路。在这看似“女性缺席”的场景中,处处蕴藏着女性的身影。画中右下角的三层楼建筑是当时沪上闻名的茶楼———阆苑第一楼。从晚清画报可知,自从公共租界工部局禁烟以后,流妓在“烟馆中无处容身,乃相率而啜茗”,“无不浓妆艳服,围坐于明窗净几”,看到穿着华丽的客人便“眉目传情”。[5](第8册,P141)《点石斋画报》中有“博士肇事”一则,就发生在阆苑第一楼,讲述了妓女家的女仆被“茶博士”调戏而大打出手的闹剧。[5](第1册,P19)从画面来看,围观的人群中有不少女性。阆苑第一楼的二层是当时有名的弹子房。1883年的《申报》有竹枝词题咏女子入弹子房打弹子:“玉手轻抛银弹去,打球肯让醉三郎。”[6]在《申江胜景图》中,我们就能找到女性于弹子房中观赏游戏的场景。而到了《海上百艳图》出品时,就已经有妇女围在一起打弹子的画面了。
阆苑第一楼对面是连排的里弄住宅。19世纪70年代末的竹枝词中提到:“四马路两旁统是妓馆,游人出入之所。”[7](P54)随着公共娱乐区域的“北移”,上海的高等妓业从老县城内虹桥一带转移到了租界四马路中段,出现了连成一片的“壮观”景象。《点石斋画报》中的“提人酿祸”,就用鸟瞰的视角给出了晚清上海妓业空间“里”的典型形象。在“四马路中段”图中,尚仁里沿街二楼的窗户里,隐约可辨女子的身影。而在画左下方的一处弄堂口,一台轿子正从弄内出来。在《飞影阁画册》中也有相似的场景。“香衣相逐”表现的是书寓应召出局的场面。中式装扮的女子与轿子,穿梭在由石库门、百叶窗和西式路灯构成的里弄街巷,构成了晚清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除了轿子这一传统代步工具,四马路上出现的新式交通工具东洋车、马车也与女性出行息息相关。《申江胜景图》的“龙华进香”描绘了4个前往龙华寺烧香的女子,她们两两分坐在东洋车和独轮车上;而“华人乘马车脚踏车”则描绘了男女共乘马车、悠然自得的景象。乘坐马车成为晚清上海女子值得炫耀的行为之一。在《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册》中,就有不少女性乘坐马车的图画。而她们的足迹也已经越出四马路,沿着越界筑路的方向向西延伸。《飞影阁画册》中的“以水为鉴”,描述的便是女子在静安寺外“天下第六泉”逗留的场景。在当时租界的边郊地带,除了马车经过时留下的女性身影,一座座烟囱下也有着别样的女性景观。在《申江胜景图》中,缫丝厂这一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成为上海城市的重要景观之一。在“缫丝局”图的左下角,局门口依稀行走着几名女子。这一女性出入缫丝局的场景,被纳入吴友如的《飞影阁画册》,成为晚清上海重要的女性景观之一。在“女执懿筐”中,和远处乡野风光形成对比的是缫丝厂西式的篱笆和门灯,大门口挥手告别的女工们来自乡野,却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庞大的西方工业文明中。
2.凝视中的女性:公共空间中的女性群像在领略了女性活动空间伴随租界空间的延伸而拓展后,让我们回到“远眺”的起点———四马路中段,开始一段“凝视”的旅程。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租界娱乐区内,女性身影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移动景观。(1)戏园早在1874年,就有人对租界戏园中看戏妇女之多作了描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杳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8]在《申江胜景图》的“华人戏园”中,台上唱念做打,台下男女杂坐。二楼偏厢中,还有结伴而来的女子。从该画的视角分析,画家的关注点显然“半在台上半在下”,座中男女杂坐的情形是画家极力突显的。而到了《点石斋画报》的“和尚冶游”中,由于要讲述的是一名和尚携妓到老丹桂戏园看戏的奇闻,画家干脆将视角完全瞄准观众席。画家对每个女性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勾勒,加重笔墨,使其看来比男性人物更为显眼。这种表现手法,一方面是为了取悦画报读者的男性身份,同时也表达了画家对女性入戏园这一现象的关注。在同一空间,当一部分女性作为消费者出现时,另一些女性正要开始她们的谋生之旅。19世纪八九十年代,髦儿戏从最初的官绅宅第“堂唱”演变为在固定场所演出,日渐成为上海全新的娱乐内容。《飞影阁画册》中的“巾帼须眉”便描绘了女艺人们在后台扮装的场景。(2)书场随着评弹的传播,听女弹词日益成为晚清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女弹词依旧保持着“堂唱”、“书寓”、“书场”三种不同空间的表演形式。但书场已经日益成为弹词女艺人的主要活动空间。出版于1898年的《海上游戏图说》中指出,书场的开设并不复杂,“葺屋一大间,延请一二女郎先生,或三四人,中设高台,小几下列,听客座位多至百座……届时先生乘舆而至,登台高坐,台下之客环坐而听”。[9]在《申江胜景图》的“女书场”中,空间设置正如文字记载:两位“女先生”高坐台上,宽敞而气派的书场座无虚席,门口还有大量涌入的人群,显示出时人对女弹词的极度追捧。#p#分页标题#e#
成书于1891年的《海上冶游备览》中讲到,女弹词演出的顺序是先唱开篇。“开篇者,编成七言字句,于说正书前先唱一篇,不知传自何人,永奉为例,往往一座数先生,先令雏鬟唱开篇,亦有两雏唱开篇者。俟开篇唱毕,乃唱正书焉。”[10]正书后再唱小曲一支作为结束。《飞影阁画册》中的“更唱迭和”,台上不同年龄、不同座位的女艺人,显示了不同的分工和地位。(3)烟馆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租界中的烟馆已呈现鳞次栉比的态势。1883年出版的《淞南梦影录》中提到:“租界烟馆向以雏妓供奔走,名曰女堂倌。少年子弟输钱百余文,使之调山介片,绞芳巾,品足评头,略不避忌……近有所谓打野鸡者,抹粉涂脂,奇形怪状,花街柳陌,扶婢闲行。往往借一塌之烟霞,订三更之云雨。”[4](P114)《上海小志》也提到:“(烟馆)初以法租界之眠云阁为最,继则互相争赛,复以南诚信为首屈一指……入夜,雉妓纷集,粥粥群雌,尤形热闹。男女相对,一塌横陈,不以为怪,而野鸳鸯多成就其中,以是贾大夫一流趋之若鹜。”[11](P40~41)果然,在《申江胜景图》的“南诚信正厅”中,女子或与男子谈笑风生,或几人交头接耳,还有横卧榻上、吞云吐雾者。而《点石斋画报》一张名为“烟狗”的画中,女子抽烟榻上,神情慵懒,丝毫不顾及旁人的眼光,可算是早期的女烟客了。(4)番菜馆到番菜馆吃饭是晚清中国人“现代性”的一种想像。出版于1893年的《沪游梦影》在提到沪上菜馆时指出:“番菜馆为外国人之大餐房……向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消夜馆者……惟杏花楼、中华园为最。”[4](P158~159)最初进出番菜馆的女性是妓女和女艺人。小说《九尾龟》第四十二回中,章秋谷等人到一品香吃大餐,叫了蟾珠等妓女的局,席间还从隔壁包间转了一个局。[12](上,P278~281)第六十二回中,章秋谷等回到上海,辛修甫在一品香为他们接风,也叫了局。[12](中,P413)20世纪初的《图画日报》将“大菜间请客之热闹”列为“上海社会之现象”,其间也有被叫局的妓女作陪。可见,妓女出入番菜馆是家常便饭。在《海上百艳图》的“队结团云”中,几名女子正要进入一间西式楼房。仔细辨认屋内匾额上的文字,原来是当时著名的杏花楼番菜馆。手持琵琶、乘轿而来的女子是往番菜馆出局的妓女。而《海上百艳图》的“别饶风味”中,在番菜馆中品尝西餐的群体变成了女性。从空间中的被消费者到消费者的变化,暗示着女性空间权力的扩大。
二、晚清女性在城市空间中的尴尬与危险
1.女性禁入与距离规训传统中国社会对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存在种种限制。1872年的《申报》有文章指出:“妇人女子原宜深藏闺阁,不令轻见男子之面,所以别内外而防淫欲,意至深也。乃上海地方妇女之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13]在《点石斋画报》的“游园肇祸”一则中,有妇女乘马车游玩张园,不慎跌入池中丑态尽现。尽管作者也认为“该园荷花池畔亦宜围以栏杆,免致偶不经意倾跌堪虞”,但还是将根本原因“归咎于妇女不宜轻出闺门”。[5](第10册,P206)1893年的《申报》更以“妇女不宜轻出闺门说”为标题,劝说妇女远离公共领域。作者在文中提出一个独特的论调,即“殊不知他处妇女或可于中馈之暇出外游行,独上海则浇薄成风,万不可使妇女偶然游玩”。至于晚清上海的哪些场合最应禁止妇女出入,作者列举了戏园、酒肆、茶馆、园林。[14]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几年,《申报》上出现禁止开设“夜花园”的言论,居首位的理由无非“上流社会人多青年子弟、良家妇女,借游园之名作秘密之机,失节丧名不知凡几。罪恶滔天,实较北里为甚”,[15]“男女联袂偕游,有伤风化”。[16]在这类看似保护妇女、整肃风化的言论和举动背后,暴露出传统社会男女正常交往的缺乏,以致公共场所一有女性出现,不是引发两性非正常的接触,就是引发社会不必要的恐慌。一些以“传统礼教卫士”形象出现的文人本能地察觉到社会失序的威胁———城市化迅速发展,大行其道的西方文明动摇了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等级、性别界限日益模糊。于是,“关于社会动荡或男性美德失堕的焦虑就投射到女性身上”,[17](P133)对女性实施隔离成为停止这种焦虑和恐慌的灵丹妙药。然而,时过境迁,在西方文明以倾泻之势涌向中国的晚清时期,传统的“隔离”不具备可操作性。在“隔离”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制造距离”成为改变公共领域男女杂处的权宜之计。
1909年出版的《图画日报》将“升平楼野鸡之嘈杂”视为“上海社会之现象”之一。绘者写道:“租界雉妓向皆聚集于四马路之青莲阁。自去冬青莲阁关闭后,即群集于四海升平楼。六七点钟时,翔集飞鸣,嘈杂至不可耐,而附膻逐臭者,转以此为乐境焉。”[18](第1册,P487)显然,茶馆中男女混杂的情形令绘者十分反感。而在同一时期的小华园吃茶,却被视为风雅写意之事。“楼上另设有女客间,桌椅均以竹制成,朴而不野,华而不俗。午后三四钟时,明珰翠羽,粉黛如云,风生七碗之余,令人作飘飘欲仙之想。”[18](第1册,P439)出入小华园的女性仍以妓女为主体,但这种男女分座的形式,却能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在晚清,女性不仅作为书场中的“被观赏者”,即弹词女艺人或妓女出现,同时,她们也逐渐成为书场的消费者。在《图画日报》“上海社会之现象”的“书场年节会书之诙谐”中,就有女性观者的身影。而另一幅“上海社会之现象”则以“妇女听书之自由”为题写道:“书场另有女坐,凡小家荡妇、富室娇娃、公馆之宠姬、妓寮之雏婢,莫不靓妆艳福,按时而临……此种书场三四马路之间所在多有。”[18](第2册,P151)可见,晚清已经有了女子听书的书场,且所来的女子各阶层都有。不过,从图像上来看,女座位于舞台侧面,且与男座保持距离,显示着社会舆论对男女杂处的通融底线。当时,在倡导西学的进步人士当中,男女界限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蔡元培在谈到1902年筹备爱国女校时讲:“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彦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19](P609~610)爱国女校成立多年后,我们可以在《图画日报》中找到一幅名为“演说家”的图画。图释提到:“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最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18](第1册,P211)在“开通知识、灌输文明”的演说会上,女听众仍然与男子分坐,且用屏风隔出一块专门区域。不知如此标榜男女界限的中国社会,要如何开通这知识文明的第一步。#p#分页标题#e#
2.“危机四伏”的街道空间在娱乐空间中制造“距离”,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除男女杂处的“危害”。但在一些日常生活必须出入的空间,“距离”便无法发挥作用。街道是女性从传统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女性消费者,还是女性生产者,都必须通过街道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通过各类发生在街道上的新闻,一个“危机四伏的街道”形象,开始浮现在晚清女性面前。晚清发行量最大的画报《点石斋画报》中有“擅冒巡丁”和“龟子横行”两则新闻,讲述的是女子在街道上遭遇男子冒犯、打劫的故事。[5](第3册,P5)如果说扫墓所走的是通往郊外的道路,那在最为繁华的租界娱乐区,街道依然充斥着各种危险。华灯初上的四马路一带,以妓院男佣(俗称“龟子”)为首的一些无赖之徒聚党而游,专拦街头的随轿婢女调笑,甚至强抢其首饰,众目睽睽,毫无顾忌。[5](第4册,P32)1909年创刊的《图画日报》中,“流氓强攫妇女首饰之凶横”被列为“上海社会之现象”。除此之外,调戏是女性在街道上遭遇的又一经历。《点石斋画报》的“马夫恶剧”中讲到,两名少妇途经泥城桥一带,被一个名叫明春的马车夫和同党上前调戏,用该处正在修筑的阴沟污泥抹在少妇脸上,少妇向巡捕大声呼救,无赖们才纷纷奔逃。[5](第12册,P125)19世纪末,随着缫丝、纺织、火柴等业在上海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平民女子开始从事女工职业。伴随上下工的日常化,女工经常受到流氓无赖的欺侮。“有青年子弟,猎艳寻春,俟妇女出栈之时,任意轻薄”;[20]“见姊妹花有妖娆艳冶者,即近前调戏,恣意癫狂,偶或反唇斥之,则攫取簪环,甚至撕其衣袂”;[21]“顾(散)工之际,被流氓拦截调戏,以致滋生事端者时见于报”。[22]《点石斋画报》也曾报道两起女工回家途中遭遇调戏的事件,其中一则新闻写道:“人生不幸作为女子身,其或生长名楣香闺深处,并不知有井臼操者,固几生修到也。至于蓬门弱质,压线年年,藉十指为糊口计者,露面抛头,事非得已,有心人方怜悯之不暇,何忍于陌上相逢,恣其调笑哉?怡和丝厂多女工,放工后,三三两两结伴归家。路遇流氓数辈,遽行调戏。”[5](第4册,P13)《图画日报》有流氓向女工喷镪水的图画,其原形是1910年3月26日《申报》上的一则新闻《机器匠之淫恶》。原来,这些地痞因调戏女工被辱骂而用镪水喷向女工以求报复。而《图画日报》上的“流氓调戏湖丝阿姐之泼赖”俨然已经成为晚清典型的“上海社会之现象”。
三、从图像到史料:图像学方法的运用
新文化史研究和图像史料的提倡者彼得•伯克(P.Burke)在《图像证史》(Eyewitnessing:TheUsesofImagesasHistoricalEvidence)一书中提到:“一两代人以来,历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事件、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而且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等。如果他们把自己局限于官方档案这类由官员制作并由档案馆保存的传统史料,则无法在这些比较新的领域中从事研究……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23](P3,P9)事实上,无论是新文化史旗手林•亨特(L.Hunt)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还是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都将图像史料作为建构史实的重要工具,通过分析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像,揭示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及其变化。而在女性史研究方面,伯克提到图像对“日常生活中的妇女”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分别列举了中国、日本、欧洲的绘画作品是如何透露出城市妇女对街头活动的参与程度、妇女从事哪些生产劳动、妇女的空间和角色。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很难在官方档案和文字史料中找到的。在关于女性识字率的问题上,伯克列举了希腊和法国的两幅图像:两名古希腊少女手牵手,其中一人拿着用皮绳捆着的写字板,透露了当时女性或许需要学习识字的历史细节;而在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的学校中,男女学生虽然一起学习,“值得注意的是,男生那边有写字的桌子,而女生则把双手放在膝上,似乎只需要听课,说明她们正在学习朗读,而不需要学习写字”。[23](P145~153)
需要指出的是,新文化史学对图像史料的认识和分析,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瓦尔堡学派(theWarburgSchool)图像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1939年,潘诺夫斯基(E.Panofsky)出版了《图像学研究》(StudiesinIconology)一书,开创了对艺术主题和意义进行分析的有组织、渐进且逻辑性强的系统———图像学。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学分为“三个解释层面”(threelevelsofinterpretation):第一个层面是“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description),也称“自然”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人们识别绘画最基本的主题,即展示的内容。理解这个层面的意义,人们只需将日常生活的经验带入其中。第二个层面是“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analysis),也称“传统”层面,这是图像学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潘诺夫斯基提出,为了理解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我们必须将现有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知识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分辨出随意的一餐和“最后的晚餐”之间的区别。第三个层面是“图像学解释”(iconologicalinterpreta-tion),也称“本质”层面。画家“对国家、时代、阶级、宗教或者哲学信仰的基本态度———被无意识透露出来并压缩在作品里”,[24](P7)这就要求我们对潜在的意义进行揭示。第三个层面是图像学的最终目标。同样,晚清上海的各类画报和画册上的图像,也为我们勾勒女性的活动空间和她们在生产、消费领域的身份特征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挖掘这些图像的史料价值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图像学方法的三个层面:
在第一个层面,我们应该对“女性在场”的图像进行搜集,这是一个不需要特殊能力便能实现的步骤(当然,如果对于晚清男女形象特征一无所知,可能首先面临“男女不分”的尴尬)。
在第二个层面,我们必须判断这些女性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这便需要特定的背景知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途径获得信息:首先是画面上的文字。这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图像名称,如龙华进香、四马路中段等。第二种是隐藏在画面中的文字,如“香衣相逐”(《飞影阁画册》)中灯笼上的“书寓”两字交待了轿中女子并非大家闺秀,而是青楼女子;又如“以水为鉴”(《飞影阁画册》)中井栏上有意无意露出的“六泉”两字,提示这并非随便一口井,而是静安寺前著名的“天下第六泉”。第三种则是新闻文字,如《点石斋画报》上的新闻。这些画面上的文字,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获取女性身份和环境的信息。简而言之,晚清平面媒体上的图像可以根据“有图内文字”还是“无图内文字”分为两大类,即画报图像和画册图像。画报图像的使用,首先分析“解说文字”,然后分析图像所反映出的文字外的意义;画册图像的使用,首先分析“题名”,如果有“景观内文字”也应结合,这往往是画家希望我们发现的线索。当然,无论图像上的文字多么直白,也不能帮助我们处理诸如“四马路中段”这类意象丰富的图像。如果没有《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之类的文人笔记,我们便不能解析画面中丰富的性别意向。即使是“队结团云”(《飞影阁画册》)这样主题单一、简单的图像,如果不了解晚清番菜馆也可“叫局堂唱”这一文化背景,画面中手执琵琶的女子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士绅阶层的夫人或闺秀。因此,文献资料仍是我们获取图像信息不可或缺的助手。#p#分页标题#e#
第三个层面,也是最困难的阶段,我们必须通过整体分析画家的绘画风格以及整体把握时代风气来进行图像创作背后的潜意识的分析。从《申江胜景图》到《点石斋画报》到后来的“飞影阁系列”,吴友如着力表现着西方文明对上海城市的影响。他笔下的城市空间有着一种蒸蒸日上的明快色彩,而他笔下的女性在异国文明的包围下不仅没有一丝局促不安,反而表现出从容享受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而画家对女性出入公共空间的态度,也通过主题的选择、构图的安排等无意间流露出来。因此,在对晚清图像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时,我们还要引入另一个视觉文化的解释维度,即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学者穆维(L.Mulvey)提出过著名的“男性窥视者”观点,认为大部分电影都反映了潜在的性别政治,“女人被偷窥,男人对银幕上的女子浮想联翩,银幕上的男人则是行为者和发号施令者”。1972年,伯格(J.Berger)出版了《观看之道》(WaysofSeeing)一书,借鉴了穆维的观点,指出由于传统观点认为“男人行动,女人显现”,绘画也揭露了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25](P70~74)
以晚清图像为例,无论是《申江胜景图》中将女性作为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还是《飞影阁画报》中的仕女系列,显然都在满足“男性窥视者”的审美喜好和市场的消费需求。即使在《点石斋画报》这类新闻图像中,“考虑到(画报对女性新闻)类型的选择、趣味的偏向以及简化或放大的策略,我们会发现,《点石斋画报》里展示的‘海上女性’形象,与男性的性别化观看、情欲想象有着怎样密切的关联”。[26]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有些图像更像是要唤醒观看者“男女大防”、“严别内外”的传统观念。晚清报刊上频频出现的女工受辱的新闻,客观上成为反对女性做工的“帮凶”。而画报选择这类题材进行二次创作,一方面是为吸引男性读者的“眼球”;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通过向男性受众传播这种“危机四伏”的街道形象,可以令他们意识到规训女性活动范围的必要性。这种舆论营造的效应,是否要比官方禁令更作用于无形呢?总而言之,图像史料的价值已经日益受到历史学者的肯定。晚清上海发行的画报和图册中,大量女性与城市空间的图像为我们勾勒女性的活动空间和她们在生产、消费领域的身份特征提供了重要帮助。尽管图像史料的运用仍处在探索阶段,即使西方历史学界也不曾实践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解读图像的手段,但是,因噎废食绝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诚如亨特在回答对于新文化史的质疑时说:“针对这些问题的方法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够断言是权威的,但如果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对如此困难问题的任何形式的探索,历史学家只会丧失他们理解过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