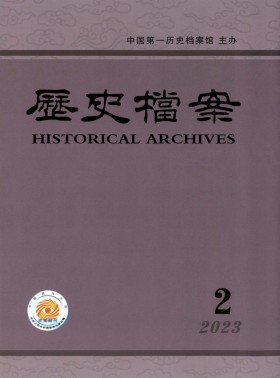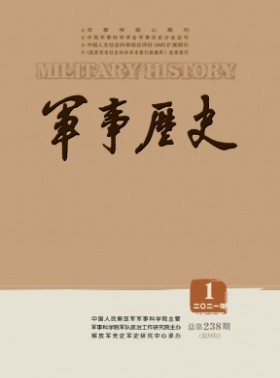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文学多层次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童庆炳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奇葩,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也引起了争议。史学家常常指责和批评当前历史剧、历史电视连续剧、历史小说没有写出历史的原貌,违背历史真实;文学批评家中多数人则认为历史文学家有权力虚构,不必复制历史原貌,况且何处去找历史的原貌呢?就是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中不也有不少推测性的虚构吗?“鸿门宴”上那些言谈和动作,离《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少说也有六七十年了,他自己并未亲睹那个场面,他根据什么写出来的呢?他的《史记》难道不是他构造的一个“文本”吗?另外,现实生活无限丰富多彩,无限生动活泼,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从中寻找到无限的诗性,寻找到无限的戏剧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却对现实生活似乎视而不见,总是扭过头去对那过去的历史情有独钟,愿意去写历史,愿意去重建艺术的历史世界呢?这里就关系到一个作家重建历史文本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还有,人们需要历史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需要它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吗?或者说历史的教训可以古为今用?对于历史文学来说,还有没有更为深层的东西?我发现上面所提的问题,恰好就是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对这三个层面进行必要的探索也许能揭示历史文学所面对的一些难题。
重建历史世界
我在重读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深感历史文学应老老实实地定位为“文学”,而不能定位为“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历史文学家生活在现在,可他写的却是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前的历史故事。他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历史文本(史书)。问题是这历史文本能不能反映历史的原貌呢?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情景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他无法亲眼去看去听,更无法亲身去经历、去体验,他所根据的仍然是前代史官和民间传说留下的点滴的并不系统的文本。这些前代史官所写的文本和民间传说文本,也不是作者的亲见亲闻亲历,他们所提供的也只是他们自认为真实的文本而已。无论是前代的资料,后人写的历史,都只是“历史是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它只是后人对那段历史文本的阐释而已。第二,既然是对前人文本的历史阐释,当然也就渗透进阐释者本人的观点。对一段历史,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方面,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更不用说,史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秉笔直书”、“按实而书”,这里又有一个避讳问题,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情之难免。
所以史剧作家所依据的历史文本就存在一个真假难辨、有无难分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那么历史文学家是如何来解开这个悖论的呢?换句话说,历史文学的创造者是如何来构筑他的作品结构框架的呢?在重读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我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重建”。我的意思是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构筑艺术世界的方法既非完全的虚构,也非完全的复制,而是根据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寻找历史根据,以艺术想象重新建立“历史世界”。艺术重建就是另起炉灶,对历史文本加以增删,加以改造,不照抄历史文本,而以自己的情感重新评价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另辟一个天地,构思成一个完整的世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371年的战国时代。史剧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的晋国还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魏国有一位武力高强的青年聂政,他因为小时候杀过人,只好到齐国隐没在民间,做一个屠狗之夫。他受到韩侯卿相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在母亲去世后,来到了濮阳见了严仲子。严仲子主张韩赵魏三家不分裂,联合抗强秦。但他遭遇到当时韩侯的丞相侠累的反对和排斥,他希望聂政能帮助他,把侠累刺杀掉,使国家不致分裂,人民免遭痛苦。聂政认为这是正义的事情,慨然应允。
聂政来到韩城,利用一个机会把侠累刺杀掉了之后,他自己也自杀了。但在自杀之前他先把自己的容貌毁掉,使韩城的人不能把他认出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的姐姐,不连累姐姐,因为他的姐姐聂与他是孪生姐弟,相貌十分相似。但聂知道后,与爱着聂政的姑娘春姑,来到韩城认尸,她们为此也都死在这里,为的是要把聂政的英名宣扬出去,不能让他白白死去。《棠棣之花》的整个的历史语境是郭沫若构想的。拿《史记》来对照,严仲子与侠累有仇怨是真的,但严仲子与侠累的分歧是主张抗秦还是亲秦,主张三家分晋还是反对三家分晋,完全是郭沫若的艺术构思的结果,总体的历史语境是作者重建的。作品中重要的人物酒家母、春姑、盲叟、玉儿,及其整个的人物关系,聂政与姐姐是孪生姐弟等等,都属于重建历史世界过程中的合理想象。至于剧中另一个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人物韩坚山,《史记》中只字未提到。所以,写历史文学不是写历史,不必受历史文本的束缚,可以按照历史文学家的艺术评价,重新构建出一个历史世界来,把古代的历史精神翻译到现代。然而,如果我们对照司马迁所写的《刺客列传》中聂政的有关段落,那么我们会发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虚构,作者的确抓住了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聂政确有其人;他确有一个姐姐;他因为“杀人避仇”而到齐地当屠夫是事实;严仲子曾亲自去齐国拜访他,请他出山,他以母在暂不能受命为由没有同意,这也有记载;母死后他来到濮阳,见严仲子,毅然受严仲子之托而刺杀了韩相侠累也是真的;甚至他杀了侠累之后自杀前自毁容貌都有文字可寻。
可见,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创作的确是有历史文本作为根据的。换句话说,历史文学又要以历史文本所提供的事实为基本依托,在历史框架和时限中重建历史世界,展现出艺术的风采。所以,我认为历史文学作品的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所谓“重建”可以大体概括为三点:第一,重建的根据:把握和发扬历史精神;第二,重建的空间:只需符合历史框架和历史时限,不受历史文本的束缚;第三点,重建的关键:艺术世界的完整性。第一点,我将在第二节具体论述,第二点则是常识了,上面已经反复讲过了。第三点最为重要,因为历史文学是文学,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世界,必须是完整的、自成一个天地的、自构一个系统的。史学家追求的主要是历史真实,零碎的东西对他们很重要;文学家追求的是艺术,零碎的真实没有意义,唯有展现整体的世界,才会具有艺术的印记。#p#分页标题#e#
隐喻现实世界
现实生活无限丰富多彩,无限生动活泼,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从中寻找到无限的诗性,寻找到无限的戏剧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却对现实生活似乎视而不见,总是扭过头去对那过去的历史情有独钟,愿意去写历史,愿意去重建艺术的历史世界呢?这里就关系到一个作家重建历史文本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这是历史文学作品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历史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常常令人惊异。但经常出现“历史的重演”。在这“重演”或“重复”中往往蕴涵宝贵的“历史精神”。什么是历史精神?我认为就是反映人民的利益、希望、愿望和理想的精神。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精神,才能称之为“历史精神”。例如,爱国主义精神、以人为本精神、望合厌分精神、精诚团结精神、天人合一精神、清廉洁净精神、临危不惧精神、直面现实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等,都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些精神在更高阶段上的重演或重复。这样,历史精神就往往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似乎更能清楚地看清现实的种种问题和可能的演变。因此人们很重视“以史为鉴”,力图在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掌握历史精神,并以此映照现实,采取措施,使现实不再陷入历史的死胡同,不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要知道,我们处在现实生活中,现实与我们离得太近,或利害相关,不得不装聋作哑,明知故犯;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习焉不察,常常看不清楚现实真相。但是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则可以拉开距离,可以居高临下,可以看到远方已经起火,那火正在向近处蔓延,危机或灾难已经迫近。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学做家还可以把握历史精神,挖掘历史精神,重建历史情境,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所以在历史和历史文学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也更具有美感。
这就是历史文学家钟情于历史的原因吧!也是现代人需要历史想象的原因,需要把握历史精神的原因吧!那么,1941年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写了历史剧《棠棣之花》,这是举起什么样的镜子呢?他看到了什么危机呢?郭沫若自己说:“《棠棣之花》是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合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鉴今,所以这种参合我并不感其突兀。”〔1〕原来,《史记》只写严仲子与侠累“有谷卩”。“谷卩”即“隙”,就是仇怨,他们之间有何仇怨,《史记》没有写。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则把三家分晋的事情结合进去,这样就成为了是主张统一还是要搞分裂的斗争,是联合抗秦还是单独亲秦的斗争。郭沫若在1941年写历史剧《棠棣之花》,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黑暗时期,就是以要团结反分裂的历史精神警示人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我们应该做出何种选择。所以《棠棣之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一面镜子,就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在历史文学中这种以历史精神警示现实的功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说“影射”,即以古代的人与事影射当前的人与事。如说“翻译”,即把古代的精神翻译到今天来。最为流行且影响最大的说法是“古为今用”,强调“用”,写古代的人与事似乎只是一个躯壳,对比性地说明现代的一个道理,才是真正的“用”。这样就把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寓言化。我总觉得这些说法都有一点“急功近利”,在这种思想和说法指导下去写历史题材,被写的历史变得不重要,而为现实服务才是根本。并且作为历史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失之于浅露、直白和机械的生硬的类比。时过境迁,“用”的功能丧失,也很难作为真正的艺术品流传下去。
因此,对于历史文学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想用“隐喻”这个概念更为恰当。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用言语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棠棣之花》是一个重建起来完整的历史世界,但这个世界中的反分裂的历史精神(彼物)被转移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此物)中来了。对于历史文学作品来说,隐喻也大体可概括为三点:第一,隐喻的根据是现实中的问题,历史文学不但不回避现实,恰好是要针对现实,没有现实针对性的隐喻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隐喻的关键是必须要深幽、隐微、曲折、朦胧,让人觉得作品完全是在写古人的故事,并且那故事有自己的艺术逻辑,不直白,不浅露,历史对现实的比较在那里似有似无,似是似不是,似可言又似不可言,直奔主题的隐喻没有艺术特性,可能成为借古人的服装演出现代人的戏;第三,隐喻的艺术理想是要为它所构造的艺术世界着色,应更有氛围,更有情调,更有韵味,更有色泽,因而更具有审美品格,更具有艺术魅力。
暗示哲学意味
人们需要历史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需要它来隐喻现实吗?郭沫若有一个说法,他说:“总结写历史剧主要有三点:一是再现历史的事实,次是以历史比较现实,再次是历史的兴趣而已。”〔2〕这实际上道出了历史文学作品的三个层面,“历史的兴趣”就是历史文学作品的第三层面。“历史的兴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历史场景往往具有戏剧性,或说得宽一些,就是文学性,如历史场景那种氛围、气息、情调、韵味、色泽等,大体相当于“赋比兴”中的“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诗经•周南》中《桃夭》的第一节,意思是说,桃花开得红艳艳,这个姑娘出嫁了,找到了一个好家室。“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所谓的“兴句”,它所描写的场景似与第二句“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似有关又似无关。说无关,找不到直接的联系,说有关,似乎是借桃花的风调来烘托姑娘出嫁时候的红火、热闹的气氛、情调,仅仅一句“之子于归”是没有“兴趣”的,现在有了前面的句子“桃之夭夭”就有“兴趣”了,这“兴趣”是通过“兴”而获得的。历史文学的情形与此相仿。作品中所写的“历史的事实”以及“以历史比较现实”,如果只是机械地生硬地去写,那是不会有氛围、气息、情调、韵味、色泽的,不会有文学性,不会有兴趣。必须透过对于历史场景的艺术的渲染,像依托诗中的“兴”那样,历史场景才会获得一种让人品味不尽的艺术氛围、气息、情调、韵味、色泽等,“文学性”、“兴趣”才会油然而生。但是我觉得把历史文学作品的深层仅仅归结为“历史的兴趣”和“文学性”是不够的。真正的历史文学作品应该通过历史场景的描写延伸到人生“哲学意味”的呈现。“哲学意味”这个概念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p#分页标题#e#
他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3〕这就是说历史文学作为一种诗性的活动也是哲学活动,同样可以达到对于人生真谛的揭示。在亚里斯多德以后的大约两千年,法国作家加缪也说:“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4〕实际上,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提出文学源于“道心神理”,也是讲文学的哲学意味,与后来韩愈讲的“文以载道”殊异。那么哲学意味是什么呢?“哲学”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意味”则是“形而下”的、感性的,“哲学意味”就是作品中所暗示出来对人生真谛的那种可言不可言、可道不可道的状态。历史文学若要达到极致,像其它伟大作品一样成为不朽的经典,就不能停留在对于历史的重建上,不能停留在对现实的隐喻上,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有暗示人生“哲学意味”的效能。那么,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是否有“哲学意味”,由谁说了算?是作者自己说了算,还是由读者说了算?有的作者过于骄傲,常把自己的平庸之作说得天花乱坠。但有的作者则过分谦虚,讲自己的作品“过时”了。郭沫若就属于后面这一类。他的史剧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翻译成俄语,在苏联发行。郭沫若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一文中认为,他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它所针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他“耽心”这个剧本不一定能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因为它“很快地失掉了象征现时代的那一段意义”。郭沫若的“耽心”是多余的,他的《屈原》不但在当时受到欢迎,就是在今天仍然受到欢迎。在现今的中学和大学的教材里,《屈原》仍然闪耀着它的光芒。郭沫若自己没有看到他的《屈原》所暗示的“哲学意味”,但读者发现了,众多的读者发现了。
这里且不说常为读者津津乐道的第五幕的大段的“天问”式的“雷电颂”充满哲学意味,就整个故事而言,我觉得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险恶和人生的温暖。剧中人物南后竟然是那样阴险,在几秒钟前还让屈原兴高采烈,觉得他的《九歌》在南后的改编和导演下变得那样美丽,就要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当着楚怀王和秦使张仪等人的面演出,可几秒钟后在楚怀王等人进来的一瞬间,南后假装站不稳故意倒在屈原的怀里,诬陷屈原要调戏她。人生的险恶只是顷刻间的事情。你不要认为你一切都很幸运,也许再过几秒钟厄运就会降临。但人生也有温暖,如郭沫若的朋友徐迟所说的“人间的阳光”。屈原遭南后陷害,以为再也没有洗清之日,但剧中人物“钓者”,竟然就是目睹屈原遭受南后陷害的证人,他的突然出现,洗清了屈原的不白之冤,这不是人生的温暖吗!婵娟被抓到宫中的牢里,以为必死无疑,但看守她的卫士甲良心发现转而帮助她脱离险境,这不是人生的温暖吗!屈原最后眼看要被毒酒害死,但这酒无意间被婵娟喝了,婵娟替他死了,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温暖吗?对于人生,险恶和温暖并存,这就是《屈原》暗示给我们的难以言说的真谛。它让我们激动,让我们沉思。历史文学中的哲学意味大体上也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这哲学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第二,这哲学意味是从作品的整体中透露出来的,不是个别细节插入;第三,哲学不同于常识,因此历史文学中的哲学意味应该是深刻的,它像火种那样点燃人生的希望,像阳光那样照亮人生的道路,像魔镜那样照耀人的心灵,让你的灵魂阴暗无所逃遁。历史文学三个层面:重建———隐喻———哲学意味,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重建完整的历史世界,才能艺术地隐喻现实;而哲学意味则不是外加的,就在重建、隐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