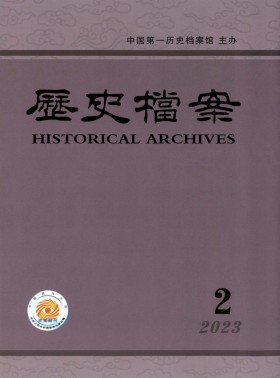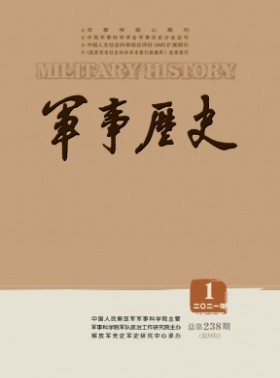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历史文学的价值取向,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历史文学的古为今用是个传统的话题,古往今来谈论很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不少应该探讨的向题尚未很好地展开,例如古为今用原理及其两极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研究就是两个薄弱环节‘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可资满意的理论析说.即使有,大多也倾近于经验感性的颖悟而显得比较粗浅。在文学领域中,“单凭经验性的观察决不能充分地证明必然性。”①因此,这就不仅影响到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反过来给它的创作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制约。实践证明,古为今用原理及其两极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仿史文学创作中的大端问题。深入地就此展开探讨,对当代历史文学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古为个用的基本原理
历史文学为什么可以而且必须古为今用?这里归纳起来‘,其主要的理论缘由有以卞这样三占.
(一)古为今用的原则是以古与今即历史与现实虽不相同但却具有某种内在的继承联系作为自己的逻辑基点。历史辩证法向我们表明:历史的发展是以螺旋型的形式上升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在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重复出璐,因而历史与现实是割不断的,它在不饲的阶段,常常会发生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像旧东西的回复.”②用系统的眼光看问题,•把古为今用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历程中考察,历史不是节节逝去的外在事物,而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发展着的人的本质力量,丰富和展开的过程,它们在精神主体上彼此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今天是昨夭的发展,不可能不留下昨天的痕迹,昨天是今天的由来,也必然能从中找到今天的某些渊源‘因此,要把握厉史、就不能人为地分割过去与现在,而必须将它们视为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乌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把钥匙。下等动物身上透露的高等动物的预兆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③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情同此理:对现实社会中一某些事物的理解,有助于理解历史中与此相通相近的事物:反之.对厉史的重新认识,一又能促进对现实的深;刻的理解。因为诚如奥特加和科林伍德所说,“厉史是一干体系,是全部人类经验之联成为一个单一的、无可抗拒的链锁体系”④,’它的历程无始无未而只有“转化”、历程Pl转化为P2,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标志着Pl的结束和PZ的开始、内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而成为PZ。PZ也并没有开始,它以前就以Pl的形式存在着了。一部作品引进的事件可以有其开始和结束,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本身却没有开端和结束,只不过被纳入下一种形式即PZ并和它融为一体而己。⑤西方存在主义从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存在观”出发,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了明显的偏狭和极端,他们完全抹煞现在与过去的因果依存关系,认为古今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异质性”,现在的一切都与过去无关,它只不过是人为了现实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自我“设计”。⑥他们这种所谓的“时间辩证法一点也不辩证,不独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古为今用的论述相抵悟,就是与奥特加和科林伍德提出的“历史是一个体系”、“历史转化说”相比也大相径庭。因此,在这些人的眼里,古为今用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合理的正确命题。
(二)强调古为今用,是以价值论作为它的哲学基础。根据最近有的同志的研究,认为哲学应该包括认识论和价值论两方面内容。认识论是研究人对客观世界本身固有属性和规律的掌握,价值论则研究主体的需要及对象的价值属性。这两方面在实践论基础上得到统一,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哲学思想。离开了认识论,价值论就失去客观依据而导致唯心论;离开了价值论,认识论就成为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只有二者互相联系又互相依存,才能避免片面的客观性和片面的主观性真正上升到科学的高度。⑦历史文学所以要古为今用,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历史文学真实作为人类精神形态,它既包括认识方面也包括意向方面,如果仅仅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角度进行阐释,还不能说明它的审美活动的本体价值、它的意向归宿所在。人创造精神文化以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有益于自身,协调与现实的关系,达到对象的本质化。作家进行历史文学创作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总是挑选在他看来于“今’,有用的史实对象。历史文学真实当然必须是文学的,它是属于文学功能圈范围的真实;但历史文学真实又从来都不仅仅是文学的,它从来不仅仅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真实形态的体现,而且也是社会意识、政治意识、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尤其是忧患意识的体现。为历史而历史、为真实而真实固然可以宣称“永恒”,却永远得不到为人生为时代的艺术的博大深沉、痛切热烈.雨果说得好:对于一个历史文学作家来说,“自以为超越共同利益和民族需要之上,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对当代人有所影响,把个人的利己生活和全社会伟大的生活隔绝起来,这是一种错误,而且是犯罪性的错误。如果诗人不献身,那末谁献身呢?如果竖琴的声音不去平息风暴,那末什么声音会在风暴之上升起?如果既具有古代智慈所赋予的调和人民和国王的能力,又具有近代智慧所赋予的分化人民和国王的能力的那种人,不去触犯无政府主义的仇恨和专制主义的轻蔑,那末又有谁去呢?”⑧他的话与我们此说的价值论无疑是十分相吻的。从哲学的语言讲,这就叫物的有用性或主体需要的对象化,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体现。日本学者中岛碧在《郭沫若史剧论》一文中批评中国的历史文学普遍具有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等目的,并说他们日本的历史文学便不复有这样明晰的特征。⑨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日本历史文学创作古为今用特征也同样十分明显。就拿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来说,这之中大量地出现写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人物和北方领土回归题材,就是为了激发日本民族经济赶超欧美大国、收复被苏联占领的北方领土的目的之需‘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了哲学价值论存在的不可抹煞和无法超越。客观情况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又怎么能否定古为今用的合理性呢?
(三)强调古为今用,还与艺术是通过社会中介项进行消费、协调主客关系的功能特征密切有关。早逝的英国美学家考德威尔在他的《论美》中指出,艺术创作总不免存在主客体关系矛盾的问题.如何调和这种矛盾呢?他认为主要靠主客关系里的“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与个人对立的人群—就是社会”。一因为作为主体的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客体的环境对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就是真正的中介项”,只有通过社会的联合调节,艺术才能成为‘种消费,才能产生真和美.⑩考德威尔的论析殊为探刻。的确,不管客体还是主体,无论它们怎样客观或主观,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或一部分,它们必然烙上社会的因素,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作家主体之于史实对象是有选择的,他只能接纳他所感兴趣的那部分。⑩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主体的这种选择并不是作家个人“纯主观”的一厢情愿,它同时还暗含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指向.为什么拿破仑建立帝国之时,西欧许多国家的作家不约而同地从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养料进行历史文学的创作,为什么抗战之时我国大后方的作家纷纷青睐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一时形成了历史文学(主要是历史剧)的大潮,这之中就有鲜明的时代因素在起作用。它与其说是作家个人的主观选择,还不如说是时代社会的选择。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融时代社会选择于作家个人主观选择之中,或者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归结到心理学上讲,就是“意识不是在刺激物(作用于人脑的事物)的影响下人脑某种神秘的放射意识之光的能力的表现,而是人们所参与的并通过人们的头脑、人们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所实现的那种特殊关系即社会关系的产物。”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他永远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即使他最忠于自己,矢志真实,他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一定的社会心理。#p#分页标题#e#
二、古为今用两极不同的价值取向
然而,以上仅仅是历史文学古为今用的前提条件。所以古为今用是一回事,怎样古为今用又是另一回事。而后者事实上才更具时代旨趣,也更合乎历史文学创作的实际。因为不要说今天就是在过去,将历史文学创作视为单纯的为古而作或文字游戏的毕竟微乎其微,不会有多少市场。人们分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怎样古为今用”即对古为今用采取怎样的价值取向上.这才是问题的关彼所在。那么,历史文学古为今用的两极取向到底又是怎样表现的呢?我认为按内容、性质划分,不妨可以试述如下:一种极向的古为今用可以称之为广阔的或者开放的古为今用,它的对象范围是很广大的。
凡是有益无害于今天时代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内容都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概念。不一定打倒了写吕后,今逢改革写李世民。茅盾六十年代初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认为以下五种方案都属于古为今用的范围:(1)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对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思想教育;(3)强调历史题材之积极的、符合今天需要的部分而删去或者修改其消极的不符合今夭需要的部分,(4)可以为今天鼓舞人心、加强斗志的助力或借鉴;(5)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对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茅盾的概括着重于题材内容方面。从美感作用来讲,凡是具有娱乐性,能调剂生活情趣,为读者喜闻乐见,就算做到了“为今用”;从教育作用来讲,凡是能培养高尚情操,提高读者品格修养,就算做到了“为今用”;从认识作用来讲,凡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能增进一点历史知识,开阔读者的心胸视野,就算做到了“为今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历史文学与其他品种相比之下,它的功利性、目的性常常是最间接的,它最长于潜移默化而短于立竿见影.在过去斗争酷烈的非常年代,民族存亡系于一发,人民处于内忧外患的生死关头,民族性、阶级性的内容压倒一切,作家创作的题材内容多集中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必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然而,美的愉乐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⑩现在时代变了,我们的社会早已告别了黑暗离乱洒进入了比较平稳的和平时期,原先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已被经济建设所代替,在此条件下,我们就应顺时应势地将“为今用”的范围扩大,而不必像过去那样把眼光吃紧地盯在能直接煽起人民阶级、民族情感的题材内容上面;除了反动淫秽、迷信落后的东西外,其他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创作的视野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写“今用”性较强、社会涵义较深的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重大题材,也可以写“今用’,性颇淡、审美价值颇高的历史文学“美文学”,还可以写娱乐性很浓、趣味性很足的历史传奇或历史通俗文学。如果说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方面的题材内容主要功能是给人以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理性教育,那么后两类作品的现时价值就是通过较纯粹的审美观照和富有趣味的精神宣泄,来陶冶人们的情操,慰籍他们的娱乐心理,这也是古为今用。当人们的生活一旦摆脱了灾难忧患而进入了正常运转的轨道时,当人们在为社会也为自我存在发展紧张劳作、精神灵魂过于疲惫或郁结的情怀无处排解时,给他们来点审美的东西,提供一些娱乐性的内容,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也许有人洁问道“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西方现代历史文学中颇流行的“单纯消遣”倾向,并认为这是不足取的吗?⑩是的,但正如那篇拙文说,西方消遣之作之所以不足取,主要在于它的创作旨趣消极颓废、逃遁现实;在于它完全堕入猎奇、癖好者流中。至于消遣所对应的宣泄快感而又维持心理平衡的娱乐性、趣味性,笔者并没有否定,也不应否定。积极健康的娱乐以及超离一点理性教育的纯审美是对文学与大众欣赏趣味、审美水平之间固有矛盾的一种调节,也是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剧变的一种有效的疏导,只有这种调节和疏导工作同时做好了,那些富有很强现实性、很深社会涵义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之美的内容才能真正有效地被人们所吸收、转化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随着现代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不仅是整个时代社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对文学的需求也愈来愈趋向多元:娱乐、审美和受教,我们都需要,缺一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我们对继《李自成》、《大风歌》、《秦王李世民》、((秋瑾》、《谭嗣同》之后,我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些通俗历史文学和带有纯审美意向的历史文学美文学如《括苍山恩仇记》、《津门大侠霍元甲》、《少林寺》、《东陵大盗》、《绝代名妓》、《梅妃怨》等等,不仅感到容易理解,而且有些篇什阅读欣赏起来还别有趣味,收益匪浅。历史文学古为今用的广阔性,在今夭已经愈来愈明显的显示出它的潜力。
另一种极向的古为今用与之不同,它从范围到观念都是偏狭的,这是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在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不防称之为狭隘的古为今用。以“史”的眼光观照,狭隘极的古为今用在旧时代无疑更为盛行,也更有市场。最典型的也是最恶劣的例子是明臣郭英的后代郭勋为了咨自己争位,托名写了《英烈传》为祖宗邀功。当然,这样的现象毕竟比较少见,就多数情况而言丁其根源主要还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用以及作家自身为浓厚的封建思想所囿这两方面。前者如清统治者为了笼络蒙古诸汗,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对《三国》中的忠义之臣关羽极尽算崇,将这部演义降为政治的简单附庸和工具。后者如写于康熙年间的《女仙外史》,述青州农民首领唐赛儿事迹,为了达到以表“正名讨燕(燕王)之旨”,弘扬封建正统思想,作者竟将史实改得面目全非:唐赛儿成了月宫里的嫦娥降世,学了道术后遂成“能上天入地的活神仙”,而永乐皇帝朱棣则是天狼凶宿下凡,因在天庭侮辱嫦娥,“转生到下界,两家便成为敌国”。唐起义后,迎汽辟,妨故主……还有像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拉辛等不少作品也都明显如此。他们为了阿谈王权和取婚时俗的所谓“劝善”、“典雅”,不仅让人物在舞台上不时地进行大段大段的抽象说教,而且还十分可笑地叫其满嘴尽吐高贵的言辞,如勒古维的《亨利四世》,亨利四世一句“我希望我的王国的最穷苦白尔农民至少在礼拜日能吃到炖鸡”,为显得高贵和典雅,竟让他说成这个样子:“旋之我希望奋在标志着休息的日子里,住在贫苦村庄里的一位勤劳的主人,多亏我的善举,在他那不太寒酸的餐桌上,能陈列几盘为享乐而设的佳肴。”这简直是拿历史真实来玩。#p#分页标题#e#
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是流行于现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狭隘极的古为今用。按说,到了大工业出现的近代无产阶级的时代,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学创作中,这种狭隘极的现象一直不绝如缕,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有时候甚至达到惊人的地步。如苏联在斯大林当政期间拍摄的颇多历史影片,包括《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等,其中列宁每到一处,身边总跟着斯大林这位“首席战友”,至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列宁那时的其他战友,即使在1918年,也被描写成资产阶级侦察机关的特务。更有甚者,有的竟然把沙俄反动军队美化为欧洲人民的解放者,连起码的历史真实都不顾。我国建国后的历史文学创作也有这个问题。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历史剧大讨论,它所反映出来的间题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在这相隔十年的两次历史剧创作高潮中,相当多的作家,出于古为今用良好愿望,竟这样不顾一切地生拉硬扯,将历史与现实简单附会在一起:为了歌颂“抗美援朝”,宣传“保卫世界和平”,有的写信陵君“窃符救赵”、古代晋国“假道来藐”的剧本叫信陵君等具有国际主义思想,让古人口中唱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赞扬劳动创造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帮凶及帝国主义分子,有的取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剧就不时地让和平鸽和象征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破坏分子鸥果进行斗争,还叫老牛唱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为了配合“反修”的需要,有的描写吴越战争的剧本,非但要两千四百年前的越国有妥协分子,有恐吴(吴国)病者,而且还叫他们的言论极像“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歌颂、大炼钢铁,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就有声有色地描写越王勾践领导人民大兴水利、大炼钢铁,还请了外国专家来越国帮助铸造武器、改良农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五十年代初期那一次,由于“批判受电影《武训传》运动’渐催发的“左”倾情绪的影响,此种倾向在当时还俨然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戏改方向”自居而碰不得。可不是吗,当有些同志对庸俗化、狭隘化的古为今用提出正确批评时,负有戏改一定领导责任的杨绍置便气势汹汹的贵间批评者“这是替谁说话‘,,这是“打击了革命而便宜了敌人”,将其扣上"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什等帽子。“上纲上线”到了吓人的高度。当时以及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杨绍置和与他相同观点人的创作及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实际结果是让人感到幻灭;到头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也没有给当时的社会提供真正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杨绍置等人急切地想要“为今用”反而事与愿违呢?这里的症结,主要是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理解得简单和机械。首先,他们没有认识到古为今用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旧时代是可取的或不得不然的做法;在今天伴随时代的变化,就可能变成不可取或不必要。质文代变,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阶级关系毕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也是颇吻合的几因此,我们在创作时如果简单地将昔日惯用的“影射”、“类比”之法搬引到现代生活中来,无疑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次,退一步说,即使这种以政治实用、政治急用为目的的历史文学也算是一种古为今用的话,那也只能是低层次的古为今用,它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所实践的通古鉴今、历史感与现实感高度统一的追求目标距离未免太大了。这样的古为今用,从文艺社会学角度讲,如黑格尔批评的,它只是把艺术的目的仅仅“狭窄化为教益”,而看不到它的“快感、娱乐、消遣”作用⑩,从正确的功利观完全滑落到“只是被使用或被利用来作为工具,或实现一个自身以外的目的”的实用主义档次上⑩。从历史文学本体论角度讲,它忘记了历史文学不同于一般的现实题材文学,它的“为今用”有其自我的独特性:它的题材对象与作家创作关系,不像现实题材文学那样处于共时态的一个时代,可直接反映现实和干预现实;而是中间隔开少则上百年、多至几干年的距离,彼此有时间的鸿沟,有观念的变换,只是相通、相似而不是也不可能相同。所以,它在这里的现实作用是间接的,主体感悟的暗示,触类旁通的联想,比之简单的影射、比附就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写过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的老作家肖军说得好:“历史既不可能单纯的重复,由此把今天的社会现实,和过去的历史硬粘贴在一起.加以‘比附援引’这是很危险的。历史之所以称为‘历史’,就因为它毕竟属于‘历史’范畴以内的事了。我们利用历史材料创作艺术作品,援引历史上某些故事、语句……作为今天某些问题的比拟、说明……等等,这只能从其中寻绎出它的一般发展规律,有某些典型性的、类似性的……东西,作为我们处理当前现实的一种借鉴、一种参酌、一种启示、一种标准••一之用而已。所谓‘古为今用’,它的意义应在这里。”⑩高层次、高质量的古为今用都是如此.曹禺执笔,梅叶、于是之共同创作的《胆剑篇》所以高出同题材百来个卧薪尝胆剧本,“能够有更上一层楼的成就”(茅盾语),主要就在于突破了当时盛行的以古喻今、以古证今、以古类今的狭隘创作观,富有成效地实现了肖军所说的“借鉴”、“参酌”、“启示”、“标准’,作用即所谓的间接的“为今用”。应该看到,今天时代的人们因和平环境的影响作用,阅读欣赏历史文学在情感上心理上与过去是不大一样的,他们一般不会带着太直接太强烈的功利心。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社会条件下广阔极古为今用的历史文学作品较之以影射、类比为主要功能特征的狭隘极之作有更广大群众的社会原因吧。
这一点放在文尾论说也许不无必要。不仅是狭隘的古为今用,就是广阔或开放的古为今用也总是相对的。作为一种多元动态的而非单一静止的人类经验和情绪的复合产物,它不能不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始终包含着朝向新经几验的倾向。”⑩当我们说它狭隘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对它采取一种历史的态度;而当我们称道它广阔的时候,难道就可以认为它有超然于历史的特权吗?既然人类的经验和情感、人类的思想和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那么,他们对历史对象的价值评判也必然以开放的、变化的与发展的形态出现,具有永远走向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的特征及可能。从系统的眼光谛视,处在社会无限发展的一个中点上的人,他的认识总是有限的,甚至不无片面与不成熟。这样说绝非倡导无是非、不可知论,而是站在一个更高远、更辽阔的境次看待包括艺术审美在内的人类功利,它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链条的“有限”环节中更好地认识自我历史使命,获得与历史相谐一致而又富有活力的开放意识。事实确实也是如此,以中外文学史上为数颇多的民族题材为例。不可否认,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创作时无疑是带有鲜明的“为今用”的民族思想倾向和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自然也有进步和落后、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即使是进步和正义,不也是一种历史范畴的东西吗?如果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对它进行深刻的反思,它的先在的局限和狭隘性有时往往也很容易找到。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把法国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写成自私、虚荣、邪恶的化身,从他自己本民族的立场出发是可以理解的.苏联“莎学家”阿尼克斯特曾指出:《亨利六世》将平常的封建主与侵略者塔尔博写成一个爱国英雄,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待的。他在剧中所以丑化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原因就在这里.”⑩但是,当我们一旦跳出民族思想情感的纠葛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观照,就感到他的如是处理有失公允。《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作者巴勒克拉夫说过:“获得民族独立以后,亚洲历史学家—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很自然地集中于发掘本国过去的历史,尤其是集中于反对前辈欧洲学者对历史所作的‘殖民主义’解释。迄今没有任何人否定过亚洲历史学家这种反应的必要性及其有益之处。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承认,从长远看,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神话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的神话同样是劳而无功。……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树立至今尚未树立起来的那种立足全世界的观念。”尽管巴氏这段话是就历史科学研究而论的‘,但我以为它所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创作同样真有参考价值。情况既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已然广阔的古为今用就是绝对恒定了的呢?怎么能用静止的非历史的方法对它进行评判呢?在“古为今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像巴勒克拉夫所说的树立起“立足全世界的观念”,让自己的思维与时代同步对应地开放广大.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古为今用,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或理论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