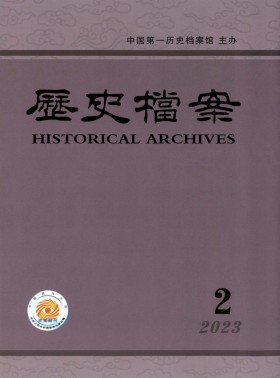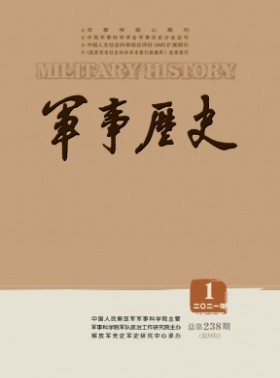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历史文学真实的现代转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所说的“两度创造”,是指历史文学以历史真实为基点参与现代消费的一种能动的转换过程,其意相当于黑格尔说的“既真实而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或伽达默尔说的“效应历史”,它是历史文学实践性很强而又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命题。但过去有关的历史文学研究,我们往往不是将它忽略就是用简单的机械还原论进行解释。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既有悖于创作事实,又缺乏理论的内在逻辑。实践表明,从原生态的已然历史到创作而成“为今用”的历史文学文本,这一整个的转换过程,对历史文学作家来讲,就是从原生历史心理历史审美心理历史的转换过程;而就文本创作的角度来看,则就是从历史真实到现代消费的“两度创造”即语言形式创造和题材内容创造的过程。所谓历史文学真实,严格地讲,是历史心理化与心理历史化的有机统一,是后(今)人以社会心理为中介、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对历史真实的一种富有理性的现代转换。
一为什么作家的文本创作首先要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改变呢?因为他们选择的历史题材对象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它所创造的艺术成品则属于现代精神文化消费的范畴,两者由于时间鸿沟的作用,彼此在语言表现方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诸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过去耳语惯熟的用语,在今天听来可能稀奇古怪,十分生疏隔膜。譬如“冰人”、“致仕”,除了少数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史家外,现在能有几人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人”和“退休”?古今表现形式上的这种差异,给历史题材的现代消费即古为今用设置了为现实题材所没有的特殊难度。很显然,如果我们的作家为了所谓的“真”,让人物在作品中特别在舞台屏幕上漫口说诸如“冰人”、“致仕”之类的“当时语”,那么读者和观众一定如堕云雾之中,他们只好用西方喜剧《锁》中人物芒戈批评摩里特里安人的音乐所说的那句话来对付作者:“俺要是听不懂,就算听得见又有何用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目前西方有人提出的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将莎士比亚史剧适当浅显化现代化的主张作法原则上表示赞同。这倒不仅仅是一般观众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只接触语体文而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无韵素诗感到陌生,更主要的是为莎剧能藉此与缓缓有所变易的新时代的观赏者互通声息,焕发新的艺术美感。借用英国历史教授罗恩的话来说,就是“我要让莎士比亚活在世上,而不能老是让人把他搁在冰箱里”(1)。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非常赞赏郭沫若、陈白尘早在50年前提出的历史文学不能使用真正的历史用语而只能采用“根干是现代语”(2)来进行写作的艺术主张,认为他们总结的“历史(文学)语言=现代语言,‘减’现代术语、名词,‘加’农民语言的质朴、简洁,‘加’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术语、词汇”(3)这样的语文公式,虽嫌简单但却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可谓触到了问题的本质。
文学史上,对社会变更而造成语言形式变易规律有所察知的,历来都有。如我国唐代刘知几在《史通•言语》篇中,就曾鲜明地提出了作者应在书中运用当代语记事而不可“稽古”的主张,他说:“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时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刘知几斯论主要是针对史书记载而发。史书崇尚实录、讲究科学性准确性况且也要反对语言“稽古”,那么作为艺术创造的历史文学就更不用说了:它怎么能够置当代读者现时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于不顾,偏要“追效昔人”,给他们本来愉悦易解的审美接受人为地增设翳障呢?自然,在这方面说得最深刻的还是德国美学大师黑格尔。为什么历史题材向现代消费转换时必须要在语言表现形式上进行一度创造?包括刘知几在内的多数哲人都是从艺术的通俗化或质文代变的观点予以解释。黑格尔的深邃就在于,他认为这种创造主要还是为艺术自身的特有规律所决定的:“艺术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它可以破坏所谓“抄肖自然”的原则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虚构创造。他举例说,“在特洛埃战争的年代,语言表现方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还没有达到我们在《伊利亚特》里所见到的那样高度的发展,希腊人民大众和王室出色人物也没有达到我们在读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和更为完整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时所惊赞的那种高度发展的思想方式和语言表现方式”。但这种改变对于创作来说却是许可的,不能与“反历史主义”相提并论;只要表现品的内在实质没有变,它都属于正常的虚构范围而不应受到指责。为什么这样说呢?黑格尔极富见地地指出:这是因为“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它也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民的,也用不着凭广博的知识就可以懂得清清楚楚,就可以使我们感到它亲近,而不是一个稀奇古怪不可了解的世界”(4)。
实践雄辨地证实了刘知几、黑格尔上述道理的正确。它告诉我们语言形式的改变与否以及改变得当程度如何,不但对历史文学的本体价值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而且有时甚至还直接关乎它的成败毁誉。以英国18世纪初著名艺术家、考古家斯特拉特的历史传奇《奎因瑚大厅》为例,这部经西方历史小说鼻祖司各特续写润色的作品所以花时甚多而又未能取得预期成功、受人冷遇,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如司各特所说:“那是因为那位有才华的作家使用了过于古老的语言,同时又过分地卖弄了他的考古学知识,因此它们反而成了他成功的障碍”(5)。我国古典历史文学创作中类似的例子亦有不少。包括《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本来,早在晚唐时代,李商隐在他《骄儿》诗中描述他五岁的儿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已经可以证明那个时代“讲史”的艺人高明到至少能维妙维肖地扮演数个角色以致于儿童也能模仿这些角色为乐。但是到了《三国志平话》,作者虽然给了张飞以主角的身份,却没有利用他黝黑的皮肤或其他面部特征作取笑的材料。至于征服蜀汉的魏将邓艾就更差了,他充其量留下一个匆匆带过的名字而已。《三国演义》稍好些,编者毛宗岗在第一次提到邓艾名字时补充了他口吃的史料:新投诚的魏将夏侯霸告诉姜维,“艾为人口吃,每奏事必称‘艾艾’。戏谓曰:‘卿称艾艾,常有几艾?’艾应声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但是在此后的叙述中,毛宗岗仅依照罗贯中的原本,用一种简洁的文体把邓艾的话记录下来,毫无口吃之象。美藉华人夏志清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表现形式一直都有个与说话传统艺人对抗的问题,他们的作者虽然远比说话艺人有学问,但由于以所谓高雅古朴为鹄的,不从谈话人那里吸取艺术营养,因此在生动的写实上反不如说话人而显得刻板枯燥。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小说落后于西洋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6)。夏氏的结论是否公允可以讨论,但他所指出的现象则不容否定。这与刘知几、黑格尔以及三百多年前冯梦龙对文言小说所作“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7)的“稽古化”的批评,应该说是颇吻合的。在历史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可能是受崇史尊史思想观念的浸渗或文言文体的影响的缘故吧,我们历来总强调文要师古,辞要隐幽,语言“稽古化”的倾向一直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稽古”,从历史文学本体论角度看,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以欣赏者易解为前提条件的语文形式的一度创造;而归落到语言学的层面审视,它的问题主要在于向读者输送构成形象的信息时,因语言“稽古”或“稀奇古怪”不可解达不到应有的阈值。惟其“达不到”,它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引发读者的心理感应,使他们借运语言信息来调动自己的感性经验去充实、构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一个作品本体一旦失去了感应,那么它的一切的“真”就将变得毫无意义,根本不可能转化为现代的精神文化消费,即使具有最大的“为今用”的价值也等于白搭。#p#分页标题#e#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吧,文学史上那些社会责任感强、艺术经验丰富的历史文学作家才都那样殚精竭智地在语言表现形式上下苦功。他们从不以维护历史真实性为由,向读者和观念大摆凛然漠然的“历史架子”,兜售深奥生冷的历史用语;而总是采用为现实人们能够轻而易举欣赏接受、感到近切生动的语言款式。为了实现这一点,有时候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郭沫若的《屈原》,初版本开头写屈原朗诵《桔颂》,作者开始曾让屈原直接从《离骚》中照读原文:“后皇嘉样,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后来修改时,为了能使广大观众都能听懂理解,很快地进入审美享受,作者就遂将它翻译成颇带现代意味的白话诗文:“辉煌的桔树呵,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郭老的剧作为什么能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备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语言表现形式上的随时就势,力戒“稽古化”而赋予新的美感形态就是其中一因。
已故著名戏剧家焦菊隐曾称道郭老的历史剧创作,“是以科学家、历史学家在作渊博的准备,而以革命诗人在作丰富的构思,最后再以戏剧家的绚丽风格去落笔。”焦菊隐的话很值得玩味。我们的历史小说家在进行以语言表现形式为主旨的一度创造时,也应该象郭老那样把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禀赋发挥限制在“准备”阶段,而在“构思”和“落笔”时则不希望过多地显示科学家历史学家的渊博和细密。当然,这是语文的一度创造,小说与戏剧、影视因文体形式的规范不同,彼此在运用时是各有所别的。小说是阅读的艺术,它可以细细咀嚼,可以反复玩味;可以随时放下,也可以随时拿起,这都无碍于读者的艺术接受。而戏剧与影视是临场观赏的艺术,它是顺流直下,一泻千里,以直观的、连续的形式直接显影于舞台和银幕,不能有半刻的停顿,所以它在语言方面与小说的要求也是有所不同的。李渔说:“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明言直说。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8)。李渔说得太好了,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小说(广义的诗文)与戏剧(那时还没有影视)的文体自觉问题,这对我们历史文学作家怎样“度其体宜”(曹雪芹语)地用好语言关系极大。郭老的《司马迁发愤》在写司马迁在赶写《史记》末篇时与来访的益州刺史任少卿交谈一段情节,该小说结尾处,作者直接抄引了《史记•太史公自叙传》中一段颇有点长的文言文入书:“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作为文字,我们读到这里可能有点拗,但这无关紧要,你可以放慢节奏,细嚼慢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古味十足的文言,它给予我们以特有的历史感。这就是小说给我们的便利。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责怪郭老,反要感激他。至于戏剧、影视一般就不允许这样。如果它们的作者为了求得历史感,简单效仿小说作法而不“直说明言”,那么只会令观众如坠云雾之中;真则真矣,但历史感也就在这莫名其妙中被化为乌有。由此可见历史文学语言形式的一度创造,它其实是涵盖着复杂的文体因素,所谓的“熟悉可解”,只有与各自的形式规范的特点联系起来,才是可行的、合理的。
二历史真实转化为现代消费的一度创造表现在语言形式的改变上,二度创造则主要体现在题材内容的改变方面。为什么题材内容要改变呢?这是因为历史文学创作如同“凡人作事,贵于见景生情。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传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当与世迁移,自啭其舌,必不为胶柱鼓瑟之谈,以拂听者之耳”(9)。特别是考虑已然题材对象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往往是非掺杂,美丑并存,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些内容或已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或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日见突出,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截成抵牾,如封建伦理道德、迷信宿命思想、大汉族主义等等。这就决定了我们作家在创作时不能简单照搬历史,据实而作,而只有根据时代精神的需求对题材内容进行有选择有分析的处理。同样一个赵贞女题材,从南宋《赵贞女蔡二郎》到元末的《琵琶记》、清朝的《秦香莲》,其间七百余年之所以被翻来覆去地改变,道理即此。
同样一个诸葛亮故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把他写成唤风呼雨、神乎得有些“近妖”的超级智圣,而80年代李法曾主演并得奖的电视连续剧《诸葛亮》则将他处理为很具“人味”特点的古代智人,道理也正在这儿。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末的今天出现披发仗剑借东风之类的场面,总得有个契合时代、合乎情理的说法。我们总不能以“继承遗产”为由,象罗贯中那样抱着绝对忠信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去宣扬封建迷信宿命思想(当然也不能置原著于不顾,将诸葛亮面目尽改,赋予他以现代人才有的新的天地鬼神观)。
大家知道,真的并不等于美的善的,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它只有经过美的统纳和善的同化才和它们凝结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历史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自身,更取决于它与我们时代关系的功能特质。就是说,历史文本作为第一级存在,既有客观“范”式的一面,它并不随意听从后人的主观搓捏编派而更改自己的原生本体;而作为第二级存在,它又有主观“导”式的另一面,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我们留下某种理性规范、某种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可资现时活动参照的文本对象。真正的历史是不会凝固的,美也永不凝固,它们的内容在时间的长河中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我们固然可以说一部仅仅具有美的魅力和符合善的原则的历史文学作品未必就是好作品,但却可以说一部完全缺乏美的魅力和违背善的原则的历史文学作品必然不是一部好作品,尽管它的描写都来自历史,在真实性方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卢卡契在论述德国现代历史小说时讲过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当时德国不少作家“常常沉溺于描写残酷的处死和用刑等场面,而忽视了这一点:读者———正是在读一本历史小说时———极快地就‘习惯’于这些残忍了,并且把它们理解为所描写的时代的必然的特点,这样就失去了任何效用,也失去了宣传反对过去阶级统治的非人性的作用。”他认为在这方面老一辈作家“把古老的阶级统治的非人性中发生的人性的冲突推到描写的中心点上去”的写人方法值得效仿,因为它弘扬了人性,“根本不需要有效地实现残酷的法则”(10)。#p#分页标题#e#
卢卡契的见解是深刻的,他无意道出了历史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就是一切历史包括美丑善恶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作家写什么、怎样写,只能根据现实时代“对话”的审美需求;也只有根据现实时代“对话”的审美驱需,他才能对题材内容中美丑善恶的历史涵义进行增损贬抑的处理,特别是对那些有悖于时代旨趣的丑恶的、非人性的东西进行必要的淘汰剔除。古往今来的历史文学作家,为使自己的作品能畅通无阻地参与现实的精神文化消费,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作的。剔丑抑恶,这可以说是历史文学内容转换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面向读者、面向时代的作家的起码的艺术良知和社会道德的问题。拿我国人民非常熟知的昭君题材来说,为什么除曹禺的《王昭君》外,迄今有关此类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到昭君被逼出塞或半途殉身(纯系虚构)为止就煞住了,这里分明就有这样的含意。即便是正面直笔昭君出塞后生活情景的《王昭君》吧,曹禺也只是写昭君与呼邪单于“长相知,长不断”,维护了蒙汉之间的团结;至于单于死后的昭君如何“从胡俗”,嫁给了单于前妻的儿子,就一概避而不述了。因为这虽然是历史真实,如果不加选择地表现出来,那不仅有损于昭君形象的美,同时也为今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所难以接受;这毕竟是原始群婚制的余脉,愚味落后的婚姻陋习。再比如勾践复国题材,为何历来的作家几乎无不都抓住他的“卧薪尝胆”做文章,而没有听说有谁对他的“尝粪疗疾”进行刻意渲染。推究一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尝胆”和“尝粪”尽管都是历史真实,都能表现勾践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的精神品格,后者毕竟不雅不美,如果将它照实搬上舞台或银幕,就会使人不堪入目,恶俗至极,演员也觉得难以忍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灭。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11)。历史文学终究是一种精神性、情感性的艺术,它不能悖离现代人正常的人性和人情;也不能为了所谓的真,而置今天起码的伦理道德和审美特性于不顾。真要服从美,更要接受善的制导。难怪莱辛说:“身体苦痛的情况之下的激烈的形体扭曲和最高度的美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不得不把身体痛苦冲淡,把哀号化为轻微的叹息。这并非因为哀号就显出心灵不高贵,而是因为哀号会使面孔扭曲,令人恶心”(12)。
自然,我们这样说并无意于将审美的“淘汰剔除”当作历史文学内容转换的全部。从实际的创作情况来看,它往往是与作家“扬善崇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而且它也可以通过逆向或视点转移的艺术方法,将丑的题材内容转化为人们公认的审美欣赏对象。这也就是说,面对丑的历史与历史的丑,作家并非消极无为的,它同样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当代历史长篇《金瓯缺》中有关李师师与宋徽宗情感关系的描写,在这方面就很可佐证。本来,对这样一对名妓与昏君的风流艳事,我们当然毋须称颂,不仅不值得称颂,如果不加剔除地正面展开,恐怕还会陷作品于自然主义泥沼,招致其思想艺术价值的不应有贬损。《金瓯缺》的内容转换,其成功主要就得益于富有意味的理性淘漉和逆向性、视点转换的表现手法。对于李师师,他一方面着意表现她以“冷美人”的态度处置与宋徽宗赵佶的关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又强化突出她思想性格中的深明大义、嫉恶如仇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情感,赋予善的内涵;还用诗化的语言和诗化的意境,极写她的外形美、内心美。这样,原型形态中的否定性内容就很自然地变成了艺术美,以致我们挑剔的评论家看了也止不住惊呼:“李师师的描写是全书最美、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在历史上也许不存在的、动人心魄的奇迹”(13)。
而对于与李师师有关的宋徽宗赵佶,作者对其昏庸无能、灵魂可鄙一面进行了必要揭露,但也腾出许多篇幅,同时描写赵佶对真正心爱的人不忍用强的涵养和苦心,以及写了赵的高度的艺术才能,特别是作为“丹青妙手”的精湛造诣。作者甚至还用描绘李师师的诗化笔调,描写赵为李师师作画的情景,让人在一种浓重的艺术氛围中感受到这幅堪称神品的画的意境之美。至此,丑的历史对象和历史内容经过作家富有意味的加工创造,不着痕迹地升华为第二自然形态的艺术美。从这里我们可知,历史文学所谓的“逆向或视点转移”,其实就是作家按照善的原则和美的规律对否定性历史内容的一种对象化的认同,它是集客观的社会性和作家主体的审美理想于一体的。具体地讲,“逆向”即是依逆反性思维,化腐朽为神奇,从否定性对象身上发现美,创造美;而“视点转移”,则是变换艺术表现的角度,暗渡陈仓,丑中见美。从这里我们也可知,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丑恶并非就不能写,关键在于怎样写:是以丑为美,嗜痂成癖?还是“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14),“把具有全部戏剧性深度的心灵和自然纳入表现中”(15)?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是后者,即使写到丑,那它不但不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龃龉,反而使他们在美丑对比的高反差中看到内中固有的丰富的思想涵义,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历史文学,此种情形就不乏存在。如司各特《米德罗西安的心》中的处决场面的描写,由于作者“第一用的是十分节省的篇幅,第二强调了人性的先决性和结果,强调了人性的特点,而不是处决的残忍的特点,不是把处决作为处决来强调”(16),所以,能把世俗视为残忍丑恶的负价值转化为人性美好的正价值。当然,在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极端的要数本世纪兴起的现代主义历史文学的审美造型。在此种形态的历史文学作品中,诸如此类的残忍丑恶场面描写不仅愈来愈多,而且被大大推向了极点。施蛰存写于30年代的《石秀》等几个短篇历史小说,那大段大段地描绘石秀的性变态心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80年代中期出版的王伯阳的历史长篇《苦海》,其对明末清初历史和郑成功、施琅人性弱点、污点和人性恶的细致入微的放笔描写:如郑成功在刚毅果敢的同时又是怎样专断暴戾、多疑、寡信、杀伐无当,甚至借治长子之罪的名义挟杀董夫人,施琅在威武勇猛的外表下又是如何残忍冷酷、心狠手辣、心胸狭窄,为了达到个人复仇的目的,竟背信弃义地杀害千余名明军战俘;包括在新时期颇具影响的准历史小说或曰拟历史小说《红高粱》、《红蝗》等,无所顾忌地写杀人、写大便、写性,这更是以前历史文学所不可能有、也不敢想象的事。尽管这也许有一些夸饰、偏颇的成份,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却可以通过这种强刺激的特殊方式而让丑恶的历史内容由自我曝光走向自我否定,并因此释放出震憾人心的审美价值。#p#分页标题#e#
这大概就是鲍桑葵所说的“普遍知觉目之为丑的东西,往往是最高贵的艺术中十分突出的东西,深深地灌注着不可否认的美的品质,以致不能解释为只是同丑自身明确区别开来的美的要素的衬托物”(1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前面引用的鲁迅和莱辛的话又不够全面。看来,对历史文学有关残忍丑恶的描写,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历史的范畴中作全面的、具体的、辩证的把握才是。
三作家将已然历史对象人化为现代真实形态的艺术成品,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语言和内容的“两度创造”尽管不可避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并不是说只要实行了“两度创造”就可以直抵成功的彼岸,创作出有分量的、能充分体现自我个性魅力的真实佳构来。历史文学毕竟不同于现实题材的文学,它取材于一定的历史故实,原本就与历史具有某种“异质同构”的联系,堪称是真正的“戴着镣铐跳舞的文学”。因此,这就使其现代转换在总体上只能纳入“历史———现代”的特殊审美机制中加以表现,这也就是说,历史文学真实的现代转换是二维的,它的一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沃土,而另一端则维系着现实社会的思想心理,并受与之俱来的历史真实性的制约,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能动感应和对话。
大量事实表明,历史文学上述这种双向互动感应和审美复合,看似矛盾抵牾实则正常合理,它不但完全合乎历史文学独特的文学本义,而且也是历史文学有效凸现自我、避免不适应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拿语言来说,为了使历史文学消除不必要的审美阻隔,我们在这方面诚只能要求作家使用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现代白话文。不过,这恐怕也只是一种非常笼统、原则的说法,并且主要还是站在纯现实立场的一种观照。如果将问题推进到历史文学本体论角度审思,即把历史文学看成是一种有限度的文学,认为它可以而且应该体现一定的历史质感和实感,那么就会感到以上所说的现代白话语体的采用又不免有失简单,需要充进历史内涵加以合逻辑合情理的改造。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现代语言包括语感、语态、语调、语势、语汇、语词毕竟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今天的精神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深受其规约;在传递、表达历史生活内容方面有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构建既使读者可以满意接受但又具有历史感的艺术意象。语言学原理告诉我们,语言作为一种思维和交流的符号系统,它是用来指称被反映的客体对象。语言符号虽不是客体本身,但由于它是意义的载体;而意义则是客体的反映,是客体的观念表现形式,所以它同客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客体具有特殊的价值指向。正因为语言具有符号、意义和指称这样一种三元一体的关系,故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为使语言符号携带的信息能传递历史对象的意义,给作品以应有的历史真实性和真切感,那就不能主观随意地将一些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的语言符号输送给读者。例如:我们在描写昭君出塞、贞观之治时,为使作品为现代人可欣赏了解,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采用颇富现代意味的语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让王昭君、汉元帝、呼邪单于、李世民、魏征等人嘴里漫口吐出诸如“民族大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代新名词。道理很简单,这些词如果作为一种信号输送给读者,只能诱使人们将它和现代生活内容直接挂钩联系,从而使审美心理上积储起来的历史感倾刻崩溃倒塌,造成符号与意义、指称的截然分离。人们经常批评的历史文学现代化倾向所指即此。大概是有鉴于此,迄今为止我们见的历史文学之作,特别是成功或较成功之作,都无不避开那些为现代所独有的、带有特定涵义的名词术语,并在现代人能读懂的范围内,有意识地融进大量的诗、词、曲、赋、碑、铭等古代韵文和词汇,它们这样作,从审美感知上说,就可因此而给作品平添“熟悉的陌生化”、“远近的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能使人感到是亲切可解的,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陌生奇异,从而在艺术欣赏时既能达到感情与共而又处处隐伏历史距离的特殊美感。高层次的历史文学语言就是这样,它从不为了现实面忘了历史。这也许就是阿尼克斯特为什么称道司各特作品虽然具有“传达出小说人物的民族性、地方性和历史性的语言特点”但他“并不滥用这种手法,他的小说人物说话所用的语文虽然包含某些表达出历史色彩的典型的字句,但仍为现代读者所了解”。(18)
历史文学真实的现代转换,不但语言表现形式有个历史感的问题而且其题材内容的选择处理也要自觉接受历史可然律的必要规范。历史文学中美丑善恶的增损贬抑当然离不开作家现实性原则的参与乃至接受美学所谓的符号异化的处理,但作为一种客体对象,美丑善恶本身毕竟来自历史,它带有特定的历史气息和历史内涵;更为主要的是,在颇多情况上,它的古今表现形态虽然并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难以切割的深刻联系。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是以螺旋型的形式上升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在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重复出现,因而历史与现实是割不断的,它的美丑善恶的历史内容在不同的阶段,常常会发生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向旧东西的回复”(19)。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历程考察:美丑善恶的历史不是节节逝去的外在事物,而是作为类存在的、发展着的某种本质力量丰富和展开的过程,它们在精神主体上彼此具有内在的深刻继承和联系。今天是昨天的发展,不可能不留下昨天的痕迹;昨天是今天的由来,也必然能从中找到今天的某些渊源;甚至象菊池宽所说的德川时代“不记仇不报仇”思想与20世纪“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20)。不期而合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不乏其倒(菊池宽的历史小说《恩仇之彼方》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内容)。正因这样,我们作家在进行内容转换时,就不应置其历史涵义于不顾,将对美丑善恶的增损贬抑处理当作一种完全无干的纯现实的单项创造。须知,真虽然并非等于美和善,但它毕竟是美和善价值兑现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为什么传统历史文学《清宫谱》、《赵氏孤儿》等虽有明显的封建糟粕但却通体透出一股毕肖酷似的历史氛味和大气磅礴的正气,让人看了真实动情,悲怆不已,而5、60年代创作的《信陵公子》、《窍符救赵》以及不少卧薪尝胆的新编历史剧一心想“为今用”但最终效果适得其反,竟遭人拒绝?这个中就是历史之“真”的功能价值在起作用:前者,它在实施内容转化的现实性原则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历史的质定性和客观“范”的一面;后者,则把美丑善恶的内容转化处理完全等同于作家文学主体的单向运作,而忽视了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历史自身也能产生一部分能量。从社会学、发生学角度讲,就是只看到历史发展过程的变异性,而看不到它的连续性,是变异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统一,互为因果。#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