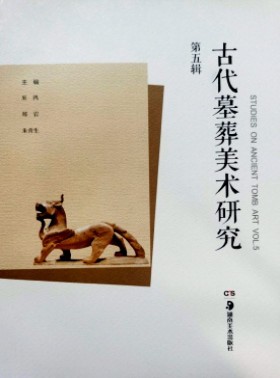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文学研究的窘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早熟的文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成为后人在创作中频频回顾的典范。”[1]同时,创作散文(包括骈文)和创作诗歌、小说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历代文人晋身仕林、治国安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诗闻名的李商隐、杜牧,亦工于散文写作,更遑论韩柳欧苏。然而在当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变得边缘化,古代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戏剧研究相比亦显得创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针对散文内容的研究,比如庄老思想、荀子思想、韩愈谏佛骨、袁宏道谈性灵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个散文家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来,古代散文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本文将力图呈现古代散文研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期帮助广大研究者发现更广阔的视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当代显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当今却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模仿式戏谑文体(或曰“恶搞”),如《凤姐列传》《药家鑫列传》《苍井空列传》等等。由某不知名网友杜撰的《药家鑫传》云:药公家鑫者,华朝长安人氏。华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药公诞于古都长安,时天生异象,群驴乱吼,或曰:莫非如《水浒》所载之“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再现?……人皆称:药公不亡,则法律亡。药公不死,则国家死。药公之事,举国牵动,药公之名,举国牵挂。由此观药公,真乃关系国运之达人也。在F•詹姆逊看来,这种“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词汇、句式,但内容却是当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模仿被詹姆逊称为剽窃,因为“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4],才是别具一格的、能够适应这个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艺术形式。用古代文体记录当代日常生活的确算不上创新,“后现代主义”亦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古代散文这种历史上的精英式文类却面临着现实中的庸俗化挑战。 其次,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古代散文的创作较少直接关联,因为在当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学”,后者至少不是“纯文学”。在陈剑晖先生看来,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不是审美需要,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间关系疏远,但在当代,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研究学术和创作散文不一样,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确的东西,可称为“学术”;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带动了感情,只有在这样的“角落”里,才能写作散文。此处余秋雨并没有把散文当作“经国之大业”或者“圣贤书辞”,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学术”固然不同于经世致用或者齐家治国,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决定了学术本身也是“实用性”的。所以,研究学术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来是要一分为二的,他的散文观也因此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强调的现代散文一脉相承,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和强调个性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紧密相关,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创作目的、创作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和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相比,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系统,缺少电影、电视等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这无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赵氏孤儿》《花木兰》《西厢记》《薛仁贵》《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电视剧版《红楼梦》(李少红导演)更是建构起一个全民海选女主角的媒介议程设置。①相比较而言,古代散文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动画视频版的古诗对于幼儿启蒙教育的影响,以优酷网和土豆网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进行搜索,赏析类、中学课件类视频不过数十段,而用“古诗”、“唐诗三百首”搜索,视频数量累以千计。此外,散文与当代媒介的结合体“电视散文”自央视三套1996年开播以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电视专题片,是“受到文学散文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艺术样式”[6],是“中国化的电视艺术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现代媒介形式,更何况,由全国各地电视台制播的电视散文,其取材选题也大多是现当代散文作品,极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见,在多媒体、宽带网络和计算机、大众传媒已经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图书,图书又以作品集为主,以译注、赏析等普及类读物为主,其中《古文观止》有数十种译注本,仅中华书局便出版了选译本(2010),钟基(2009)与葛兆光(2008)的注释本,名家精译本(2007),以及繁体竖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读本也有数十种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类著作仅有三十余种,②形式不可谓不单调,内容不可谓不单薄。但是,古代小说、诗词、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传播内容要丰富得多,不仅图书有单行本、选注集成、佳句赏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样化,研究类著作则涵盖文献与史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类型与理论研究等等多种角度。必须承认的是,图书是一种依靠理性思辨来完成传播与接受的媒介,但诗歌、小说、戏曲所利用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能够同时激发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对于文学作品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至关重要,古代散文在这个层面上又处于下风,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样局限于书籍,所传播的内容也受局限[9]。#p#分页标题#e# 二、古代散文研究体系与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这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10]王兆胜先生指出:“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11]笔者认为,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Es-say)出现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而定名,与诗歌、小说、戏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对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论辩为特点,故而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情绪放纵和宣泄来净化读者(观众)心灵的“净化说”背道而驰,后者显然被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随时被剔出“文学”之外,更何况对它的研究想当然地被视为与文学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概念体系,二是研究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现当代散文概念的影响下,或与韵文相对,或与骈文相对,有时又与诗歌、小说相并列,陈平原先生就此认为古代散文是一个“滑动”[12]的概念。南帆先生则指出:散文的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诸散文,这种“否定性的定义”,不仅促使一些文类衰老,同时还催生另一些文类……散文是文类的结束,又是文类的开始[13]。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骈文研究、古文研究、汉赋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为战,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为题名关键词搜索,粗略计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时间,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与此同时“骈文”381篇,“汉赋”576篇,“辞赋”515篇,“古代小说”984篇,“古代戏曲”329篇;期间以时代或作者为维度的,并以“散文”为题的博士论文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说”为题,并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14篇,这还不包括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博士论文。兄弟阋墙、左右手互搏,这确实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 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问题因人因时而异,但研究方法却面临着裹足不前的问题。陈剑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散文研究者总是从谋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类的文章做起,即仅仅从外在的组织方式来看待散文的结构[14]。古代散文学者从古至今皆习惯于从细枝末节的修辞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为例,余恕诚先生将“汉以后的赋、骈体文以及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都称为“散文”[15]。在介绍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学色彩时,《孟子》的“戏剧性”、《庄子的》“生动故事”、《左传》的“叙事之最”、《战国策》塑造的“形象”、《史记》创造的“人物”、南北朝时的“修辞”与“典故”、韩愈散文的“生动形象”、柳宗元散文对形象的“想象夸张”、欧阳修散文的“论说技巧”、归有光的“细心刻画”……都被余先生视为散文“文学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这些比喻、夸张、论辩、描摹、形象化、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实际上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古代散文与研究古代诗词、小说相比并无独到见解。 此外,当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较为孤立,主要是作品赏析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历史学模式,缺少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双向传播。尽管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认为形成《庄子》恣肆风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结构”,“《内篇》的结构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表现了庄子的复杂的艺术构思。”[16]可惜这种类似于结构主义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把神话、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把小说都归入到散文理论中来,西方文艺研究的对象并不包括散文,导致我国研究者难以直接借鉴。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实用性,加之作为散文作者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科举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文学史中能够得以流传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备官僚、学者、文学家三合为一的身份,后世学者所归类的文学之文在作者创作之时未尝不将之当作应用之文而煞费脑筋,斧削雕琢。陈平原先生曾举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传诵为表达感情的名篇,如书信和日记,皆是有意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专本,文人写信时不免存了给第三人乃至举国上下、子孙后代传阅的心思”,“郑板桥的家书别出心裁,写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脱做文章的心思。”[17]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说服帝王将相,或者用于说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说服亲朋至友,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从修辞学角度入手,从说服的手段和表现的技巧入手。于是,针对散文的文学研究就渐渐侧重于实用主义,继而不免滑向功利主义。这又和自康德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悖,因为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说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显然是功利性的,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晓原先生在2006年时提到:“过往的散文研究比较多的是一种批评,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史、理论批评史的梳理与述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散文写作指导之类书籍。真正有理论含量、高端而又切实的研究相当匾乏。”[18]不过,这种尴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观,这一年内,谭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国散文史纲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将从此进入新的一页。#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