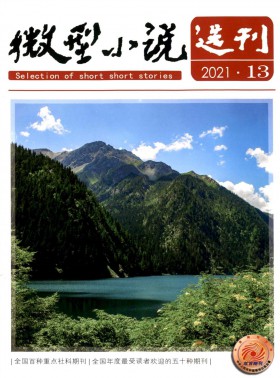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吕翼小说的爱与痛,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七十年代出生的吕翼,是近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彝族青年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 吕翼的故乡是地处滇东北的云南昭通,这里因为所处地理位置偏远,属于云南比较贫困的地区。但是,历史上昭通却又是中原入滇的重要通道,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块土地上崛起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吕翼属于这个群体的后起之秀,已经体现出比较强的创作实力,正在成为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底层写作和苦难的呈现。 不是作家们有意要以苦难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人生。作家不过是以自己的良知在对人生进行文学的拷问与探寻。吕翼的小说主要关注点是乡村底层的现实生存,在表现苦难人生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这一层面人物的爱与痛。走进吕翼的小说,同样可以感受到作家的心灵在苦难面前的挣扎与沉浮,同时他也在努力寻找着光明的方向。 一 底层写作在中国文坛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关于它的概念、范畴等等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但是,面对底层生活的文学创作实践,又以不可抵挡的态势提供了风格各异的文本,它们考量着评论的视野与境界。所以一提到“底层写作”,总是和“问题”“困惑”“争议”这些词语相关联。评论家孟繁华清醒地意识到:“在‘整体性’已经破碎,多元性已经建构了新的文学格局的时候,妄论统一的‘文学本色’是试图建立新的‘整体性’,但要实现这样的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既不是今天文学的现实,也不是文学未来发展需要的路线图。”①应该说,所谓“底层写作”是一部分作家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尤其是农村的复杂现实作出的文学选择。既是作家情感的要求,也是作家良知和理性的自觉选择。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作家和评论家都在努力探索着关于“底层”的写作方向。2006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曾经举办了一场“底层与文学”研讨会②,会上作家和评论家们各抒己见,虽然未能形成统一的定论,但却从不同方向拓展了“底层写作”的维度。当评论家们在为概念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曾经做过矿工的北京作家刘庆邦在研讨会上发言说到自己的创作时,称自己是“不自觉中就进入了写底层”。这是作家的人生阅历中积淀下的底层情怀在起作用。生活在边远的云南边地乡村,同样身为农民之子的青年作家吕翼,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后,也是以“不自觉”的方式选择了他最熟悉、最有痛感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小说中底层叙事的主要内容。 虽然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议比较多,但似乎很多评论家都认同一点,即所谓底层,应该看到小人物和贫困、苦难的不可分割。小人物,意味着远离权力,远离中心,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乡村的小人物,更是和贫穷、落后的生存环境密切相联。社会发展进步的浪潮,很难波及到一些地处偏远的乡村。那里生息的小人物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贫困。出生于乡村的吕翼,在成长中经历过贫穷与苦难,也经历过对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他曾经非常渴望逃离乡土融入城市。但在城市的喧哗声中,他又发现乡土才是灵魂的依托之所,天然地拒绝欲望城市对灵魂的“异化”和“压抑”。就像很多“寻根”作家所经历过的那样,“虽身处闹市却魂系乡村”,成了吕翼进入小说写作的最初动因。血液中天然积淀下的“底层情结”,使在他获得文学表达的话语权后,自然地把目光投注到那些无法逃离乡土的小人物身上,关注他们的生存与挣扎。吕翼的小说也经历了由“不自觉”地关注底层,到“自觉”表现底层生存的过程。某些作家对乡土的回归,是“用温馨诗意作基调,构筑一个个高山流水般的理想世界”,以此来建构自己心目中的乡土世界。而吕翼的小说则不同,他更关注农民的精神困境和现实的苦难境遇,为他们还生活在贫困中而备受煎熬。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有爱才会有痛。 吕翼笔下的乡村小人物,和他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他们是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是他文学写作道路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才会那么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他的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名叫杨树村的村庄,聚集了一批“留守”的乡村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些卑微的小人物,卑琐而生动地活着:配种人王矮三、独眼赵四、姜寡妇、罗二嫂,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而杨树村是一个“周围都是山”,封闭、落后的偏远乡村。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生命的形态变得单纯而又驳杂,他们为基本的生存而忙碌,却又不忘记互相斗嘴、调情,苦中作乐,把日子过得滋味齐全。 在《雨水里的行程》、《方向盘》、《别惊飞了鸟》、《你的爹,我的儿》、《树叶风尘》、《果农》等小说中,吕翼延续了杨树村这个村名,在几篇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中,也让杨树村的人物继续出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关于“杨树村”的系列小说,对乌蒙山乡底层民众的生存有了比较集中的展示。读者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乡村现实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杨树村和外面那个日益变化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距离。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里都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现象。尤其在小说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物身上,这种滞后更加突出。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外面的文明进步的现实之间还远远不能“同步”。在《你的爹,我的儿》这个中篇小说中,杨树村的运转体现出一套自己独特的“秩序”,村主任老转对王矮三说的一番话透露了这套秩序的秘密:“我们有政策,可以让你成为富有的人,也可以让你一辈子穷下去。”村妇小桃红对村主任老转的几句抱怨则一下子就点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你一纸责任状,就把责任落实下来。每年村里发生什么坏事,都跟你没有关系。……要不是你那责任状,将责任落实在每一家每一户,你早就当不了村主任的。”在一个偏远落后的乡村,社会秩序的运转似乎跌入了一个怪圈。一个小小的村主任成了权力的至高代表,他手上的公章、红头文件便可以把村民的一切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甚至可以说出“你的羊在我的文件里”这样的话。而村民在权力面前却只有以卑微的姿态,才能得到些许的利益。于是代表着这套秩序的公章的丢失,也就成了杨树村的一件大事,老转甚至以找不到公章,要“剁”掉全村人的手指来威胁人。虽然村民在权力面前也可用放肆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但是也就仅仅限于语言为止,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反抗。“逆来顺受”已经成为一些底层民众血液中不可更改的符号。所以小说的最后一节,吕翼让矮三和赵四两个小人物走在村庄的暗夜里,踩着满地污秽,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冷与黑”。两人拉着手互相取暖,呼喊着那个偷走公章的能人阳庚的名字,一个喊他爹,一个喊他儿,以此宣泄内心的愤懑与无奈,也传达了一种虚无的精神寄托。#p#分页标题#e# 吕翼对乡村的现实非常熟悉,对乡村小人物有着深切的同情与悲悯,所以他能以在场者的身份,以含泪的笑讲述那些小人物在生活中挣扎沉浮的故事。这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在场,看似平静、幽默,实则充满疼痛感的叙事,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深沉的力度。 二 落后的自然环境加上失衡的乡村“秩序”,小人物的生存不可避免地在贫穷落后的旋涡里打转。与贫困相生相伴的是命运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彰显出来的人性的力量。吕翼对文学中的苦难有自己的理解与认识。他曾在一次发言中阐释过自己的观点:“如果作品是花朵,苦难则是风雨,经历过了,美丽的花萼才能开放,才能脱出魂魄一样的香艳,才会花谢花飞,结出累累果实,让你生命力得予延续。如果作品是一块矿石,苦难则是烈火,浴火再生,就会刚硬无比,无坚不摧。如果作品是刀具,苦难则是粗砺的磨刀石,脱了一层锈,就会变得更锋利。”③对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来说,正视苦难都需要勇气和良知,需要悲悯的情怀去关注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有的苦难是显在的,可以直接从生活的表象中去感受。比如《孝子》中的母亲,就是一个承载了太多人生苦难的乡村妇女形象:17岁嫁做人妇,二十年中生育十个孩子,死了三个,活下来的七个,丈夫在挣钱养家中意外死去。题目的“孝子”,暗含反讽。养育了七个孩子的母亲在重病住院的时候,三千块钱的住院费,让子女们“个个将脸迈开”,只有身为长子的孝子独自苦苦支撑着一切。而同样身居底层,靠打工为生的孝子为母亲尽孝的路程也是无比艰辛。打工挣来的几千块钱小心地缝在裤裆里,又一张张送进医院无底洞似的窗口。历尽艰辛上山采来天麻出售,再给母亲买救命的中药,结果却发现中药里包有几片薄薄的天麻。在充满荒诞的现实面前,苦难也染上了几许黑色幽默。《雨水里的行程》这个中篇所描写的母亲,更是经历着人生苦难的重重折磨。 小说以母子二人从杨树村到桑树坪的一天中的“雨水”行程开始,层层叙写了一个乡村母亲曲折漫长、与苦难相伴的人生。小说中73岁的瞎眼母亲以买棺材为由,带着打光棍的儿子到老家桑树坪相亲,想完成一个母亲的心愿。途中经历了爬山涉水,走过阴霾、沉闷、压抑的一天。最后却在儿子冷漠目光的注视下“跌”进河水,消失在浑浊的波涛中。一对身世曲折的母子纠缠半生的爱与恨,在小说中一点点浮现出来。很难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评判这对母子之间的是非恩怨,说出谁对谁错。只能说在人生的苦难面前,他们都在努力挣扎,只是前方却是一片迷雾。只有当迷雾散去之后,才以看清悲剧的结局:儿子冷漠地看着消失在河水中的母亲,那一刻既是苦难的结束,也是苦难的高潮。吕翼在这篇小说的叙事角度上有意识地进行着一些探索,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生故事,只有从多角度叙述才能一点点揭开真相。标题中的“雨水”“行程”也是一种意象,象征着人生漫长的苦难行程。环境和物质的贫困似乎不能完全解释悲剧的成因,灵魂的贫困有着更令人深思的意蕴。在文学的世界中,苦难也有多种、多重存在的方式。显在的苦难让人同情,深层的苦难则令人深思。在《割不断的苦藤》中,吕翼为了表现苦难的深重,不惜为人物营造一个“苦”意弥漫的环境氛围。人居住的地方叫苦寨,寨边的河叫苦水河,地上长的是苦竹、苦楝子树,山上终年爬满苦藤,苦寨人的脸上则是一脸的苦相。从这里走出去的副县长,名字叫辛苦。 严格说来,小说的主人公辛苦不能算是底层人物。因为他已经跳出苦海,官至副县长。但是,他的生活乃至最后的结局,又处处和他出生、成长经历过的底层的贫困、苦难有着掰扯不清的关系。他希望以修路的方式来实现改造贫穷环境的愿望,却无法穿过现实中纵横交错的“网”,或者处处碰壁,或者同流合污。好人做不成,坏人也做得不彻底,辛苦的灵魂因此而充满悲苦与挣扎,最后只能以死亡而告终。人物灵魂深处的苦难,比他少时承担的物质苦难更有一种令人震憾的艺术效果。吕翼对这个人物是用了心力的,他力图深入人物内心深处,去寻找、剖析他蜕变的原因。从一个深山里的苦孩子到一县的副县长,他的成长实属不易,他的沦落也就更加令人心痛。作家的意图似乎是为了揭示辛苦堕落的环境和更多的外部因素,对人物多少有些辩护的意思,这也是因为对笔下人物爱得太深之故。贫困和苦难,为吕翼的小说增添了一重深沉的色彩。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展示苦难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苦难进入作家的视野之后,为他催生的应该是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 三 底层社会的种种问题,与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但是底层写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展示贫穷与苦难,更应该通过现实存在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弊端,“引起疗救的注意”,寻找到光明的方向。作为一名“70后”作家,以及一名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化人,吕翼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一定研究和思考。他写乡村的那些小说,既看到农村的贫穷与贫穷带来的种种苦难,也在对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进行追问、思考,寻求解决的良方。从这个角度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正在得到提高和增强。 吕翼的小说在叙写苦难,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他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乡村式的幽默,那些小人物虽然活得无比卑微,却有着乐天的生存态度。他们以坚韧的姿态面对苦难,消解苦难,努力活出人生的滋味。“杨树村”的村民王矮三、独眼赵四之类人物的语言就于粗俗中体现出民间生活的诸多情趣。同时,他的小说既写了一些逆来顺受的农民形象,也出现了一些体现着乡村发展方向的新人形象,这些人是小说中的一大亮点,代表着希望也代表着新农村的发展方向。 在《你的爹,我的儿》这篇小说中,主要人物阳庚虽然没有出场,但是他的“名声”却通过很多人的口被神话和传扬。小说特别强调了他一双手的与众不同,别人的手除了掏大粪,就是用来偷东西、扇别人的耳光。而阳庚的手却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在杨树村创造了很多奇迹。他帮助赵四在门前修了石桥,帮助王矮三修了一栋砖房。帮助村里的女人做木梳、木甑,编竹箩。不仅如此,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他还对杨树村的发展有思考与设计,写成文章到县报上发表,让村主任老转处处感觉到来自他的心理压力。如果说阳庚代表着乡村的一种理想,那么在《方向盘》中,大学毕业生尉涪则是现实中新农村建设的新生力量和希望。这个人物出场时还显得比较幼稚,在事业和爱情之间摇摆不定,对前途也比较迷茫。“像一片飞扬在空中的白杨树叶,上不沾天,下不落地。”让他当村文书,他也不放在眼睛里。但是杨树村的发展变化、建设前景对他还是有着吸引力,加上女朋友许玫的吸引与劝说,使他最终能留在乡村。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加入对一个乡村的发展来说,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而尉涪一家三代的理想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乡村的变迁。爷爷早年做过马锅头,赶着马帮上云南下四川。父亲这一辈,先是赶马车,然后开上了手扶拖拉机。到尉涪这里,一心想的则是学习小车驾驶,过另一种新的生活。中国乡村的变迁虽然缓慢,但是从这一家三代向往的交通工具上,还是体现出乡村发展进步的趋势。杨树村在现行农村政策的指导下,开始修路、建厂,吸引人才,环境和人心都在发生变化。#p#分页标题#e# 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体现出的杨树村年青一代价值观念的更新,他们在生活、事业、理想方面都有着和老一辈完全不同的观念与追求。这才是乡村最值得期待的希望之光。外人看到的是杨树村人的种种不是,尉涪看到的却是杨树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开发利用的大好前景。他还看到杨树村的问题是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少,宣传不够。这说明他的意识已经在渐渐进入一个“杨树村人”的角色,开始有了主人翁的姿态。小说结尾部分,通过他对方向盘的把握,有意强化了尉涪立足乡村的意象。他“手握方向盘”“箭一般地朝着杨树村驶去”。 这篇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叙事比较拖沓,原本是站在主人公尉涪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叙事,但是在叙事视角上过于开放,未能使第一人称叙事的“限制性”特点很好地体现出来,人物主体的聚焦不够集中,多少影响了一点小说的表达。和其它几篇小说相比,《方向盘》中的杨树村更加充满活力和希望。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在社会和时代的潮流中也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为改变乡村面貌,创造新的生活而努力着。一些评论家在讨论“底层写作”时,特别强调要“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④,因为它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则。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写作,需要作者坚持一种朴素、诚恳的文风。“虽然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⑤吕翼的小说在朴素、诚恳这一点上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没有夸大乡村的苦难,也没有对未来作虚浮的想象。而是坚持立足大地,呈现出中国乡村一隅的真实图景。 从吕翼目前发表的小说来看,他的对乡村底层生活的关注一直倾尽心力。一方面是他对乡村、底层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写作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一名作家的责任感和良知使然,如吕翼自己所言:“文学应该不是保健和护肤,而是苦口的良药;不是装饰摆设而是刀剑斧锤。它强调的是批判和解剖,重量和光芒。”⑥所以他的小说既有令人沉重的苦难和黑暗,也有令人感动的光明与温暖。出生自乡村和长期在基层工作的阅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比较清醒的理解,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也能有理性的把握,这是他创作上的优势。 如果从小说的艺术角度看,吕翼的小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对底层人物人性深度的开掘,以及叙事的方式、语言的个性和小说风格的形成,都还需要在写作实践中进一步思考,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他如今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对他下一步的小说写作来说,也许是个重要的提升契机。所以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下一篇作品会带给读者新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