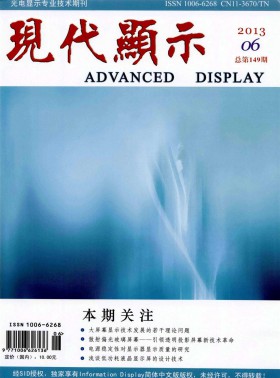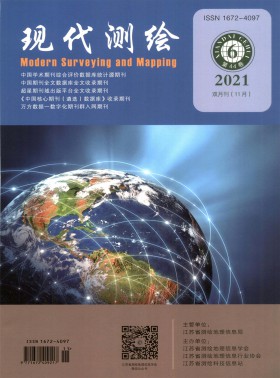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音乐的创作本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音乐艺术发展至今,无论是音乐的形式,如节奏、音色、音程等,还是音乐的组织手段旋律、和声、复调、配器,都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人们对于它们的使用是突破以往的音乐形式、组织规则,追求的是一种大胆、新奇,极具个性化的音乐技法。如新音色的追求,将常规乐器进行改装,或是将自然界的物质(比如石头、水等)直接引入到音乐作品中;节拍不再遵循以往的常规规律;旋律不再追求优美性、线条性;和声不注重其功能性而注重其色彩性;配器不再追求乐器之间的和谐,而注重个别乐器的极限音高等。这些新的音乐手法将音乐艺术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音乐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这对于完善音乐基础理论,以及指导现代音乐的创作和给予现代音乐以正确的评价,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现代音乐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反传统性”,可以说现代音乐的创作理念,是在最大限度上考验着人们的审美心理承受力。对于现代音乐语汇的丰富,现代音乐独特的创作理念,以及音乐思维方式,我们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些“新颖”音乐思维模式中,音乐材料的本质属性也被这些“新颖”所替代,让现代音乐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走入了一个“误区”(现代音乐作品已经不是用来“听”的,而是“看”的或是“想”的)和“盲区”(欣赏者面对现代音乐作品的茫然与困惑,该如何去理解现代音乐作品)。音乐的和声语汇、旋律风格、复调写作、调式调性等,都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但是对于音乐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这些关键的要素却不能改变,这些特质可以说是音乐艺术所独有,一旦忽略或失去,那么音乐艺术存在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了。 我们用音乐材料所具有的基本属性,来看看“现代音乐大师”约翰•凯奇的作品,会发现他的作品是不能被定义成音乐作品的,而称之为“声音行为艺术”更为恰当。因为在凯奇的作品中,他多引用的“声音”大多是“自然声音”(如水、石头、压汁机等),“语言声音”(人们的说话声),这些作为现代音乐素材进入音乐作品是可以的,但是关键在于音乐材料的基本属性———“语义性”上,凯奇的音乐作品让人们获得的不是审美基础环节的情感体验的感性环节,而是凯奇本人的创作动机、理念等理性思维。可是在这些“新奇”的想法中,凯奇本人有时都处于模糊状态中,如在《变化的音乐》中,约翰•凯奇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作品的创作与演奏,在这当中他至少抛了上万次的硬币,而当时担任演奏的大卫•图德实在是无所适从,但仍不遗余力地向凯奇的思路靠拢。而事后,凯奇也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他实在迷惑的不得了。” [1](45)如果“作曲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创作什么,那么他如何向欣赏者们传达作品的情感色彩,甚至于更深层的思想内涵呢?还有著名的旅美音乐家谭盾创作的部分音乐作品,如《死与火》(和画家保罗•克利的对话)、《九歌》《乐队剧场Re》等为例,这些音乐作品在创作思维上是沿着西方后现代的音乐思维而做,并得到凯奇的大加赞赏。而中国的音乐界则褒贬不一,并引起一些权威音乐人士的批评,中央音乐学院蔡仲德教授在听了谭盾的音乐会就指出:“谭盾音乐会的每部作品和其他作品没有给我以美感,不可理解、不可感受。”[2](20)至于有的后现代“音乐作品”,如:以股票行情表的升降来决定旋律的高低(希格林),以昆虫的爬行状况决定音高与强弱(杨内)之类的作品,《为带有钢琴家的钢琴而作的作品》(莫兰,“钢琴家上台,直接走向大钢琴。他爬到钢琴里面,坐在琴弦上面。钢琴来演奏他”)……之类,从表面来看它应用了一些音乐的表现手段,可是从音乐材料的基本属性上来说,这类作品,不具备“声音”所要求的基本属性,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作品虽然奇特,但是它们有非物质性、二度创作性,但是它们缺失了最重要的一个属性———语义性,音乐材料的“语义性”对于音乐艺术而言,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和人们情感运动的“似原型”上,其次是对于人们情感直接而又迅速的“说明”上,这一点是其他“视觉艺术”做不到的,因为它们都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后才能获得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色彩,即使有些艺术的基本材料能迅速给人一定的情感影响,如绘画色彩艳丽的红,会给人喜庆之感,但是它确无法像音乐能给予人们普遍而又广泛的情绪影响,并且总是这样直接而又准确,古语说“为乐不可为伪也”,一段明亮活泼的音乐会以它的“语义性”让人迅速地感受到乐曲所要说明的“轻松、愉快”,不会有歧义,而艳丽的红却有时也会人感觉很"血腥"的情感色彩体验,让人觉得不安。 我们纵观西方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从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到微分音乐、噪音音乐、偶然音乐、新音色、点描音乐……,作曲的手法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但是,西方音乐界却还在感叹音乐的创作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这种感叹的原因,正是由于现代音乐在创作过程中忽略甚至摒弃了音乐材料所具有的基本要素,而导致的严重问题———音乐艺术发展到现在,它好像不是为听而存在,作曲家有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或是一个深刻的思想,似乎就等于作品已经成功了。“当作曲家把自己的哲学立场、全新的艺术观说得头头是道时,听众的耳朵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当耳朵不再是音乐的检察官时,音乐创作的世界也就成了聪明头脑的竞技场。”[3](42)如果音乐材料“声音”的基本属性———非物质性、二度创作性,以及最能体现音乐特质的语义性被丢弃时,当音乐的基本材料似乎可以不再是“声音”时,“文字”、“思维”似乎都可以替代它的时候,那么是否只要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呢?而且会使得经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也自叹不如呢?是否音乐应该也就是视觉艺术或是哲学的隶属者呢,如果是这样,那么音乐艺术将走向何处?[3](43)综观后现代音乐众多的音乐流派,我们看到从偶然音乐、简约派、新即物主义、具体音乐……这些形式多样、观念各异的后现代音乐中,真正优秀具有可听性、耐听性的音乐作品几乎很难出现。而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忽略了音乐材料的基本属性而最终让音乐与其他艺术相混淆的结果。#p#分页标题#e# 而从音乐的结构上来看,“无论人们在音乐实践中如何创新,……但它并没有越出由音响、表现和意义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结构边界。”[4](7)我们先看音乐结构的第一个要素———表现,“科林伍德曾说,艺术表现就是某种内在感情得到明朗化。”克罗齐耶说过,“只有当情感在头脑中转化为意象时,才算得上艺术的表现。”[4](11) 当然,艺术都具有表现性,但是音乐艺术却是最能准确、直接传达出表现性的艺术,这和音乐所应用的基本材料———声音,分不开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声音”的基本属性具有“非物质性”和“语义性”的特点,声音“非物质性”的特点,决定了音乐在表现情感时与人的心理活动“线条”之间存在着“似原型”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音乐的“语义性”,在对于人情感世界的“阐述”上,有着非其他艺术门类所不能企及的“清晰”和“准确”。“表现”作为表达音乐结构中的逻辑手段,也是音乐结构要素之一,它必然应具有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于人情感状态的迅速的影响上。这是由于,音乐的“表现”是依赖于旋律,而旋律是以“声音”为最小单位的“组合体”,那么“声音”所具有的基本属性特征无疑是应包含在“表现”中,并作为“表现”手段中的基本要素而存在,同时也是检验“表现”是否脱离音乐结构本质边界的一个重要依据。 很多现代作品的创作,在表现性上可以说是花样百出、观点新奇、想法独特,但是我们如果依据表现中的表情因素审视大部分的现代作品,我们会发现它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法直接感染人们的基本情绪活动,这些作品是用来“想”的而不是“听”的。这显然违反音乐结构“表现”的基本要素,脱离了音乐结构的框架,这样的作品显然是不能被称为音乐作品的。有着“现代音乐作曲家”之称的凯奇,他的作品,如《0分0秒》(1962)、《变化的音乐》等,我们不能赞同它们是音乐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具备音乐“表现”的基本要素———快速、准确的音乐情感“语言”。凯奇本人也曾说,我是想努力的向音乐家靠拢的,但是“几年以后,我的音乐作品最热烈的拥护者却是一些画家、舞蹈家而不是音乐家。”[1](68)事实说明,超越了音乐结构“边界”的作品,已不再是“听觉艺术”,而是“行为艺术”,因此受到视觉艺术家们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个是音乐结构中的物质形态———音响。 “音乐的音响具备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它必然体现某种精神内涵;其二,它与精神内涵之间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依靠某种逻辑手段而成。”[4](88)第一个先决条件,说明的是音响所包含的基本情感色彩,如:喜、怒、哀、乐等,这是由于对于音响而言它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声音”,因此“声音”具有的“语义性”就是它的第一个先决条件的要素;第二个先决条件,则说明的是音响对于内在情感的影响。我们知道情感包含着两层含义,表层含义是人的基本情绪状态,与人的自然性需要相关,具有较大的情景性、短暂性,带有明显的外部特征,如:一首明亮欢快的乐曲能给人轻松、愉悦之感,一首沉重暗淡的乐曲则给人忧伤、哀愁之感。但是音乐对于人情感的影响力是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这就是情感的深层含义,它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关,是人类特有的高级而复杂的体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深刻性,即人们对于音乐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建立在第一个的基础之上,它们顺序不能倒置,更不能缺失任何一个。如果缺失第一个条件,音乐艺术材料———声音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就被忽略,这就脱离了音乐结构的“边界”,缺失第二个条件,这样的作品只是具有浅显的娱乐功能,难以起到良好的社会教化功能,难免会是一些庸俗之作。 其实,音乐的物质形态———音响,就其本质来说应该说是表情,即用音响象征或暗示类似于人的情感活动状态,这是因为构成音响的两个条件,实质上都在以对于人情感的影响为其基本功能。 由于“声音”的“非物质性”的基本属性所决定,使得构成音响的基本要素(音色、力度、速度、节奏、音高等),不是以物质形态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活动,而是以精神的形态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感情,虽然构成音乐音响的这些因素看似和音乐材料无直接关系,可是它们以“声音”的“基本属性”为媒介,因而也就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在现代作品中,有些作品对于音响的追求,不仅标新立异甚至于有些让人的听觉难以接受,比如在音高上,作曲家往往在谱例中不会标出具体的音高,并且在音乐作品中夹有嘈杂、尖锐的大量非乐音音响在作品内,以加强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潘德雷茨基《广岛罹难者的哀歌》,在作品的第一主题中,作曲家将五十二件乐器均分成十个声部,分别都以ff的力度奏出没有具体指定极限的音高,十个声部在第一时块中先后出齐,并且每个声部都以尖锐的“音头”进入后再平稳地持续下去,加上它们的音频极高,从而产生一种尖锐、紧张、刺激,同时又比较透明的音响,有如一种“被挤压出来的残忍嘶叫之声”。作曲家通过这种非常规的音响应用,将人们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恐惧、战争的残忍,形象的表现出来,使得作品极具震撼力。 还有在节奏上,现代音乐之前的音乐作品,在节奏、节拍的应用上一般都较为规整,而现代音乐在创作上,打破传统节奏强弱的规律限制、突破小节线的限制、突破节拍的规整性,使节奏更为多样化、复杂化。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作曲家将节奏的变化与突破作为重点,在舞剧第二部分中《对当选少女的赞美》,小节的节拍几乎是每小节都在变化,或者拍子是规整的,但是打破传统的重音位置(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如在第一部分里《少女们的舞蹈》。类似的节奏性几乎通篇都是,这样复杂的节奏动感,虽然使得排练的舞蹈演员大伤脑筋,但也正是这样复杂、难以捉摸的节奏,使得《春之祭》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生命的活力。它似乎告诉人们:在蛮荒的大地上,无处不蕴涵着生命的萌动,无处不是怪异生灵的躁动,使人们在茫然无从中寻找着生命的永恒含义。#p#分页标题#e# 这些现代音乐中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潘德雷茨基《广岛罹难者的哀歌》、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等,给了人们以耳目一新、完全不同的听觉感受。虽然,最初人们的耳朵无法接受这些与传统的节奏、和声、音色不同的音乐作品,可是当人们逐渐适应了这些新奇的音响、打破传统秩序的节奏等一系列音乐表现手段时,人们对于现代音乐开始由抵触而逐渐地接受了。《春之祭》在最初首演时,曾引起一片哗然,使得剧场发生音乐史上少见的骚乱,以至于斯特拉文斯基不得不从剧场后台的窗子上逃跑。但是,一年后当它以音乐会的形式公演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原因在于:人们理解了作品中描述的俄国古代未开化民族在春天祭祀大地的仪式,也接受了只有使用一些反传统的音乐表现手段,才能形象、准确的体现出一些特定情况下的音乐含义,就像《春之祭》中所要描述的原始部落的混沌与粗犷。 这些现代音乐作品的创作,虽然突破以往的音乐形式传统规则,但是从音乐结构上来说,它并没有逾越结构的“边界”,始终还是在围绕着音乐材料的基本属性,并遵循着最为重要的“语义性”要素———以最直接、迅速的方式作用人的情感这一特点。尽管有着音乐发展过程中有史以来最大胆的革新,但这些作品始终在音乐结构的框架之内,并符合着现代人越来越强的“审美心理承受压力”,基于这个基础原则,人们的耳朵和时间最终接受了它们。 第三个是音乐结构中的精神内涵———意义。 在音乐作品中,基本意义也就是情感的表层(喜、怒、哀、乐等),还有内在意义也就是深层的情感内涵。按照哲学的思维来看,理性阶段才是最高的层次,对于音乐作品而言,理解作品所蕴含的深层情感内涵才是对于音乐作品最完美的诠释,可是这最完美的诠释是必然要建立在表层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的音乐作品,是不能用音乐结构框架来衡量的。音乐精神内涵中意义的表层,其特质由"声音"的基本属性决定,莫•卡冈也曾说:“音乐的声音———音调符号能够准确地体现和传达以情感为主的信息。”[5](221)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事物的结构来说,它既是变化的,同时也是稳固的,变化的是内部的结构,稳固的则是其"本质"的边界。对于音乐而言,音乐材料所具有的基本属性是构建音乐结构的三个方面的“基石”,它是音乐不可超出的“本质”边界,一旦违反,这样的作品将会超出音乐结构框架,也就不再隶属于“听觉艺术”了。[4](111) 当然,音乐艺术也决不是反对创新与突破,相反创新与突破,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欲进步之必需;创新与突破,边缘化所必然。但创新与突破应以能其“本质”为底线,而边缘化往往产生的是另一个新的艺术品种。我们不以保守的观念、态度忽视或鄙视它,但是它已不再属于原有的任何一个母体,因此也不必硬用原有的任何一个艺术品种的名称去套,如前面所述的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 总之,在音乐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忽略很多,但只要冠以“音乐”之名,便不应丢弃音乐材料所独有的基本属性,这对于音乐艺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亦当是后现代音乐走出创作误区的一个底线和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