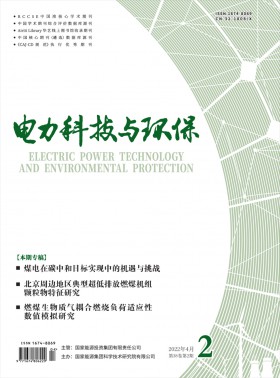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香港电影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浅谈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
一、什么是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
香港电影批评的写作环境截然不同于内地写作环境,其主体不是职业电影批评者,而是非职业电影批评者。香港“几乎没有一个是全职影评人,”④担任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李焯桃坦言,“香港的影评人从不期望可以单靠写影评维生。他们通常是新闻从业员或有一份与电影无关的正职。他们的境况从未好转过……文章的长度愈缩愈短”⑤。有论者质疑,“香港几乎人人都可以是‘影评人’。有人想建立影评人的专业身份,但‘专业’本身是一个未必站得住脚的理念。”⑥在这种业余写作处境中,香港电影批评者不断追问自身的个体批评者身份和总体的香港电影批评身份,“集中讨论一般的写作环境与影评策略问题”⑦,“反问自身为何写影评?而影评人有没有一个相对实在的标准?”⑧“还要写影评?”⑨什么是影评(电影批评)?如何面对“影评战争——当代影评危机”⑩?“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当找不到集体的影评路向”,如何办?又如何“回归到个人去”?而在“浮城”的香港,——“许多年来,大家公认香港是一块没有历史意识的地方”(梁秉钧语)——“香港青年‘影评家’的成因”何在?什么是“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什么是“香港电影批评”?
置身于身份危机中的香港电影批评者,一方面致力于和电影实践始终紧密共鸣的电影批评定位,秉持一种共同的“迷影人”(cinephile)立场,“写影评……因为喜欢电影”,他们“大都同时从事与之(电影)有关的工作,如编剧,电影策划,电影教育,又或电影资料整理等,均是有利丰富的电影文化发展的好气候”;另一方面,香港电影批评者则竭力落实电影批评的自身独立性,声称“理想之影评,当有独立成家之气度,不论电影当时是荣或是辱,电影评论是个专门项目。”由此,香港电影批评者的影评写作和影评姿态,迥然有别于内地电影批评者。与此关联,对于电影批评是一种分析还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表述还是客观研究,在香港电影批评者看来,本是不可分切的一回事:正因电影批评是主观化的影像分析,故能超出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学理性学术操演的规训与狭隘。在此情形下,香港影评人的共识首先不是基于逻辑、立场上的一致,而是源自感情上的共通,这一共通点即:对电影的热爱,由此自证其共同的“迷影人(影痴)”身份——“影评人必需喜爱电影”(舒琪语);“影评人始终不能失落的,是对电影的热情”(张伟雄语);“只写喜欢的电影,有些电影,不交心就是不交心”(黄爱玲语);“我们写影评,也只是为了兴趣;服务读者只是次要,主要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非心爱的电影,我们可以不写”(李焯桃语);“要明白自己为何喜欢电影,面对自己影痴之心,若将写影评当成搵食工具,卖白粉赚得更多,何必爬格子?”(陈耀荣语)——要言之,香港电影批评在其社会语境中,更接近于一种非功利的迷影话语的个性化表述,“不需要从学术的角度去写,也无需拉到现实政治去发泄,去吵。”这样一种民间和个人立场的迷影电影批评观念,正可警醒学院派电影批评的机械僵冷。
对于国内电影研究者而言,郑雪来提倡的“电影学包括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这三个分支”的观念影响至今。同时,罗艺军所称“中国电影理论在形态上往往与影评合流,论评合一,以评带论”的论断,同获广泛传播。然而,把一些电影批评文本拔至“理论文本”的高度,表面上似乎是一种提升,却隐含着狭隘化电影批评的盲点——首要以电影理论的观念统摄电影批评,电影批评的理论化痕迹愈重,其价值愈高。如此一来,电影批评的“标准装”愈来愈被剪裁成“理论休闲装”,从而遮蔽其主观化阐发的空间。这其实正是郑雪来所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迄至当下的一个现状。处于“特色之外”的香港,自然不存在理论化钳掣电影批评的限制,便形成其更加开放的“专业电影批评”观念:“影评除了分析电影,会看镜头、故事结构之外,也有很感性的处理方式……不是一定要追寻清楚电影是甚么的理论,而是很感性地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此同时,电影批评的“业余写作方式”,并不取消香港诸多“非职业影评人”的“专业影评人”身份。这一基本定位,正和上世纪60、70年代艺术电影活跃时期众多欧美知名电影批评者的“专业电影批评”与“专业电影批评者”的观念相近。相较之下,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建构下的电影批评观念显得过于“特殊”了。
二、什么是“香港电影批评”
1981年1月底,香港《电影双周刊》“双周特辑”登出《全港影评人评选1980年十大影片》。其中,“全港影评人”既包括石琪、舒琪、列孚、林离、吴昊、文隽、陈廷清等华裔,也包括KeithAnderson、TerryGeary、TonyRayns等“鬼佬”;电影候选名单既包括《名剑》《撞到正》《地狱无门》等港产电影,也包括《源》《踏浪而来》《小城故事》等台湾电影,还包括《小花》《舞台姐妹》《女篮五号》等内地电影,更有《发条橙》《现代启示录》《巴黎最后探戈》《尼罗河谋杀案》等外国电影——这些都在参与建构一个极其开放多元的“香港电影批评”的主体身份和空间视野。进一步结合自二战后“七人影评”直至目前的香港电影批评的历史踪迹,则可戡掘出四种样式的“香港电影批评”:其一,在港香港电影批评者对港产电影的中文批评;其二,在港香港电影批评者对港产电影的外语批评(多为英语批评);其三,在港香港电影批评者对非香港电影的批评;其四,不在港香港电影批评者对香港电影的批评(刊登在香港报刊上)。第一种批评是香港电影批评的核心,但非一贯主导,50至70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所评论的外国电影远胜港产电影,直至70年代末创刊《大特写》及其后《电影双周刊》的自觉努力,参与推动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使得对香港本土电影的评论才成为香港电影批评的主导样式。第二种批评一直是香港电影批评的边缘,但也有译为中文进入主流的,如高思雅(RogerGarcia)的《剧照散文》。第三种批评体现出香港电影批评的观影视野,始终具有重要地位。值得提醒的是,藉由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及在此环境中第五代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连获佳绩,使得创刊不久的《电影双周刊》及其主导的香港电影批评书写,愈来愈关注内地电影。第四种批评往往通过报刊特刊版面的专辑或特稿形式出现,
如凤毛和游静离港求学时写作的影评,又如汤尼•雷恩(TonyRayns)刊于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上的《胡金铨:龙翔凤舞》。此四种电影批评,共同建构出香港电影批评的多重性存在形态。现今的香港电影评论学会(HongKongFilmCriticsSociety),仍然包括在居住空间上在港与不在港的两种影评人(华裔或外裔)、在批评文字上运用汉语(国语或粤语)与外语的两种影评人,也自然容纳由此产生的四种样式的香港电影批评。其中,如方保罗(PaulFonoroff)是在港犹太裔影评人,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写作影评;冯嘉琪是不在港、现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影评人,在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上发表多篇中文影评;张建德(StephenTeo)是不在港、现居新加坡的影评人,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多篇英文影评。在事实上存在双重国籍的香港,其电影批评虽然仅是中国电影批评的一小部分,其批评主体身份的情况却最为复杂,其批评视野的宽度却几乎最广阔。就后者而言,如卢伟力所述,“香港人看香港社会、香港电影有自己特别的角度,这发展出一种特别的本土文化特色、文化认同。”其中亦隐含着一个作为前提的香港电影存在形态:香港电影广泛接纳非港产电影并被境外地区所广泛接纳。在相当长时间里,香港电影批评者的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畛域,远远超过内地电影批评者和台湾电影批评者。和四种空间视野相呼应,香港电影批评文本的表述文字也存在多重性,国语、粤语、英语既可各自纯粹独立地统摄一篇影评,也可混杂汇聚在一篇影评里,如“刺激到冇得顶”、“揸fit人Laughing哥”、“有些东西难免overtheorize”等等。尽管国语是香港电影批评的主导语言,但是英语影评一直连绵至今,如TerryBoyce、TadStoner、MelTobias等在英文报刊的英语影评影响广泛。与此同时,还有从英文重新回译为中文的影评文本,如李欧梵、张建德、李诗才(MaggieLee)的一些影评。香港电影批评从来不是一个整饬方队,其内在存在多种混杂、纠结、混乱、丰富、多元的文字、话语、视域、路径、线索、情结、趣味、意旨,“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类型电影与表演形态
作者:厉震林 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一新的世纪以来,泰国电影突然发力,颇有成为继中国、日本、韩国、伊朗之后的亚洲电影新势力之趋势。有的论者将它称为泰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甚至惊呼“担心泰潮来袭”。这里,颇耐咀嚼的是它的时间,正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此时,泰国经济遭受重创,电影业却在经济复苏中逆势再生,频频在国内外获得重要的文化和商业影响,超过了此前泰国电影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它不禁令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美国电影,当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但是,电影业却是异常繁荣,出现了一系列经典电影以及“微笑天使”秀兰•邓波儿等时代流行人物。
经济危机与电影复兴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条神秘的内在通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与发达国家的美国的情形是否一样?泰国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它是否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发展规律?毫无疑问,30年代的美国电影,乃是经济危机时期人们的“精神冰淇淋”,“银色之梦”成为美国人逃避现实的情感避难所和寄情物,从而也成为了美国人精神和梦想的救助站与孵化器。新世纪的泰国电影并不如此,它的振兴首先是外国力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风暴后的泰国泰铢贬值,在泰国的拍摄费用仅为在西方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加上泰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使泰国成为许多西方电影的外景地,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偏爱来到泰国取景,《早安越南》、《天与地》、《007系列之明日帝国》、《古墓丽影2》以及奥利弗•斯通的《亚历山大大帝》等好莱坞影片都在泰国拍摄完成。亚洲金融风暴除了自身的经济泡沫原因,西方国家的“金融大鳄”乃是它的直接“黑手”;由于西方影片的猛烈冲击,到了20世纪末期,泰国电影几乎已经没有还手之力,2000年只生产了七部电影;现在,西方电影资本又充分利用在它操纵下形成的泰国低廉物价,生产准备返销到泰国的西方电影,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用泰国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具有浓郁东方地域特色的建筑,使东方国家再度成为“他者”,是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及其价值指称。
殖民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第一世界大国在不断增加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以文化判断和传媒干扰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编码和程序控制。这种后现代文化战略,体现了一种经济至上的全球意识。在实业发达与商品过剩的工业强国,文化与精神产品成为它的最大受惠者,而形成世界意义的经典神话,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批发中心。(1)故而这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编码和程序控制”,导致1999年好莱坞拍摄的以19世纪泰国历史作为背景的电影《安娜与国王》,它以“白人拯救史”作为主题,演绎东方“专制君主”与西方“自由女性”之间的浪漫情史,在电影故事的“母国”泰国引起极大反弹。不但该片遭到禁映,而且泰国自己拍摄了气势恢弘、规模盛大的史诗巨片《素丽瑶泰》,它描写了在民族战争中鏖战疆场的古代女英雄,泰国人开始书写自己心目中的民族影像史。这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较量以及斗争,颇有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某些观点的意味:所有第三世界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自主的或独立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
这种文化搏斗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了资本的不同程度的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的和利比多(欲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尽管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第三世界理论”是一种第一世界内部的“他性政治”,即所谓的总体制度内的“飞地抵抗”,需要警惕它的主客体位置及其权力关系,但是,它仍然可以给予一些与现实相符的启示。正是在这种“生死搏斗之中”,《素丽瑶泰》在民族精神上的立场,这种自我确认与自我张扬的价值形态,“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开始辨识自己的民族历史,同时,使长期被当做“他者”对待的第三世界观众,激发了他们对于本国电影的热情支持,市场票房获得极大成功,犹如一次全民性的电影狂欢。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文化搏斗”,政府开始介入其中,加大对于电影业的扶持力度,相继出台了几项促进电影发展的优惠政策,泰国一位王子甚至亲自执导电影,参与电影制作。
但是,这种“文化搏斗”,实质上是与磋商、妥协等相互博弈过程中发展的。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夺文化权利甚至霸权的过程,而这种争夺必然是充满复杂局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统治者/统治阶级的思想要在社会中取得最广泛的接受,获得多数人由衷的拥戴和认同,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系统和表述,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吸纳、包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表述于其中”,“文化霸权与其说是一种既定事实,不如说是一场无休止的争夺战。这场争夺战不断地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利益始终处于一种谈判、协商(negotiation)之中”。(2)葛兰西论述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按照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观点,“第一世界”的无产阶级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功能,已经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因为实物生产已经基本转移到第三世界和地区,故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休止的争夺战”,也已经转移为世界不同区域、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冲突、抵抗和斗争。正在由于这种冲突、抵抗和斗争,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传统的政治启蒙身份,而且,表现得异常的活跃。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和“现代化”,必然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复杂情怀。
正由于在第三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仍然是相当活跃的社会功能角色,而且他们大都首先是政治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文学书写,首先是对他们所置身的本土现实的直面。而对于第三世界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而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的多数首先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者,是本土社会政治生活中压抑性力量的批评者。而关于“传统”的叙述、尤其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多种形态,则频繁地为本土社会生活中的压抑性力量所借重,也因此而成为本土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抗的重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间或在明确的国际视野中,对抗“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并反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渗透;但正是由于这一渗透过程,不时被委婉地称之为“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本土的知识分子则在类似的本土视域中,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者,而不时成为这一渗透过程、至少是文化渗透过程的代言人。在类似情形中,相对于第三世界的他者——第一世界(准确地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立场、观点便间或成为第三世界批判知识分子高度内在化的视点;而所谓第三世界的自我/第三世界的生存现实与文化现实,便成为这一内在的他者视点中的“外在客体”。(3)泰国电影也是如此,同样置身于一种悖论的情景,一是面对西方电影的文化争夺及其霸权,“对抗‘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并反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渗透”,二是由于“这一渗透过程,不时被委婉地称之为‘现代化’进程”,故而“不时成为这一渗透过程、至少是文化渗透过程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对于本土传统文化,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文学书写,首先是对他们所置身的本土现实的直面”;二是“关于‘传统’的叙述、尤其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多种形态,则频繁地为本土社会生活中的压抑性力量所借重,也因此而成为本土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抗的重要对象”。#p#分页标题#e#
合拍片中文化认同窘境及启发
随着越来越多“新的国际分工”的出现,文化生产开始在世界各地重新布局,这种全球分工的趋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电影文化工业中,以跨国资本主义为首的全球文化和世界各地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变化中重组着。传统的国家通过“大叙事”建构起来的个人身份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也在电影媒介文化中遇到了挑战。具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文化所享有的优越性与独一性,在全球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价值冲突中遭到了冲击。中国题材的合拍片是这种冲突表征的主要阵地之一。这类影片所传播的文化价值判断,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对电影的抵抗性接受,加强了中国观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个体的自我认同。 一、含义 关于“认同”(Identity,这个词另有同一,身份、某种本质或特性之意,文内将视所需而选择使用)的研究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等领域受到很大的关注,但正如亨廷顿所言“,Identity”这一概念“既不明确,又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确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P17)。可见“,identity”的概念在国外像在国内一样的难以界定。综合不同的学者研究,我们可以将“认同”的含义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首先,认同是在外界的互动的基础上建构的。霍尔(StuartHall)将认同的概念分为三个阶段:启蒙时期主体、社会学主体与后现代主体。[2](P277-279)在启蒙时期主体的阶段中,将启蒙思想中人与生俱来的理性意识作为基础,认为人是一个“统一”的个体。对世界的阐释是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存在者的主体”。[3](P301)社会学主体则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后天与世界的互动而产生的,认同是连接内在的个人与外在世界的桥梁。这与社会学家库利与米德的“有意义的他者”及“镜中之我”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体,则涉及了一种非固定的,具有流动本质的认同观。主体在后现代多义、片段的社会结构互动之下,产生了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分叉的认同观。后现代主体的认同更多的依赖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与之互动而产生的主体认同。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特(PaulGiltoy)表示了相似的认识“:Identity”既不是某种客观条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种主观幻觉支配下的随意构设,它是一种被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Identity”这一个概念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4](P301)”。 其次,认同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索绪尔认为“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意义的根本,没有它,意义就不存在。巴赫金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差异”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他认为意义不属于任何单个说话者。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差异的标示是文化的基础,因为事物与人的既定意义都在文化中产生,而在分类系统中,这些事物与人也被分派到不同的位置上。“认同是透过差异的标示而打造出来的,而差异的标示则通过再现的象征体系,以及各种社会的排除形式而产生”[5](P49)。霍尔则指出,差异的建构,可以藉由将那些界定为“他者”或局外人排除在外,或边缘化或否定性的达成。他还叮嘱人们“差异”在许多不同学科中包含的差异与他性问题,已经愈来愈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差异具有这自相矛盾的性质。既是消极的又是积极的。[6](P241) 因此,认同是通过差异建构的,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同一”“,同一”正好象征了差异。再次,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指出,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通过实践建构的。根据安德森的研究,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报纸与书籍的普遍印行,使得身处各地的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同步想象发生在遥远的事件,并借以产生对遥远的人们的同一性的建构,并藉此形成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安德森的研究是建立在传统纸媒的基础上,因为纸媒的传播范围的有限性,就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这样的认同是建立在社群、共同体或国家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当今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纸媒的边界渐渐被新媒体的兴起超越,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并未因此发生重大变化。爱德华•霍尔也曾表示了类似的认识: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设置一道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屏障。因此文化以多种形态决定我们该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7](P44) 这样的边界或曰屏障正好阻止了认同的形成。认同的“实践性”就在于文化的实践性,在作为区别差异的象征结构中,主体在文化的选择性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建构。关于“文化认同”的内涵,霍尔曾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一种将“文化认同”定义为一种共享的文化,一种“唯一真我”的集合体。即是,要我们共享一种历史和血统的人们,也共享了大家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共享的文化符码,而这些历史经验与文化符码是稳定的,不变的。另一种立场认为,在“想象的共同体”内部,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霍尔指出,文化认同既是一种存在(being)也是一种成为(be-coming)。他们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文化认同并不是永恒的固定在某些本质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持续作用。建立在后殖民立场上的霍尔关于文化认同的观点,其实质是“,后现代的主体没有固定的或永久的身份,主体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身份,有的身份自相矛盾,无法统一。”[8(]P209-211)因此,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在共同的符码下寻找意义共享的过程,同时,符码又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重构的过程,文化身份认同受历史、文化和权力游戏的制约,随异质文化间的力量的转化而不断地分裂并重构。#p#分页标题#e# 二、裂隙 从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看,中国题材的合拍片从1987年《末代皇帝》、《太阳帝国》等片的合作开始,到近些年的《卧虎藏龙》、李安的家庭三部曲(《喜宴》、《推手》、《饮食男女》)《上海红美丽》、《面纱》、《雪花密扇》、《魔咒钢琴》,上影还将推出《神奇》、《上海公报》和《海上交响》等,一直以来从未间断,然而,合拍电影却命运多舛。这些电影基本上具有共同的市场命运,即在中国市场上并不赚钱,但是在国外却获得了很好的票房收入,而中国电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似乎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国内票房很好的电影比如《让子弹飞》在国外却几乎无人问津。电影传播过程中,受众接受呈现出来的差异性,其问题的实质是电影接受国观众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如前所述,认同是建立在不同主体的互动基础上,是差异化的“同一”,同时,认同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这里不防以《面纱》为例。2006年岁末,电影《面纱》抢在中国贺岁档推出。以“好莱坞经典,中国制造”为口号进行媒体宣传,周黎明更是盛赞该片为“偶像作家作品被搬上银幕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次。”但最终颓势难改,以跨越元旦假期的累积票房不足200万元的尴尬局面草草收场。与此相反,《面纱》却在北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影片《面纱》于2006年12月22日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城市进行点映,不仅上座率超过90%,甚至单影院的票房成绩达到1.1万美元。《面纱》改编自英国作家毛姆(W.SomersetMaugham)描写1920年代中国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浅薄的英国女子在中国内地战乱中逐渐发现她那位古板丈夫的价值的故事。虽然有强大的表演阵容及主流评论支持,但影片却仍然显得与中国观众有些疏离。通过仔细分析《面纱》可以发现在影片内容同中国文化认同存在裂隙: (一)想象的“同一性”建构与中国观众的反抗性阅读。同一性是认同的基础。“自我”的实现,依赖于民族共同体所共享的文化根基,依赖与共有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规约。导演、编剧与制片人试图在西方经验与中国观众的历史经验间建立某种共同的“同一性”以实现认同。但他们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特定的历史与文化中书写并说话,其说话的位置是被指定的:在西方文化中,受过高等教育,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充分感知。在《面纱》中,导演卡兰与诺顿及编剧对小说进行了大改编,对中国语境进行浓墨重彩。所以整部电影似乎都是关于中国的,其显在目的是电影“导演(卡兰)希望制作一些主要是符合中国国内市场的电影。”[9]其策略则是通过文化系统建立一种同一性的“历史记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在集体记忆和历史基础上建构认同”。[10]影片通过电影语言再现了一种共有的文化秩序与历史记忆,旨在唤起中国观众与之共享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符码,建立起某种“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既能再现中国经验的真相与本质;同时,又是电影通过表面的“自我”,实质上是通过意义框架建构出来的。很明显,这样的“同一性”的建构是虚幻的,一厢情愿的,并不为中国观众所接受,仍然是异族导演,特别是西方白人文化站在“文化优越性”的基点上,对中国的一种想象的历史叙述。这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与真实“自我”(中国人之特性identity)相去甚远。有网友发表评论“看完电影,我只能说这是外国人又一次自视太高和‘爱心’泛滥”。[11] (二)欧洲的在场与中国的缺席。根据霍尔的研究,认同不仅是以共享稳定的和连续的文化为特征的;认同更是通过差异打造出来的,而差异的表示,则是通过象征体系,以及各种社会的排除形式而产生的。[5](P49)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差异研究中,诸多的学者都表现了共同的认识:西方在构筑东方的形象时,并不是站在平等的角度来叙述的,而是将东方贬低,将东方视为非理性的、野蛮的,而将自己定义为理性的,文明的,代表了现代精神的。于是在影片中,出现了诸多的二元对立的差异:西方/中国,落后/先进,停滞/进步,野蛮/文明。在差异的叙述过程中,电影屏幕不仅仅是用来给我们放映图像的媒介,而且是西方投射自己对他者的“恐惧、幻想、渴望”的镜子,通过这一镜像,西方实现了“自我认同”,这一结果也可以从北美电影票房佐证。在影片中,中国被僵化为一个原始的、停滞的影像,成为一个没有时间的空间化的存在。电影借叙事,将邻近与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戏剧化,与原本是遥远的,无关的中国建立关系,借以强化西方本身的存在感,或在场。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完成的存在“be-coming”而缺席。连演员兼制片人爱德华•诺顿在中国的新闻会上都说过,“小说的视角有些窄,只是关于两个英国人的故事,跟中国并没有实质关系。”因而,电影中的中国,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甚为陌生的想象物,这样的存在,实质是缺席。影片中,欧洲无休止的言说,而中国则是无语的、无名的。中国的抗日、抗英运动、五卅运动都被场景化,这些被植入的西方化的历史,经不起中国人历史经验的检验与推敲。吕燕饰演的半裸的清贵族遗少,在鸦片的氤氲中,迷离的眼神,幽灵般的、似博物馆与活化石般的存在,展现的是自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眼中的神秘,充满欲望的东方的形象。霍乱发生地的村民们,封建、愚昧、保守、无知的群像与高雅、漂亮、文明、知识渊博的瓦尔特夫妇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在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先进,中国人的愚昧/西方的文明,这一系列的差异中,西方观众完成了对中国的又一次想象性的确认。正是在这一意义层面上,中国观众看到了一部陌生的跟中国没有关系的“中国电影”。 (三)象征秩序中野蛮的“东方性”再现。根据周宁的研究,十八世纪中期以降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重要特征体现的就是“东方性”。东方性来源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周宁认为,在西方叙事语境中,中国国民性中最突出的就是其“东方性”,其特点是专制、停滞封闭、文化自大守旧、风俗愚昧简陋。《面纱》再现了疫区的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群像。这是一群数量庞大,面目模糊的黄种人,落后、愚昧、封闭、坚守着古老陋习的一群中国人。影片借助精准的电影语言,将一个懂得西方科技文明,并像白求恩大夫一样,愿意为中国的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西方的白人拯救者搬上银幕。而中国人群像则是无名的、愚昧的。当家中有感染了瘟疫死去的人时,首先选择的不是与传染源隔离,而是把家人放置家中,并且装神弄鬼的驱鬼。这种野蛮的“东方性”还表现在对中国的民俗奇观与异国想象。导演为了让电影具有更多的中国现实性,选择了风景如画的漓江山水做背景,选择中国名模吕燕,并让吕燕以半裸的、神经质的样子出现在屏幕上。中国文化中的传统符码,一一展现在银幕上。通过对电影的深度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在《面纱》中不过又是好莱坞电影喜欢讲的那类“出门在外”故事,尤其是爱情故事之一:奇异的旅程,战争、灾难,主人公在通往外部世界的途中,寻找或者迷失了自己的爱,于是爱的故事、异域,野蛮人和远离都市文明的自然世界就成了故事中亘古不变的一个母题。有网友评论:“诺顿和导演约翰•卡兰在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法,使得电影更有中国味,更关乎于中国,可是,结果并不如人意,总觉得流于表面。诺顿以他的视角来看中国,并期待中国人能产生一样的共鸣,未必太过想当然也,事实上,任何老外所拍摄的电影中的中国,无论他们看来是如何的真实可信,无论其中有多少华人演员和群众,但在我们眼里,总还是呈显着异国情调。”[10]网友的这番评论似乎解释了认同难以建立的深层原因。在差异中寻求同一的过程是认同建立的过程,在好莱坞与中国观众的互动之中,在电影文化实践中,真正的文化认同并未建立。如《面纱》这类电影通过异国情调所呈现的“东方化”与张艺谋早期的民俗电影的“自我东方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文性,中国观众表示了类似的批评与抵抗。#p#分页标题#e# 三、启示 电影《面纱》所呈现的认同上的矛盾与裂隙至少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电影身份的混杂性、多重性与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碎片性,导致了接受上障碍。中国题材的合拍片,电影的身份来自于西方主体的界定,由于地域的混杂性与奇观性,电影中的中国,也是中国观众心中陌生的他者,电影中所展现的历史记忆,只是中国民族记忆中断裂的碎片,中国观众难以从文化心理与民族心理层面实现认同。 (二)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努力克服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反抗立场的解读。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解读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揭示的,统一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的解读。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信息都是多义的,因而没有“最终的”、“真实的”意义。这样,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受众的立场决定了传播效果。因此,对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来说,好莱坞电影国际传播成功的例子或许给我们启示,《泰坦尼克》3D版在中国首周放映票房超4亿,《阿凡达》以13亿的中国票房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超越。中国电影人,观众,学者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国元素的应用,其实质是寻求文化上的认同,尽管我们有很多的批判之声,但传播效果是明显的。 (三)电影跨文化传播应寻求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早期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被学者,观众所极力反对的就是其自我民俗化,奇观化迎合西方受众对中国的想象。在这方面印度与伊朗电影以其民族性矗立在世界电影之林,而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在21世纪前后所面临的电影发展桎梏应该给大陆电影的发展提供具有意义的参考价值。值得庆幸的是被称为第六代导演或者新生代导演的一代电影人,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电影的国际性上有了一定的自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尤其要注意的是电影跨文化传播中,注意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这类合拍片在中国市场上传播失败的例子表明,电影媒介的编码被输入国所对抗式解码,造成心理上的排斥。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有中国电影的爱好者,就如同好莱坞电影在世界市场上对观众的培养一样。中国电影要向国际观众提供一个“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借以来想象中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电影传播者要站在文化传播的立场上,选择正确的传播策略,让国际观众了解、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兴趣。仅就中西方观众来讲“,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12](P104-109)”。同样一部电影在东西方电影市场上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借助电影媒介与受众的双重编码与解码,找到不同文化间的“契合点”“,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13(]P.103) 在受众接受过程中,其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与本土文化相契合,又要适当的借助外围的诸如国家、资本、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等多种合力,打造出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在这方面中国的武侠片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仍需继续努力。 结语 在资本国际化的时代,未来中国电影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混合杂交的“现代电影”。面对当前的大的全球化主流,中国电影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几千年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民族电影又要接受来自非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任何简单的移植或试图保持中华文化的纯粹性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中国电影文化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Spaces:ChineseCine-maasWorldFilm”)坦陈“: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14](P77)中国民族电影在面向国际市场、国际观众,与世界电影潮流保持互动的过程中,大胆创新,积极进取才能取得走向国际市场,求得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