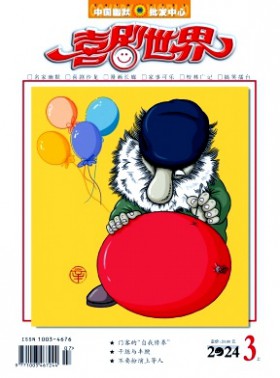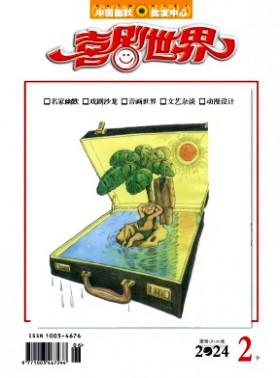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喜剧的修辞术与阶级叙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好莱坞“情”路难与中国经验 看过喜剧电影《人在囧途》的观众,想必不难想起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雨人》(RainMan,1988),两者之间的相似,相信明眼人不会放过。但若以为前者只是盗用或沿袭了后者的结构,则又显然是小觑了前者。无疑,这两部电影都是属于公路电影这一准电影类型的模式,故事的主部都发生在路途上,而艰辛曲折不断延宕的行程,以及两个不同类型的主角人物之间在艰辛中的冲突磨合,都在在使得剧情波澜起伏跌宕回环;同时也正是在经过多重磨难和主角人物间交往的深入后,剧情往往会在尾声时出现逆转,脱离常轨的主人公(或秩序的破坏者)终将回归正常的秩序中来,故事发展到最终也大都皆大欢喜。显然,公路电影属于情节剧之一种典型的模式,而就这一模式所具有的象征性而言,旅途这一流动的特定时空无疑是稳定而理性的正常秩序之难以企及的存在,因此当旅途结束,主人公超出常规的行为方式也最终回到正常秩序中来。在这里,旅途既成为秩序之破裂的象征,也是修补秩序的必经之途。 从这点而言,《人在囧途》明显带有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烙印,但若以为这仅是一部向好莱坞致敬和模仿之作,则显然是没有抓住这部电影的内核。与一般的公路电影不同,《人在囧途》中之公路这一剧情的背景设计并非可有可无,或仅仅是主人公回归正常秩序的必经之途,而是联系着独有之中国经验的关键。 影片以大年三十前后几天中在外工作(打工或经商等)的民众千辛万苦赶赴回家这一极富象征意味的潜文本作为“人在囧途”之“囧”意,仅从这一点来看,显然这部电影就带有浓厚的中国之象征味。而更为独绝的是,这一“囧途”之设计又是联系着2008年春节前后之影响中国的冰灾,因此,路途之多艰更是可想而知了。而就是这样不断发生的囧事,其实也是对个人之面对挫折困窘的考验,中国/民众独有的面对挫折之百折不饶而坚忍乐观的态度呼之欲出,因此,当主角最终走出困境并回归到正常的现实中来时,这一结果就不仅仅是对主角的酬慰和允诺,某种程度上也是历经磨难之中国的隐喻和象征。 电影中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一个是“傻根”牛耿(王宝强饰)反复渲染的“人间自有真情在”,另一个就是当徐峥饰演的李成功回到家里,试图向妻子忏悔时,妻子的一句“回家就好”。这两个细节看似毫无关联,而且发生在截然不同的主人公身上,但若联系在公路电影这一特定剧情模式中,或许可以把这两句话理解为,人间其实处处有真情,即使是在人生之“囧途”,也莫不如此。而家庭则是这种真情之蕴藏地,回家也即意味着真情的回归。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显示出了独有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特点。而说这是中国经验之书写,还在于它以中国传统价值/理念重塑了现代商业文明;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带来的紧张,在这种重写中都得到了某种想象式的缓解和调和。借用西方著名理论家杰姆逊的说法,这显然是一种象征行为,是一种欲望的象征写作和想象性的自足叙述。就其严格意义上说,现代商业文明所体现的商品生产及其消费无疑是拒绝“真情”的,它推崇的是赤裸裸的资本逻辑,而非什么抽象的道德或伦理。 因此,其一旦遭遇传统伦理道德必定会生出许多波折和困窘,从这个角度看,电影中的李成功和牛耿,其实可以理解为分别代表或象征了商业文明的逻辑和传统道德伦理。而从电影中李成功的一言一行来看也无不体现出商业逻辑的思维惯性,在他眼里,一切无非都是以利来衡量或为先导的,无论是对待属下还是家人,都是如此。所以,影片中才会有他多次嘲笑牛耿的“人间自有真情在”这一剧情的出现。而从电影中潜在的叙述者的角度来看,李成功一定程度也是被善意讽刺的,其被属下戏称为“灰太狼”即可看出这点。牛耿则不同,他来自农村,虽在城里打工,但对传统道德伦理仍执着不已,这使得在他面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时候,尤其显得笨拙而朴直。 但也正是这朴直和笨拙,更加反衬出李成功自以为是的精明和狡黠,因此一旦他们遭遇天灾个人变得渺小而无能为力时,李成功的自以为是就更加显得滑稽和相形见绌,其最终能在牛耿的“人间自有真情在”中幡然悔悟,也无不与此有关。因此,可以说,所谓“人在囧途”其实也就是商业文明遭遇传统伦理道德而经受一次蜕变升华的过程,对个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囧途”,但这无疑也暗示了某种历经磨难后的提升,是人生走向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有与没有这种磨难,其意义显然并不相同。 二、有关“家”的隐喻的故事 这部电影无疑是一部讲述回家/返乡的故事,这从旅途——回家这一十分清晰的剧情结构中可以看出,家/乡在这里显然被赋予了极具象征和寓言式的含义。但问题是,家/乡的含义并非明晰而确指,而毋宁说只是一个能指,其有无限的可想象的空间和可能。从这一角度看,电影临近结局“回家就好”这一句充满温情的表白,与其说是把李成功推向了充满温馨的家庭,不如说是把电影所欲表达的深刻内涵推向了远方或更加晦暗处。“回家”首先意味着“家”之存在,但“家”对人们而言,并非不证自明的,而毋宁说充满了歧义,是歧义重生的空间。“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是抽象意义上的存在,又是有其具体的所指。其既可能指向精神上的归宿或家园,或者某种和谐自足的秩序,又可能是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而这单位有时又是同家族甚至国家联系在一起,所谓“家国”,有时候“家”是等同于“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家”就是某种隐喻。而对电影而言,“回家”其实又预示了离家的存在。这一离家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千百万的中国民众外出谋生的经历,家对他们而言实实在在而念兹在兹;另一层面则是,当李成功以及和千万计的中国百姓匆匆赶往家乡的时候,牛耿却踏上了更为远离家乡的路途,这是另一重离家。而第三个层面则是指,对温暖而和谐之家或秩序的背离。这在电影中主要是表现为李成功婚姻感情上的外遇。从这个角度看,显然,离家/返乡这一过程所关涉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意义的行为,而毋宁说同集体甚至国家纠缠在一起,而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p#分页标题#e# 在这里,不管何种离家,都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问题是,李成功及千百万民众纷纷赶赴家乡的时候,牛耿却踏上了再度离家的“囧途”。牛耿无疑是被市场和全球化所剥夺的底层,他的离家讨债其实早已注定了一次没有结果的无望之旅。从这个角度看,当李成功的妻子以“回家就好”的表白完成对和谐秩序的重建的时候,牛耿的再度出走其实从另一个层面预示着另一重分裂,这是一重更大而根本的分裂。如果说李成功的妻子完成的只是家庭伦理的重建的话,牛耿所早已注定的命运则意味着现代文明所潜含的颓败和无力。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仍不失对生活的赤子之心。命运百般捉弄他(所谓囧途),但他没有为命运的捉弄而丧失生活的乐观向上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可能是一种天真,但却是一种饱和生活智慧和传统的伟大的天真,是对社会和国家充满信心和期待的体现。 而说这是有关“家”的隐喻还在于其对家庭伦理的渲染。 影片显然还可以看成是关于第三者或小三的故事。但这一小三并非破坏情人家庭幸福的小三,而毋宁是对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幸福的强化。影片中之让人忧伤之处就在于两种真情之间的选择。李成功无疑很爱自己的妻小,这种爱是真爱;但他又是非常爱他的情人,这种爱也并不比对妻子的爱要少。 同样,他的妻子和情人对他的爱也是真爱,不掺杂半分虚饰和矫情。得知丈夫与她人有染,其虽心有戚戚焉但仍不动声色,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怨言,足见其贤德良惠和对丈夫的深情。 情人对他亦是如此。面对这样的两个人间之奇女子,作为中产阶级的李成功可谓幸矣,但这对他无疑也是一种煎熬和难以割舍。显然,对于他(她)们三人而言,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道无解的选择题;但主动做出选择的却是小三。她之退出并非因为其小三身份的暧昧和不合伦理,而毋宁说是因为爱。 其因爱李成功而投入他的怀抱,又因爱他而释然离他而去。这俨然就是一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间尤物。但若细加分析便会发现,在这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毋宁说是传统家庭伦理及其道德规范。影片中小三是在看到了李成功的妻子之温良贤惠之后才决定离他而去的。李成功妻女及婆婆之间其乐融融的家庭场景深深感动了小三,也使她坚定了放弃的决心。这无疑是传统家庭伦理及其道德观念的伟大力量,其能使得任何充满“原罪”的感情得到升华,也能使得本就真诚的感情变得更加真诚。影片之让李成功回归家庭,毋宁说是对传统家庭伦理和秩序的回归。 三、两个阶级的遭遇与和解,及其政治修辞术 显然,春运期间回家对不同阶层的民众而言,其意义是不同的。春运这一现象无疑是带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经验之一部分,但春运对不同阶层的民众来说,并非都成其为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只有对于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而言,春运才真正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对于中产阶级,则不尽然,春运回家之艰辛是他们难以想象的。《人在囧途》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制造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春运时空:在这个时空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平等而面对面的接触,这一时空也为他们之间截然不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观的戏剧性或喜剧性冲突创造了可能。从时间上看,这一时空(影片叙述的时间)正好与2008年冰灾巧遇,影片虽然没有指明其间的联系,但其实是以后者为背景展开的,这就使得社会上不同阶层的民众有了一次直面接触的可能,处于两个不同阶层的李成功和牛耿这才阴差阳错地遭遇,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走在了一起,自然也就引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家”的隐喻显然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含义,电影通过“家”的形象符号试图化解不同阶级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对立。其以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符号——“家”的形式,表现出的是对这种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的超越,并最终达到对阶级间矛盾的消弭;其以貌似永恒的道德诉求和命题,其实掩盖地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以此论之,《人在囧途》显然是阶级矛盾的象征性文本。 影片中充满了喜剧的元素,但喜剧剧情的营造并非影片叙述的意图所在,而毋宁说是通过喜剧式的剧情,建构了一个不同阶级间和解的方式和场域。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当前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即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一现象往往也造成民间社会中仇富心理的普遍滋生,其在近几年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热点新闻事件中都可见出。两个阶层或阶级间的隔阂和距离无形中在加大,矛盾在加剧,这一加大的表征往往呈现为叙述上的两个极端:要么是像电影《我叫刘跃进》那样对底层妖魔化的想象和叙述,要么就是像电影《高兴》和《叶落归根》那样对底层的浪漫化的想象;而少有电影真正表现出对两个阶级间和解的想象和叙述,两个阶级间显然缺乏平等而面对面的接触。从这点而言,《人在囧途》无疑提供了一个两个阶级和解的文本。李成功和牛耿之间从最开始的隔阂戒备,到最后的肝胆相照成为朋友,显然表现了这样一种阶级和解的想象。通过一路同行及其历经的种种磨难,彼此磨合之后,两个人的人生都在“囧途”之后,获得了质的提升,中产阶级的代表李成功最终成为一个合乎伦理的好男人,牛耿在李成功的暗地帮助下,事业也开始真正的起步。 但细细看来,影片的叙述中其实存在大量的裂缝和可圈可点之处。牛耿无疑是一个极其符合中产阶级对底层的一厢情愿的无害式想象之人,其虽粗鲁无知,但本质上却相当憨厚,这种带有“原初性”的对于底层的想象,既能让中产阶级无所顾忌地“亲近”底层,同时又能保持其天然的优越性。反过来看,如果牛耿不是这样一个无害的形象,而是《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那样的农民,相信中产阶级的李成功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走近牛耿,受其“折磨”的。所以,从表面看来,是牛耿朴素的世界观(“人间自有真情在”)以及他的行为举止感染并触动了李成功;其实是遮蔽和覆盖这样了这样一种预设或逻辑,即,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发生,显然是因为预设或假想了一个可供言说的无害的底层形象。而正是在这种对底层的想象中,中产阶级和底层间的和解才能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这种和解只是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叙述。#p#分页标题#e# 表面看来,是牛耿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触动了李成功,而使得李成功幡然悔悟,似乎是牛耿改变了李成功。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在经历了一番囧途和磨练之后的李成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底层的偏见,底层之受窘迫的命运也并没有获得根本改观;牛耿后来的成功也并非因为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劳,而毋宁说是源于中产阶级的施舍和恩赐。在这里,底层在这里其实是很被动的,某种程度上是“被和解”了。 实际上,从后面的剧情来看,如果不是李成功拿出自己的钱帮助牛耿的话,牛耿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而不可能有结尾处的发家。可见,这部影片其实反映出对底层的潜在的恐惧以及和解的愿望。结尾处,对于高调出场的牛耿来说,此时已经不再是底层,而毋宁说是另一个李成功了。显然,这种和解并非阶级之间的和解,也并非对彼此间矛盾的消弭,而毋宁说是以底层迈向中产阶级的方式表现出对两个阶层间矛盾的遮蔽:底层作为底层的结构性存在一仍其旧,改变的只是底层中往上升的个体性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影片一方面表现出在两个阶层间和解的潜在愿望,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其间存在的差距和矛盾。 对于一部喜剧电影而言,《人在囧途》无疑是成功之作,其能赢得无数中国观众的掌声和笑声,也能包含独有的中国的经验于其中,且剧情设计也并不显得十分生硬牵强,但也正是如此才更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注意。喜剧之让人大笑而后放松并得到宣泄,这些都是喜剧的特有功能,但往往也是在这笑声和宣泄中,在故事贴切的叙述和呈现中,某些内在或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某些深层的意识形态内涵隐而未彰并被有效的遮蔽;以此观之,对于《人在囧途》而言,其遮蔽的内容,显然不比其表现的要少,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