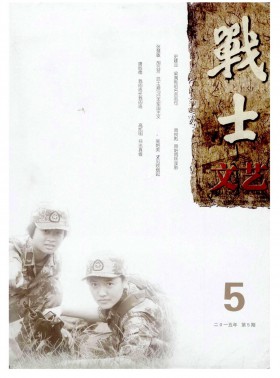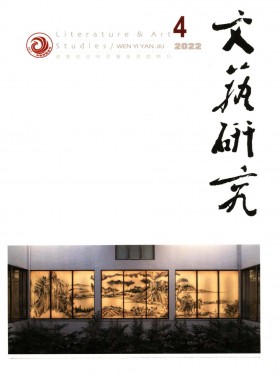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艺联盟的文化政治价值,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杨红英 单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成立于1934年5月6日的台湾文艺联盟(以下简称文联)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次最为广泛的全岛性文艺联盟,其活动时间虽然不到两年,却造成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空前团结情绪高涨的盛况,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更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台湾人主办的刊物中发刊时间最长、登场作家最多的文学刊物。台湾现代文学大家王诗琅认为:“这时期的作品已渐摆脱初期的暴露式的政治色彩,站在文学的立场去观察,描写渐多,所以都有艺术气味。”因此称赞道:“全部出了十五期,不但寿命长,几乎网罗全台的作家,在台湾新文学建立辉煌的一页,即以对于整个文化的影响而言,也是深且巨的。”[1]P152-153文艺联盟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但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它的几番社会活动对开拓台湾上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活动领域、传达殖民地心声以实现知识分子使命的重要文化政治意义。在这里,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文化政治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的肯定;是对“命运”、“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些似乎预先存在的东西进行重组;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或建基于经济政治的“副现象”,而是在建构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联开创了台湾30年代在三大民族运动相继偃旗息鼓后知识分子参与文艺、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公共舞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文联的结成情况及其主要文艺活动;1935年台中地震灾后救援活动与组织延请崔承喜来台公演。
一、以文艺代政治———文联的结成
1.文联结成的社会背景
台湾自割让日本后,开始其由殖民宗主国日本所主导的被迫的现代化进程,其间渗透着被殖民的屈辱与悲哀。作为现代化之一环,日本殖民当局所开办的现代教育体制,尽管充满歧视,它所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上世纪20年代初逐渐成熟,并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日本大正时期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潮和威尔逊民族自决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展开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1921年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讲演会和讲习会、创办报社、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等一系列的活动启发民智,宣扬民族文化,促进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台湾全岛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高潮。但由于民族运动路线方针的原则性分歧,文化协会内部形成了连温卿代表的无产阶级派(主张无产青年应占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派(以农工为基础的全民运动的路线)和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将文化运动局限于文化的范畴),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1927年林献堂等的退出标志台湾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协会采行了激进的斗争方式,殖民当局全力取缔,因而在新竹讲演会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的打击后,文协在1931年宣告解散。1927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为其纲领。其主要活动有抨击总督专制统治和警察的横暴、向国际联盟控诉台湾“卑劣的”鸦片政策、揭露所谓总督府评议会花瓶摆设意义、要求废除封建保甲制、取消限制台湾与大陆间往来的渡华旅券制度、反对所谓始政纪念日、举办大规模的讲演会等,其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很快取得了台湾大众的广泛支持。但蒋渭水以农工势力为中心、联合各阶级的全民政党,即所谓“大众政党”的建党思想,同蔡培火、林献堂等以舆论的力量来逼迫总督府放松专制统治,着重于启发民智,最终实现殖民地自治,斗争的手段以合法性为原则之一派之间产生矛盾。
在蒋渭水一派实际掌握民众党主导地位,“左倾”色彩日渐浓厚的情况下,林献堂等人酝酿脱离民众党,并于1930年8月17日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931年2月18日,日本殖民者宣布取缔民众党,理由是:第一,民众党随着稳健分子的退出已为左派所把持,故不得不予严正处分;第二,民众党的目的,在于反对总督政治、宣传阶级斗争,妨害日台融合,违背本岛统治大方针,断难容许[3]P185。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纲领的核心内容是确立台湾地方自治。在台湾岛内设立支部,进行巡回政谈讲演会,举办地方自治改革促进运动,推出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案,恳请太田总督实施诸如义务教育、改编教科书、重组公众团体政策等等。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叩头请愿的自治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在法西斯分子日益猖獗,军部势力急剧膨胀的背景下,岛内一切有碍日本殖民统治及同化方针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均遭殖民者横加镇压,就连温和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林献堂也因祖国事件遭法西斯浪人的殴打,以至于台湾岛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4]P448。1934年9月台湾总督向林献堂等下令,停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逐渐无所作为,趋于瓦解。自此,台湾在20年代所形成的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成为过去。
此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继“九•一八”侵占我国东北后积极为全面侵华作准备,对内强力镇压左翼组织,台湾社会运动因此几陷窒息状态,岛内情绪一片低靡。民族运动所担负的启蒙大众、唤醒民族意识、批判殖民统治等使命,使其成功开拓出一片政治公共领域来,遭到镇压瓦解后,公共领域自然开始萎缩。对这一危机,台湾文艺联盟的发起人如张深切和赖明弘都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前者在自己的自传中这样写到:“民国二十三年,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我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我看左翼组织已经被摧毁,自治联盟也陷于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台湾民众意气消沉,不得不决意承担这个带有政治性的文艺运动。”[5]P609后者也深有同感:“回忆当时台湾的客观情形,有着使台湾文学运动发生的各种因素存在,盖当时反对异民族统治的政治运动受了最严重的威胁和打击,……趋入地下活动,表面上看来,进步的台湾政治运动被摧残,被压迫得零落无声,呈现着一片萧条景象,这使台湾知识分子必然的要找一出路,自由主义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由于这客观情势的要求,台湾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对建立新文学这一条路认真的做起来,大家并且认为有组织文学团体的必要,所以才很快的就能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在那时的台湾,看上去有如文学运动替代了政治运动之概,所以当时的台湾文化与政治界受文学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重大的。”[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联的发起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目的是为台湾知识分子保住一块公共领域,以文艺之名行政治活动之实。而在哈贝马斯那里,文学自能成为一种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就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发展而来的。“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7]P32因此文联是对20年代台湾民族运动涵养启蒙大众、实现文化抵抗的光荣传统的延续与传承。#p#分页标题#e#
2.文联的章程与主要活动
1934年5月6日的第一回全岛文艺大会在经过讨论商议后通过了文艺团体组织案,宣告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文联在其创立时就遵循政党社团的模式来操作运营,有严格的文艺联盟章程,并选举了执行委员黄纯青、黄得时、林克夫、廖毓文、郭水潭、赖庆、赖明弘、赖和、何集璧、张深切等15名,后5位为常务委员。联络台湾文艺同志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兴台湾文艺,是文联的宗旨。发刊杂志、刊行书册、开文艺座谈会、开文艺讲演会是文联的主要事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上曾分四次刊载了文艺同好者的名单及其住所,第一次183人,第二次83人,第三次72人,第四次54人,除去几位个人信息变动导致的重复外总计396人左右。从这份名单来看,同好者遍布台湾各个领域如律师、医生、商人、金融家、企业家、教师、文艺家等。其中不乏台湾民族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物如林献堂、蔡培火、林幼春、杨肇嘉、彭华英等,台湾精英阶层的人物如医生赖和、蔡阿信等,律师杨基先、陈逸松等,金融家陈炘等,新闻人如吴三连、刘捷、叶荣钟等,教师如林茂生、江璨琳等,他们不一定都从事文艺创作或批评,但都是社会使命感非常强的知识分子,在正常的政治社会运动受到极大打压后,文艺成为其新的战场,他们后来都成为台湾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一创举式的行为,充分显示了文联同仁为贯彻其联络台湾文艺同志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兴台湾文艺的宗旨所作的努力。台湾知识分子在文联号召下,一扫此前的沉闷之气,出现空前团结情绪高涨的局面。其正式的联盟成员也达101人。其后嘉义、埔里、佳里、台北、东京等支部相继成立,又先后或在台北,或在台南,或在嘉义,或在东京举行了文艺座谈会,文联声势日显浩大,一时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对此,当事人也是发起人之一的赖明弘先生有段公允的评价:“由于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才确立了文学运动的第一步,才起了领导台湾文学运动的作用,文联团结了作家,团结了知识分子,更溶化所有反封建反统治的,富有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于一炉,展开了提高台湾文学和文化水准的工作,并确保了台湾精神文化的基础而对异民族表示了坚毅不移的抵抗。”[6]因此可以说,文联是台湾反抗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虽然从事文艺文化活动对大多知识分子来说有点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但是现代文化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实践,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说“……要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和继续存在,只有(而且只有)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一个自主的(也就是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权力)知识世界赋予的,他尊重这个世界的法则;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将这种特殊权威用于政治斗争。他们远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处于寻求自主(表现了所谓‘纯粹的’科学或文学的特点)和寻求政治效用的矛盾之中,而是通过增加他们的自主性(并由此特别增加他们对权力的批评自由),增加他们政治行动的效用,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在文化生产场的特定逻辑中找到了它们的原则”[8]P396-397,正是文化的自主规律为知识分子赋予了特定的权威性,使其政治参与显得更为公正无私,从而更具合法性。
二、命运共同体———台中地震的灾后救援
1935年4月21日新竹、台中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规模达到里氏7.1ML,有感区域几乎遍布全岛,更达福州、厦门地区,除造成大范围的山崩地滑外,并在苗栗、台中地区产生狮潭与屯仔脚地震断层,给台湾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死3,276人,伤12,053人,房屋全毁者17,907间,半毁者11,405间,破损者125,376间[9]P280,成为台湾20世纪灾情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文联成员、《台湾文艺》日文版编辑杨逵亲自到灾区现场考察慰问,并对当时的灾后惨况有一个真实的记录:“数百户的人家棋牌般倒成一堆,连路都被倒塌的房屋埋没了。刚挖出的尸体散放四处在炙热的阳光下曝晒着”,“快到村庄的路上,又碰上棺材的行列,有许多送葬的人。台湾人对死者的葬礼非常隆重,一般是八个人抬棺,而现在却用拖车搬运,有时一辆牛车还堆叠四五个棺材,形成行列运往坟场。这和平常不同的出殡行列,凄凉的哀号,深深震撼着我”[10]P137。作者非常巧妙地用早已积淀在人们心中对葬仪的高度看重的慎终追远的集体无意识反衬出此次灾情之惨烈。
由于文联总部及其机关刊物编辑、发行地设在台中,文联的核心成员也多在台中地区生活、工作,使得他们对这次地震有了最直接和深切的了解,产生强烈的震撼,更为他们提供了实现社会理想的空间与舞台,原定于4月28日召开的第二回全岛文艺大会也因为全力以赴于救灾活动,而推迟到8月11日方始举行。面对这一突发的自然灾难,张深切利用文联这个全岛性的组织和自己任主编的《台中新报》同仁成立一个救灾总部,参加的人员分为募捐班、调查班、配给班三个班。募捐班主要由叶陶、张碧姻、林月珠等女士组成,她们从附近的乡镇开始,一直进入嘉义市,用扩音喇叭在街头征募小额捐款和生活用品。调查班和配给班则深入灾区台中、新竹等所属的山涧僻地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随即进行救灾物质的配给和分发。各班的负责人,每晚一直到一二点还聚在救灾总部讨论活动报告及次日的活动计划。从各班投入活动到5月6日解散的十几天,他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地投入到紧张的救援活动中去,直接参加的文联成员多达60人(超过文联半数)。因为周密策划与热情投入,所以虽然收到的钱和东西很少,却都是急灾民之所急,真正是雪中送炭,意义颇大。特别是在神冈的新庄子、圳堵等地,尽管整庄灾情惨重,但却长期被弃置不顾,直到地震3天后,灾民才因为调查班的深入调查而首次每人分配到壹碗米饭,发挥了民间赈灾团体的巨大作用[11]P137。张深切对文联成员们高涨的热情这样描述到:“号召的文书一发,各地文联成员立刻驰来应援,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灾运动。他们都自备旅费,日常生活也自己负担,分队挨户募捐,把所集的许多物品和金钱,直接送到灾区去,发挥了极好的效果。”[5]P615而尤其突出的是杨逵。他从一开始就对此次地震给予深切关注,积极参与救援活动,并把灾情及救援活动状况用报告文学形式及时发表在东京的《社会评论》上,引发更多的人们对震灾的关注与支援,既讴歌了对灾区深富同情心的人们的善良,也暴露了某些淡漠冷酷乃至发灾难财的黑暗现实。他在《台湾文艺》上发表《台湾大震灾记———感想二三》,反思人们应该丢掉对天灾的宿命论的消极,加强震灾预防的科技意识,一定能大大减轻灾难的严重后果。在人们渐渐淡忘的时候,他写下《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区劫后情况》为那些未被关注的人们呼吁,批评漫无章法的重建情况,抨击恶劣的保正多拿配给恐吓殴打请愿灾民的罪行[10]P165,切实地用笔和行动来实现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使命,真正让自己所高唱的社会理想落到了实处。因为赈灾行动未配合政府经过例常程序,所以取得很好的效率,但终为争功善妒的御用走狗所诬告,引来台中州政府的敌视,张深切也遭警察局传讯。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赈灾行动虽然充分显示了文联积极融入台湾自身乡土与社会,为展示自救自治能力,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所作的殷殷努力,及其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在异族殖民统治下,这注定要被视为威胁殖民统治的叛逆行为,逃脱不了被敌视被取缔的结局。这也是一种殖民地的悲哀吧。#p#分页标题#e#
三、由民族而世界———延请崔承喜来台公演
崔承喜,现代朝鲜舞蹈的开拓者,1911年出生于京城(今首尔)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本属两班士大夫阶层,日本入侵后,原有土地被日帝没收后沦为贫民,以私塾为业,哥哥崔承一是著名的卡普———朝鲜无产阶级联盟———作家。1926年崔承喜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京城淑明高等女子学校,那一年她与哥哥去京城公会堂看日本现代舞开拓者石井漠公演的《囚人》舞蹈,受到西洋现代舞的冲击与感动,因而立志成为舞蹈家,哥哥崔承一于是说服了石井漠收妹妹为留学生。同年5月,崔承喜到东京跟随石井漠学习现代舞,三年后就担纲成为主角舞者,更被提拔为“首席代教”指导后进。1929年夏天,因石井漠在演出中途突然失明,崔承喜回朝鲜开舞蹈研究所,18岁就成为朝鲜第一位现代舞蹈家。1930年到1932年,她在京城公会堂举办了三场公演。作品主要有两类,一是以传统朝鲜民族舞蹈为基础而创作的《剑舞》、《僧舞》、《灵山舞》、《丰收歌》,二是《印度人的悲哀》、《失去祖国的人们》、《向着太阳》、《劳动者的行进》、《苦难的路程》、《迎着希望》、《两个世界》等现代舞,主要反映了弱小民族的悲哀和朝鲜人民的反日精神。公演得到很高的赞誉:“她负了衰落已久的朝鲜舞蹈艺术复兴的责任,在恢复朝鲜久已失传的特殊舞艺的努力上,她凭着坚毅的力量和稀有的才干,奠定了整个东方民族舞蹈艺术新时期的一方有力的基石”[12]P51。1933年崔承喜再度到日本随石井漠习舞,翌年在东京“青年会馆”举行公演,盛况空前,由此引起日本文艺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半岛的舞姬”的美名随之传播开来。此时其舞蹈逐渐摆脱石井流派的舞风,形成自己融合西洋现代舞和朝鲜传统舞蹈的独特风格。
1936年7月,崔承喜到台湾巡回公演,造成巨大的轰动,是台湾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和台湾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此行完全由文联主办,从盛情邀请到宣传报道再到交流座谈,文联为此费尽心机,也对此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确定在台演出日程后,文联东京支部为她举办了欢迎会,并制作了一万册收集了她许多照片的“崔承喜专辑”。1936年的《台湾文艺》5月号刊载了欢迎会活动的介绍,从日本的《会馆艺术》转载了崔承喜《我的自白》,并以文联名义发表《关于崔承喜的舞蹈会》。6月号转载崔承喜《尊敬的母亲的眼泪》。公演结束后文联作家曾石火和吴天赏分别撰文《舞蹈与文学》、《崔承喜的舞蹈》描述对其舞蹈的观后感,高度肯定了崔承喜的舞蹈艺术成就,并对现代舞这种在台湾还不多为人了解的艺术作了赏介。而崔承喜的电台广播稿《关于我的舞蹈》也同期———第三卷七八合并号———在《台湾文艺》上刊出。宣传不可谓不竭力。张深切在崔承喜的台中公演结束后,与之有一番关于殖民地人民的性格扭曲的会谈,颇有同病相怜之感,崔承喜没有祖国就不会有艺术的强烈的爱国情感也给了张深切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由于公演的巨大成功,使一度因日文编辑杨逵的离开有所削弱的文联显示了其在台湾文艺界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张深切称其“使文联蓬荜生辉,声价十倍,至此反对派不得不暂时缄默”[5]P625。但此番活动却遭到当局的默杀,也让文联招致日本政府更大的压迫,文联活动渐次无声,几成文联最后的绝唱。但崔承喜的台湾公演的重大意义却是不容抹煞的。崔承喜将西洋舞蹈和传统的朝鲜舞蹈融合在一起,在殖民统治下创造了近代民族艺术,不容殖民者小觑,1936年到1940年的环球演出更是为她自己、她的民族赢得了世界声誉。正如一位外国新闻记者所说“日本奴役朝鲜,却奴役不了崔承喜”[12]P10,她为专注于艺术活动的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提供了一个在艺术领域里可以发展并保留民族文化的成功典范,更为那些在殖民统治下失去民族自信,在民族身份认同中苦苦挣扎的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作为主办者的文联的深刻用意即此得以彰显!虽然在殖民统治的监控、镇压与瓦解之下,文联活动不到两年,渐至覆灭,未能尽如所愿,但其强大精神感召与鼓舞的力量却是不能低估的。其冲破政治的黑暗,用文艺为台湾人开创一个公共舞台,传达自己的声音,团结振奋民心,以实现对异族统治的坚定的抵抗,成为文化抵抗的重要一环,书写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