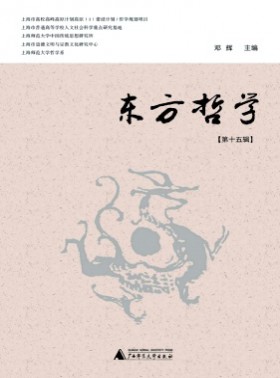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哲学创新论文:我国哲学发展前景思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陈嘉明 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知识是否由“真、信念和确证”这三个要素所构成,这不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样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习惯性联想的产物,还是属于先天性的、用以综合感觉质料的范畴,这一类解释的价值,其差别只是在于何种解释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在于它们究竟出于哪一国家的哲学,不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从“特色”的角度来发展中国哲学想法的人,容易引证的一个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题里,“民族的”意味着特殊的,“世界的”意味着普遍的。上述说法的含义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现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说法从特殊与普遍的联系上来强调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义。不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本来讲的是有关民族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弘扬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同一种艺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同样是声乐,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声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们通过不同的发声与演唱方法,来求得共同的悦耳的声乐美感,体现的是共同的本质。不过,“民族的”就一定会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在艺术领域本身就遭到了质疑。赵本山的“二人转”很够“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国表演却不受欢迎。可见上述命题是否能够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某一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则也成不了“世界的”。进一步说,艺术表演追求的特殊性与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追求某种新鲜感,由此可以愉悦人们的感官,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哲学学说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取悦感官的方式来获得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通过其思想的意义来获得接受。虽然哲学学说可以通过不同的论述方式来传达,如庄子的散文诗般的叙事方式、康德的先验论证方式、维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论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种哲学的价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们的表现方式,而是在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内容。而这类思想内容的价值,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取决于它们在解释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关哲学研究的途径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那里也出现过。这里我们举冯友兰、陈荣捷和牟宗三作为三种类型主张的代表。冯友兰主张哲学的普遍性,陈荣捷持相反的观点,而牟宗三则介于两者之间,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张特殊中有普遍。我们先来看冯友兰这方面的具体主张。在他看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①显然,冯友兰认为哲学只有一种,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凡能够称之为哲学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哲学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中有普遍的公共底义理。”②这意味着哲学不分东西,思想不分国界。假如想以语言的不同来论证某一民族的哲学的特殊性,这在冯友兰看来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连民族性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追求哲学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④。
由上可见,冯友兰主张的是普遍性的哲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即使对于中国的哲学家而言,也不应当以追求所谓的“民族性”为目标,不应当以“民族语言”为口实来强调所谓的“特色”。与冯友兰的上述主张相反,陈荣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的中国哲学。他明确提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⑤之所以应当如此,陈荣捷的考虑是,如果在中国哲学中发现的东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便完全没有意义。因此,为了凸显中国哲学的价值,以吸引西方学者的目光,陈荣捷便强调它与西方哲学的异趣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将哲学视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着需要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认可相同的研究对象,并不见得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解释就是相同的,譬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的解释(西方近现代主流性的观点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国从古代以来的主流性观点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张,其论证也不尽相同。如中西哲学家都有主张性善的,但他们的论证则大相径庭。其二,中国哲学家可努力开拓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即使与西方哲学家具有相同的哲学理念(比如认为,哲学是研究真善美的学问),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西方哲学本身曾经拓展的那样(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等。仅以语言哲学为例,也有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之分)。比起冯友兰与陈荣捷,牟宗三则有另一番考虑,可称得上是“第三条道路”。牟宗三也认为哲学具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却是出自中西哲学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学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体论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学各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两者各自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它表现为中西哲学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发展而来的。由于这种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学各自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虽然中西两种哲学的开端及其主要课题不同(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而西方哲学的传统则是“科学”),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关键是要从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从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虽是山东人,但他讲“仁”却是对着全人类讲的;此外,仁既然是个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样的,因此与之相关的普遍性也是多样的,也有其独特性。③这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能够“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对于上述牟宗三的论述,有两点应当说明的是:其一,它是从哲学的历史形成的角度(开端)来谈中西哲学所具有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谈论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着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论述中西哲学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为了说明这两种哲学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第一点的说明尤其重要。#p#分页标题#e#
本来,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学说,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科学”。哲学自然也不会例外。特别是从思考的性质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尤其是从“普遍”的角度来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给出的解释,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知识,它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反之,数学则是从特殊中考虑普遍。⑤我们还可把康德的这一解释延伸开去,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也是从可观察的特殊现象中,来归纳、概括出普遍性的规律的。哲学之所以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向相反,这是由它的非经验的性质决定的。哲学的思考起于科学止步之处。譬如,科学研究事物之间具体的因果现象,并使用因果概念来把握这类现象。但对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学本身并不探究。哲学对于这类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学使用的概念为前提的,因此这类概念就不表现为通过归纳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现为既有的、“验前的”(apriori,或译“先天的”)的存在。这样,当哲学着手对这类概念进行研究时,它们就已经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现。哲学思考所进行的,乃是对这类概念的性质、语义、功能等进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为具有一种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对两个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相续的感觉现象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规定为假言判断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应的综合判断。对于诸如“善”之类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学并不通过归纳来说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为一个既有的范畴来加以分析,以此来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尔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论述了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他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①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学既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那么要寻求特殊性以作为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方向的做法,就显得是悖理的。说中国哲学的思考应当与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应当跟着西方哲学亦步亦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可以追求所谓的“特色”,这在学理上则是说不通的。在本人看来,如果不从普遍性的角度上着眼,而仅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哲学是不利的。它可能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限制哲学家的视野,使得他们对哲学问题的考虑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寻求所谓自己的“特色”,往往是“传统”的新包装的代名词。一讲到中国哲学,就局限于传统的旧框架,如“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仁义礼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内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从“本心仁体”这一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外王”。但实际上,在牟宗三思考这一使命的年代,对于思想界与理论本身而言,民主与科学已不是能否开出的问题,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本身(如,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等),对科学的价值、科学对环境、社会的影响进行反思、检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停留于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此,不能去开拓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与领域,就会妨碍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儒家的一个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们停留于特殊,执守于儒学的心性论,把它作为“道统”来奉行,作为判断某种学说是“正宗”还是“别出”的标准,继而以正统自居。换言之,“道统”成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似乎离开了这一“特色”中国哲学就无路可走。
“道统”成了独断论的最好的遁词,成了束缚中国哲学发展的“绳索”。其结果是,越想继承道统,越是失去道统,因为道统在保守中趋于陈旧,从而落后于时代,于世无补。以上述的由内圣(本心仁体)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的哲学理路为例,一方面,停留于理想化的“本心仁体”状态,把原本只是属于“设定的”的心灵状态当作是实有的,并把它加以绝对化,夸大化;另一方面,停留于五四时期对于社会本质的认识,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认识阶段,而不能深入到更为深层的人的“权利”的根本,其结果是从理论层面到现实层面上下两头的把脉都失准。由于道统与学统的观念的束缚,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反思与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具有这类意识,发现并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不足与缺陷,传统才能真正得到推进与发展。这就像医生治病的道理一样:假如一个医生只是一味地称赞病人身体好,而不指出他的毛病,其结果只会是害了病人;反之,指出病之所在,帮助病人把病治好了,这才是良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倡导普遍性的哲学观念,并不意味着把哲学理解为一元的东西。普遍离不开特殊,它在特殊中得到体现。哲学不过是哲学家们各自所提出的哲学。他们既可以对不同的对象提出自己的哲学,也可以对相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哲学,所以它总是展现为多元的、多样的。本人在拙文《新儒学与哲学创新问题》中曾论述哲学与经验科学、数学的不同在于,它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对语言(如语词的意义问题)的解释如此,对价值概念的解释(如“正义”概念)也如此,因此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哲学的多元性,不仅在于对不同的现象领域(如语言、生存、心灵等)的解释可以产生不同论域的哲学,并且在于对相同领域的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产生不同解释的哲学。
这样的说法似乎与哲学具有“普遍性”的说法相矛盾。不过,哲学解释的普遍性在于,虽然对于同一的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每一种解释却各有其普遍性,只是这种普遍性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或关涉的方面不同而已。例如,语词意义的“使用说”与“指称论”,两者都有其解释的效力,只是后者适用的范围要小些。如“鲁迅”之类的专名,其对象已经不存在了,无法指称了,但这一语词仍然有其意义。再如,对人的本质是“理性”或是“非理性”的解释也是如此。人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加上每个人又有其特殊性,因此他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况下是理性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情况下则是非理性的。本人的上述解释与牟宗三的“特殊中的普遍”的解释在结果上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两者依据的基础不同。牟宗三依据的是黑格尔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学说,而本人则进一步借助于“多值逻辑”。在笔者看来,各种哲学之所以能够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在于它们具有各自的真值。不过由于这些真值分布在“0”与“1”的区间之内,因此它们“真”的程度并不一样。这意味着不同哲学的解释可以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因此哲学可以是多元的、解释可以是多样性的,并且某种哲学具有的真值度越高,它就具有越大的普遍性。#p#分页标题#e#
主张哲学的普遍性与赞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哲学是不相矛盾的,这就像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可以这么做是一样的道理。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助于使问题的研究更趋全面,而不至于陷于片面性。此外,认同哲学的普遍性,从普遍性的立场来研究哲学,也并非导致由此而来的成果就没有“特色”。上面提到,冯友兰是赞同哲学的普遍性这一性质的,但他的《新理学》等著作,恰恰是很“中国”的。这是因为他的中国哲学的功底,使得他谈论问题往往会从这一角度加以考虑,加上他又有西方哲学的知识,因而这两者的结合,自然就有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因此所谓“特色”的问题,实际上是哲学家们从哪些哲学资源中吸取其思想元素的问题,是他们的“视域”的问题,而并非与哲学本身的性质相关。哲学的普遍性,应当说在知识论、语言哲学、科技哲学、形而上学等领域中表现得比较充分、明显。因为如同前面提到的,语词是否有其指称,其意义是否在于使用之中,这样的解释只有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无具体语言与地域性限制的问题。普遍性的争论一般出现在价值论、道德哲学这类主观性与文化背景色彩比较强烈的论域里。哲学家们受所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容易产生某种价值倾向,乃至产生排他性的哲学认识。此外,国内目前的哲学教学与科研的体制(即把哲学分为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也容易产生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分离,形成某种学科壁垒,造成哲学认识上的误区,似乎研究中国哲学就同西方哲学不相容,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必定是与西方哲学相排斥的。这样的认识误区是必须予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