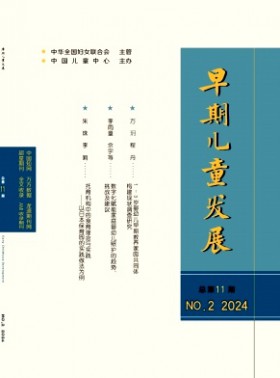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早期法律的翻译史,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英语世界对中文法律的系统英译盖滥觞于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于1810年翻译出版的英文版《大清律例》(TaTsingLeuLee;BeingtheFundamentalLaws,andaSelectionfromtheSupplementaryStatutes,ofthePenalCodeofChina)。1815-1823年间,比小斯当东仅年幼一岁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完成鸿篇巨制三部六卷本《华英字典》,其中的《五车韵府》(1819)对中文法律词语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屈文生,2010:79-97)。本文拟考察的重点不在于早期中文法律词语的英译情形,而在于早期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状况。对于英文法律词语传播至华的主体,文章的主要考察对象亦不在于诸如马戛尔尼(GeorgeLordMacartney,1737-1806)、老斯当东(SirGeorgeLeonardStaunton,1737-1801)、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等早期外交使节及商人,而主要在于19世纪中叶前后的来华传教士。如果说19世纪中叶前后的传教士在“中法西传”中发挥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那么他们在“西法东渐”中则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传播者甚至是布道者角色。早期西方法律词语的中国化及其“跨语际实践”过程实现,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华所编、所译、所著的各类书籍介质。1839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9)和四川人袁德辉节译出《滑达尔各国律例》,是文盖为的英文法律著作汉译之嚆矢,并在日后被收录于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三(王维俭,1985:58-62)。及至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译出《万国公法》,西方法律词语的一部分明显进入了汉语语言之中,并成为当时乃至今日中文法律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近代中文法律词语或话语体系至此还远未形成。自西徂东的法律词语除大量见于《滑达尔各国律例》和《万国公法》等主要由传教士完成①的译作外,还散见于传教士亲纂的双语字典、创办的报刊及撰写的文字作品之中。 一、传教士字典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在19世纪中叶传教士编著的众多字典中,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的《英汉字典》(1847)和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最值得关注。单就英文法律词语汉译(而非中文法律词语英译)的课题而言,其他传教士字典的研究意义则要稍逊一筹。比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大体上属于汉英词典(特别是其中的前两部,即《字典》和《五车韵府》),因而最好作为汉译英研究的史料,而非英译汉研究的脚本。马礼逊于1828年出版的《广东省土话字彚》(AVocabularyoftheCantonDialect)也属于汉英性质的辞书,它们不同于前述麦都思、罗存德等人编纂的由西向东式英汉词典。马氏辞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是中西初遇时中译英水平的忠实记录者,成为早期词汇交流中由中向西的重要载体。是故,在做英译汉研究时,马礼逊汉译英式的《华英字典》和《广东省土话字彚》均似无需过分着墨。 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1841年编纂的《广东省土话文选》(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于1842年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LessonsinChinese;orProgressiveExercisestoFacilitatetheStudyofThatLanguage;EspeciallyAdaptedtotheCantonDialect,Macao)和1844年出版的另一本辞书《英华韵府历阶》(An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均意在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以《英华韵府历阶》为例,它最初意在用拉丁字母为一批日用词汇标记官音,使外国人能掌握官话,方便他们到新开放的口岸与当地人交流,因为广东话在这些地方是不通行的(程美宝,2010:90-91)。它们的编纂目的因而主要在于解释或标记中文,而不在于将承载英语国家观念、制度、文化的词语翻译成中文,因而亦可不作重点研究。为使读者能对麦都思《英汉字典》和罗存德《英华字典》中的法律英文的汉译情况有一个大致的、直观的了解,笔者从上述二书中摘取数例,见表1。 相较而言,罗存德的字典因出版在后,所以它较麦都思的《英汉字典》收录的法律字词更多,解释也更为精细和准确。收词方面,以bankrupt为例,前者收录了与bankrupt直接相关的诸如bankruptcy(theactofbecomingabankrupt/倒行、倒灶、败盆)以及bankrupt-law(折本律例)等词条,而后者则未收录这些相关词语。再以law为例,罗存德的字典中新增了与该字有关的若干词语,如divinelaw(上帝之法)、humanlaws(人法)、municipallaw(民法/民例)、lawsofnature(性之法)、criminallaw(刑例/刑法)、ecclesiasticallaw(圣会律例)、commonlaw(通行之例)、statutelaw(律例/所书之例)、mercantilelaw(通商章程/通商法律)、lawofnations(公法/万国通行之法)、theMosaiclaw(摩西之律例)、ceremoniallaw(礼/礼仪)、doctoroflaw(律法博士)、topervertthelaw(枉法)、law-maker(设法者)等。而诸如Tort这类常见法律术语,麦氏的字典根本未加收录,但在罗氏的词典则可查到此字。解释方面,以bigamy为例,罗氏的字典已明确将其译成达意的某种犯罪——“双室之罪”,离今日通用的“重婚罪”已是一步之遥。 还要注意的是,从表1来看,麦都思早在1847年的《英汉字典》中就已将law译成“法律”(虽然二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尚未确立),更早的,在马礼逊《五车韵府》中,即可看到law与“法律”的对译(Morrison,1819:146)。可见“法律”并不是一则“外来词”(高名凯、刘正埮,1958:131),准确地说,中日“书同文”的“法律”二字只是借清末大规模的日本法律译介和法律新词的输入,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使用,进而与英文词语law正式确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此外,上述两部词典中也有部分英文法律词语找到了汉语中的对应词,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得到了后世学者、字典及书籍的认同,并一直传承到了今日。如witness(证人)、bribe(贿赂)、plaintiff(原告)、defendant(被告)、testimony(证言)等。当然这些词语的对应早在马礼逊的《五车韵府》(1819)中即已确立。(屈文生,2010:95)#p#分页标题#e# 二、传教士报刊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也是早期英文法律词语汉译的重要载体,其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andWesternMonthlyMagazine)尤其值得一提。前者被认为是已知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主要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于1815年8月5日(嘉庆乙亥年七月初一)在马六甲创办;后者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ützlaff,1803-1851)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1837年后出版地迁至新加坡),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内地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政法类文章较少,米怜曾自称该刊“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宁树藩,1982:65)。但该杂志曾连载前述麦都思撰写的《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Catechism)文章,对英美两国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些许介绍,故涉及不少法律词语;该文于1819年单独出版,共21页,用作小学生简明教科书(熊月之,1994:115-116)。现择其要者,对文内法律词语的中译名列表分析如下,材料主要来自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从上表可知,《地理便童略传》保存了早期中文法律译词的形态,但它们大多尚未定型;传教士在翻译上述词语时,多采用“归化”译法,以贴近当时的中文习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世代公侯”“乡绅世家”“乱拿”等译词即为例证。“总理”二字看似熟悉,但笔者认为它并非是今日PrimeMinister或Premier的译词②,而是President一字的翻译;关于这一判断可从如下引文判断得出:“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熊月之,1994:116)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涉及政治与法律的文章较多。王健教授认为,《东西洋考》是最早将世界各国的国情、政治和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重要文献;它为考察与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法律的概念、术语、思想和制度传入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路径(王健,2001a:40)。刊物中刊登的不少词语与《地理便童略传》中的相似,但又不尽相同,译词体现出演进与变化的特点。除表3中的文章涉及法律词语,1838年戊戌四月号的《论刑罚书》、五月号的《侄答叔论监内不应过于酷刑》、七月号的《侄答叔书》、八月号《侄奉叔》、九月号《侄复叔》等文章,多触及清朝刑罚残酷的弊端,因此也值得细查。 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发现,在若干早期英文法律术语汉译中,不少英文法律词语在最早翻译成中文时,曾有多个不同的汉语译名。比如President有“总理”“首领主”“统领”等译法。实际上,在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等文献中还被译为“伯理师天德”⑤,在下述《万国公法》中又被译为“伯里玺天德”(何勤华,2003:50),此外还有诸如“民主”(取万民之主的意思)“国主”“酋”“长”“酋长”“大酋”“头目”“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花旗合部)大宪”“头人”“邦长”“总领”“大统领”“皇帝”“国君”“国皇”“伯理玺天德”(熊月之,1999:58-61)及“伯理玺”等译法。再以juror一词为例,它有诸如“有名声的百姓”“副审良民”“批判士”等不同译法。这还不是全部,它实际上还有如“乡绅”“衿耆”“有声望者”“绅董”等译法。(胡兆云,2009:46-50) 三、《滑达尔各国律例》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出于“制夷”的需要,“天朝大吏”林则徐于1839年奉差赴粤查办烟案,期间在广州组织节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deVatell,1714-1767,今译“瓦泰尔”)的国际法著作——《滑达尔各国律例》(TheLawsofNations,orPrinciplesoftheLawofNature,AppliedtotheConductandAffairsofNationsandSovereigns,1758年出版),它是最早翻译到中国来的国际法,比《万国公法》早25年,林则徐因此成为晚清最早的一位翻译赞助人(王宏志,2011:49,51-52)。节译部分的译者是伯驾和袁德辉,总字数不到2000字⑥,有学者认为林则徐请伯驾翻译依据的是滑氏著作的法文版,而袁德辉重译和增译依据的是该书英译本,理由是滑达尔国际法著作原为法文,袁德辉“不谙法文”而伯驾“精通法文”,但王维俭先生认为,“可以确凿无疑地断定不论伯驾还是袁德辉均依据英译本。而且是奇蒂(JosephChitty)的英译本”(王维俭,1985:63)。还需指出的是,美、中两位译者翻译的实际是同一国际法文本中的同一个片段,尽管他们在对源语及目的语的处理和取舍上确有差异,袁德辉增译了一小节。笔者按图索骥,分别查阅了《滑达尔各国律例》(光绪二季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的中译本和奇蒂的英译本(Vattel,1833:38,171-172,291-292)。现将典型的法律词语包括短语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发现,作为已知最早的法律翻译作品,《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使用的译词不少传至了今日,成为今天通用的译法;上述某些英文词语基本上与中文法律词语建立了“词词对应”关系,这其中典型的有“law/法律”“confiscation/充公”“smuggling/走私”“export/出口”及“makelaw/立法”等。这恰如挪威汉学家鲁纳所言,伯驾严格依据当时的汉语以及瓦泰尔著作的原意和语言,创造了一种勉强能为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的“混合式”(hybrid)语言。而袁德辉发现伯驾的语言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在伯驾文本的基础上,将他的译文改造为更接近中文习惯的文本。袁创造了一些表达核心概念的语义上的新词,并使整个观点都简化和中国化了(鲁纳,2000:309)。若以信息为取向的翻译视角来看,或许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本均已接近达到了林则徐组织翻译该法的目的。#p#分页标题#e# 虽然我们尚不能直接证明汉译法律词语在这一时期的传承情况,但种种间接证据指明,上述二位译者在翻译《各国律例》时极有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先生的文章指出,袁德辉曾从北京出发,专程赴广州购买过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1985:67);而据裨治文发表于《中国丛报》的《鸦片贸易危机(续)》(CrisisintheOpiumTraffic)一文,林则徐在虎门接见美国商人经氏(C.W.King)和他时,曾直接提出索要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马礼逊编字典(Morrison’sDictionary)(Bridgman,1839:76)。林索要字典全本之时正值其委托伯驾翻译滑达尔著作之际,由此可判断他们完全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字典。(王健,2001b:110)仔细翻阅马礼逊《华英字典》之《五车韵府》,我们发现“夹带”“漏税”“走私”对应的均是tosmuggle(Morrison,1819:388,768,795),再对照《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两位译者对于smuggling的翻译,发现它们是一致的;一个严肃的译者常会认真查考以前的译本以吸取其中的优势,基于这一朴素的判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译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沿用或传承。另,上述麦都思的字典(第1186页)中将tosmuggle也翻译为了“夹带、漏税、走私、逃抽”,足见部分译词的传承至此并未断裂。就《滑达尔各国律例》所译片断而言,它们“给读者留下的仅仅是有限而艰深的印象”(鲁纳,2009:80);它们对于下述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正如鲁纳所言,伯驾和袁德辉的译文之所以意义不菲不是因为他们对后来的中文国际法语言和逻辑产生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原创性以及他们在国际法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鲁纳,2000:309) 四、《万国公法》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与麦都思、罗存德、伯驾和袁德辉等人简单的、片段式的译介相比,丁韪良主译的惠顿(HenryWheaton)著《万国公法》(1864年)则有系统地创造了一套与国际法上主要英文法律术语相对应的汉语译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译事”。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万国公法》有张剑先生点校本(惠顿,2002)和何勤华先生点校本(惠顿,2003)两种,围绕该书的论文和专著已有不少,比如《<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何勤华,2001)、《<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张用心,2005)、《1864年清廷翻译<万国公法>所据版本问题考异》(王开玺,2005)、《关于丁韪良译介<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吴宝晓,2009)和《“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赖骏楠,2011)等,还有马西尼(1997)、王健(2001)、刘禾(2009)、林学忠(2009)、崔军民(2011)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或文章多从宏观、中观层面分析了《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引进之于近代中国政治、法律、外交及战争等问题的影响。而从微观上,列举全书中典型法律词语汉译的作品,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万国公法》的点校本共计262页,但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截取部分加以考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分析上表,我们发现丁韪良创造了不少法律术语。马西尼的研究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有诸如半主、动物、公法之私条、公使会、过问、离婚、民间大会、民主、判断、权、全权、人之权利、上房、首领、特权、下房、信凭、义务、债欠、掌物之权、植物、自护、总会等(马西尼,1997:188-274)。何勤华教授考证后则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概有下列24个,如万国公法、性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何勤华,2001:142-143)。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统计还有待挖掘,将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分门别类地分析可使研究变得更加深入和有说服力,比如“沿用至今的”与“已被淘汰的”;“归化的”与“异化的”“;逼真的”与“失真的”等等。对此,笔者将另撰文予以论述。丁韪良的翻译显然受到了中国文化不小影响,以致其部分译文出现了“变异”或“失真”。比如他将“alegislativepower/ajudicialpower”(立法权力机关/司法权力机关)一概译为“君”。而这一简单化处理,无疑使当时的读者误以为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有正当化的理由,进而具备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将law和positivelaw一概译为“律法”,则可能会使法的科学分类不易被人们察觉。将citizen译为“庶民”、obligations译为“名分”也属这一范畴。还有一对有趣的例子,丁氏在翻译realproperty与personalproperty这组词语时,将前者译为“植物”后者译为“动物”。后来,可能它与表示animal的“动物”相同,在和制法律新名词的影响下,property不用“物”而用“产”来翻译。所以这种对应关系出现不久就被两个日语汉字词汇“动产”“不动产”所取代(张璐、赵晓耕,2009:81)。词语由于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意义(俞江,2008:6),但由于能指与所指、所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致使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无法固定下来“,植物”与“动物”因而终究未在法律语言中被确立。 有学者认为,同治年间中西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构成了启动《万国公法》翻译工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向中国介绍国际法,能够引导中国自觉地遵守刚签订的条约,从而使条约上的权益现实化,这要比使用武力的强制手段远为高明(赖骏楠,2011:4)。但实际上,这可能并非是丁氏翻译《万国公法》的真正动力。西方在当时也不乏有人将丁韪良看成是制造麻烦的人,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Michel-AlexandreKleczkowski)曾抱怨:“有人想让支那人窥探我们欧洲国际法的秘密,这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会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一译“威廉士”)则担心,把国际法引入中国,会刺激中国人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譬如“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法律依据(刘禾,2009:165)。可见不少外国人对译介国际法到中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担心的。#p#分页标题#e# 不过,令卫三畏等人“稍感安心”的是,中国历史上系统翻译与引进之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的《万国公法》,似乎并没有让中国立刻找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天朝并未将国际法利用为保护国家权益的法律武器;甚至连国际法用语在中国的传播也未产生即刻的影响。倒是我们或许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万国公法》的翻译帮助我们创设了一批近代中文法律词语,它之于现代中文法律词语的形成与传播意义在于,它使得部分重要法律新词不但从英语世界进入到了汉语世界之中(特别是“主权”“权利”等极为重要的法律新词皆通过《万国公法》进入汉语),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还最终成为今日通用的法律词语,而这有助于缓解法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们的现代性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此外,《万国公法》中的这些新词和衍指符号还第一次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知识系统,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虚拟对等关系,并构成起码的可译性。(刘禾,2009:147) 五、结语 《万国公法》的出版只是揭开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的大幕,这一时期之后诸如法国人毕利干、中国人汪凤藻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李提摩太等人的作品以及谢清高著《海录》(1820)及比这一时期更早的《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著,1745-1751年间成书),均在近代法律词语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较大的影响。它们发挥的介质作用理应被深入挖掘,但限于文章旨趣在于考察19世纪中叶时期传教士汉译法律词语的形态,故不展开。 从19世纪上半叶前始至20世纪初期止,近代法律词语汉译的主力一直是以传教士居多的外国人,而国人仅扮演着“配角”的角色。该时期的法律翻译策略与路径亦明显有别于自1902年晚清“变法修律”以降的翻译策略与路径。1902年以降,和制法律新名词大规模传入中国,但在这以前,传教士与部分本土译者始终未放弃自创译名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似乎未成正比,但却无疑已赢得了人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