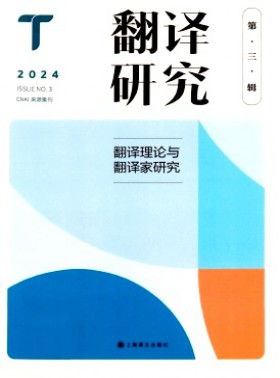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译作西风歌的体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Odetothewestwind”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于1819年创作的不朽诗篇。在这首诗中,雪莱以热烈的革命主义者情怀赞颂了西风横扫旧事物的摧枯拉朽之势,孕育新生命之功。这首诗感情真挚、气势磅礴、格调激昂,表达了诗人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和追求新生活的渴望,被认为是“战斗性的政治诗”。而雪莱也被马克思赞誉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对雪莱极其推崇的文坛巨匠郭沫若,于1922年将其译作《西风歌》介绍到中国,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激荡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此后很多著名翻译家又将其重译,版本多达八、九种,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本文通过分析郭沫若首译的《西风歌》,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内涵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教授于2004年提出的。该理论利用人类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和自然界“求存择优”法则的共通性和关联性,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明确指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连互动的整体”。[1]16,84,102翻译的过程则是译者不断追求自我适应与优化选择的一个循环过程。具体地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因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方面做出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从而产生“整合适应选择程度”最佳的译作。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译作《西风歌》中的体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群情激荡。它鞭挞封建专制思想,传播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塑造了当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于是,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它启迪了民智,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推动了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文学大师像鲁迅、胡适、茅盾等都积极投身于翻译活动,开始大量地介绍和翻译国外的文学作品,创办进步刊物和文学社团,带来了我国译学研究的一个繁荣时期。郭沫若作为一名思想上进、热情洋溢的五四启蒙时代的活动家、翻译家更是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办了“创造社”,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此过程中,英国文学有如春夜喜雨般悄悄浸润着他热血澎湃的心。他热烈地、义无返顾地爱上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他的斗志、才情所折服,翻译了他的一系列作品,并首译了这首抒发壮烈革命主义情怀的《西风歌》。这首诗歌的翻译是郭沫若对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一)翻译《西风歌》是郭沫若对自身需求的适应与选择 胡庚申认为译者在翻译一件作品时,“适应和选择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致力于适应和选择的一个内在动因和目标”[1]。郭沫若从小饱读四书五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有着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功底。但郭沫若童年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制度行将崩溃,资产阶级新文化不断冲击的时代。特别是从1903年开始,各种新学书籍和新式教本不断冲击他的视野。对新学的涉猎,开启了郭沫若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思想之门。年少的郭沫若不但善于钻研书本,而且在中学期间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意识。1914年郭沫若抱着报效祖国的宏伟志愿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在日期间,他学的科目是医学,可他却说自己“走错了路”。面对横七竖八的解剖尸体,他心里流淌的竟是诗的旋律。当的汹涌浪潮吹到日本时,郭沫若心中压抑的文学情愫犹如山洪般爆发。作为一名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翻译家,郭沫若对新的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渴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渴望“生底颤动,灵底喊叫”[3]208。雪莱所创作的“Odetothewestwind”在这时闯进了他的视野。作为一名19世纪的作家,雪莱所处时代的背景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非常的相似。雪莱于1819年写了这首诗。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人民在酝酿着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的革命斗争。面对着欧洲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雪莱为之振奋,为之鼓舞,诗人的心中沸腾着炽热的革命激情。这时,一场暴风骤雨的自然景象,触发了诗人难以抑制的革命激情,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立刻冲出胸膛,一泻千里。它是诗人“骄傲、轻捷而不驯的灵魂”的自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与此相距一百年之后的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国家内忧外患,战事频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需精神上的慰藉与鼓舞。相似的革命环境与革命追求,促发了郭沫若对雪莱的崇拜,对他作品的喜爱。他在《〈雪莱诗选〉小序》中写道“男女结婚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4]334作为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郭沫若找到了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目标,《西风歌》的翻译成为抒发自己愤懑之情,唤起民族斗志的利器。 (二)翻译《西风歌》是郭沫若对自身能力的适应与选择 郭沫若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著的时代背景要有深入的了解。”[5]他和雪莱相似的时代背景,使他能深刻体会《西风歌》中所表达的一种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种打破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西风精神。同时他还强调翻译者应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语言修养,“语文修养是一切翻译工作的基础,尤其是本国语文的修养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6]翻译者如果缺少这一条件,从事诗歌翻译将是举步维艰。还在孩提时代,郭沫若就受母亲的影响,诵读“唐人绝句”,至六岁入家塾读书,开始全面接触中国古代诗歌,背诵《三字经》、《千家诗》和《古文观止》等,同时进行了古典诗词写作方面的训练。到十三岁读乐山高等小学时,郭沫若已能翻检深奥难懂的古典史籍,背诵先秦诸子、《史记》,并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传统的中国文化给郭沫若在诗歌的翻译与创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国学修养是一般的翻译家难以企及的。而在日本留学的十年间,郭沫若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并能够在这些不同的语言中自由穿行,其雄厚的外文功底也使人难以望其项背。在翻译《西风歌》之前,郭沫若已于1921年出版了诗集《女神》,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本自由体诗的诗集,冲破了中国旧体诗僵硬格律的束缚,运用现代白话的方式进行写作,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为诗歌的创造和革新树立了榜样,郭沫若也被认为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在诗歌译介方面,郭沫若在翻译海涅、歌德、拜伦、惠特曼诗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翻译主张—“风韵译”和“以诗译诗”。他的风韵译指的是“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不在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7]211。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既是对前人的超越,又启迪了后来的翻译家,也具体体现在了他的翻译实践中。由此可见,翻译《西风歌》是郭沫若根据自身能力所做出的适应与选择。#p#分页标题#e# (三)翻译《西风歌》是郭沫若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1.对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语言维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形式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西风歌》是一首格律诗,是三行诗节和十四行体的混合。全诗在形式上是由五首十四行诗构成的,即每一诗节都是十四行,其中四个三行诗节,一个双行偶句。每个诗行基本都是五步抑扬格,韵脚为aba,bcb,cdc,ded,ee,句法严谨而又富于变化,较好地抒发了作者慷慨豪放的激情,表现了西风狂烈不羁的气势,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作为“风韵译”的主张者,郭沫若认为理想的翻译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应该在不损害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对原文中字句的先后综析可以自由移易,但一定要保持原文的气韵和情绪。所以他的译文也正体现了他强调文章“气韵”的主张,完全打破了原诗的格式,以恢宏的气势译出了独特的神韵。以原诗第五部分来看:原文:Makemethylyre,evenastheforestis:Whatifmyleavesarefallinglikeitsown!ThetumultofthymightyharmoniesWilltakefrombothadeep,autumnaltone,Sweetthoughinsadness.Bethou,Spiritfierce,Myspirit!Bethoume,impetuousone!DrivemydeadthoughtsovertheuniverseLikewither’dleavestoquickenanewbirth!And,bytheincantationofthisverse,Scatter,asfromanunextinguish’dhearthAshesandsparks,mywordsamongmankind!Bethroughmylipstounawaken’dearthThetrumpetofaprophecy!OhWind,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译文:请把我作为你的瑶琴如像树林般样:我纵使如败叶飘飞也是无妨!你雄浑的和谐的交流会从两者得一深湛的秋声,虽凄切而甘芳。严烈的精灵哟,请你化成我的精灵,请你化成我———你个猛烈者哟!请你把我沉闷的思想如像败叶一般,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请你用我的诗句作为咒文,把我的言辞散布人间,如像从未灭的炉头吹起热灰火烬!请你从我的唇间吹出醒世的警号———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阳春宁尚迢遥?从译文来看,郭沫若抛开了原诗的格律,未采用任何韵脚,而是根据作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和气韵,打乱了原诗的语言顺序,运用文言白话的形式,重新构建出一套符合汉语行文的格律诗,读后仍感“气势奔放,音调雄厚,有如暴风驰骋,神韵不减原作”。[8]189在文中,“deadthoughts”,“incantation”和“thetrumpetofaprophecy”分别译作“沉闷的思想”,“咒文”和“醒世的警号”,既符合了原诗暴风驰骋的音调,又反射出五四时期中国人沉闷的急需激励奋进的精神状态。而“Bethou,Spiritfierce,Myspirit!Bethoume,impetuousme”被译为“严烈的精灵哟,请你化成我的精灵,请你化成我———你个猛烈者哟!”两个“化成”语气迫切,情感真挚,气势恢宏,堪称传神之笔。结尾句中“严冬”和“阳春”的对照,更显文章典雅庄重。 2.对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对原文的曲解,同时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时,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郭沫若翻译《西风歌》时,中国的文学体系正处于由传统诗歌向白话新诗的转型过渡时期,诗歌的翻译也必然受到这种客观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诗歌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自身对本国民族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定有密切的关系。作为白话新诗的鼻祖,郭沫若在翻译此诗时,既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五言”、“七言”格律诗的形式,又没有彻底使用白话,而是以文白夹杂的形式作为目的语语体,以风韵译的翻译思想接近译文读者,在对原语语言进行转化之时,注重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态。在诗的第二节,原文在描绘狂暴西风的精神面貌时说:“LikethebrighthairupliftedfromtheheadofsomefierceMaenad”。“fierceMaenad”本指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女祭司,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对西方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直接翻译并不能产生似原文读者般所理解的文化意象,因而译文中采用了“猛烈的预言者”来消除异域文化的陌生感,以期译文读者会和原文读者一样产生强烈的共鸣。 3.对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其自身的目的与意义。郭沫若认为翻译家在翻译作品之前,若对所译作品作过精深的研究,有正确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创作精神,在译述之时,就会感受到迫不得已的冲动,这样产生的作品才会生出效果,引起读者的兴趣,达到交际目的。郭沫若有感于当时中国大地的黑暗和沉闷,有感于人们精神状态的愤懑与沉沦,满怀激情译就《西风歌》。它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罪恶,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革命主义精神,燃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激情与斗志。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曾经激励着无数爱国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前行。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的“一百多年来,当革命者在旧社会的黑暗深渊里,感到心情沉重,不少人是吟咏着这两句诗又重新抬起头来的”。 三、结语 通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译本《西风歌》的翻译过程进行解读,不难发现作为“风韵译”的首倡者,郭沫若在创作过程中完全贯彻了其翻译思想,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他的个人气质、艺术功力、行文习惯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在翻译过程中反映了出来,直接影响到了其译文的形成。[9]作为拥有深厚国学功底和外语天赋的翻译家,郭沫若在新旧社会和新旧文化过渡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下,从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并维持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形成了“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