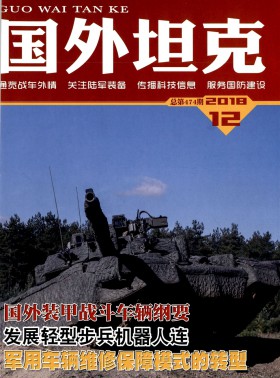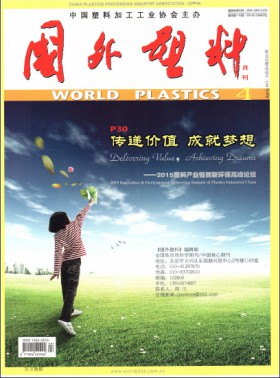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国外对契丹和辽的认识与研究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145年,安条克公国派出的使节于格(Hugh)向罗马教皇讲述了“约翰长老(耶律大石)的事迹”,“当约翰长老的传说远播到西亚和欧洲的时候,十字军正处在极端的劣势之中,一个又一个堡垒陷入穆斯林手中,绝望的思想开始在军中漫延”。而“上帝派来的同盟军‘约翰长老’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苏旦•桑加尔(SultanSanjar)”的消息对十字军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军中士气一时无比振奋。他们把挺进东方寻找契丹,与“约翰长老”会师联盟当成了终极理想。然而东西方之间横亘着的穆斯林势力却阻断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西方第一部关于辽代的通史性著作是《辽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该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译魏复古)和中国学者冯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王朝断代史。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阐释了辽代的社会功能[8]。用人类学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了契丹族的中国化过程,称辽为“征服王朝”。该著作的主体部分论述了辽代的经济史,次要部分解析了辽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才叙述辽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该书借鉴和采用了中国《辽史》中的部分史料,但决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照搬,而是经过大量的实证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该书结合大量的考古发现,收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主题多变,论述范围极广,从畜牧业到帝王陵寝,从辽代官印到长达55页的哈喇契丹的专题性述论,无所不至其极。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辽王朝的历史地位,辽代文化的双重性以及10世纪以来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径。该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认为辽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辽代文化的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再如“高丽”应是写“Koryǔ”,而不是“Korea”,“县”应译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书中关于女真一词,有时用Jurchen,有时用Nu-chin,交叉使用极易误导读者。
法国学者韩伯诗在其《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法国科学院金石文艺院会议报告集》,1953年)中开始尝试着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发表了《谈谈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达佩斯大学学报》语言学分册,1975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福伯是研究辽金史的专家,他的《论辽朝的语言关系》(载《中亚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辽代契丹语的起源、派生关系及流向,同时从契丹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辽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及西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黄振华将其译成中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该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同行的瞩目,德国学者道尔弗将阿尔泰学家对福赫伯的评论写成了一篇综述,即《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的〈论辽朝语言关系〉》,大致介绍了阿尔泰学界对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评析和争议。德国学者门格斯《通古斯与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则是从通古斯语和辽代契丹语的语系联系中寻找通古斯族与契丹的族系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辽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自1954年开始,辽宁法库县叶茂台镇发现了20多座辽代墓葬群。特别是1974年5月发现的7号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帐”,绢轴画“深山棋会”、“郊原野趣”等辽代罕见文物;1976年4月发现的辽代北府宰相萧义16号墓葬,其墓志详细记载了萧义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该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和敛葬用具。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区发掘了耶律阿保机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壁画。特别是1975年,两具保护得极其完好的辽代装饰银鞍在美国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辽代艺术和文化的瞩目。这些文物为世人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壁画及出土文物上丰富的色彩图样、巧夺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学者强烈的探求欲望。#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有关辽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现在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集中对辽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美国学者走在西方辽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发现方面,罗伯特•潘恩的《一个辽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记述了1956年发现于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村的一个辽代早期的王冠(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远东精品艺术博物馆)。洛舍•莱德罗斯(LotharLedderose)在亚洲研究协会1992年的年会发表了《辽代大量生产的佛经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时代趋向尾声也是推动河北房山区云聚寺佛经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建筑的专家。她的《辽代考古:中国北部边疆的坟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北部发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文化。罗伯特•阿尔布莱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辽代墓壁画与辽帝国公主的婚礼仪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门别类地论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发现的四座辽墓中的壁画。作者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入手分析了辽代社会的政治阶层、经济水平、文化娱乐和风俗习惯等多项内容,特别结合大量中方文献重点论述了辽代公主的婚礼仪式和婚姻生活。同时,针对辽墓室的装饰和修建风格揭示了辽代墓葬文化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过程。罗伯特的另一篇文章《辽代墓壁画与中国画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点通过对吉林省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辽墓壁画、河北宣化的辽墓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相册页的比较,论述了以蔡文姬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饰、艺术、建筑及风俗习惯上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美国学者扎奇斯钦(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学的专家。他对辽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猎。其《契丹与他们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论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点、分布等自然情况,指出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有关辽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应该是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内蒙赤峰宝山墓壁画出土后不久,她发表了《辽代建筑传统》(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该文主要论述了身为半游牧部落的处于定居社会边缘的契丹人,一直笃信萨满教,从未有过寺庙中的神,也从未在城市中居住过,在与中国式文明接触以前从未用砖室墓埋葬过先人。然而契丹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改变了。作者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中国文献记载,从建筑、宗教学的角度对山西应县木塔、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等现存的辽代建筑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契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借鉴、转换、采用、适应、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关系。她的另一篇论文《石室:与阿保机在祖州相关的石头建构》(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着重讨论了在耶律阿保机的世居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边境上所发现的一处石头房子。作者先综合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座石室的隶属关系、功能用途、设施构造、方位位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观点,然后结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献论述了契丹与中国石质房屋建筑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推测出该石室的建筑时间、功能和意义。
南希的专著《辽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辽代建筑传统》一文上扩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关辽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辽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平,提及丧葬习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结合前述提出了辽代建筑为何发生变革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点论述了辽代五个都城(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从辽代建筑的木框架传统、辽代丧葬传统和辽代建筑遗存等三部分论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辽代契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有的继承、借鉴、改变与适应等关系。她指出:“辽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过程中,辽代成为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个参与者和保护者。”[10]该著作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讨论了契丹的族源问题,指出契丹建筑文化还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丽和渤海建筑等)中获得了经验。因而契丹建筑师可能源于高句丽或渤海国。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美国学者蒂耶特•库恩(DieterKuhn)针对南希的《辽代建筑》一书发表了长达38页的书评:《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库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开创性、艺术性和丰富性。之后就南希对契丹民族的族源问题、辽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问题、史料运用问题、建筑术语的翻译问题等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书中图片缺乏独创性和清晰度、参考书目有遗漏等缺陷。蒂耶特还发表过有关契丹坟墓外形构造的论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国圆顶形墓的传统》(“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对于库恩的质疑和意见,南希在其《回复蒂耶特•库恩:〈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并对库恩的评析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体现了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学术交流态势。#p#分页标题#e#
有关辽代与北宋关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论。该论文结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国宋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宋朝与辽契丹之间在11世纪的战争、盟约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同时对于双方长期的和平贸易、朝贡外交体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博士学位论文。莫里斯•罗斯比(Morris,Rossabi)《在对手之间的中国:中国与其在10-14世纪之间的邻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统论述了中国与辽、金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该著作揭示了宋朝时期的中国打破了历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国,四夷宾服”以朝贡体制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辽、金视为平等国家对待。虽然源于军事和国力上的羸弱,却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弹性。戴维•瑞特(DavidWright)《从战争到外交对峙: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详细论述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起因、经过、外交谈判及“澶渊之盟”的订立等内容,分析了北宋与辽、契丹之间特殊外交关系的形成与对峙原因。戴维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对峙、世系与和平:宋朝使辽的外交使团》(《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与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亚洲历史学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渊之盟的和平及其对中国与辽契丹帝国关系的影响》(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澶渊之盟上。相关论文还有安东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关于北宋时期外交决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钦《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争》(“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统描述了辽朝末期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数次战争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分析了辽王朝覆灭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综合性著述中涉及到辽和契丹的外交及贸易类的著述主要有费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译为《辽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该著作详细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揭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论述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塞本•达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罗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国及其邻居:边疆、中国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纪的对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关于辽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描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外交政策改变的综合因素,指出军事实力的羸弱和国内政治纷争频发是导致中华帝国外交政策和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扎旗斯钦《和平、战争与长城沿线的贸易:游牧民族与中国两千年的互动》(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外交编年史。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千年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有贸易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一说,指出贸易和战争时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汉斯•别伦斯坦(HansBielenstein)《汉人世界里的外交与贸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关系系统介绍了589年至1276年之间东南亚的交趾、乌孙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高句丽、渤海、西突厥、辽、金、党项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贸易联系。托玛斯•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危险的前线:游牧帝国与中国》(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论述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如何强大起来,建立独立国家并与中国产生边境疆土纷争的史事。
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辽代契丹统治者的婚姻、血缘与继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该文考察了辽代婚姻系统的起源、在辽代每个王者身上的实施情况以及其与辽代血缘和继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辽代的姻亲系统对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中国非汉族政权的政治组织:魏、辽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该文概述了宋元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政权组织及其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非汉政权的更迭与各方军事实力的消长等。琳达•库克•约翰逊(LindaCookeJohnson)《论契丹的文字体系》(美国《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论述了契丹的文字体系。#p#分页标题#e#
赫伯特在《满洲的森林人:契丹与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契丹、女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再从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间的领土、利益纷争及其承接关系。简奈特•麦克莱肯•诺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关于契丹当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遗作《武溪集》,论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谏,致力于宋辽和平的史事及其意义。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西方关于契丹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论述了契丹名称的起源、契丹历史的演变及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
契丹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民族,其后裔的流向至今仍是一个待解的谜团。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中外学者对契丹和辽史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这也令辽和契丹史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史学的繁荣和进步需要不同的声音,海外学者对辽及契丹的研究必然会对中国史学界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赵欣 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