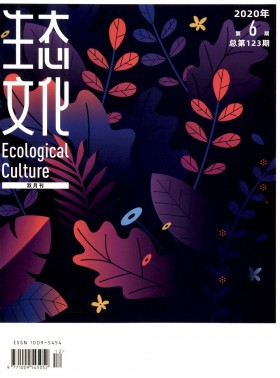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其发展运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生态博物馆理论 1.1生态博物馆的起源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起源,研究界有比较统一的认识,都认为生态博物馆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欧洲逐渐兴起。1971年,在总结有关保护理论的基础上,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他们在向法国环境部介绍博物馆发展新方向时首次提出此概念,表达了人、文化、自然环境必须紧密结合的新思维。他们认为博物馆应改变传统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ofmuseums)的概念。所以生态博物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回归自然呼声的高涨而出现的。到二十世纪末,生态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保存的特殊形式,目前全球共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1][2][3] 1.2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国际博物馆协会前领导人、生态博物馆运动和生态博物馆学的倡导者之一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HenriRiviere)先生在“一个进化的定义中”有这样的描述:“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构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是一面镜子”,“是一个资源保护中心”,“是一个实验室”,“是一所学校”,“是人与自然的表现”,“是时间的一种表现”,“是对特殊空间的一种解释”[3][4]。但这只能是一种界定,研究者们并不满意这样的描述[5]。国际博协认为这个描述背离了它原始的“生态”意义,因此推荐了自己制定的定义:“生态博物馆是这样一个机构,通过科学的、教育的或者一般来说的教育的方式,来管理、研究和开发一个特定社区的包括整个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整个传统。[5]”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5][6]” 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是对旧的传统博物馆理念的发展,但是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不成熟,仍在不断地发展当中[7]。 各国在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时,都与自己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对生态博物馆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再理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如在我国,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第一人苏东海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保护、原地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地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新方法[6]”。 1.3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 1.3.1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 生态博物馆理论是从博物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二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的博物馆是将文物在传统的博物馆建筑内进行展示,缺少了生命力;而生态博物馆则不同,它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文化在它的原生地予以实时实地展示,让来到博物馆的人能真正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遗产[2]。 另外杨俪俪在“生态博物馆——经济与文化的思考”一文中认为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的博物馆是一处静态的独立建筑或者建筑群,藏品脱离了其原生环境,其文化内涵、价值也随之脱离了大众,生态博物馆则是将整个特定的社区当作整体的博物馆,社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原状的动态的保护在其原生环境之中,这里的文化是鲜活的,不再是孤立的。(2)传统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普通的观众、公众,是一个提供教育、娱乐、增长知识的场所。生态博物馆首要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提高社区居民的创造能力,掌握自己未来发展方向。其第二服务对象是来社区参观的访问者,给他们提供一个体验异质文化的动态情感过程。(3)传统博物馆的藏品多指具有文物价值的经过历史沉淀的具体实物遗存。生态博物馆更注重社区中的一切资源,包括文化的,也包括自然的。这里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具体的有文物价值的实物遗存,传统的风俗等非物质文化更为重要。[4][8]上述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研究人员对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区别的认识,具有普遍性。 1.3.2生态博物馆的特征 国际博协瑞典国家委员会主席科吉尔•恩格斯托姆(KjellEng-strom)对生态博物馆的特征作了如下说明:(1)多科学性。与传统博物馆按一个学科划分博物馆不同;(2)地区性。不是指行政区域,而是由文化传统、自然传统和经济生活的融和体;(3)开阔性。不局限于建筑;(4)协调性。和当地居民协调起来,反映他们开拓记载和介绍自己历史的愿望。[5]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特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研究人员有自己的理解。如董广全、翟启帆在“试析生态博物馆概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生态博物馆应有如下几个特征:(1)生态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原生性;(2)生态博物馆是对传统博物馆的一种扬弃;(3)生态博物馆的展品就是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2]。杜倩萍的“略论西部大开发中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9]、刘旭玲等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地开发中的应用”[10]、彭家威的“生态博物馆及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研究”都提到相似的观点[11]。综上所述,在研究生态博物馆理论时,我国的研究人员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生态博物馆这一新兴事物的特征予以概括,指出我国生态博物馆应具有的时代特点。#p#分页标题#e# 笔者认为,生态博物馆最大的特征在于:生态博物馆将一个社区当作一个大的“活体博物馆”,展示的内容既有建筑等物质文化遗存,又有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等非物质遗存,还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将鲜活的文化保存在原产生环境中,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生态博物馆强调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生态博物馆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强调人的生存利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谐统一。 2.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应用 2.1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兴起与建设 生态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当代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开始兴起的。1986年,《中国博物馆》杂志发表南开大学研究生胡妍妍的《博物馆与环境科学》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甄朔南的《环境主义与博物馆》。也是从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杂志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一批与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之后,这一新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5]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把国际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引入实践,并使之中国本土化[12]。1995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苏东海先生的倡议和推动下,贵州省文化厅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开始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作为“中挪1995~1997年文化交流项目”,课题组参照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创新理论,在全面考察贵州省苗、侗、布依等十余个民族村寨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地,并完成了《在贵州省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3]。1997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设计划。在挪威政府无偿提供部分资金的情况下,梭嘎生态博物馆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1][14]。这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我国又陆续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生态博物馆等[2]。迄今为止我国已先后在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建成苗、布依、汉、侗、壮、瑶、蒙古族等生态博物馆[11]。 由上可见,生态博物馆理念进入中国不过20多年的时间,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成距今也不过12年时间,而且目前生态博物馆理念主要应用在民族旅游的开发建设方面。生态博物馆还是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新鲜事物,它在与中国文明融合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2.2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融合与发展 生态博物馆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变化[15]。其理念在与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结合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发展形式。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中国化”色彩,这是由中国的国情、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广泛根植在欠发展的广阔农村的实际所决定的[16]。 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中,第一个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并在贵州进行实践的苏东海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四维保护”模式。第一维是整体保护,即将村寨里的自然遗产、人文遗产、有形的遗产、无形的遗产以及环境作为一体来保护。第二维是村民自己保护,就是把保护变为村民自觉自愿的行动。第三维是原地保护,即在文物的原生地保护,使村民在村寨里按照传统的习俗生活。第四维是动态保护,这种做法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17]。在这个理念中,苏东海先生特别强调,村民的生活毕竟还是要向前发展,不断与外界融合,逐步走向现代化,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放弃自己的一些习俗或吸收一些新的文化,生态博物馆不可能冻结村民的生活。另外,关于梭嘎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和经验,苏东海先生在2000年8月5日中挪国际培训班第一阶段总结中指出:“在这个贫穷的民族村寨中我们创建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做法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保护遗产、发扬文化。[5]”可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这与欧洲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已经有了一些出入。当年在建设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时,挪威专家杰斯特龙甚至反对在长角苗地区进行文化教育,因为他担心现代知识会污染长角苗的传统文化;并且他还认为生态博物馆开展旅游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传播社区文化,而不是创收,因此他要求在生态博物馆社区内的居民不能向游客兜售旅游商品,也不能像一般的博物馆那样收取游客和观众的门票。可见“保护传统、传播文化”在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被视为其追求的根本目标[18]。但仅将保护与传播文化作为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唯一目标,在目前中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落实起来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在与中方有关人员讨论后,杰斯特龙也作了适当的妥协和让步。这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保护[4]。西方生态博物馆所在的社区居民的生存不是问题,探索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谋求物质和精神文明及生态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发展,才是他们关注的问题[19]。而在中国,许多民族地区的生存条件、经济、教育、社会发展的程度非常落后,所以在中国的生态博物馆里,保护、传承文化的同时,更需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19]。 因此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该区域特有的文化,使其文化持续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生活上对社区居民有所改善[19]。作为一种舶来的理念,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建设不应忽视中国国情。相似的观点还出现在杨俪俪的“生态博物馆——经济与文化的思考”[4]、黄萍,游建西的“求变与保护:中国首座民族博物馆的处境与对策”[20]、刘艳的“生态博物馆发展创新初探——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21]、苏东海的“建立与巩固: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思考”[22]及“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23]中。#p#分页标题#e# 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使得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开发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潘年英在“变形的‘文本’——梭嘎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24]一文中对这一问题阐述得较为深刻。他认为,保护与开发是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矛盾。这是因为“生态博物馆”这一理念的核心目的仍是保护传统的文化艺术,但是在中国,所有的“保护”行为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自发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愿,整个保护过程都是被强加的,是他们被动接受的,“保护”只是外部要求,而“开发”才是当地居民更强烈的现实意愿,这就构成了矛盾。另外,他还认为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的急迫追求与民族文化自觉能力不足的矛盾构成了所有矛盾的基础和核心;当地人长期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文化反思和自觉的能力。而外来的“替代性反思”毕竟难以取代本土的反思,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25]。在他两次对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考察后,他认为那里的生态博物馆已经变形,背离了当初的设计方向,演变成了一座在中国最常见的普遍存在的民俗旅游村。 对此,苏东海先生认为,就全世界已建成的300多座生态博物馆来看,虽然大多数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但也都存在着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矛盾,完全没有矛盾的文化保护模式是不存在的[26]。但对这些矛盾完全视而不见,那也是危险的。对此,雨果•戴瓦兰(HuguesdeVa-rine)的“生态博物馆和可持续发展”[27]、埃里克•巴博•罗如杜(DrEricBabarZerrudo)的“地方感觉、力量感觉和特性感觉”[28]、WiburSchramm的“人类传播史”都有相似观点[29]。 3.结语 综上所述,发源于西方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以“保护”为核心理念,同时兼顾“发展”的需要,是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新模式。它为我国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对接,并且这种对接在实践过程中要复杂的多[20],理性的思考、深入地研究,提出我们自己的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模式则尤显重要。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如何使之中国化。探索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亦或说寻求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之路,应首先去了解生态博物馆诞生的土壤和环境,唯此才能科学地移植和改良,使之健康地成长发展[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