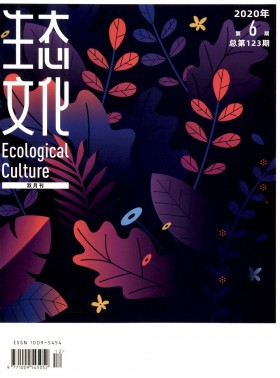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审美民族性的本质与特征,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人具有自然属性,与自然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获得了各个学科的重视,生态审美即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美学范畴。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它打破了以往所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的审美范畴及伦理范畴,是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真正实现了真善美的共生统一。它所面对的是整个生物圈,是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关系的集合体,即生态审美是一种关系范畴,它的审美对象是由各种存在物所组成的关系,这种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在共同的协作中达成整个系统的运转、再生和协调发展。它的审美旨趣是人类对生存状态的一种终极向往,它试图超越人类自身的狭隘,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理想化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审美境界。生态审美所指向的是现代生态危机下人类面临的“共同焦虑”,它的价值观与审美旨趣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但是,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族群下,生态审美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美学中的具体化与差异化问题:“作为一个积淀着深刻的人文性、精神性、体验性内涵的概念,生态美学总是跟特定具体的时代、地域、民族、文化中的人相联系,总是一个具体的、此在的概念。”① 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所产生的生态审美,它必然要涉及“人”以及“人”所浸润其中的文化、民族的差异性,关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生态关系以及审美认知,必然是一个充满了相对性和差异性的概念。生态审美差异性问题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生态审美的本质。一方面,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和传播,需要汲取不同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理念;另一方面,生态危机也正是由文化的单一性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构建人类整体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永葆人类精神世界生机与活力的必然要求。 一 生态审美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生态审美的民族性特质。生态审美的主体是人,人具有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是所处的那个文化系统的小小产物,受到不同的地域环境、历史、习俗、观念的影响。生态人类学将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归之为不同的“民族生境”,“民族生境”是指“一个民族能动地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某些特有部分建立密切的关系”。在其结合部,“相关的民族文化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发生了密集的物质和能量交换”②。生态审美的民族性是在生态审美的普遍价值框架之下所呈现出的不同民族生境、民族文化的审美特性,包括将特定区域的自然景观、风俗、风物、风情纳入生态主义的视域中,从世界性的整体意识出发,呈现一种特殊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之美和生态整体观照。不同的地域存在着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引力———随你怎样叫它都行。”①从不同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特征以及民族生境的呈现对丰富生态审美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生态审美的区域化特征,在某种层面上与审美场理论是相一致的。封孝伦博士认为,审美场是“全社会相同相似的情感体验形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情绪、情感氛围。”②袁鼎生更进一步指出:“审美场是由审美活动、审美氛围、审美风范有机构成的结构。”③在此基础上,袁鼎生对民族生态审美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批评、审美研究、审美创作活动中形成的审美境界、氛围称之为民族审美场。民族审美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系统发展形态。民族审美场由微观、中观、宏观走向统观化时生成了民族生态审美场,民族生态审美场是民族审美场的最高层次,是与相应的审美氛围、审美风范对生并不断走向整生的民族生态审美活动圈。④生态审美的民族性与民族生境、民族生态审美场密切相关,这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生存而建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态。欧洲游牧先民与动物界建立的关系,形成了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审美场;古希腊城邦生活与海洋建立的关系,形成了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民族审美场;中国农耕先民与土地植物建立的关系,形成了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民族生审美场。虽然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都生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美。但无论从文化保存的多样性上,还是在民族生态审美的特殊性上,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下的多民族生态审美场更具典型性。在中国农耕文化的民族审美场中,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生态审美场的根基。在中国这个大的民族生态审美场中,生态审美的民族性的实质即是在“区域特色”或者说“地方色彩”中表现出不同形态的生态美。 二 生态审美的民族性首先体现为不同民族区域环境中的自然生态美。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在人类和自然所构成的生物圈中,人类是依附于自然而生存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类、土壤、水、植物、动物都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并且每种生物都是平等地在阳光下占据一个位置。“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已由对历史的生态学认识所证实。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⑤这种生物圈既是人类的宇宙空间,也是不同族群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因而,生态审美的民族性首先体现的就是不同生境之下人们对他所属的那片土地的审美情感,对自然生境的感悟与体验。这种感悟与体验并非是简单地对自然生境的概念认知,对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土地的依赖,而是人与自然生境以及自然资源之间相互依生所产生的相生相依相宜的和谐美。审美主体对土地和生境的热爱是生态审美民族性的一种重要的特征。相对于现代生态主义精英文化的自觉审美追求,民间生活世界的自然生态美以多姿多彩的面貌自在地存在于民间、大地上。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正在日益疏离,而在农耕文化中或者人类童年时代,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非常强,人类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原生态的自然生态美在那些发展相对比较晚近的民族地区,或者不同民族古老的生活习俗和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中更为常见。如以居住习俗为例,在很多民族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不同自然生境之下对自然的利用和适应,这种合理的利用与适应在现代生态审美关照中,恰恰是人类与自然亲密关系的完美呈现。在原始时代,南方民族曾经多以穴居形式居处,以天然的山洞或者树洞为屋,在傣族的古歌中,可以看到南方民族的先民们与自然环境相生相依的和谐之美:“山洞在野外/山洞在森林/野外有大蛇/林中有虎豹/孩子们,快进去/老人们,快进去/我要关门了/我要堵洞了/搬来干树枝/拉来绿树叶/抬来大石头/堆在洞门口/挡风又防冷/野兽进不来/我们才安全/关门了,关门了/秋、秋、秋”(《傣族古歌谣•关门歌》)。①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方式无不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相生相依,同样,北方民族的“撮罗子”也是不同地域生境的反映,是人类对自然生境的主动适应。对远古先民来说,顺应自然、就地取材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宜使用,当然,这种对自然的认知与依赖固然体现的是人类较为初级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其中所蕴涵的生态合宜之美,符合现代审美的旨趣与价值。只有对自然规律和自然资源本身有着深刻的认知,才有可能合理利用自然,与自然确立平等共生的关系。在满族民俗中有大量习俗反映了满族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利用,体现了在宇宙生物圈中人类与自然共处的生存智慧。如“关东三宝”之一“乌拉草”就是在高寒的民族生境下满族先民的文化发现:“乌拉草,蓬勃丛生,高二三尺,有筋有节,异常绵软,凡穿乌拉者,将草锤熟垫籍其内,冬夏温良得当。其功用与柳絮同,土人珍重之,辽东一带率产此草,出自白山左近尤佳。”②乌拉草,又名靰鞡草,穿乌拉草做成的棉“靰鞡”或者在鞋中絮上乌拉草,是满族民众在高寒的生活环境下对自然生境的积极适应方式,这种对自然的认知是满族先民的文化创造。在满族的民间也有很多关于乌拉草和靰鞡鞋的传说,表现了满族对这一文化发现的愉悦之情。后来,人们开始用猪、牛、马皮缝制乌拉。在居住、饮食、医药等方面,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智慧,生动地再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相生相依相宜的关系。在各个民族中传承的生态智慧以及对自然的生态认知,为生态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为区域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是现代生态文化的重要构成。在不同民族生态智慧和生态认知中,也呈现出了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自然生态之美。#p#分页标题#e# 三 生态审美的民族性也体现在不同地域的生态文化上,包括自然观、价值观、生产方式以及风俗文化等。生态审美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是现代生态环境危机下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重新审视和关照,也是对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生态思想资源的总结与提升。它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生成的,也是在现代性的社会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膨胀后的反思。如果说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面对的是人与自然相疏离的焦虑,那么,人类与自然之间产生最亲密的联系是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这里的童年不仅指个体的童年,也指人类整体的童年—原始时期。个体的童年与人类的童年都是在一种最接近自然的状态下度过的。个体的童年生活环境尽管千差万别,但是对自然世界的好奇与亲近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在个体走向成熟之后,人便逐渐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在人类迈向工业文明之后,这种童年思维和原始思维也逐渐丧失,人类与自然的纽带被切断。城市生活、工业文明切断了人类与自然的亲密联系,消解了童年的诗情,并实现了自然的祛魅。现代生态审美目的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生命最初的活力与诗意。人类童年的原始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野性世界,也为我们保留了人类与自然亲密关系的历史记忆,既有不断增长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今天,这些记忆可能只能在一些古老的习俗、仪式和信仰以及民间口头记忆中得以复现。原始的自然崇拜和民间信仰虽然是在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其中对自然的敬畏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体现了原始的生态审美趋向。如今,这些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民间信仰依然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民俗文化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文化的遗存和在当代的变异。民族文化中对自然的敬畏与人类的中心主义观截然不同,在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人类将自然、动物以及一草一木都赋予了生命,将它们视为平等的生命的存在,尤其在原始时代,“我们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所划的严格的分界线,对于原始的野蛮人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许多动物跟他们是同等的,甚至比他们优胜,不仅在勇气方面,而且在智力方面都为优胜。”③在原始的自然崇拜以及宗教中,一些与民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物被奉为神祇,昭示了原始信仰所生成的生态背景以及对待自然物的特殊情感。如满族萨满教中对鹿、虎、狼、鹰、乌鸦等动物的崇拜,还有民间各种禁忌,如满族、锡伯族不食狗肉的习俗等,都体现了特定区域环境中民众的自然观。各民族文化中保存下来的这些古老的信仰和习俗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然生物的敬畏,这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原始情感正是现代生态主义所试图重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原始的、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美也构成了生态审美民族性的重要内容。 四 生态审美的民族性特征还包括不同区域的生态人格美,也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出的人性之大美,这是一种和谐之美,是促进整个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最高人格的体现。因为人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最具有能动性的存在物,生态人格美是生态审美民族性中最具个性的因素,是不同民族审美场中民族精神和心理的外在表现。舍勒曾说过,“最深切地植根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同时,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人,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他达到了辉煌的理念世界的最高点,这样的人正接近全人的理念,并且,世界本源的实体理念就通过这样一种经常增长着的精神和内驱力的相互渗透而成为现实。‘有着最深刻思想的人,爱恋着最有活力的事情。’(荷尔德林)”①自然就是最有活力的世界,融入生机勃发的自然界,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全人”。在生态审美的民族场域中,生态人格美更多地体现为人性的生态本原之美,也即是生成现代生态人格美的基础。民族生境的自然生态和自然观为现代生态人格美的形成提供了富有生命力的民间土壤,随着生态自觉意识的增强,现代生态人格美也将成为展现民族精神和心理的重要方面。在民族生态场域中,民众真正融入自然之中,与自然共生依存,这些民族身上的人性之美更能体现人类的生态本原性。在一些文化发展比较晚熟的民族中,民族的生态本性之美保存得相对要多一些。比如东北区域中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先民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其性格和体魄形成了一些共性特征,即精神上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勇敢而坚定,情感炽烈真挚,在体格上往往强壮魁梧,这种充满强力和野性的人性之美也广泛地存在于一些原生态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民族中,是尚未被现代文明所异化的人性之美。当然,民族生态审美视域中的人格美还要和现代生态价值观相契合,即在物质欲求与精神需要、感性冲动与理性秩序、现实主义与理想追求、本我与超我、功利与审美的两级趋向之间达到符合人类本性并有利于人性生成的和谐,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舍勒所说的“全人”。②作为人性自由的最高状态,生态人格美在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平衡中,还要具有自觉的生态实践、生活方式上的生态化自律。生态审美的民族性趋向中,生态人格美是建立在民族自然生态美与特定区域的自然观、习俗和精神信仰之上的,是不同的生态文化所模塑的族群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它不仅存在于生活中的民众身上,同时也普遍地存在于民族文学和民族艺术之中。近些年以乌热尔图等为代表创作的一些民族题材的生态文学作品日渐增多,他们不仅关注生态环境,更关注民族生境之下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境况。 生态审美民族性问题的探讨是生态美学和生态主义价值体系走向深入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生态审美的单一性和同一性标准所造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危机,生态审美的民族性既丰富了生态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提高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认知。同时,生态审美民族性的提出,为我们审视和发掘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民间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使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民间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当然,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