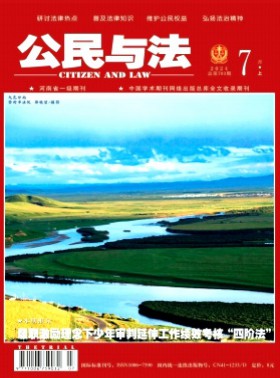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公民哲学教育思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程广云 夏年喜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城市(城邦),并不是简单地从家庭和村坊的发展中自然出现的,而是希腊古代社会各种因素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表现。顾准曾分析过从远古希腊的神授王权,经过海外殖民城市、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到公元前8—前6世纪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以及公元前5—前4世纪城邦制度从极盛到衰亡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2]7,[3]6。由此,亚里士多德将城邦定义为:“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3]3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生活归结于人的政治本性:“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2]7,[3]6
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就作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4]19,[5]13亚里士多德所谓人类的政治本性以及城邦的政治属性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所谓政治,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组成社会的、与经济文化相并列的领域,就其实质而言,政治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公共领域。家庭生活属于私人领域,城邦生活属于公共领域,亦即政治领域。阿伦特说过,希腊人只有政治的概念,没有社会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只会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不会将人理解为“社会的动物”[6]。这是因为希腊人对人性的理解不像后来人对人性的理解那样将人理解为理性人或经济人。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就形成了所谓社会关系。反之,希腊人将公共领域(城邦)和私人领域(家庭)划分开来,认为政治是人类公共生活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规定中,他特别强调城邦的多样性,反对柏拉图的单一论或划一化。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使以‘单一’为归趋,即它将先成为一个家庭,继而成为一个个人;就单一论,则显然家庭胜于城邦,个人又胜于家庭。这样的划一化既然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那么,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求其实现。”[2]45,[3]32城邦生活的本质就是它的多样性。反过来说,没有多样性的生活,也就没有城邦(例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代城市,由于缺乏生活的多样性,不能称为城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公有制主张,认为公有等于一无所有。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共产、公妻和公子,其实增大了分母,降低了分值。例如,一个孩子归一对父母所有,他能获得百分之百的父爱和母爱,倘若归一百对父母所有,他所得到的父爱和母爱并不因此增加一百倍,相反,每一对父母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一的父母,趋近于零,谁也不会真正关心这个孩子。所谓财产公有、妇女公有,也是这个道理。
亚里士多德由此提出了“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我们应当理解,归根结底,亚里士多德不仅仅是捍卫财产的私有、反对公有,而是捍卫城邦生活的多样性、反对单一性。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建立在公民定义的基础之上。他明确指出:“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公民的一般意义原来是指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至于就他的特别意义说,则公民在个别的政体中就各有不同;在一个理想政体中,他们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2]114,157,[3]74,102这就是“轮番为治”的含义。公民不是臣民,臣民只有政治义务,没有政治权力,公民既有政治义务,更有政治权力。因此,只有在法治中才有公民,在人治中只有臣民,依照这一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代社会因为实行人治,所以只有臣民、没有公民,因而只有单一性生活的城市、没有多样性生活的城邦。
关于城邦与公民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2]116-117,[3]75,84这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城邦,没有公民团体就没有城邦制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兼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重身份,这里涉及统治权问题。柏拉图未必理解这一点。他习惯于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别开来,将统治权专门赋予统治者。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统治。在《法治篇》中,柏拉图是这样讨论统治权的:“在一个共同体中,必定要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中合法性的统治权可分为七种:一是“父母有资格统治他们的后代”;二是“出生高贵的有资格统治出生卑贱的”;三是“年长的有权统治,年轻的要服从”;四是“奴隶要服从,而他们的主人要统治他们”;五是“强者统治,弱者服从”;六是“愚蠢的人追随和接受聪明人的领导和统治”;第七种统治是“依据上苍和命运的青睐”,由抽签来决定[7]445-446。柏拉图显然是赞成第六种合法性统治权的,这就是他在《理想国》中论述的哲学王的思想。同时,柏拉图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将“‘最优者的统治权’让位给了一种邪恶的‘听众的统治权’”[7]458。
显然,与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具有人治倾向。但这种人治只有符合理性才算合法。柏拉图认为,理性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的统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主张神的统治,反对人的统治。“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来统治,那么其成员就不可能摆脱邪恶和不幸。”“‘神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胜过他们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既然神的统治是理性统治,也就是法治,那么“最高职位”只能交给“绝对服从已有法律的人”,“次一等的职位则通过竞选产生,其他职位也同样通过有序的选拔来确定。”[7]472,476,475这样,柏拉图晚年弱化了人治思想,强化了法治思想。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晚期的法治思想。此外,柏拉图晚年把公民与党派分子对立起来,党派分子是为个人与集团谋利益的,而公民则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服从城邦法律。柏拉图晚期的公民思想也为亚里士多德所发展。至于公民教育与城邦政治的关系,乃至哲学教育与城邦政治的关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作了论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专门探讨了理想国护卫者的教育。柏拉图企图通过环境的严酷考验,选拔理想国的护卫者。由护卫者的教育进而到哲学王的教育,柏拉图是在提出三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即“三个浪头”)中提出的。所谓“三个浪头”,一是女子教育问题,主张男女可以做同样的工作,受同样的教育;二是妇女、儿童公有;第三个浪头就是哲学王,哲学家做王,或者王做哲学家。因此,“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8]257,[9]498。#p#分页标题#e#
这样,柏拉图就将理想的国家与哲学王联系起来。所谓理想的国家,就是通过理性进行统治。柏拉图通过对无知、知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意见的区分,把哲学家和普通人区别开来,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普通人不能称为爱智者,仅仅是爱意见者。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除集中探讨他的理想的政治制度(王治)外,还探讨了四种现实的政治制度:斯巴达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在《法治篇》中,晚年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寡头制、独裁制“这些制度实际上是‘非政制’。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制,它们的恰当名称是‘党派的支配地位’。”[7]591柏拉图认为,“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8]314,[9]547这里就探讨了城邦的政治制度与城邦公民的习惯的关系。毫无疑问,公民的习惯是由城邦的环境和教育决定的,这里就包含了城邦政治与公民教育的关系,不过这种教育绝大部分只是隐性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不是显性的(例如学校教育)。柏拉图认为五种城邦政制对应五种个人心灵: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应的是善者和正义者;与斯巴达、克里特政制相应的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与寡头政制相应的是寡头分子;与民主政制相应的是民主分子;与僭主政制相应的是僭主。柏拉图分析的逻辑是:一种政制形成一种精神,斯巴达、克里特政制的精神是爱荣誉,寡头政制的精神是爱钱财,民主政制的精神是爱自由,僭主政制崇尚专制和恐怖。政制的不同精神养成公民的不同习性,随着各种政制和精神逐步走向极端、走向反面,公民的习性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摧毁旧的政制,建立新的政制,各种政制的变革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但物极必反。
亚里士多德只讨论现实的政体。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资产制或共和制,三者由最好到最不好排序;每种政体都有一种变体: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由最坏到最不坏排序。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三种统治:主人对奴仆的统治、家长对家属的统治、城邦宪政统治。在探讨城邦宪政统治时,亚里士多德将各种政体划分为两类:正当或正宗的政体、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正宗政体有三类: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共和政体。而变态政体也有三类: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柏拉图只是划分了一种理想政体和四种现实政体,亚里士多德没有确立理想政体,但却对现实政体进行了批判,将其区分为正宗和变态两种政体。虽然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论述哲学教育和城邦政治的关系,但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划分中,明确“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变态政体就是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主奴关系,或者君臣关系;正宗政体就是城邦公民政治,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公民才能建立城邦,只有公民教育才能确立城邦政治。
总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讨论了城邦政治与公民教育、哲学教育的关系。柏拉图通过哲学王与理想国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哲学教育与城邦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通过公民与城邦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公民教育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尤其公民教育与城邦政治的循环,说明它们之间互为前提。古典时代,公民教育以城邦政治为前提,而哲学教育则以贵族文化为前提。在希腊,尤其在雅典,哲学是贵族的生活方式。尼采认为“希腊人是典型的哲学民族”。他说:“希腊人……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何时需要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像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10]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讲了一个故事,把人分成黄金等级的统治者、白银等级的辅助者(军人)、铜铁等级的劳动者(农民以及其他技工)。柏拉图不完全坚持血统论,但却完全坚持等级制度,号称“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8]128-129,[9]387。
为了论证他的等级制度,柏拉图提出人的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同样,国家由三等人———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组成。柏拉图认为,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对应于三等人,欲望对应于生意人,激情对应于辅助者,理性对应于谋划者。显然,柏拉图的等级制度确立了黄金等级的至高无上地位,这反映了希腊奴隶主贵族等级的社会地位。在《法治篇》中,柏拉图又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按照公民的财产数量决定他们属于哪个等级,在他们由穷变富或由富变穷时改变他们的等级,让每个人隶属于恰当的等级”[7]503。应当注意的是,柏拉图确认了黄金等级是由理性主导的人构成的群体。只有理性人(不是经济人,而是政治人)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和谋划者。理性确立了统治权的合法性。而理性则是贵族精神的首要特征。顺便指出,古性是逻各斯的同义语,主要表现为政治理性、公共理性;现性是现代性的同义语,主要表现为经济理性、私人理性,当今出现了由现性向古性的回归,如交往理性等。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探讨了家庭,认为家庭包括三个要素: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他们之间构成主奴关系、配偶关系、亲嗣关系。他研究了家庭的致富技术。亚里士多德对财产的研究,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特征。他把奴隶当做“有生命的财产”、“有生命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务管理技术包括管理奴隶的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运用夫权的技术。
他将家庭的主从关系移用于对灵魂的研究。在家庭关系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关系,每一种关系都区分了统治者和从属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主导与服从关系。应当注意的是,正像柏拉图认为理性是黄金等级(统治者和谋划者)的品德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是统治者的品德,两人在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接着,亚里士多德又论述了城邦公民的阶级划分,认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2]208,[3]140-141。亚里士多德主张中产阶级的统治,这与他主张中庸的生活方式相应。无论中庸伦理还是中庸政治,其实质是理性的伦理与政治。我们发现,在希腊,尤其在其城邦雅典,所谓贵族文化或贵族精神,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首要的是理性或理智。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理解。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部分:欲望(爱钱或爱利)、激情(爱胜或爱敬)、理性(爱学或爱智),相应地,人的基本类型有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对应着也有三种快乐。柏拉图将哲学家或爱智者的爱学或爱智的人性(理性)当做最好的人性,并且能够得到最真的快乐。这样,柏拉图就将理性、德性和幸福联系在一起了。在讨论政治制度时,柏拉图比较了五种个人和国家的美德和幸福,他认为“在美德和幸福方面,不同类型的个人间的对比关系就像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对比关系”[8]360,[9]588。其中,王者最正义,也最幸福;依次为贪图名誉者、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僭主。僭主最不幸,也最恶劣。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无逻各斯的部分和有逻各斯的部分。#p#分页标题#e#
无逻各斯的部分包括植物性的部分(不分有逻各斯)和欲望的部分(在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有逻各斯的部分包括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的部分和在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的部分。人的灵魂的逻各斯部分就是理性,有实践理性和玄想理性之别。理性就是德性,德性有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之别。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就是善,善就是幸福,幸福在于善行。由理性—德性原则,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落实到中庸(适度)原则。亚里士多德中庸(适度)原则的思想渊源是“万勿过度”,这是德尔斐神庙的门匾上用希腊文刻写的一句话。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区分了四种主要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在《法治篇》中区分了四种好生活(节制、智慧、勇敢、健康)和四种坏生活(愚蠢、胆怯、放荡、有病)。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和德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庸(适度)。什么是中庸(适度)呢?“第一,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4]55,[5]41亚里士多德将中庸(适度)原则与人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他指出:“(一)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而(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2]208,[3]140。由中庸(适度)伦理,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过渡到中产阶级政治。他说:“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2]209,[3]141-142中庸(适度)原则是贵族生活的伦理—政治原则。
除了理性—德性的精神风貌、中庸(适度)的生活准则之外,具有闲暇、并且懂得充分运用闲暇是希腊雅典贵族生活的基本特征。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黑格尔对希腊雅典贵族生活有精彩的描述:“他们最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大部分工作……在那时则是由奴隶作的,工作被认为对于自由人是不光荣的。”[11]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贵族闲暇生活、建立在城邦制度基础上的贵族社交生活,这就是当时希腊雅典令人向往的地方。一帮精神贵族,在“无所事事”、“闲逛”、“游荡”、“聊天”中度过了无数优游的岁月。他们有教养,有风度,只有在这样一个国情、时代背景下,哲学对话才能进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和印度,还是近代欧洲、现代西方,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充分地复制和翻版这一生活方式。当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指责当时希腊人奴役奴隶和在社交生活中拒斥妇女的社会制度,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剥削、压迫制度下,一个小民族对于人类作出了许多大民族不及的贡献,当时希腊人、尤其雅典人享有这样一种荣誉。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哲学起源时提到了几个关键要素。根据他的说法,哲学首先根源于人的一种形而上学本能———“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世界是奇异的,人生是奇异的。人们是由于感到诧异,感到困惑,觉得自己无知才开始研究哲学。这是哲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其次,哲学根源于一种社会历史条件:“只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识。”因此,在一个大家为生计而奔波的时代和国度,人们是不会考虑哲学的。只有在文化(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和地方,才能产生哲学。这是哲学发生的外部条件。总之,“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求知是爱智的表现。只有获得闲暇的人们,才能发生哲学的兴趣。哲学,“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12],[13],[14]。概括地说,不务实际的纯粹理论兴趣、不事辛劳的闲暇生活时光,这是哲学和贵族文化发生的内在动因和外部条件。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三种主要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显然,沉思的生活就是他倡导的生活。
他区分了幸福和消遣,将幸福归结为沉思,认为幸福这种实现活动就是沉思。幸福在于沉思,亚里士多德倡导的沉思的生活就是哲学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德性的生活,也就是贵族的生活。换句话说,贵族文化、贵族精神就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德性的精神、哲学的精神。只有贵族文化才能实现哲学教育,只有哲学教育才能实现贵族文化,这是哲学教育与贵族文化的循环。古代希腊教育通常是指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代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体制代表了古代希腊教育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在某种意义上,斯巴达式的教育是极权主义教育的典范,儿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均由国家监管,尚武教育(军事、体育)是其主要特征。雅典式的教育是自由主义教育的典范,儿童教育是家庭的职责和家长的义务,除体育、军事外,广泛涉猎其他人文教育领域。斯巴达教育的理想化部分表现在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如儿童公有、教育公有等,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则反映了雅典教育的精神。雅典教育是名副其实的公民教育,只有在公民教育中,才有哲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古代希腊雅典的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上,智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当时在希腊、尤其在雅典,有一批专门收徒取酬、传授所谓政治技艺的职业教师,号称“智者”。在柏拉图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讲了一个神话,用这个神话来说明智者传授的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技艺的政治技艺,通过这种政治技艺人们获得廉耻和公正的美德,从而维系政治社会。
在这篇对话中,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虽不是知识但可教,苏格拉底认为美德虽是知识但不可教。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理解“知识”、“教”、“学”。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口说:“当他把知识交出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教’,而当别人从他那里得到知识时,我们称之为‘学’,当他把知识关在他的鸟笼中,在此意义拥有它们时,我们称之为‘知道’。”[9]732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借客人口极尽讽刺“智者”说,“智者的技艺是制造矛盾的技艺,来自一种不诚实的恣意的模仿,属于制造相似的东西那个种类,派生于制造形象的技艺”[7]82。由于智者末流流于诡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智者看成是歪曲真理、玩弄似是而非的智慧的人,亦即诡辩论者。这是希腊哲学传统称哲学为“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称哲学家为“爱智者”而不是“智者”的根据所在。#p#分页标题#e#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儿童教育问题。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学前教育体系的人。同样,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探讨了儿童教育问题,论述了从优生、节育到儿童教育,尤其论述了儿童教育的四门科目———读写(书算)、绘画、体操(体育)、音乐。应当注意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是服从于他们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的。柏拉图指出:“我们把人称作温和的动物,但实际上,若是拥有正确的天赋和教育,那么人确实比其他动物更像神,更温和,但若训练不足或缺乏训练,那么人会比大地上的任何东西更加野蛮。”[7]521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关于教育和培养公民的原则纲要”。柏拉图认为,除了体操(体育)和音乐之外,自由人还需要继续学习几门课程———算术(算学)、几何学(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直到辩证法。这些为后来形成所谓七艺(sevenliberalarts)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斯巴达的尚武教育,为雅典的人文教育作了辩护。因此,教育不应当是斯巴达式的片面教育,只顾身体、不顾心灵;而应当是雅典式的全面教育,兼顾身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讨论了哲学教育,他们一致认为,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最高形态。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阐明了哲学教育的主体———“哲学家的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8]233,[9]477,486。其次,柏拉图通过“太阳喻”和“洞穴喻”阐明了哲学教育的目的。所谓太阳喻,就是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认为太阳照亮了可见世界,而善(好)则照亮了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肖像和事物,与之相应的是意见,包括猜测和相信;可知世界包括数学对象和理念(相、型或式),与之相应的是知识,包括了解和理解。所谓洞穴喻,柏拉图认为,人们在洞穴中由于没有太阳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事物的影子,不能看见事物本身;同样,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没有善(好)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理念的影子———事物,不能看见理念本身。因此,哲学教育是传授最高形态的知识(理解),认识理念。再次,柏拉图通过回忆说阐明了哲学教育的方法。人们是怎样认识理念的呢?柏拉图认为认识就是灵魂的回忆,“学习就是回忆”[15]。
柏拉图将知识和意见对立起来,认为关于感觉世界的意见是经验的,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先验的,人们通过回忆获得知识。在柏拉图体系中,回忆说和灵魂不朽说、灵魂轮回说结合在一起。复次,柏拉图阐明了哲学教育的过程。柏拉图把算术(算学)、几何学(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当做类似于法律序言的学习的准备阶段,把辩证法当做类似于法律正文的哲学学习的阶段。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第一次运用“辩证法”这一概念,并将它提到哲学的高度,认为辩证法是最高级的知识,它不必凭借假设而可以认识理念和第一原则。柏拉图认为,“有无辩证法天赋的最主要的试金石”就是能在联系中看事物,“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就是一个辩证法者,不然就不是一个辩证法者”[8]305,[9]541。他认为,一个人必须经过长期准备,到了50岁可以学习辩证法。最后,柏拉图阐明了哲学教育的任务。柏拉图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称为四种美德。培养人的理智是哲学教育的任务。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初等教育的四门科目———读写(书算)、绘画、体操(体育)、音乐,没有来得及论述高等教育的科目。但是,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哲学教育体系。亚里士多德将理智德性区分为知识的部分和推理(考虑)的部分,知识的部分的目标在于真,推理(考虑)的部分的目标在于正确。获得真和正确的五种方式是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这里,除了科学、技艺之外,其他三种———明智、智慧、努斯都与哲学、哲学教育有关:明智属于实践智慧。“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努斯属于直觉智慧,同“始点”相关。“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4]173,175-176,[5]125,127这是理论智慧。明智(实践智慧)、努斯(直觉智慧)、智慧(理论智慧)构成了哲学的三个领域,而培养明智(实践智慧)、努斯(直觉智慧)、智慧(理论智慧)则构成了哲学教育的三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