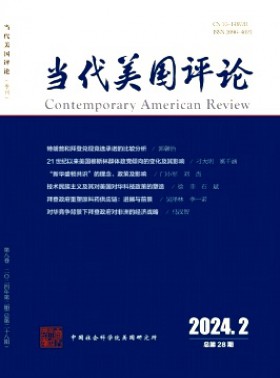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革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潘希武 单位: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小学教育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活动。它在公立学校内部尝试突破官僚制结构,实现多元中心治理,并采取凭单制形式在公立学校内外推进择校制,整顿“失败”学校,挽救“失败”的学生。这项改革至今仍在艰难中推进。对于这项改革,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进而研究中国自身的教育公共治理,但是我们还主要停留在或主要关注教育公共治理模式本身,即主要关注教育公共治理的结构本身,而忽略了其教育发展新阶段下的治理公共性结构与内涵的转型。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公共性衰退问题。现在看来,这不是一种衰退,而是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对教育公共治理的公共性内涵的一种扩大和提升。
一、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两个维度:多元中心治理和择校制
所谓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是相对于传统教育公共管理而言的,它包括两个维度:从治理结构上看,其主要改革框架是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突破教育官僚制结构,实现多元中心的治理;从机制上看,它在公共教育系统内注入市场因素,引入竞争机制,比如采取凭单制的形式为学生择校提供自由。教育官僚制包括学校内部官僚制与外部官僚制。学校内部官僚制虽然也侵入了学校日常教学生活,但学校教育还是在科学训练与艺术性之间求得相对自治的空间,因为学校毕竟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独有的专业领域。外部官僚制主要是指学校外部力量对学校治理形成的官僚制结构形态,它具有垄断性经营与生产的特点。教育外部官僚制结构的缺点在于,学校一旦“失败”,官僚系统内的治理力量很难实行自救;而且这样一种垄断性特点使得公立教育系统过于笨重,缺乏灵活性,不能回应学生的教育需求。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引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突破教育外部官僚制,改进教育的公共治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各自在公共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限度问题,实际上是个如何在相互合作与相互监督的关系中加强政府的主导、控制与监管的问题。特许学校就涉及到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生产者相互分离的问题,政府如何与学校经营者处理好关系是特许学校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此外,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兴建职业技术类或特色实用类的学校,关键也是要处理好各自的权限与职责,在此基础上谋求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
公共教育多元中心治理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性,它既可能导致公共性的衰退,也可能保障教育公共性。拥护与反对的声音都有。从公共行政理论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拓展“公共”和“治理”的内涵,认为“公共”不是政府的同义词,[1]它既不属于公共权力领域也不是市民社会领域,而属于一个超越私人领域之外的空间;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同时,学者们认为,公共行政的范式也需要转换。欧文•休斯认为,公共行政是与官僚范式、技术路线、服从、政治与行政二分、过程等范畴紧密相联,公共管理是与非正规组织、市场范式、技艺、责任、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结果等范畴紧密相联的。[3]治理理论想要突破的正是官僚制结构,寻求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治理主体不限于政府,还包括社会公共组织,市民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各组织形成相互协作机制,最终形成一个有别于官僚系统的自组织网络。教育公共治理也需要形成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种力量之间的合作治理,它强调的是三种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框架或模式。倡导者认为,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学校间竞争,可以改善效率;反对者认为,市场的力量会损害教育的公共性。后者包括,个人利益超越公共利益之上;[4]个体价值超越于教育的公共目的之上;[5]公共教育对培养公民精神与德性的公共责任的放弃;[6]强化种族分离。[7]同样,对于公立教育系统内部的凭单制式的择校改革也有不同的声音。倡导者的出发点是在公立学校之间实行竞争,可以提高学校质量,也为学生提供择校自由,特别是为那些“失败”的学生或得不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学生提供择校机会。反对者认为,自由择校的结果必然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利益受损:普遍的凭单制方案只会加剧美国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隐蔽与阻碍对平等的追求;[8]学校教育中的择校制,包括凭单制、特许学校和磁石学校使富裕的、白人家长和学生享有更大的特权。[9]显然,改革教育外部官僚制,并非是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完全推行多元中心治理。以查布(JohnChubb)和莫伊(TerryMoe)为代表的教育市场化改革倡导者认为,公共教育可以由政府供给,但不一定由政府生产;市场化的教育生产更能提高学校的学术成就。这样的说辞有它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如果市场化的教育生产完全被证明更能提高学校的学术成就,那么,多元中心治理就完全有理由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外全部推行,它就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事实上,教育多元中心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官僚制系统内的学校失败使得外部力量治理的尝试可以推行,所以它主要是充当传统公共教育的外围竞争物,改善了一些“失败”的学校,也满足了“失败”学生的教育选择需求。同样,择校也并非是完全的择校。个体择校虽然来自于个人自由的理念,但这样的改革首先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全面地推行凭单制必定因损害低收入者的教育公平而造成公共性的衰退,这是哲学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考虑。
二、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转型的可能:政治的考虑与家长的需求
教育公共治理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还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话语,[10]在实践上也还不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当教育公共治理成为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时,改革开始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教育公共治理成为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即“失败”的学生和学校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当然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通常认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与福利国家的失败有关。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势和新保守主义学说抬头的背景下进行的,或者说是在福利国家的失败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把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放到公共服务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总体上说是对的,但是,它与其他公共服务改革的原因与动机还是有重大差别,虽然采取的形式基本类同。通过比较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关涉到公共教育利益和个体教育利益。#p#分页标题#e#
公共服务改革主要是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的,着眼于缩减公共开支,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则不同。其一,国家希望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增强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以满足经济竞争的需要。1983年《国家在危机中》的报告把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归结为公立学校的平庸和失败,一些公司也把注意力引向学校失败和经济衰退。于是,教育市场化取得了政治因素的支持。其二,个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财富的向上转移,大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的大量解雇,信贷市场化加深出现了大量的个人债务,制造业转向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急剧萎缩。身份危机中的中产阶级放弃了对教育公平政策的支持,优质的公共教育成为首要资源。[11]一般公共服务的改革主要着眼于缩减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的“善治”。教育服务改革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被期望是国家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手段,同时也与个体的教育需求密切相关,不过这种需求并非完全基于学业考虑。作为教育市场化的主要形式———公共投资凭单制,最初目标是瞄准低收入者,特别是黑人低收入者,其后扩展到在公立学校失败的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最后扩展为所有家长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凭单计划。从凭单制的参与学校来说,起初是在公立学校内进行,其后扩展到私营学校,后甚至扩展到宗教学校。凭单制的推行从所有人到所有学校,表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考虑外,即实现教育的公共性,解决教育公平,提升劳动力的经济竞争力,它还表明教育服务改革与个体的教育需求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择校制,尤其是跨学区的择校,对学校管理者并没有产生预定的影响,即学校教育模式并没有产生改变,学校的行为表现也没有得到改进,[12]对部分学校而言倒是减少了问题学生,降低了入学率。择校制的存在与家长的需求密切相关,然而,家长的择校需求并非完全基于学生的学业失败,学校的安全和种族歧视问题对家长的择校有很重要的影响。拉波斯基(ThomasRabovsky)认为,家长的择校在低年级阶段主要基于学校的安全与种族歧视的考虑,而在高年级阶段才是基于学生学业失败的考虑。[13]所以,就择校制而言,政治的考虑与学校和家长的考虑是不相吻合的:政治上的考虑是基于学校与学生“失败”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但学校没有改进教育效率的愿望,家长则是基于学校安全、种族因素与学业因素的多种考虑。应当说,政治的考虑与家长的需求共同推进了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的转型。
三、在教育均衡政策与官僚制失败下的个体择校需求应对中实现公共性的转型
教育外部官僚制比较好地保障了教育公共性,较好地实现了教育公平,但是公平永远是动态的。教育外部官僚制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存在学校教育的失败问题,其自身系统内难以迅速调整,缺乏回应性和灵活性。其在系统内的可能解救办法就是寻求外部力量,改革教育官僚制型态,实现多元中心治理。同样,公共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教育均衡和相对优质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按学区就近入学政策如何应对学生“失败”就成为一个问题。可能的解救办法是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外推行择校制。这两个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问题,即教育官僚制系统如何应对学校“失败”与学生“失败”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政治性使美国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使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教育市场化或私营化会冲击政府垄断性生产教育下的公共性问题,因为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在形式上是中性的,而教育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也是中性的,缺乏对“公共性”的价值追求。因此,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在教育的政治性与哲学性之间存在冲突。公共教育关切公共利益,而教育哲学则关切个体幸福。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要保卫公共性,但同时也需要避免呆板的教育均衡政策与公共性对个体教育需求的忽略。均衡化的教育政策与“失败”学生的择校需求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这就是美国教育公共治理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境遇。这种境遇实际上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体现。
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始终跟随着现代性自身。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议,除了各持自身的理论观点之外,至今没有也不会有同一化。现代政治哲学就是这样,“诸善共舞”,既要公平,又要自由。但正如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ille)的深刻洞察,自由与平等往往是矛盾的。事实上,集体与个体的矛盾问题在卢梭那里就有了最为深刻的探讨。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是最为自由的,而人的社会化因为使人活在他人的认同中,从而使人失去了内心的快乐和真正的自由。当然,卢梭知道,人是无法逃避政治社会的,也不可能重返自然状态;卢梭的政治哲学也不是主张回到自然状态,而是要为政治社会的联结的正当性找到合适的方式,[14]为在人道的范围内朝向自然状态寻求最大可能性。对择校制的探索实际上在一个层面上保持了这种卢梭式的追问。
从终极上看,教育公共性与择校自由之间一定是矛盾的。作为问题的实际解决,教育政策必定是调和的产物,必定是在两种政治哲学———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和以家庭选择为中心———之内寻求平衡。有些学者试图调和这种冲突,[15]还有一些学者,如帕奎特(Paquette.Jerry)、[16]库克森(Cookson.Peter)、[17]库恩斯(Coons.JohnE)[18]等从治理结构上对择校制、凭单制、特许学校等提出了很多改进策略。比如,帕奎特主张在某些领域实施政府管制,为公立学校择校制提供平等框架;库恩斯主张实行有目标的凭单制(针对穷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与普遍的凭单制。这些策略都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治理结构以解决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解决公共教育系统的低效率状况,既想保持学校教育的公共性功能,又想有限地满足个体的择校自由。教育公共治理正是在这种价值冲突中、哲学的追问中实现了公共性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仅表现为治理结构上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公共性内涵的转型:既持守教育均衡,又尝试满足个体择校自由。在转型中对教育公共性丧失的担忧是对的。但是,从终极上看,多元中心治理与有限的择校是方向性的策略是必然的趋势,这是由教育官僚制的缺点所限定的。只要操作方法得当,它不但不是教育公共性的衰退或丧失,反而是教育公共性的提升。当然,多元中心治理与择校,只可能是某种限度内的突破,或者说它是教育官僚制的外围存在物,旨在给传统的教育官僚制解放出某些活力,弥补均衡教育政策下的对个体教育需求的反应迟钝。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想突破教育官僚制系统,也不会以个体的教育需求作为最高的指向。它的基本的政治逻辑是,始终要体现教育的公共性。作为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政策成果,特许学校通过实现多元中心治理,为学校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外部力量的保障,弥补了教育官僚制的缺陷,既保卫了教育公共性,又在均衡教育政策下通过择校制回应了个体教育需求。它是对教育公共性内涵的重要拓展和提升。这种内涵的拓展与提升,可以解除我们对义务教育治理与政策的保守的认识:即认为教育的公共性意味着教育的政府生产与治理,意味着统一的就近入学。#p#分页标题#e#
四、对中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反思
中国当下的教育公共管理改革(指义务教育阶段,下同)并不处在美国教育改革的阶段,因此,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对中国有多大的借鉴意义是值得反思的。多元中心治理与有限的择校制对中国并没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可能的借鉴在于,实行多元评价,推进教育评价机制改革。当下中国的教育官僚制系统存在的问题与美国教育官僚制的问题并没有相似性,我们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灵活性和回应性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教育官僚制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表现为教育质量普遍还不高、教育还不够均衡,自身该承担的职责还没有履行好。我们现在还不是引入外部力量实现多元治理的问题,外部力量无法改变教育官僚制普遍的效率不高(教育质量不高和不均)的问题;也不是推行择校制的问题,相反还需要杜绝择校制,因为教育不均衡的条件下更应禁止择校。
中国与美国的教育官僚制系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义务教育的政府统一提供与生产;而差别主要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教育行政与专业发展的关系。教育教学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艺术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有自身相对自治的空间。美国虽然也有官僚制侵入日常教学领域的问题,但总体上对于行政与教学有一套区分的系统。教育官僚制有自身的优势,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生产、强有力的教育质量监管,但统一指挥是指教育理念、教育大纲、教育监管的统一,而不是教育公共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的质量改进与均衡发展有赖于教育官僚制系统自身的改革,而不是靠引进外部力量。美国教育的多元中心治理,改变的是教育生产的主体结构,而不是改变教育模式;中国教育最需要改变的是教育模式,而不是谁来治理的问题。多元中心治理对我们当前教育问题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