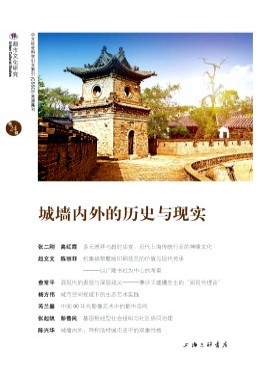摘要: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对文化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时,总难绕过英国文学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学术遗产。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学院体制赢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则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专著《识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当时,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太过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无法关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命运。他希望发起改革,使现实社会中那些对普通民众影响甚大的文化能够进入正式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体制。《识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广播、电视及广告等“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文化与道德践踏。霍家特的文学革新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运动,即由解读莎士比亚小说一类的“经典文化”,转向考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当代文化”。电视、流行音乐、电影等社会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长期远离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文学研究与教学随之得以和当代社会变迁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走势形成紧密联系。关于这一点,曾协助霍家特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S.Hall)早已做过梳理,[7]无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创建文化研究时的城市语境、“城市教育”关切与“城市教育学”贡献。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开始便将语境定在了伦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会把自己发现的“大众文化”又称作“大众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实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城市教育”关切,提请“大众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义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乐”、“消费”,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们兜售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就是将他们隔离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当企鹅出版社因发行大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控“有伤风化”时,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声辩,也是为了反抗精英势力认为该书只能让所谓“有教养的阶层”阅读,工人阶级等普通市民没有道德辨识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触。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关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样,他的出庭作证也是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势力划为没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总之,虽然霍家特从未以“城市教育学”之名来统领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实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阶级遭遇的文化教育难局,从而为后人发展“城市教育学”提供了一大经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主题涉及精英阶层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视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生产商又以何种不义甚至低劣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向他们提供堕落的“大众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并为他们生产“健康的大众文化”。[10]无疑,霍家特通过研究当代都市社会中新兴的“大众文化”来彰显自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关切,正符合前文所说的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本文即因此认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仅贡献了一种“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更为发展“城市教育学”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进路。这样说,是为了丰富“城市教育学”的既有路径。进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径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难题,霍家特的现实主义路径显然能将“城市教育学”引向具体的城市社会,都市众生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与教育难题随之亦能得到生动呈现。
三、一项实验:杨德昌“新电影”与都市人生教育学
当下中国都市同样充斥着“大众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学”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样借助文化研究,描绘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包围,以至难有时间和空间接触有利于工人子弟实现社会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让本土“城市教育学”变成仅是为验证霍家特的理论提供中国案例。由此出发,本文决定以杨德昌(1947-2007)的“新电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项文化研究实验,寻觅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议题。电影也在霍家特的视域之内,但他当初仅看到好莱坞商业电影,未曾考察当时法国文化界正兴起“新电影”运动。[11]“新电影”不是为了将观众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而是表达新一代艺术家对于西方社会人生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新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杨德昌正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核心发起人。只要将杨德昌电影列为研究对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很适合用来建构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学”。杨德昌1965年在台湾读大学时喜欢上了电影。1974年,在佛罗里达大学拿到工程硕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学学电影,但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12]之后杨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决定“改变人生,做真正喜欢的事,拍电影”,[13]于是返回台湾,与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当时业界流行的乃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片,[14]这群年轻人则立志拍不一样的电影。如侯孝贤所言,1982年是“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年代”,[15]“其标志是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杨德昌在其中执导《指望》”。[16]之后,从1983年推出《海滩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共留下7部“新电影”。这些作品曾赢得50余项电影节奖,《一一》更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杨德昌因此被国际电影界誉为“大师”。[17]至于杨德昌电影蕴含什么大师级的思想或理论,焦雄屏、黄建业、米歇尔•付东等电影及人文学界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权威已做过诸多揭示。[18]然而由于专业限制,无论国际电影业界,还是国内外电影及人文学界,探讨杨德昌电影的艺术、哲学及社会学内涵时,均忽视了杨德昌的教育热情与忧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当作缺点加以批评,声称真正的艺术不该为说教。只看到有观众曾替杨德昌的“说教倾向”做辩护,认为杨德昌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他是“一个热忱的传教士”。[19]杨德昌的确是电影界难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的教育热情与忧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台北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实感人的“新电影”叙事表达出来的“都市人生教育学”。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杨德昌是从都市女生入手展开他的台北观察与教育思考,他发现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独立要强,学业、家事均能对付,但在初潮、情窦初开等重要成长时刻,总是陷入孤独与无助。是为杨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论文。到1983年推出独立执导的《海滩的一天》,女生已长大,变成可以在台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来往的女白领。杨德昌的思考随之也有变化,他开始更关注台北社会的复杂变迁,以便弄清女白领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种人生。结果在传统体制瓦解、资本投机风行等变迁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领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与爱情到头来均变得面目残非,仅在经济层面尚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黄建业等曾言,《海滩的一天》蕴含“台湾传统电影中未出现过的女性处境论述”,并为认识、超越此处境“提供了一个反省机会与一项参考:那就是在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与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这些解读堪称准确,但《海滩的一天》绝不只是为了展示导演的都市社会学和生命哲学发现。杨德昌考察都市白领的现实处境,特意以人物对话与回忆引导观众反省自我人生,均是为了教育都市众生:先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变迁,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滩的一天》其实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学”实验。只是这次以社会学观察为主的教育实验虽能启示人们从社会转型入手认识人生,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及1991年的史诗大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表明:杨德昌越是了解台北女白领、中学生和市井百姓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越是难以向芸芸众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杨德昌因此变得既忧伤,又愤怒。而在“新儒家”推动下,当时海内外学术界恰好兴起一股理论热潮,认为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有“儒家伦理”暗中起支撑作用,仿佛商场各路人马都是孔子式的谦谦君子。这更让杨德昌感到忧伤与愤怒。1994年,杨德昌以一部新作《独立时代》对骤起的“新儒家”经济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彻底不顾“艺术不涉及说教”的陈腐教条,史无前例地在片头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着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句话:“两千多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之一”。杨德昌故意隐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换上后面那句反映台北现实的话,以及特意将影片英文名定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这些显然意在提醒人们,如果将孔子请来,一定能发现,台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举的“伦理教条”富裕起来的,富裕的台北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教育。那台北社会有什么呢?杨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领女性,即琪琪、小凤等。她们时尚漂亮,特立独行,在台北商场展开各自人生。但这个暴富的商业社会并没有那种可以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及人际关系维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样难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围人恶评为“装的比真的还像”。结果大家除了像小凤那样不顾一切地赚钱外,便不知道能从都市社会中得到什么。总之,在富裕的台北社会暗中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儒家伦理”,而是疯狂追求经济成功及顺带而起的分裂与竞争。1996年,杨德昌推出了《麻将》。这一次,导演对于台北都市社会又有新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台北成为恐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汇集地。如那些来台北淘金、有钱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国人,其中一个还想将台北作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辉煌统治”。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原本紧张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追求成功。连初涉商场的青少年都信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动感情”,变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还要疯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说:“《麻将》是一部高潮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21]的确如此,只是评论者未曾留意《麻将》其实是在延续《独立时代》的教育忧思,即富裕的台北社会急需一种可以将都市众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从《独立时代》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认为,要想解决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让学生、白领等都市众生获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会的道德危机。可多年探索下来,又找不到那种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实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会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为找不到解答,杨德昌其实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杨德昌仍拍出了《一一》。还有什么都市教育议题值得他以这部电影来展开探讨?得益于转换议题,他终于还能继续进行都市教育实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而是思考如何安顿都市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存在,使都市个体获得美好人生体验。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难题入手,杨德昌将台北中产阶级个体NJ作为观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经济合伙人等都市个体的生命存在事实:众多都市个体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离、压抑、孤独、失意等无人察觉的苦楚心相。连尚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没一个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长连他们是怎么上学的都无暇顾及,老师们也仅在意他们上课是否认真听讲。只是面对众多都市个体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杨德昌虽可以慈悲地将它们一一揭示,却只能为NJ提供一种教育解答,认为像NJ这样的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即使因为责任满身注定疲惫奔波一生,也还是能通过古典音乐获得安顿和美好人生体验。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学校以缓解NJ一双儿女的内心孤独,怎样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产阶级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难题,《一一》均没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终究贡献了一种旨在理解、超越都市个体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学”。
四、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学因此必须研究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难题。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正是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样把城市建设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将“城市人”培养成“现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难题。但这些城市教育追问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构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教育难题。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教育学”既有的议题建构方式,开拓“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从而使“城市教育学”的理论生产真正能够揭示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难题。如本文所述,在创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电视、电影等当代都市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霍家特之所以创立文化研究,则是为了揭示“大众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之后,会使都市工人阶级陷入什么样的文化教育难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实是一种旨在认识、改善当代都市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环境的“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生产商以低劣乃至不义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都市民众,将他们推入“堕落”的“大众文化”世界,把他们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正是当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但却被学界忽视的一大教育难题。可以说,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将发展某种和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教育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教育学”。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学”贡献外,本文还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做了一项文化研究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即电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说的意图低劣的“大众文化”),而且能发展出某种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阴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一直都在以“新电影”的深刻观察与生动叙事来揭示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个体等都市众生在台北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难题,诸如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富裕台北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使生于其中的学生、女白领等都市众生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如何安顿自身诸多无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体验。就像许多人不同意伽达默尔的美学教育结论,即艺术可以拯救当代西方意义迷失的“生活世界”,[22]杨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种能够净化整个都市社会人心的教育力量,不过都市个体最终可以依靠古典音乐获得生命安顿——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太过悲观,或不符合多数都市众生的美学口味。杨德昌是不该对学校、公司等都市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乐列为“福音”,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杨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观察都市众生日常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本文即因此认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文化研究路径乃是以杨德昌“新电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像杨德昌那样真正深入台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最后想起,罗蒂曾呼吁学术界“抛弃理论,转向叙事”,理由是数学式的抽象理论无法认识人类的苦难处境,“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才能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23]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对数学式的抽象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抹杀抽象理论本身的知识与教育价值。不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的确很适合用来详细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就像杨德昌,他其实很喜欢做抽象的理论思考,甚至如吴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写“论文”,[2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以电影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都市社会观察与人生教育思考。以此为参照,本土“城市教育学”如果想深度呈现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等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也需尝试更有效的叙事方式。何况如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叙事其实还是中国教育最初首选的理论及实践表达方式。
作者:周勇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风笑天.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J].教育研究.2005,(10):28-34;郑金洲.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病理现象[J].教育发展研究,2006,(4):12-19.
[2]文娟,李政涛.从“教育城市”到“城市教育学”[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30-137.
[3]孙丽丽.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教育价值探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38-143.
[4]吴研因.序[C]//孙逸园.都市教育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
[5]孙逸园.自序[C]//孙逸园.都市教育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3.
[12]王昀燕.再见杨德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55.
[14]林青霞.窗里窗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3.
[15]侯孝贤.另一种视角[A]//付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6-177.
[16]米歇尔•付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
[17]安德森.杨德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3.
[18]焦雄屏.台湾新电影[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8/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付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9]无心.杨德昌以及《一一》[EB/OL].
[20]黄建业等.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M].台北:耀升文化有限公司,2007:.40-46.
[21]林文淇.麻将:杨德昌的不忍与天真[EB/OL].
[22]德维尔诺.艺术能拯救我们吗——关于伽达默尔的沉思[J].国外社会科学.1992,(1):29.
[23]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24]吴念真.他在写论文,而非描述[A].王昀燕.再见杨德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0.
[25]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97.